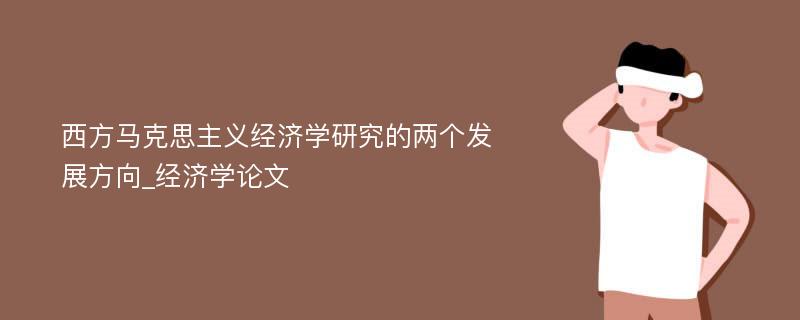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两种发展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发展方向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506(2006)02-0009-05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这种研究大多集中在哲学、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方面。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了,但国内学术界明显对此重视不够,这种局面不利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本文对20世纪末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两种融合方向进行探讨,以期对国内此方面的研究有所启迪。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概况和主要特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大致是指由英美等西方各国的经济学家所开展的,自称把其方法论和研究建立在卡尔·马克思理论基础上的那些研究成果。它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范围上有重叠的地方,但又不完全一致。这里的“西方”也主要是一个政治经济概念,而不是地理上的概念。这些研究者在政治上可能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展开科学研究。
19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心由德国、俄国和东欧转向了西欧和北美,由此开始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感兴趣的著名经济学家有里昂惕夫、琼·罗宾逊等,但真正展开研究的则有保罗·斯威齐、罗纳·米克等人。1970年代,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普遍出现“滞胀”以后,西方学者掀起了一股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浪潮,这个复兴的迹象表现在:主题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书籍和论著的大量出版,大学里课程和学术讲座数量的增加,传媒中论坛数量的增长等等,这股热潮一直持续到新世纪之初[1]。西方学者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一方面是由于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一些重大的社会经济事件,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具有的生命力和持久魅力所致。
与流行于前苏东国家的“官方马克思主义”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多是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出身,了解和掌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重视实证研究。他们十分厌恶那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官方学者”仅仅满足于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只言片语来解释一切经济问题的做法,天生就反对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范本笼罩下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经院哲学。因此,他们的研究既不同于“官方马克思主义”,又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贯的蔑视、排挤和打压。其研究特点可以概括为:一方面号召“回到马克思”,通过直接阅读《资本论》等经典文献来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另一方面又不拘泥于条条框框,不是谋求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狭窄的圈子里发展,而是广泛吸收西方经济学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力求实现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突破。大量使用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念、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融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最显著的特点,也正是这种特立独行的风格使他们在学术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虽然早在1942年以琼·罗宾逊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版为代表,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就开始被西方学者纳入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中去。但是,直到冷战结束前夕,这种趋势才演变为一股清晰可辨的潮流。1970年代末,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支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加强了与老制度主义的沟通,创建了激进制度主义这一新流派。80年代,约翰·罗默、乔恩·埃尔斯特等人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中的均衡概念和博弈论、数学形式化等分析工具和技巧用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从而诞生了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90年代,除了与老制度主义的联系和融合进一步加深外,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开始与生态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等异端经济学的新兴流派展开对话,诞生了诸如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性马克思主义等流派。进入新世纪,随着被称为“21世纪经济学”的演化经济学在西方的崛起和不断壮大,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开始出现新的转向。
在笔者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融合方向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承认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正确性,试图通过使用博弈论、数学形式化建模等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来改造马克思经济学,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古典化,这种方向以分析马克思主义为代表;另一种则是在继承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批判的同时,加强了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异端经济学诸流派的联系和对话,力图将老制度主义等异端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结合起来,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激进制度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性马克思主义、演化经济学的综合等都可以看作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融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古典化
这种方向以分析马克思主义为代表。分析马克思主义也被称为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兴起于上世纪70、80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反映了西方学者的一种研究思路。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在价值取向方面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同时又都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信徒。他们认为,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其基本理论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标准来看,它显得很粗糙,至少存在三个问题[2]:一是概念不清晰,论证不严谨;二是对社会历史问题只有宏观论述而缺少微观分析;三是它的一些理论或者已经过时或者是错误的。他们坚决反对自普列汉诺夫以来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一致认同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在方法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相反,他们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的理论就必须运用分析的方法对其进行重构、修正和补充。他们所说的分析的方法,主要是指以流行于英语国家的实证主义哲学为基础、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本教义、以数学形式化分析为特征的一种思维和研究方法,大量使用博弈论等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牛津大学的柯亨(G.A.Cohen)、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约翰·罗默(John E.Romer)、芝加哥大学的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和威斯康星大学的赖特(Erik Olin Wright)。
柯亨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1978)一书中,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解释进行了辩护。在该书中,作者坚持马克思关于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两种区分,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进行了功能性解释,并对历史唯物主义一些基本原理做出了与众不同的说明,比如从人具有理性和自然环境不能满足人的需要出发说明生产力在社会历史中的决定作用等。埃尔斯特的工作范围仅限于方法论层面,他特别赞赏理性选择方法的使用和博弈论的应用,在《理解马克思》一书中,他对马克思的几乎所有论点都作了批判性分析,并力图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修正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
作为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罗默认为,要解决很多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体系和数学形式化建模方法不仅是适当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在其早期著作《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1981)中,罗默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采用了高度数学化的重建,尤其是讨论了阶级与技术之间的关系。然而,罗默最富争议也是反映了分析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最具突破性的和最有创造力的成就之一的就是《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1982)[3]。该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受主流经济学寻找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的影响,罗默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等宏观社会现象的描述建立在个人微观动机的基础上,在严格遵循了主流经济学使用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的前提下提出了整个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课题;第二,罗默使用了主流经济学认可的一般均衡模型和博弈论方法,从个体效用函数最大化出发,在对剥削和阶级身份进行独立定义的前提下,经过严格推导,提出了阶级——剥削一致原理。这样,罗默就提出了非劳动价值论的剥削概念:剥削归因于个人的不同禀赋以及他们的不同偏好。由此,阶级和剥削理论就从劳动价值理论中解放出来,马克思的剥削和阶级概念就可以被解释为源于标准的新古典经济模型,而且,劳动过程也不再被看作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工人和资本家签订工资合同,劳动是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出现的。
分析马克思主义引起了英美学术界高度重视,并使英美这两个多年压制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第一次出现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然而,理论界对它的评价却褒贬不一。一些学者认为,分析学派创造性地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题,可以更加科学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助于改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国家受迫害的不利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未来的发展方向。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分析学派言过其实、似是而非,尤其是方法论上个人主义等主流经济学理念与马克思经济学的“社会化个人”思想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这种道路可能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曲解,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本质的东西被稀释、淡化甚至抛弃,不应当提倡。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异端经济学的融合: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属于异端学派[4],自诞生之日起就被主流学派所敌视,这种情形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同时,长期以来,由于马克思本人的一些论述,以及官方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性解释,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异端经济学是无法沟通的。然而,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世纪之交的工作改变了这种传统看法。
拉威[5](1992)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老制度主义、后凯恩斯经济学和女性主义经济学等异端流派的关系,认为它们除了对主流经济学持共同的否定态度外,还存在如下共性:(1)强调阶级(或阶层)分析;(2)重视财富的生产而不是存量资源的配置;(3)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容易爆发危机,再生产出不平等,带来贫困、异化和不平衡的发展;(4)这些流派都为妇女、少数民族和穷人权利辩护,主张政府保持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的干预,以此作为潜在平台来形成对抗资本的大众压力;(5)在方法论上,也大都认同广义上的实在论、有机整体论和过程理性。奥哈诺[6](1999)认为,马克思与凡勃伦之间具有充分的连续性,这足以用来支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老制度主义经济学之间建立某种基础意义上的融合。此外,缪尔达尔、格鲁奇等人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目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加强了与这些流派的联系,相互参加彼此发起的学术会议,在由其它流派主办的杂志上发表论文,担任由其他流派主办杂志的编辑等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保罗·斯威齐、霍华德·谢尔曼也分别是1999年和2005年演化经济学协会颁发的凡勃伦——康芒斯奖的获得者。这种融合不仅大大开阔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启发了智慧,而且由此诞生了一些新的学术流派,如以下的几种。
激进制度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老制度主义两大流派杂交的产物。它继承了老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许多原理和有机整体论方法,强调演化并把权力和文化纳入到分析中来,同时又抛弃了传统的老制度主义者对马克思的阶级、异化分析的轻视,吸收了马克思的社会化个人的思想和激进阶级分析。代表人物有比尔·杜格(Bill Dugger)、罗恩·斯坦菲尔德(Ron Stanfield)、里克·惕尔曼(Rick Tilman)等。1980年代以来,激进制度主义者对大公司和文化霸权、阶级异化等进行了彻底批判,主张在企业中实行工人分享的民主和自我管理,在美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调节学派[7] 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异端经济学思想杂交的产物。法国的一些经济学家通过对马克思、凯恩斯和卡尔多经济理论的独特理解,并从布罗代尔等人的法国年鉴学派和波拉尼、熊彼特的理论中汲取灵感,发展了一种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演化的“调节”方法,从而把制度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结合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调节学派最著名的工作就是运用其框架对美欧资本主义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进行了分析,目前它的思想和方法已经被吸收到经济地理学、社会学、国际政治经济学、转型经济理论、发展中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研究之中,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经济学流派。
此外,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在20世纪末的快速发展使原本就存在的全球生态危机进一步加剧,美国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生态经济学结合起来,提出生态马克思主义概念;女权运动在西方各国的蓬勃发展最终攻破了主流经济学的堡垒,创立了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经济学,这一崭新的流派迅速吸引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注意,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女性主义经济学联系起来,创建了女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异端经济学的融合使学者们最终提出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这一崭新课题。演化经济学的兴起是20世纪末国际学术界的主要事件之一,作为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它有可能成为替代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主导范式,被称为“21世纪的经济学”,目前也逐步成为我国经济学界新的学术研究热点。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外学者逐步认识到演化经济学的创新和创造性综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例如英国学者霍奇逊就指出,马克思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师,他的经济学有时也被认为具有“演化的”性质;C·弗里曼和F·卢桑把马克思看作是演化经济学的前驱之一。我国学者也已经认识到这一重大课题,并开始做出自己的贡献。例如,贾根良教授强调了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尤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指导;孟捷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译丛》总序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硬核”即历史唯物主义,及马克思对其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和演化经济学所强调接纳新事象这个本体论的标准并不是相互排斥;未来的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某种创造性的综合。
四、评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两种融合方向实际上与马克思的经济学本身具有的两重性有关。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表明,经济学研究具有两大传统[8],它们可以分别称为“牛顿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和“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一方面,由于时代的限制,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不可避免地带有牛顿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某些特征,例如理性人假定、均衡思想等等,这正是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指出,《资本论》中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解释就是一个通过个人理性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导致整体状况变差的经典例子;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价值规律”中也有很深的物理学上的均衡的影子等等。另一方面,马克思的经济学在整体上又属于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这表现在他的利益关系和有机整体论的分析方法以及他对技术和经济动态的强调等等。尤其是,近年来被称为科学哲学的“哥白尼革命”的批判实在论的兴起和发展,更是加强了马克思作为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重要来源的地位。目前,批判实在论已经成为西方异端经济学众多流派共同的哲学基础,而马克思被称为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的先驱,关于这方面的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正在进行。因此,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根本上的对立和差异,笔者相信,与西方异端经济学的融合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所在。
近年来,国内经济学界围绕中国经济学是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全盘接受西方主流经济学而展开论战。笔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启发。
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繁荣发展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科学,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启发力,这是吸引众多接受过主流经济学熏陶和灌输的西方学者克服阻挠,转而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原因。众所周知,在主流经济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西方各国,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不仅无法获得主流学术界的认可,还要冒相当大的政治风险。他们中的许多佼佼者如斯威奇等人娴熟地掌握了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技巧,然而正是由于深谙主流经济学的弊端和非科学性,在探索真理的强烈使命感的驱使下,他们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将其作为终身事业。
其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决不能固步自封,而是要与时俱进,大胆创新。创新意味着要广泛吸收和借鉴已有的理论成果,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是在吸收和借鉴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得到不断发展的。
再次,中国经济学在理论创造中应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广泛吸收西方异端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并有选择地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某些内容(尽管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不科学的),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唯有如此,中国经济学才能获得健康发展,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标签:经济学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