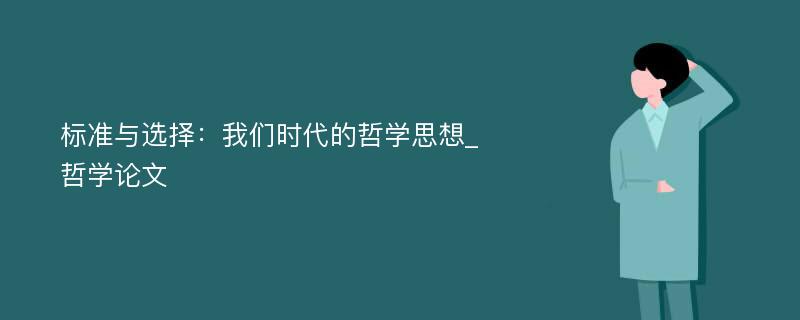
标准与选择:我们时代的哲学理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理念论文,标准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15)06-0001-05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不仅反映和表达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而且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正因如此,马克思不仅把哲学称之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而且称之为“文明的活的灵魂”。 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每个时代的哲学都有其表征自己的时代精神并塑造新的时代精神的根本性的哲学理念。这种根本性的哲学理念,集中地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向。一套著名的哲学丛书,曾对不同时代的哲学理念做出这样的概括:中世纪——信仰的时代;文艺复兴——冒险的时代;17世纪——理性的时代;18世纪——启蒙的时代;19世纪——思想体系的时代;20世纪——分析的时代。 对于这种概括,人们可能会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质疑;然而,认真思考这些概括,会使我们形成对这些时代的时代精神的鲜明而深刻的总体性的理解和把握。通过这种总体性的理解和把握,不仅会使我们深刻地理解人类的文明史,而且会使我们深刻地思考人类文明的现在与未来。因此,在当代的哲学研究中,我们不能不持之以恒地向自己提出一个根本性的追问:我们时代的根本性的哲学理念是什么?它如何表征自己的时代精神并塑造新的时代精神? 在把“哲学”称作“时代精神的精华”时,我们还把文学称作“时代的敏感的神经”。一位当代中国的著名作家曾经发过这样的感叹: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不缺少“故事”,缺少的是“哲学”。有“故事”而无“哲学”,这意味着讲述“社会”“历史”和“人生”的当代文学,却对“社会”“历史”和“人生”充满着困惑和迷惘,既不清楚我们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时代精神,更不清楚我们要塑造怎样的新的时代精神。例如,许多评论家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的小说定位为“魔幻现实主义”,这似乎是具有标识性地向人们透露了一个令人困惑的信息:我们的时代精神不是“现实主义”,也不是“理想主义”,而是一种“魔幻”的现实主义——哲学家所说的“存在主义的焦虑”或“无底棋盘上的游戏”。如果对比一下《生死疲劳》中的变为猪、狗、牛、驴的主人公西门闹和《红楼梦》中的“顽石”与主人公贾宝玉、《水浒传》中的“天罡地煞”与主要人物一百单八将,再进一步对比这三个“故事”所蕴含的“哲学”,我们也许会更为痛切地体悟有“故事”而无“哲学”究竟意味着什么,从而更为深切地提出这个追问:我们时代的根本性的哲学理念是什么?它如何表征自己的时代精神并塑造新的时代精神?我们如何在自己时代的哲学理念中“保持清醒的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 时代性的哲学理念集中地体现了时代性的哲学使命。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对时代的变革与哲学的使命做出这样的论述:“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马克思的论述明确地指出,近代以来的哲学是“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异化给“神圣形象”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人;现代哲学的使命则是“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异化给“非神圣形象”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人。马克思的概括,不仅从人的历史形态提出哲学的历史任务,而且从哲学的历史任务揭示人的历史形态的文化内涵,从而不仅反映和表达了不同时代的时代精神,而且塑造和引导了新的时代精神。 近代以来的文明史,从经济形态上说,是以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过程;从人的存在形态上说,是从人对人的“依附性”转化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过程;而从文化形态上说,则是从“神学文化”转化为“后神学文化”的过程。人类存在的历史性飞跃,以及由此形成的时代精神的飞跃,以理论的形态而构成哲学理念的飞跃,这就是从中世纪的“信仰的时代”的哲学跃迁为近代的“理性的时代”的哲学。 作为“信仰的时代”的中世纪哲学,它理论地表征着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人把自己的本质异化给作为“神圣形象”的“上帝”,“上帝”就成为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圣形象”,而人本身则成了依附于“上帝”的存在。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近代哲学,它的根本使命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由此便构成了贯穿整个西方近代哲学的“上帝”的自然化、物质化、精神化和人本化的过程。这就是以“理性”代替“上帝”的过程,也就是用“理性”这个“非神圣形象”去代替“上帝”这个“神圣形象”的过程。这种“代替”,集中地显示了以“理性的时代”为标志的近代哲学的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近代哲学实现了以“理性”消解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人的本质“归还”给了人的“理性”;另一方面,近代哲学又使人在“理性”中造成了新的“自我异化”,即以“理性”构成了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理性”变成了凌驾于人之上的“本质主义的肆虐”。马克思说,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人类“最现实”的生存状况——“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相互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2]。这深切地表明,把人的本质“归还”给“理性”的近代哲学,其实质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了正在受“抽象”统治的近代以来的人类生存状况,也就是人的“独立性”建立在对“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之上的生存状况。因此,现代哲学的历史任务是“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即把异化给“理性”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作为个体的个人。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把整个近代哲学所表征的时代精神称之为“理性的时代”,那么可以把超越近代哲学的现代哲学概括为“理性的批判”,并进而把现代哲学所表征的时代精神称之为“反省理性的时代”。 同整个现代哲学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任务,同样是“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但是,马克思认为,现代哲学所要“揭露”的“非神圣形象”,并非仅仅是抽象的“理性”,更为根本的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因此,马克思要求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把“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并由此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的“实践转向”。以“实践转向”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像科学主义思潮那样,仅仅把近代哲学所弘扬的理性视为“狂妄的理性”,也不是像人本主义思潮那样仅仅把近代哲学所弘扬的理性视为“冷酷的理性”,而是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揭示人与世界之间的无限丰富的矛盾关系,用“现实的理性”去批判“抽象的理性”,从而达到对人与世界之间的否定性统一的辩证理解。以“实践转向”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人对世界的实践关系出发,不是把哲学视为凌驾于科学之上的“解释世界”的“普遍理性”,而是把哲学视为“改变世界”的“世界观”,即从总体上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因此,从根本上“消解”了人在以“哲学”为化身的“普遍理性”中的“自我异化”,并把新的时代精神定位为人类以自身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所实现的人类自身的解放。 由近代哲学对“神圣形象”的批判而发展为现代哲学对“非神圣形象”的批判,这理论地表征着人类存在的历史形态的变革。在“人的依赖关系”的历史形态中,个人依附于群体,只不过是“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因而造成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与人的这种存在形态相适应的哲学,只能是确立“神圣形象”的哲学,即作为“神学文化”的哲学。为了挣脱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人从“依附性”的存在中解放出来,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近代哲学的历史任务就是“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但是,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形态中,虽然个人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而获得了“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却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在对“物的依赖性”中“再度丧失了自己”,这就是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马克思在对“非神圣形象”的揭露和批判中,明确地承担起把人从“抽象”的“普遍理性”中解放出来的使命,把人从“物”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的使命,把人从“资本”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的使命,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使命。从全球视野看,人类今天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正是人的“物化”问题,人类在新世纪乃至新千年所追求的根本目标,正是把人从对“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因此,马克思自觉地承担起的哲学使命,不仅理论地表征了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而且理论地塑造和引导了新世纪乃至新千年的新的“时代精神”。我们要从马克思明确指认的历史使命去锤炼我们时代的哲学理念。 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人类的哲学思想,归根到底是对人类自身的存在的关切。从哲学的宏观历史上看,哲学对人类存在的关切,可以区分为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以“深层”文化的“基础性”“根源性”来规范人类的全部思想与行为,从而将“深层”文化作为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标准”;另一种则是以文化的“顺序”性去关切人类存在,即把“重要”的文化选择为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以它作为“标准”来规范人的思想与行为。哲学的这种具有革命性的变革,首先是表现为“从两极到中介”的思维方式的变革。 从两极到中介,这是人类的哲学思想及其所表现的人类的思维方式的空前革命。“传统哲学”之所以“传统”,是因为全部的传统哲学都是力图获得一种绝对的、确定的、终极的真理。这样,它就把世界分裂为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非此即彼、抽象对立的存在。这是一种统治人类思想几千年的非历史的、超历史的思维方式。这种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超历史的思维方式,理论地表征着前现代社会的人的存在方式。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前现代社会中,“上帝”是神秘化了的真善美化身的“神圣形象”,“英雄”则是世俗化了的真善美化身的“神圣形象”,这样,人们就不仅在“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两极对立中造成了“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而且在“此岸世界”自我分裂的两极对立中造成了“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上帝”和“英雄”作为真善美的化身而构成人们的一切思想和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每个个人则无权对“标准”做出“选择”。这可以称之为“没有选择的标准的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的本质主义的肆虐”。现代哲学所“拒斥”的“形而上学”,从根本上说,就是这种“没有选择的标准”。 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它在使“上帝”自然化、物质化、精神化和人本化的过程中,逐步地“消解”了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从而使人类文化从“神学文化”过渡到“后神学文化”即“哲学-科学文化”。然而,近代哲学所“消解”的只是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并没有“消解”马克思所说的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现代哲学“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从根本上说,就是“消解”一切“超历史”的规范人的思想和行动的根据、标准和尺度,把哲学所寻求的真善美理解为时代水平的人类自我意识,把人类已经达到的认识成果理解为时代水平的“合法的偏见”,把人类自身的存在理解为“超越其所是”的开放性的存在。这就是现代哲学所实现的“从两极到中介”的转化。在这种哲学变革中,哲学一向所追寻的终极性的“本体”变成了历史性的“本体论的承诺”,从而孕育并形成了“从层级到顺序”的新的哲学走向。 哲学的“层级”性的关切与“顺序”性的关切,其本质上的区别,首先是“非历史”的与“历史”的两种不同的关切。“层级”性的关切,它先验地断定了文化样式的不同“层级”,并先验地承诺了“深层”文化对“表层”文化的基础性和根源性,因而它给自己提出的是“非历史”的任务——寻求超历史的、永恒的、终极的“本体”。与此相反,“顺序”性的关切,是以否定文化样式的先验的“层级”性为前提,并致力于“消解”文化样式“层级性”的先验原则,因而它给自己提出的是“历史”的任务,也就是在自己时代的水平上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做出慎重的文化选择,把对终极性的“本体”的寻求转化为对历史性的“本体”的承诺。这表明,哲学从“层级”性的关切转向“顺序”性的关切,不只是从思维方式上体现了现代哲学的从两极到中介的变革,而且是从价值诉求上实现了现代哲学的从两极到中介的变革。 哲学追求的“层级性”与“顺序性”,从根本上说,是如何处理“标准”和“选择”这对范畴的相互关系。人的生命活动是寻求和实现“意义”的“生活”活动,而“生活”活动的“意义”则总是存在于“标准”与“选择”这对范畴的矛盾关系之中,即“选择”什么样的“标准”来确定生命活动的“意义”。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关于人类存在意义的自我意识,它的全部理论活动,都可以归结为处理“标准”与“选择”这对范畴的矛盾关系。传统哲学是一种“层级”性的追求,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以“表层”与“深层”的对立关系弱化甚至是取代了“标准”与“选择”的矛盾关系。把“本体”作为无须“选择”的“标准”。现代哲学是一种“顺序”性的追求,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以“重要”与“次要”的历史性的矛盾转化关系看待和对待“标准”与“选择”的矛盾关系。具体地说,现代哲学是从“重要”与“次要”的“选择”中历史性地确认“标准”,而不是先验地确认“标准”并排斥历史性的“选择”。就此而言,传统哲学追求的是一种“没有选择的标准”,而现代哲学则承诺的是一种“可以选择的标准”。“标准”的历史性和可选择性,是现代哲学的根本性标志。 在“层级”性的传统哲学的追求中,哲学的任务,只不过是寻找那个作为永恒真理的“本体”,并用它来“解释”一切的存在。正因如此,以“层级”性的追求为使命的传统哲学,只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并且只能是以“超历史”的“神”或“非历史”的“物”作为“本体”或“标准”,去规范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这就是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的肆虐”。而在“顺序”性的现代哲学的追求中,“顺序”既是对历史文化的一种承诺,更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选择”和“安排”,因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活动。从层级到顺序,并不意味着从“没有选择的标准”到“没有标准的选择”。然而,现代西方哲学在20世纪的长达百年的“消解哲学”运动中,不只是动摇了传统哲学的“层级”性的追求,而且是把现代哲学的“顺序”性的选择引向了“拒斥形而上学”的“没有标准的选择”。当代哲学在“层级”性的追求与“顺序”性的选择中所陷入的困惑,根本的问题是对哲学的“人类性”与“时代性”的矛盾关系的理解。传统哲学之所以在“层级”性的追求中去确立“没有选择的标准”,是因为它把哲学的“人类性”追求诉诸超历史、超时代的“独断论”。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之所以在“顺序”性的选择中陷入了“没有标准的选择”,是因为它把哲学的“时代性”“历史性”的选择变成了非人类性的即“断裂”性的选择,并由此形成了“没有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 哲学从“层级”性的追求到“顺序”性的选择,它所改变的是以“层级”的先验性而确认的“标准”的永恒性、终极性,而不是取消人的历史性选择的标准。哲学作为社会的自我意识,它所承担的使命,总是以“历史的大尺度”(人类的、社会的、整体的、世代的尺度)去观照和反省人类的思想与行为,把“历史的小尺度”(当下的或局部的尺度)所忽略的东西提升到“重要”的位置,从而在价值“排序”中“选择”某种“历史的大尺度”作为人的思想与行为的“标准”。正因如此,哲学总是不仅“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而且“塑造”和“引导”时代精神。 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它的根本性的社会功能,是以自己的概念系统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即从根本上规范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内容、行为方式和行为内容。哲学理念作为这种“规范”作用的集中体现,就是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意义上的“标准”。“中国梦”是我们现在思考最多的问题。怎样理解“中国梦”?梦想是一种追求,它既是追求的目标,也是追求的活动,是人的追求的“标准”和“选择”的互动中的过程。因此,梦想不是抽象的,不是空洞的,“中国梦”更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和一个空洞的套话。从“标准”与“选择”的矛盾关系出发,在我们思考梦想的时候,起码要想到四个方面:梦想是历史性的;梦想是分层次的;梦想是有具体内涵的;梦想是有现实基础的。 作为“标准”和“选择”的“梦想”是历史性的。在封建社会,帝王们的梦想是把自家的统治传至千秋万代,所以叫“万岁”。知识分子是“朝为田野郎,暮登天子堂”,“学而优则仕”,而起义的农民是“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它所构成的是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本性就是不断地去形成更多的利润,把一切的社会关系都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它所构成的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我们的梦想是推翻“三座大山”。在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的梦想是“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梦想”是有层次性的。每个人的梦想是有层次的,群体、国家的梦想也是有层次的。西方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人的层次需要理论,把人的需要分为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审美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人的这种需要层次的满足,体现了梦想的不同层次。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这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人生四境界说:最低是自然境界,高一点是功利境界,再高一点是道德境界,最高是天地境界。人源于自然,又在更高的层次上和大自然合而为一,这是一种天地境界。选择不同的层次需要或以不同的人生境界为标准,这构成不同时代的根本性的哲学理念。 梦想是有具体内涵的。梦想反映的是一种追求,它要实现的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目标。“中国梦”的最深刻的内涵是我们的国家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要成为什么样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要在整个世界的人类文明史中树立一种什么样的形象。所以,我们的梦想必须具有这样两个方面的力量:对内它要具有一种强大的凝聚的力量,能够引导全体人民达到什么样的发展;对外它要能够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作为一个世界大国能够为整个人类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梦想是有现实基础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3]我们今天能够凝练成这样一种“中国梦”,既是百年来中华民族抗争的过程、革命的过程、建设的过程、改革的过程所凝练形成的,同时它也深刻地体现了我们整个民族的追求过程所达成的现实条件,所以,我们才能够在今天提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梦想。这是我们今天用以评判我们的全部实践活动的“标准”,也是我们自觉地做出的根本性的“选择”。 从全球的视野看,当代人类选择什么样的文明?各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每个个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时代的最为根本的时代性课题。而隐含在选择背后的更为深层的问题则是: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保持清醒的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为选择而反思标准,从而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哲学对当代人类实践的理论支撑,也是当代哲学的根本性的哲学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