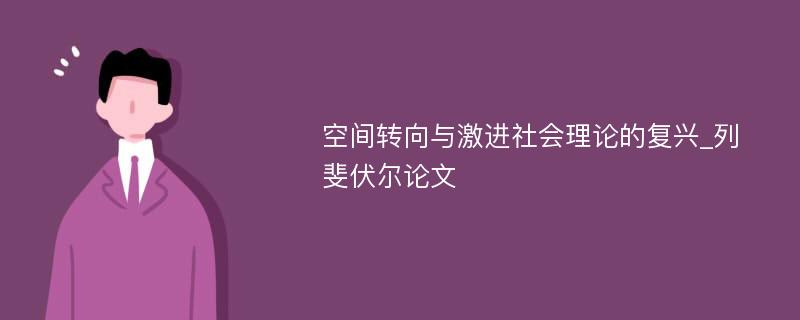
空间转向与激进社会理论的复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激进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70年代,以法国思想界为中心,发生了一场被当下学界称为“空间转向”的思潮。空间转向向由结构功能主义、实证主义以及现代自由主义主导的社会科学传统发起挑战。在法兰克福学派之后,哲学、社会理论、文化理论、政治学、地理学、史学等多个学科或领域,出现了激进思想的复兴,并在80年代以后回击新自由主义及其新保守主义,通过持续的努力,积聚成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影响至今。
一
马克思的批判性的社会理论,乃是对实证主义的社会哲学传统的批判,因之形成了激进的社会理论传统,也开创了经典社会理论。而在经典社会理论的三大传统及其格局中,涂尔干的实证主义社会哲学传统与韦伯的解释性的社会理论,实际上都是对马克思社会理论的激进性质的抵制与修复。经典社会理论及其现代走向,基本上是以结构功能主义与解释性的社会理论为主导的,因而主要说来是韦伯的社会理论传统及其变种,实证主义传统则与社会学学科和职业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之后,激进的和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则经历了涂尔干、特别是韦伯的社会理论的过滤及其处理。总的说来,其激进性质逐渐衰退。
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即通过韦伯的物化思想、文明研究及其话语体系进而拓展的社会文化批判。虽然这一批判一直在秉承对实证主义社会学以及自由主义传统的批判,但无论如何,马克思激进批判理论的两个基本维度不断受到质疑。
第一,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治批判因现实中无产阶级的空缺而转变为阶级意识的焦虑,进而成为文化批判的空的“理论前提”。在青年卢卡奇那里,阶级意识的焦虑即已呈现,并由随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及其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所激活且被问题化。在此,“激活”是指阶级意识的焦虑撕开了意识形态的文化结构。韦伯从阶级、地位等级以及民族国家不同主体把握社会行动的思想,突破了马克思的阶级及其阶级分析方法,也带给卢卡奇及其法兰克福学派新的启示:意识形态不再被仅仅归结于经济基础的单一结构,而是直接归属于由文化工业所支撑的文化系统。这同时意味着,作为马克思展开意识形态批判前提的激进实践,无论从主体还是从境遇方面看,都越来越不可能作为文化工业及其意识形态批判的现成的前提。
第二,消费主义的兴起动摇了马克思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基础。马克思的激进社会理论,乃是对其所谓一般的实证科学的社会哲学的批判,这一批判特别表达为基于生产领域而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是,在马克思之后,从生产领域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资本批判,越来越受制于消费逻辑。在现代西方学术视野里,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连同整个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均退回实证主义的解释视野,历史唯物主义直接等同于历史决定论,《资本论》也成为资本主义的辩护理论。在西方经济学及社会科学视域中,《资本论》已经被作了实证主义化的解读及处理,从而成为福利社会以及风险社会的理论资源。与此同时,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则被置于边际效应理论的强势语境,经济学领域为欲望经济学所宰治,生产方式理论被消费理论、文化理论以及生活方式理论所代替,由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所开出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学术中则被边缘化。对于马克思而言,尽管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一个历史过程,但因为生产危机的存在,因而这一过渡总体上是不可避免的和不可逆转的。然而,一旦主题从生产转变为消费,情况又会怎样呢?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及法兰克福学派将主题从经济领域转向文化领域,但对于解放及其可能性的考量,总体上却没能跳出当初韦伯设定的“铁笼”。
阶级意识的焦虑意味着以解放为主题的历史意识的危机。20世纪持续强化的实证主义加剧了史学的计量化趋势,消费主义则以其持续“在场”消解历史性,进而消解自我解放的可能。通过历史而诉诸解放的叙事似乎已经终结。不过,在文化论域内,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却成功地展开了“否定的辩证法”,借此揭示当代人及文化的自我悖反性,并激起解放之焦虑。这种焦虑连同存在主义及其当代精神心理学的助推,并经由西方激进左翼思想改装过的“毛主义”的引导,终于在1968年引爆,成为当代史上最为著名的社会运动及文化政治事件。其中,法兰克福学派将批判性的社会理论引入对文化本身的批判,存在主义则看起来彻底释放了个体自由以及社会的不可沟通性,“毛主义”及其“文化革命”则被想象性地看成是现代性及其知识革命的符号。1968运动试图在历史逻辑中释放解放的焦虑,但终究陷入了法国启蒙运动以来革命——游戏——节日狂欢——自爆的循环。正如一个世纪以前的巴黎公社终究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位,1968运动再次表现出理论上的贫血。无论是阿尔都塞还是阿多诺,都无意于为这一运动提供理论上的支持。从很大程度上说,1968运动既为法兰克福学派提供了实践空间,也意味着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效应的终结。马尔库塞亲历了这一转变,马尔库塞尝试发扬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以回击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及其巩固的现代自由主义传统。但是,其高度主观化的策略与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所出现的“工业文明以前所没有过的内部团结和凝聚力”之间实际上呈现出了极大的错位。因而,其文化策略,连同其所解释的1968运动本身,均成为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及其所解释的当代资本主义展开自我改良的决定性的环节。此后,哈贝马斯的“向右转”实际上意味着激进的社会批判理论传统的中止。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曾被看成是对1968运动及其当代社会运动的两种最重要的理论修正,社会学家亚历山大曾断定,这两种理论努力实际上都“以自己的方式回到了帕森斯著作的基本原理上”①。1968运动最后以政治的强力介入以及运动本身沦为无政府主义而告终。此后,同先前历次激进社会运动一样,照例是保守的右翼势力的复辟,直至新自由主义及新保守主义的兴起。
但是,1968运动同时也使得激进左翼思想寻求到了新的坐标,这就是空间。列斐伏尔以及随后福柯、詹姆逊、吉登斯、哈维等一批理论家的杰出工作,导致了当代哲学及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
这里有必要补述本课题研究的重要性。这一研究可能是突破当代社会理论研究的一种努力。比如,亚历山大那部写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对空间问题好像毫不敏感。该著仅仅把阿尔都塞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向结构功能主义的回溯,其认为阿尔都塞承认当代资本主义结构“确实存在着帕森斯描述过的那种内在区别”,而阿尔都塞及其结构主义的努力“使激进者转而研究帕森斯理论”②。然而,如果相关研究注意到阿尔都塞同时已经重视的空间概念及其激进性质,问题的阐释便会有所不同。阿尔都塞的空间思想与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存在着多大的联系,或者究竟如何定位阿尔都塞空间思想的理论地位,尚需学界探讨。若置于当代激进空间论域,人们发现,正是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倒逼着人们弄清阿尔都塞的空间思想,并激活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空间维度。但目前社会学以及社会理论界对列斐伏尔同样并不敏感。亚历山大另一部写于1998年的《新功能主义及其后》,还有瑞泽尔同样完成于1998年的《后现代社会理论》,都没有提到列斐伏尔③。华语学界中黄瑞祺对西方社会理论甚为关注,不过其《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也没有专题探讨列斐伏尔。这种状况当然并不奇怪。因为它本身就表明主流社会学学科传统甚至于社会理论传统依然受迪尔凯姆与韦伯传统的支配,即使马克思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资源,都只是主流社会学传统的“配料”;即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传统中,列斐伏尔也一直处于“不知名的状态”④。正因为如此,清理空间视域下当代激进社会理论的课题,才显得特别重要。
二
下面笔者对列斐伏尔及其空间转向论域下相关激进社会理论的努力做一简要勾勒与定位。列斐伏尔因提出空间生产理论,从而开启了空间转向与当代激进社会理论的复兴。此前的激进社会理论大体属于被韦伯解释性的社会理论传统所定位的时间—历史主义。在此,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在思想史上超越了“历史主义”,但在当代史的意义上,即在实证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的批判版图上,历史唯物主义再次被命名为“历史主义”,而历史主义也从此前的浪漫主义典型过渡到现代语境中的历史决定论。在列斐伏尔之前,海德格尔尽管已引入诸多空间话语,但海氏显然不会从空间引入所谓解放及其反抗叙事。海德格尔大体上是最后一位时间存在论者,对他而言,空间的意义除了栖居之外,并无存在的足够呈现方式。当海德格尔承认“空间的存在论阐释依然困难重重”时,他所关注的是能否回复传统的自然空间或空间的自然状态,即回到本质上时间化的空间。然而,在现代性处境中,这样的浪漫主义愈发带上了神秘主义意味。海德格尔的空间,既与激进无涉,也与社会理论无关。
在空间转向中,萨特与阿尔都塞均显示了一种过渡性。在揭示个体生存的境遇及其修辞学意义上,萨特凸显了空间⑤。存在主义大都持有保守主义情绪,但萨特的存在主义稍微另类,其代表着一种无政府主义取向。从萨特的虚无且荒诞化的个体经验,虽不能、也无意于开出激进社会理论,但却切入当代人的生活政治,并敞开了当代社会空间中人的处境。而为阿尔都塞所重视的结构,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时间—历史逻辑的一种反读。苏贾曾做过如此评价:“结构主义是20世纪在批判社会理论领域对空间进行重申的最重要的途径。”这样的评价显然是针对阿尔都塞而言的。阿尔都塞将作为意识形态的主体性置于“人类世界的客体”结构中,由此定位历史。在这里,历史不是从属于时间而是社会空间。“历史的‘主体’是特定的人类社会”⑥。阿尔都塞的“虚空”(void)概念显然指向于激进政治⑦。如果说萨特敞开了当代社会空间中的人的处境,那么,阿尔都塞则给出了作为社会空间的结构与形式。苏贾就认为:“萨特的马克思化的现象学本体论,代表着一种解释学,其中心是围绕知识渊博的人类代理人的主体性、表象性和意识,而人类代理人不仅致力于创造历史,而且还专注于打造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日常生活的政治文化。截然不同的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强调了更加客观的诸种条件和社会力量,这些条件和力量形成了资本主义发展和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它们均有助于将战后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开掘成两条不协调的溪流:因为关于结构—主体关系的各种对立观点而分离。但奇怪的是,两者均向空间化的可能性开放。”⑧萨特与阿尔都塞之所以均向空间化开放,并不令人困惑。如果说此前无论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还是解释学化的人文主义,均纠结于德国式的时间—历史逻辑,那么,正是萨特与阿尔都塞将视域拓展到空间或面向空间开放,从而为空间转向作了准备。就这一努力的理论定向而言,乃是从结构功能主义化的社会理论以及解释学的社会理论传统向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的回复,哲学的中心效应则从德国移到法国;法国取代德国成为当代哲学的中心的过程,正是围绕以空间转向开启的激进社会理论的复兴而展开的。
肯定萨特与阿尔都塞在空间转向中的过渡意义,丝毫不意味着调和两者的哲学取向,因为空间转向本身即体现于从存在主义向结构主义的转变及其结构本身的深化。列斐伏尔难以接受的正是萨特式的非社会的个体性,因而从存在主义转向结构主义,与此同时也接过了为萨特人学所摒弃掉的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并进一步批判作为历史决定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结构的理论,并且是自身支撑开放空间的革命性质的结构。如果说此前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解放话语不断延宕,那么,由辩证唯物主义支撑的空间反倒构成了激进政治话语不断的在场。空间不只是一个僵化的客体,不只是经济学的载体,它本身就是社会性的并且是政治性的。由此,列斐伏尔提出用“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取代“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以阐述空间的社会性与政治性。尽管西美尔早在20世纪初即已提出“社会空间”概念,但依然只是指某个对象物,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则是主体本身,是解放叙事得以可能的前提。当这样的社会空间被运用于都市及其地理学分析时,其激进意义不言自明。因此,没有脱离社会的“空间”,空间的本质的社会性意味着解放政治持续的在场性。
列斐伏尔之后,福柯、吉登斯、詹姆逊、哈维、卡斯特等进一步推进了激进的空间社会理论。福柯高度重视空间概念,认定“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⑨。福柯提出的谱系学的或微观空间理论也许不属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激进社会理论,但其理论较为成功地分析了空间同传统的历史—时间的断裂,且晚近以来的各种激进社会理论在阐释空间时多要借助于福柯的分析。不仅如此,同样是1968运动的产物,福柯与列斐伏尔等激进左翼理论家分享了空间理论,其在政治愿景上与列斐伏尔存在着明显区别,福柯虽然一度参加过法共,但其批判的目标是整个现代性构成机制,是自近代以来形成的启蒙及其宏大的历史话语,因而无论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从属于这一机制及其话语。在这个意义上,福柯的微观空间本身就是针对列斐伏尔所代表的激进社会政治空间,福柯用谱系学代表了批判的社会理论,或者,换句话说,其谱系学是另一种类型的激进社会政治批判方法。关于空间,福柯主张用“异托邦”取代“乌托邦”,诸如花园、公墓、博物馆、图书馆等等,这是一种解放得以可能的另类社会空间。不过,人们注意到,当福柯把这种异托邦空间变成无处不在的空间,以之消解存在于人们观念中并实际地影响人类进程的乌托邦(善良意志)及“歹托邦”(邪恶意志)时,其“异托邦”空间其实是十分激进的,甚至比新马克思主义及其新左翼理论家们的“空间”还要激进。对此,凯文·安德森即作如是评价:“正如新自由主义者所说,马克思的问题不在于其太激进,而在于其还不够激进。更有人补充道,真正的激进思想家是那些像福柯、德勒兹,甚至尼采这样的人”⑩。在这里,福柯、德勒兹以及更往前溯的尼采(其实理应还有海德格尔与列奥·施特劳斯等一些现代保守主义哲学家们),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基于传统而展开的对现代性的最极端的抵抗。当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依然只是在进步主义理路上展开的激进社会政治理论,本身已陷入解放的迷局时,一种基于保守主义的姿态倒显示其对现代性的激进抵抗。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关于空间的激进思想有两类。一类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大体限于早期资本主义的空间理论,空间是条件性的,但却是客体的和对象性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提出了空间转移思想,但却是属于“以时间换空间”性质的,是隶属于以时间为中轴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另一类是以列宁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时代的空间思想,在列宁那里,空间问题被敏感化,列宁有关帝国主义最为重要的不平衡发展思想,即包含着空间及其地理发展的不平衡。空间问题被关注并被激进化,实际上是在列宁之后,并随卢森堡、布哈林等人,形成了影响当代激进空间理论的资源。除列斐伏尔、福柯、哈维等形成当代激进社会理论(同时也是政治理论)外,曼德尔、沃勒斯坦、詹姆逊、鲍德里亚、布迪厄、奈格里、巴迪欧、苏贾、卡斯特等一批学者的思想中,同样包含并激起了激进空间理论的想象,其中如哈维、苏贾、卡斯特等更是直接继承了列斐伏尔的激进空间理论。
以哈维为代表的激进政治地理学,并不反对唯物辩证法,事实上这依然是其激进政治地理学及其都市理论的基本方法,但他通过对《资本论》的创造性的解读,赋予历史唯物主义以新的形式,即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从对《资本论》的解读中,哈维获得了这样一种见识,即马克思以资本为核心的空间转移理论,转变为以空间本身为核心、并以资本扩张为表现的空间转移理论。哈维的激进空间理论特别针对新自由主义及其全球资本主义境遇,并提出了新帝国主义理论,其实质依然是激进空间及其解放叙事。在哈维那里,新社会的获得完全取决于人们对社会空间的积极占有。
吉登斯非常明确地肯定哈维等打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学与地理学彼此互不往来的状态,其实质是社会学为结构功能主义所统治,而地理学则为实证主义所统治。吉登斯非常明确地将激进空间理论(涉及地方性、区隔化、时空抽离、场所、在场等一系列重要的空间社会学概念)纳入社会学理论传统,并建构了独树一帜的结构化理论。这一理论不像列斐伏尔、哈维的社会理论那样激进,但对于实证主义及其保守主义取向占主流的当代社会理论传统而言依然是激进的,并且事实上构成了对结构功能主义的直接冲击。正是这一结构化理论成为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基础。吉登斯也许是自觉遵循空间转向逻辑从事社会理论创新研究,并获得西方主流社会学认可且扎下根来的唯一一位左翼社会理论家。而在吉登斯自己也有意淡化其左翼资源的背后,再次表现出西方主流社会理论传统何以有意保持了对马克思主义资源的拒斥。
三
激进社会理论在当代既名之为“复兴”,当包含两个维度:一是面向历史的回复;二是面向当下及未来的问题意识及其方向。当代激进空间社会理论,也许前所未有地显示出现代性背景下的理论想象力、跨学科效应以及理论与实践的融合趋势,但面对空间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对空间转向的当下及未来向度的评估尚须迟缓,本文特别关注其历史回复维度,这一维度特别有益于展开对问题本身的反思。总的说来,空间转向及其引发的激起社会理论的复兴,在历史维度上,乃是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社会理论传统中的空间维度的激活。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本身就是空间对于时间的一次大胆的破除,黑格尔的观念论以及整个德国古典哲学见证了一种依时间的内在性展开的历史哲学及精神哲学,但马克思通过借助英法先进国家的空间破除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观及其时间上的自我迷恋,青年马克思激进思想是在空间经验而不是在时间体验中进行的(时间体验更多地是青年马克思所破除的神学意识),包括马克思的历史意识,主要说来还是受到黑格尔历史哲学过滤掉的、来自于法国大革命的激进空间及其解放意识的影响。是的,对于依然保持着法国大革命的热情与动力而言,对于风生水起、思潮激荡、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的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而言,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矛盾及其伴随的巨大社会活力而言,时代精神的感受一定是空间性的;更深一步说,如果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造中包含着时间的维度(这是确定无疑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十分明确,即历史进步与人类解放,基于此,马克思依其唯物史观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构造了“人的历史”),那么,人的历史一定是在当下的空间被激活的。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可以理解马克思的判断:时间是一种积极的存在。总之,在问题意识层面,马克思主义是因对空间而不是时间的敏感从而把握到了时代精神。19世纪50年代,依苏贾的判断,欧洲历史依然是“历史性与空间性大致平衡的时代”(11)。此后,尽管欧洲的情形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自己有关欧洲革命形势的新判断也见证了这些变化,但是,由新的空间的开发从而刺激欧洲资本主义活力、并因而分担欧洲各国资本主义矛盾的想象一直盛行,只是限于欧洲现代性的自我巩固以及对非西方文明的排斥,直到巴黎公社,马克思主义作为基于激进空间而展开的对欧洲资本主义的批判,仍一直在发挥着作用。然而,巴黎公社的失败,同一时期德国的统一及其伴随的巨大的民族主义声浪,使得激进的空间观越来越自觉地受限于欧洲民族国家论域,而基于空间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作为典型的激进批判,则“开始退隐于力量更强大的有关时间和历史的革命主体性的欧洲中心论主张的背后”(12),由此出现了自由主义传统的去空间化,并在社会学乃至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显现出来:
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可以被看作在批判社会思想方面历史决定论正在崛起而空间观念相应湮没的一个时代。社会主义评论紧紧地依附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周围,而孔德和新康德思想两者结合起来的影响,重塑了自由的社会哲学,促发了各种新“社会科学”的形成。这些社会科学的主旨,也同样是想要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种历史过程,但仅仅是偶然的地理过程。一种去空间化(despatializing)的历史决定论的跃然升起,只是到了现在才为人们所承认,并得到了人们的检视,这一情况与资本主义第二次现代化以及帝国和公司寡头卖主垄断时代的肇端恰好同时发生。它十分成功地对空间进行了堵塞、贬低和去政治化,将空间当作批判社会话语的一个对象,这样,即使是解放的空间实践的可能性也销声匿迹了将近一个世纪。(13)
事实上,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由于自由主义传统的不断更新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统治下官僚制的持续巩固,社会理论甚至整个社会科学中都存在着抑制空间的倾向。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存在主义的兴起开始向结构功能主义发起挑战,但这种挑战本身终于耗尽了来自于激进资源的文化和历史动力,也抽去了自身的存在论根基,直至激进理论决然地诉诸空间及其想象。
激进空间社会理论的回复有两个起始点。第一个起始点是马克思主义传统。这其实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某种修复。概而言之,这是一个新的空间,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资源被限于、并且被堵塞于传统视域(欧洲自由主义之转变及其欧洲民族主义兴起过程)时,通过诉诸列宁、毛泽东等帝国主义理论及其非西方民族主义实践从而释放出的新的全球地理空间,在这一政治空间的转换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空间观被进行了一次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解读。尽管这一转换只是呈现出激进政治下全球社会建构的理论端倪,并且事实上依然面临诸多困难问题(如全球资本主义、东方主义、当代社会主义的自身改革及其发展),但其意义愈显重大。另一个起始点,则是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到的,即法国启蒙运动及其法国大革命正在成为当代激进空间理论的灵感来源。无论列斐伏尔的激进空间理论是否意识到,这里都包含着一种对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的前溯。作为回复的历史记忆,法国启蒙运动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的空间,也不再只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客体的和被动的地理概念,马克思主义论说其唯物史观及其新唯物主义(同时也是其批判性的社会理论哲学基础)的主体性以及激进性,本身就是置法国唯物主义的空间于直观性与客体性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激进空间理论尝试将法国唯物主义置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框架,这正是列斐伏尔及哈维所谓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努力的思想史意义。
在整个激进空间理论兴起的背景中,还存在一个近乎于强制性的设定,即认定整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被确定为历史决定论,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耗尽了源自于法国启蒙运动的空间资源,并使得时间与历史完全抑制空间,甚至使得时间与历史本身就丧失了激进性质,由此也就直接赋予了空间以激进性。但空间转向带来的激进社会理论是否可以轻易地“舍弃”历史,以及这一“舍弃”本身意味着什么?恰恰是值得深长思之的。从马克思激进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经卢卡奇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理论及社会批判,再到空间转向下激进社会(政治)理论的复兴,实际上见证了一条从共产主义到启蒙再到民粹主义的“跌落”。这种跌落不是人们愿意看到并接受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人们可以看到,空间转向下激进社会理论的复兴实际上卷入了后现代主义。那些诉诸空间的思想家们,如福柯、詹姆逊、吉登斯、哈维、苏贾等之所以不约而同地并在不同程度上诉诸后现代主义,绝非偶然。用空间替代时间,用生存替代历史,既是激进空间理论的特征,同时也是其缺陷。
本文初稿系作者提交“网络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北京·香山,2011年10月)会议论文。
注释:
①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贾春增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274页。
②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第274页。
③杰弗里·亚历山大:《新功能主义及其后》,彭牧等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④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第65页。
⑤邹诗鹏:《空间转向与虚无主义》,《现代哲学》2012年第3期。
⑥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28页。
⑦参见林青《试析阿尔都塞哲学思想中的虚空概念》,《现代哲学》2010年第6期。
⑧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3页。
⑨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载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⑩Kevin B.Anderson,"Not Just Capital and Class:Marx on Non-Western Societies,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Socialism and Democracy,2010(3).
(11)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第5页。
(12)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第6页。
(13)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第6页。
标签:列斐伏尔论文; 法兰克福学派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资本论论文; 福柯论文; 社会学论文; 实证主义论文; 地理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