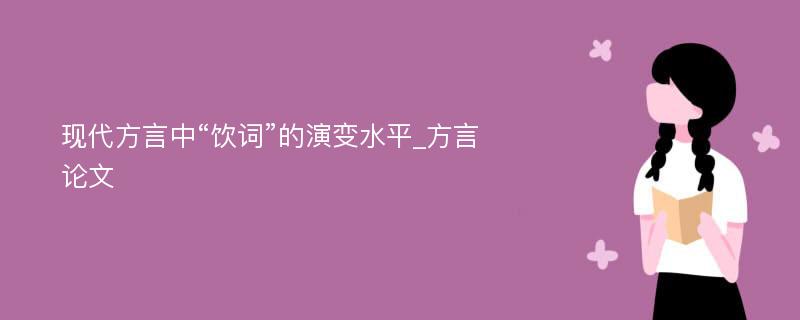
现代方言中“喝类词”的演变层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层次论文,喝类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利用方言材料,从音韵史角度探寻方言的历史层次,已有不少学者做过研究,并取得了斐然成绩。比如有关闽、客方言历史层次的研究,较有影响的就有罗杰瑞、丁邦新、梅祖麟、何大安、李如龙等,他们的研究极具开创性,论述也非常经典。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此类研究中,词汇方面的研究并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在谈及闽、客方言的来源和历史层次的研究时,邓晓华、王士元(2003)就曾极力建议“应当采取一种音韵、词汇并重的方言历史层次的分析方法,而非单一的音韵史的方法。”研究方言的词汇历史层次,大体有两种思路,一是研究某一具体方言内部的词汇层次,二是研究某一类词在不同方言中的历史层次。前者已见零星成果,如邵百鸣(2003)曾对南昌话词汇的历史层次做过概述,盛爱萍(2004)也考察过温州方言地名词的语源及历史层次。后者还少见研究,在论述汉语义位“吃”的普方古比较时,解海江、李如龙(2004)曾涉及到“吃”在方言中的历史演变层次,但没有深入展开。本文正想从这一角度作出尝试。
我们把从古至今能表示现代汉语“喝”这一概念的词统称为“喝类词”,把含有“把液体或流食咽下去”这一语义特征的语义场称为“喝类语义场”。“喝类词”是汉语的核心概念词,也是斯瓦迪士基本词表中的第一阶词。对这类词进行考察不仅有助于理清它在不同汉语方言中的历史演变层次,而且有益于判定方言间的历史渊源和亲疏关系。
2 “喝类词”的使用分布及特点
汉语史上“饮、啜(歠)、食、吃、欱、呷、喝”等都属于“喝类词”。王力(2001:571—572)指出,“现代‘喝’的概念,上古用‘饮’字来表示,到六朝时代也还是如此……用‘喝’来表示‘饮’的概念,那是明代以后的事。”这是就通语而言的,具体到现代各地方言,情况要复杂得多。根据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词典》的调查,42个方言点中“喝类词”的使用分布情况如下:
词项 喝 饮 吃 呷 其他 词项 喝 饮 吃 呷 其他 词项 喝 饮 吃 呷 其他
地点地点地点
哈市 + 乌市 + 娄底 +
济南 + 万荣 + 南昌 +
牟平 + 太原 + 萍乡 +
徐州 + 忻州 + 黎川 +
扬州 + 绩溪 + 于都
食
南京 + + 丹阳 +
+ 梅县
食
武汉 + + 崇明 +
+ 南宁
+
+
+
成都 + + 上海 +
+
呼广州
+
+
贵阳 + + 苏州 +
+ 东莞
+
+
食
柳州 + + 杭州 + 建瓯
馌
洛阳 + 宁波 + 福州
食、歠
西安 + 温州 + 厦门
食、啉
西宁 + 金华 +
+ 雷州
食、啜
银川 + 长沙 + 海口
食、啜
表1 “喝类词”在现代汉语42个方言点的分布
(说明:哈市:指“哈尔滨”;乌市:指“乌鲁木齐”;南宁:指“南宁平话”。)
可见,“喝类词”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分布非常复杂,有两个明显特点:1 )方言点间的用词差异极大。“食、饮、吃、呷、喝、啉、饁、啜(歠)、呼”等在方言中都有使用。2)在不同的方言点中,“喝类词”的分布数量不均。有的1个,如哈尔滨、济南、牟平、徐州、洛阳、西安、西宁、银川、乌鲁木齐、万荣、太原、忻州、绩溪、扬州、杭州、宁波、温州、长沙、娄底、南昌、萍乡、黎川、于都、梅县、建瓯;有的2个,如南京、武汉、成都、贵阳、柳州、丹阳、崇明、苏州、金华、广州、福建、厦门、雷州、海口;有的3个,如东莞和南宁平话。
3 “喝类词”的演变层次及其制约因素
3.1“喝类词”的演变层次
张光宇(1991)指出,方言是历史的产物,静态的方言现状实际蕴含着历史脉动的轨迹,横向的地理分布诉说着由古至今的历史故事。同样,“喝类词”在现代方言的共时分布,也是历时发展沉淀的结果,记载着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词汇现象。从方言里体现出来的不平衡性中,可梳理出历时的发展脉络,探寻出词汇现象的不同历史演变层次,像徐通锵(2004:105)说的那样,“从容地‘横’观语言在漫长时间中的发展动程”。根据各方言点对“喝类词”保留情况的不同,可大致把这类词的演变划分为六个主要层次。
1)南宁、广州、东莞处于演变的第一层次,保留着“饮”。
这一层保留了上古汉语里的词汇现象,演变速度最慢,是最为古老的一层。“饮”是上古汉语“喝类语义场”中的核心词。搭配对象主要是“酒、水、汤”,如《诗经·鲁颂·有駜》:“夙夜在公,在公饮酒。”《孟子·告子上》:“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据笔者考察,“饮”在元朝之前一直是通语中最常用的一个词,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喝”,清朝末期它才退出语义场,但是它在以上几个方言点中保存了下来。
2)于都、梅县、福州、厦门、雷州、海口处于演变的第二层次,都可用“食”。
王凤阳(1993:750)指出,“食”的古字像张口吃饭的形状,指食物经过口的咀嚼咽下去的过程。“食”虽然也是个上古词,但它和“饮”有比较明确的分工,主要用于固体食物。如《论语·述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庄子·逍遥游》:“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在《十三经索引》中,“食”字共出现1224次,其中与半流体“粥”等搭配的仅11次。(注:数据转引解海江、李如龙(2004)《汉语义位“吃”普方古比较研究》。)中古时“食”的义域开始扩展,据解海江、李如龙(2004)调查,在东汉至隋的汉译佛经里,“泉、水、甘露、羹、汤药、饭汁、乳、酒、粥”等都已经可以成为“食”的搭配对象。在以上方言点中,“食”都可以接流体或半流体名词,它在中古的新兴用法被延传下来。
3)崇明、上海、苏州、金华处于演变的第三层次,用“吃”和“呷”。
“吃”(注:中古用“喫”字形。除引文外,本文统作“吃”。)和“呷”都是中古才进入“饮食类语义场”的新成员。《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友闻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无事可咨。”《洛阳伽蓝记·城东景宁寺》:“呷啜莼羹,唼嗍蟹黄。”但是二者的用例都非常少,尤其“吃”接流体的例子更是罕见。(注:杜翔(2002:14—17)指出,中古“吃”仅10处用例,且9例接固体食物。接流体的用例只在吴支谦译《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中出现一例:“饮食无极,吃酒嗜美。”当存疑。)唐朝时,它们后接流体的用例渐趋增加,如《拾得诗·后来》:“博钱沽酒吃,翻成客作儿。”周昙《咏史·淳于髡》:“穰穰何祷手何賷,一呷村浆与只鸡。”据笔者研究,“吃”在近代汉语中曾经历了一个发展高峰,至清朝中叶发展为“喝类语义场”的主导词,成为表示“喝”概念的最常用词。而“呷”虽在近代汉语有所发展,但始终用例不多,处于弱势。上述方言点中“吃”并没有替换“呷”成为主要用词,二者并用,基本上保留了中古后期新兴的词汇现象。
4)扬州、杭州、宁波、温州、长沙、娄底、南昌、萍乡、黎川处于演变的第四层次,只用“吃”(注:汪维辉师告之,从总体上看,苏州和上海的方言要比宁波、温州等地要变得快,但为什么“喝类词”却相反?这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近代汉语“饮食类语义场”经历过一场大的调整。据崔宰荣(2001)和白云(2004)的研究,五代以后“吃”成为“吃类语义场”的核心词。“吃”使用数量的急速增加使其义域范围也随之扩展,它后接流体或半流体名词的用例迅速增多。据解海江、李如龙(2004)的考察,仅在《古尊宿语录》中,“吃”的流体对象就有“药、水、醋、菌羹、乳、粥、茶、酒、汤”等。清朝中叶“吃”战胜“饮”,发展为“喝类语义场”的强势词。这些方言点反映了近代汉语中后期“吃”已经替换了“饮”而“喝”还没有侵入的词汇现象。
5)南京、武汉、成都、贵阳、柳州、丹阳处于演变的第五层次,“吃”、“喝”并用。
“喝”字始见于宋元时文献,最初可能产生于北方方言。如关汉卿《关大王单刀会》第二折:“林泉下酒生爽口,御宴上堂食惹手,留的残生喝下酒。”但一直到清朝中叶,“喝”的使用范围并不广泛,用例也非常有限。直到清朝中后叶,它才迅速发展起来,并且与“吃”和“饮”形成有力竞争。这些方言点反映了近代汉语末期“饮”已被排挤出语义场,而“吃”与“喝”还处于相持阶段的词汇现象。
6)哈尔滨、济南、牟平、徐州、洛阳、西安、西宁、银川、乌鲁木齐、 万荣、太原、忻州、绩溪处于演变的第六层次,只用“喝”。
这一层次反映了“五四”以来“喝类词”的变化,是演变最快的一层。清末民国初“喝”取代“吃”成为“喝类语义场”的主导词,但“吃”并没有完全退出语义场,在通语中还在少量使用。“吃”完全退出是现当代的事情。上述方言点绝大多数处于北方方言区,在这些方言点中,“喝”已经完成了对“吃”的替换,与现代普通话的语言事实相一致。
另外,建瓯用“馌”。《说文·食部》:“馌,饷田也。”“馌”的原义是给耕作者送食。先秦多用此义,如《诗经·豳风·七月》:“馌彼南亩。”毛传:“馌,馈也。”清朝时还可见用例,和邦额《夜谭随录·王侃》:“从此,三哥耕,嫂炊,儿馌,无忧不作个好人家。”不过,其词义已由给耕作者送食扩大泛指“馈食”。通语中“馌”已经很少用。建瓯方言中,“馌”使用频率非常高,义域也很大,后可接固体、流体和液体名词,相当于普通话的“吃”与“喝”。但“馌”什么时候用来指称“喝”概念的,文献中没有反映。暂且存疑待考。
以上是就“喝类词”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分布梳理出的一个大致的演变层次,确切地讲,应该是按方言中所保留的汉语史上最早出现的词汇现象而分的大类。因为在以上六个层次中,演变层次和这一层方言点中所保留的词汇现象并不是全部一一对应的。有的是对应关系,比如第一层肯定是最古老的一层,因为“饮”是上古词,根据文献可以知道以前没有发生过用词替换。又如在第六层次中,基本上都是官话区的方言点,根据我们的考察知道这些方言经历了“吃”“喝”竞争的阶段,是直接从第五层次演变而来(注:参见拙文《近代汉语中“喝类语义场”的演变及相关问题》。)。但有的是否有对应关系我们还得研究,像第三层次崇明、上海、苏州、金华现在虽然用“吃”和“呷”,保留了中古后期的词汇现象,但是二词的前身是“饮”?是“食”?是“饮”“食”并用?还是另用他词?它们的替换时间是发生在中古还是发生在近代?也就是说,“吃”和“呷”是替换了哪些词以后才保留到这几个方言点的,它们之间又是什么时间替换的,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像第三层中的方言点只是记载反映了发生在中古时期的新兴词汇现象。
3.2“喝类词”演变层次的几种复杂情况
1)不同层次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有的方言点可能跨越几个层次。如东莞用3个词“饮、食、呷”,它就保留了上古的“饮”,中古“食”的用法,和中古出现的“呷”,至少反映了上古和中古才兴起的词汇现象。而南宁平话中用“饮”“吃”“呷”3个词,“饮”是上古,“呷”是中古,“吃”跨越了中古和近代, 由此看来,从上古一直到近代的某些词汇现象在平话中都有所沉积。
2)即使在同一层次内,每个方言点的用词情况也是存有不少差异的。如于都、梅县、福州、厦门、雷州、海口都处于第二层次,于都和梅县仅用“食”,福州、雷州和海口除“食”外还用“啜”,而厦门则用“食、啉”。上海除用“吃”“呷”外,还用“呼”,而处于同层次的其他方言点则不用。再如广州和东莞,东莞还在用“食”(~茶、~糖水),而在广州“食”已经少接流体名词。
3)具体到一个词,在同一层次中,不同方言点的分化和演变也不尽相同。比如,在第六层次中,哈尔滨、济南、牟平、徐州、洛阳、西安、西宁、银川、乌鲁木齐、万荣、太原、忻州等地都只用“喝”。“喝”除用来指称“把液体或流食咽下去”这一动作之外,在济南还“特指喝酒”;在牟平可指“吃(西瓜)”;在忻州可指“吃(带汤的面)”;在徐州还有另外3个义项:①赢(多用于游戏); ②吃茶(较老的说法,现代多说“喝茶”);③饮,给牲畜水喝。而其他方言点就没有这些用法。可以看出,徐州“喝”的义项最多,牟平和忻州“喝”的义域最广,“喝”的对象含有[+固(流)体]的语义特征,“喝”从而也具有了[+咀嚼]的语义特征。
再如崇明、上海、苏州、金华均属第三层次,都还用“呷”,但它在这几个方言点的用法却不完全相同。崇明和苏州用法限制较少,“呷”与现代汉语中的“喝”用法相似;金华则不能带宾语说成“~酒、~茶”等,只能说“侬酒~去”这种句式;而在上海“呷”只指具体的动作,如“~一口酒”,不能泛指。
4)不同层次的方言点对一个具体词的吸收选择程度也不同。 总的来看大体有四种。先以“呷”为例:a.排斥。“呷”第四、五、六层次中的方言点都不用。b.保留义项。崇明和苏州的“呷”与普通话中的“喝”用法相似;而广州和东莞,“呷”只表示少量地喝。c.保留固定搭配。广州和南宁平话中“呷醋”可以表示“忌妒”义,而其他很多方言点,如济南,表示同样意思用“吃醋”。d.转义。“呷”在娄底和福州话中用来表示“用嘴吸”这一语义,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吸”。如“吸烟”在娄底俗作“呷烟”。
再如“饮”,牟平、洛阳、西安和万荣只保留了“给牲畜水喝”这一义项,而宁波和绩溪除此义之外,还有“给植物浇水”之义。但在广州、东莞和南宁平话中其词义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喝”。
3.3“喝类词”演变层次分布的制约因素
“喝类词”在一具体方言中的演变线索可能非常复杂,往往不是单一地层层渐进,而是呈现出“非线性发展”。这是因为方言的形成不仅和汉语自身发展密切相关,还与民族迁移密不可分。罗杰瑞(1997)在研究闽语时指出,在中国南方,每次移民都带着自己特殊的汉语,语言借用的过程被几次移民浪潮搞得十分复杂。正是汉语本体的演变和不同时期的语言接触导致了“喝类词”在方言中的复杂分布。具体来讲,至少有三个因素制约了现代方言点对“喝类词”的选用:1)纵向的历时发展。历时发展会制约词汇和词义使用的传承性。比如现代官话区的某些方言点,如北京话,“喝”就直接来自于近代汉语。2)横向的方言接触。 方言的接触会影响词汇和词义的借入。比如现在还用“食”表示吃喝义的某些方言点,如海口,它有11个义项,其中“依靠某种事物来生活”和“耗费”两个义项和普通话中的“吃”完全相同,而且当“依靠某种事物来生活”讲时有“食工资”等这样的组合,很显然是受普通话“吃”的影响。3)人的认知因素。 认知因素往往会使人们原发性地创造新词新义。蒋绍愚(1999)指出,不同的民族以及同一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事物、动作和性状的分类不同,把哪些事物、动作和性状概括为一个义位和哪些义位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词也是不同的。蒋先生两次分类的思想在共时的不同方言点中也有体现。如在牟平,“喳”这个词就是当地表示“猪狗等大口吃食”的特有词。它的产生定然会打破原有“饮食语义场”的平衡,从而调整语义场成员的语义分配。这样,在牟平表示“猪狗等大口吃食”就不用“吃”表示,相对普通话而言,“吃”的义域就缩小了。当然,我们更应该看到一个方言点中某种语义场的复杂状况有时是综合因素形成的,并非一种原因所致。但每一种变化都会引起语义场的自我调整,这是勿庸置疑的。
4 结语
现在归纳一下“喝类词”在现代汉语十大方言区中的大致分布,见表2:
官话 晋语 徽语 吴语 湘语 赣语 客家 粤语闽语 南宁平话
饮+ +
食 + +
呷+
+ +
吃+ ++ +
喝 + + +
其他
歠、啉、啜
表2 现代汉语十大方言区中“喝类词”的分布
表2反映出,官话、徽语和晋语演变较快;吴语、湘语和赣语保留了中古和近代的词汇现象,但也有差异,湘语和赣语演变得要快些;客家话和闽语较多地保留了中古的词汇现象,演变速度要慢一些;粤语则保留了上古的词汇现象,演变速度最慢;而南宁平话最为特殊,能找到从上古一直到近代的词汇现象。“喝类词”演变的总体趋势是自北向南依次放慢,以长江为线,长江以北演变得快,长江以南演变得慢,而沿江流域处于过渡地带。
结合方言,对基本词作分类的演变研究,对于更客观地判定方言间的亲疏关系有很大参考价值。比如从表2反映出的闽、客、赣三方言的用词异同, 我们就可以判断出就“喝类词”来说,闽、客方言的关系要比闽、赣方言密切。从词汇角度来判断闽、客方言的关系,邓晓华、王士元(2003)已做了研究,认为从核心同源词角度来看,闽、客的谱系亲缘关系较近,而相对而言,客、赣方言关系则较远。再比对从音韵角度的研究成果,他们进一步得出“音韵层面的同一性较多反映方言之间的较晚期关系,而核心同源词则反映方言之间的较早期关系。”
李如龙(2003:209)曾说过,“地域方言的形成和演变都有复杂的历史和独特的道路,现存的方言系统都是许多不同历史层次的成分经过整合的现代共时系统。”“喝类词”在现代汉语方言中五彩缤纷的表现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李先生的论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