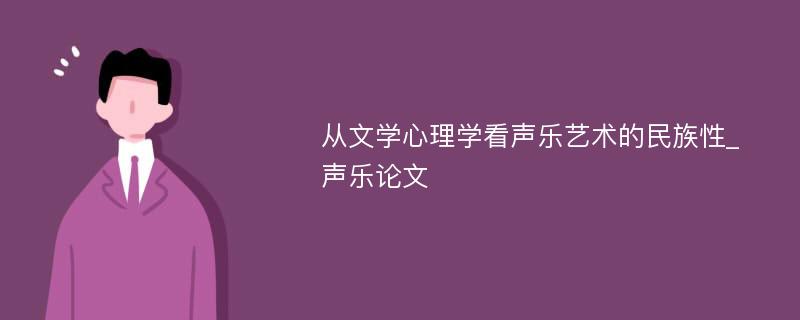
从文艺心理学角度谈声乐艺术的民族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声乐论文,心理学论文,性问题论文,文艺论文,角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但“音乐家却是有祖国的”,这句话除证明了音乐家的爱国情怀之外,还可以从音乐要扎根于民族文化肥沃的土壤之中去理解。现在,国内声乐界有所谓“美声唱法”(Bel Canto应译为“美歌”较为合适,因为“美声唱法”容易使人误以为这种唱法只注意声音而忽视音乐的情感及其它)和“民族唱法”之分。“美歌”是起源于意大利的一种歌唱方法。经过多少代歌唱家的探索,Bel Canto已被许多国家的观(听)众所接受,也是专业人员公认的最为客观的科学的发声方法。它能使人在音色音量方面的潜质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强调发展民族声乐,建立“民族声乐学派”呢?(有人认为“民族唱法”就是唱民歌,其实民歌的演唱仅仅是民族声乐所要表现的一个领域,另外象古诗词、民族歌剧乃至戏曲、曲艺等都可以称得上广义的民族声乐范畴)这就需要从文艺心理学的民族性特点这一角度来做一分析。
创作心理中的民族性因素
习惯上我们把创作主体心理结构与流程研究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社会、民族的心理历史层次;二是艺术家的心理构架层次;三是艺术家的生活与社会的碰撞交流所导致的第三层次。下面我们对这三个层次进行逐一分析:
一、社会、民族的心理历史层次
我国历史悠久,历经多次民族大融合最终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种乐器的产生与改进都有着相当久远的历史,并来源于各不相同的民族。比如二胡、琵琶、古筝等等,这些乐器具有音乐独特、表现力强等特点。正是因为这些特点使他们能够穿越千年,流传至今。这些乐器中的大多数都以“音色明亮”见长,如笛子、唢呐、高胡、京胡等乐器,这种音响与音乐氛围直接影响了中华民族在音色方面的欣赏标准。
另外,我国幅员辽阔,大多数民歌来源于地广人稀的高山、丘陵、大川、平原等地区的号子与山歌。由于人员稀少,为了排解寂寞与繁重的劳动和阶级压迫所带来的心理重负,人们逐渐形成了所谓喊山歌和喊号子的习惯,以此与远处的朋友和内心的希望交流。我们民族歌曲中歌声偏亮、偏假、偏高等(民歌中极少有男女低声部)演唱与欣赏习惯与此有直接关系。古代市井小调、流行歌曲、诗词曲赋的演唱、创作与欣赏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刘鹗所著《老残游记》中对歌女王小玉的演唱有这样一段描写:“王小玉便启朱唇、发皓齿,唱了几句书儿。声音初不甚大,只觉入耳有说不出来的妙境,五脏六腑里象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象吃了人参果,无一个不畅快。唱了数十句之后,渐渐地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象一线钢丝抛入天际,不禁暗暗叫绝。”从这里不难看出我们的民族声乐在创作与欣赏中对音色的要求,这正是我们的民族声乐区别于其他唱法的一个首要特点。
我国历史上的音乐创作几乎没有完整而又成体系的文艺理论专著为指导,但在诸家学说中又处处闪烁着精辟的美学思想之光。这些在社会、民族、习俗的思维习惯的支配下所产生的舆论和观点随着历史车轮的颠簸而积淀下来,并对后来的创作者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著名的语言学家、教育家及音乐家赵元任先生在创作《卖布谣》的时候,在旋律走向上很自然地想到使用他的家乡话无锡口音的音调与节奏作为模仿对象,而他的生活经历与艺术素养也决定了他的创作内容与题材。
二、艺术家的心理构架层次
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基于不同的地域、风俗、文化传统等等背景会形成不同的心理特征,进而影响到整个意识形态,影响到艺术家的创造思维和艺术品的特色。歌唱家也不例外。
西方的歌唱家在演唱某一作品时,除了要充分表现其感情和意境之外,还将相当的精力投入到如何运用更加科学的发声方法去挖掘更美的音色和更宽的音域、更强的力度。他们理性地运用解剖学、声学、力学等方面的科学手段来达到目的(这一点在歌剧的发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在有着相当久远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背景下的中国,却哺育着一代又一代非常“感性”的艺术家们。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中关于艺术创造的最高境界是要合乎“天人合一”之“道”。只要声音优美连贯,感情充沛,不必过多地追求和炫耀自己的高音、力度等方面的技巧问题,最关键的在于一个“意”字。演唱者只要用心去塑造一个物我合一的意境来感化听众就达到表现上的目的了。这也许正是中西方在艺术表现观方面的一点区别吧。
不同民族的艺术家为什么会如此不同,这需要提一下荣格的“群体无意识”理论。每个地域或民族都有着他们独特的传说、寓言、神话、童话,这些都是他们“群体无意识”转化为有意识的反映,它们折射出了这些民族所共有的埋藏在群体意识深层的一种无形的力(这种力荣格用晶体在结晶过程中那个决定晶体形状的无形的轴架作比喻,它是无形的,但在开始结晶时就已经决定了晶体的结构)。这种无形的力决定了这一民族的共同气质——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人生观、处世哲学等方面的问题。
每位艺术家都是以生活在他们所处民族地域这个大环境中为个体的,这就使他们在进行艺术创造与再创造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带上民族的气质与特征。比如普契尼(Puceini)的歌剧《图兰多特》,众所周知,他的题材来自东方,而且为了使他的歌剧具有更浓郁的东方韵味,他还借用了一些中国民歌的旋律。但即使是这样,也仍旧不会有人说:“这是一部中国歌剧”。它仍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大利歌剧。仅仅因为作曲家是意大利人这一点足以决定其意大利气质。因此中国歌唱家在演唱中国作品时就更应该正视这一点,多注意民族风格与气质,将本民族内在的蕴味表现得深刻、透澈(其实,中国歌唱家在演唱西方作品时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东方气质,这也正是打动听众的个性抑或风格之所在)。有些人在艺术上一味崇洋,强调全盘西化,这大可不必,作为一位中国的艺术家,就象摆脱不掉黄色的皮肤一样,我们永远也不会抛弃掉自身所具有的中华民族的气质。只有正视这一点才能正确看待自己,摆正位置,扬长避短,使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而不是被人评论为“学得挺象”的摹仿者。
三、艺术家的生活与社会的碰撞交流所导致的第三层次
每位作曲家、歌唱家的创作都是以其所在的民族为土壤,以其生活经历为源泉的。他的生活与社会交流则是其创作的契机。
我们每演唱一部作品时都要去研究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作曲家在创作这首歌时是处在怎样一个时代?怎样的一个社会大环境?如何产生了这首歌曲?这一来大家就会发现无论哪件作品的产生都与民族和社会的因素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比如八年抗战期间曾产生了多少抗战歌曲,而又有多少歌唱家与群众将他们传遍了全中国,这不正是有感而发吗?即使有一些与抗战无直接关系的作品也流露出了在那种大形势下或消极、或压抑、或逃避的情绪。作曲家的每一首歌曲都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即使有些作品是作曲家为古代诗人的作品谱写的曲子,那也是在他的生活经历、审美情趣以及他所属的民族所特有的思维方式的支配下选择写成的。例如舒伯特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写了许许多多优秀的作品,有些作品的歌词并非同时代或同民族的诗人所作,但谁也不会说他们的创作脱离生活,舒伯特站在本民族思维习惯的立场上来选择歌词,无处不受到民族、社会、时代及其所受教育等因素的制约。舒伯特的作品就是舒伯特的作品,不会成为俄罗斯风格的,更不会成为中国风格的,这一点充分体现了研究作曲家的生活与民族习惯对于演唱者的必要性。
通过对创作主体(包括创作者与再创作者)的心理结构与创作心理流程的分析,我们看到民族气质不是强调出来的,也并非可以刻意追求的,而是生活环境潜移默化地滋润给每位艺术家的,我们应当正视民族风格,研究民族风格、发扬民族风格。
作品结构心理学中的民族性因素
艺术作品是沟通创作者与欣赏者的一座桥梁。作品的艺术构成是创作者思想与情感的载体,同时又是唤起欣赏者审美愉悦的客体。声乐艺术中的语言、旋律、和声、织体乃至演唱者的音色、呼吸都作为构成艺术作品、传达思想感情的符号映射出创作者的心理素质构成。它们被称作艺术构成中的物质媒介。
语言是最直接地表达歌曲创作者思想感情的构成材料,歌词的创作与选择都符合每位作曲家的审美情趣。这与上面提到的创作主体的民族性特点是分不开的。中国的艺术作品讲究“写意”、“含蓄”,即使是豪放的作品也有其显著的含蓄的特征。这正是中国人所欣赏的意韵所在,是任何一位中国艺术家所追求的,但其他民族就未必如此,拿我国民歌的歌词与那波里民族风格的歌词相比较就可见一斑。
川南山歌《槐花几时开》在刻画怀春少女形象时并不直接说这个姑娘如何爱着并思念着一位小伙子,只是失神地唱着:“高高山上(啰)一树(哟)槐(啰喂)手把栏杆(啥)望郎来(啰哎)”。歌曲用含蓄的手法将这位少女思念情郎时痴痴呆呆的可爱模样刻画得活灵活现。当母亲责怪女儿为什么失神时,少女却羞涩地掩饰道:“儿望槐花儿(啥)几时开(哟喂)”。整首歌曲只有四句,却内涵丰富,意韵深远,耐人寻味。我国还有许多民歌都以含蓄地表达思想感情为特点,如《小河淌水》、《茉莉花》、《拔根芦柴花》等歌曲。在民歌与传统美学观点的影响下创作的歌曲也大都具有上述特点。刘半农创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的歌词(赵元任曲),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怀念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虽然没有那波里民歌风格的《重归苏莲托》在表达对祖国、对故乡的依恋时的豪放热烈,但很确切地表述了那一时期中国游子的感受。意大利民歌和意大利民族风格的创作歌曲以热情奔放、直抒情怀为多。例如人们非常熟悉的《负心人》这首歌曲,一开始就直呼负心姑娘的名字:“卡塔丽!卡塔丽!”并责问她伤害“我”的原因:“你为什么对我说这些话呢?为什么这样折磨我?”而后坦率地表达了“我”对卡塔丽的爱情:“你忘了我把整个的心献给了你……。”整首歌曲流露出哀怨情绪,发展到高潮时是这种情绪压抑后的迸发——虽然悲伤,但悲伤得真诚、率直,歌曲情感起伏跌宕、牵动人心。
不同民族的歌曲在歌词上产生如此的差别,是与各自民族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有直接关系的。中国的绘画、诗词都讲究“移情”、“会意”,这是中国古典美学观的精华,它对歌词创作者的思路产生着直接的影响。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整个民族所背负的封建意识影响下的道德伦理等方面的思想枷锁十分沉重,从而促使人们在感情表达上(尤其是爱情表达上)转向含蓄、深沉。西方民族在其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的影响下形成了与我们不同的意识形态,尤其在西方文艺复兴后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艺术家们尽力摆脱宗教的束缚,喜欢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世界,因而在艺术创作结构上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
如果说歌词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学底蕴的话,那么歌曲的行腔则最能体现该民族在韵味上的审美情趣。其实,追求“科学”的发声方法与强调民族性之间并无绝对的冲突与矛盾,任何艺术门类都不可能抛开民族性、阶级性而只谈技术。
建国后的一二十年内,我国涌现出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歌唱家,虽然在演唱技术上他们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毛病或缺陷,但依然得到了听众的青睐,这是因为他们从演唱作品、舞台表现到歌曲行腔,无不汲取了民族传统中优秀的成分,并将它们发扬光大。比如对于郭兰英的演唱艺术,所有专业人员都能听出她在技术方面的不足,但她仍不失为一位民族歌唱艺术家。原因之一就在于她深入研究了民间演唱的行腔艺术,同时注意积累各类曲目和锤炼自己的民族艺术表现力。她的曲目涉及面广,风格差异大。从创作歌曲到传统民歌;从地方戏曲、曲艺到民族歌剧。从民族文化艺术修养的角度看,她是一位立足于民族的歌唱家。
从京剧艺术与西洋歌剧在物质构成上的区别也能看出艺术构成的民族性特点。
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一根马鞭便是一匹千里神骏,几个打旗的龙套便是浩荡三军,抬一下脚便是进一道门或出一道门,所谓“六七人便为千军万马,三五步已是万山千水”。西方人面对这些可能惊奇莫解,中国人却认可这就是艺术的真实。而西洋歌剧传统中往往要求布景的真实、可信(当代歌剧舞台美术受现代美学思想的影响也开始走向简单化、抽象化)。
京剧艺术在演唱方面也是如此,讲究的是演员的个性。演唱时演员可以根据曲牌任意发挥。伴奏乐器比较单一,配器也较单薄,重要的是演员对“意”的表达是否到位以及观众的领悟。而西洋歌剧则是在音乐构成及表现手段等方面颇下功夫。这与他们民族思维方式重逻辑、讲理性是分不开的。从演唱的旋律到和声配器基本上是要尊重原作。剧情发展、曲式结构都从整体角度做一非常理性的安排(这里并非全面肯定我们民族只重感性,欧洲各民族只重理性,只是侧重程度不同罢了)。
刘勰曾在他的《文心雕龙》中提到:“……良由内听难为聪也,故外听之易,弦以手定,内听之难,声与心纷;可以数求,难以辞逐。”意思是说客观的听琴的声音可以知道它是否和谐,而内心意韵的体验是比较困难的,这种体验只能是感受到它内在规律之存在,却难以言语表达。在此我们可以看出“写意”这一“思维定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族音乐的创作者。他们不在乎乐队的编制是否庞大,配器效果是否震撼人心,伴奏织体是否复杂多变。考虑最多的是不能将观众的注意力分散到其他艺术构成的表层即感官刺激上去,而是集中精力体味作品中的深层意蕴。这就使得中国的民族调式、和声、曲式等各种音乐的物质构成与西方炯然不同。音乐构成有着如此鲜明的民族性色彩,因此在学习演唱民族声乐作品的时候,首先要研究民族音乐的内在特点以及与其它民族的区别。另外还要学习民族发展史,熟悉或掌握民族歌曲的表现手法与艺术构成(艺术构成不仅仅是艺术符号拼接的物质构成,它还包括作品深层的艺术形象与创作的心理走向以及民族文化的内含与意蕴——这些更值得我们注意与研究——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去表现风格纯正的民族歌唱艺术。
欣赏心理中的民族性因素
“观众是歌唱家的上帝。”虽说歌唱家不能一味迎合观众口味,但却很有必要研究欣赏者的心理态度与构成——即所谓欣赏心理学(文艺心理学中,我们强调创造与欣赏的辩证关系,过分强调任何一面都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对欣赏心理学的研究也有许多角度:审美体验的深度、广度;艺术联觉与通感;职业敏感;不同艺术门类欣赏活动的层次构成;欣赏者心理特性的研究;认识定势与群体无意识理论,另外还有审美习惯与情趣的民族性、社会性、时代性与阶级性的特点等等。在此,本文仅就欣赏心理学中民族性的有关问题加以阐述。
一、心理定式与认识定式
生活环境与所处的时代能使一个人对事物接受的心理过程形成定式走向。比如有些老年人一看到日本国旗就产生一种厌恶感甚至敌视的情绪;有些从“文革”走过来的人一听到“革命京剧样板戏”就会禁不住打个寒战。人们非常容易理解他们形成这一心态的原因。同时,整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在艺术欣赏习惯上,也会形成与其它活动较为接近的心理活动方式,这在文艺心理学中称之为心理定式。
认识定式是指某个民族在其文化背景或生活经验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共有的认识某件事物的习惯性思维走向。个人会因为他的生活阅历形成认识定式,一个民族同样也是如此。
在艺术欣赏过程中,某个民族的心理定式与认识定式是该民族意识深层的审美情趣的逻辑推延的决定性因素。它们直接支配欣赏者接受何种作品,同时也决定他们将以何种方式去理解、体验这些作品。每个民族在艺术欣赏中认识的过程与深度以及心理态度都是不同的。
曾有些外国朋友向笔者问起京剧演员在念白时为什么要拖长腔以及为什么要用脸谱等一系列问题。对此我们可以做一些非常简单的回答,但他们未必能真正理解。专业研究者也可以从心理学、文化学、人文科学、语言学等各个范畴作出各种解释,但外国人会有深刻的体验、真正的领悟吗?相反,大多数中国人却很少提出类似的问题,因为他们知道或潜意识中认识到那都是以我们民族的审美情趣为标准艺术化了的形式。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没有为什么。上述在认识定式与心理定式上的差距使中国观众与外国观众在京剧欣赏过程中的欣赏角度与深度截然不同。
外国人如果不对剧情、背景乃至中国的历史、文化再作更深入的了解,就永远不会理解京剧为什么会是那个样子。正如对西方历史文化发展不太了解的中国人无法理解西方现代派绘画艺术为什么会是那个样子一样。进而,就谈不上欣赏他们了。歌唱者只有领悟到这一点才会明白自己要表现什么样的作品,给什么样的人看(听)。
演唱者除了应该意识到认识定式与心理定势的民族性特点以外,也不应忽视其阶级性、时代性等特征。比如现在流行演唱“红太阳”歌曲之风,但在现在的演唱中怎么也听不出“那个年代”的感觉与味道。又如一些老一辈音乐家听了现在演出的《黄河大合唱》之后认为在声乐、交响乐队的技术水平和表现力度都比抗战时期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但又总感到不如那个时代的演唱更能打动人心。这一点说明某一民族在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会形成有区别的认识定式与心理定式,这一点也是歌唱者在研究欣赏心理时应注意的。
二、艺术欣赏中通感、联觉与想象的民族性
通感是指在审美体验中感官印象之间的表象联想。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中有这样一段:“……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这正是典型的通感修辞手法。作者写月下的荷塘从景物观赏者的视觉、嗅觉和听觉等方面细腻地绘写了荷塘活脱脱的种种情状和景象,贴切传神、如诗如画。通感在文学创作与艺术欣赏中经常出现。
通感、联觉与想象也是具有民族性的。如前面提到的《老残游记》中王小玉说书的那段。刘鹗由王小玉的唱腔感受到在“黄山三十三峰之腰”飞舞盘绕的蛇,又仿佛是“看”到了“东洋烟火”。这种欣赏过程中唤起的通感、联觉与想象无疑与刘鹗所处的民族、时代与地域有直接的关系——“黄山”、“飞蛇”、“人参果”、“三万六千个毛孔”、“东洋烟火”……无处不流露出浓郁的民族色彩。他不可能联想到阿尔卑斯山、玫瑰花、风笛等西洋人生活的构成部分。
国画大师刘海粟曾将欣赏京剧各流派演唱的感受用国画的技法风格来表述:
“梅先生的表演风格以画相喻应是工笔重彩的牡丹花,而花叶则以水墨写意为之。雍容华贵中见洒脱、浓淡相宜,艳而不俗。
谭鑫培是水墨画的风格,神清骨隽,寓绚烂于极平淡之中,涟漪喁喁,深度莫测,如晋魏古诗,铅华洗尽,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老三麻子的戏,实具大泼彩风情,每观演出,给人的艺术享受在瞠目结舌之余,回味几十年。
杨小楼如泰山日出,气魄宏伟,先声夺人,长靠短打,明丽稳重,纵横中不失精严,如大泼墨作画,乍看不经意,达意实极难……
…… ……”
在这儿,海粟大师以他那深厚的国画功底和民族文化底蕴为基点,发挥想象,将各流派的特点总结得精辟之极。“工笔重彩”、“牡丹花”、“水墨写意的花叶”、“晋魏古诗”、“大泼彩风情”、“泰山日出”等等无处不闪烁着我们民族聪颖与隽秀的一面。如果让西洋艺术家来欣赏京剧就不会有如此深刻、贴切的体会,但他们自有他们民族的欣赏习惯。德国诗人海涅在欣赏了肖邦的音乐之后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他不仅是一个具有高度技巧的钢琴家,也是一个诗人。他能把他心中蕴藏的诗境描绘出来……我们会立刻发觉,他和莫扎特、拉威尔、歌德生在同一个地方,他真正的家乡是诗的神秘王国……有时候我真想打断他问:那个善于俏皮地在绿发上戴上银网的女水神近来好吗?我们的玫瑰花不是那么火一般的骄傲吗?我们的树还在月光下那么美妙地歌唱吗?……”
自然,肖邦的音乐不会使海涅联想到泼墨山水、泰山日出,但他也有自己的审美参照。他是诗人,于是他也感到肖邦的音乐正如诗人的诗,同时也联想到了与他生活有很大联系的莫扎特、拉威尔、歌德,又联想到他们民族传说中美丽的水神、如火的玫瑰花、月光下歌唱的树……在艺术欣赏过程中民族的心理差异在这几个例子中可窥见一斑。
其他艺术形式的欣赏也是如此,直接包含有各民族语言的歌曲欣赏在这一点上就体现得更加明显了。
歌唱家的困难就在于既要尊重原作要求,在演唱过程中尽量达到作曲家预期的效果,同时还要根据当时观众的特点,尽可能使调整后的自我在审美方向和情感倾向方面与他们产生共鸣。但这绝不意味着要完全迎合观众而抛弃自我。每位歌唱家都明白“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道理,我们只要注意揣摩“民族性”这一共性规律就不必太在意每一位观众欣赏心理的个性要求了。
我们除了要明确创作、再创作以及作品的民族性特点以外,还应该明白:欣赏群体无论受到歌唱家在演唱过程中多么尽力的引导或暗示,他们仍是站在自己所处民族的角度按照个人生活实践中的知识经验和欣赏习惯去理解歌唱者的表演。民族的文化、处境不同,联想的结果与情感的构建都不会相同。
三、艺术欣赏中的感情因素
一般情况下,不同的欣赏群体对不同民族的音乐作品的欣赏需求与情感唤起都是以民族文化背景(作为潜意识)为指导的。张廷竹的小说《五十四号墙门》中有段中国驻法使馆人员在一次酒会上欣赏音乐的情景描写:
“……音乐奏起来了,先是奥斯卡管弦乐队演奏的《风流寡妇》,吱吱吜吜,叮叮咚咚,然后便是瞎子阿炳的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这无比美妙动人的哀歌打动了在场的一切黄皮肤黑头发的人的心弦。盛着金黄色芬芳香槟酒的杯子停留在唇边,手僵在半空中,一缕淡淡的乡愁笼罩在客厅中,混合在甜腻腻的空气里,巴黎人理解这种乡愁,音乐是最深刻、最博大的世界语……。”
这段文字非常真切地描述了当时人们在欣赏音乐过程中的心理活动方向。尽管张廷竹在这段文字里提到“音乐是最深刻、最博大的世界语。”但《风流寡妇》却没有唤起这位东方人的审美注意,只是有些“吱吱吜吜,叮叮咚咚”的感觉罢了,但“阿炳”的声音一出就“打动了在场的一切黄皮肤黑头发人的心弦。”这是因为创作者(包括再创作者)与欣赏者的情感交流是建立在同一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一致的审美情趣基础之上的。因此当《二泉映月》奏响后才能勾起这些驻外人员无法掩饰的思乡之情:“手僵在空中,一缕淡淡的乡愁笼罩在客厅中……”这段文字不仅使我们体味到了音乐欣赏过程中情感唤起的民族性之特点,还使我们看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作品与欣赏者在欣赏过程中的反应所产生的对比。
欣赏过程中,情感的激发和灵魂的升华是艺术欣赏的最后阶段,也就是所谓“移情”。“移情”是建立在直觉、认识、思维、理解、联想、通感等心理流程的基础上的。这些因素通过前面的论述,证实了欣赏过程中以民族性特点为前提的情感的激发与流露自然也就具有民族性的一面了。一位受人欢迎的歌唱家到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演唱几乎都会得到观众掌声的回报,但掌声却是以不同民族的心理特征与欣赏方向为背景的,因而歌唱欣赏过程中情感的激发也会各有不同。无论哪个国度的欣赏者听到阿炳的《二泉映月》和柴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时都会唤起一种悲哀的感情,但这两首曲子的伤感情绪是绝对不会相同的,既然我们谈到了欣赏过程中感情唤起的民族性特点,那么为什么中国人听到《如歌的行板》时也会体味到具有俄罗斯风格的辛酸呢?这是由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民族的融合,文化的交流以及人类的共性所决定的,这就是康德所称的审美感受的“通感”。意识形态与文化氛围的前期交流是音乐欣赏过程、心理情感交流的前提,也就是欣赏情感唤起的预期性。
有人在谈起为什么我国民族唱法较受欢迎时总是说:这是因为民族唱法给人以亲切感。对这一观点,笔者颇不以为然。只有演唱者的唱腔与表现为观众所接受,也就是演唱者与欣赏者的审美情趣相吻合时才能使欣赏者有亲切感。西洋唱法在大多数中国观众中没有亲切感,这是因为语言、行腔、旋律等作品构成因素都很难与他们的心理波动产生谐振。同样,我国的民族歌唱家在国外演唱时给国外听众带来的也只是新鲜感而绝不会是亲切感,掌声只是礼貌的、赞赏的表示。他们的亲切感只能由他们民族的歌曲唤起。
小结
我们从三个角度分析了声乐创作、演唱和欣赏过程中的民族性特征。在实践中,这些因素是互为因果与前提的,影响着创作与欣赏的全过程。因此,我们应该综合地、整体地去看待和理解歌曲创作与演唱中的民族性因素,不能割裂开,片面地去谈其中的某一方面。
我们强调歌曲演唱的民族性的目的是为了使其更具世界性,决不能在音乐中讲大民族主义,妄自菲薄,固步自封。只有在承认声乐艺术的民族性特点的前提下发扬本民族声乐表现艺术中的长处,同时善于发现吸收别人的长处方能使民族声乐更具魅力,同时也有利于推动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发展。
纵观声乐发展史,所有有成就的声乐艺术家都是立足于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兼收并蓄,在学习声乐技巧、钻研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同时拓宽眼界,吸收外来的一切有利因素,使自己的表现功力日见深厚。声乐学习者只有认识到并努力做到这一点才有可能从一位“歌者”渐渐成长成一位“声乐艺术家”。
标签:声乐论文; 艺术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音乐论文; 民族心理论文; 歌剧论文; 音乐论文; 二泉映月论文; 通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