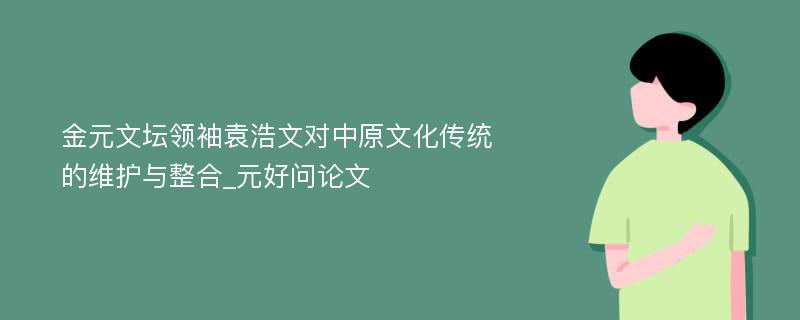
金元之际文坛领袖元好问对中原文化传统的维护整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元论文,文坛论文,对中论文,领袖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公元1233年金都汴京沦陷,至1260年忽必烈建元中统,蒙古政权的决策者顺应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一历史发展规律,逐步由基本上保持着草原游牧奴隶制政权对被征服的定居农耕区实行间接统治的格局,过渡到“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注:《元史》卷四《世祖纪·中统建元诏》。)这一在汉地实行汉法、继承中原历代封建王朝的轨道上来。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原的知识分子本着救世活人,存文保道的目的,积极地用中原传统文化对蒙古高层中的进步人物进行开导渗透,对推进这一历史进程发挥了巨大作用。文坛一代宗师元好问在金亡前夕,便以存文保种为己任,上书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列出中原秀士名单乞求聚养(注:《元好问全集》卷三十九《寄中书耶律楚公书》。本文用199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版本,间以他本参校。以下只注卷次。)。此后在身为亡国遗民的漫长岁月里,元氏除继续与在中央的耶律楚材保持密切联系外,又以文坛领袖的声望四方奔走呼吁,通过种种渠道方式进言地方权要人物,劝勉实行儒家仁政(注:除见诸本集中为东平严实、顺天张柔等所撰的碑记外,王恽《秋涧集》卷四十八《左丞相忠武史公家传》载:“北渡后,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好贤乐善,偕来游依。若王滹南、元遗山、李敬斋……为料其生理,宾礼甚厚。暇则与之讲究经史,推明治道。”由此可见元氏在汉人世侯幕府中游说之一斑。)。当耶律楚材推行的汉法中道受阻后,元氏又及时发现了忽必烈这个“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注:《元史·世祖纪》。)的贤王,先通过王鄂、张德辉等进讲儒道,最后亲自同张德辉到金莲川觐见忽必烈,奉之为“儒教大宗师”,从而奠定了其以儒治国的思想基础。《元史·张德辉传》记载了忽必烈与张德辉就以儒治国这一问题的问答。张的对话蕴含着在少数民族第一次即将一统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原文明面临最严重的威胁之际,以元好问为首的中原士人根据时代的需求对文化传统所推出的维护整合思想。本文以这段对话为线索,将元氏对文化传统的维护整合思想勾稽于下。
一、以倡导儒家仁政为时要的救世观
《元史·张德辉传》:
又问:“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对曰:“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不使预闻。大抵以儒进者三十之一,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注:这段问答原在“孔子殁已久”下,为了论述的需要,特提前。)
忽必烈虽自辛导(公元1241)以来就在漠北藩邸延见中原文人,对以儒治国有了一定的认识,但究竟该不该用守旧派所谓的“亡国之政”,心中尚犹疑不决,因此在召见“封龙三老”之一的张德辉时,他又提出这个问题。从当时涌入中原的各种文化看,与中原定居农耕经济相适应的儒家文化仍是最切合时宜的。在“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的社会现实中,用儒家学说来拯救生灵,维护安定的生产环境,协调人际之间的社会关系,制定严密的典章制度,这在当时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张德辉驳斥了“金以儒亡”的谬论,其以儒治国的主张自在其中,代表了包括元氏在内的中原士人维护文化传统的殷切愿望。下面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结合元氏有关记述来考察。
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所建立的大帝国,东起朝鲜,西达波兰,北到北冰洋,南至土耳其、波斯。在初期的战争中,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复仇和掠夺财物,并非夺取土地人民,所以攻城掠地时实行“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坑之”(注:姚遂《牧庵集》卷四《序江汉先生事实》。)的血腥屠杀政策;屠保州,“尸积数十万,磔首于城,殆于城等”(注:郝经《陵川集》卷三十五《须城县令孟君墓铭》。);屠忻州,“倾城十万户,屠灭无移时”(注:《中州集》卷五赵元《修城去》。);其时“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殆尽,金帛子女、牛马羊畜皆席卷而去,房庐焚毁,城郭丘墟”(注:《两朝纲目备要》卷一四宁宗嘉定七年七月乙亥“金人告迁于南京”条。)。金宣宗迁都汴京后,河朔无主,群雄四起,多如牛毛。在蒙古主力西征、木华黎经营中原的十余年间,这些汉人地主武装或投靠蒙古,或投靠金及南宋,相互争战,杀戮不已。“其存者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注:刘因《静修文集》卷一七《武强尉孙君墓铭》。)。金泰和七年(公元1207)全国人口有4500万,到蒙古太宗窝阔台乙未(公元1235)括户时,人口只有470余万, 由此可见这场浩劫的酷烈。
窝阔台执政初期,中书令耶律楚材竭力在汉地推行汉法,奏立十路科税所,任用儒者为科税使,制定新税法,使中原的经济一度有所恢复。但在奴隶分封制的基础上,这一推行汉法的力度也极有限。宋子贞所撰《中书令耶律文正公神道碑》中对这种情形概述说:“国家承大乱之后,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所谓更造夫妇、肇有父子者,信有之矣。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诸国之人,言语之不通,趋向之不同,当是时,公以一书生而欲行其所学,戛戛乎其难哉!”乙未括户,有百分之七十分封给宗王投下。这些蒙古贵族勒索无度,往来使者不绝于道,远非新税法所能限。再加征宋战争旷日持久,军需征集有增无减,急于星火,同时蒙古统治者又积极支持回回人发放高利贷(注:即斡脱钱,俗称羊羔息。每年要收倍于本息之利。),致使无数人民倾家荡产,卖身为奴。后来,窝阔台又索性将征税权卖给回回大商人奥都刺合蛮,随其任意搜刮,终使耶律楚材“礼乐中原”的抱负成为泡影。在这种竭泽而渔、混乱不堪的压榨下,人民或为奴,或逃匿,户口又几减过半(注:参见《元史·刘秉忠传》。)。
“要能够劫掠,就要有可以劫掠的东西,因此就要有生产。而劫掠的方式本身又决定于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实践证明,在中原这一定居农耕区中,只有实行汉法,才能有效长期地统治。所谓“汉法”,就是几千年来在中原所建立的与定居农耕经济相适应的以儒家学说为主的统治体系。然而由于版图广阔,蒙古在汉地的执政者除蒙古人外,还有许多西域人,种种统治管理方法混杂乱用。蒙古人又特别相信尊崇宗教,西域的基督教、伊斯兰教,西藏的藏传佛教,中原的佛教、道教都很受礼遇。儒教在他们的心目中地位很低,到宪宗蒙哥即位后,还有“儒家何如巫医”的疑问(注:《元史·高智耀传》。)。儒士同为编民,交纳赋税,奔走徭役,有的沦为奴隶,有的遁入空门(注:南宋徐霆《黑鞑事略》“其官称”条载:“……有亡金之大夫混于杂役,堕于屠沽,去为黄冠,皆尚称旧官。王宣抚家有推车数人,呼运使,呼侍郎。长春宫多有亡金朝士,既免跋焦、免赋役,又得衣食,最令人惨伤也。”)。在中原士人看来,蒙古裂土分民,军权、政权不分,无典章制度,人民沦为属民、奴隶,生杀由己,这是历史的大倒退,所以他们对昔日的辽金之政也无限神往(注:卷二十七《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辽人主盟二百年,至如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县长官专用文吏,其间可记之事多矣!”)。
元好问亲历鼎革,对这场浩劫有锥心之痛。他从儒家立场出发,在给蒙古权要人物撰写的碑文中,凡涉及仁爱之迹,都大书特书。如述东平万户严实保全生灵的事迹云:“彰德既下,又破水栅。郡王怒其反复,驱老幼数万欲屠之。公解之曰:‘此国家旧民,吾兵力不能及,为所胁从,果何罪邪?’王从公言,释不诛。继破濮州,复有水栅之议。公为言:‘百姓未尝敌我,岂可与兵人并戮之?不若留之农种,以给刍秣。’濮人免者又数万。其后于曹、于定陶、于楚丘、于上党,盖未有不然者(注:卷二十六《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当时蒙古人尚复仇滥杀,元氏在此文中对严实以宽大为怀的事迹也特书之:“初,公之部曲有亡归益都数十人。益都破,皆获之。人以为必杀,而公一切不问。王义深,义斌之别将,闻义斌败,将奔河南,凡公族属在东平者,皆为所害。河南破,公获义深妻,厚为周恤之,且护送还乡里,终不以旧仇为嫌。”谓其在统治区实行仁政云:“画境之后,创罢之人新去汤火,独恃公为司命。公为之辟四野,保完聚,所至延见父老,训饬子弟,教以农里之言,而勉之孝弟之本,恳切至到,如家人父子,初不以侯牧自居。官使善良,汰逐贪墨,岱逋赋以宽流亡,假闲田以业单贫,节浮费以丰委积,抑游末以厚风俗。至于排难解纷、周急继困,……人出强勉,我则乐为。”(注:卷二十六《东平行台严公福堂碑铭》。)谓冠氏千户赵天锡云:“侯在军校中,日以文史自随,延致名儒,考论今古,穷日夕不少厌。……行台公所统百城,比年以来,将佐令长皆兴学养士,骎骎乎齐鲁礼义之旧。推究原委,盖自侯发之。”(注:卷二十九《千户赵侯神道碑》。卷二十六《顺天万户张公勋德第二碑》。)他称赞顺天万户张柔“日与文儒考论今古,见仁民爱物之事,辄欣然慕之,恩拊吏民,恒若不及”时,还特别提到张柔与真定万户史天泽联合上奏窝阔台,为天下民众请命的事。他如为张汉臣、毕叔贤、赵振玉等所撰的碑文中对仁政的铺写比比皆是。从这些奖掖开导之中,可以看出元氏的良苦用心。他把推行儒家仁政视为当时最理想、最文明而且也是最切合时宜的治国措施。
二、以道统为体、正统为用的中华文化一统观
《元史·张德辉传》:
部曰:“孔子殁已久,今其性安在?”对曰:“圣人与天地终始,无往不在。殿下能行圣人之道,性即在是矣。”
“性”指精神。张德辉不仅正面回答了孔子的精神是否存在的问题,而且又十分巧妙地针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现实,端出“殿下能行圣人之道,性即在是矣”这一涉及到道统、正统的问题。“道统”即圣道承继的统系。儒家指由尧、舜、禹而至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的统系(注:韩愈《原道》。)。“正统”则就政权方面言,旧称一系相承、统一全国的封建王朝为正统。儒家所谓“一系相承”,实质上是指承继道统而言。唐韩愈《原道》有“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语;金赵秉文《蜀汉正名论》谓“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认定金国承继正统;元初郝经《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更旗帜鲜明地说:“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张德辉的对答,代表了包括元好问在内的当时杰出士人的共识。从元氏的有关著述看,他对这一重大问题有着更深刻的体认,概括起来就是以道统为体,正统为用的中华文化一统观。
元好问在《博州重修学记》中阐述了他的道统观:“草昧之后,道统方开。……有天地,有中国。其人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其书则《诗》、《书》、《易》、《春秋》、《论语》、《孟子》;其民则士、农、工、贾;其教则君令、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睦、朋友信;其治则礼乐、刑政、纪纲、法度;生聚、教育、冠婚、丧祭、养生、送死而无憾。”他认为这一道统乃天理人心所在,万古不能变,一刻不能离,他断定蒙古以武力夺取天下后,必然会承继王道,实行文治。元氏早在癸巳(公元1233年)汴京沦陷之初,就把蒙古灭金入主中原视同中原历代王朝的更迭。其《寄中书耶律公书》说,“阁下辅佐王室,奄有四方,当天造草昧之时,极君子经纶之道”,“自汉唐以来,言良相者,在汉则有萧、曹、丙、魏,在唐则有房、杜、姚、宋。数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当时百执事之人,毗助赞益者,亦不为不多”;“南中大夫士归河朔者,在所有之”,此乃“造物者挈而援之维新之朝”,“他日阁下求百执事之人,随左右而取之,衣冠礼乐、纪纲文章,尽在于是,将汉有少助阁下萧、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当丁未年(公元1247年)忽必烈为藩王颁旨修复真定庙学时,元好问兴奋地称颂道:“洪维大朝,受天景命。薄海内外,罔不臣属。武克刚矣,且以文治为永图。……王府忠国抚民,一出圣学。比年宾礼故老,延见儒生,谓六经不可不尚,邪说不可不绌,王教不得不立,而旧染不得不新。顺考古道,讲明政术,乐育人才,储蓄治具,修大乐之绝业,举太常之坠典。其见于恒府庙学者,特尊师重道这一耳!……盖兵兴四十年,俎豆之事不绝如线。独吾贤王为天下倡,是可为天下贺也。”(注:卷三十二《令旨重修真定庙学记》。卷三十五《清真观记》。)由此可见元氏以天道至尊,圣贤传道,道统为体,正统为用,不分中外,不辨华夷的道统观。他的这一观点在金亡后的史学著述中得到具体的贯彻。遗山致力纂修金史,这故然有保存故国历史的情份,但更重要的是为蒙古新王朝提供有益的借鉴。观其《与枢判白兄书》所云“惟有《实录》一件,只消亲云顺天府一遭,破三数月功,披节每朝终始及大政事、大善恶系废兴存亡者为一书,大安及正大事则略补之。此书成,虽溘死道边无恨矣”及王恽《秋涧集》所载“近读遗山先生《镜略》书,所谓‘立片言而得要’者也。其驰骋上下数千载之间,总理繁会数百万言之内,骈以四言,以叶音韵,世数代谢,如指诸掌”的记载,其为后世提供借鉴的宗旨甚明。中统初元,儒臣们编进《大定政要》,忽必烈在制定制度时,除继承唐、宋外,尤其注重以金朝的制度为其定制之法的借鉴。由此亦可看出元氏以道统为体、正统为用,不分中外,不辨华夷,旨在经世致用的思想在晚年史学著述中的具体实施。
纵观元好问金亡后的一系列文化活动,我认为仅以“道统”、“正统”之说尚不足以概括,应当把它放在中华文化这个大范畴中来考察。他说“文章,圣心之正传。达则为经纶之业,穷则为载道之器”(注:卷三十六《鸠水集引》。),认为道与文章不过表里体用之别,故于金元之际毅然以斯文命脉自任,弘扬道统。郝经《遗山先生墓铭》云:“方吾道坏烂,文曜噎味。先生独能振而鼓之,揭光于天,俾学者归仰,识斯文之正,而传其命脉,系而不绝,其有功于世又大也。”徐世隆《遗山集序》云:“自中州斫丧,文气奄奄几绝,起衰救坏,时望遗山。遗山虽无位柄,亦自知天之所以畀付者为不轻,故力以斯文为己任。”特别是元氏编纂有金一代的诗歌总集《中州集》,将辽人、宋人,契丹人、女真人,都视为中州人物,把先进的中原文化视为各民族融合的凝固剂,体现出用先进文化变外为内、变夷从夏的中华文化一统观。家铉翁《题中州诗集后》谓此云:“世之治也,三光五岳之气,钟而为一代人物。其生乎中原,奋乎齐鲁汴洛之间者,固中州人物。亦有生于四方,奋于遐外,而道学文章,为世所宗,功化德业,被于海内,虽谓之中州人物可见。”“迨夫宇宙中分,南北异壤,而论道统之所自来,必曰守于某;言文脉之所从出,必曰派于某。又莫非盛时人物范模宪度之所流衍。故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在万里之外皆中州也。”“盛矣哉,元子之为此名也。广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于中原,而视九州人物,犹吾同国之人。生于数十百年后,而视数十百年前人物,犹吾生并世之人。……余于是知元子胸怀卓荦,过人远胜。”中华民族在虞夏时自称为“夏”,至周而自称为“中国”和“华”。“中”是就地域而言,谓其居天下之中央。“华”是就质性而言,谓其如花之美丽茂盛。正因其居中,便于吸收周边文化,故发展水平最高,与四夷合成了花瓣式的文化格局。这种向心结构产生出巨大的凝聚力,使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纵观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实非以地域、血统为纽带,也非以武力兼并所驱使,而是以华夏为主体所创造的先进文化凝聚而成。南北朝时期和唐末之后出现的两次民族大融合,都是以中原先进文化为核心的。不过,这两次民族大融合又有所不同:前者为同汉,即将本民族的姓氏、服饰、语言、风俗全部汉化;后者为同华,即学习中原的先进文化,把儒家圣贤的经典作为安邦治国的思想基础,但要保留本民族的语言、习俗,且进而创造本民族的文字。元好问是被汉化了的拓跋氏后裔,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现实容易接受,对中华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及其永不衰竭的生命机制也有深刻的认识。在蒙古以席卷之势即将统一南宋、少数民族将第一次一统中华之际,他能够脱出“夏夷之辨”的狭隘观念,结合时代的特点,继承和发展了先祖魏文帝的汉化思想,形成以道统定正统、同经不同字、同华不同汉的中华文化一统观,以此沟通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心理,从而实现统一、文明的中华民族这一历史要求,确实是“胸怀卓荦,过人远甚”的。
三、以学政为主、刑政为辅的政教观
《元史·张德辉传》:
问曰:“祖宗法度具在,而未尽设施者甚多,将如之何?”德辉指银盘,喻曰:“创业之主,如制此器,精选白金、良匠,规而成之,畀付后人,传之无穷。当求谨厚者司掌,乃永为宝用。”
这里所谈论的是如何秉承汉法来治国的问题。张德辉引譬设喻,其大旨在建立典章制度方面。对此,元好问在《东平府新学记》中作了精要的阐述:“治国治天下有二,教与刑而已。刑所以禁民,教所以作新民,二者相为用,废一不可。然而有国则有刑;教则有废有兴,不能与刑并,理有不可晓者。故刑之属不胜数,而贤愚皆知其不可犯;教则学政而已矣。去古既远,人不经见,知所以为教者亦鲜矣,况能从政之所导以率于教乎?何为政?古者井天下之田,党庠遂序,国学之法立乎其中。射乡、饮酒、春秋合乐、养老、劳农、尊贤、使能、考艺、选贤之政皆在。聚士于其中,以卿大夫尝见于设施而去焉者为之师,教以德以行,而尽之以艺。淫言詖行诡怪之术不足以辅世者,无所容也。士生于斯时,揖让、酬酢、升降、出入于礼文之间,学成则为卿、为大夫,以佐王经邦国;虽未成而不害其能至焉者犹为士,犹作食者之养吾栋也。所以承之庸之者如此。庶顽谗说,若不在时,侯以明之,挞以记之。记之而又不从,是蔽陷畔逃,终不可与有言,然后弃之为匪民,不得齿于天下。所以威之者又如此。”元氏站在孔孟性善论的基础上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认为“仁、义、礼、智,出于天性,其为德也四;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著于人伦,其为典也五。惟其不能自达,必待学政振饰而开牖之,使率其典之当然,而充其德之所固有者耳”(注:卷三十二《令旨重修真定庙学记》。卷三十五《清真观记》。),主张全民大教育:“先王之时,治国治天下,以风俗为元气,庠序党术无非教,太子至庶人无不学,天下之人,幼而壮,壮而老,耳目之所接见,思虑之所安习,优柔于弦诵之域而厌饫于礼文之地。……故以之为俗则美,以之为政则治,以之为国则安且久。”(注:卷三十二《博州重修学记》。)他把兴学养士视为弘扬道统的根本:“庠序党塾者,道之所自出也;士者,推庠序党塾所出之道而致之天下四方者也”(注:卷三十二《博州重修学记》。),郑重提出“夫风俗,国家之元气:学校,王政之大本”(注:卷三十二《令旨重修真定庙学记》。卷三十五《清真观记》。),“学校所在,风俗所在”(注:卷三十二《寿阳县学记》。),把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的“学政”提到至为重要的位置。
元好问针对中原板荡几十年,纪纲礼乐荡然不存的社会现实,对《礼记·学记》所载“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精神作了系统的论述,把它看作当务之急和长久之计的核心所在,并就如何以文教立国,以图长治久安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在经济方面,提出国家通过立法为兴学提供坚实的基础;(注:卷三十二《东平府新学记》:“古者井天下之田,党庠遂序,国学之法立乎其中。”)在行政方面,“兴学之事,贤相当任之,良民吏当为之”(注:《归潜志》卷九。)。这些观点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四、取精用弘“以适改新之路”的文化传统整合观
忽必烈所说的“金以儒亡”,其实也并非无稽之谈。钱钟书《宋诗选注》304页注金以儒学误国, 征引了杜本《谷音》卷上金遗老程自修《痛哭》诗句:“乾坤误落腐儒手,但遣空言当汗马;西晋风流绝可愁,怅望千秋共潇洒。”东晋人看到“中原倾覆”“神州陆沉”都是崇老庄尚“清谈”的恶果,金遗老把腐儒空言与“清谈”相提并论,由此可知当时文人对执政诸儒批评之激烈。河朔丘墟、金廷南渡后,君主宰执无越国勾践报仇雪耻之心,文坛上也乏南宋爱国诗人那种驱敌复土、壮怀激烈之气。主盟诸人固然无权参与军国大事,但在大敌当前、灭顶之灾迫在眉睫的形势下,仍大谈儒佛道三教之异同,无补于时,确有空谈误国之弊。元好问在金亡前后的所作所为,文人们赞誉的虽多,毁谤的也不少。其所以如此,也因不同的评判标准所致。凡此种种不切时要、不合时宜、墨守成规、不务实用的文化观念,皆在元氏的排拒之列。在中原大坏几十年、蒙古统治者渐趋注重文治之际,文化传统将如何重新整合建构呢?纵观二千年来的儒学发展史,其间道路曲折,门派林立。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历代名儒都对儒学作了相应的调整改造,使之以不同的方式服务于社会。对此,元好问有深刻的体认:“窃以穷则变,变则通,圣人之道所以亘万世而无敝。”(注:卷四十《南宫庙学大成殿上梁文》。)至于如何变通,他提出“若人者必当戒覆车之辙,以适改新之路”(注:卷三十二《东平府新学记》。),“淫言詖行诡怪之术不足以辅世者,无所容也”(注:卷三十二《东平府新学记》。),主张惩前毖后,革除弊端,取精用弘,务为实用,以服务于时代。
首先,元好问根据时势的需要,对儒家的“仁”、“忠”作了重新认识和重大调整。他阐述人生价值观时说:“死生之际大矣!可以死,可以无死。一失其当,不以之伤勇,则以之害仁。然自召忽、管仲折衷于圣人之手,斯不必置论。……夫惟志士仁人知所以自守也,不汩于义利之辨,不乖于云就之理。端本既立,确乎不拔;静以养勇,刚以作强。……语有之:‘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信斯言也!匹夫为谅,自经于沟渎,其可与求仁而得仁者一概论乎!”(注:卷二十七《恒州刺史马君神道碑》。)管仲没有为公子纠殉节,后来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尊王攘夷”,不仅维护了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声誉,更重要的是维护了诸夏的文化、习俗,使中原人民得有安宁的生存环境。孔子认为这是大仁大义,远非“自经于沟渎”者所能比,体现了个体对整体华夏民族利益的社会责任高于忠君的价值观念。此后孟子从“以民为本”的思想出发,提出“忠君、忠国、忠天下”之说,其价值取向更加明确,自儒家学说成为封建帝王的统治工具后,忠君这一价值筹码不断升值,成为衡量褒贬人物的最重要的标志。在金亡前后,元好问从儒家人道主义出发,其价值观由忠君、忠国调整到救世活人这一终极目标上来。当金哀宗出奔、汴京更加危急之际,元氏为了使京城百万生灵免遭屠城之祸,上言二执政,谋划改立荆王,献城出降;当崔立兵变,“省庭日流血”,其党羽威逼朝官、士人撰写功德碑时,元氏为了使这些文士、朝官免遭横祸,又积极主动参与以促成此事;蒙古兵入汴时,元氏又冒然上书中书耶律楚材,恳请保全救护中原士人。从这些行动可以看出,在中原生灵将被杀戮殆尽之际,元好问站在民生的立场上,把保全人命视为第一要义,其它如忠君爱国之类价值观皆从属于此,即使投降求全也在称道之列(注:卷三十《濮州刺史毕侯神道碑铭》载:“丁亥,国兵围益都,城中食尽,保宁(李全)计无所出,闭户将自经。侯排户直前,曰:‘公死城即破,大兵一纵,城中呒噍类矣!太师日望公降。公降必不死,保惜屈一身,而不为数十万生聚之地乎?’保宁悔悟,随诣军前。太师受其降,悉以全境付之,而不戮一人,竟如侯所料者。”)。因此,他不顾时人及后人的诟骂,不为传统的君臣大义、个人名节所羁囿,“立心于毁誉失真之后而无所恤,横身于利害相磨之场而莫之避”(注:卷三十八《写真自赞》。),这实在是那个特定时代孔孟所谓大仁大义的具体表现。
其次,元好问根据时代的需求,对儒家学派——理学给予严厉的批判。理学家忽略了孔孟忧时济世的精神,究心于“天理人欲”,肆言于“格物致知”,对此元氏是深恶痛绝的。他在中年时就对程、张自立门户,诋毁“文以载道”的做法表示出强烈不满:“学道有通蔽,今人乃其尤。温柔与敦厚,扫灭不复留。高蹇当父师,排击剧寇仇。……先儒骨已腐,百骂不汝酬。胡为文字间,刮垢搜瘢疣。吾道非申韩,哀哉涉其流。大儒不知道,此论信以不?我观唐以还,斯文有伊周。开云揭日月,不独程、张俦。……九原如可作,吾欲起韩欧。”元氏晚年离燕京时,著名理学家赵复赠言,以“博溺心,末丧本”为戒(注:《元史·赵复传》。),望其专心致力于心性的修养。对此,元氏也不以为然(注:凌廷堪《遗山先生年谱》。)。后来,元好问在《东平府新学记》中集中抨击了理学之弊;认为它绝不可用来治国,儒者“必当戒覆车之辙”,改革不切时要的弊端,“以适改新之路”。他的这一指导思想直接影响了郝经、许衡等元初理学家,使元代的理学呈现出重实用、轻虚浮的时代特色。
再次,元好问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对道、佛中有补于世的学说给予充分肯定。元氏处于三教合流的时代,对道、佛二家的学说有深入的了解。特别是中原板荡之后,他于宗教有补于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重构以儒为主的文化传统中,对佛教救世活人的业绩予以热情的赞美。他自己忍辱负重,矢志不移地推行圣道,也可以说是佛家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一献身精神的表现。
从以上的勾稽中可以看出,元好问虽然没有像董仲舒、朱熹等汉宋大儒那样对其儒学理论作系统严密的表述,但他以救世活人存文保道为核心,从务为实用的角度出发,继承弘扬了先儒们经世致用的思想,兼收了道、佛中有补于世的精华,基本上构成了整合文化传统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集中体现了中原板荡几十年之后社会各阶层对久乱思治的深切愿望,(注:金元之际儒士杨叔能《事言补》云:“老氏、释氏吾有取乎?曰:有。老氏,吾取其佳兵不祥;释氏,吾取其戒杀。”见鲜于枢《困学斋杂录》。)因而能够联合中原知识分子(包括佛、道人士),结成广泛的思想文化阵线,以全方位地合力推动蒙古上层建筑的变革,加快历史的进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文化传统自身发展的历史看,元好问没有多少新的理论建树,他的功绩在抢救和培育了一批优秀士人,维系了文化传统的命脉,对文化传统作了适当的扬弃和整合,使之适应了时代的需求,可以说是文化传统的勇猛卫士和卓越功臣。
元好问站在中华文化一统观的高度,承认少数民族一统华夏、承继正统的合法权益,在政治上形成蒙古贵族与中原士人联盟;在施政方面,他主张以学政为主、刑政为辅,实行文治,以保长治久安;在文化阵线上,他继承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力求改革无补于时的弊端,吸收道、佛二教的精华,结成了广泛的文化阵线,以推动蒙古贵族的文明进程。元好问的这些思想举措,达到了那个时代所应有的高度,完成了时代所赋予的责任。忽必烈在征大理、并南宋的战争中,姚枢、徐世隆等中原士人竭力阻止其滥杀,遂使再没有出现蒙古攻金时那样的浩劫。文人积极应用传统文化来救世活人,成为那个时代的潮流。可以这样说,忽必烈时期的吞并南宋,已属同一文化形态下的中华民族内部的统一战争。这一巨大的历史进步,是有元好问的一份功绩的。
标签:元好问论文; 儒家论文; 中原文化论文; 蒙古文化论文; 中原论文; 国学论文; 读书论文; 学记论文; 元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