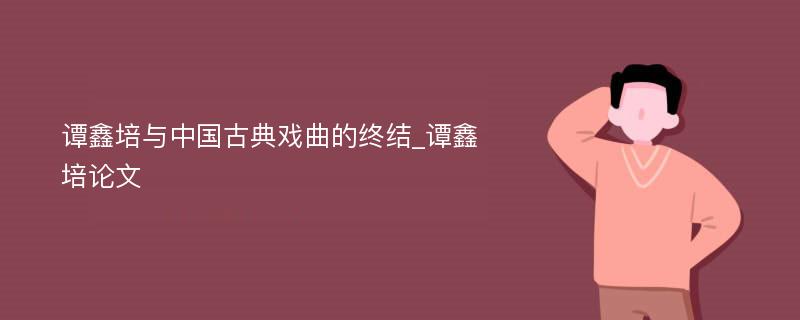
谭鑫培与中国古典戏曲的终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曲论文,中国古典论文,谭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补续前文,特别需要申明的是,我绝非是说程长庚的“雄风”之声就是与古典性无关;果然如此,那就致古典性于“偏废”而非“偏胜”了。这里所作的种种分析,只是要进一步证明前文之所说,即京剧在程长庚初创时,曾经存有背离古典精神的可能,而这其中有它相关的多种条件。首先是在东西方文化的对应发展中,从文化形态的角度看,中国文化中的壮美、阳刚之气更有可能与西方文化“接轨”,其次是在社会形态上,晚清的西风东渐所带来的整个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给这种“接轨”提供了契机。换言之,阳刚之气在这里只是个必要条件,没有特定的社会因素,它只能是在既成的古典范畴系统中,而不可能越出,去对应更大系统中的相关文化形态。不然,汉唐艺术多偏于雄健,岂非早就突破古典美了?正是在有了相关社会形态条件的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程长庚张扬的“雄风”之声,至少在客观上是一次走出古典主义壁垒的尝试,一次对古典美的冲击。不过,这次尝试,这次冲击最终还是未能成功。
这里还须特别指出的是,程长庚的未能成功,表明了在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中,艺术并不总是社会的“奴仆”,而是有其自身的要求。“柔靡”的胜于“雄风”,显然是中国戏曲古典性发展的顽强要求的结果,亦即是合于美感逻辑演进的一个必然。这是因为,作为“雄风”的初始之音,其美感是较少的。表现为,一是形式因素较弱,显得贫乏单调而意味不足;一是情感因素较强,流于粗犷朴实而美感不足。谭鑫培的所谓“柔靡”之音,正是应时而生,它是京剧在自身成熟发展的过程中,加强形式因素,弱化情感因素,从而将美感扩大、提升的一次重大突进。谭鑫培所以能赢得“无腔不谭”、“满城争说”的局面,根本原因即在此。
还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所谓谭鑫培偏于“阴柔”,不等于就无“阳刚”;说程长庚偏于“阳刚”,也非即少“阴柔”,这些都只是相对而言的。所谓“柔靡”与“雄风”,也不是“一锤定音”、真如程长庚所说“中国从此无雄风”;换句话说,谭鑫培的“柔靡”亦有其弊端,“亡国音”是不能总唱下去的。事实上,这种偏向不久即得到某种程度的厘正,余叔岩发而为“清刚”之气,“劲拔”之声,即是。不过,那就是后话了。
程长庚的不成功,也许延缓了中国戏曲的近、现代化的发展,从这个层面看,谭鑫培的接续古典主义便是一种倒退了。然而,从构筑一个完整的中国古典戏曲体系的层面看,谭鑫培拨“乱”(“乱弹”初生时之带有的初始之音)返“正”(经整合、规范后的典雅之声),从而为中国文化,扩大而言之,也是世界文化,保留了一份最为形象、生动,既博大又精深的古典艺术的遗产。未尝又不是一次进步。就此而论,程长庚的冲击遭挫,确乎是中国戏曲近、现代化的一个不幸;然而,却又未必不是中国古典戏曲之有幸。而从假以时日,中国戏曲的近、现代化终能成功,而中国古典戏曲的完整性能否构成却只在那稍纵即逝的历史一瞬间,谭鑫培能拨“乱”返“正”,则更是幸甚!幸甚!
由此我还想到,古典戏曲之有幸,又是因国家之不幸——近代化之曲折发展——所带来的;莫非艺术真要如赵翼之所言,须在“国家不幸诗家幸”中衍生?
由此我又进而想到,在中国跨入现代化进程的今天,我们也许应该赓续程长庚之未竟事业,像他那样打破戏曲的古典性,使京剧走向现代化;复又转念,只是彼一时此一时也,既然历史已艰难地造就了京剧这座古典艺术的“大厦”,我们又何苦将它击碎呢?更何况其由历史付出之巨大代价才得以换来,我们不是更应该珍视它吗!
作为跨越时代和世纪的人物,在戏曲艺术的古典性终结与近(现)代化发展的两难选择中,谭鑫培促成了前者,延缓了后者,他就扮演了这么个历史“角色”。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