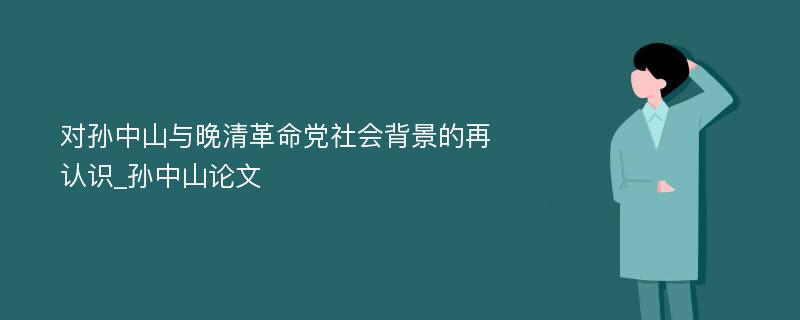
孙中山与晚清革命党人社会背景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党人论文,晚清论文,背景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8;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12-0027-08
是资产阶级吗?
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是他率先举起革命大旗,向清王朝的专制皇权挑战。然而,从1894年到1900年,他的支持者少之又少,他的起义只是昙花一现,甚至未发即败。他自己也处处受人谩骂、嘲笑。用孙中山自己后来的回忆,是“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1](p235)。他是孤独的先行者!然而在进入20世纪以后,他的境遇却大为改观,他的革命事业如一日千里般发展,终于在1912年使清王朝退位。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就革命的主动力量来说,是因为革命的领导者、参加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处在社会边缘的与中国社会联系较少的先行者变为与社会联系较广的新的追求民族主义目标的知识分子。
按照中国大陆史学界传统的主流说法,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党,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或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派”是标准的定性描述他们的概念(注:1981年在武昌召开的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便是以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为主题,即间接强调孙中山及革命党的资产阶级属性。)。
笔者80年代初开始步入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领域时,对此曾深信不疑,甚至试图找出这种说法的更多证据。但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笔者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尽管这种改变是艰难的、逐渐的。事实上,孙中山及革命党人,根本不是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代表,换句话说,资产阶级不是他们的社会基础(注:80年代以来已有一些学者对资产阶级的结构和政治态度问题提出新的看法,如1983年上海“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上,耿云志先生对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立宪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说法提出质疑;杨立强、沈渭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郭世佑:《辛亥革命阶级基础的再认识》,《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上册,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另如应用较广的大学教材《中国近代史》(李侃等著,中华书局1994年第四版)在谈到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时说:“革命派和改良派代表着同一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是这个阶级在政治上的两翼:左翼……右翼……”(第354页)不分上层和中下层,这与郭说基本相同。但该书谈到同盟会成立时仍说:“同盟会的主要成员,是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第346页)大多学者仍然坚持孙中山与同盟会是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代表。)。
如果说孙中山与他领导的革命党是民族资产阶级或其中下层的代表,那么必须在孙中山组织兴中会的时候(也正是维新运动发轫的时候),中国就有了一个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已经如此成熟,不仅已经分化出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甚至在民族资产阶级之中,又分化出上层和中下层。而这实际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甲午战争之时,中国还只有少得可怜的现代经济!它不可能支撑起以这种经济为背景和活动舞台的新阶级(注:参见林增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于何时》,《湖南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更何况,孙中山和他的兴中会同志们与中国现代经济最发达的上海地区的资本家几乎处于隔绝状态。
那么,进入20世纪以后如何呢?笔者仍然认为,20世纪初,孙中山及其为领袖的同盟会,仍然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诚然,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的时候,上海、武汉、天津、广州、无锡等城市,确实有了一些近代企业和企业家,如果算到1911年,也就是辛亥革命爆发这一年,他们的数量就更可观一些。然而第一,这些资本家们决非革命的主动者和领导者,这只要列举一下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物和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革命党人物就可以清楚;第二,如果说,那些革命者本身虽不是资本家,但他们是资本家们的代表,这种说法放到上述少数现代企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尚有探讨的余地,但是在广大的内地,在那些甚至要用放大镜才能找到现代资本家的地方,如云南、贵州、广西、四川、陕西、山西、江西等地,革命党人也相当活跃,上述说法就很难自圆其说。像湖南这样的著名革命领导者很多的地方,现代企业也很少。当时中国的领土有一千多万平方千米,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没有资本家的地方,革命者代表谁?况且,如果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只是代表那人数少得可怜的资本家们的利益、要求,而无关全中国人的利益,那么不但这革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甚至其正义性也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凡正义性的事业,可以不为大多数人理解,但必须是对多数人有好处。第三,我们再比较一组经济数据。晚清时代的经济统计极不完备,国内生产总值、工矿业及近代交通金融业这些现代经济部分的总产值几乎都无从谈起,但从我们可以见到的若干数字也能看出一些问题。1895年到1911年,整整16年中,国人创办的资本超过万元的近代民用企业只有490家,总投资额11131万元。而1910年一年的进出口总额,即达84400万海关两(进口46300万两,出口38100万两)[2](p184-218)。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近代企业还包括了官方拥有和官方控制的企业在内,如果只算私营企业,就更少了。1901年《辛丑条约》签字,条约规定中国向列强各国的赔款总数为白银四亿五千万两,这个数字也远远高于16年的总投资额。我们再比较一下财政收支。宣统二年,清政府试办财政预算,经过资政院修正公布的宣统三年预算岁入为30191万余两,岁出为29844万两[3](p565)。16年的总投资额尚远不及一年的财政收入,远不及一年的出口。当时的预算与实际财政运行状况有相当大的距离,但大体可以说明问题。这些数据说明现代经济只占全国经济的很小部分。将少量的私人拥有的现代经济放到传统的经济体系中,那就只是汪洋中的一艘船。要这一艘船的拥有者和操纵者来搅动整个海洋(领导辛亥革命),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最多是在海洋中航行和趋利避害(见风使舵)而已。
今天看来,中国大陆史学界以往常说的资产阶级,是个极为模糊、笼统而又自相矛盾的概念。当人们谈论资产阶级的来源(惯常的说法为官僚、地主、商人包括买办)的时候,谈论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既抗争又妥协)的时候,实际指的是现代企业家;但当人们讨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些政治运动或其领导者参加者的时候,所用的资产阶级概念,又极为广泛,不仅包括了现代企业家,而且包括了一定程度接受新观念的士绅、学堂学生和教师、留学生、科技人员、报刊杂志社工作人员、新军军人甚至某些政府官员(注:笔者的硕士论文中,也曾将某些倾向改革的政府官员作为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人物。见《端方与清末宪政》,《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九辑,中华书局1997年出版。这篇论文发表于90年代,但写作是在80年代中期。)。这种笼统的说法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都不同。翻开马克思主义最权威的经典著作之一《共产党宣言》,在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下面,恩格斯加有一段注释:“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4](p250)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对资产阶级的解释是“占有生产资料剥削雇佣劳动者以榨取剩余价值的阶级“[5];另一部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写的是“占有生产资料作为资本以榨取雇佣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资本家阶级”[6](p328),后两者基本相同,应是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实际上,这些解释与西方学术界现今对资产阶级概念的理解大致相同。显然,以往中国大陆史学界所理解的资产阶级与上述定义相比,太过宽泛,而且一本书中甚至一篇论文中概念前后都不一致。
不仅如此,关于资产阶级结构的划分,更是模糊、随意。我们向来把资产阶级划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又分为上层和中下层。但是,究竟什么叫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什么叫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中下层是以财产划分还是以社会地位划分?其中有些问题已有学者提出质疑,但大都还为学术界习惯沿袭。对资产阶级按照不同的特点划分,研究其经营、管理、政治倾向、社会活动及其影响,完全是必要的,但如果机械地贴政治标签,则不可取。
限于论文的篇幅和主题,笔者不能对现代经济问题展开更多论述,而较多直接从革命领导者和参加者的出身及社会背景立论。
孙中山出生地:边缘地带?前沿地带?
既然讨论的是革命党人的社会背景,我们就先从革命党的领袖孙中山谈起。
众所周知,孙中山1866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翠亨村处于珠江三角洲,离澳门只有三十多公里,体力较好的成年人步行一天便可以从翠亨村到达澳门。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珠江三角洲是西方势力和西方影响都率先渗透的地方,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最先对外开放和感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地区,也是这里的人率先背离中国传统,倡导学习西方。另一方面,这里与北京距离遥远,又是偏远和清朝统治薄弱的地区,造反和革命者容易在这里滋生和成长。最早的中国留美学生之一,并且是第一个获得美国大学学位的学生容闳,出生地在南屏镇,比翠亨村更靠近澳门(今属珠海特区)。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冯云山和洪仁玕出自花县,算是珠江三角洲的边缘。洪仁玕还写下《资政新篇》,主张学习西方。以后,维新运动的倡导者康有为是南海人,梁启超是新会人。算是孙中山的老师、被人们称作早期启蒙思想家之一、居住在香港的何启,也是南海人。出身买办商人,后来进入李鸿章等创办的洋务企业工作,也被人们称为早期启蒙思想家的郑观应是香山人。我们注意上述人物的出身背景,会发现除了康有为和梁启超外,他们都没有传统的功名——进士或举人,换句话说,他们没有传统士大夫的地位和经历,当然他们的学识并不低下贫乏,只是他们是从另一个途径获得知识的,他们已经背离或正在背离传统社会。由以后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也正是如此。以色列学者史扶邻把他们称之为“边缘集团”(注:见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但是换一个角度,笔者更愿意把他们视作前沿人——率先接受外来影响的前沿地带的前沿人。
笔者就已故陈旭麓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出版)中所收录的籍贯在香山、南海、顺德、新会、番禺、花县、佛山、三水几个县的人物(除个别外,出生时间限定1800-1890年)做粗略的统计(不包括孙中山自己)。该辞典共收这几个县的人物96人。其中有进士功名的只有6人,占96人的6.25%;而在国外留学成就很高的就有5人,他们是容闳、伍廷芳、何启、詹天佑、王宠惠,他们都获得了货真价实的现代教育学位;在海外有学习、经商经历和华侨39人,占40%;参加过晚清革命或太平天国等造反的有56人,竟占58%,仅黄花岗起义牺牲的就有16人;相比之下,有过任官(包括军官)经历的只有18人,占19%,而这18人中还有如下情形:清新军高级军官许崇智是同盟会员,做过知县的陈景华后来参加革命,侍郎级的伍廷芳和高级军官徐绍桢在武昌起义后站到革命阵营。
上面的粗略统计说明了一个事实:这里不仅是中国传统和现存秩序影响的边缘的和薄弱的地带,是西方影响率先登陆的地方,而且有着最适合造反者和革命者成长的土壤!中国最早的革命先行者在这里诞生决非偶然!
孙中山的求学:西式启蒙
孙中山的早年经历,早已为人们熟悉,似乎已无需多费笔墨。但是,为了说明作者的想法,还是需要对他的早年生活和经历作一番描述。
本来孙中山的家庭是比较贫寒的,由于哥哥孙眉在檀香山经营的成功,才使孙中山家的经济状况大为改观。1879年,孙中山到檀香山投奔他的哥哥(注:关于孙中山赶檀香山年代,有不同说法,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24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他在这里进入英国教会办的意奥兰尼学校学习,这所学校全部用英语教学。1882年毕业后,他又入夏威夷群岛的最高学府奥阿厚书院学习,这是美国教会办的学校。
在到檀香山之前,因为家境并不富裕,孙中山9(周)岁才进村塾读书,时间只有两年,大概只能读到《三字经》、《千字文》之类较简单的入门书。孙中山自己就说:“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7](p359)换句话说,孙中山在少年时代没有接受传统士大夫们都要接受的儒家教育,至少是没有系统接受儒家教育,反倒是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的教育。孙中山对西式教育相当着迷,这从他在奥阿厚书院学习不久,就想正式接受洗礼入基督教一事上可以反映出来。
由于哥哥孙眉强烈反对孙中山入教,孙中山于1883年回到中国。但是回到中国的孙中山并没有研习传统学问,而是到香港的学校读书,在当时绝大多数读书人仍在努力研读八股,争取考科举的氛围下,孙中山的做法是耐人寻味的。因为这时他的家庭已完全有经济能力让他学习儒家经书和八股文,以便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可以进入上等人的社会,可以获得一官半职。须知此时包括南海人康有为(比孙中山大八岁)在内的多少读书人都正在这条路上辛勤跋涉。而孙中山也完全有可能走通这条路。是孙中山自己对科举丝毫不感兴趣吗?是兄长孙眉的支持吗?还是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曾在澳门当过鞋匠——的意愿?可能都有。这一点足以说明孙中山周围的人的价值取向。当孙中山1892年从西医书院毕业时,他已经26岁了。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孙中山的汉文阅读能力甚至不如他的英文阅读能力。直到1894年上书李鸿章的时候,他的文章还需要陈少白等人的润色。他最初阅读中国古典文献,需要先读英文的,然后再读中文的。如果说孙中山周围的文化氛围首先影响到他的话,那么早年的孙中山没有接受系统的传统教育这一事实,则对他以后选择反清革命的人生道路进一步发生影响。
1894年,正是甲午战争爆发那一年,孙中山写了一封约8千字的《上李鸿章书》。通览孙中山的上书,思想内容和深度并没有超出一再上书皇帝的康有为,建议的系统性和语言的迫切也不如康有为。本文感兴趣的并不是他的上书本身,而是他上书失败后与康有为完全不同的选择。孙中山绝对不是遇到挫折就退缩的人,从他以后的经历我们应该明白,他反倒是一个屡败屡战、愈挫愈勇的人,那么,是什么使孙中山一次上书不成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康有为却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书以求得皇帝的支持?这还要到他们的经历中寻求答案:孙中山少受传统的儒家教育,他不是传统的士大夫,他的头脑中根本就没有传统的那套忠君观念。所以,他不同于康有为,上书不成,他立即开始了另一方面的活动。
从以上两节的探讨,我们可以说,使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的,是他的出身和教育、地域文化背景,而不是他与资产阶级的联系。因为通观孙中山到甲午战争为止的活动,孙中山并没有与企业家打交道的经历,至于国内资本家的团体就更不存在(注:相当多学者按照孙中山的回忆将其革命思想的形成放到中法战争时,果真如此,那时国内更谈不上有个资产阶级。)。
兴中会:背离传统社会的少数密谋者
1894年秋,在孙眉的支持下,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成立兴中会。
1895年,孙中山与以杨衢云为首的辅仁文社联合成立香港兴中会。
让我们考察一下兴中会骨干的出身和经历背景。
杨衢云(1861-1901年)比孙中山大五岁,是兴中会领袖的竞争者。他原籍福建,出生于香港。他在香港的英国人办的学校读书,毕业后在香港担任英语教师、招商局职员、外国洋行职员。从他的经历看,他也像孙中山一样没有受到过系统的传统教育(注:史扶邻指出,杨衢云对政治的兴趣,是在一种比孙中山更为欧化的背景中成长起来的。杨衢云的反满思想比孙中山还早。见《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41页。)。
郑士良(1863-1901年),广东人,比孙中山年纪略大。他与会党有广泛的联系,但是他的求学也是在广州和香港外国人办的学校,曾与孙中山为医校同学,并且也受洗入基督教。
陈少白(1869-1934年),广东新会人。在孙中山的朋友圈中,陈少白受的传统教育算是比较多的,所以中文的功底比较好。1888年他19岁的时候,入美国传教士在广州办的格致书院,次年入基督教。1990年,陈少白结识孙中山,由于孙中山的怂恿,陈少白也入香港西医书院学习。
陆皓东(1868-1895年),与孙中山同出生于翠亨村,少年时代即为好友。陆皓东在上海就学于电报学堂,毕业后进入电报局工作。他与孙中山同时受洗为基督徒。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陆皓东随行。
谢缵泰,原籍广东,出生于澳大利亚,在香港政府当职员。他也是基督教徒,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他是辅仁文社成员,杨衢云的挚友。
邓萌南,大孙中山20岁,檀香山华侨富商,离开檀香山回国进行革命活动,并变卖家财充当革命经费。
黄咏商,香港商人,其父即与容闳一同去美国留学的黄胜。
其实,兴中会还有一位幕后的总军师,他就是香港议政局议员、律师何启。何启是广东南海人,在英国学的法律,可以说是一位西方式的绅士,由于与胡礼垣合著有《新政真诠》一书,被现在的历史学家列为早期启蒙思想家之列。
这里列举的兴中会骨干之所以以香港兴中会为主,是因为檀香山兴中会的政治宗旨不够明确。檀香山兴中会的会员,除个别人外,大多数并没有参加后来的革命运动,包括其正副主席刘祥与何宽在内(注:对于大多数会员来说,檀香山兴中会可能是一个类似甲午战后国内维新派人士创办的宣传改革的团体,而只有少数人知道孙中山的真正意图并支持他的革命。参见林增平:《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第一部分,《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上述这些兴中会骨干,有一些明显的共性:第一,他们与孙中山一样没有受过系统的中国传统教育,他们所拥有的是有关西方的知识和技术。第二,与前者相关,他们没有进士举人甚至秀才的传统功名,因此,他们不但不能被传统士大夫认同,甚至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群没有文化的人。第三,他们没有显赫的家族和地位。第四,他们大多是孙中山的同乡广东人,或广东的出国华侨。第五,他们大多是基督教徒。由于所受的教育、出身、地域,他们是最容易萌生反抗现存体制思想的一群人。
兴中会的基本群众,是旅居海外的华侨和国内他们能够影响得到的部分会党。有学者根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的不完全记载,对1894、1895年参加兴中会的178人的身份背景作了统计,其中商人96人,工人39人,会党12人,自由职业者9人,公务员10人,农牧等6人,军人4人,学生2人。而其中79%是华侨[8](p90)。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商人,并非近代企业的经营人,在这96个商人中,没有一个是产业资本家,他们大多是小店主,有的不过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个体户”而已(注: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第25-4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武装起义依赖的力量,主要是会党。但会党不是兴中会的社会基础,而是作为一种可利用的对于现存社会秩序的破坏力量。孙中山等人走上革命道路,也决非会党的影响。
显然,兴中会的基本群众与骨干的出身背景非常近似,这些人不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之中,而是游离于传统社会体制之外。
从以上这些人的出身背景,我们还可以说,1900年以前的兴中会,是个在国内缺乏社会基础的组织,这些背离中国传统的人物只局限在珠江三角洲这样的地区和海外华侨中(注:冯自由说,兴中会存在期间,会员总数不满500人。见《革命逸史》第四集,第64页。)。康有为的变法固然由于社会基础薄弱而失败,而兴中会革命比康有为变法的社会基础还要薄弱,士大夫们把这一小撮革命者当作洪水猛兽,所以兴中会的革命在1901年以前闹不起来几乎是必然的,甚至不能发动一次像样的起义。孙中山只是孤独的先行者,他真正发动起革命还要等待中国社会的一些变化。如果没有庚子事件对清廷的打击,没有后来的晚清新政对社会的重大影响,孙中山、杨衢云的革命可能就是孤独的绝响。
我们把上海与珠江三角洲做一下比较,就会印证孙中山及兴中会的活动与资产阶级无关。1900年以前,中国为数有限的新兴企业家差不多都集中在上海,与他们联系较多的知识分子也集中在上海和江浙一带。如果说孙中山和兴中会是资产阶级,他们的活动和出身更应该在上海和江浙而不是广东。
新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产生
1901年以后,事情发生了变化。
从这一年开始,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
新政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推广新式教育。
由于新学堂的设立和留学运动,产生了一个在晚清和民国初极为活跃的社会阶层,他们就是新学堂的学生和留学生,他们的活动给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们有的曾受过相当不错的传统教育,其中不少人是秀才。进入20世纪初,在清政府致力新政,列强的侵略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他们猛然抛弃了旧八股学问,而从事新知识的学习。他们受过传统的很大影响,但正在背离传统。就曾受过传统教育,因而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这一点,他们与孙中山、杨衢云等兴中会骨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批新知识分子有什么特点呢?他们的思想核心和奋斗目标是民族主义。这民族主义是双重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希望中国摆脱落后和受欺辱的地位,进而反对以至试图推翻清朝的统治(注:应该承认,新知识分子中,也有不少人不反对清王朝,他们参加到立宪派的行列,有些人甚至到清政府中任职。但是不能否认,他们的主流是民族主义,即反帝反满的双重民族主义。又,反对帝国主义和反满(也即反对现存统治)的关系,是尚未充分研究的问题。我认为,反满相当大程度来自反帝。也可以说,反帝强国是所有新知识分于的强烈愿望,而反满则是其中的大部分人的追求。)。在他们的心目中,推翻了清王朝,由汉族人来领导国家,中国就可以转弱为强。其中一部分人认为,建立共和制国家是中国的惟一选择。
1903-1905年,是新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关键3年。而其转变的关键又是影响深远的拒俄运动。中心人物是在日本的留学生和上海的新学堂里的教师、学生。
1903年,留日学生已有1242名;1904年有2557名[9](p196-197)。他们大多是20岁上下的年青人。人数虽然不多,却是中国最活跃的一群。年青人活跃、敏感、容易激动、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观念,他们掌握的新知识在中国社会的各种人群中是最多的。就在这几年,他们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众所周知,1900年,沙皇俄国趁八国联军进军北京之机占领了我国东北的大城市和铁路干线,按照后来中俄签订的条约,俄军应分期撤出东北。但到1903年第二期撤军时,俄国不但不撤军,反倒提出七项无理要求,企图永远霸占中国东北。消息传开,以留日学生、上海教育界人士及学生为主,掀起拒俄运动。留日学生组织了拒俄义勇队,稍后改名学生军,进行军事训练,准备回国参军,与沙俄决一死战。不久学生军又改名军国民教育会。由于清廷压迫这些学生,说他们名为拒俄,实则革命,愤怒的留学生日益倾向革命。在上海,情况也与此类似。这说明排满风潮的兴起与反抗列强的斗争有密切的关系。在这以前,学生们大多是梁启超的信徒,这以后,倾向革命的越来越多。
我们以湖南出身的黄兴、陈天华、宋教仁,浙江出身的蔡元培、章太炎和广东出身的汪精卫、胡汉民为例来分析这些倾向革命的新知识分子骨干人物的特点。
黄兴,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秀才,善诗词。1898年入武昌湖广总督张之洞办的新式学校两湖书院读书。1902年为张之洞选派赴日留学。他在日本参加了拒俄运动,并作为军国民教育会的运动员于1903年回国。他很快组织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成立了华兴会。华兴会骨干除黄兴外,还有章士钊、刘揆一、宋教仁、胡瑛、周震鳞、秦毓鎏、陈天华、杨毓麟、刘道一等,他们主要是湖南人,经历与黄兴非常相近。
陈天华,湖南新化人。自幼家贫,但他天性爱好读书。民间少有艰涩的儒家经典,所以他读的多是民间话本弹词之类。1902年赴日留学。拒俄运动中撰《猛回头》、《警世钟》。他的文笔通俗流畅,贩夫走卒之流皆可读懂,而又充满激情,所以影响特别大。
宋教仁,湖南桃源人,生于书香之家,秀才。1903年入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文普通中学堂学习。黄兴自日本归国,在武昌宣传革命,教仁与之结识,遂相约投身反清革命。宋教仁攻边疆史地有心得,后又曾研究王阳明心学,再加上秀才的资格,说明他的传统学问有相当的功底。
章太炎,浙江余杭人,书香门第。太炎少从外祖父及父亲读书,治文字音韵学。23岁拜名儒俞樾为师,受业七年。以后成长为学术大家,后人称国学大师。同盟会中,论传统学问之精深,当以太炎为首。
蔡元培,浙江山阴人。自幼饱读诗书,1892年成进士。甲午战败后倾向维新,尤服谭嗣同。变法失败后,蔡立志投身教育事业。1902年与友人创办爱国女学、中国教育会,复创办爱国学社。光复会成立,蔡为会长。而进士竟为革命党领袖,蔡元培实为第一人。
汪精卫,广东三水人。自幼熟读经史,曾当过塾师。1904年考取官费留日学生,就读东京大学学法政。
胡汉民,广东番禺人。少有才气,1902年中举,次年赴日留学,其间一度归国任梧州中学教习。1904年,与汪精卫、朱执信等再赴日,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
综合上述诸人,有这样的特点:第一,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先学中学,后学西学。第二,比起兴中会领导人,他们与社会各阶层有更广泛的联系。第三,他们不限于珠江三角洲这样的传统文化和地域的边缘地区(或接受西方影响的前沿地区),而是来自全国各地。
1901年以后加入革命阵营的革命青年(章太炎和蔡元培年纪较大),是在庚子以后沉重的外患,特别是庚子事变的刺激和新政影响这双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由新教育而产生,是新政造就的新人。他们是新的社会精英——即将取代传统绅士阶级的新的社会精英。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同时反满,其中部分人接受共和主义,但反帝反满也就是民族主义始终是他们的最主要特征。他们反帝不同于义和团,故称新民族主义。他们的成长,代表了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一个阶段(注:笔者以为,从整个近代中国看,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甲午战争以前还处于低级的或萌生的阶段,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是兴起阶段,北伐及大革命时代为成长阶段,抗日战争时期为高涨阶段。),他们是中国人民族意识兴起的载体。他们成了革命的主动者。在国外,他们主要集结在日本;在国内,他们主要集结在新学堂和新军。比较之下,新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与兴中会成员有着明显的不同特点。除了人数较多之外,他们与中国社会的联系明显地多。他们不是兴中会骨干那种生活在中国社会边缘的人,而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之中,与这个社会同呼吸。因此,当他们加入革命阵营之后,才能动员社会成员投身或同情革命。
新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们不是资产阶级,与实业家们也没有多少联系。把黄兴、陈天华、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邹容、杨毓麟等活跃的新知识分子与上海有影响的资本家祝大椿、朱志尧、虞洽卿、严信厚、孙多森、王一亭、朱葆三、徐润、曾铸、沈缦云等相比,两者缺少共同点(注:沈缦云、王一亭在辛亥革命前夕加入同盟会并有所作为,但很难代表这整个阶层的动向。)。
新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不全是思想意识的原因。他们的反满,与他们自身的处境、利益有一定关系。但不是与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他们具备了社会精英的学识和能力,但他们大多没有绅士的资格,不能进入上流社会,就这一点来说,他们与兴中会骨干有一定的共同点。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政府也已不能通过给他们一个可能的仕宦前途的办法笼络他们或使他们为政府所用(注:学部、商部等新机构成立后,有部分新知识人进入这些部任职。)。另一方面,晚清最后十年新教育和留学极为迅速发展,但整个经济文化特别是现代经济部分的发展却没有给他们提供那么多合适的工作和谋生的岗位。这一切,使新知识阶层很容易变成反现存体制的力量。
我们再提上海。显然,1903年以后,上海同日本一样,成了革命者的大本营。这是因为,上海是新学堂及新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聚集之地。上海当然也是新兴实业家集中的地方,而且上海商会也领导了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但如前所说,显然新兴实业家与新知识分子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实业家们愿意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大都不愿意反满,不希望社会动荡,不想看到革命的发生,至少在1910年以前也就是国会请愿失败以前是这样。他们的政治信念,更接近立宪派。换句话说,国内革命活动的中心从广东转移到上海,除了租界提供的可以逃避清政府的迫害(香港也可以)的客观条件外,主要因为上海是新知识分子的聚集之地。
孙中山转向新知识分子与同盟会的成立
1903年以前,日益活跃的留日学界对孙中山缺乏了解。清政府为丑化孙中山,将他的名字孙文写成“孙汶”,让人看起来像个江洋大盗。由于孙中山联络的多为会党这些下层的社会边缘类的人物,有些留学生觉得孙中山非常神秘,甚至以为孙中山不识字。反过来,孙中山也认为读书人不足与谋大事,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这种情况在1903年前后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1902年,一直热心支持孙中山革命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写了回忆录性的书《三十三年之梦》,书中不少地方写了孙中山的革命事迹。1903年,华兴会骨干章士钊将其中写孙中山的部分译为汉语印行(取名《孙逸仙》),章太炎为之题辞。章士钊在序中说,孙中山是“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秦力山在书序中说:“四年前,吾人意中之孙文,不过广州湾之一海贼也,而岂知……彼独以一人图祖国之光复,担人种之竞争,且欲发现人权公理于东洋专制世界,得非天诱其衷、天锡之勇者乎!”[10](p90-91)这部小册子在倾向革命的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孙中山的威望大大提高。除了这本书外,在日本的程家柽、冯自由(兴中会员)以及日本人宫崎寅藏等也常向革命学生介绍孙中山的情况。
1903年到1904年,革命团体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相继成立。这些革命团体聚集了一批有威望的能干的青年人,而青年知识人倾向革命的日益增多,组织大的革命团体或政党的条件渐趋成熟。但是,他们需要一个领袖,资格老、威望高、对西方有较多了解的领袖,孙中山就是这样的领袖。
与此同时,孙中山也开始了组织大的革命党的活动,并且逐渐改变了学生不足与谋大事的观念,转而积极联络学生。1905年初,孙中山到比利时,与在比利时留学的倾向革命的学生史青、魏宸组、朱和中等见面并商议革命方略。据说双方争论了三天三夜,孙中山同意以后大力向留学界做工作,让留学生作革命的领导[11](p6)。
1905年,孙中山再到日本,立即着手组织大的革命党,于是同盟会很快成立,孙中山与新知识分子终于结合。
同盟会就是新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政党,而不是资产阶级的党。有学者根据现今留下来的1905、1906两年同盟会员名册,指出同盟会成立之初,留学生和一般学生占会员90%以上(注: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第63页。名册参见《革命文献》第二辑,台湾国民党党史会编纂、出版。)。那么同盟会的主要干部呢?根据冯自由所记,同盟会初期主要干部,几乎百分之百是学生(注:《革命逸史》第二辑,第139-142页。冯自由所记并不完备,如宋教仁代理过执行部庶务,冯氏就未记载。)。如果说同盟会是资产阶级政党,如何想象没有一个资本家参加的组织却能代表这个阶级?那就如同没有工人参加的工会一样不可想象。同盟会的纲领也不是资产阶级的,反满的民族主义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而得到大多数国人——包括许多社会阶层的支持,而不只是资产阶级的要求;民权主义只能得到部分人的认同,而还没有真正形成的资产阶级对此似乎不感兴趣,他们要的是权威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和民主;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民生主义则既不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更没有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资产阶级要的是秩序,希望的是给他们发展现代企业最大的空间,而不是对他们可能的限制。
同盟会骨干甚至普通会员的社会背景与兴中会明显不同。除了孙中山成为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外,原来与孙中山共事的兴中会的密谋者在同盟会中大多已退居次要地位,而内地出身的新政中成长起来的新知识分子充当了同盟会主要领导人。这决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才干超过了原来兴中会的骨干,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的出身背景更能得到广大的新知识分子和中国社会的认同。
从现有记载看,孙中山的改变,即从原来只在华侨和会党中进行革命工作,转向注目和联合国内新知识分子——也就是新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在更广的范围聚集了革命力量,成了革命事业的一大转折。这正如孙中山自己所说:“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为之开一新纪元。盖前此虽身当百难之冲,为举世所非笑唾骂,一败再败,而犹冒险猛进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满事业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过欲有以振既死之人心,昭苏将尽之国魂,期有继我而起者成之耳。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1](p237)换句话说,孙中山主要是得到新知识分子的强有力的支持而不是新兴实业家们的支持,才成就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大业。事实上,不仅在辛亥革命时期,包括在孙中山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他从未得到过资产阶级的有效支持。反过来,一个从未得到资产阶级有效支持的政治家,也很难说他是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代表。
晚清产生的新知识分子也有很多的弱点。与兴中会阶段的革命领导者相比,他们的人数的确要多得多,与中国社会的联系也的确要广泛深厚得多,然而他们的力量仍然不足以领导全社会,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反满能够得到整个社会的赞同,只有在反满运动上他们才能做到广泛的社会动员,其他目标则很难得到广泛的支持。不仅如此,这些新知识分子,也就是未来的社会精英,他们本身的政治信仰还不够确定,不够成熟。一旦反满的目标完成,甚至他们自己内部都发生很难调和的分歧:有的人信奉共和主义;有的人却更愿意在共和的名义下实行某种形式的独裁主义。民国初年,强有力政府论曾盛极一时,原因就在于此。我们常说的辛亥革命失败,此因素也占了重要的部分。
【收稿日期】2002-10-15
标签:孙中山论文; 兴中会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历史论文; 康有为论文; 民族资产阶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