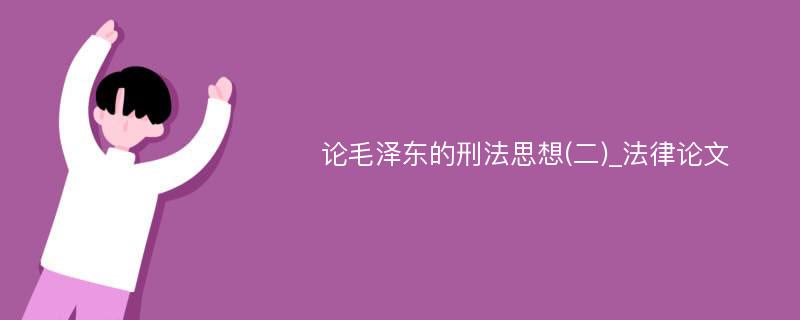
论毛泽东的刑法思想(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刑法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刑法的基本问题是犯罪与刑罚。毛泽东同志正确阐明了犯罪问题。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犯罪是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触犯刑律的行为。他对犯罪论述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对犯罪论述的继承与发展,是我国刑法规定犯罪概念的指导思想。他关于认定犯罪必须运用犯罪概念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的思想,对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 刑法思想 犯罪 刑罚
一
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之一,是掌握政权的阶级即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利益,根据自己的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并给犯罪人以何种刑罚处罚的法律。由此可知,刑法的基本内容就是由犯罪与刑罚两部分构成。任何刑法思想也不外是围绕这两个基本问题展开的,毛泽东同志的刑法思想亦是如此。
正确认定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被告人来说是国家对其行为的一种政治上与法律上的否定评价,用通俗的话来说即对其“列罪状”、“扣帽子”,定罪是劣行的记录,恶作的标志,被定罪的人必然要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压力即威慑作用。同时,定罪总和刑罚联系在一起,定罪是刑罚惩罚的前提,刑罚惩罚是定罪的必然结果。正确定罪才能给正确量刑打下基础。
正确定罪对于社会和被害人还可以起到伸张正义与安抚的作用,维护国家与人民的利益,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与此相反,如果不能正确认定犯罪,如将无罪定有罪、轻罪定重罪,或者将有罪定无罪、重罪定轻罪,都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对正确认定犯罪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同志是持非常严肃、谨慎的态度的。他曾指出:“进行镇压反革命的工作,要注意讲规格,没有规格那是很危险的,要合乎标准的才叫反革命……要完全合乎标准,货真价实,硬是真反革命,不要冤枉好人。”①毛泽东同志讲的认定反革命罪要注意讲规格标准的精神,对于认定其他刑事犯罪也是适用的,也就是认定一切犯罪都要讲规格标准。
为什么认定犯罪要讲规格与标准?用毛泽东同志的意思讲就是这样做,第一,按标准定罪,能够正确实现“货真价实”;第二,按标准定罪不会发生错误,不冤枉好人。按标准定罪就不允许随意性,各行其事。
什么是定罪的标准?孟子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②。意思是要成方圆就必须有规矩,规矩是方圆的标准。认定犯罪的标准,就是认定犯罪的准则。这个准则也就是“规矩”,笼统地说就是法律,就是刑法关于犯罪的规定,具体地说,就是刑法规定的犯罪概念。
什么行为是犯罪?什么行为不是犯罪而是合法行为?犯罪是一个阶级的、历史的范畴,因立场、角度不同和国家法律不同而不同。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把人民的反抗行为,特别是把共产党及其军队所进行的革命斗争视为政治犯罪加以镇压、他们强加给共产党以种种罪名,什么“共党”、“奸党”、“共匪”、“叛军”,为他们的镇压穿上合法外衣。他们把自己镇压、屠杀革命人民和共产党的行为,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视为合法行为。与此相反,毛泽东同志站在民族的、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认为国民党反动派出卖民族利益、反共反人民的行为是犯罪行为,在各个历史时期,彻底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是“盗匪”、“刽子手”、“战争罪犯”、“卖国贼”的罪行。他指出:“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1927年4月12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③
建国后,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从前,在旧中国,讲改革是要犯罪的,要杀头,要坐班房。”④在新中国,“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而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则是合法的行为。……在外部,放纵反革命乱说乱动是犯罪的行为,而专政是合法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正相反,那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不许革命人民乱说乱动,只叫他们规规矩矩。”⑤
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什么行为是犯罪?毛泽东同志虽然没有对犯罪概念作出表述,但是他对若干涉及犯罪的论述,表明他的刑法思想中的犯罪概念还是清楚的。他说:“什么叫‘严重违法乱纪’?就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而这种损害,是在屡戒不听一意孤行的情况下引起的。”⑥他这里使用的“严重违法乱纪”一词,实际上是指犯罪行为。他还说,对于“右派分子”一般不予办罪,“只有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屡戒不戒,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⑦。从毛泽东同志对犯罪问题论述中可以分析概括出关于犯罪概念的几个基本特征:第一,犯罪是使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行为,这说明犯罪必须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这是犯罪的本质特征,行为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就不构成犯罪。第二,犯罪是触犯刑律的行为,即犯罪行为必须具有刑事违法性。他在谈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指出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制裁的“犯法”与“法律制裁”均是指触犯刑律;在谈少数人闹事时指出的“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应当法办”,以及对“行凶犯法的人”要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都是将“犯法”“触犯刑律”的行为与犯罪行为当着一回事的。这个特征实际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在法律上的反映。另外触犯刑律要给予法律制裁,也反映了犯罪的应受刑罚处罚的特征。第三,犯罪通常是有犯意的,有主观罪过的。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屡戒不听”、或“屡戒不戒”、“继续活动”,是说明行为人不听劝阻与教育,是明知故犯。将以上特征结合起来可知,犯罪是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触犯刑律,应该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这个犯罪概念是社会主义国家正确认定犯罪和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界限的标准。
二
毛泽东同志对犯罪论述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对犯罪论述的继承与发展,是我国刑法规定犯罪概念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从事创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对犯罪现象的产生、本质与形式及其将来的归宿,都曾作过深刻、精辟的论述。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深刻指出:“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相反地,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⑧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揭示了犯罪的实质是“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其表现形式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犯罪产生的条件与现行统治产生的条件相同,即相同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又指出:“蔑视社会秩序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⑨这一句话形象生动地将犯罪的阶级性与社会性恰当地表述出来,并揭示了犯罪构成的特征。“蔑视”是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反映是有罪过的故意的行为;“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是行为人客观行为及其危害程度的描述,即行为人破坏社会秩序达到了最严重的程度;“社会秩序”是被蔑视的对象,也是行为表现最明显最极端的侵犯客体。什么是“统治关系”?什么是“社会秩序”?这二者是否不同?我们认为统治关系就是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所确认和维护的对社会实行统治的关系,它包括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所确立的各种关系。统治关系的体现就是社会秩序,有什么样的阶级统治关系,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秩序。正如恩格斯说的,社会秩序就是“由社会上一部分人积极地按自己的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极地接受下来的秩序”⑩。由此可见,统治关系与社会秩序是一致的。维护统治关系与社会秩序,与反抗统治关系作斗争的行为和禁止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就是统治阶级利益的根本所在,也就是一切统治阶级的意志表现和通过国家规定犯罪与刑罚的原因所在。
在社会主义国家,犯罪也是反抗统治关系、蔑视与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这种行为达到了最明显最极端的危害程度。因此,毛泽东同志关于犯罪的论述,即犯罪是严重危害国家与人民利益,触犯刑律的行为,必然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犯罪论述思想的继承与运用。值得强调的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犯罪的论述还有了发展。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结合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情况,把犯罪所反抗的统治关系与破坏的社会关系具体化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统治关系是人民群众居于统治者,反动阶级、阶层、集团与个人居于被统治者;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是根本一致的。因此,犯罪行为所反抗的统治关系与破坏的社会秩序也就集中危害国家与人民利益。刑法是国家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触犯刑法的行为必然是构成犯罪的行为,应当受到刑罚惩罚。
侵犯统治关系和蔑视社会秩序的行为在表现程度上有所不同。一般的违法行为如民事违法、行政违法、经济违法等也侵犯统治关系,但不是反抗统治关系,也危害、蔑视社会秩序,但不是最明显最极端的蔑视社会秩序,只有犯罪是反抗统治关系,最明显最极端的蔑视社会秩序。因此,毛泽东同志讲的犯罪危害国家与人民利益,不是如同一般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危害,而是严重危害国家与人民利益的行为,并以触犯刑律为标志。
毛泽东同志关于犯罪概念论述的思想,对我国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实践均有重要指导意义。我国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条规定,刑法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第十条规定的犯罪概念,正是体现了毛泽东的刑法思想。该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破坏社会秩序,侵犯全民所有的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这个犯罪概念是将毛泽东同志关于犯罪的论述思想具体化、条文化即法律化,揭示了犯罪的本质特征,即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对国家与人民利益的危害。具体表现了我国刑法第十条列举的两个“危害”、两个“破坏”、三个“侵犯”,以及概括性规定“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显然,行为对国家与人民的利益没有造成任何危害,国家就没有必要把它规定为犯罪而予以刑罚处罚。另外,我国刑法第十条犯罪概念也揭示了犯罪的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处罚的特征,这与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应受法律制裁和触犯刑律的犯罪特征也是一致的。因而可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将犯罪的阶级本质和法律形式融为一体的我国刑法第十条规定的犯罪概念是科学的,与其他国家刑法比较,对犯罪概念的规定也是完善的。
在我国刑法对犯罪概念作出明确规定以后,正确理解与掌握毛泽东同志关于犯罪概念论述的思想,有助于贯彻实施刑法规定,正确认定犯罪。在刑法颁布以前国家法制不健全的时期,正确理解与掌握毛泽东同志关于犯罪概念的论述思想,对正确认定犯罪更具有特殊意义。在当时刑事司法实践中,能正确理解与贯彻毛泽东刑法思想最好的要算长期从事政法领导工作的董必武同志。董必武同志精辟地指出:“一切犯罪行为都是侵害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都是侵犯我国正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它不单纯是犯罪者同被害人间的矛盾问题,而且是同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相矛盾的,是同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相矛盾的。”(11)董必武同志讲的“一切犯罪行为都是侵害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对犯罪本质论述的结晶,与毛泽东同志指出的犯罪是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行为是一致的,同时又作了展开,指出犯罪是侵犯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行为,犯罪所体现的社会矛盾不是单纯犯罪者与被害人间的矛盾,而是犯罪同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矛盾,是犯罪同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矛盾。我国刑法规定犯罪与刑罚,同犯罪作斗争,不但是为了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更为重要的是维护国家与人民的利益,维护正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
三
毛泽东同志一贯指出,认定犯罪必须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这对界限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犯罪与一般违法的界限;另一种是犯罪与错误的界限。非罪的范围是很广的,如一般违法、错误以及正确合法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都会发生这些混淆界限的情况。毛泽东同志较多的是谈到要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犯罪与一般违法以及错误的界限。例如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指出:“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12)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13)在《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中指出:“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14)。这里的意思是一般贪污行为,不构成犯罪,只批评教育,严重的如大贪污犯才论罪判刑。在《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中指出:“除了划清敌我界限之外,在内部还有个是非界限。……比如贪污分子大多数还是个是非问题,还是可以改造的,他们与反革命不同。”(15)在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斗争方面,毛泽东同志也指出:“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予法律制裁”(16),也就是违法严重者为犯罪,不严重者为一般违法乱纪。
关于犯罪与工作错误或思想错误的界限,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一文中曾指出:有的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是错误的,但“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问题”,张子善的问题是贪污犯罪问题。“财经贸易系统的110万干部和职工,绝大多数是好的,有少数人是不好的。这些不好的人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应当清除;一部分是犯错误的革命者,包括党员和非党工作人员,应当用批评教育的方法来改造他们。”(17)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反革命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问题时指出:“对于混入合作社领导机关里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加以审查、清洗和处理,是完全必要的。不过清洗的必须是真正的反革分子和真正的坏分子,不能将好人或只有某些缺点的人说成是坏人。”(18)毛泽东同志还总结了历史上的教训,指出对罪与错的界限正确划分的意义并采取正确的方针。他指出,在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19)“我们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么呢?这是表示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象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20)
毛泽东同志关于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的思想,对政法实践中认定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才能正确解决定罪的问题,进而才能正确解决刑事责任与刑罚的问题。一个人的行为如果没有实施犯罪,则不能承担刑事责任与受到刑罚处罚的。从我国的刑法任务来看,要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就必须首先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否则,如果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则不是冤枉好人,就会放纵犯罪,这样就会违背刑法的宗旨。
董必武同志对毛泽东同志关于划分罪与非罪界限的思想理解是最明确,在政法实践中贯彻也是最坚决的。他曾科学地论述道:“我们要注意犯错误和犯法的区别……。错误可以批评来纠正,犯法则一定要受法庭的审判和处罚。”(21)他还指出:“必须切实分析案情,认清事件是否构成犯罪,应否处刑;行为错误而不违法,或违法而非犯罪的,不能用司法手续处理”(22)。
彭真同志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案件时,也曾强调指出要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特别是其中的反革命与错误的界限。他指出:“这次审判,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地区分好人犯错误与坏人做坏事,区分领导上所犯的错误与林、江反革命集团所犯的罪行,这是一条根本原则。”“为什么必须严格地把党内、人民内部的错误与反革命罪行分开?因为它们是两类根本不同性质的问题。如果不注意严格地从本质上加以区别,势必扩大打击面,误伤好人”,“反革命罪行同工作、政治错误能不能分得开?难是难,但只要认真研究事实,还是可以分清的”(23)。
如何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马克思曾说过:“实际的罪行是有界限的”“犯法的一定内容就是一定罪行的界限。因而衡量这一内容的尺度也就是衡量罪行的尺度。”(24)
从总的讲,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刑法规定的犯罪概念为标准。而犯罪概念的本质特征又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因此,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主要看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与危害社会的程度。正如毛泽东同志讲到的区分贪污犯罪与一般贪污行为的界限,主要看贪污是否严重,渎职犯罪与一般违法乱纪的界限,主要看违法乱纪情形是否严重。当然,今天在司法实践中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必须按照唯物辩证法,依据刑法总则与分则规定的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要件,加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判断,以便得出正确的结论。
注释:
①④⑤⑥⑦(14)(15)(16)(17)(18)(19)(20)《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0页,第411页,第158页,第428页,第438页,第54页,第68页,第74页,第90、91页,第246页,第284页,第302页。
②《孟子·离娄上》。
③(12)(1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80~1381页,第1445页,第1478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9页。
⑨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16页,第515页。
(11)(21)(22)《董必武选集》第467页,第59页,第467页。
(23)《历史的审判》第3~5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40~1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