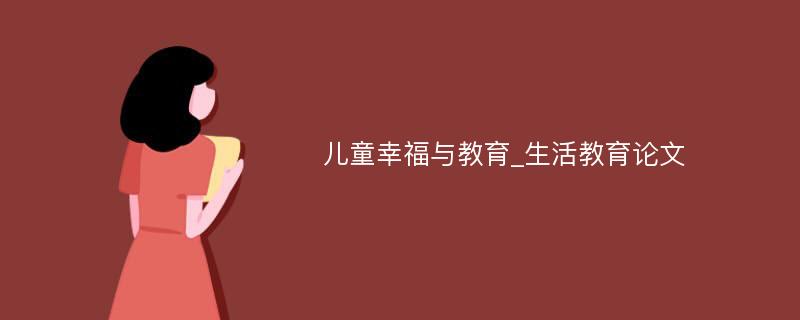
儿童的幸福与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儿童论文,幸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幸福是什么?
幸福是什么?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回答。从儿童的发展和教育的角度看,心理学的有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美国哈佛大学讲师泰勒·本-沙哈尔所讲授的积极心理学在哈佛成为最受欢迎的“幸福课”。[1]
对于幸福的理解,本-沙哈尔认为: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是所有目标的最终目标。
本-沙哈尔从人们经常吃的汉堡里,总结出四种人生模式:第一种汉堡,口味诱人,却是标准的“垃圾食品”。吃它等于是享受眼前的快乐,但同时也埋下未来的痛苦。用它比喻人生,就是及时享乐,出卖未来幸福的人生,即“享乐主义型”;第二种汉堡,口味很差,里边全是蔬菜和有机食物,吃了可以使人日后更健康,但会吃得很痛苦。牺牲眼前的幸福,为的是追求未来的目标,他称之为“忙碌奔波型”;第三种汉堡是最糟糕的,既不是美味,吃了还会影响日后的健康。与此相似的人,对生活丧失了希望和追求,既不享受眼前的事物,也不对未来抱期许,是“虚无主义型”;第四种汉堡,好吃又健康,这是一种“幸福型”汉堡。一个幸福的人,是既能享受当下所做的事,又可以获得更美满的未来。
本-沙哈尔认为,现实生活中的大部分人,都属于“忙碌奔波型”。人们习惯性地去关注下一个目标,而常常忽略了眼前的事情。
本-沙哈尔经常讲“蒂姆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晃动着许多人熟悉的影子。
蒂姆小时候,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但自打上小学那天起,他忙碌奔波的人生就开始了。父母和老师总告诫他,上学的目的,就是取得好成绩,这样长大后,才能找到好工作。没人告诉他,学校,可以是个获得快乐的地方,学习,可以是件令人开心的事。因为害怕考试考不好,担心作文写错字,蒂姆背负着焦虑和压力。他天天盼望的,就是下课和放学。他的精神寄托就是每年的假期。
渐渐地,蒂姆接受了大人的价值观。虽然他不喜欢学校,但还是努力学习。成绩好时,父母和老师都夸他,同学们也羡慕他。到高中时,蒂姆已对此深信不疑:牺牲现在,是为了换取未来的幸福;没有痛苦,就不会有收获。当压力大到无法承受时,他安慰自己:一旦上了大学,一切就会变好。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蒂姆激动得落泪。他长长舒了一口气:现在,可以开心地生活了。但没过几天,那熟悉的焦虑又卷土重来。他担心在和大学同学的竞争中,自己不能取胜。如果不能打败他们,自己将来就找不到好工作。
大学4年,蒂姆依旧奔忙着,极力为自己的履历表增光添彩。他成立学生社团、做义工,参加多种运动项目,小心翼翼地选修课程,但这一切完全不是出于兴趣,而是这些科目,可以保证他获得好成绩。
大四那年,蒂姆被一家著名的公司录用了。他又一次兴奋地告诉自己,这回终于可以享受生活了。可他很快就感觉到,这份每周需要工作84小时的高薪工作,充满压力。他又说服自己:没关系,这样干,今后的职位才会更稳固,才能更快地升职。当然,他也有开心的时刻,在加薪、拿到奖金或升职时。但这些满足感,很快就消退了。
经过多年的打拼,蒂姆成了公司合伙人。他曾多么渴望这一天。可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他却没觉得多快乐。蒂姆拥有了豪宅、名牌跑车。他的存款一辈子都用不完。
他被身边的人认定为成功的典型。朋友拿他当偶像,来教育自己的小孩。可是蒂姆呢,由于无法在盲目的追求中找到幸福,他干脆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眼下,用酗酒、吸毒来麻醉自己。他尽可能延长假期,在阳光下的海滩一呆就是几个钟头,享受着毫无目的的人生,再也不去担心明天的事。起初,他快活极了,但很快,他又感到了厌倦。
做“忙碌奔波型”的人并不快乐,做“享乐主义型”的人也不开心。由于找不到出路,蒂姆决定向命运投降,听天由命。但他的孩子们怎么办呢?他该引导他们过怎样的一种人生呢?蒂姆为此深感痛苦。
为什么当今社会有那么多“忙碌奔波型”的人呢?本-沙哈尔这样解释:因为人们常常被“幸福的假象”所蒙蔽。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是这样的:假如孩子成绩全优,家长就会给奖励;如果员工工作出色,老板就会发给奖金。人们习惯性地去关注下一个目标,而常常忽略了眼前的事情,最后,导致终生的盲目追求。
然而一旦目标达成后,人们常把放松的心情解释为幸福。好像事情越难做,成功后的幸福感就越强。不可否认,这种解脱让我们感到真实的快乐,但它绝不等同于“幸福”,它只是“幸福的假象”。这就好比一个人头痛好了之后,他会为头不痛而高兴,这是由于这种喜悦来自于痛苦的前因。“忙碌奔波型”的人,错误地认为成功就是幸福,坚信目标实现后的放松和解脱,就是幸福。因此,他们不停地从一个目标奔向另一个目标。
根据本-沙哈尔的研究,寻找真正能让自己快乐而有意义的目标,才是获得幸福的关键;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对儿童来讲,幸福既是快乐的现在,又是美好的未来,是快乐的现在与美好未来的结合。
二、教育怎么办?
教育要促进儿童的幸福,一方面要让儿童享受现在的快乐,另一方面要让儿童享有美好的未来,因而必须处理好儿童的现在与未来的关系。这是教育和教育学的一个难题。
美国教育家巴格莱在论述教育理论的历史发展时指出:“两种对立的理论很明显地贯穿在漫长的教育史中——有组织的教育实际上和文明一样的古老。虽然过分地简单化往往是危险的,但是如果谨慎从事,人们可以用某种相反的概念概括出成对的对立物,把这两种教育理论加以对照,例如‘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纪律’、‘兴趣与努力’、‘游戏与工作’——或者用最近流行的说法,如‘目前需要与长远目标’、‘个人经验与种族经验’、‘心理组织与逻辑组织’、‘学生主动性与教师主动性’。用这些名词表达的根本的二元论已持续了若干世纪。”[2] 应当指出,这里所概括的情况确实是存在的。从这种概括中还可以看出,人们对两种对立的理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把握。
从儿童的发展和幸福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两种对立的教育理论分别称之为“自由教育论”和“强制教育论”。[3] 这两种理论的对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实质上看,它们是儿童的现在与儿童未来的对立。由于儿童的现在主要表现为儿童的需要,儿童的未来主要表现为社会的要求,所以儿童的现在与未来的对立也就是儿童(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在教育过程中,教师主要受社会的委托,代表社会来教育儿童,所以儿童的现在与未来的对立又表现为学生与教师的对立。
强制教育论认为教育的一切都是为着儿童的未来。但是,儿童并不理解自己的未来,在现在与未来的冲突中,他选择了现在;他也不懂得成人对他的未来操心的意义,他甚至把成人的这种操心看作是对他其乐无穷的现在的蓄意侵犯。换句话说,他把人们为他的美好前途而做的善事,看成是旨在反对他的恶事。在他们强制儿童服从自己意志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动人地说:“善良的人们!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儿童们根本不懂得自己的未来的意义!我们不能容忍他们调皮!对他们要严厉些,不要轻易地表露你们的感情。在将来,他们会衷心感谢你们今天的严厉和拳头的!”[4]
强制教育论只重视儿童的未来,忽视或否定了儿童的现在,实际上是忽视和否定了儿童本身。而忽视和否定儿童本身的教育不仅不能有效地促进儿童的幸福,反而会成为儿童幸福的桎梏,因而必然受到以卢梭和杜威为代表的自由教育论的批判。
较早对强制教育进行系统而深入批判的是卢梭。卢梭批判封建教育把儿童看作小大人,只注重儿童的未来,忽视了儿童的现在。卢梭则主张教育要遵循儿童的自然,按照儿童自然发展的顺序和特点进行,他还把“自然人”与社会“公民”对立起来,实际上是只重视儿童的现在,不重视儿童的未来。
杜威反对二元论,他主张把教育目的与教育过程统一起来(实际上是把儿童的现在与未来统一起来),他还要求教育既要以社会为中心,又要以儿童为中心。但是,在批判传统教育的时候,他又主张以儿童为中心,并认为儿童中心的确立乃是教育领域里发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杜威最后还是陷入了二元论,在儿童的现在与未来之间,他更重视的是儿童的现在,是儿童现在的需要和兴趣。
上述两种对立的理论在儿童的现在与未来之间各执一端,形成两种不同的教育实践,并造就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一种是“忙碌奔波型”的人;另一种是“享乐主义型”的人。他们都不是真正幸福的人。这些理论启示我们,教育要促进儿童的幸福,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要从儿童的现在出发,重视儿童的生活和活动,遵循儿童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利用儿童的需要和兴趣,尊重儿童的意愿和要求;第二,要面向儿童的未来,考虑社会对儿童发展的要求,强调教师对儿童发展的责任,重视教育对儿童发展的规范和引导作用;第三,要自觉地把儿童的现在与未来辩证地统一起来。
教育促进儿童幸福的条件,分开讲是三个,实际上是一个,即处理好儿童的现在与未来的关系,把儿童的现在与未来辩证地统一起来。因此,问题的关键是,怎样处理儿童的现在与未来的关系?
从哲学角度看,人的现在与未来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或者说是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反映。中国人有一句口头语叫做“人生在世”,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所谓“在世界之中”,或简称为“在之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有两种意义的“在之中”:一是指两个现成的东西,其中一个在另一个“之中”,例如水在杯子“之中”,椅子在教室“之中”,学校在城市“之中”。按照这种意义的“之中”来理解人和世界的关系,就是一个现成的东西(人)在另一个现成的东西(世界)“之中”存在,这两者的关系是两个平等并列的现成的东西共处的关系。简言之,两者处于外在关系之中。海德格尔认为,西方传统哲学中的主客体关系就是这样的“之中”关系:客体是现成的、外在的被认识者,主体是现成的、内在的认识者,两者彼此外在。这样的关系必然产生一个问题,即主体怎么能够从他的内在范围走出来而进入一个外在的客体范围中去?
另一种意义的“在之中”,海德格尔称为“此在和世界”的关系。按照这种意义的“在之中”,人乃是“融身”在世界之中,“依寓”于世界之中,世界乃是由于人的“在此”而对人揭示自己、展示自己。世界不是首先作为外在于人的现成的东西而被人认识,而是首先作为与人打交道、起作用的东西而展示出来。人在认识世界之前,早已与世界融合在一起,早已沉浸在他所活动的世界之中。所以,融身于世界之中,依寓于世界之中,繁忙于世界之中。这样的“在之中”,乃是人的本质特征。人(“此在”)是“澄明”,是世界之展示口,世界在“此”被照亮。至于“主体—客体”式的“在之中”关系,在海德格尔看来,必须以这里所说的“此在和世界”的“在之中”关系为基础才能产生。为了使世界作为现成的东西而可能被认识,人首先必须有与世界打交道的活动,然后才从制作、操作等活动中,逐步走向认识。按照海德格尔的解释,认识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已经在世界之中,或者说,已经融身于世界之中。
海德格尔对人与世界两种关系的理解,对于我们认识儿童的现在与未来的关系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实际上,儿童的现在与未来也存在着两种关系。一种是外在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儿童的现在与未来是两个并列的现成的东西,它们彼此外在。在教育过程中,把儿童的现在与未来的关系当成这样的外在关系来处理,其结果便是儿童不能认识未来的意义,便是难以形成现在与未来的联系,便是儿童的现在与未来的对立。强制教育论和卢梭的自然教育论虽然各执一端,但它们对儿童的现在与未来关系的看法却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把儿童的现在与未来的关系看成一种外在的关系。
儿童的现在与未来的另一种关系,是内在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儿童通过自己的生活、活动,即同世界打交道,使他们的现在与未来融合在一起。在教育过程中,把儿童的现在与未来的关系当成这样的内在关系来处理,其结果便是儿童的现在与未来联系的形成,便是对儿童的生活和活动的重视。从杜威的“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连续不断的改组和改造”、“做中学”等教育主张来看,他实际上是把儿童的现在与未来的关系当作内在关系来处理。与前一种做法相比,这种做法更科学、更有意义,因为它把儿童的现在与未来密切联系起来了。但是,仅仅从内在关系的角度来处理儿童的现在与未来的关系,也会带来“儿童中心”的问题。
因此,应当从上述两个角度处理儿童的现在与未来的关系,或者说把儿童的现在与未来的关系当作上述两种关系来处理。一方面要把儿童的未来提携到、渗透到儿童的现在,重视儿童的现在与未来的联系(内在关系);另一方面要把关心儿童的未来作为教师的崇高任务,并要求教师一定要完成社会赋予的这一任务,重视儿童的现在与未来的区别(外在关系)。我们认为,在把儿童的现在与未来的关系当作这样两种关系来处理时,还要处理好这两种关系之间的关系:内在的关系是基础,外在的关系应当建立在内在关系基础之上。据此,要处理好儿童的现在与未来的关系,首先要通过儿童的生活和活动把儿童的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然后在此基础上引导儿童认识自己未来的意义,并引导他们向着未来发展。在这里,儿童的现在与未来既是统一的,又是矛盾的。这就是儿童发展的辩证性。教育要有效地促进儿童的幸福,就必须辩证地处理儿童的现在与未来的关系。
三、有益的探索
教育能否辩证地处理儿童现在与未来的关系,从而有效地促进儿童的幸福呢?前苏联的合作教育学从理论到实践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从促进儿童幸福的角度看,前苏联的教育理论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建国初期,“儿童中心论”曾一度泛滥。20世纪30、40年代形成的凯洛夫教育学,虽然纠正了“儿童中心论”的错误,却成了“没有儿童的教育学”。80年代,主要由实验教师提出的合作教育学一方面对“没有儿童的教育学”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另一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尊重儿童、让儿童自由发展和幸福的人道主义教育思想。①
合作教育学把“没有儿童的教育学”称作权力主义和强迫命令的教育学(简称“权力主义教育学”)。权力主义教育学的主要特点,简单地说就是强制。而强制的基本做法就是对学生的学习进行严格的检查。为什么要对学生进行强制和检查呢?简单地说就是“目中无人”。许多教师认为,儿童——这是盛装教学内容的口袋,即正确回答了教师提问的学生。学生尚在学习,因此他们尚不能被视为人;他们学习的不是怎样成为人,而是怎样读、写、复述,怎样在物理、化学等课上回答问题。学会了这一切就成为了人;学不会就不能成为人。由于教师不把儿童当人,所以他不信任儿童,认为他们不想学习,不想成为人;为了使儿童成为人,应该与他们作斗争。这样的教师在跨进教室上课时,看到的不是在他领导和帮助下形成中的个性,而是懂不懂教材、是否专心听讲、是否妨碍他工作的学生。儿童只是已学过的教材(以知识、技能、技巧为形式)的载体——这就是教师所关心的主要的东西。让儿童经常处于恐惧的压力下学习,这就是没有儿童的教育实践的写照。
在权力主义的教育过程中,学生的学习活动势必大多为听讲、做作业、复习、回答问题。教育过程变成了一个全面强迫的过程。强迫学生接受一切:知识、道德、信念、对现实的评价,等等。学生仅仅是教师教导的接受者。由于无法预测学生接受的效果,所以教师需要有多种制裁手段来保证:强制、禁止,甚至对不喜欢的学生给予开除学籍的处分。在这样的教育过程中,儿童变得固执而又任性,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可是教师从中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你们要知道,这些孩子是怎样的人,现在的这一代是怎样的一代——不听话,不想学习!
权力主义的教育学完全把儿童排斥在教育过程之外,只重视儿童的未来,忽视儿童的现在。这种没有儿童的教育学必然导致师生之间的冲突。阿莫纳什维利把这种冲突叫做“教育的悲剧”。在阿莫纳什维利看来,教育悲剧的本质在于儿童的现在与未来的矛盾。虽然儿童向往着未来,但他有现实的、此时此刻的需求。这种需求是在他的发展中的机能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的。儿童总是自己现实需求的俘虏,他不能摆脱现实需求的锁链。现实需求像迷雾一样模糊了他的意识,蒙住了他的理智。他始终没有能力把自己现在的“我要”挪到明天去。儿童现实需求的力量有可能阻挡成人施加的合理的教育影响。成人如果采取强制的措施,就不可避免会引起儿童的不满并发生冲突。
上面是从儿童的立场看问题的。它是否意味着面向未来的儿童在用自己的现实需求反对自己的未来?不能这样说。全部问题在于,儿童是按照怎样的逻辑成长起来的。他想成长,但也想游戏和在游戏中成长。他想学习,但不想失去自由。这就是儿童成长逻辑的辩证法。如果教育过程中,儿童与成人的交往与这一逻辑并不矛盾,就会有互相理解,也许还会有精神上的一致性。但这取决于教师。
教师的立场是怎样的呢?他的出发点不是儿童今天的愿望,而是儿童未来的生活。未来的生活要求儿童在今天、在此时此刻学习物理,而不是娱乐;要求他坐在教室里上课,而不是上电影院。关心儿童的未来是教师最崇高的任务。这是他对儿童怀有的人道目的。他必须达到这一目的,因为这是社会对教师的要求。但受今天生活支配的儿童不能理解教师的善良意图,他把教师的这种意图看作是对他的自由,对他今天的满足和快乐的蓄意侵犯。这样,悲剧就发生了:儿童不愿意接受教师对他未来的关怀,与教师发生冲突。可是,教师的这种关怀恰恰是他的成长所必需的。
能避免这种悲剧吗?儿童有自己的生活,他们把它看得比什么都宝贵,如果没有阻力,他们是不会放弃自己的生活。教师有自己的任务,他不能也没有权利放弃自己的任务。能不能让教师带着自己的任务、自己对儿童的关怀、自己的生活转移到儿童生活中,使师生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一致起来呢?要做到师生的生活、目的和任务完全一致起来,虽是不可能的,但也不是完全做不到。关键取决于教师本身,取决于他的个性和技巧。如果教师带着自己的生活加入到儿童的生活中去,他们就能成为儿童的“自己人”、大朋友、和蔼可亲的“出谋策划者”。只有在这种协同一致的生活的深处,儿童才能理解教师和追随教师,而教师也才能致力于深层的教育,而不是“表面”的教育。[5]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用合作教育学代替权力主义教育学。合作教育学的思想可以表述如下:“使儿童成为教师、教育者、家长在对他们进行教育、教学、教养和形成他们的个性中的自愿的、有利害关系的战友、志同道合者,成为教育过程的平等的参加者,成为对这一过程的成果抱关心和负责态度的人。”[6] 合作教育学对儿童的教育采取的是人道主义的立场。下述经典的公式就是人道主义教育立场的依据:“儿童不仅在准备走向生活,而且他现在已经在生活”。儿童的唯一兴趣集中在使他得到快乐和满足的现在上面,并且,只有通过这些快乐和满足,他才能够看到“未来”模糊的轮廓。如果我们能够把未来提携到现在,我们就能够获得真正快乐的、生气勃勃的教育学。这就是说,要在儿童现在生活的河流里引入一股未来生活的水流,要把我们藏匿在遥远地方的教育目的的种子移植到生机勃勃的儿童生活的心田里。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将获得这样的果实:儿童现在的生活将为内容丰富的未来生活的实质所充实;我们将从儿童自己的立场出发去教育他们;我们将能够使儿童成为乐意接受教育的人。
合作教育学是在长期教育实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为了避免教育的悲剧,使儿童成为乐于接受教育的人,合作教育学在教育实验中采取了许多具体的教育措施,如强调在教育过程中贯彻自由选择的原则,取消分数、代之以评价,等。
据介绍,阿莫纳什维利主持的一个以六岁儿童班为重点的小学教学新体系的实验,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这种效果主要体现在实验班学生与对照班(普通班)学生的不同特点上:(1)学习动机对比:实验班学生以学习活动本身产生的乐趣为主要动机;对照班学生则以分数刺激为主要动机。(2)主动积极性对比:实验班学生乐于上学并主动积极地参加课堂活动;对照班学生则大为逊色。(3)学习方法对比:实验班学生在学习上惯于对事情自己决定、自己判断,以批判的眼光提出问题,参与评论,提出假设和建议,进行“发现”,得出结果;对照班学生则习惯于死记、硬背、重述等。(4)胆量对比:实验班学生能无顾忌地大胆发表意见,回答问题;对照班学生则顾虑重重、沉默不语。(5)选做难题对比:实验班学生争做难题,因为没有“打坏分”的后顾之忧;对照班学生则惟恐得个坏分而尽量挑选容易的题做。(6)择友对比:实验班学生的择友标准无“好学生”(成绩好)、“坏学生”(成绩差)之分;对照班学生则多以“成绩好”为标准。总之,实验班学生拥有优于对照班学生的许多可贵品质。[7]
合作教育学力图避免教育的悲剧,为的是儿童的自由和幸福。它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否定了儿童的学习与强制、压抑、痛苦、羞辱等不良情绪之间人为建立的虚假联系,肯定了学习作为人的自我解放和发展的活动的真相,并且证明了只有人道的、不加强制的、自觉愉快的学习,才是最有效率的学习。合作教育学深刻地意识到了儿童的现在与未来的矛盾,并把它看作是导致师生冲突这种“教育的悲剧”的基本原因。面对儿童的现在与未来的矛盾,合作教育学反对片面的做法,主张把儿童的未来渗透于儿童的现在之中,强调教师要引导儿童不断地向未来发展。这种理论较好地体现了教育促进儿童幸福的辩证法。合作教育学不仅提出了促进儿童幸福的理论,而且进行了长期的教育实验。虽然合作教育学提出的时间还不长,它的合理性还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但它的基本思想却为我们认识教育促进儿童幸福的条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注释:
① 合作教育学是由一批实验教师共同提出的,这些实验教师既有共同的教育思想,又有不同的教育主张。本文对合作教育学的阐述,以合作教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阿莫纳什维利的教育思想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