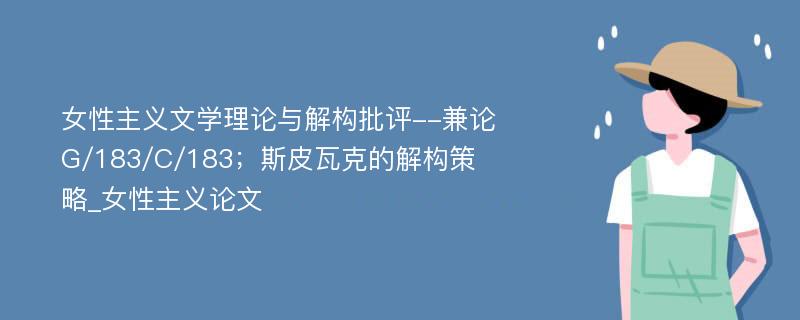
女性主义文论与解构批评——兼论G#183;C#183;斯皮瓦克的解构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皮瓦克论文,文论论文,批评论文,策略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04)05-0086-05
一
女性主义文论本身便是广义的解构思潮的一部分,女性主义文论与狭义的解构批评(Deconstructionist Criticism)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消解中心”的努力在女性主义文本中随处可见。乔纳森·卡纳说:通过对批评思想一直想当然视为靠山的各种哲学的二元对立的质疑,解构提出了必须或视而未见或孜孜以求的理论问题,通过打破批评概念和方法赖以驻足的等级关系,它防止了将概念与方法视为当然的事实,仅作为一种可靠的工具来使用的偏颇。批评范畴不仅是用以产生完美解释的工具,更是有待通过本文与概念的相互作用进行探究的问题。[1](P180)因而解构批评自然地接近了对于男女对立二分(dichotomy)模式的颠覆或消解。解构批评对女性主义批评是十分有用的,它提供了消解等级森严的对立的方法,鼓励更多的发展中的理论;它让人们重新估价或质疑经典作品的释义,从而使其内涵丰富扩大;它消解了传统批评的权威地位,超越了那种企图去界定只有一种真正意义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说得颇好:对于男性统治的社会来说,男人是基本原则,女人是受到排斥的对立项,只要牢牢保持这个区别,整个社会系统就可以有效运行。“解构批评”是这样一种批评操作的名称,它可以部分地颠覆这类对立组,或部分地证明这类对立组在本文意义过程中是互相颠覆的。女人是对立项,是男人的“他者”;她是非男人,有缺陷的男人,她对于男性第一原则基本上只有反面价值。同样,男人之成为男人,只是由于不断排除这个“他者”或对立项,因此他是相对于她来规定自己的。他力图以这样的姿态来肯定他独特的、自主的存在,然而正是这一姿态抓住了他的整个身份,并且给它造成危险。女人并不是一个在他视野之外的“他者”,而是一个与他关系密切的“他者”,是他所不是者的形象,因而是一个从根本上提醒他对自己身份加以注意的事物。[2](PP165-166)玛丽·维朴(Mary Poovey)在《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一文中论述了解构主义对女性主义批评的贡献:它揭示了意识形态的虚幻性,暴露了像“本性”和性别这些范畴的内在诡计,从而有利于女性主义揭示“女性”的各种矛盾;它向等级制和对立统一逻辑挑战,可以使女性主义者更准确地列出存在于个人、社会位置和社会权力中的多重决定因素;其“中介物”的观点(the idea of"in-between"),可以使女性主义者重新思考权力关系,以便认清权力的不连续的本质。解构批评的代表人物德里达也曾指出,离开必要的“解构”,女性主义的话语便会赤裸裸地重造其旨在进行批判的东西。对于解构主义的挪用,G.C.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可算是最典型的了。斯皮瓦克出生于加尔各答,大学毕业后赴美深造,后留美任教。她因将德里达的《论文字学》译成英文而享誉西方学界。作为德里达的学生,斯皮瓦克熟练掌握了解构批评的各种操作方法,宣称解构主义的视点能使她坚持拒绝本质先于实在的僵硬的心理性别、种族及阶级的概念,强调非连续性、多相性和类型学。她在德里达《论文字学》译本所写的序言中,详述了怎样利用解构批评的方法读解文本:如果在以传统方式解析作品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个似乎潜藏着无法解决的矛盾的字——仅仅是一个字,其有时可以以一种方式产生作用,有时又可以以另一种方式产生作用,且就这样标明了一种僵化固定意义的不存在,这时我们就紧紧抓住这个字不放。如果一种隐喻掩盖了这个字的意义,我们就抓住那个隐喻,跟随其在作品中冒险,并窥见作品逐渐展现,如同一个隐藏的结构,显露出它的自我背离及不确定性。[3]这种紧紧抓住某个字不放,而“显露出它的自我背离及不确定性”的读解法,在斯皮瓦克的论著中随处可见。便是阅读马克思的论著时也一样: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讲到的对这个世界的解释与改变之间存有不对称关系。这里的词语haben interpretiert(现在分词interpretieren的完成形式,罗曼语的动词,强调以适当的比拟与某一现象建立起相应的意义联系)与zu veründern(动词不定式,总是指向未来的,严格说来是标示“意味着”的德语动词,“使它者”)之间有一种对比。后一表达无论是在其拉丁语哲学的影响力,还是在很贴近与完整的意义上与haben interpretiert都不相对应,因为transformieren可能已经完成。……所有的理论都会有一种无尽的敞开性。[4](P208)在斯皮瓦克看来,被压迫的下层人民是哑声的,不能记录下自己的历史,“属下人不能说话”。她的代表性论文《属下能说话吗?》探讨了这一问题。周蕾指出,“代理人”的再表现是问题的关键,斯皮瓦克将“代表”与“说话”二词互换运用,“属下能说话吗?”的准确含义应是“属下能代表吗?”“说话”一词会引起歧义,会让人觉得指日常生活中的任意行为,属下人士当然可以“说话”,用“代表”更突出了弱势群体是否能够占据积极代表者的位置问题。[5]在讨论印度的“属下研究小组”文本时,斯皮瓦克指出,要了解被殖民者的意识或“自我表现”,可以用解构的精神去读解殖民者文本(如报告、电讯、记录、评论、法律及书信等),“只有反起义文本或精英文献能带给我们被压迫者意识方面的信息,抗争的‘农民’观点可能永远不会恢复”,“只要记载朱特面粉厂工人的意识有困难,他们抗拒和质询雇主权威的意识就只能在掌权者的危机感中读到,如果我用较深奥的法国后结构主义的术语来说的话,那便是‘这里的意识(这里指遭压抑的意识)对我来说是十分中性的,文本中的空白部分,是未来不同时代必要而不确定的标志’”。[6](P204)“我逐渐倾向于把被压迫意识的恢复视为受后结构主义语言里所称的被压迫主体效应(subject-effect)的牵引,主体效应可概述如下:某一主体的运动,可能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巨大而不连续的网络(广义上称为“文本”)的一部分。这些组成部分可被称为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历史、性别及语言等等(其中每一个部分又由相互交织的许多部分组成)。这些组成部分不同的联结点与排列,由依赖于多方面条件的异质规定性界定,从而产生运动主体的效应。”[6]用解构的批判精神读解压迫者的文本,便会产生“去蔽”的作用,消解“霸权史学”,接近被压迫者的意识,恢复其明确性。而对一贯性及逻辑的强调必然会危害被压迫者,“并陷入一种权力知识游戏”。[6](P207)将解构主义与社会历史分析结合,斯皮瓦克发展了所谓的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积极滑动的“解构史学”(deconstructing historiography)。“那些看似很成功的、被称为精英史学的、或左或右的民族主义者或殖民主义者自身是由认知失败(cognitive failure)构成的,……许多当代史学复杂的词汇成功地遮蔽了这种认知失败与失败中的成功,这种已被认可的忽视与殖民控制是密不可分的。”[6](P199)有“历史”便有“解构”,仅有那些“没有历史的”才是可严格划定的,但这无疑也“把自己从定义中撤离”了。斯皮瓦克如此的读解方式,爱德华·W·萨义德称之为“对位法阅读”,即在阅读一篇文字时,读者必须开发性地理解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写进文字的东西,另一个是被它的作者排除在外的东西。即便是对待女性文本,斯皮瓦克仍喜好这种紧紧抓住某个字不放的解构式阅读法。如:我想回顾一下那篇写于多年以前的著名短文《美杜莎的笑声》中有关母亲和多元化的部分。这篇短文包含了两种呼语模式——一种是亲密地称呼一位妇女为“tu”。……关于育儿的那一部分仍然是用“tu-toi”(你—你)的形式写的,但它似乎分解了被称呼者的性格特征……。[7](P119)同时,作为女性主义者,斯皮瓦克由对埃莱娜·西苏的人称呼语的解析,悄悄地进入了她复杂而诡谲的女性主义:西苏是以母亲和孩子的空间在展示人们的奇特存在,像谈到妇女的多元化时,呼语则采取了说明文或非人称模式,其“同他者的伦理关系使得将个体普遍化成为必需。而且在母亲作为类生命而不是类存在物、作为前占用的空间中,并没有伦理—神学的我—你(I-thou)的位置”。[7](P120)
斯皮瓦克关于“女人”的定义,也可看到德里达“延异”论的影子。她在《女性主义与批评理论》中写道:我不能一般地讨论女性主义。我只能作为一名妇女在文学的范围内讨论这一问题。我关于女人的定义很简单:它依附于“男人”(man)这个词,它正如用来为我栖居其中的文学批评机制的角落提供基础的文本。或许你们会认为,以“男人”(man)来定义“女人”(woman)是一种反动的立场。难道我不想为身为女人的我建构一个独立的定义?可于此我必须重申我经常重复的那个自己在过去十载悟出的解构典律:对任何事物的严格定义最终都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想如此,你就得不停地消解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并最终表明那是一个可自我替代的二元对立。因此,作为“一名解构批评家”(as a deconstructivist),我不能成就这种二元对立。但是,为了让我们能继续下去,能保有一种立场,我觉得下定义是必须的。在我看来我作的定义是滑动的和可争辩的:建构我作为妇女的立场不是根据公认的本质,而是根据经常使用着的词,“男人”(Man)便是通用的一个词,不是任意的,而是特指的一个词(Not a word,but the word)。[8](P77)在斯皮瓦克看来,没有世界不是被词语建构的,而对词语的读解是移动的(即德里达所谓的“延异”),给某一事物下一个固定的定义,便是在树立相对于另一事物的二元对立,这是想消解男女二元对立的解构主义/女性主义者的她所不愿看到的。一个人的性别身份认同在理论上是流动的,“女人”像其他任何术语那样只能在一系列复杂的差异中界定,其意义的形成依赖于文字的彼此相互对应关系。可为了鼓动妇女的需要,在特定的场合仍可策略性地援用“女人”这一概念,但从事鼓动工作的人必须认识到这种灵活性。这样,斯皮瓦克发展了一种“策略性本质说”(strategic essentialism)。这种被广为接受的主体论,不是根据一个女人假定应有的本质,而是根据通常使用的关于女人的话语,根据女人与男人变动不居的差异及其在社会生产中的特定关系,通过“身为女人的我”的亲身经历,来构筑女人的定义,审视女人,既表现了解构主义倾向于言语分析(包括隐喻)的嗜好,又坚持了女性主义立场。故她的解构策略既有表现别人/他者,又有自我表现或认证的性质,并非完全是一些人所攻击她的“代表身不在其中的属下群体发言”,有别于将“代表者”与“被代表者”分离的所谓“超级叙事”。
二
解构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也存在相抵牾的地方。德里达有一句常被引用的名言,即“文本之外无他物”。他说:“解构活动并不触动外部结构。只有居住在这种结构中,解构活动才是可能的、有效的;也只有居住在这种结构中,解构活动才能有的放矢。”[9](P32)德里达式的解构批评与结构主义相近,本质上仍是一种形式主义。在这种理论中,人的主体性像语词的意义一样,总在不断扩散、“延异”。譬如“延异”(différance)这个“术语”,便标示了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它无特定意义,在否定其他术语的同时,还否定自身,既非词语又非概念,既指“区分”,又指“延搁”,它使“欲望”或“意愿”暂时得不到实现和满足。德里达宣称,“语境在两个意义上无边无涯。第一,任何给定的语境都为进一步的阐发敞开。从理论上讲,一个给定语境的含量及特定言语行为的指涉可能性,皆无止境。……语境还在第二种意义上难于掌握:无论什么把语境符码化的企图,总能移进它所想描述的语境,遂产生一个出于原初模式的新语境”[1](PP123-124)因而卡纳批评德里达说:它立足于差异又对它大肆攻击,强调二元对立又有意回避其哲学内涵。这导致了它二面受敌:一方面被指控是骄狂,是故意捣毁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另一方面又被认为是它所反对的等级制的同伙。[1](P151)
结构主义及解构批评,均存在一个与主体断裂的问题。分解的结果,导致了真理观的淡化,导致了文学研究所驻足的共同点和基本价值的消解。实际上,解构批评并未“解构”一切,没有对既存的其他理论造成真正的威胁,只使它们学得谦恭一点,态度不那么自信。无论是德里达还是德曼,其理论并不想回应历史及现实处境,深陷于文本(text),自我指涉而与现实无关,也无伦理方面的吁求。在德里达看来,男性中心主义文本也是自我解构的:有时候,那些其主题非常阳物中心或阳物理性中心论的文本(在一定意义上,任何文本都不能完全规避这一程式),在某些情况下也能够是最解构的。……像尼采、乔伊斯、蓬热、巴塔耶、阿尔托等人的那些文本,是极端阳物中心论的,其方式多种多样。它们产生解构的效果,同时恰好又反阳物中心论。阳物中心论的逻辑随时准备着翻转或颠覆自己。[10](PP24-25)这无异于说,男性中心主义其实并不存在,女性主义批评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另一位解构批评的代表J.H.米勒在谈到解构式阅读时也表达了同样的倾向。米勒在《阅读的伦理学》中指出,阅读是一种“自由活动”,是一种“对于伦理的时刻进入阅读、教学或撰写评论的行为中的方式所持的基本误解”,每一阅读行为中必然发生的就是“不可读定律”或“挫败”的重复示范。米勒的《时间的地理志:丁尼生的眼泪》,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倾向。他对丁尼生的《眼泪,无端的眼泪》评析道:“眼泪”表征了符号的无法识读性(unreadability),它的非存在(non-being),像一个反复被复述的词,因为重复了多次,乃至失去了原意,最后变成单纯、无意义的声音。文学批评的相对主义必然隐含着伦理相对主义,作品所寄寓的道德层面完全被消解了。米勒对伊面莎白·盖斯凯尔《克兰福德镇》的解读也是同样。一方面,他肯定小说表达了“女人有离开男人面生存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认为其“表达出女人对男人的需要”。[11](P225)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必须以解构的方法或策略对德里达式的解构主义进行解构。她们认为,解构主义的政治是最典型的保守主义,它不愿检验自己实践中的策略和历史的具体性,除了解构主义本身外,没有任何稳定的位置可以存在,它并不重视作为整体或作为个人的妇女作家,妇女仍被放到了他者的位置上,“再现”的问题也被无限地往后推移。如果恪守解构主义的方法而不能超越它的话,那只能导致女性主义自身的解构。尽管屡遭解构批评或后现代主义的嘲讽,对主体性的坚守,却是女性对抗男性中心主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后现代学者相信“作者已死”,而主体也随之消失的主张,却未必适用于女性,且此主体也过早封杀了能动主体的问题。因为女性在历史认同方面,并未经历男性在面临源头、体制及生产等常承受的“自我”、“本我”、“我思”等过多的负担。原则上,基于女性主体在古代城邦中被排斥在外,故女性早已偏离中心、源头及体制等;那女性与整体、文本、欲望及权威(作者)的关系,在结构上与那种(男性)拥有的普世适用的位置,恰恰突出了男女之间存在许多重大差异。[12](P106)作为女性主义者,斯皮瓦克坚持认为解构批评所提供的仅是一种方法而非见解。“解构(deconstruction)的最大礼物是:质疑研究主体的权威性而不是附和他,坚持不懈地将不可能的条件转化成可能的。”[4](P201)她表示了对德里达的明显不满:“德里达没有考虑到‘女人’这一符号穿越正统本文暴虐时的不确定性。”[4](P91)在她看来,“表现”或“叙事”与种族、阶级及社会性别等因素是密不可分的,即使是“自我表现”,也浸透了历史文化的规定性。譬如,1926年在印度北加尔各答自杀的那名下层女子,由于不能完成起义组织交给的暗杀任务而自杀了,但为了保证自杀不被认为是不清白(不正当的怀孕)所致,她故意等到月经来后才自杀。这样一种以身体(经血)为代价的“自我表现”,渗透了男权制的历史要求和弱势者对这类要求的控诉。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斯皮瓦克审理了“左右着我们关于世界观和自我观的背景和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依德学说,宣称“马克思和弗洛依德却避而不谈子宫作为生产场所”。在论文注解中,她还专门提醒读者要注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使用的各种相关隐喻。她批判了欧洲中心论,倡导一种关注心理性别、种族及阶级的阅读方法,不像德里达那样恪守“本文以外无他物”的读解典律,要求注意异常复杂的化妆品、内衣、外衣、广告、妇女杂志、色情描写所表现的皮肤及外表所引起的妇女的(性)客体化,并援引1982年发生在汉城的跨国公司数据控制站的妇女罢工事件,来说明共同的女性本质是一个陷阱,妇女有不同的“性处境”,全世界的妇女并不全都以差不多同样的方式将本质特权化。她还用童年在印度的经历证明自己的观点,即为了充分地认识第三世界并扩展不同的读者群,第一世界的女性主义者必须学会放弃做女人的优越感,必须重视其多相性、多态性研究。斯皮瓦克宣称,在女性学术界,存在一种西方的“国际女性主义”,这种女性主义对东方的了解是东方的西方化,或者说决定了“西化的东方人”想要了解“自己的世界”。故第一世界的女性主义者必须放弃做女人的优越感,充分地认识到第三世界并扩展不同的读者群及其多相性研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早于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者,斯皮瓦克对J.克莉斯蒂娃的《关于中国妇女》展开了后殖民主义批判。克莉斯蒂娃因对60年代的法国现实不满,将目光转向了东方,但由于欧洲中心主义作祟,对古代中国采取的是“尚古主义”,赞扬中国的过去,对“当代”中国则采取轻蔑现实政治的态度。她“没有分析中国妇女的经历,便得出一个论点:‘如果有一天(即在社会主义社会,要在家庭之外通过各种升华的形式找到一条发泄性能量的渠道)会到来,如果中国传统不受干扰,那么这种情况就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国会不加拘谨和充满盲目崇拜地去接近它,会更甚于基督的西方去追求性自由。’不管基督的西方整体上是否狂喊过‘性自由’,克莉斯蒂娃对中国的断言当然是善意的;我的观点是说它带有殖民主义者乐善好施的症状”。[13](PP83-84)一旦一些人将另一些人变成了“符号”,其表现与阐释的“客观性”或“准确性”便值得质疑。在跨文化再表现中,“第三世界”往往成了表现“第一世界”的被扭曲的陪衬物。正是斯皮瓦克对第三世界下层妇女的同情,使其成为著名的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家。她激烈解构西方帝国主义霸权,将自己当成了“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向表现的核心问题,即依附于差异的道德评价问题开刀”,突出了“表现”中的阶级及权力问题。[5]故女性主义批评家对主体性的恪守,也体现在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中。
三
由上可知,女性主义批评与狭义的解构主义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解构主义向女性主义批评提供了质疑与颠覆父系意识形态的策略与方法,女性主义批评也无意中支持了解构批评消解现存意识形态的总体原则;但解构主义颠覆现存话语后并不特别企求重构,玩赏意义却并不加以更新,而女性主义批评颠覆与重构同时并举,力争改变既存意识形态,确立新的主体性。诚如斯皮瓦克在评价德里达时所言:如果尊奉德里达,我们就不易觉察他的谬误,在他质疑形而上学的樊篱时,却又被这种樊篱困住了,因而他的文本也像其他所有文本,对其曾反复表述的文本开放。这样一来,德里达的话语又表明什么?他不能成功地运用自己的理论,因为按其原则,成功的运用应永远是被推延的,延异/写作/踪迹作为一种结构,仅仅是对尼采玩弄的知识与忘却游戏的煞有介事的表述。[4]
解构主义对女性主义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其负面影响在西方兴起的“酷儿理论”(queer theory)或后现代女性主义(postmodern feminism)中鲜明地呈现出来。90年代以降,从女性主义内部发展出一种“酷儿理论”,对包括了女同性恋在内的各种性行为选择理论或规范皆形成了挑战。“如今在美国(在英国,在低得多的程度上),选择人类学、文学、电影研究或文化历史的课程,不碰到所谓酷儿理论家的作品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少了”。[14](P152)英语queer,一般指与预期不同的、古怪的意思,譬如,说“那鱼有一种古怪的味道”,用英语便可以说:“The fish had a queer taste.”打乱德里达所称的“圈里”与“圈外”的界限,一个“酷儿”完全可按自己的意愿,想做哪个性别便做哪个性别,且在同一时间可是男的也可是女的,还根本不必做变性手术,藉此而试图建立尊重个人性别选择的自由空间或存在的极端自由主义状态。“酷儿理论”在“性别”(gender)与性征(sexuality)区划方面解构一切,戏谑一切,被视为破坏性别常规与建构的与“社会结构女性主义”(social structures feminism)相左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质疑所有关于性别和性征的传统设定,宣称“男人”、“女人”、“异性恋”、“同性恋”、“男子气的”、“女子气的”等范畴只不过是一种行为与展示。像社会结构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性别是由我们的穿着,用我们的身体及言行举止创造的。但后现代女性主义并不关注重复的性别行为建构的社会结构现象,认为性别和性征总是含混而非固定的,不存在持久的身份,对身份的界定在政治上是有问题的。从政治角度看,后现代女性主义坚持解构我们从大众传媒、通俗文化与艺术所获得的关于性别与性征的信息。这些信息或“文本”是关于怎样才是一个男人、女人及每人应具异性恋爱欲的潜意识说教。如果我们能通过这些信息了解这些东西,如愿意的话,我们也能拒绝或改变它。[15](P188)显然,德里达的“补遗”概念对“酷儿理论”起了工具式的作用。所谓“补遗”则什么也不是,既非现存的也非缺席的,既非实物也非人的本质,是一场“现存的与缺席的戏剧”,其位置是靠“空白的标记”规定在结构中的。“酷儿理论”探讨了性政治中的边缘性问题,扰乱性别区划的常规及自然态,有意识、有目的地制造无序和性征的不稳定性,形成一种性别主体的掏空或无止境的推迟(延异),虽然比起德里达等人的解构理论更具社会政治色彩,但其性取向方面极端的相对主义又将丰富多姿的两性差别中性化或者说“空白”化了。
标签:女性主义论文; 解构主义论文; 德里达论文; 瓦克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酷儿理论论文; 他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