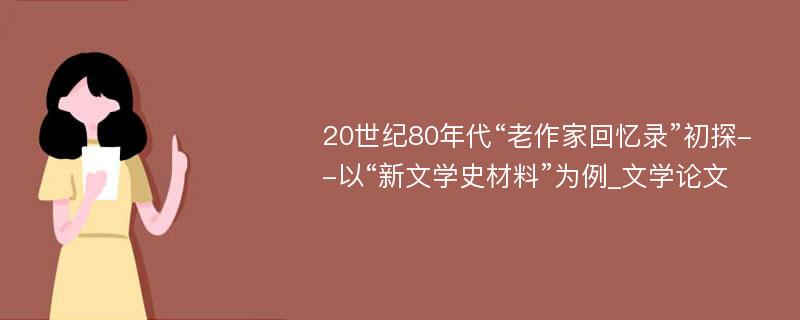
八十年代老作家回忆录初论——以《新文学史料》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为例论文,史料论文,回忆录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80年代”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内涵,转折、回归、反思、繁荣都是其中应有之义。有人笼统地称之为“红火的八十年代文坛”。基于这种红火,当80年代文学成为历史,接受文学史的规训,就有了多种剪裁的可能。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当代文学史,了解到精神、流派甚至代表性作家作品都不尽相同的80年代文学。被反复言说者,成为80年代文坛标签,鲜有提及者,则日益边缘化。是彼时文坛的红火,成就了80年代文学史的多种言说,也为我们今天反思甚或重写那段历史提供了更丰富的对象和更广阔的空间。 80年代初,一批五四运动前后登上文坛的老作家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他们已进暮年,过了文学创作的巅峰期,因此把目光转向过去,以回忆录写作的方式重返文坛。这批回忆录长期以来被视为普通的现代文学研究史料,置于文坛边缘。但将这一现象还原到80年代文坛的大背景中,则回忆录文体的选择,回忆录中蕴含的契约内质和作者的叙事姿态,回忆录写作与彼时文坛的内在关联等问题就变得颇有意味。老作家的回忆录写作,作为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不仅可以丰富对“80年代”文学史的认识,也为重新审视“红火的八十年文坛”提供了别样的历史视角和“冷眼旁观”的考察姿态。 1978年末,由《人民文学》杂志社主办的《新文学史料》丛刊第一期正式出版,刊物以抢救1919年至1949年三十年间与新文学相关的历史资料为宗旨,主要刊发五四以来作家们的回忆录和传记文章①。刊物得到老一辈作家的支持,茅盾、巴金、丁玲、沈从文、冰心、胡风、阳翰笙、徐懋庸等纷纷为刊物撰写回忆录。这些回忆录不仅为现代文学研究者所关注,还吸引大量普通读者,部分文章在刊发后结集出版。《新文学史料》成为“五四”一代老作家在八十年代重返文坛的主要途径,回忆录则成为老作家回归的主要方式。这一独特现象长期为巴金、杨绛等人的回忆、反思性散文写作所遮蔽,不仅未能进入任何一部当代文学史,即使关于“五四”老作家80年AI写作作专题研究的成果,也鲜有论及。基于此,有必要先梳理和描述此现象。 在这批回忆录中,刊发最早,累计篇幅最长,回忆的时间跨度最大,视角最宏阔的,当属茅盾。从1978年第一期刊发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一》,到1986年第四期刊发的《访问苏联·迎接新中国》,《新文学史料》累计刊发茅盾回忆录33篇,时间跨度从茅盾1916年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局工作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长达30余年。回忆录视角开阔,不局限于个人的文学生活,将自己目光所及的重要事件、重点问题全部纳入“回忆”的范围,正如茅盾自己所说“通过回忆录,对那个时代的人生问题和思想问题,提出解答,使后来的年轻人得以借鉴。”②像茅盾这样,借助个人回忆记录宏阔社会现实的还有徐懋庸(1980年第二期至1984年第四期,累计刊发7篇,时间跨度为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结束)、胡风(1985年第二期至1989年第三期,累计刊发17篇,时间跨度为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等。 与茅盾等人的“大回忆”不同,多数老作家的回忆更贴近个人,或将个人经历中最重要的阶段、事件作为回忆的主体内容,如丁玲对参加“左联”活动③、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④和被囚居南京⑤等经历的回忆;阳翰笙对就读上海大学⑥、参加南昌起义⑦和在重庆文化工作委员工作⑧等经历的回忆;陈学昭对两次去延安的经历⑨的回忆等。或将目光集中于个人成长、文学创作经历,如冰心回忆成长经历的《记事珠》⑩;巴金回忆个人创作的《关于〈神·鬼·人〉创作回忆录》(11)《关于〈激流〉创作回忆录》(12)等。 还有一类回忆录,以追忆旧事怀念文坛故友。如沈从文回忆陈翔鹤的《忆翔鹤——二十年代前期同在北京一段生活的点点滴滴》(13);丁玲的《鲁迅先生于我》(14)《回忆潘汉年同志》(15);巴金回忆沈从文的《怀念从文》(16);夏衍回忆宋之的(17)和廖沫沙(18)的文章等。 一部分晚于“五四”一代,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登上文坛的作家也参与到回忆录写作中,如梁斌回忆成长经历的回忆录(19),秦兆阳回忆童年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生活经历的《回首当年》(20),秦牧的《文学生涯回忆录》(21),李又然回忆毛泽东、丁玲、艾青的文章(22)等。刊发老作家回忆录的刊物也不仅限于《新文学史料》,阳翰笙回忆左翼电影活动的《泥泞中的战斗——影事回忆录》三部曲(23)刊发于《电影艺术》;柯灵回忆早期创作活动的《文艺生涯第一步》(24)刊发于《读书》;张中行回忆孙楷第(25)、俞平伯(26)的文章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80年代的老作家回忆录写作,是以“五四”一代为首的老作家应《新文学史料》刊物邀约,并以该刊物为主要载体的一次较为集中的回忆书写。由于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它始终与80年代文学潮流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也因此能够贯穿整个80年代,开启了我国新时期以来第一次文学回忆录写作出版高潮,也培养了新时期第一批回忆录读者群。 《新文学史料》的创办初衷是抢救以“左联”为主的年迈老作家的相关历史资料,刊物名称也在萧乾的建议下由“资料”改为“史料”,以突出其权威性(27)。这决定了老作家们应邀撰写回忆录的着眼点在于历史的真实性而非文学的审美性与抒情性,而且在作家人选、内容剪裁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政治约束。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回忆录不仅作为史料为现代文学研究界所关注,还吸引很多读者将其作为文学作品阅读。 秦牧在其《文学生涯回忆录》的“卷前漫语”中谈到“高等学校和社会上既有若干研究我的作品的人,这么一部稿子,大概也可以提供他们一些原始材料吧!但是,写这么一部书,较大的意义毋宁说还是提供文学爱好者一些参考的材料。社会上的文学爱好者数量颇众……”(28)此文刊出时间为1988年,作者对作家文学回忆录的接受和影响已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为研究者提供史料,更为文学爱好者提供有益的阅读资料。而茅盾(29)、冰心(30)、丁玲(31)等人的回忆录刊出后迅速结集出版甚至再版,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彼时回忆录受欢迎程度。1982年创刊不久的《新文学史料》因“介绍‘左联’不够全面;党内有些机密不应公开;社会主义方向不明确,有问题”等政治原因面临被中宣部停刊的局面,但调查后给出的结论是“刊物不宜停,高校、香港、海外都有影响,但要改进”(32)。 刚刚从“文革”中解放出来人们,文学阅读需求空前,看似繁花似锦的80年代文学创作在初期并不能满足社会阅读需求,客观上推动了老作家回忆录受到关注和追捧。从这批回忆录撰写、刊发、阅读的过程不难发现:80年代初,政治因素仍在文学作品的生产环节具有较大影响,但作品一旦进入阅读、接受环节,政治干预力就会在庞大读者群的作用下减弱,文学重心开始由顺应政治要求向满足读者期待悄悄偏移,读者意识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文坛。 回忆录是当事人回顾自身经历所形成的一类文体,它可以弥补历史记录缺失,澄清历史悬案,丰富丰满历史资源,因此是一类重要历史资料。回忆录的关键在于回忆内容与作者阅历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回忆录的历史价值。回忆录的价值逻辑非常明确:回忆人作为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亲历者、旁观者、见闻者,客观上有呈现历史本来面目的能力。同时,人的记忆并不完全可靠,会因为岁月流逝遗忘或混淆某些内容,也会受个人情感、思想和心理因素的制约,主观上影响回忆录的真实性降低其历史价值。回忆录的“契约性”就是由此提出的。 所谓回忆录的“契约性”,简单地说,就是作者对读者的承诺:写回忆录的初衷,主要回忆哪些内容,自己与相关事件的关系,如何保证回忆的真实性等等。结集出版回忆录的序跋、刊出回忆录的写作说明等是回忆录契约的主要载体。但从刊出的文章看,老作家80年代的回忆录写作,其契约性并不明显。多数回忆录刊出时直接进入正文,没有自序或卷首语为回忆做必要的注脚或说明。对回忆录通例的忽视,可以做两方面解读: 其一,《新文学史料》作为专门抢救和整理现代文学相关历史资料的刊物,自创刊起就持有很强的文学史眼光,最初邀约撰写回忆录的作家都是在现代文学史上发挥重要作用、产生重大影响者,刊物很快在文学界树立了权威。进而在《新文学史料》刊发的回忆录具有了某种隐喻色彩:回忆者在现代文学史上地位高、影响大,参与或见证了很多重要的文坛过往,撰写回忆录的缘由、目的无须多言,《新文学史料》能够刊发就是对回忆内容真实性、准确性的保证。刊物的权威性取代了作者的“回忆契约”。还有一现象可以由反面验证笔者的解读。当回忆录结集出版,只要作家在世,都会主动增补序跋,在其中表明自己的回忆具有“契约精神”。茅盾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序,冰心回忆录《记事珠》自序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这里值得反思的是,社会各界大量文学爱好者阅读作品,参与文学活动,一直被视为80年代文学繁荣的重要表现,但当文学爱好者的参与超出一定界限,尤其是进入文学研究界,某些本属于文学爱好者的偏好、想象甚至盲从,会否因为“人多势众”而干扰到文学研究者和作家,形成80年代文学研究之“魅”呢? 其二,《新文学史料》的权威性,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受邀为其撰写回忆录的作家,使他们的回忆录中蕴含了某种历史优越感。受邀撰写回忆录的老作家,都曾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在现代文坛发挥过重要作用,多已被记入现代文学史。《新文学史料》邀约撰写回忆录,给作家们的感受与进入文学史的感受略有不同,重点由作品和事件转向作家个人。当自己成为关注的中心,成为一类亟待被了解的知识,优越感生发并产生影响在所难免。 在这批老作家回忆录问世前,作家生平都是围绕其文坛经历和创作生涯,做粗线条的勾勒,作家个人往往要让位于作品和事件。而这些回忆录则彻底改变了这一情况。文章或夹杂较多与文坛大事、文学创作无关的枝节,或视角宏大以个人串起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进程。 以茅盾为例,其回忆录视野宏大,可称得上一部现代思想文化史,这自然与他“平生经过的事,多方面而又复杂”有关,但依靠大量翻阅整理资料撰写的回忆录(33),传主作为一条若隐若现的红线,串起了宏大庞杂的社会历史进程。另一方面,茅公回忆录中还用了大量篇幅记录母亲和弟弟泽民的生活,如送弟弟沈泽民去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报到的经过(34),母亲如何为自己照看孩子料理家务(35)等。这些内容与传主的文学创作或文坛经历毫无关系,但可以展现其生活,使读者和研究者对其认识更加生动而立体。显然,“我”成为回忆录的核心尺度,不能不说是带有某种优越感的叙事姿态。茅盾是比较典型的例子,但上述两种倾向在其他作家的回忆录中也有体现,只是程度上略有不同。 作为新时期最初一批有影响的回忆录,带有优越感的回忆书写姿态,主要产生了两方面影响。其一,确立了以传主本人为核心的回忆录写作方式,在回忆剪裁中,“我”成为第一标尺与中心线索。其二是影响了新时期的作家研究。从粗枝大叶的作家生平,到视野宏阔、历史背景清楚、细节丰富的文学回忆录,回忆录不仅带给研究者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还逐步反作用于研究者,将他们的视野从文学事件、文学作品逐步转移到作家本人,将生活经历、生活细节纳入作家研究范畴。还以茅盾为例,邵伯周在80年代中期撰写的《茅盾评传》(36)照比伏志英早年撰写《茅盾评传》(37),明显增加了很多生活经历和生活细节,摆脱了以作品串接写作家评传的模式。这种变化之于文学研究是利是弊,恐难一言蔽之,“度”的把握当为关键。 “真假是非”一直是回忆录的核心问题。谈老作家在80年代的回忆录写作,这个问题自然无法回避。 回忆录之“假”,主要指两种情况,一是弄错了史实,一是漏掉了某些重要内容。这样的情况在老作家的回忆录中显然是存在的。由于本文的主旨并非史实考辨,这里仅举一个最典型的例证。茅盾与秦德君的恋情算得茅公一生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秦德君曾在其回忆录《火凤凰》第三部《樱花盛开又悄悄落下》非常详细地将这段恋情公之于众(38)。但在《火凤凰》出版前,茅盾的回忆录中却对这段恋情只字未提。把母亲、弟弟的生活详细记入回忆录,却对一段重要的情感讳莫如深,这显然是茅盾的主观故意。究其原因,无非主客两个方面。客观上,当时确实对回忆录写作有比较多的限制,比如对重大问题的叙述评价要与中央保持一致,与伟人交往中的对话不能做直接引语,对几次肃反扩大化和尚未有结论的事件不宜过度涉及,有损党员干部统战对象形象的内容不宜涉及,涉及军事机密的不宜写入回忆录,关于民族敏感话题和外交方针的不宜涉及等等(39)。显然茅盾作为曾经的文坛领军人物和文化界领导,与秦德君婚外恋情的隐去是对其正面形象的保护。80年代初,随着第一次回忆录出版高潮的到来,文化界出现了一批督导回忆录写作的文章,这些文章为回忆录写作设置了很多条条框框,客观上影响了老作家回忆录的真实性。此外年代久远,文坛纷繁造成的记忆模糊,为叙事清楚回忆完整所做的空白修补,也是造成回忆录内容不实的客观因素。 主观方面,凡回忆录写作都会有传主有意自我美化的倾向,老作家们自不可免。首先,这些老作家都是现代文坛颇有影响的“大人物”,80年代已近暮年,自知撰写的回忆录很可能是他们在文坛留下的最后印记,如何总结自己的一生,如何把最好的形象留给后人,如何把损害名誉的问题表白清楚,显然是他们撰写回忆录时无法克服的想法。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和在场者身份,《新文学史料》权威性带给他们的历史优越感,则将作为老人“情理之中”的想法放大,几乎改变了回忆录应有的内在精神。 叙事完整,细节生动,相互矛盾是老作家回忆录内容不实的明显表征。今天回看,回忆录中的不实在80年代虽然也曾引起过争论(40),但强度和波及范围还比较有限,众多现代文学史也没有因此而被改写。但这不能排除回忆录不实对文学研究的负面影响。笔者粗略统计了《新文学史料》所刊回忆录的引用情况,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引用的就有近300篇。这些论文引用时是否对回忆录做了考辨我们不得而知,笔者更无意强调史料考辨的重要性或学术态度问题,而只是希望换个角度反思80年代:文学红火、文坛火爆,究竟给文学研究留下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呢?文坛繁荣是否意味着随后的文学研究要对其负责呢? 再看回忆录中包含的“是非”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回忆录就是原原本本地呈现个体记忆中的历史,与价值判断无涉。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回忆录的内容是指向过去的,但其根本目的却是面向未来。回顾梳理过去,明辨是非曲直,给出公允的评价,以正后人视听,这才是有灵魂的回忆录。奥古斯汀和卢梭所撰写的自传回忆录都叫《忏悔录》,他们奠定了西方回忆录的忏悔基调:坦白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在真诚告解中完成内心的救赎。 遗憾的是,我们在老作家的回忆录没有读到忏悔的意味。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自序中谈道:“然而尚欲写回忆录,一因幼年秉承慈训而养成之谨言慎行,至今未敢怠忽。二则我之一生,虽不足法,尚可为戒……所记事物,务求真实。言语对答,或偶添藻饰,但切不因华失真。”(41)冰心在《记事珠》自序中有“书名为《记事珠》,也是我临时想起的。美其名曰‘珠’,并不是说这些短文有什么‘珠光宝气’。其实就是说明每一段文字都像一串珠中的一颗,互不相干,只是用‘我’这一根细线,把它们穿在一起而已。”(42)可见老作家们更重视将回忆录与文学作品区分开,以突出回忆录的真实性,而价值判断并不在考虑范围。茅盾虽谈及“为戒”,但指向的是别人而非自己。 文化差异也好,无宗教信仰也罢,老作家们的回忆录中,以是非判断为基础的忏悔被所谓的尊重历史真实高调置换。充斥着各种整风运动与派系斗争的现代文坛,为平淡不惊的语言娓娓道来,为与价值判断无涉几乎零度的情感叙说,这背后是对回忆录内在精神的放逐,对人生轨迹的最后放任。 反思、忏悔是80年代文学(尤其是1985年后)的重要主题,也是书写80年代文学史的重要标尺。缺乏忏悔意识的老作家回忆录,虽然拥有大量读者,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终于还是被排斥在文学史之外。相反,巴金的《随想录》、杨绛的《干校六记》等具有强烈忏悔、反思意味的作品,则作为新时期老作家创作之典范,载入80年代文学史。顺应文学潮流者,被视作文学作品为文学史所接受,与潮流不符者,则只能作为史料,徘徊于文坛边缘。足见,在文学红火的80年代,主题和潮流势力之强大,它们不仅规划了文坛,决定了其时文学史的基本形态,甚至划定了文学的疆域。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以“五四”一代为首的老作家,借《新文学史料》创办的契机,并以该刊物为主要载体,撰写并刊发了大量文学回忆录。这些回忆录不仅为现代文学研究界所关注,也吸引了大量普通读者,在高校、文化界乃至海外部分地区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回归”是80年代初的文坛主题,老作家以回忆的方式回归文坛,有主客两方面原因。客观上,这些老作家多数创作巅峰已过,一时难以适应新的文学环境和话语体系,而已近暮年恰适合回顾总结自己的文学历程。主观上,以这部分作家的文学成就,都终将留名文学史,而曲折的政治经历时时告诫他们,一定要把握有限的机会盖棺定论,借助回忆录把“不清楚”的历史“说清楚”,给后人留下一个“完整”又“完美”的形象。主客观条件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些老作家无法与当时任何其他作家群“结盟”参与文坛重组,他们只能选择边缘游离。 “回归”不仅指作家的重返文坛,也是80年代初的文学主题。“重返十七年”“回归五六十年代”,所谓“重返”“回归”实为“文革”噩梦中醒来,文学界一段不明未来的徘徊。《新文学史料》的创办,也是一类“回归”,回归最真实的过去,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中寻找未来的出路。老作家的回忆录写作也是回归,回归记忆深处自己最辉煌时候或最希望澄清的片段。 笔者无意评判老作家的回忆录写作,更无力考辨回忆内容的真伪,只是希望呈现这一文坛边缘现象,探索反思80年代文学的零散可能。与“回归”生题的“偶遇”,决定了这些回忆录与80年代文坛的独特关系:入乎其内。作为文坛主题的组成部分,记录了一个类现象,折射出某些机理。出乎其外。游离子文坛边缘,所谓主题的“偶遇”,实则构成了与文坛的“互文”,为反思那段80年代文学提供了一个可以冷眼旁观的独特视角。 ①参看《致读者》,《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一期卷首。 ②引自《记茅公为本刊撰写回忆录的经过》,《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第199页。 ③参看丁玲:《关于左联的片段回忆》,《新文学史史料》1980年第1期,第29-32页。 ④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第37-47页。 ⑤丁玲:《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1期,第4-75页。 ⑥阳翰笙:《回忆上海大学》,《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2期,第19-31页。 ⑦阳翰笙:《参加南昌起义》,《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2期,第19-28页。 ⑧阳翰笙:《战斗在雾重庆——回忆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斗争》,《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第39-64页。 ⑨参看陈学昭:《两次去延安的前后》,《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第183-196页;1980年第2期,第49-64页。 ⑩冰心:《记事珠》,《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第105-110页。 (11)巴金《关于〈神·鬼·人〉创作回忆录》,《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第18-26页。 (12)巴金:《关于〈激流〉创作回忆录》,《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2期,第15-22页。 (13)沈从文:《忆翔鹤——二十年代前期同在北京一段生活的点点滴滴》,《新闻学史料》1980年第4期,第147-150页。 (14)丁玲:《鲁迅先生于我》,《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第21-29页。 (15)丁玲:《潘汉年同志》,《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第190-193页。 (16)巴金:《怀念从文》,《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第4-13页。 (17)夏衍:《之的不朽——〈宋之的选集〉代序》,《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4期,第21-29页。 (18)夏衍:《风雨故人情——〈廖沫沙的风雨岁月〉代序》,《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1期,第185-187页。 (19)梁斌回忆录共21篇,主要涵盖了他童年、少年、青年逐步成长参加革命活动的内容,《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2期至1988年第1期陆续刊发。 (20)秦兆阳回忆录《回首当年》共4篇,在《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至第4期发表。 (21)秦牧:《文学生涯回忆录》共7篇,在《新文学史料》1988年至1989年刊发。 (22)李又然撰写了回忆毛泽东、丁玲和艾青的文章,先后发表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第4期和1983年第2期。 (23)阳翰笙:《泥泞中的战斗——影视回忆录》共三篇,先后在《电影艺术》1986年第一期、第4期和第12期发表。 (24)柯灵:《文字生涯第一步》,《读书》1982年第1期,第113-119页。 (25)张中行:《孙楷第先生》,《读书》1989年第4期,第138-142页。 (26)张中行:《俞平伯先生》,《读书》1989年第5期,第87-94页。 (27)牛汉:《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92-193页。 (28)秦牧:《文学生涯回忆录》“卷前漫语”,《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1期,第4-20页。 (29)以《新文学史料》刊发文章为主体的茅盾回忆录《我走的道路》198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4年即再版。 (30)冰心在《新文学史料》刊发文章基础上扩充而成的回忆录《记事珠》,198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31)丁玲在《新文学史料》刊发的两篇回忆录合并后以《魍魉世界风雪人间丁玲的回忆》于198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32)牛汉:《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94页。 (33)参看《记茅公为本刊撰写回忆录的经过》,《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第198-200页。 (34)参看茅盾回忆录之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二》,《新文学史史料》1979年第2期,第43-54页。 (35)参看茅盾回忆录之六《文学与政治的交错》,《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第165-182页。 (36)参看邵伯周:《茅盾评传》,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37)参看伏志英主编:《茅盾评传》,开明书店,1936年版。 (38)参看秦德君、刘淮:《火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39)参看人民出版社《关于出版回忆录中一些问题的处理方法》,《编创之友》1982年第2期,第9-13页。 (40)80年代围绕老作家回忆录产生的争论,最著名的当属李何林对夏衍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部分内容的质疑,可参看李何林《读夏衍〈懒寻旧梦录〉》,《群言》,1986年第六期。 (41)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42)冰心:《记事珠》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