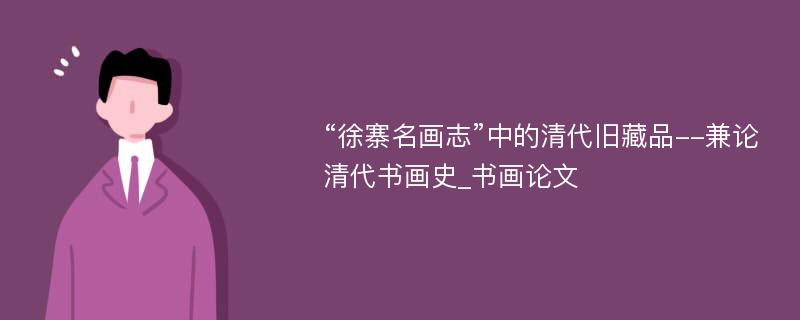
《虚斋名画录》里的清宫旧藏——清代书画鉴藏史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宫论文,名画论文,清代论文,书画论文,鉴藏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浙江南浔人庞元济(1864-1949),字莱臣,号虚斋。其父以丝业起家,为“南浔四象”之一。庞元济继承父业,先后在杭州、塘栖开办丝厂和纱厂,又在上海开办机器造纸公司等,财力颇为雄厚。他酷嗜中国古代书画,其藏品曾先后编入《虚斋名画录》16卷、《虚斋名画续录》4卷和《中华历代名画记》之中。 关于庞氏及其藏品,已经有了一部硕士学位论文,①但《虚斋名画录》这部集大成的古代绘画著录著作本身却未经详细探讨。本文拟从此书著录的42件清宫旧藏画作出发,讨论与清宫旧藏相关的种种问题。 在清季民初收藏家中,庞氏对书画真伪较为敏感。尽管他从未在著录中公开考证自己的藏品,但在《虚斋名画录》、《续录》和《中华历代名画记》的序言里,他反复说明甄别标准之严格。同时,这三篇序言也都透露出他选择藏品的重要准则,即流传有绪。 《虚斋名画录》成书于宣统元年(1909),其序有曰: 每遇名迹,不惜重资购求,南北收藏,如吴门汪氏、顾氏、锡山秦氏、中州李氏、莱阳孙氏、川沙沈氏、利津李氏、归安吴氏、同里顾氏诸旧家,争出所蓄,闻风而至,云烟过眼,几无虚日。② 《虚斋名画续录》成书于民国甲子(1924),序言仍说: 比年各直省故家名族因遭丧乱,避地来沪,往往出其所藏。以余粗知画理,兼嗜收藏,就舍求售者踵相接。③ 两年后(1926),《中华历代名画记》问世。此书是为了参加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向世界介绍中国历代名画而印行的。庞氏自序中说: 唐宋迄今,千有馀载,代远年湮,真迹日少,赝鼎日多……余搜求三十馀年,自辛酉庚子丕变,内府秘本流落人间者,既获快睹购置,而南北鉴藏之家,间有二三名迹,余皆不惜重值,罗而致之。④ 三条序言都讲到购求世家旧藏之事,但仅有第三条提及流落人间的“内府秘本”。事实上,若从具体数量论,《虚斋名画录》及《续录》中的内府旧藏至少有42件,其中《名画录》26件,《续录》16件。⑤这个数目恐怕远多于从各个世家中分别购求的作品数目。不难判断,早在涉足书画鉴藏之初,庞氏已经注意收集内府遗珠,只不过清廷未亡、初亡之际,面对中国读者,可能多少有些忌讳,才未曾公开揭出。 单独来看,这个数目平平无奇,在741件⑥虚斋藏画中不过百分之五。但如果读者熟悉晚清书画著录,可能不难认识到,42件已足以傲视侪辈了。⑦如此体量足以使我们从虚斋藏画入手,观察清宫书画聚散的轨迹。 如众所知,清宫大肆收集书画始于乾隆帝临朝之际。词臣将画作整理编目,乾隆十年编成《石渠宝笈初编》,乾隆五十八年《续编》问世,到嘉庆二十一年,《石渠宝笈三编》亦告完成。至此,清宫不再锐意搜求民间书画。尽管乾隆执政只一甲子,但他持续不断地“收藏书画”,实已彻底改变了书画鉴藏活动在民间的生态环境。虚斋旧藏清宫书画足以从侧面说明这一点。 《虚斋名画录》卷二著录的钱选《浮玉山居图》,是一幅赫赫有名的重宝,在入宫之前,它曾经明代姚绶、项元汴等题跋收藏。卷七著录的赵孟烦《桐阴高士图轴》,入清宫前,康熙年间吴其贞《书画记》、吴升《大观录》等私家著录都曾记载。卷七尚有元柯九思《清閟阁竹石图轴》,这幅画自晚明起流传众手,先后经过项元汴、卞永誉、安岐、归希之等诸家递藏,随后进入乾隆内府。王蒙《夏日山居》也同样曾经在《墨缘汇观》、《式古堂书画汇考》、《平生壮观》、《江村销夏录》、《大观录》五部康熙年间私家著录中大出风头。 一旦入宫,这些作品就有可能销声匿迹。有一些画,到庞元济著录时,至晚仅有乾隆、嘉庆御题和玺印,从那以后,直至宣统,一百多年间流传情况几成空白。例如前文刚刚提到的《夏日山居》,尽管康熙年间煊赫一时,但自乾隆钤印题诗之后,到《虚斋名画录》著录此画之时,竟然没有添加任何其馀藏家的印记。又如卷八丁云鹏《灌蒲图轴》,在明末陈眉公钤印之后,也仅有乾隆诸印。《虚斋名画续录》里,元代赵善长《合溪草堂图》,仅有乾隆御题和玺印,明代陆治《秀石玉簪图》,仅有嘉庆诸玺印,恽寿平《花卉山水册》,仅有乾隆诸玺印。 相似地,乾嘉间词臣奉诏而作的一些画,例如张宗苍《万木奇峰》、董邦达应制画册、关槐《仙山楼阁》、董诰《名山大川》等等,也都仅有内府诸印。它们究竟怎样流散人间,至今还不可确知。 不过,多数清宫作品的散出轨迹仍然清晰可考。比庞元济年长二十岁的陈康祺(1840-1890),在一条讨论《石渠宝笈》的笔记中谈到内府收藏的散出: 今时隔百馀年,或分颁朱邸,或恩赏近臣,且经庚申淀园之变,金题玉躞亦竟有流落人间者,详晰纪叙,庶博雅嗜古之士,获睹瓌宝,知所慎焉。⑧ 这里所谓“庚申淀园之变”,指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烧毁圆明园之事。庞氏在《中华历代名画记》序言中所说的“辛酉庚子丕变”,则分别指1861年慈禧导演的北京政变和1900年的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战乱。要言之,他们都将清末乱局与宫廷旧藏流散的现象联系起来,这类情况易于理解。有学者论及清宫旧藏书画散佚问题,便贵近贱远,对赏赐群臣的书画一笔带过,着重突出以上几次事变的坏影响,并补充了清季逊帝溥仪、大臣与太监将书画盗卖出宫,以及伪满国兵的哄抢等情况。⑨其实,成书于宣统元年,已收有26件清宫故物的《虚斋名画录》,适足以说明藏家不待沧海横流,便早有机会接触内府故物——这26件画作中,乾隆以后流传可考的起码有15件,足以说明它们并不是在乱世中突然被带出宫廷的。甚至在成书于1924年的《虚斋名画续录》中,16件清宫故物里,也有11件流传有绪。这些作品重返人间的路径如出一辙,即由皇帝赏赐贵戚近臣,随着代际变迁,逐渐从故家散出。 在讨论赏赐散出之前,首先要介绍《石渠宝笈》著录书画的钤印规则。参与编辑工作的阮元在《石渠随笔》里详尽解释了钤印规则: 钤用宝玺,曰八玺。全者“乾隆御览之宝”椭圆朱文、“乾隆鉴赏”正圆白文、“石渠宝笈”长方朱文、“宜子孙”方白文、“三希堂精鉴玺”长方朱文、“石渠定鉴”圆朱文、“宝笈重编”方白文。凡列朝及臣工书画皆用此七玺。其藏乾清官者,则用“乾清官精鉴玺”;宁寿宫、养心殿、御书房皆如之。此玺并上七玺为八玺。其在圆明园者惟七玺而已。至于乾隆十年以前先入《石渠宝笈》之件,则无“石渠定鉴”、“宝笈重编”二玺,而间有“石渠继鉴”者,乃已入前书而复加题证者也。⑩ 但我整理《虚斋名画录》中42件清宫旧藏作品,发现除了2件例外,此外40件都有符合钤印规则的乾隆御印,有些还有嘉庆御印,(11)而这40件却并不都见于《石渠宝笈》初编至三编之中。事实上,钤印俱在,而不见于著录的反而是多数。除了一件题为《董文恪应制画册》的作品,由于题名方式特殊,无法查考之外,在剩下39件作品中,《石渠宝笈》收录的仅有13件,没收的倒有26件。(12) 进一步考察钤印和著录情况,还能发现更多有趣的信息。凡阮元所谓“乾隆十年以前先入《石渠宝笈》之件”,也就是主要只盖“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石渠宝笈”、“宜子孙”和“三希堂精鉴玺”五玺的画作,《虚斋名画录》与《续录》共收有26件;但我在《石渠宝笈初编》中仅仅找到2件,此外24件都没有找到。凡依阮元所言,钤有“宝笈重编”等印的,庞氏共收8件,这8件全部能在《石渠宝笈续编》中找到。凡钤有“嘉庆御览之宝”与“宝笈三编”诸印的共5件,2件见于《石渠宝笈三编》,另外3件同样找不到。 钤印制度如此精详,画上清宫玺印基本相合,其中部分画作流传过程又比较清楚,因此就表面证据而言,这些没有进入《石渠宝笈》的作品不太会是乾隆以后的伪作。然则见载著录与否,何以如此纷歧,又无准绳呢? 故宫博物院的杨丹霞曾提供一种解释: 常会看到市场上一些作品,尤其是清代宫廷绘画,幅面上有许多内府印记,但是都缺少殿座章,而《石渠宝笈》著录作为内府书画总帐,是按书画所存放的地点登记的,如重华官、养心殿、静寄山庄、御书房、乾清宫、学诗堂等,存放在各处的书画画心必定有以其所放宫殿名称专刻的“殿座章”。如冯承素摹《兰亭》中左侧最末一印“重华官鉴藏宝”。(13) 她又谈到,这个规则是乾隆帝亲自制定的: ……谕旨曰:“何者贮乾清宫,何者贮万寿殿、大高殿等处,分别部居,无相夺伦,俾后人披籍而知其所在。”《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各编也都依此体例,并无更易,如果画幅上没有标示这些宫殿的殿座章,也就意味着此物从未经《石渠宝笈》著录,否则,皇帝要看时去哪里找?所以,判断是否确经《石渠宝笈》著录,殿座章是不可或缺的。(14) 杨氏承认确有少量例外。譬如多卷多册的作品,殿座章可能只钤在其中一卷或一册上。若今日已非全帙,看起来便是一件没有殿座章而确为《石渠宝笈》系列书籍著录的作品。但这并不影响其以殿座章为著录标准的根本观点。可是揆诸《虚斋名画录》中的记载,杨氏所言显然不确。 《虚斋名画续录》收入了曾经《石渠宝笈续编》著录,旧藏于懋勤殿的《宋徽宗鸜鹆图》。核对两书著录的文字与印章,分毫不爽,当为同一件作品。《石渠宝笈续编》说明这件作品“七玺全”,没有额外著录殿座章。(15)而《虚斋名画录》的著录,仅在此基础上多了一枚“嘉庆御览之宝”。(16) 同样见于《石渠宝笈续编》的《宋李嵩西湖图卷》,旧藏于淳化轩。《虚斋名画续录》著录七玺与“古稀天子”、“寿”、“八徵耄念之宝”、“水月两澄明”、“中心止水静”诸玺印,(17)与《石渠宝笈续编》完全相同,(18)殿座章并未出现。 这两例足以证明,以殿座章来判断是否经过《石渠宝笈》著录,起码对《续编》并非全然适用。同样供职于故宫博物院的王赫也讨论过《秘殿珠林》与《石渠宝笈》的钤印规则,他的结论比杨丹霞更为细致一些。仍以《石渠宝笈续编》为例,他说: 初入选的书画钤盖“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秘殿珠林”(或“石渠宝笈”)。最终著录于书中的书画加盖“秘殿新编”、“珠林重定”(或“石渠定鉴”、“宝笈重编”)二玺。另外,贮藏于养心殿、乾清宫、重华宫、御书房、宁寿宫5处的书画加盖相应的殿座章(“养心殿鉴藏宝”、“乾清官鉴藏宝”、“重华宫鉴藏宝”、“御书房鉴藏宝”、“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即所谓的“八玺全”。(19) 审其文意,似乎入于《石渠宝笈续编》,而并非藏于乾清宫、养心殿、重华宫、御书房和宁寿宫的书画,是只钤七玺,无所谓殿座章的。若果如此,《虚斋名画录》中两例当然不再成为问题,但事实亦非如此——在《石渠宝笈续编》中,紧挨着《宋李嵩西湖图卷》的《马远探梅图》,除了“七玺全”,赫然还有“淳化轩”、“淳化轩图书珍秘宝”等玺印。(20) 前引两文致力于提出涵盖全局的钤印规律,从而进一步认识《石渠宝笈》系列书籍,其意诚然可嘉。但两位作者意见已难免彼此扞格,而与实例相较,又各自不能相符。这起码说明《石渠宝笈》著录远比我们认识的更复杂,是否存在统摄全局的规律,或者“例外”的比例有多大,都还不宜断言。不过,具体到《虚斋名画录》,对其中那些钤有诸玺而不见于《石渠宝笈》的作品,确实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它们大多是乾嘉两帝赏赐群臣的作品。 以下将依据本证与旁证来讨论赏赐问题。 1、赏赐内容: 42幅画中,有直接证据说明出自赏赐的——钤有“恩赐”或“赐本”印,或由臣子亲自题跋说明受赏——有7幅;有间接证据,即加盖“臣××印”,或钤印者属于皇亲和词臣,说明极可能出自赏赐的,有6幅。另外我还找到1幅本身没有任何信息,但文献证明出自赏赐的作品。这说明臣子确实可能把赐画小心收藏起来,却不在画上留下痕迹。因此,对前文提到的那些仅有乾嘉玺印,没有后代流传情况的画,仍然要慎重对待,不能一概认定为晚清动乱时仓促出宫的作品。 在总共14件赏赐作品中,仅有1件著录于《石渠宝笈》,那是钱选《浮玉山居图》,咸同间由慈禧太后赏给军机大臣孙毓汶,当然是特例。剩下13件,《石渠宝笈》初编至三编均无著录,说明赏赐群臣的作品确实不在《石渠宝笈》著录之内。 亲历《石渠宝笈》编撰的阮元,留下两段重要文字,说清了赏赐臣工书画的一般逻辑。吴荣光《辛丑销夏记》卷二记有《宋游昭春社醉归图》一卷,道光十六年,阮氏跋曰: 此卷确是宋人真迹。其落款四字,尤苍莽可喜。项氏跋印皆佳,惟子京标题为《秋林醉归》,未确……当改称曰《春社醉归图》。此乃乾隆间办《石渠宝笈》时误挑落者。惟时落者每以分赐诸王大臣,元亦曾被赐数件,今敬藏于家。(21) 《雷塘庵主弟子记》转记阮氏《揅经室再续集》卷七自叙平生之语: 乾隆癸丑,臣三十岁。正月茶宴,赐题杜琼《溪山瑞雪》一轴。御笔题云:雪景溪山写杜琼,玉为世界不孤名。老翁驴背循溪路,输与凭窗望者情。谨案:此等旧画,皆办《石渠宝笈》时挑落次等之件。御制诗己酉春题。此轴圣旨留待茶宴时分赏近臣,而臣适分得此轴。(22) 览此两条,可知编选《石渠宝笈》时曾对入藏书画进行甄别,凡打入次等,也即“挑落”者,往往分别赏给王公大臣。这说明了何以钤印俱在,赏赐轨迹清楚的作品却不见于《石渠宝笈》。从阮氏行文语气来看,“挑落”这个工作,乾隆似乎并不亲自参与——阮元胆子再大,也不敢说乾隆“误挑落”了某画——但“挑落”的画如何处理,则确实出自金口玉言,需经“圣旨”决定,方才在茶宴上公开赏出。换句话说,好东西留在宫里,“不够好”的,才有机会重返人间。至于“好”与“不好”的标准,隐含着乾隆宫廷对书画的品鉴趣味和真伪观念,值得日后详加探讨。 2、赏赐制度: 《虚斋名画录》里这些赏赐画作,分别赏给了彭启丰(1701-1784)、张若淮(1703-1787)、刘墉(1719-1804)、金士松(1730-1800)、董诰(1740-1818)、阮元(1764-1849)、英和(1771-1840)和载铨(1794-1854)。从生卒及仕履来看,这些主要是乾隆的臣子。除了载铨,活跃于嘉、道、咸时期的不算太多,且诸人入仕之初都还在乾隆末年,又大多从词苑清华之职起家: 彭启丰雍正五年状元,历官修撰,入职南书房,乾隆间历任多部。张若溎为张英之孙,雍正八年进士,从外任做起,历任侍郎及左都御史,在殿试、乡试中充任考官,做过山东学政,又总裁四库全书馆。刘墉乾隆十六年进士,做过学政、知府、乡试考官,四库馆副总裁,直至体仁阁大学士。金士松乾隆二十五年进士,以后从庶吉士做起,历任编修、学政、侍郎、尚书,直南书房。董诰乾隆二十九年进士,庶吉士、学士、侍郎、四库馆副总裁,直至东阁大学士。阮元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庶吉士、编修、詹事、直南书房,后来历任各地学政、巡抚、总督,直至体仁阁大学士。英和乾隆五十八年进士,庶吉士、编修,直至军机大臣、户部尚书。 仕履如此,这些人都有机会接近天颜。反过来讲,则不妨作一推测,即:品级低于这个档次的官员,可能就没有机会获得赏赐。而书画是怎样赏下来的呢?《虚斋名画录》卷二著录金代李山《风雪杉松图》,乾隆五玺俱全,后有彭启丰自跋,写明赏出原委: 乾隆二十八年春孟六日,皇帝御重华宫,召廷臣共二十四人赐宴。臣启丰蒙恩与焉,有顷,御制律诗二章,即命臣等赓和。又特颁内府鉴藏名人画卷各一,臣启丰得《风雪杉松图》。顿首祗受,宴毕携归邸舍……(23) 卷八又著录明代杨基《淞南小隐图》。(24)此画本身没有任何信息,但我在陆锡熊《篁村集》和钱大昕为陆氏写的墓志铭里,都看到陆氏蒙赐此画的记载。《墓志铭》劈头就说: 文渊阁直阁事大理寺卿陆公锡熊以博洽通儒承天子知遇,由郎官入词垣,领袖四库书局,洊登学士,遂列九卿……大理尝被召预重华宫联句,赐御题杨基《淞南小隐》画卷。公以里居在淞江南,因自号淞南老人,以识君恩。(25) 卷八另著录两件五玺俱全的文徵明画作,分别有董诰、刘墉跋: 乾隆三十八年正月十二日,重华宫茶宴联句,赐内廷供奉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臣董诰。(26) 乾隆丁酉岁正月六日,重华宫茶宴蒙恩赐臣刘墉敬识。(27) 《虚斋名画续录》卷二著录明唐寅《古槎鸜鹆图》,同样五玺俱全。后有张若淮自跋,则是这么写的: 乾隆甲午孟春八日,承恩召至重华宫联句侍宴。恭和御制元韵二首,蒙赐御题唐寅画一幅,玉如意一柄,金星砚一方,旷典殊荣,传示子孙,永为世宝。(28) 以上所有记载,都说明赐画得自每年正月的重华宫茶宴。这是乾隆八年以后成为定例的仪式性宴会,于每年正月举行,活动内容年年相同,赏赐也是例行公事。《国朝宫史》卷七〈乾清宫曲宴群臣仪〉对此有详细的说明: 恭遇每岁新正,特召内廷大学士、翰林于重华宫茶宴联句。奏事太监预进名签,既承旨,按名交奏事官员,宣召入宫祗俟。届时引入。宫殿监预饬所司具茶果承应宴戏。懋勤殿首领太监等具笔墨纸研,诸臣俱以次一叩列坐。御制诗下,授简联赓。宴毕,颁赏诸臣,跪领趋退。其恩赐之物,宫殿监临期恭钦定,排列呈览。(29) 而沈初《西清笔记》对赏赐之物记载更详,有“如意、画轴、端砚、荷包等件”,且“是日所赏名人画轴,必有御制诗句题帧间”。(30)因此我们知道,乾隆年间每逢正月,清宫藏物总会赏出去一些,画轴也在其中。这个赏赐,每次数目肯定不太多,因为沈初记载联句情况时,曾经说过“近常派二十八人……大约派入宴者二十人,馀八人与联句而不入宴”(31)的话。但年年如此,从书画流通的角度,就必须承认,自乾隆初年民间书画成批入宫之日开始,也渐渐有一部分画作,像水滴一样,从清宫中又慢慢跌落到人间。 根据陆燕贞〈清代重华宫茶宴联句〉一文研究,乾隆归政嘉庆时,要求将重华宫茶宴著为家法,世代遵行。后来嘉庆朝确实年年照旧,道光时偶尔仍之,咸丰时才停办茶宴。(32)陆氏还根据《御制诗集》,数出乾嘉两朝总共举办茶宴次数为60次。文献记载确也证明,嘉庆时重华宫茶宴照旧会赏赐书画——黄鉞《壹斋集》里,就曾提到嘉庆丙寅正月四日,他在重华宫茶宴联句之后,蒙赐沈周《评砚图》的事。(33) 倘以每年20位臣子每人得一幅画来计算,六十次茶宴之后,可能有一千件左右的旧画缓缓流出了清宫。这当然不是确数,因为有时预宴人数超过20人,(34)有时画轴又不在茶宴赐物之中。(35)异日若有人能通盘检阅乾嘉两朝宫中档案,或许可以得出精确的数目。不过,重华宫茶宴并不是清宫颁赐藏画的唯一渠道。就以阮元为例,在参与编辑《石渠宝笈续编》的乾隆五十六年,他曾经“被赐宋人《货郎图》一轴,元人《戏婴图》一轴,蒋廷锡《牡丹》一轴,董其昌手札一册,恽寿平山水一册,赵孟頫《无量寿佛》一轴,王维烈《九如图》一轴”,(36)画共7幅。 至此起码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六十多年内,清宫似一个水库,一边大量吸纳民间藏品,一边缓慢地,可能也是匀速地开闸泄洪。只不过蓄水量毕竟远大于泄水量,因此不大为人注意罢了;有学者认为“乾隆时期,内府书画外流的现象基本绝迹”,(37)恐是想当然耳之辞。 此外,根据刘迪统计,《石渠宝笈》初编至三编共收画11011件,其中包括2096件乾隆御笔。(38)若我的推断没有大误,那么乾嘉两朝散出的清宫旧藏画作,在比例上就不算很小。前文已经说明,这些作品几乎不入《石渠宝笈》。这就证明《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系列著录并不能完整地反映乾嘉书画府库的体量。事实上,去内府中报过到、打过转的书画,肯定比著录数目还要多。当我们讨论清宫书画鉴藏的数量、趣味和整理情况时,必须把这默默无闻的一部分也考虑进去。 最后我想讨论一下清宫画作散出后的情况。让我们回到《虚斋名画录》。我无暇详考所有清宫旧藏书画赏赐出来之后的流传轨迹,仅能就较为明显者介绍一二: 《虚斋名画录》卷二李山《风雪杉松图》,自彭启丰(1701-1784)受赏以后,又钤有吴云(1811-1883)印。卷八张宏《秋山观瀑图》,和《续录》卷二沈周《杏花》,都经金士松(1730-1800)之后,归于左仁。左氏为道光八年(1828)举人,后任邳州知府。《续录》卷一吴镇《峦光送爽图》,则经英和(1771-1840)收藏之后,可能曾在谢刚杰(1892-1968)(39)之手。据此观察,咸同以后,世家子已未必能保守先人的荣耀记忆,“金题玉躞”渐渐散布出来。但我竭力检查清中期以后的书画著录和相关文献,却发现收藏清宫故物实不自庞氏始。与他同时的端方(1861-1911),在《壬寅销夏录》里,已著录十馀件清宫旧画;比他早一辈的李佐贤(1807-1876)——也就是《虚斋名画录》序中提到的“利津李氏”——也收藏过十馀件清宫故物。再往前找,吴荣光(1773-1843)《辛丑销夏记》亦记数件,而辛丑为道光二十一年(1841);更有甚者,书中所记一件清宫旧藏倪瓒《优盋昙花轴》,早在嘉庆丁卯(1807)年已入吴手。(40)这些藏品是否全出于赏赐散出,本文无法一一考定。但起码知道,早在嘉庆年间,清宫散出的画作已经开始引人注意,甚至进入了新一代收藏家的府库。 尽管这些藏品总体来说数量有限,但我认为它们仍然可能影响到晚清的书画鉴藏。乾隆内府藏画体量如此庞大,真伪不能无疑,乾隆误判《富春山居图》的故事就足以为证;而“挑落”的作品,质量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更下一等。乾隆拿这些画赏赐臣下,以今视之,实在不大厚道,但在当日却是多数臣子难以企及的殊荣。从前文所引题跋来看,这些获得颁赐的人根本没有把赐画当成普通的“古画”来鉴定、评价、讨论。就算画真是假的,或者确实画得不好,又有谁敢说出来触霉头呢? 如此,赐画的真伪失去了讨论的馀地,它们“只能是真的”。倘作进一步推论,恐怕那些未必全经赏赐而出的清宫画作,也因本身玺印俱全,同样变得不宜评断。晚清鉴藏家购求这些画时,上距乾隆赏赐已隔数代。他们很可能根本不会对这些自证其真的东西产生有效的怀疑——若非相信内府旧藏皆是真迹,庞元济何苦辛苦裒集这42件古画?要知道,这个数目比端方、李佐贤和吴荣光三家加起来还要多! 我曾在另一篇文章里讨论过,比起康熙时期来,晚清鉴藏家面对早期书画时,真伪判断标准有所下降。(41)清季的葛金烺父子等人面对所谓早期名迹之时,只要画得好,兼有清代的递藏轨迹,也就能信之为真。我认为这一定程度上跟清宫大肆搜求民间藏品,致使民间藏家不再像康熙时期那样有机会大量接触早期书画有关。市面上的书画变少了,但对早期真迹的渴望偏偏总是存在于鉴藏家心中,因此他们选择降低标准,以维系早期真迹仍然传世的信念。这就说明,鉴藏家面对真伪问题,并不总是在做事实判断,尽管他们自己未必自知。这一点对本文也同样适用:清宫旧藏当然不都是真迹,但身处晚清民国之际,面对乾嘉两朝的赐画传统,确实有一些鉴藏家愿意信之为真。归根结底,这本不过是编撰《石渠宝笈》时无心抛向百年后的一段波澜;但风浪虽小,却也提醒我们,胶柱鼓瑟不足以语历史,每一个故事都彼此相关。 注释: ①姚沐撰,《庞元济虚斋书画收藏研究》,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②[清]庞元济著,《虚斋名画录》,序,载《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09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74页。 ③[清]庞元济著,《虚斋名画续录》,序,载《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09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82页。 ④转引自姚沐《庞元济虚斋书画收藏研究》,第26页。 ⑤这个数字是我翻阅《虚斋名画录》及《续录》后,根据御题和清宫钤印整理得出的,可能偶有挂漏。因此,这个数字是《虚斋》两录中清宫旧藏作品的下限。 ⑥姚沐统计《虚斋名画录》及《续录》藏画共741件。见《庞元济虚斋书画收藏研究》,第18页。 ⑦7参见第四节。 ⑧[清]陈康祺著,《壬癸藏札记》,卷九,清光绪刻本。 ⑨参见赵聆实撰〈清宫书画散佚问题研究〉,载《博物馆研究》,2011年第3期,第70-74页。 ⑩[清]阮元著,《石渠随笔》,卷八,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169-170页。 (11)其中一件是张宗苍应制所作,仅钤“乾隆御览之宝”、“乾隆宸翰”、“几暇临池”三印,尚可理解。另一件唐戴嵩《斗牛图轴》,本身无款,仅钤有不成体统的“乾隆御览之宝”与“石渠宝笈”两玺,其馀“宣文阁宝”、“尚书省印”、“□□司印”和“安仪周家珍藏”四印也散乱无章。康熙末年,安岐曾经著录此画,孙承泽、吴其贞也都提到过它,可知起码是一幅旧画。但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宫旧藏《戴嵩斗牛图》,却有乾隆诸玺和题诗,与此画尺寸也大为不同,并非一幅。因原画不可见,何以只有两印尚不可知。推测或是画从清宫流出后曾遭割裂,或是此画始终不曾进宫,贾人故意加此两印以为之增重。 (12)这一结果是根据雅昌艺术网提供的书画著录检索得出的,该检索数据库包括了《石渠宝笈》初编、二编和三编。我使用作者和画名两种方式分别检索,以期避免因为画名著录不同而导致的误差。事实上,同一画作,在《石渠宝笈》与《虚斋名画录》中,确实偶有异称。 (13)杨丹霞撰,〈《石渠宝笈》与清代宫廷书画的鉴藏(中)〉,载《艺术市场》,2004年11月,第134页。 (14)同注13,第135页。 (15)[清]王杰等辑,《石渠宝笈续编》,宫内等处藏五·懋勤殿三,载《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07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2页。 (16)同注3,卷一,第196页。 (17)同注3,卷一,第197页。 (18)同注15,淳化轩藏四,载《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073册,第524-525页。 (19)王赫撰,〈图说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的钤印〉,载《艺术市场》,2011年6月,第83页。 (20)同注18,第525页。 (21)[清]吴荣光著,《辛丑销夏记》,卷二,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37-138页。 (22)[清]张鉴等著,《雷塘庵主弟子记》,卷八,清光绪间仪征阮氏刻本。 (23)同注②,卷二,第320页。 (24)同注②,卷八,第510页。 (25)[清]钱大昕著,《嘉定钱大昕全集·潜研堂文集》,〈封通议大夫日讲起居注官文渊阁直阁事翰林院侍读学士加三级陆公墓志铭〉,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55页。 (26)同注2,卷八,第519页。 (27)同注2,卷八,第520页。 (28)同注3,卷二,第232页。 (29)[清]鄂尔泰等编,《国朝宫史》,卷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6页。 (30)见[清]沈初著,《西清笔记》,卷一,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6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97-598页。 (31)同注(30),卷二,第605页。 (32)陆燕贞撰,〈清代重华宫茶宴联句〉,载杨新编《故宫博物院七十年论文选》,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第108页。 (33)[清]黄鉞著,《壹斋集》,卷二十,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2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71页。 (34)前引彭启丰题跋就能证明这一点。 (35)乾隆五十七年,阮元参与重华宫联句,所受赏赐为“端砚一方,三清瓷碗五器”。见王章涛著,《阮元年谱》,黄山书社,2003年,第43页。 (36)同注⑩,第170页。 (37)刘迪撰,《清乾隆朝内府书画收藏——以〈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为基本史料之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78页。 (38)同注(37),第83页。 (39)画上有“慈舟秘笈”印。晚清谢刚杰字慈舟。见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72页。 (40)同注(21),卷四,第297-299页。 (41) 参见陆蓓容〈管窥清代鉴藏史——葛金烺与《爱日吟庐书画录》〉,待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