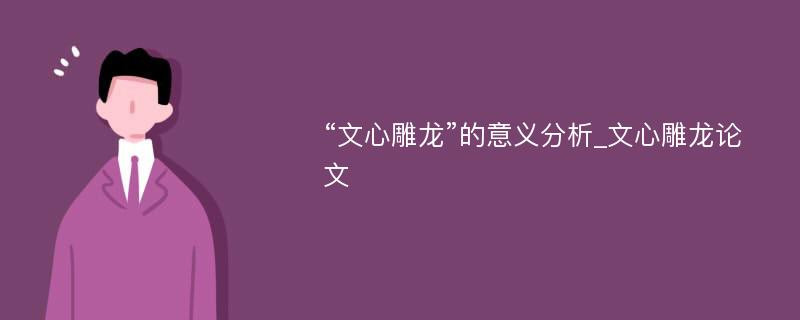
《文心雕龙#183;风骨》篇义析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心雕龙论文,风骨论文,篇义析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文心雕龙·风骨》篇义的关键问题,自然是对“风骨”概念内涵的理解。“风骨”可以说是《文心雕龙》中歧说最多的概念之一了。陈耀南先生在《文心风骨群说辨疑》一文[1]中,曾搜罗六十四种说法分为十类,并加以按断,可见纷纭的概况。不过概要说来,可大致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意见是将“风”“骨”分属意、辞,认为“风”指“文意”,“骨”指“文辞”。黄侃先生在《文心雕龙札记》[2]中说:“风即文意,骨即文辞。”这一说法曾发生很大影响,后来也颇遭到一些人的非议,认为“风”不就是文意,“骨”不就是文辞。这自然是不错的,但也包含对黄先生说法的某些误解。如不以辞害意,综观《札记》全文,则黄先生的本意实是说,“风”是属于文意范畴的事,“骨”是属于文辞范畴的事。故其释《风骨》篇之“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二句时说:“明言外无骨,结言之端直者即文骨也;意外无风,意气之骏爽者即文风也。”于释“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二句时又说:“即谓辞精则文骨成,情显则文风生也。”这说明黄先生并非说“风”即是文意,“骨”即是文辞。“意”能达到“风”的高度,“辞”能达到“骨”的高度,是有其标格与要求的。所以他又说:“辞精则文骨成,情显则文风生。”辞不精则有辞而无骨,情不显则有意而无风。范文澜先生深得其意,故在注《风骨》篇中阐释篇义说:“窃复推明其义曰:此篇所云风情气意,其实一也。而四名之间,又有虚实之分,风虚而气实,风气虚而情意实,可于篇中体会得之。辞之与骨,则辞实而骨虚,辞之端直者谓之辞,而肥辞繁杂亦谓之辞,惟前者始得文骨之称,肥辞不与焉。”[3]不过,黄先生与范先生都没有对“风”和“骨”的内涵做更细致的分析罢了。
周振甫先生也是将“风”“骨”分属于意、辞的。他说:“‘风’是感动人的力量,是符合志气的,跟内容有关。”“‘骨’是对构辞的要求,用辞极精练,才有骨。”[4]不过他对情而具风、辞而备骨的标格要求,更多是从文章的力度上及对人的影响方面着眼。如果说周先生提出感动力还只是偏于“风”,那么宗白华先生的说法就明显趋于全面了:“‘风’是由情感发出的感动力”,“‘骨’是由词所表现清楚的概念内容发出的感动力”[5],虽然感动力的基础还在于内容,但承认“辞”也具有加强感动力的作用。罗宗强先生认为风是“感情的力”,骨是“表现出力量的笔致”[6],也是从力度上着眼的。
周、宗二位先生提出“志气”“情感”的感动力,虽未明确阐明“志气”“情感”的内质,其中必然含有思想教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陆侃如、牟世金两先生就在这一方面有明确的发挥了:“‘风’是风教:作品内容的教育感化作用”,“‘骨’是骨力完善的文句对读者的影响力量”。[7]后来牟世金先生又指出:“‘风’是要求作者高昂的志气用周密的思想,表达出鲜明的思想感情,并具有较大的教育意义和感人力量”,“‘骨’是要求用精当而准确的言辞,把文章组织得有条不紊,继而产生刚健的力量”。[8]这种意见虽然还不脱“风”“骨”分属意、辞并对意、辞的标格有所要求的范畴,但强调风教,着眼点已有明显的分别了。
第二类意见虽也是“风”“骨”两分,但以“风”指情思,“骨”指事义,并特别强调二者之间的关联。这样“骨”就不单纯是辞语范畴的事,而与“事”特别是“事”中之“义”紧密关合在一起了。刘永济先生说:“风者,文之情思也,情思者,发于作者之心,形而为事义。就其所以运事义以成篇章者言之为‘风’。”“骨者,树立结构之物,喻文之事义也。事义者,情思待发,托之以见者也。就其所以建立篇章而表情思者言之为‘骨’。”[9]很明显,这已将“风”“骨”二者联成一体,意谓事义在内体现为全篇文思者为“风”,事义在外体现为全篇树立结构之物者为“骨”。廖仲安、刘国盈两先生的说法可以说是对这一主张的进一步发挥:“‘风’是情志”,“是发自深心的,集中充沛的,合于儒家道德规范的情感和意志在文章中的表现。惟其发自深心,合乎规范,才能‘成为化感之本源’;惟其集中充沛,才能风力遒劲,不致‘思不环周,索莫乏气’。”“‘骨’是事义”,“是指精确可信、丰富坚实的典故、事实,和合乎经义、端正得体的观点、思想在文章中的表现。事义的运用和取舍虽然得从属于情志,但是也能加强情志的力量。”[10]廖、刘二位先生对“风”的情志、“骨”的事义有了更为具体的界定,而且无论“风”还是“骨”,都更加强调与儒家经义之间的密切关系。
第三类意见是对“风”“骨”是意、辞的较高标格要求的意见的升华,进一步认为“风骨”乃是一种风格和美学风范。此说尤其与讲“风”“骨”的力度有关,力度接近于一种遒劲的风格。罗根泽先生说:“‘风骨’为文字以内的风格。”[11]马茂元先生的《说风骨》[12]、吴调公先生的《刘勰的风格论》[13]都认为风骨“即风格”。王运熙先生说:“‘风’是指文章的思想感情表现得鲜明爽朗,‘骨’是指语言质朴而劲健有力”,他认为风骨合起来,是指作品具有明朗刚健的艺术风格。[14]詹锳先生说:“‘风骨’是刚的风格,就是鲜明生动、雄健有力的风格。”[15]由此再进一步推衍,“风骨”就被评定为一种审美价值了。周振甫先生说:“‘风’是内容的美学要求”,要求“写得鲜明生动而有生气”,“写得骏快爽朗”;“‘骨’是对作品文辞方面的美学要求”,“是对有情志的作品要求它的文辞精练,辞义相称D有条理,挺拔有力,端正劲直。”[16]
第四类意见是把“风骨”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有的禧个看作是一个东西,不可分说;有的虽遥承认二者有分别,但把其相互关联渗透看成是更为主要的,并且认为二者都是属酉内容泛畴的。郭预衡先生说:“‘风骨’都指深厚的内容,不指形式。”[17]徐复观先生提出:“‘风’是气之柔者,内容为感情”,“‘骨’是气之刚者,内容为事义理义”,“合而言之,由有刚有柔之‘气’……由内在情性通到外在文体的桥梁……落实到文体而形成‘风’与‘骨’,即人之生命力在文章中表现之两种艺术形象。”[18]郭绍虞先生又提出:“风谓风采,骨谓骨相,一虚一实,组合成词;‘风骨’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体;两者虽有区别,但又紧密联系,互相渗透。”[19]张少康先生说:“‘风’是侧重感情形态”,“‘骨’是侧重思想内容特点”,“‘风骨’是完整概念,指神而不指形。”[20]又说:“风是指作家的思想感情、精神气质在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气度风貌特征。而刘勰所提倡的‘风’要‘清’则是指具有儒家纯正的思想感情、精神气质的作家在其作品中所体现的气度风貌特征。”“骨的含义是指作品的思想内容所显示出来的义理充足、正气凛然的力量。”因此他认为应当“把风骨理解为文学作品中的精神风貌美,风侧重于指作家主观的感情、气质特征在作品中的体现;骨侧重于指作品客观内容所表现的一种思想力量。”[21]
还有一些说法,不一一备举。上述四类已足可代表意见纷纭之一斑,甚至同一位作者也会发生游移,前后说法有所变化与不同,可见论定之难。那么到底应当怎样认识《风骨》篇义呢?
2
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风骨》中说:“风骨,二者皆假于物以为喻。文之有意,所以宣达思理,纲维全篇,譬之于物,则犹风也;文之有辞,所以摅写中怀,显明条贯,譬之于物,则犹骨也。”说“风骨”都是假物以为喻,是很正确的。刘勰在《风骨》篇中就明确说:“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也正是在一种比喻义上立说。古代文论中许多概念都是借人体为喻,诸如体、形、神、气等,不一而足。加之在刘勰之前,“风骨”一词本是用来品鉴人物的,这一方面已有很多人搜集了丰富的资料做过有力的论证与说明,这里不再重述。理论著作应当赋予概念以科学界说,比喻之义笼统含混,易生歧义,绝非理想的作法。但是刘勰既已用之,也自当与喻义不远。
《风骨》篇说:“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至少从中可以得出三点结论。第一,说明“风”与“骨”实指两事,不可将其混而为一,不分彼此。第二,“风”“骨”二者,一如人体之有骨,一如人身之有气,统一在一个完整的人的身上,所以又不可将二者视为截然不相干的两事。正是二者的合一,而显出人的一种独特的风貌。这一点颇可用晋宋人以“风骨”称誉人物的事例作为参证。《世说新语·赏誉》注引《晋安帝纪》曰:“羲之风骨清举也。”同篇又一处注引《文章志》曰:“羲之高爽有风气,不类常流也。”风骨是高爽不类常流的一种形象。《宋书·武帝纪》记刘裕:“身长七尺六寸,风骨奇特。家贫有大志,不治廉隅。”刘裕所以风骨奇特,与他身长七尺以上,有犬志,不拘小节分不开。又《世说新语·轻诋》载:“旧目韩康伯,将(景宋本作‘捋’)肘无风骨。”注引范启语曰:“韩康伯似肉鸭。”似肉鸭的人,便没有风骨。所以刘勰提出“风清骨峻”,必须风神清爽,骨格坚实,方是文有风骨之徵。第三、一言“辞之待骨”,一言“情之含风”,可见“骨”属于辞的范畴,也就是文之外体范畴的事;“风”属于情的范畴,也就是文之内蕴范畴的事。所以刘勰在此篇中分举两篇范文以示风、骨的楷模:“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潘之《册魏公九锡文》“规范典诰,辞至雅重”(范文澜语),所以称其“骨峻”;司马相如之《大人赋》,武帝听了之后,“飘飘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想象丰富,命意不凡,所以称其“风力遒”。二者所指的范围与标格是清楚的,只是沿着这样的思路,方能摸索到《风骨》篇的真实含意,而得刘勰的意旨所在。比喻之义既明,可以进一步探讨“风骨”的实际内涵了。
3
在具体分析“风”“骨”含义之前,先来考察一下《文心雕龙》及其《风骨》篇的写作意图是必要的。《文心雕龙》的整个创作意图就在返本救末。《序志》篇自言其作意是“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并批评魏晋以来的文论著作“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又批评当时的形式主义诗风说:“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并严肃地指出:“离本弥甚,将遂讹滥。”这一宗旨是贯串全书的。刘勰赞扬建安文学“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论正始文学,则言“嵇志清峻,阮旨遥深”,肯定嵇康、阮籍,却批评“何晏之徒,率多浮浅”;论两晋言“晋世群才,稍入清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江左篇制,溺乎玄风”,非议之意十分显然。而说到刘宋以后“近世之所竞”,则言“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22],也是叹惋其追逐形式的风气的。所以作者在《通变》篇中总论道:“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今疏古,风末力衰也。”远离古之质实,追求近之浮艳,就变得“风末力衰”了。《情采》篇也说:“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所以反讹归质,是刘勰的一个基本意向。
《文心雕龙》在总体结构安排上,除开端数篇讲文之基本原则外,前半部分论文体,后半部详析文术。因此很容易使人以为后半部仅仅是谈写作方法、文章体貌风格之事。《风骨》篇在后半部中,也就很容易被看成是讲一种风格或提倡一种美学风范。其实作者的主要用意还是在反对绮靡柔弱的文风,要引导当时从质及讹、采滥忽真的文风归返到宗经、徵圣的道路上来,能够“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做到“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23],做到“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文成规矩,思合符契”[24],至少也可以与建安、正始媲美,具有建安那样的风力,不致于“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风骨》篇的写作意图是与全书主旨一贯的。
在后半部的安排中,《风骨》为第三篇。首篇为《神思》,是讲文章的构思的,其中强调了“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要求为文者“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次篇为《体性》,是讲才性与文章体貌的关系的,分析先天后天诸要素。其中提出“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而着重指出“才有天资,学慎始习”,要求“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重在学与习,而习又“必先雅制”,次篇便是这《风骨》篇了,作者要通过它树立一种标格,使文风由讹而返本,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
4
明确了作意,就可以来分析“风”、“骨”的具体内涵了。文中言“情之含风”,“风”属于“情”的范围,也就是属于思想感情内容的方面。不过它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情”,而是为“情”立一种标格与标准。作者采用“风”字为文情树立标准,与“风”字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形成的意蕴密切相关。《毛诗序》曰:“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又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刘勰是很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的,或上以风下,或下以讽上。《情采》篇曰;“风、雅之兴,志在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即其一证。刘勰首先是采取了“风”的这一意蕴。故本篇开篇即云:“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很清楚是从“风”的教化作用立论的。“风”是“化感之本源”,“情”必须含“风”,也就要求内容必须有教化意义,这就不是吟风弄月的作品所可能具有的了。
“风”所以能成为“化感之本源”,则因为它是“志气之符契”,是“志气”在文中的体现。在《文心雕龙》中,“情”“志”可以互通,常常对举成文。如《徵圣》篇曰:“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也可以合为一词,如《附会》篇曰:“必以情志为神明”。所以“志”也就是“情”。在这一点上,又是“诗言志”这一古老文学传统的重提了,《毛诗序》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文学或文章必须是表志的,不仅仅是“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还必须“吟咏所发,志惟深远”[25]。
但是正如上文所言,“风”并不简单等于“情”,所以也并非凡志皆可称“风”,还有一系列内容与状态上的标格要求。篇中言“风清骨峻”,首先是这“情”的标格。“清”当有二义,一是纯,纯正无邪。《章表》篇所谓“必雅义所扇其风”,《宗经》篇所谓“风清而不杂”。要求文章必须有纯正的思想,很强的讽谕教化作用,犹如风过草偃。一是思理清通明晰,绝无枝蔓繁杂。所谓“不杂”,也当有这一方面含义。
“风”的本义,最早见于《庄子·齐物论》,曰:“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风”乃“气”所形成,所以“风”又与“气”密切相关,故《风骨》篇十分重“气”。篇中特别拈出曹丕《典论·论文》中“文以气为主”的观念,并详列其以“气”评论诸家作者之说和刘桢以“气”品评作家之论,总括说:“并重气之旨也。”其重气之意,十分显然。这一点早已为人所注目。明代曹学佺在天启刻本《文心雕龙》序中说:“风,化感之本原,性情之符契。诗贵自然,自然者,风也;辞达而已,达者,风也。……岂非风振则本举,风微则姆坠乎!故《风骨》一篇,归之于气,气属风也。”又在《风骨》篇的批酗中说:“风骨二字虽是分重,然毕竟以风为主,风可以包骨,而骨必待乎风也。故此篇以风发端,而归重于气。”[26]清黄叔琳进一步提出“气即风骨之本”。纪昀在《文心雕龙辑注》更曰:“气即风骨,更无本末。”范文澜在《风骨》篇注中也说:“本篇以风为名,而篇中多言气。……盖气指其未动,风指其已动。”“风”具“气”意,是刘勰拈出“风”字的又一层重要用意,可以为文树立更广的标格。
《风骨》篇说:“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情”能够达到“风”的高度,就象人体中含有气。就比喻上的意义而言,“骨”是人体的骨骼支架,“气”则是气脉生命。人如无气,则不过是僵死的躯体,所以“气”是人的精神生命的源泉。从比喻义上看,人的气脉畅通,才能精神饱满,移之于文,则必思理畅达,一气贯注,毫无壅滞,方可言“风”。所以《风骨》篇曰:“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思理不能首尾绾合,连成一体,就会“索莫乏气”,是一种无风的症候。司马相如赋仙,所以“风力遒”,正是因为它“气号凌云”,想象丰富,思理高扬无阻的结果。
“气”不只有流动通达之义,还是一种力的表现。“气”流动而为风,风行草偃,呈现为一种风力。故曹学佺云:“风振则本举,风微则末坠。”《风骨》篇曰:“夫翬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在这联骈语中,上下联“力”与“气”对举成文,实是互文见义,气即力,力即气。气猛则力强,力沉则气弱。故《风骨》篇说:“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骏爽”即奔流高扬之意,是一种力度的表现。总起来说,文章之“情”而能含“风”,不只要有讽谕教化的作用,还要思理畅达,富有气势,既有教化的力度,又有思理清通奔腾的力度。
正因为“气”如此重要,刘勰重视养气,《文心雕龙》专有《养气》篇,讲作者在进入创作过程前和在创作过程中,保持精神饱满的意义。他说:“心虑言辞,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励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之数也。”真正有了创作冲动,笔墨得心应手,毫无苦思勉强之处,这就是“率志委和”的状态,也就会“理融而情畅”,能以做到思理环周。否则,过分钻励,强自为文,则必神疲而力衰,文章也就脉理不通,上气不接下气,也就要落到《风骨》篇所说的“思不环周,索莫乏气”的境地了。他主张为文要“适分胸臆,非牵课才外”,“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他的结论是“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以保证能够“刃发如新,凑理无滞”,文思奔腾而下,流畅而有气势。所以《风骨》篇首段于“风”“骨”分说之后,特别提出:“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务盈守气”就是《养气》篇说的“清和其心,调畅其气”,保持创作时精神状态饱满,气势充沛,这也是《风骨》篇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内容。
5
《风骨》篇言“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骨”无疑属于“辞”之范畴。情虚而辞实,义不藉辞则无由显现。将“骨”解释为“事义”也未尝不可,但“事义”在文章中也必须通过辞才得以表现出来。况且文章也并非全用“事”构成,不用“事”而以“辞”直言理者,亦文中所习见,《文心》中《诸子》《论说》等篇所论之文,尤多此种。或者纯为记事之文,只以文辞叙事,甚至白描其事,如《文心》之《史传》《诔碑》等篇所论之文,常常如此。如果认为除事义则非“骨”,那么这些文章不就都是无骨之作了吗?刘勰之意,显非如此。用事取义也好,直言说理也好,白描叙事也好,率然抒情也好,凡为文章都有“风骨”问题。但不是何等样辞都可称为有“骨”,刘勰在《风骨》篇中说得很清楚:“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结言”即是遣辞,“端直”就是达到用辞有“骨”的标准,“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徵也”。但是何谓“端直”呢?还是先从比喻意义上看起。
刘勰说“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以人体作比,则有骨之辞如人之骨骸,见出一种骨骸坚实的力量。韩康伯似肉鸭,便没了“风骨”,“翬翟”“肌丰”,也没了“风骨”。《说文·骨部》:“骨,肉之核也。”“骨”乃是附肉之物,如果肉埋没了骨,只见肉而不见骨,那就成了无骨的症候了。所以晋卫夫人《笔阵图》以骨肉论书法说:“多骨微肉者筋书,多肉微骨者墨猪。”多骨才见出筋力,如果只是多肉,那就成了见不到骨的肉猪了。
正是由于“骨”的这种状貌,“骨”字常与“骾”字相连。《国语·晋语》韦昭注:“骨,所以骾刺人也。”“骾刺人”便是坚挺力度的表现。《汉书·杜业传》则“骨骾”连文,颜师古注曰:“骾,亦鲠字。”后大都作“骨鲠”,今也作“骨梗”,乃是指一种刚直不阿的品格,总之不离一种坚硬质实的形象。《文心》中多次提到这个词语。《檄移》篇曰:“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这是说该篇“抗辞书衅,皎然露骨”,敢于“指曹公之锋”,正是刚直无畏之义。《奏启》篇曰:“杨秉耿介于灾异,陈蕃愤懑于尺一,骨鲠得焉。”也是说杨秉、陈蕃敢于抗言直谏,卓立不惧。《辨骚》篇曰:“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这几句是在分析《离骚》“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的大前提下所云:“骨鲠”指文章的主干,即取熔经意而成,下文称之为“气往轹古”,是完全肯定的。“肌肤”是指辞语,所谓自铸伟辞,即下文所谓“辞来切今”,然而辞能成为伟辞,至少也是接近于“骨”的要求了,作者也似无非议之意。这是将“骨鲠”与“肌肤”分用于义、辞两个方面,义合经意,气往轹古,自是有“风”之作;辞虽切今而为伟辞,也大体合于有“骨”的标准了。《封禅》篇曰:“树骨于训典之区,选言于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义吐光芒,辞成廉锷,则为伟矣。”封禅文乃“一代之典章”,“宜明大体”,所以更须规摹训典以为骨干。但意古而不晦涩,辞今而不浅薄,义则光耀千古,辞则坚实挺拔,则自是合乎“风骨”的文章了。《诔碑》篇论蔡邕所撰碑曰:“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则是指该碑规摹《尚书》训、典以为骨干之意。下文总括言曰:“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此中事与采、词与义双论,事能“该而要”,即全面而精要;采能“雅而泽”,即典雅而光华,词又能达到“清”的标格;义则巧而卓出,也自然是有“风骨”的文章了。在这里,“义”属于“风”,“事”“采”“词”则皆属于“骨”。《文心》各篇之中,“骨”及“骨鲠”的含义不尽相同,但大体说来,指义则指文章的主干,指辞则指文章的骨架,前者与经意关系密切,后者则不离沉实坚挺之义。这也正是针对当时排比典实、铺张辞藻、臃肿无骨、瘠义肥辞的浮艳柔靡的文坛风气而发,故《风骨》篇要求要“蔚彼风力,严此骨鲠”,还特别引了古训说:“周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盖防文滥也。”
《风骨》篇共分三大段,第一段阐述风骨之义,第二段言“气”与风骨的关系,第三段则指示达到文具风骨的门径。刘勰告诫作者要“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熔范偏于昭体,要从经典中来;翔术偏于晓变,要从子史中来。如此才可以创新意、造奇辞。所谓“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如果“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岂空结奇字,纰缪而成轻矣。”未能以经典子史为学习楷模,练好骨采与风辞,那就虽有巧意,也必危败,虽有奇辞,也必轻谬,就不会是有风骨的文章了。这里面固然表现了作者的宗经思想,所谓“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27],同时也再一次说明情风、辞骨实为二事,不能笼统合而为一。故《风骨》篇之赞语说:“情与气偕,辞共体并。”
6
文章从大的方面说,无非义、辞两端,刘勰于情中提出“风”(包括“气”),于辞中提出“骨”,在论述义、辞即内容与形式的《情采》篇之外,又特别写了《风骨》,如前所言,实与当时文坛风气不正有关,但它除了具有现实针对性之外,也同样具有一般理论的意义。其本质的含义是与《文心》许多篇中的论述相通的。
《附会》篇说:“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附会》篇是论“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的问题,包括了文章的基本要素。“情志”属于“风”的范畴,“事义”“辞采”属于“骨”的范畴。“宫商”为声调,虽附于辞,非形体可见之类,而音调流美,则有助于文思畅达,气脉通贯的感受,在主要点上应属于“风”的范畴。所以《风骨》篇说:“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不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捶字”句属“骨”,“结响”句属“风”,“凝”是沉重之意,所谓掷地作金石声,“不滞”就是流美,足见声韵是属于“风”的一方。刘勰论文主张宗经,其《宗经》篇总论以经典为宗可以达到的文章规范,曰:“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这六条可分为三类,“情”“风”是一类,即“怊怅述情,必始乎风”的表现,主要指通贯全篇有化感意义的思想内容;“事”“义”是一类,主要指文章所用的题材及其含蕴的义理,属于“骨”的内核部分;“体”“文”为一类,基本属于“辞”的范畴,但能够做到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则亦合于“骨”的要求,是“骨”的外在表现部分。《熔裁》篇也是讲结构剪裁全篇的,其文曰:“草创鸿篇,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这里的“设情”“酌事”“撮辞”显然就是《左经》的“情”“风”、“事”“义”、“体”“文”。所以《风骨》篇虽有改革齐梁柔靡绮艳文风的强烈倾向,却仍不失为一条重要的创作理论。他对“风”与“情志”、“骨”与“辞”、“风骨”与“采”的骨系的论述是非常精辟的,他所提出的理想艺术境界也是具有久远的生命力的:“夫翬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这对今天的写作,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注释:
[1]载《文心雕龙综论》,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第37—72页。
[2]《文心雕龙札记》,北京文化学社,1919年再版,第29页。
[3]《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516页。
[4]见《人民日报·新闻业务》第一期,1962年,《文心雕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第143—144页。
[5]《中国美学史中主要问题的初步探索》第三题,载《文艺论丛》六,1979年,第55页。
[6]《非文心雕龙驳议》,载《文学评论》1978年第2期。
[7]《刘勰创作论》,香港文昌书局,1962年,第70页。
[8]《文心雕龙精选》,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0页。
[9]《文心雕龙校释》,1948年初版,1972年香港中华书局重印,第106—107页。
[10]《释风骨》,载《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559、561、562页。
[11]《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34页。
[12]载《文汇报》,1961年7月21日。
[13]载《光明日报》,1961年8月13日。
[14]《文心雕龙风骨论诠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94页。
[15]《“文心雕龙”的风格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53—55页。
[16]《文心雕龙注释》,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325—326页。
[17]《文心雕龙评论作家的几个特点》,载《北京师大学报》1963年1期。
[18]《中国文学中的“气”的问题》,载《中国文学论集》,台北民主评论,1966年,第305—306、312—313页。
[19]《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台北木铎出版社,1981年,第200—201页。
[20]《齐梁风骨论的美学内容》,载《文学评论丛刊》第16辑,中国社科1982年,第227—238页。1982年。
[21]《文心雕龙新探》,齐鲁书社,1987年,第128、131页。
[22][23][24][25][26][27]分见《文心雕龙》之《明诗》、《宗经》、《徵圣》、《物色》、《序志》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