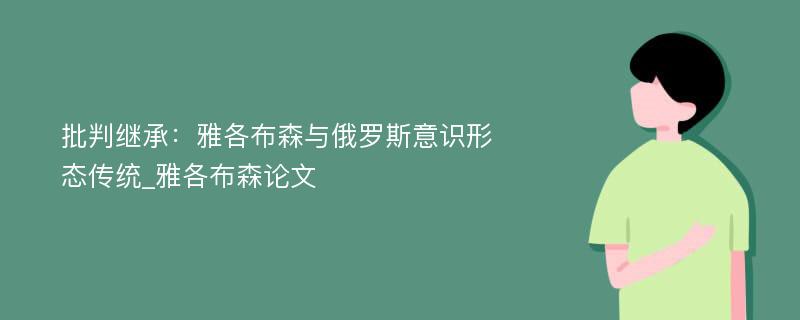
批判地继承:雅各布森与俄罗斯意识形态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雅各布森论文,俄罗斯论文,意识形态论文,传统论文,批判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曾经用这样两句话来形容他自己:一句话是经常被引用的,他说:“作为一个语言学家,凡涉及语言的一切东西于我而言都不是界外之物。”另一句是在1976年,当有人问他:“你用这么多的语言说话和写作,又在这么多的国家工作、教学和生活过,那么,你是谁?”“一个俄罗斯的语文学家,”雅各布森非常简洁地回答道。这显然是深思熟虑的回答,因为几年后,在他的剑桥墓碑上,我们看到了用俄文镌刻着同样简洁而意味深长的墓志铭:“罗曼·雅各布森——俄罗斯语文学家。”
纵观雅各布森曲折的一生和漫长的学术生涯,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语言研究是带有强烈主体性的研究,是自身感知经验和科学方法高度契合的研究;虽然他大半生都流亡于俄罗斯之外,既拥有美国护照,也曾是捷克公民,但他最看重的还是作为俄罗斯语文学家的身份,而就其学术立场而言,他也一直是在“俄罗斯意识形态传统”(Russian ideological tradition)中进行言说的。
俄罗斯思想史领域的所有专家一致同意的观点是,1840年代,世界知名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开辟了新纪元,此后,黑格尔哲学便和俄罗斯思想密不可分了。黑格尔哲学在俄罗斯的接受,是内含于浪漫主义而得到传播的,总体而言,俄罗斯知识分子当时对浪漫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采纳或吸收非常强烈,这或许只能由俄罗斯固有传统的运动来解释,而这种传统正是由“拜占庭”所塑造的。辩证地看,俄罗斯固有传统促进了浪漫主义和黑格尔哲学的接受;反过来,俄罗斯的拜占庭遗产又在浪漫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German Idealism)思想之下被重新审视,简言之,我们可以认为,“俄罗斯意识形态传统一方面植根于一种拜占庭的世界观,另一方面植根于德国浪漫主义和黑格尔哲学。”[1](16)
对雅各布森而言,拜占庭-中世纪的俄罗斯艺术以及一战前的先锋艺术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1911年马蒂斯(Matisse)访问莫斯科更加深了雅各布森对这些艺术的亲近,正是这种亲近,使得后来他还推荐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阿拉贡(Louis Aragon)的一本拼贴艺术书,作为对拜占庭诗歌特殊结构的介绍(1973)。也就是说,雅各布森的兴趣并非仅仅是德国浪漫主义和黑格尔理念世界的文化,归根结底,还在于拜占庭-希腊文化和它的宗教-斯拉夫文化(church-Slavonic Culture)的民族传承,这从他早年对俄罗斯民间故事的搜集与整理以及二战后对俄罗斯古代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Igor' Tale)、拜占庭对斯拉夫的使命、斯拉夫民族自决(Slavic self-determination)的历史等一系列研究中可以看出,①而这些研究从总体上来说又是服务于“民族神话”的重建任务的。
移居美国之后(1941),雅各布森从个人神话(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等诗人诗歌)转换为民族史诗这一问题出发,走上了一条更开阔的道路,即系统阐释“斯拉夫神话学的比较重建”,以及这种神话学在普遍的印欧神话学(Indo-European mythology)重建中的广泛利用,他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时期即致力于这些研究,比如他在1964年莫斯科人类学代表大会上、在1968年布拉格斯拉夫学者大会上所做的报告等。在他看来,“民族宗教、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是“民族神话”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体现,是实现“民族自决”的根本规则,比如就斯拉夫世界而言,虽然拜占庭帝国把一种民族语言的最高权力视为一种伟大的特权,但拜占庭帝制的倾向是将斯拉夫语从宗教中逐出,代之以希腊语;而以希腊语为范本发展而来的宗教-斯拉夫文化(或者说意识形态)保证了斯拉夫民族的独立性,它改变了拜占庭的这种选择少数的观念,否定了特权民族和特权语言,于是,斯拉夫文化的意识形态潮流在捷克、克罗地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地蔓延开来,斯拉夫世界由此而获得了民族宗教、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民族自决”。民族语言作为民族神话的核心载体,一定程度上成为民族精神的表征,这正如19世纪德国古典语言学家洪堡特所言:“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语言形式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极为密切……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性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2](52)也就是说,在比较神话学中,民族语言(尤其是民族史诗所表现出的语言)发挥着文化区分和精神认同的双重功能,而“神话”结构正是支配民族语言、体现民族精神、实现“民族自治”的深层结构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雅各布森的这些比较研究与一般的民族主义或历史主义的怀疑论者截然不同,其方法论原则在于对资源的系统利用,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地重建前基督教斯拉夫(pre-Christian Slavic)的信仰,在他看来,中世纪作品和当代民间故事中涵纳了斯拉夫神话的遗迹,某种神话学的命名在口头的和书写的遗产中也已得到证明,并发现了它们所在的语境和功能,因此,必须对斯拉夫所拥有的类似命名,甚至存在于伦理的和宗教仪式中的意指术语,进行比较分析,必须对斯拉夫神话的遗产与其它印欧分支的相似遗产进行比较。而在斯拉夫和印度-伊朗世界(Indo-Iranian world)之间的宗教关系的历史中,也能够发现同样的现象,也就是说,许多斯拉夫的神话遗迹比古代日耳曼民族(ancient Germanic)或古印度吠陀(Vedic)的神话更古老,后者的神话学虽然也古老,但已服从于文学重塑了。
如果说上述与拜占庭文化相关的神话学研究是一位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与民族意识的情感外泄和深沉呐喊,那么,对德国浪漫主义的接受则表现出这位“未来主义诗人”的浪漫情结和审美理想。19世纪上半叶,德国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俄罗斯,就哲学而言,俄罗斯对德国浪漫主义的接受,其实也就说对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的审美哲学、谢林的自然哲学)的接受,当然,这种接受是与俄罗斯本土对伦理问题、社会政治问题、历史问题、人的命运问题的长期关注纠结在一起的。
对雅各布森来说,浪漫主义的影响既是文学意义上的,也是哲学意义上的。比如,他少年时最先关注的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其早年便曾受过德国浪漫派和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而另一位他心仪的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哲学家诺瓦利斯,其诗论、哲学思想对他诗学观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直到晚年,雅各布森仍对这位英年早逝的诗人念念不忘,他对德国科隆大学的师生说道:“正如诺瓦利斯观察的那样,诗歌的价值重在表达——词语的最大限度的表达。正是语言的外在形式和内在形式使一首诗成为一首诗,”[3](72)在这里,我们仿佛再次听见“文学性”的回声,而这种对诗歌本体价值始终不渝的审美追求,也正是“浪漫主义”的最好注脚;此外,雅各布森对浪漫主义诗歌的关注与批评实践是始终如一的,比如,他对俄罗斯浪漫主义诗人普希金、爱尔兰浪漫主义诗人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以及捷克浪漫主义诗人马哈(Macha)、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和画家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等人的诗作进行了细致解剖。可以说,浪漫主义思想所彰显的直觉、想象力和感觉等特质,在雅各布森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比如他对文学、绘画、音乐等艺术的直觉力,对诗歌与绘画、视觉符号与语言符号、语言学与诗学之间关系的想象力和感觉等,都显得异常敏锐。当然,雅各布森毕生追寻的目标不是非理性主义的“诗化哲学”,而是理性主义的语言哲学,可以说,在科学上,雅各布森终生都是一位浪漫主义者。
正如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为浪漫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雅各布森对康德哲学的继承与批判也奠定了他形式主义语言诗学的基础。早在《达达主义》(1921)一文中,他就借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S.Spengler)和未来主义诗人赫列勃尼科夫之口,对康德哲学的应用效力进行了初步的批判:
按斯宾格勒所言,当康德推究关于规范的哲理的时候,他确信他所做的对所有时代、民族和人民的事业是实在的,但是他没有陈述得彻底,因为他和他的读者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与此同时,他所建立的规范只对西方思想模式尽了义务。典型的如赫列勃尼科夫在十年前就曾写道:“康德,思考着建立人类理性的边界,仅仅决定德国精神的边界:这是一个学者的一次漫不经心。”[4](35)也就是说,康德哲学所建立的理性规范只具有相对的效用,只是对德国思想和精神模式有效,而并非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当然,雅各布森的这种批判是为了凸显建立“相对论”的历史认知的必要,可能并非针对康德哲学内涵本身,但这种引用本身无疑也表明了他对斯宾格勒和赫列勃尼科夫观点的认同。实质上,他早期对诗歌的形式主义认识与判断,还是可以看见康德哲学“越界”投射的阴影的。在康德那里,“美,它的判定只以一单纯形式的合目的性,即以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为根据的。”[5](64)也就是说,美具有独立自足性,与概念或逻辑判断无关,只与单纯形式有关,审美判断是一种无利害的形式愉悦;而对于雅各布森来说,“文学性”、“手法”、“无意义语(诗)”等同样具有独立自主的形式意义,“诗歌是发挥其审美功能的语言”(《俄国现代诗歌》,1919),文学(诗歌)不以指称事物为旨归,而是以专注于语言形式本身为审美目的,正如日尔蒙斯基在评价雅库宾斯基的诗语系统特征时所说:“在这一系统中,‘实用目的退居末位,语言组合获得自我价值’。诚然,自我价值的言语活动(按照雅各布森的定义就是‘旨在表达的话语’)的概念,对于鉴定诗语来说未免过于宽泛……但是,雅库宾斯基毕竟指出了诗语的许多重要并行特征中的一个特征,此特征在康德的美学体系中被称为‘没有目的的合目的性’。”[6](219)日尔蒙斯基在《论“形式化方法”问题》一文中说得更具体:“康德的美学公式是众所周知的:‘美是那种不依赖于概念而令人愉快的东西。’在这句话中表达了形式主义学说关于艺术的看法。”[6](365)可见,康德哲学对雅各布森等俄罗斯形式主义者的影响是巨大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先验的唯心主义哲学对于未来主义美学和形式主义诗学不啻为一种莫大的精神激励和理据支持。
如果说此时雅各布森是在不知不觉中受了康德美学影响的话,那么后来他对康德美学的拒绝,便带有了强烈的为形式主义诗学和自己正名的意味了。在布拉格时期的一篇重要诗学文章《何为诗?》(1935)中,雅各布森写道:
批评界非常流行的做法是,对他们所谓的“文学的形式主义研究”提出某种质疑。这些贬低者说,形式学派没有抓住艺术和现实生活的关系;这是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研究;它跟随的是康德美学的脚步。持这种反对倾向的批评家从单一的角度看问题,因此是完全片面的、极端的,忘记了还存在第三种维度。[4](377)显而易见,雅各布森此时对康德美学是格外警惕甚至排斥的,在他看来,这些别有用心的批评家有意混淆了诗学的形式主义观念与“为艺术而艺术”学说,虽然他们共同的来源都是德国浪漫主义,但二者之间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对此,托多洛夫认为,形式主义诗学涉及的是文学中语言的功能问题,而“为艺术而艺术”涉及的却是文学或艺术在社会生活里的功能问题。[7](375)从某种程度来说,正是为了避免堕入康德形式美学的偏颇之中,为了与“为艺术而艺术”拉开距离,雅各布森布提出了新的方法论取向,即主张“审美功能的自治性(the autonomy of the aesthetic function)而非艺术的分离主义(the separatism of art)”:
无论是迪尼亚诺夫、马雅可夫斯基,还是什克洛夫斯基和我,都从未声明过艺术的自足。我们所试图表明的是,艺术是社会结构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与其他结构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由于艺术范畴及其与社会结构其他构成部分的关系处在不断的辩证变化中,因此艺术自身也是易变的。我们所代表的并非艺术的分离主义,而是审美功能的自治。[6](377-378)
在这里,雅各布森以一种辩证、动态的结构主义立场和观点,明确修正了早期形式主义过分偏重文学(语言)内在性的弊端,又坚决避开“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自足论,既强调文学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结构而存在,而应在社会结构中承担相应的社会功能,又强调文学艺术审美功能的自治;既突出文学艺术与他者(其他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的关系是始终变动不居的,也突出在这种“关系”中文学艺术自身的动态演变性。当然,如何处理文学艺术的内在“文学性”及其与外在社会性之间的关系,对于雅各布森来说,依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这正是他此后力图以语言交际多功能结构和诗歌的多功能结构来解决的问题。
在19世纪下半叶,康德的德国后继者们,如谢林和黑格尔,在俄罗斯影响更大,正如当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赛亚·伯林所言:“德国形而上学在俄罗斯的确使观念方向剧烈改变,无论左派右派,无论民族主义者、正教神学家、政治激进分子,皆然,而大学中比较先觉的学生,乃至于一般具有思想倾向的青年,也都深受感染。这些哲学流派,尤其黑格尔与谢林学说,所演成的种种现代化身,今日犹不无影响力。”[8](163)可以说,其时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基本受养于德国思想的精神食粮,他们从谢林那里学到了整体性思想,又从黑格尔那里学到了辩证法的思想。虽然后来黑格尔哲学在俄罗斯被批判的命运算得上悲惨,但至少在当时,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还是深刻影响了一代追求真理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如赫尔岑、别林斯基、巴库宁、屠格涅夫、斯坦凯维奇等。
事实上,雅各布森与“黑格尔”这个名字的关联远远小于他和“浪漫主义”的关联,因为雅各布森出生和成长的时期,黑格尔哲学已在索洛维约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批判下变得暗淡,已和浪漫派哲学一样成为俄罗斯意识形态传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正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雅各布森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特性:既是结构的,整体的,也是辩证的,和强调动态的;既是历史性的,一定程度上是进化论的、目的论的,也是现实的、反归纳主义和反实证主义的;而且,它特别关注普遍的、主体间的、无意识的以及特殊的审美方面。[1](16)在雅各布森的语言学和诗学理论中,这种意识形态传统和方法的影响是清晰可见的。
很显然,雅各布森向黑格尔借取的不是某个概念范畴,而是一种哲学原则或逻辑思维,比如辩证法。如果我们把辩证关系理解为一种特征的相互说明,而它们自身又是相互排斥的话,那么,我们不妨把雅各布森所建立的语言语音的区别性特征之间的二元对立也称作一种辩证关系。正如光明与黑暗,它们自身是相互排斥的,因为一种东西不可能同时既是光明又是黑暗;另一方面,光明与黑暗又是相互包容的,不知道光明,也就不知道黑暗,只有当光明从黑暗的背景中突显出来,我们才能理解什么是光明。这样的例子同样可以用来解释逻辑学结构主义和现象学结构主义,比如像马丁内(A.ndre Martinet)提供了一种纯粹语言结构的逻辑分析,他把一种关系的相互排斥定义为一种对立,实际上,我们如果要分析语言现象学的结构,分析说话者意识到的或说出的语言结构,我们就必须像雅各布森那样,把同时的排斥和包容界定为辨证的对立,从这个意义上说,雅各布森的现象学结构主义比马丁内的逻辑学结构主义更具合理性,而后来在此观念上,通过实证研究而建构的音位学模式,一定程度上也以科学结构主义的形式突破了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和纯粹逻辑推理的框架。
如果说哲学理论为雅各布森提供了探索的思想武器,那么,诗歌与语言之间的不可分离的关系则为其提供了经验主义的支撑,使其能够在意识形态传统中,一步步由诗歌爱好者成长为一个经验的语言科学家。雅各布森甚至认为“只有诗歌才是语言的本质”,因为在诗歌中,他发现了他语言学的非常重要的原则,他试图寻找的也正是语言的诗歌起源,或者说在语言中寻找诗歌、诗性和美,这个浪漫主义的语言学声明无疑是对海德格尔的哲学格言“语言的本质是诗”(《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的某种回应,只不过前者是科学主义、认识论意义上的,而后者则是非科学主义、本体论意义上的。对于语言和诗歌之间关系,他至少做到了这样三个方面内容:
其一,他认为诗歌利用了自然语言的普遍性。比如,在1960-1970年代,雅各布森分别与各语种的专家合作,对二十余位不同时期、不同风格、不同语言的诗人诗作,进行了庖丁解牛式的诗歌语法分析,甚至还对中国的古典格律诗和日本古典诗歌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研究时空跨度之大(近十三个世纪,横跨欧亚),内容之丰富,分析之细致,令人惊叹,至今无人能出其右。这些科学实证主义的诗歌批评实践证明:尽管横亘着语言的和时代的巨大差异,但存在着普遍使用的诗歌手法,存在着普遍性的对等原则和平行结构。
其二,面对诗歌文本与诗性功能(poetic function)之间的差异,雅各布森指出,诗性功能在诗歌文本中是主导功能,而诗性功能在非诗文本中也是非常普遍存在的。比如,他在最普通的日常语言系统中就发现了诗性的感知:有一次在瑞士的餐馆,他突然听到一句话“No service in this section”,他就思考这简单的抑扬格中,“节拍的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此外,在演说家的演讲、日常交谈、新闻、广告、科学论文等非语言艺术中,他也发现了诗性功能作为从属功能而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三,为最接近语言的诗歌起源,他还专注于儿童语言中自发的诗性语言的游戏及其对习得语言的可能意义。他从人类最早的阶段(儿童)入手,把这些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的审美态度综合起来,提出了“元语言”(metalanguage)(即对客观语言[objective language]进行解释的语言)的问题。按黑格尔的观点,现代时期的特征在于艺术是一种关系性的中介关系,就此而言,语言关系和它的审美运用也不是一种直接的、单纯的关系,而是以元语言的反映为中介的关系,即“语言——元语言——审美运用(如文学艺术)”。雅各布森的观点与此相似,但在他看来,这种反映关系不是成熟的、完成了的关系,而是历时的、普遍的关系,可以说,雅各布森的浪漫主义思想正是通过俄罗斯意识形态传统与黑格尔哲学相关联的,而当浪漫主义和黑格尔主义产生分歧的时候,雅各布森又基本上还是沿着黑格尔的线索前进的,对雅各布森而言,三者的关系是:“浪漫主义(一般)——俄罗斯意识形态(中介)——黑格尔(特殊)。”
总之,雅各布森的结构主义语言诗学没有经受像谢林“自然哲学”那样的命运,这应当归功于他作为一个经验主义研究者的方法,也归功于浪漫主义和黑格尔哲学思想的综合。如果我们考虑到雅各布森是如此之深地扎根于俄罗斯意识形态传统中的话,那么,我们或许应该这样来评价:雅各布森的语言诗学是俄罗斯黑格尔主义的最积极的产物之一,甚至可被认为是“黑格尔派语言学”(Hegelian Linguistics)的代表,可以作为佐证的一个极好的例子是,就在雅各布森逝世的前一个月(1982年6月),德国斯图加特市授予他“黑格尔奖”,雅各布森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论语言的辩证法》,发表在《黑格尔的遗产》第二卷(1984)上:这正可以看作是俄罗斯意识形态传统馈赠给他的最后一份精美礼物。
注释:
①参见 Roman Jakobson:The Puzzles of the Igor' Tale on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Its First Edition,Speculum,Vol.27,No.1.(1952),pp.43-66; The Byzantine Mission to the Slavs,Dumbarton Oaks Papers,Vol.19 (1965),pp.257-265; The Beginnings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in Europe,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7,No.1 (1945),pp.29-42.
标签:雅各布森论文; 康德论文; 浪漫主义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斯拉夫民族论文; 俄罗斯民族论文; 文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形式主义论文; 诗歌论文; 斯拉夫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