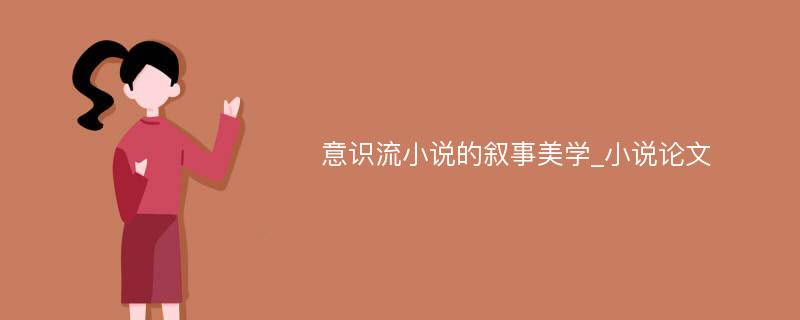
意识流小说的叙事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流论文,美学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6]10—0072—03
意识流小说家认为小说的首要任务是反映现实世界的“真实”。被誉为“英语小说批评之父”的亨利·詹姆斯把“真实感”列为小说最重要的优点,为此,他首先提出了“作者退出小说”的要求,主张小说应全面、如实地记录来自生活的经验和印象,捕捉生活本身的色彩;詹姆斯·乔伊斯提出了“唯真实论”,认为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事物,不管美丑,都要在作品中得到真实的体现;威廉·福克纳也承认,作家只应写人类的内心冲突和心灵深处亘古至今的“真情实感”。意识流小说家把这种“主观真实”视为自己的艺术追求,最大可能地“退出小说”,把人物的意识直接展示给读者。正是基于这种对客观真实的认识,意识流小说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美学。
一
在传统小说或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中,叙事基本上保持了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论悲剧的形式。从亚里斯多德把情节定义为悲剧的第一要素始,情节就一直居于传统小说或经典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中心。[1](P25) 在悲剧世界善与恶、英雄与恶魔二元对立的模本中,情节是这个模本最有力的支撑体。无论是在古典叙事作品,还是在巴尔扎克、哈代和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中,情节都是人们理解其作品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到了20世纪初,传统小说或经典现实主义小说对人物个性以及对主人公戏剧性行为的描写,在意识流这种新型小说形式中失去了原有的表现形式,作家或人物叙事的主体地位和主导意义随着全知叙事人的消失而消亡了,只剩下感觉、意识和无意识之类的主观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意识流小说更为关注作品中现代社会那些丧失了行为能力和行动意义、但在其激烈的内心过程和病理性的内心经验中顽强生存的人们。从表面看,这些人虽然在现实世界中失去了原有的生存之地,被内心感受所幻觉出的主观世界所包围,但他们并没有丧失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经历和独特的生活行为,他们的情感更加炽热强化,更具有反叛性和批判性。因此,在意识流小说中,这些主体的内心世界以及力图在主观世界中恢复自己在现实世界中失去的主体性、自主性和生存性而进行的悲剧式的努力,极大地震撼了读者,这恰是意识流作品带给世人的惊喜。意识流小说家正是试图通过自己的作品把这些现代社会经历激烈变化人们的心理世界展现给读者,使人们准确地把握人类生存的基本状况。因此,在传统小说或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叙事主体,其外部世界被剥夺或压抑,但并不是其主体性的彻底丧失,更不是作品人物的彻底解体,而是表现为一种新的再现现实,成了现实中某种新的、潜在的幕后推动者。
“作者退出小说”,实际上是一种“非个人化”的叙事方法,即作家退居幕后,把个人的主观情感掩盖起来,让作品中的人物充当“非介入”性的叙事者,把人物的自我意识直接呈现给读者,并通过这个人物的意识活动让读者去体验、感受外界事物,完成对作品中其他人物、各种关系和场景的分析。这种叙事方法,由于通过小说中人物的意识“独立化”和“自由化”来实现,因而促使意识流小说家的兴趣从关注客观世界转移到关注人物的感知和研究人物的内心世界方面来,才能实现自己“心理真实”具体化的创作思想和美学效果。意识流小说叙事主体的弱化,并没有导致作品中人物意识流动或行为动作的叙事杂乱无章、漫无边际,其叙事基本上还是围绕着某一个叙事中心来进行,以保证作者“退出小说”后作品的“真实感”和“自发性”。当然,这个中心可能是一个叙事者的意识,如《墙上的斑点》中“我”的意识;也可能是几个人的意识,如《尤利西斯》中斯蒂芬、布鲁姆和莫莉的意识活动,其中以斯蒂芬、布鲁姆的意识为主;还可能是一系列人物的意识活动,如《喧哗与骚动》中康普生家族的三个儿子和其黑人保姆的意识为叙事中心。正是通过这些饱受煎熬、叙事主体淡化的人物,意识流小说家以最低限度的叙述干预,把人物意识的流动和心理活动组合在一起,揭示了人物主观世界中的情境与事件,展现了意识流作品结构的多样性与作家完美独特的叙事美学思想。
二
由于“作者退出小说”和叙事主体的弱化与丧失,特别是叙事的时序性与意识流的无序性之间的矛盾冲突,传统小说构成故事的因素失去了现实性和可行性,小说的叙述形式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情节为主的传统和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中叙述程序几乎消失殆尽。淡化故事情节,展示意识的直接流露和表现意识流动层次成为意识流小说叙事的重要特征。在意识流小说中,情节的作用不再是统帅小说的整体布局或引导读者的旗帜,而是故事细小的附着物,在作品人物意识流动的空隙中顽强生存。因此,无论是吴尔夫赋予事物以感觉化的诗意,还是普鲁斯特赋予事物回忆性的内涵,乔伊斯的“唯真实论”和福克纳的“真情实感”都是意识流小说家重新给事物赋予的一种新的经验深度,是把人的外部世界移至其内在世界,在心理经验中促使人与事物分裂的弥合。可以说,意识流小说的发展已完全抛开了“情节”,变为一种“内在化”的过程,即超越了传统作品中的“情节”,向读者展示其全部的精神世界,让接受主体随着人物意识的流动,直接进入作品人物的灵魂深处。
解构主义批评家J.H.米勒在《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形式》一书中把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中心问题概括为叙述者的问题,认为叙述者是小说家扮演的一个角色,是一个杜撰出的人物,在小说中被赋予了一定的独特力量,能够随意在任何时候进入任何一个人物的内心和感情世界之中。对读者来说,由于叙述者具有的超人的洞察力,小说中的事件似乎不再是虚构的,而是真实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会随着叙事者的叙事节奏同小说中的人物保持一致。[2](P10) 意识流小说家在构建叙述者、作品人物和读者的某些特殊关系时,主要是通过叙述者等于人物这一叙述模式。叙述者可以由一人担任,故事始终是在一个人的视角中进行,形成固定内聚焦,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也可以由几个人物分别担任,形成转移内聚焦,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或叙述者仍由几个人物分别担任,但使同一个故事在不同人物的视角中出现,构成多重内聚焦视角,如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尽管如此,大多数意识流小说家习惯集中描写一个人物的意识,通过这一人物的视角去观察、分析其他人物与事件,展示其对客观现实的主观感受。即使一部作品中出现多个人物的意识流,从各个人物不同的视角去折射客观现实,各个人物的意识也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如吴尔夫的《海浪》从六个不同人物的角度探讨了各自所理解的人生;福克纳《我弥留之际》全书59节,穿插记录了15个人物的意识流程,每一节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人物内心活动。小说家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变换叙述角度,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基本上是用第一人称叙述,但在第一部第二卷《斯万之恋爱》中则转用第三人称叙述,到第三卷又转回到主人公“我”的第一人称叙述。福克纳的多视点叙述略有不同,其作品中人物的叙述在几个相同的视点上同时展开,没有主导视点或从属视点之分,如《喧哗与骚动》的前三章由康普生家族的三个儿子以第一人称各自叙述与自己相关的故事,最后一章由黑人保姆用作家全知者的第三人称叙述,但四个不同的叙述者都围绕着该家族惟一的女儿凯蒂的反叛和堕落以及家族衰败的历史。多种叙述视角的运用,正如观察者变换角度一样可以看到景物的全貌那样,变换叙述角度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反映作品人物的经历和全貌。
叙述角度随意识流动而转换是意识流小说叙事艺术中最突出的特征。由于人物的意识具有极大的跳跃性和随意性,时间的先后顺序和空间的转换完全取决于其意识流动的环境,不仅可以从现在流转到过去,还可以从过去流转到未来,因而表现为杂乱无章和缺乏逻辑性。人物意识这种流动的无序性,要求叙述者不断变换叙述视角,才能表现人物意识在不同时空间交替出现的情景。为达到这一艺术效果,意识流小说家借助于不受理性控制、飘忽不定的意识活动,巧妙地将时空形象与人物意识融为一体,让人物意识悄悄取代叙述者的叙述,使读者往往在不知不觉中从一个人的意识领域进入另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如吴尔夫的《达洛维太太》中叙述角度就取自人物的意识,尽管达洛维太太是小说中心人物,但叙述角度并不局限于她一人,而且常常从这个人物的意识视角转到另外一个人物的意识视角。在第一章中达洛维太太在花店买花时,听到街上一辆汽车的爆炸声,位于街道上不同地点的人物相应的意识反应;接着一架从天空飞过的飞机,吸引了广场上形形色色、仰首观望的人们,记录了他们各自的意识流动情景,连贯严密,流畅自如。吴尔夫通过不同人物的意识转换,把人物的各种活动在不同的时空间并置,表现出高超的技巧,让人物将自己埋藏在心灵最深处的想法和感受和盘托出,为读者展示一幅幅生动逼真的主观画面。
三
传统作品中“全知全能”的叙述把叙述者置于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位置上。作品中的一切,包括人物、发生的或尚未发生的事件和环境,都在叙述者的视线内,这一点,从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存在许多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全知全能”的叙述,将作品中的一切进行了理性化的解释和说明,小说的潜在价值已经清清楚楚地揭示给审美主体,使接受主体创造性的想象空间受到了极大的压制和束缚。由于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全知的人物,叙述者的叙述超出了审美主体的接受范围而变得缺乏真实感。就审美的主体而言,一部作品创作的优劣,最终都取决于审美主体,即读者。每个读者都知道自己就是这个蜿蜒伸展的叙事望眼欲穿的潜在受述者,或希望审美客体(包括叙述者)与自己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思想上的联想和感情上的参与;或希望审美客体接近自己,通过叙述者把本人从现实世界的表层带入无法达到的领域,了解那些无法了解的意义和价值。这就是接受美学上所说的“期待视界”。如果作品能与读者的期待视界保持一定的距离,读者便会感到新奇和刺激,形成独特的审美效果;反之,则平淡无奇,使读者失去兴趣。意识流小说家通过自由联想、内心独白、时空交错和多角度叙述处理,淡化了叙述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区别,让读者随意识的变化,进入人物意识最深层的心理活动,来保持适当距离的期待视界。读者一旦领悟到叙述的景象同实际发生的事情相违背,期待视界的距离也就由此产生,读者由此获得了新的审美享受。
叙述者是叙事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家可以通过叙述者的调节、控制和操纵审美距离,以期读者的思想和情感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故事之中。西摩·查特曼在其《故事与话语》中,根据叙述者可被感知的程度,提出外显的叙述者与内隐的叙述者的概念。在查特曼看来,外显的叙述者可以是一个真实的人物,或者一个从外部闯入的叙述者。而内隐的叙述者则出现在所谓隐蔽或不露痕迹的叙述中,人们可以听到一个讲述事件、人物及环境的声音,但这个讲话的人一直躲藏在话语的阴影之中。外显的叙述者与内隐的叙述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叙述者在叙述文本中在多大程度上显露出来。外显的叙述者,往往对故事中的人物与事件展示出一种话语倾向,读者往往可以从话语中隐隐约约地感受出其对故事中人物、事件与情境的态度;而内隐的叙述者在作品中几乎不露痕迹,读者几乎无法感受到叙述者的存在,也无法得到叙述者的任何暗示,只能在阅读时自己去加以判断和掌握叙述者的基本情况。[3](P34) 意识流小说家,为了更好地描绘或刻画人物意识的混乱状态和无序的流动过程,展现作品人物意识发展的进程,力求自己从其所讲述的情境与事件中尽可能脱身,让作品中人物根据意识的自然流动和各自活动方式来参与故事的发展,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作者退出作品”。
传统小说家正面描述的方法只能使读者获得对事物的间接印象,而意识流小说家,在创作过程中把描写对象,通过人物的欲望、感觉、记忆、思维等意识和无意识心理,直接和戏剧性地展现出来。为此,他们采用了大量的象征手段,如意象、比喻、形象、词语和结构形式,使表面看似孤立的场景获得了重要的象征意义及关联意义。通过作品中那些没有引号的独白或对话,意识流作家把作品中人物所在社会存在的矛盾冲突,浓缩在人物的内心冲突之中,把作品展现的现实性和象征主义美学融合在一起,并通过作家对经验统一性的恢复、对已经碎裂时间片断的重新组合,以及个人真实性和自我统一性的探讨,展现出了西方社会的现代意识与精神结构。
叙述视角的转换、表现和传达人物内在心理真实,反映了意识流小说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多种叙述角度从整体上对所叙述的故事形成一种视角网结构,不同的视角按照不同的视线方向发展,共同构成视角网的深度;而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视角之间则构成了视角网的宽度。对作品的审美主体而言,视角网的深度和宽度都会引起视点的游离和扩散,延长了审美主体的审美知觉过程,因而达到了审美的目的,加大了读者的参与性;另一方面,意识流小说家把人物的内心世界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把不同人物的意识巧妙地交织在一起,这种摄取与被摄取的观察角度以及各个人物自我意识为中心的向外发散,闪回、穿插地回忆过去和预示未来,打破客观时空的限制等手法,使不同人物的意识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一个和谐的叙事整体,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为当代文学的叙事美学拓展了新的思路。
收稿日期:2006—0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