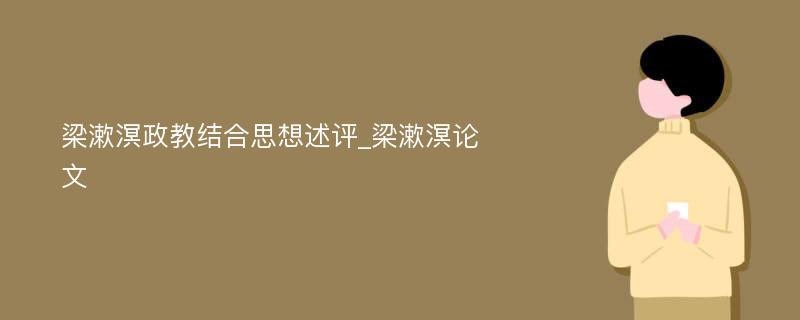
梁漱溟的政教合一思想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思想论文,梁漱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89X(2002)01-0051-04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所描述的是工农结合、城乡合作、政治经济教育相应发展的理想社会之情景,这幅情景是按照他“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的“沟通调和”之设想而构筑起来的,它既充分吸收了西方文化“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的长处,又以中国的伦理社会和儒家“人生态度”为本位,以实现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人性与现代性的完美统一。同时,梁漱溟在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过程中,对重建中国新的社会所作的具体设计,则是在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条件下,重整乡村组织,走政教合一的道路。
一
梁漱溟认为,所谓“政教合一”的“政”,即政治,是指人类社会最有权威、最有力量的团体生活。比如国家就是社会团体生活之一,不过它不是平常的团体生活,而是具有最高权威、最有力量的团体生活,即它一面能保障我们的生命安全,一面又能予我们的生命以制裁。这个团体里边的事情即为政治。所谓“政教合一”的“教”,是指教化,通过教育的方式使人心向上。据此,梁漱溟给政教合一下了一个定义:“所谓政教合一就是把人生向上这件事情亦由团体来帮助,使人的生命往更智慧更道德更善良里去。换言之,把帮助人生向上的事情亦由最高有力的团体来作,这就叫作政教合一。”[1]在梁漱溟看来,政教合一是针对政教分离而言的。所谓政教分离,是指由于西洋到了近代,要求树立个人的自由,保障个人的自由,反对团体对个人的自由的过分干涉。而从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来看,人类社会将从对个人消极的不干涉转变到积极要求团体帮助人生向上,等到团体帮助个人往人生向上作工夫的时候,就是政教合一。梁漱溟认为,中国往前要走的路只能是乡村建设的路。而乡村建设最先遇上的就是政教合一的问题,而政教合一的首要问题就是乡约。乡约一面是自治,建立将来最有力量的国家团体的组织;一面是走教化的路子,在团体帮助个人向上的方面作工夫。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的乡村,不组织团体则已,如组织团体则单从为解决事实问题以满足欲望是不行的,必须从个人要求团体在人生向上的方面去帮助和团结他人才能成功。换言之,单从自卫、自治、经济等角度出发来组织团体都不会有真的成功或好的希望,只有从较真的动机、较深的意义、较高的要求——人生向上出发,才能组成中国人的团体组织。并且中国人团体生活的成功是以自觉的、思维的、理性的要求组织为前提的,不是被胁迫强制所致;同时,团体秩序的维持,亦不能不靠理性,而依靠理性就非走教化的路不可。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以明白政教之所以不能分离而只能合一的真义所在了。
在梁漱溟看来,政教合一之所以合理与可能,是因为人生向上和人的生活完全不能分开。如考虑生活而不注意人生向上,单考虑吃饭而不考虑饭吃得对与不对,生活与向上完全分成两截,实为不通之论。所以政教分离,单单照顾人的生活,而不问人的生活有无意义是不对的;单单为谋个人的方便而消极地要求不受团体的干涉亦是不对的。基于此,梁漱溟预言:“将来社会进步之后,人类会有一更积极的要求,要求团体帮助自己的人生向上,那时人生向上不再是你的事或我的事,而是团体大家的事,由社会来帮助策勉,共趋于人生向上之途,这才是政教合一的真义。”[1]
那么,为什么将来世界要趋于合一?关键何在?梁漱溟认为,随着知识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将由零碎的不联贯的状态向越来越连贯、越来越组织化的趋势转变,把从前个人的范围打破,直至共同生活的社会化。到那时,人与人之间没有竞争,社会将发生极大的变化,即人类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大的团体组织来对付自然。在他看来,当人类各自为谋时,生计问题占据其头脑,无暇他顾;而当人类组成社会化的团体后,则个人都有相当的空闲来作思想的工夫。如此则一整个的脑筋要如何便如何,有了一个总的安排,人心就都有空闲来思考。但是,思索什么则成了一个麻烦的问题,要费事筹措如何才能使其心思活动有归着而顺理便又是一麻烦问题。从这两个问题可以看出政教合一的必要,看出社会当给予人类生活一个总的安排,人类的心思活动也须得到一个总安排。这意思是说,要使心思活动顺着理性的出路来走,既于其生活方面理出出路来,又于其精神方面理出出路来,而这一切全靠理性的教育才能做到。
同时,梁漱溟认为,现在的人类由于生活问题的压迫而不容有一个更高的要求。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们必然会产生探讨怎样生活才算对,人生怎样才有意义和价值等问题的要求,这个要求就是超生存的更高要求。当前,人类整个的要求是天天朝着组织化的方向发展,要求社会给个人一个帮助,这就是教。梁漱溟认为:“人生最大事情,即创造自己。社会应帮助人去创造自己,形成一个教育的环境,启发并鼓励个人的前进。”[1]这个教,既非古代国家之教育,也不是现在的教育,而是要求社会给个人以积极的帮助。这个帮助不仅是经济上的帮助,而且是一个更高的教育的帮助。这就是政教必趋于合一的涵义。
当然,教育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秩序。梁漱溟认为,现在的秩序是从计较心来的秩序,很显然是表面的,并不能根本转换人心。这也不是对人的态度,而是对物的态度,因为它没有要求人心的同意与同情,只是要求其身体对于社会事业的合理,只能成为一种机械的秩序。这种秩序在从前是适合的,因为以前的人是各自为谋。而现在的生活要求协同共谋,人与人之间需要一种融洽的关系。这种融洽的关系与个人本位是完全不相容的,所以只有消除个人本位,才能有真正的社会秩序。同时,这种社会秩序不能靠法律制裁来维持,而只能从人的性情上来培养,使其离开自私的心理,逐渐形成一个远大的共同的要求,这就是教育的功夫。在梁漱溟看来,现代普通的教育都没有这种功能,只有中国的礼乐才是有效的教育。礼乐予人以柔软的、自然的影响,使人养成公共的生活习惯,形成最好的秩序,从而代替了强制的法律,也代替了宗教。
梁漱溟认为,形成最好秩序的办法是实行地方自治;而实行地方自治,就是建立组织团体来过团体生活。这里所讲的团体组织,是指许多人合在一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有秩序地去活动,以求达到其目标。这中间包括了两层意思:其一,在团体里有秩序地去实行其目标时,必须是机关分职,团体中各管各的事,大家合起来去进行其共同的目标;机关虽分职,但仍为一体,大家分开做事,而所做之事仍为一个,这即所谓的组织。其二,个体是团体构成分子,个体必须有其自己的位置。如果说多数分子虽合在一起,但却失掉了原来每个分子的存在性,那就不成其为团体了。所以团体一面是有共同的结合,一面在结合里还拥有构成分子的位置。可以说,“这团体的机关分职,与团体结合中不失构成分子的位置,是组织团体顶重要的两个意义”[1]。在梁漱溟看来,团体的合成是大家彼此帮助、彼此依靠之义。合作可以产生一个社会的脑筋,对于经济可以有一个总的计划,总的安排和总的解决;同时,合作还可以改变中国人的心理习惯,训练培养新的能力,使大家在生活问题各方面发生连带关系,这种社会连带关系越往前发展越密切,中国人散漫之现状便可随之解决,经济也会随之进步。
同时,梁漱溟认为,中国将来无论地方或国家的政教天然要合一,中国的政治如果脱离了“教”,则会举步维艰。中国目前要想地方自治成功,必须经济合作,但无论是经济合作,还是地方自治,都必须经过教育的功夫才会有办法。由于国人缺乏组织能力、纪律习惯和科学知识,故中国此时需要有意识、自觉地去改善、补充及促进自己的文化,这就是一种教育工夫,亦可称之为社会教育。在梁漱溟看来,地方自治与经济合作均须养成新习惯、新能力。而新习惯、新能力的养成显然就是教育功夫。这就是说,政治经济教育三者必须合一,则中国问题才可解决。一般来说,“教”的意思较宽泛,如识文字、学技艺、求知识都可称之为教育。而政教合一所指的“教”则范围甚狭窄,是特指“关乎人生思想行为之指点教训”而言。换言之,政教合一之“教”,即是指道德问题。梁漱溟认为现在乡间最急切的事情就是整顿人心与革除陋风弊俗,其中对乡村不良分子的教育问题则是关系乡村事业能否顺利进行的问题。而这种教育须以情感化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劝导管教,勉励其向上,方能生效。当然,这种教育必须由政治、经济、教育三者合一的团体来做。在梁漱溟看来,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国家团体都是强迫构成的,都是于无意识中不知不觉地组织而成的。而中国未来的团体生活则要自觉自然地演变而成,这种团体生活不能靠强制力,而只能靠精神的感召力,走中国礼俗的路。梁漱溟断言:“中国地方自治,要想成功,必须从礼俗出发,进行组织。而礼俗的地方自治组织,亦就是情谊的、伦理的,与教学的地方自治组织——政治与经济,纯属于教学的组织之中,而教学居于首位。这就是政治、经济与教化三者合一之地方自治组织。”[1]只有这种合乎情谊和合乎伦理的地方自治组织从下往上生长,由小往大发展,才能慢慢建设成为新的国家。
在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梁漱溟认识到培养农民的新政治习惯的重要性,但是他的所谓新政治习惯仅指“团体生活的习惯”,并且这种“团体生活的习惯”之培养,在他看来也“必须合乎旧伦理精神”,合乎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之社会结构。然而,由于“团体生活的习惯”是西方“个人本位”之社会结构的产物,这与他所强调的中国“伦理本位”之社会结构在性质上是相互排斥的,因此,尽管梁漱溟再三强调培养“团体生活的习惯”之重要性,但是,他却无法解决它与所谓中国“伦理本位”之社会结构协调并存的问题。
二
然而,梁漱溟又认为,中国问题的实质既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而文化问题必须从乡村入手,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方有解决的希望。一般人对乡村建设容易产生两种误解:一是将其误解为一乡一邑小范围的事业,二是将其误解为经济一方面的事业。梁漱溟则认为,乡村建设既不是指小范围的事业,也不是指经济一方面的事业,而是包含着社会各种问题的解决。为此,他从四个方面对乡村建设运动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其一,“乡村建设运动,是由于近些年来的乡村破坏而激起来的救济乡村运动”[2]。梁漱溟认为,中国乡村破坏并不始于今日,稍一回省,就可发现其由来已久。自近百年来,世界交通,西学东渐,老的中国社会为新环境所包围,引起剧烈而严重的变化。此变化自始至终是一个趋势,即中国乡村一天一天破坏愈加尖锐的趋势。“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在近百年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固然直接间接都破坏乡村,即中国人所作所为,一切维新革命民族自救,也无非是破坏乡村。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2]。因此,救济乡村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呼声和要求,乡村建设运动自然也就成了救济乡村运动。
其二,“起于中国乡村无限止的破坏,迫得不能不自救;乡村建设运动,实是乡村自救运动”[2]。梁漱溟认为,救济乡村既然是中国社会各阶层、各方面一致共同的要求,当然就要靠乡村以外的众多力量来救济乡村。但是,此一力量在今日中国尚寻不出来。因此,救济乡村的力量就必须从乡村内部寻找,这样,乡村建设运动便成了乡村自救运动。
其三,“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之积极建设的运动”[2]。那么,中国建设为什么一定是乡村建设呢?梁漱溟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走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路,这是因为,首先,近代资本主义的路,今日过时;人类历史到现在已走入反资本主义的阶段,所以不能再走此路。其次,近代工商业的路为私人各自营谋而不相顾,不合现代国家计划经济之趋势;而且当今国际间盛行倾销政策,对中国威胁太大,故经济无发展余地。再次,中国没有一个近代工商业所需要的政治环境,所以也不能走此路。基于此,梁漱溟认为:“所谓中国建设(或云中国经济建设)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就是说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的路。换言之,必须从复兴农村入手,以达到新社会建设的成功。”[2]
其四,“今日中国问题在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乡村建设运动,实为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这最末一层意思,“乃乡村建设真意义所在”。梁漱溟认为,今日整个中国社会日趋崩溃,向下沉沦,在此大势中,其问题实非一乡一邑或某一方面所能单独解决。所以,“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2]有人认为中国问题是“帝国主义与军阀”问题,又有人认为中国问题是“贫、愚、弱、私”问题,梁漱溟则认为这两者都没有抓住中国问题的实质。他指出:“外界问题(帝国主义)虽是有的,但中国内部问题大过外界问题;个人的不健全也是有的(贫、愚、弱、私),但社会的不健全大过个人的不健全”。“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2]在梁漱溟看来,人非社会则不能生活,而社会生活则非有一定秩序不能进行。任何社会必有其组织构造者,形著于外而成为一种法制礼俗,即社会秩序。循之由之则治,建之离之则乱,是谓治道。中国此时的社会组织构造已根本崩溃,法制礼俗已被否认,夙昔治道已失,而任一秩序的建立已不成之时。总之,乡村建设运动如果不在重建中国新社会构造上下功夫,中国问题的解决是根本不可能的。
如前所述,既然建设范围意在整个社会,而不止于乡村,为何而名之曰乡村建设?既然要解决的问题于社会各种问题无所不包,为何而名之曰乡村运动?梁漱溟对此作了三点解释,他说:“一、此建设工作或解决中国问题的工作,必从乡村入手;二、此建设工作或解决中国问题的工作,必赖乡村人自身的力量为主;三、此建设工作或解决中国问题的完成,在实现政治重心、经济重心都根植在乡村的一个全新组织构造的社会。”[1]
在梁漱溟看来,乡村建设运动的目的,就是要辟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要使经济上的“富”、政治上的“权”综操于社会,分操于人人。其纲领则在如何使社会重心从都市移植于乡村。乡村是一个小单位社会,经济组织政治组织皆天然要造端于此。恰好乡村经济建设要走“合作”的路,那是以“人”为本的经济组织。现在所急的是如何遵循这一原则以培养乡村经济力量和乡村政治力量。这种培养乡村力量的工夫,谓之乡村建设。总之,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的一种社会运动,既要靠知识分子来引导,又要以乡村自身为主力。“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1]。只有知识分子下到乡村,与当地农民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中国问题之解决才有希望。
那么,知识分子下到乡村,通过什么方式开展乡村建设运动呢?梁漱溟认为:“此刻的中国,天然的要着重民众教育,或说社会教育。民众教育或社会教育,即乡村建设。中国的民众多在乡村,故民众教育即乡村民众教育。中国是乡村社会,故社会教育即乡村教育,此种教育是很活的,很实际的教育,此教育即乡村建设。”[1]故乡村建设就是要通过教育的方式,改造社会,启发农民的向上精神,提高农民的素质,把农民纳入社会团体组织之内,培养他们的团体生活习惯和互助合作精神。当然,这种教育方式不能采取学校式的教育,而应以社会式的教育为主体。其具体形式就是村学和乡学。村学和乡学既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实践之一,也是乡村建设的重要环节。村学和乡学作为乡村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化社会为学校,引导众人一齐向上学好,讲求进步。
当然,梁漱溟开展乡村建设运动,开办村学和乡学,不仅仅是简单地将其作为一种教育机构,更多的是将其作为培养乡村民众人心向上精神的一种组织。梁漱溟认为,自近代以来,随着中西交通、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精神出现了严重的不合,故彼此之间非有一个沟通不可。这个沟通不单是理论上的,而要在事实上表现出来,表现出来的这一事实,就是新社会的组织构造。其前提条件就是在根本处——中西方人的精神——找出一个妥贴点来,否则,中国社会的组织机构便会无根,一切制度也就完全建立不起来。在梁漱溟看来,这个新的组织构造就是村学和乡学。村学和乡学采取了西洋近代进步团体生活的精神,同时尽量地、完全无缺撼地容纳了中国两大长处——伦理主义和人生向上的精神。这里的所谓伦理主义,是指“这个团体里边的制度构造,是采取个人尊重团体、团体尊重个人、少数人尊重多数人、多数人尊重少数人”。其要点是“尊重对方,仿佛没有自己”[1]。只有将伦理主义和人生向上的精神合融到团体组织中,乡村组织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然而,单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还必须设法引进新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如不能进步,则村学和乡学就不能开展为一大社会,中国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也就不能开展起来。总之,只有团体组织与科学技术的辗转推进,中国社会才能进步。
针对当时中国农村劳动者文化、素质低下的状况,梁漱溟认为,只有大力发展教育,才能提高农民的素质,进而实现人的现代化。为了使教育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为建设乡村服务,梁漱溟专门设计了一套以社会为本位的教育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
其一,它改变了旧式的教育体制,要求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融合归一”。发展乡村教育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来看,他的乡村教育,不是狭义上的学校教育,而是集学校教育与民众教育于一体的“社会教育”。他认为“在中国,今日我们应当拿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合起来作”[1]。为了落实“乡村社会教育”体制,梁漱溟在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上作了新的探索。
在教育方式上,梁漱溟规定,各级学校“得随宜运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各种形式,而无分所谓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同时还规定:“乡学在职能上以基本教育为主,在程度上为当地社会及国家力所能举之最低级教育。在编制上酌设成人部、妇女部、儿童部等,旧制之小学校、民众学校等,应分别归入上项编制中(小学即儿童部、民众学校即成人部),在设备上酌设大会堂、图书馆、体育场、音乐堂等。在方式上兼用社会教育及学校教育两方式。”[1]
在教育内容上,梁漱溟认为,以社会为本位的教育应包含社会生活的基本教育、各项人才的培养训练和学术问题的研究实验等。但所有这一切,都得以“教育解决社会问题”为主旨。基于这种认识,梁漱溟特别重视职业教育和生产教育,并明确要求各级学校应因地制宜地编写各种适合乡民的乡土教材,“在职业训练中,必须打破一切非必要的学校形式而无所拘。例如入学资格、修业年限、课程标准、师资限制等,均应随宜设施”。[1]
其二,它延长了民众受教育的时间。梁漱溟认为,以前的教育,将受教育的年龄限于未成年前,是不适合社会需要的。因此,他主张将民众受教育的时间延长。在他看来,延长民众受教育的时间,其理由在于:“(一)现代生活日益繁复,人生所需要学习者,随以倍增,卒非集中童年一期所得尽学,由此而教育延及成年之趋势,日见重迫。”“(二)社会生活既繁密复杂,而儿童较远于社会生活,未及参加,在此种学习上以缺少直接经验,效率转低,或至于不可能,势必延至成年而后可。又惟需要为能启学习之机;而惟成人乃感需要。借令集中此种学习于童年,亦徒费精力与时间,势必待成年需要,卒又以成人教育行之。”“(三)以现代化进步社会变迁之速,若学习之早,俟后过时即不适用;其势非时时不断以学之不可。”[1]因此,梁漱溟认为,必须将教育扩大至整个社会,将时间放散而延长到成年乃至终身。
梁漱溟的上述种种教育主张,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弊端,作为乡村建设的一种手段,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但毕竟多多少少给农民带来了一些物质文化方面的利益,促进了农民素质的提高和精神面貌的改善;其教育主张也不乏可贵之处,诸如他重视职业教育和生产教育,主张将民众受教育的时间延长到成年乃至终身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农村文化建设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意义。
标签:梁漱溟论文; 社会教育论文; 生活教育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个人习惯论文; 经济学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