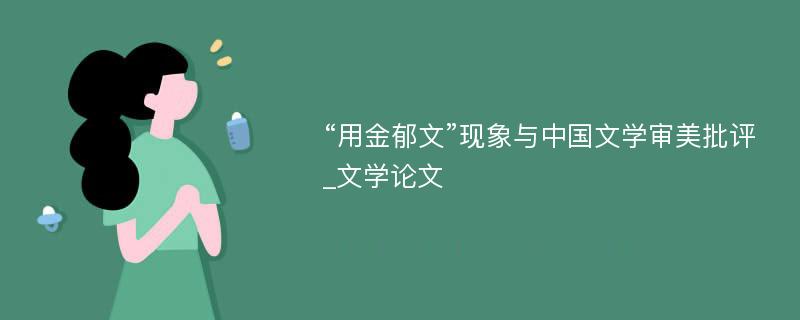
“以锦喻文”现象与中国文学审美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学论文,批评论文,现象论文,喻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锦绣”是中华民族一项伟大的发明创造。它对我国古代民族融合、古代文化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都有过重要作用。因其参与塑造中华文明早期形态的重要作用,“锦绣”甚至成为华夏文明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它不仅影响了我国古代上层社会的日常生活,培养了人们的审美观念,而且还将其影响扩展到古代社会意识形态如宗教、政治、伦理、文学和艺术等各个方面。其中,锦绣与文学的关系就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的新课题。关于这个问题,古今学者偶有涉及,专题的讨论和研究尚有待深入。近几年来,笔者对锦绣与文学的审美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研究,①本文就是此研究思路的拓展与深化。
一、“以锦喻文”现象的历史演变
在论述之前,先要解释一下本文将要涉及的几个关键词。锦绣,最好的解释者是唐人颜师古。他在为史游撰写的《急就篇》作注时说:“锦,织綵为文也;绣,刺綵为文也”。②《辞源》即采用了他的解释。所以,本文中的“锦绣”,就是泛指有彩色花纹的丝织品或丝绣品。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有以锦喻文者,有以绣喻文者,也有以“锦绣”合称喻文者,还有以锦绣的花纹图案喻文者,等等。凡此种种,本文为表述方便,皆以“锦”代之;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有以锦喻诗者,有以锦喻赋者,有以锦喻词者,有以锦喻文者,有以锦喻小说者,还有以锦喻戏曲者,等等。同样,为了表述方便,皆以“文”代之。因此,本文所谓的“以锦喻文”,就是指以锦绣之美来比喻文学之美。其实“比喻”只是一种参照,即将“锦绣”作为“美”的范式来批评文学。至于“文学批评现象”,也有两层含义:其一,它是指具有普遍性的文学批评行为。譬如“以锦喻文”,如果只是某个人偶尔使用一下,那就不能算作“文学批评现象”。只有很多人使用“以锦喻文”,使其演变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学批评行为,才能构成文学批评现象。其二,它是指具有影响力的文学批评行为。又如“以锦喻文”,如果只是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特定的一些人“以锦喻文”,在文学批评史上没有造成什么影响,那也不能算作“文学批评现象”。只有广大地域中的众多批评家使用“以锦喻文”,而且代代相传,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才能构成文学批评现象。那么,“以锦喻文”是不是这样一种文学批评现象呢?这便是本文首先要论述的问题。
“以锦喻文”的文学批评行为最早出现于汉代。当时,辞赋创作十分盛行。司马相如、扬雄和班固等人便“以锦喻赋”,即以“锦绣”作为参照,来批评辞赋创作。当时有“以锦喻文”的,东汉王充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多次以“锦绣”为参照来谈论文章。云:“绣之未刺,锦之未织,恒丝庸帛,何以异哉?加五采之巧,施针缕之饰,文章炫耀,黼黻华虫,山龙日月。学士有文章,犹丝帛之有五色之巧也”。③又云:“文如锦绣”。④王充对于“以锦喻文”的运用,十分娴熟,对后世影响较大。为什么说“以锦喻文”最早出现于汉代呢?就是因为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和王充等人将锦绣美作为参照物,来谈论辞赋美和文章美。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王充提出了“文如锦绣”的重要观点。尽管王充本人的文学观是崇尚“实用”,并不赞成“文如锦绣”的审美趣味。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并不重要。我们所看重的是“文如锦绣”背后的文学审美时尚,当然是以司马相如等人为代表的辞赋审美时尚。这对于“以锦喻文”现象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五言诗为代表的文学创作崇尚声律、文采和意象的形式美,文学批评高扬“华丽”的旗帜,“文学自觉”在创作、批评和理论三个层面上获得了更为深入的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以锦喻文”在文学批评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使用。陆机《文赋》中用了4处,如“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李善注:“言音声迭代而成文章,若五色相宣而为绣也”。⑤这是陆机“贵妍”的文学语言观的一种表述;又如“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方廷珪注:“以织喻文”。⑥其实,所谓“以织喻文”,也就是“以锦喻文”。可见陆机对于“以锦喻文”的运用也很精到。尤其是方廷珪所揭示的“以织喻文”,是一种很精彩的概括,也是一种接近文学本质的把握。葛洪也多次“以锦喻文”。如“且文章之与德行,……譬若锦绣之因素地”。⑦孙绰亦用“以锦喻文”的方法来评论文学,而且很著名,常常被人们引用。云:“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又云:“曹辅佐才如白地明光锦,裁为负版绔,非无文采,酷无裁制”。⑧鲍照评颜延之诗云:“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⑨钟嵘说:“陈思之于文章也,譬……女工之有黼黻”;“孝武诗,雕文织綵,过为精密”。⑩然而,在这个时期,“以锦喻文”运用得最多最好的人是刘勰。据我的不完全统计,在《文心雕龙》一书中,使用“以锦喻文”有48处之多。(11)由此可见,在以“华丽为冠冕”(12)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以锦喻文”在文学批评中,得到了普遍的运用。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从时间上看,大约在西晋武帝太康年间至梁元帝天正元年共270多年里,“以锦喻文”持续运用近3个世纪;二是从空间上看,这个时期“以锦喻文”的运用地域范围遍及中原和江南的广大地区;三是陆机、葛洪、孙绰、鲍照、沈约、钟嵘、刘勰等“以锦喻文”的运用者,都是当时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四是“以锦喻文”的运用,与当时崇尚“华丽”的文学审美时尚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这个时期“以锦喻文”的运用,无论从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更具有普遍性。它不再显得表面化,不再是一种修辞学上的比喻。它不仅很少使用中介词,而且将有些“丝织锦绣话语”直接转化成为“文学批评话语”了。这些特点充分表明,“以锦喻文”的运用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文学批评现象。这是一个重大的发展。
唐代文学批评对“以锦喻文”的运用比较复杂。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其一,以“锦绣”形容美好的文思。李白说:“常醉目吾曰:‘兄心肝五藏皆锦绣耶!不然,何开口成文,挥翰雾散?’”(13)这种说法影响极大,被后人不断引用。尤其是柳宗元《乞巧文》将此概括为“锦心绣口”之后,便作为成语固化下来,并流传于后世。如清朝康熙年间钱酉山有《西厢记》改写本一种,名《雅趣藏书》,又名《绣像西厢》。其《自序》说:“俾学者读之,心醉神怡,纵有锦心绣口,亦为之搁笔,而不能赞一词”。其二,以“锦绣”形容或者代指优美的诗歌作品。这种观念主要表现在诗歌作品中。如刘禹锡说:“珍重和诗呈锦绣”。(14)其三,运用“锦绣”为参照物来批评文艺作品。评论音乐,如司空图说:“文八音,则锦绣相宣”;(15)评论诗,如李峤说:“雕文将锦绣同美”;(16)评论词,如欧阳炯说:“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17)评论赋,如白居易说:“词采舒布,……掩黄绢之丽藻”;(18)评论文,如张说云:“五綵无章,黼黻交其丽”,(19)等等。从谈论构思、创作到批评,从评论音乐、诗、词、赋到散文,唐代批评家对于“以锦喻文”的运用领域有了较大的拓展。“锦绣”作为文学批评的范式,运用范围更广,运用频率更高,也更为深入人心。这是一个新的发展,尤其是“锦绣诗”、“锦绣篇”和“锦绣文章”的说法,更明确地揭示了“锦绣”与“文学”的审美关系,同时也揭示了“以锦喻文”的审美本质。
宋代以张扬“理性”为主。在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下,宋代的文学批评家对于“以锦喻文”的运用,除了秉承唐人的用法之外,在审美价值评判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总的来看,宋人对于“文采”的审美态度是由“清丽”趋向于“淡雅”。因此,宋人“以锦喻文”也有两种情况。其一,崇尚“清丽”,用于肯定性的批评之中。他们认为,人类对于“锦绣文采”的审美,是人性的基本需求。正如陈埴所说:“目不止于色,而必求锦绣文采,亦可谓之性乎?”(20)因而他们用“以锦喻文”来肯定“文采”。如吴沆说:“凡人作文,要如细花锦,须花上有花,叶中有叶,愈看愈有工夫,方谓之妙”。(21)周煇说:“某之文,……如野妪织机,虽能成幅,而终非锦绣”。(22)在宋人看来,以“锦绣”所标示的文学审美境界,并不是一般对“华丽”和“文采”的追求,而是一种汰尽人工痕迹的自然美境界。否则,就是“锦工”所为,雕虫小技。其二,崇尚“淡雅”,用于否定性的批评之中。如苏洵说:“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23)夏英公说:“杨文公文如锦绣屏风,但无骨耳”。(24)持此论者崇尚“淡雅”的文采,以为如锦如绣则人工斧凿之迹太胜,显得不自然,且又失天趣。总之,尽管两派诗学观念不同,但他们都把“锦绣”作为文学批评的参照物;而且,通过两派诗学观念的碰撞,进一步丰富了“以锦喻文”的内涵。当然,宋人最大的贡献是对于“以锦喻文”现象有了自觉意识。葛立方说:“诗人赞美同志诗篇之善,多比珠玑、碧玉、锦绣、花草之类”。(25)其中就谈到“以锦喻诗”,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不仅如此,葛立方还在调和以上两派诗学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诗学观念。他说:“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26)这样就将两派的观点统一起来。因此,在宋代文学批评中,无论是“清丽”派的肯定,还是“淡雅”派的否定,在表面上看来似乎不同,但其实并不矛盾。“清丽”派虽然肯定文采,但却是褪去华芬的“清丽”。这与“淡雅”派所倡导的“自然”、“天趣”的文采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总之,宋代人将“文采锦绣”提到“人性”的高度来认识,所崇尚的是一种“清丽”、“淡雅”的文采美,这是一种更为理性的文学批评。
明清时期,文学批评将“以锦喻文”的运用,拓展至小说、戏曲领域。先谈小说批评的运用情况。诸家或借“锦绣”谈小说创作思维与才能,如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时曾说“锦心绣口”、“锦绣心肠”;(27)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时曾说“锦绣才子”。(28)或借“锦绣”谈小说创作方法,如毛宗岗所说的“添丝补锦,移针匀绣”法,(29)张竹坡所说的“穿插法”:“而穿插之妙,又如凤入牡丹,一片文锦,其枝枝叶叶,皆脉脉相通,却又一丝不乱。而看者乃又五色迷离,不能为之分何者是凤,何者是牡丹,何者是枝叶也”。(30)或借“锦绣”谈小说语言文字之美,如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说:“李肃说吕布一段文字,花团锦簇”。(31)或借“锦绣”谈小说结构,如汪道昆评论《水浒传》说:“纪载有章,烦简有则。发凡起例,不杂易于。……又如百尺之锦,玄黄经纬,一丝不纰”。(32)再谈戏曲批评的运用情况。明人李开先批评当时的元曲选本时说,选曲如选锦:“选者如二段锦、四段锦、十段锦、百段锦、千家锦,美恶兼蓄,杂乱无章”。(33)清人李渔的戏曲批评最善于运用“以锦喻文”。他或谈戏曲创作思维:“授以生花之笔,假以蕴绣之肠,制为杂剧”;(34)或谈戏曲创作方法:“曲谱者,填词之粉本,犹妇人刺绣之花样也,描一朵,刺一朵;画一叶,绣一叶。拙者不可稍减,巧者亦不能略增”;(35)或谈戏曲批评:“(虚假的批评)不顾才士之屈伸,遂使锦篇绣帙,沉埋瓿瓮之间”。(36)总之,从以上论述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其一,明清文人除了在文采、创作、思维、批评等方面,继承了前人运用“以锦喻文”的丰富经验之外,还在才能、方法、结构和选本等方面运用了“以锦喻文”。其二,明清文人除了在诗、词、赋和散文批评方面,继承前人运用“以锦喻文”的传统之外,还在新兴文体小说和戏曲的批评中,运用了“以锦喻文”。这两点是明清文人的新发展。其三,金圣叹和李渔在小说和戏曲批评中,不仅大量运用了“以锦喻文”方法,而且运用得生动、准确,评析得鲜活、犀利,给读者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大量事实证明,以“锦绣”作为审美参照物来批评文学,是跨越时空、影响深远的群体性文学批评行为,既有普遍性,又具有影响力。因此,我们有理由说,“以锦喻文”是一种文学批评现象。从历史角度来看,“以锦喻文”现象滥觞于汉代,形成于魏晋南北朝,唐宋有所开拓,明清有所发展。汉代用于赋,有“文如锦绣”之说;魏晋南北朝用于诗文批评,有“以锦喻文”之法;唐代用于评论诗、词、赋、文和音乐等领域,有“雕文与锦绣同美”之说;宋人渐识“以锦喻文”现象,且将其延伸于肯定与否定批评之中;明清两代则发展于小说批评与戏曲批评方面。从本体构成来看,“以锦喻文”的运用,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当初的“文采美”层面,广泛地涉及文学的创作思维、创作才能、创作方法、风格神韵、篇章结构和选本批评等方面。这就表明,“以锦喻文”具有广泛的普适性,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文学批评现象。
二、“以锦喻文”现象的学理基础
那么,“以锦喻文”现象产生的学理基础是什么?“锦”与“文”二者之间有何内在关联?这是本文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首先,谈“以锦喻文”的历史根据。汉代以前,人们不仅将“锦绣”看作艺术,而且对锦绣之美推崇备至。锦绣在衣、帽、鞋、被、巾、带、帐、旗、车、室等日常生活方面起着重要的装饰和美化作用,甚至成为帝王将相、后妃佳人和大吏巨富的特权。由于锦绣在上层社会生活中的广泛使用,其功能便由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逐渐提升。诸如锦绣与国家、政治、礼仪、外交、宗教和民俗等关系,在先秦和汉代的典籍中均有记载。譬如中国,古称“华夏”,简称为“华”。这个“华”就与锦绣有关。《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正义》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这里的“服章”是指有色彩花纹的锦绣服装,即锦绣美。随着“锦绣”对外贸易的范围不断扩大,外国人将中国称为“丝国”;又如政治,桓宽说:“夫罗纨文绣者,人君后妃之服也”;(37)又如礼仪,被王国维推许为记载周室古礼的《尚书·顾命》载:“王麻冕黼裳,由宾阶隮。卿士邦君麻冕蚁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看来当时上层统治者的锦绣礼服的色彩花纹是有严格区分的;又如外交,《太上黄庭经》:“古者盟,以玄云之锦九十尺,金简凤文之罗四十匹”;又如宗教,《礼记》:“所以交于神明者,不可以同于所安乐之义也,故有黼黻文绣之美”;又如民俗,《礼记·月令》:“是月也,命妇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因此,“锦绣”的功能远远地超出了日常使用的范围,由物质层面不断向精神层面提升,为“以锦喻文”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这就是“以锦喻文”的历史根据。
其次,谈“锦”与“文”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和“以锦喻文”的学理基础。从历史与逻辑结合的视角来看,其内在关联和学理基础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锦绣之“文”(纹)与文学之“文”的内在关系。
先谈锦绣之“文”。锦绣之文,是指锦绣的花纹。锦绣的本质有三个方面:其一,它是以“丝”为材料的织品或绣品;其二,它有十分丰富的色彩;其三,它有花纹。由此可知,“花纹”是锦绣的本质之一。在先秦典籍中,锦绣的“花纹”,一般简称为“文”。《左传·桓公二年》:“火、龙、黼、黻,昭其文也。”墨子说:“锦绣文采靡曼之衣”(《墨子·辞过》)。田鸠说:“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令晋为之装饰,从衣文之媵七十人”(《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这些“文”,都是指锦绣“花纹”而言。所以,郑康成说:“文,织画及绣锦。”(38)锦绣花纹,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据考古发现,殷商时期的锦绣已经有十分规整的“回纹”、“云雷纹”和“勾连纹”了。这也证实了《尚书·益稷》对锦绣花纹的记载是比较真实的。诸如:“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等,都是当时锦绣的花纹。其中有些是具象的图像纹,有些是抽象的几何纹。汉代以后,锦绣花纹式样更加丰富。据东晋陆翙《邺中记》记载:“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斑文锦,凤皇朱雀锦,韬文锦,桃核文锦……,工巧百数,不可尽名也”。(39)现存明代装裱《大藏经》封面的锦帛“花纹”就有近1000种之多。
次谈文学之“文”。文学之文,是指语言文字。文学的本质也有三个方面:其一,它是用语言文字为媒介的艺术品;其二,它有声韵和文采;其三,它有情感和意象。所以,文学之“文”,有四层基本含义:其一,文字;其二,声韵;其三,文采;其四,意象。文学是语言艺术,语言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所以,文学也包括口语文学和书面语文学,而且经历了由口语文学向书面语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人类早期的文学形态“诗”,与“音乐”有密切的关系。这种特点衍生出后世文学的“声韵”元素。这是口语文学“审美化”的产物。因此,口语文学的审美元素“声韵”和书面语文学的审美元素“文采”,再加上口语文学和书面语文学所共有的“意象”,就是成熟形态的文学了。所以,有声韵、有文采和有意象的文字作品,就是文学。这是中国古代批评家对于“文学”的基本观念。
再谈锦绣之“文”与文学之“文”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锦绣和文学两者共用了一个“文”字。在汉代以前的典籍中还没有发现有“纹”字,许慎《说文解字》中无“纹”字。所以,汉代以前“花纹”的“纹”就用“文”字代替。“纹”是后起的俗字,段玉裁说:“纹者,文之俗字”,(40)大约出现在唐代。所以,在唐代以前典籍中,锦绣之文与文学之文长期共用一个“文”字。其二,锦绣的花纹图案与文学的文字意象有着共同的渊源。众所周知,汉字是象形文字,就是许慎说的“依类象形,故谓之文”。(41)从早期汉字(如甲骨文和金文)来看,它与史前陶器、殷商青铜器和锦绣的花纹,有着共同的渊源。这不需要再去繁琐考据,只要读者将甲骨文和金文的“龙”、“凤”、“鸟”、“鹿”、“虎”、“鱼”、“龟”、“云”、“雷”、“水”等文字,分别与史前陶器、殷商青铜器和锦绣上面的龙纹、凤纹、鸟纹、鹿纹、虎纹、鱼纹、龟纹、云纹、雷纹、水纹等对照观察,就会赞同我的观点。因此,“书画同源”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它们共同的渊源是什么呢?就是现实中的事物,诸如天上的云雷,地上的鸟兽等。我们的祖先在创造文字、陶纹、青铜纹和锦绣纹时,仰观俯察,发扬了“观物取象”的审美创造精神。所以,锦绣与文学二者具有“同根近性”的内在关系。汉字有具象、半具象和抽象三种。具象者有象形字,半具象者有形声字、指事字和会意字,抽象者有转注字和假借字。汉字具象和半具象者类若锦绣的图像纹,抽象者类若锦绣的几何纹。还有“花纹”(包括图像纹和几何纹)是锦绣的本质,缺少了“花纹”则不成为锦绣;“意象”(包括文字意象和作品意象)也是文学的本质,缺少了“意象”也不成为文学。所以,正因为这两个方面的内在关系,东汉刘熙才说:“文者,会集众綵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42)可见“会集众采”的锦绣之“文”与“会集众字”的文学之“文”是有内在关系的。
第二,锦绣之“采”(彩)与文学之“采”的内在关系。
锦绣有色彩,文学也有文采,而且两者又共用了“文采”一词。先谈锦绣之“采”。颜师古说:“锦,织綵为文也;绣,刺綵为文也”。颜氏谈锦与绣除了共用“文”字外,还共用了“綵”字,可见两者都有讲究色彩的特点。所以说,“织采为文曰锦”,(43)“五采备谓之绣”(《考工记》)。这一点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中能够得到证实。《尚书·益稷》说:“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100多件丝织品中,就有十多种色彩。墓主是西汉初年长沙国丞相利苍。这与史籍对于汉代官制色彩等级的记载是一致的。按照汉代官制规定:“列侯以上,锦缯采十二色;六百石以上,重练采九色;三百石以上,五色采;二百石以上,四采;贾人,缃缥而已”。(44)到明代时,丝织锦绣的染印色彩就有24种之多。在古代典籍中,锦绣也被称为“文采”、“文绣”和“文章”。关于“文采”的例子上文已经举了不少,现在再举一些有关“文绣”和“文章”的例子。前者如,“衣必文绣”(《墨子·非乐》),“黼黻文绣之美”(《礼记·郊特牲》);后者如,“灭文章,散五采”(《庄子·胠箧》);“必将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荀子·富国》)。总之,“锦”、“绣”、“文采”、“文绣”和“文章”等名称都与色彩有关系。《说文解字》收入与色彩有关的丝织物文字30多个,其中“红”、“绿”、“紫”、“绛”等为常见色彩。许慎说:“红,帛赤白色”;“紫,帛青赤色”;“绿,帛青黄色也”;“绛,大赤也”。(45)这些“色彩”文字的起源与丝织物染色有内在的关系。
次谈文学之“采”。如果将“锦绣”作为审美参照物,那么,文学也应该有“花纹”和“色彩”。文学的“花纹”是意象,包括文字意象和作品意象,如上文所述;文学的“色彩”是“文采”或者“辞采”。古人关于“文采”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文采”,是指文字色彩而言,即工巧、华丽和优美的语言文字;广义的“文采”,是指语言的声音、文字和意蕴的色彩。如《文心雕龙》所谓的“声采”(《原道》)、“辞采”(《附会》)和“情采”(《情采》)。但是,一般来说,狭义的用法较为普遍。本文采纳狭义的用法。文字色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色彩词”的运用,诸如赤、黄、红、绿、青、蓝、紫、白、黑之类。刘勰是很重视“文采”的批评家。据辛刚国博士的统计,《文心雕龙》中用“采”115次,用“文采”7次。(46)所以,刘勰对于“色彩词”的运用有一番很独到的见解。他说:“文采所以饰言”;又说:“凡搞表五色,贵在时见,若青黄屡出,则繁而不珍。”(47)前者囿于传统,后者来自经验,可谓语语中的,字字经典。谢榛《四溟诗话》卷2记载了一件颇有趣的事:“黄司务问诗法于李空同,因指场圃中绿豆而言曰:‘颜色而已’”。(48)将“颜色”视为作诗之奥秘,虽有点偏颇,恐也有些经验的来头。然而,“色彩词”用多了也是一种弊病。正如骆鸿凯所说:“吾师(按:指黄侃)每称陈文述诗为国旗体,亦嫌其一篇之中多用采色字也”。(49)另一个是文字的装饰和美化,指工巧的修辞、华丽的辞藻和优美的语言等。这方面的观点和例子比比皆是,不须多言。
再谈锦绣之“采”与文学之“采”的关系。这两者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共用“采”、“文采”和“文章”等术语上。据我的考察,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文”、“采”、“章”等文字的本义和起源都与锦绣色彩有关系;其二,“采”、“文采”和“文章”等术语,首先是用在丝织锦绣的审美活动中,其次才用在文学审美活动中。因此,我们可以透过锦绣与文学共用“采”、“文采”和“文章”等色彩术语的现象,看到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不仅如此,据我的考察研究,还有大量的丝织锦绣术语转移到了文学活动领域,成为文学创作、批评、理论和审美的常用术语。诸如,在文学创作方面,有编、缀、绎、纪、缉、章、回等;在文学批评方面,有经、纬、线、组、织、绪、缝、练、约、级、缘、缛、纾、绩、纷、繁、綦、纡等;在文学理论方面,有文、采、藻、综、络、纠、结、系、缩、纲、续、统等;在文学审美方面,有红、绿、紫、纯、细、素、丽、绮、绚、绣等。这只是一个相对的分类,因为有许多术语存在着“跨类”使用的现象。
第三,锦绣之“美”与文学之“美”的密切关系。
先谈锦绣之“美”。如上文所述,锦绣有花纹,有色彩,是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审美物。马克思说:“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50)在悠远的上古社会,锦绣色彩斑斓,花纹丰富,不仅表达了下层社会女性(后来也有少数男性从事锦绣生产)的审美智慧和审美趣味,也极大地满足了上层社会的审美需求,成为当时最大众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审美物。《辞源》说:“锦为美物,因以喻鲜艳华美。”(51)因此,“锦绣”成为“美”的标志物和符号,也就是本文所说的“美”的范式。所以,当时人们大多喜欢用“锦绣”谈论审美问题。诸如,墨子说:“(锦绣)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墨子·辞过》)。荀子说:“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荀子·礼论》)。司马迁说:“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52)萧统说:“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53)这些表明,古人对于锦绣的审美功能的认识是一致的。同时,还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古人认为的“美”,主要是指视觉审美感受,即所谓的“目观则美”(《国语·楚语上》)。而且,“目”的审美对象主要是“色彩”,如《孟子·告子章句上》说:“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荀子·劝学》说:“目好之五色”,即色彩愈丰富的事物则愈美。古人崇拜龙,原因之一即它是由“彩虹”变的;(54)古人喜欢凤,也因为它是“五采鸟”(《山海经·大荒西经》)。正如王充所说:“龙鳞有文,于蛇为神;凤羽五色,于鸟为君”。(55)因此,是色彩成就了它们的“王者”地位,于是色彩的使用就成为一种特权。如在我国古代服饰中,真龙天子皇帝是占有色彩最多的。同样,锦绣也是由于其色彩最为丰富而一度成为上层统治者的专用品。所以,与“龙”、“凤”图案一样,锦绣也被上层统治者所专用,成为色彩审美王国里的“王者”,成为“美”的典范。
次谈文学之“美”及其两者的关系。文学是语言艺术。所以,文学美首先就表现在语言美之上。关于“语言美”,包括口头语言美和书面语言(即文字)美的问题,古人是认识到了的。譬如,《礼记》所谓的“言语之美”(《少仪》);王充所谓的“何言之卓殊,文之美丽也”。(56)那么,锦绣之“美”与文学之“美”又是如何发生关系的呢?是色彩,色彩成为沟通两者关系的中介。如上文所述,锦绣与文学都讲究色彩美,也都看重视觉美感享受。所以,以“锦绣美”为参照物来谈论“文学美”问题,从汉代以来已成为一大传统。由此可见,锦绣之美与文学之美两者是有密切关系的。
综上所述,由于锦绣之“文”(纹)与文学之“文”、锦绣之“采”(彩)与文学之“采”和锦绣之“美”与文学之“美”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因而不仅形成了“以锦喻文”的文学批评现象,而且“以锦喻文”现象又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文学审美批评。所以,这“三个关系”既是其内在关联,又是其学理基础。
三、“以锦喻文”的文学审美批评意义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在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中,忽视了对“审美批评”的关注和研究。20世纪出版了数十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但是没有一种谈到“审美批评”。在这些各类“古代文学批评史”中几乎没有“审美批评”的位置。由于这些忽视,遮蔽了“审美批评”存在的真相,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误区。因而使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仅仅是一种教化、载道和实用的批评,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审美批评”。甚至有人认为,“审美批评”只能是属于西方的和现代的,而不是属于中国古代的。尽管早在30多年前,刘若愚在他的《中国文学理论》(英文版)一书中就已明确指出中国古代“审美批评”(或翻译为“审美理论”)的存在。但是,这并未改变“中国审美批评”被忽视的局面。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并不缺少审美批评,所缺少的只是我们对于“审美批评”的关注和研究。所以,“中国审美批评”至今仍支离分散地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资料中,有待进一步地发掘和提炼。本文所发掘和提炼出的“以锦喻文”现象,实质上就是一种典型的文学审美批评。
汉代以前的艺术谱系由诗歌、音乐、舞蹈、雕刻和锦绣等共同构成。先秦时期,人们将“锦绣”也看作是一门技艺和艺术。因为,当时绘画艺术还不是很发达,锦绣的地位远比绘画要高。所以,锦绣便与雕刻一起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要观赏品。其中前面三种艺术属于“乐”的范畴,而且是一种原始的混合形态,地位比后两种艺术要高出很多。后面两种属于实用性的造型艺术范畴(其实先秦时期的艺术都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在先秦诸子的论著中经常将“雕刻”和“锦绣”相提并论,因为两者都达到了当时造型艺术的最高水平。但是,在这几类原始艺术中,与当时人们审美观念关系最为密切的,还应该是锦绣。因为,当时流行着“目观为美”的原始审美观念。就是说,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美”与“色”(主要是色彩)有关,“美感”就是人们对于事物色彩的视觉快感。那么,色彩越丰富的事物就越美。在诗歌、音乐、舞蹈、雕刻和锦绣等原始艺术中,只有锦绣色彩最为丰富,因而是最美的,成为“美物之首”,也成为“美”的范式。它是多种色彩有机统一的审美创造的最高成就,代表了当时人们的审美理想。因此,它在中国古代审美文化史上的存在,便具有了“经典”意义。这是产生“以锦喻文”现象的根本原因。因此,在先秦典籍里,人们经常以“锦绣”作为参照物,来谈论各类事物的美。诸如,锦石、锦贝、锦鸡、锦鱼、绣壤等。这充分表明“锦绣”作为“美”的范式,具有超越自身之美的特性,具有“喻指”其他事物美的言说功能。
先秦时期,出现了“以锦喻言”和“以锦喻乐”的审美行为。在先秦礼乐文化活动中,人们不仅重视锦绣色彩之美,也很重视语言美和音乐美,即单穆公所主张的“夫耳内和声,而口出美言”。(57)所以,“以锦喻文”现象的萌生就与人们对于语言美和音乐美的认识有关。先谈“以锦喻言”。当时人们很重视语言的审美问题。但是,语言如何才美呢?人们认为,就是要像“锦绣”的美一样。如《荀子·非相》说:“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礼记·缁衣》说:“王言如丝”,“王言如纶”;《礼记·表记》说:“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这里的“文”即是“美”,就是“美化”的意思。它不仅与前面的“服”有关,而且它的本义就是锦绣色彩交错的花纹图案。这一点《考工记》说得很清楚,“青与赤谓之文”,“五采备谓之绣”;再谈“以锦喻乐”。当时人们也很重视音乐的审美问题。那么,音乐如何才美呢?当时人们也以“锦绣美”作为参照物来对音乐进行审美。《乐记》不仅将锦绣“五色成文而不乱”(《乐象篇》)的审美经验用来论述音乐,还用“文”和“文采”两个锦绣审美的术语来论乐。诸如“声成文,谓之音”(《乐本篇》);“节奏合以成文”(《乐化篇》);又如“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乐言篇》);“文采节奏,声之饰也”(《乐象篇》)。请读者注意:“文”、“文采”的本义都与锦绣美有关。“文”的例子如前所举,现再列举“文采”的例子。诸如,子产说:“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墨子说:“女工作文采”,“饰车以文采”(《墨子·辞过》);庄子说:“五色不乱,孰为文采”(《庄子·马蹄》)。这里所谓的“文采”皆指“锦绣”而言。由此可知,“文”、“文采”等术语最先是用来言说“锦绣”的,后来才用于言说“语言”和“音乐”。所以,“锦绣”成为语言和音乐审美的参照物,成为一种超越其自身美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范式。
到汉代时,又出现了“以锦喻赋”和“以锦喻文”的审美行为。汉代是辞赋盛行的时代。据班固《两都赋序》统计,从汉武帝至汉宣帝的90年间,仅王公大臣献给皇帝的赋就有一千多篇,足见当时辞赋创作之盛。汉赋是继“诗三百”和“楚辞”之后真正的“美文学”作品。这从汉代学者王符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得很明白。他说:“今学问之士,好语虚无之事,争著彫丽之文,以求见累于世”。(58)汉赋将文学的“虚构”和“文采”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按照刘熙载的说法,前者是“凭虚构象”,后者是“尚辞欲丽”。(59)这与现代人的“文学”观念已经十分接近了,因而是“文学自觉”的表现。所以,笔者赞成龚克昌、张少康、詹福瑞和李炳海等人提出的“汉代文学自觉说”。(60)确实如此,汉赋作者追求“文采”之美是前所未有的。刘勰将此特点概括为“铺采摛文”(《文心雕龙·诠赋》),就是说“文采”多得像“铺”过去一般。这种情形与锦绣上面遍布着五彩花纹图案极为相似。所以,汉代学者便“以锦喻赋”,对赋进行审美和批评。最早以“锦绣”为参照物来谈论赋的是司马相如。他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61)受其影响,扬雄谈赋时也说:“雾豰之组丽”,“女工之蠹矣”。(62)班固也说:“(辞赋)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豰,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63)后来王充又提出了“文如锦绣”的“以锦喻文”说。总之,从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其一,汉代学者之所以用“锦绣”作为参照物来谈论赋的审美问题,主要是看到了“锦绣”的丰富色彩、多样图案和悦目功能,与辞赋作品的丰富文采、多样意象和悦目功能十分接近,因而两者构成了“比喻”的审美关系;其二,汉赋是继“诗三百”和“楚辞”之后的“美文学”作品,因而以“锦绣”作为参照物来谈论辞赋的审美问题,就是谈论“文学”的审美问题;其三,从先秦的“以锦喻言”和“以锦喻乐”到汉代的“以锦喻赋”和“以锦喻文”,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其四,“以锦喻文”最初建立在“比喻”的生成机制之上,后来又超越了其“比喻”功能,成为“美”的典型和范式,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文学审美理想。因此,“以锦喻文”就不仅是一种文学批评现象,而且也是一种文学审美批评。
这一点在魏晋以降的文学批评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诸如,古代批评家们用“美”、“两美”、“三美”、“四美”、“七美”、“全美”、“醇美”、“精美”、“粹美”、“盛美”、“健美”、“高美”、“圆美”、“真美”、“和美”、“清美”、“秀美”、“华美”等审美话语批评文学,(64)这表明了审美批评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广泛存在。齐梁时,刘勰就对文学批评提出了这样的审美要求:“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65)明代胡应麟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明确提出了文学“全美”的观点。指出:“綦组锦绣,相鲜以为色;宫商角徵,互合以成声;思欲深厚有余,而不可失之晦;情欲缠绵不迫,而不可失之流。……一篇之中,必数者兼备,乃称全美。”(66)因此,从齐梁到明清,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坚持“色”(视觉美)、“声”(听觉美)和“味”(意蕴美)的“全美”思想。所谓“全美”,就是要求文学作品做到“文采”(即文字美)、“声采”(即声韵美)和“情采”(即意蕴美)三者俱美,让读者从视觉、听觉和心理上获得全面的审美满足。这是典型的审美批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刘勰与胡应麟两人相距一千多年,但是他们在谈论文学批评问题时,都以“锦绣”为参照,来谈论文学的“文采美”和“视觉美”。因此,“以锦喻文”现象从“文采美”(即语言美)的角度内在地切入了文学的审美本质,与现代文论将文学看作“语言艺术”的观念比较接近。所以,它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现象,而且是一种经典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审美批评。
四、“以锦喻文”审美批评范式的现代传承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认为,“以锦喻文”是一种文学批评现象,也是一种文学审美批评,还是一种文学审美批评的范式。所谓“范式”,就是指具有典范性或者经典性的方式。“以锦喻文”的文学批评方式自汉代以来,就被历代众多的批评家所沿用,既有典范性,又有经典性。因此,“以锦喻文”就是一种文学审美批评的范式。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现当代文学批评对于“以锦喻文”审美批评范式有无传承?说实话,要探讨这个问题是有难度的。众所周知,近百年来,在我国文学“现代化”的过程中,现当代文学批评的观念、方法和话语,受西方文论的影响很大。我国古代传统文学批评的观念、方法和话语有许多已退出了历史舞台,或者仅存活在现当代学术研究领域;只有少部分内容与时俱进,或者说经过“现代转换”之后,存活在现当代文学批评之中,而且被边缘化了。所以,要探讨现当代文学批评对于“以锦喻文”审美批评范式的传承问题,多少有一些冒险性。
经过考察,笔者发现:我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对于“以锦喻文”审美批评范式是有所传承的。比如林语堂说:“原来文彩文理之为物,……如锦如织,却有大好文章”。(67)朱光潜说:“诗必有所本,本于自然;亦必有所创,创为艺术。……正犹如织丝缕为锦绣”。“人在说话做诗文时,都是在这部字典里拣字来配合成辞句,好比姑娘们在针线盒里拣各色丝线绣花一样”。(68)艾青说:“想象是思维织成的锦彩”。(69)各家皆是以“锦绣”为审美参照物,来言说和评论文学。在当代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批评中,还大量存在着使用“以锦喻文”审美批评范式的现象。与之相关的资料触目可见,此处不一一举例。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说,“以锦喻文”审美批评范式还存活在现当代文学批评之中。
值得指出的是,现当代文学批评对于“以锦喻文”审美批评范式采用了“隐性传承”的方式。所谓“隐性传承”方式,就是与引经据典的“显性传承”方式刚好相反,它是在集体无意识层面所进行的传承,这是一种隐蔽的和深层的传承。那么,“以锦喻文”审美批评范式是如何传承下来的呢?是什么力量支配着这种“隐性传承”呢?这是十分有趣而复杂的问题。我认为,是“文化记忆”或者说是“集体无意识积淀”。丝织锦绣是我们祖先的伟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的杰出贡献。它的意义和重要性绝不亚于“四大发明”。锦绣与瓷器、汉字、京剧等一起成为中国文化的元素和符号。在最近举行的第29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仍然有“丝织锦绣”这个中国文化元素的存在。在审美文化还不发达的上古社会,花纹繁多、色彩斑斓的锦绣,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视觉审美需求,成为“美物之首”。因此,墨子、庄子、荀子和韩非子等先秦诸子经常借“锦绣”来谈论视觉美问题。而且,它在古代“礼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作为王公贵族的“专用品”,其影响扩展至上层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在宗教、礼仪、政治、外交、民俗和文字等方面都有文化增值。所以,“锦绣”作为上古社会审美文化的优秀代表,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古今文学批评家们在运用“以锦喻文”审美批评范式时,大多无师自通,随心所欲,信手而用。表面看来,彼此间似乎不存在“传承”关系,但只要透过这种表面现象,即可发现有一个强大的“文化磁力场”存在。它潜藏于每个运用者的灵魂深处,支配着每个运用者。这便是“锦绣美”积淀于“集体无意识”后所起的巨大作用。为什么在当代社会“图像”文化极度发达时,在西方文学批评观念、方法和流派盛行中国时,还有人对于“以锦喻文”念念不忘,用它来衡文论艺、品评文学呢?其中的奥秘就在于此。
古代“以锦喻文”审美批评范式的众多术语和范畴,如“文采”、“文章”、“绮靡”、“绮丽”、“华丽”、“纤丽”、“经纬”、“组织”等范畴,如“文”、“章”、“经”、“纬”、“编”、“绪”、“绮”、“丽”、“藻”、“彩”、“黼”、“黻”、“锦”、“绣”等术语,都还程度不同地存活在现当代文学批评的话语之中。如林语堂说:“有不少散文绮丽夸饰,独具一格,价值极高”;(70)又如闻一多说:“律诗之发展,丝变毫移,初非旦夕之功。其始也,有句底组织,有章底组织”。(71)其中的“文”、“章”、“丝”、“绮丽”、“组织”等就是“以锦喻文”审美批评范式的传统话语。尽管经过千百年历史的淘洗,我们今天已经从这些范畴和术语的文字本身看不出其绚丽多姿的色彩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仍然是古代“以锦喻文”审美批评范式对于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存在着一种强调“文采美”和“视觉美”的审美批评。它是通过大量运用“以锦喻文”审美批评范式而呈现的。“以锦喻文”范式在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文学批评史上都有广泛的存在,经过萌芽、形成、发展和传承的历史演化过程,构成了一部色彩斑斓、内容丰富的“以锦喻文”范式史。“以锦喻文”既是一种文学批评现象,又是一种文学审美批评,还是一种文学审美批评的范式。“以锦喻文”范式的传承,主要是通过“文化记忆”和“集体无意识积淀”的“隐性传承”方式进行的。这是一种隐蔽的和深层的传承。“以锦喻文”的文学审美批评,是一种本于中国原初审美观念、触及文学审美本质和具有民族特色的审美批评,也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具有“经典”意义的审美批评。
注释:
①参见古风:《丝织锦绣与文学审美关系初探》,《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古风:《刘勰对于“锦绣”审美模子的具体运用》,《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
②颜师古注:《急就篇》卷2,《四库全书》,经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23册,第22页。
③王充:《论衡》卷1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94页。
④王充:《论衡》卷27,第420页。
⑤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95页。
⑥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第117页。
⑦穆克宏、郭丹编著:《魏晋南北朝文论全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16页。
⑧朱铸禹汇校集注:《世说新语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34、239页。
⑨《南史·颜延之传》,《二十五史》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767页。
⑩陈延杰注:《诗品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20、63页。
(11)古风:《刘勰对于“锦绣”审美模子的具体运用》,《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
(12)穆克宏、郭丹编著:《魏晋南北朝文论全编》,第514页。
(13)《李太白文集》卷26,《四库全书》,集部,第1066册,第411页。
(14)《刘宾客外集》卷2,《四库全书》,集部,第1077册,第530页。
(15)《司空表圣文集》卷10,《四库全书》,集部,第1083册,第544页。
(16)周祖譔编选:《隋唐五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59页。
(17)周祖譔编选:《隋唐五代文论选》,第375页。
(18)周祖譔编选:《隋唐五代文论选》,第241页。
(19)周祖譔编选:《隋唐五代文论选》,第95页。
(20)陈埴:《木钟集》卷2,《四库全书》,子部,第703册,第618页。
(21)吴沆:《环溪诗话》,《四库全书》,集部,第1480册,第42页。
(22)周煇:《清波别志》卷2,《四库全书》,子部,第1039册,第103页。
(23)苏洵:《仲兄字文甫说》,陶秋英编选、虞行校订:《宋金元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112页。
(24)范镇:《东斋纪事》卷3,《四库全书》,子部,第1036册,第592页。
(25)葛立方:《韵语阳秋》卷3,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02页。
(26)葛立方:《韵语阳秋》卷1,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册,第483页。
(27)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林乾主编:《金圣叹评点才子全集》第3卷,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18、26页。
(28)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宋俭等编注:《奇书四评》,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7年,第406页。
(29)毛宗岗:《读〈三国志〉法》,罗贯中著、毛宗岗评:《全图绣像三国演义》上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页。
(30)张竹坡:《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第10回回评,宋俭等编注:《奇书四评》,第371页。
(31)罗贯中著、毛宗岗评:《全图绣像三国演义》上册,第3回回评,第22页。
(32)天都外臣:《水浒传序》,蔡景康编选:《明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211页。关于“天都外臣”是谁,有两种看法:一说是汪道昆,另一说是汪廷讷,本文采用前说。
(33)李开先:《改定元贤传奇序》,蔡景康编选:《明代文论选》,第147页。
(34)李渔:《闲情偶寄》,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年,第13、23页。
(35)李渔:《闲情偶寄》,第42页。
(36)李渔:《闲情偶寄》,第76页。
(37)桓宽:《盐铁论》卷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6页。
(38)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6,《十三经注疏》上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78页。
(39)陆翙:《邺中记》,《四库全书》,史部,第463册,第312页。
(40)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25页上,“文”字条。
(41)许慎:《说文解字序》,《说文解字》卷15,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14页。
(42)刘熙:《释名》卷4,《四库全书》,经部,第221册,第399页。
(43)戴侗:《六书故》卷30,《四库全书》,经部,第226册,第563页。
(44)《后汉书》卷40,《二十五史》第2册,第847页。
(45)《说文解字》卷13,第274、273页。
(46)辛刚国:《六朝文采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86页。据我考察,辛博士的统计有误。因为,他可能是采用《四库全书》电子版系统统计的。电子版统计时,误将“揉”(14次)也统计在内了,其实“采”只有99次。如电子版统计“文”时,误将“大”、“丈”都统计在内了。因此,电子版统计在识别字形上有误差,使用时要特别谨慎。
(47)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16页。
(48)谢榛:《四溟诗话》卷2,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74页。
(49)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7页。
(50)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45页。
(51)《辞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740页。
(52)《史记·礼书》,《二十五史》第1册,第154页。
(53)萧统:《文选序》,穆克宏、郭丹编著:《魏晋南北朝文论全编》,第466页。
(54)参见王大有:《龙风文化源流》,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118页。
(55)王充:《论衡》卷28,第432页。
(56)王充:《论衡》卷13,第214页。
(57)薛安勤、王连生注译:《国语译注·周语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30页。
(58)张少康、卢永璘编选:《先秦两汉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607页。
(59)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95、99页。
(60)参见赵敏俐:《“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61)张少康、卢永璘编选:《先秦两汉文论选》,第364页。
(62)张少康、卢永璘编选:《先秦两汉文论选》,第459页。
(63)《汉书》卷64下,《二十五史》第1册,第626页。
(64)彭会资主编:《中国文论大辞典》,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474—488页。
(65)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第388页。
(66)胡应麟:《诗薮》内编卷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82页。
(67)远明编:《林语堂著译人生小品集》,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95页。
(68)朱光潜:《诗论》,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45、97页。
(69)艾青:《诗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70)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02页。
(71)闻一多:《神话与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3页。
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汉朝论文; 读书论文; 文心雕龙论文; 锦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