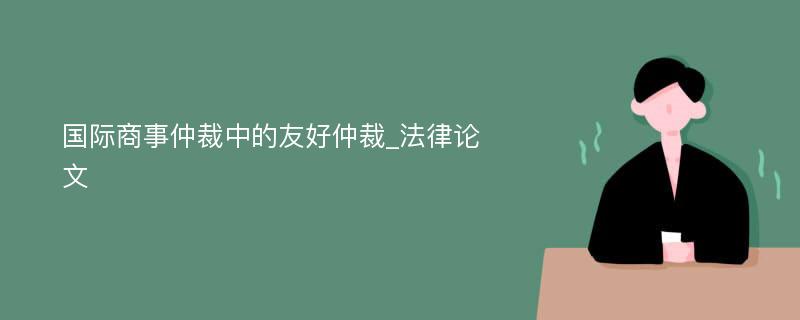
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友好仲裁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事论文,友好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 99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374(1999)06-0010-05
国际民商事纠纷的解决主要有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等几种方式。各种方式可谓各有利弊。其中,仲裁作为解决民商事纠纷的一种有效方式,因其自身具有灵活、快捷、费用低廉和保密等特点,在世界各国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我国的仲裁制度在经历了近20年的蓬勃发展后已逐步迈入了正轨,学界有关仲裁各种问题的论著和讨论亦相当丰富和热烈,大大推动了仲裁制度的健康发展,特别是1994年《仲裁法》的颁布,使我国的仲裁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毋庸置疑,与具有悠久的仲裁制度历史的其他一些国家的仲裁立法、实践及研究相比,我国的仲裁立法、实践及研究在一些方面仍存在明显的滞后,本文拟对我国仲裁研究中尚少有涉及的友好仲裁问题作些探讨。
一、友好仲裁的含义
在我国,仲裁员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处理案件是一项基本原则。那么仲裁员可否不依严格的法律规则作出裁决?或者如果经当事人授权,仲裁员是否可作为友好公断人(amiable compositeurs,也有学者译为友好仲裁人或友好调解人)不依严格的法律规则作出裁决?这种裁决是否具有执行力?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无疑对仲裁实践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但在回答这些问题前,首先要弄清友好仲裁的含义。
在我国的许多论著中,从仲裁分类的角度,以仲裁员是否必须按照严格的法律规则作出裁决为标准,仲裁又被分为友好仲裁(amiable composition)和依法仲裁。学者论著中的友好仲裁是指仲裁员经双方当事人授权,在认为适用严格的法律规则会导致不公平结果的情况下,不依严格的法律规则,而是依据它所认为的公平的标准作出对双方当事人有约束力的裁决。本文行文中以及我国学者对友好仲裁概念的描述中并没有区分仲裁员作为友好公断人处理案件(decide asamiablecompositeur)和仲裁员依公平与善良(decide ex bono et aequo)处理案件。事实上,虽然amiable compositeur与ex bono et aequo 经常被认为是同义词,例如,在法国法中友好公断人即被解释为依公平原则处理案件,但也有外国法(如西班牙法)、学者及判例认为,两者是有区别的,前者的含义广于后者。戈德曼(Goldman)曾指出, 严格地说,decide ex bono et aequo与act as amiable compositeur 是不同的,因为当解决当事人的争议时,友好公断人可以决定当事人可能同意的一切(may decide all what the parties may agree)。 只有作为友好公断人的评判员才可以在法律范畴外解决争议(may settledispute outside the ambit of the law)。意大利的一个判决认为,arbitratiors amiable compositeurs 表示的含义较仲裁员依公平处理案件的含义广泛,前者授予了仲裁员依公平裁决时所没有的一种了结(问题)的权力(
authorityto settle)。在amiable compositeur情形下,仲裁员是了结(settle)问题,而在ex bono et aequo情形下,仲裁员是裁决(decide)问题。另有学者认为,amiable compositeur 为共同授权了结(joint mandate to settle),ex bono et aequo 为调整法律的裁量权(discretional authority to mitigate strict
law)。还有学者认为,所谓的友好仲裁并不是一种真正的程序,而仅仅是一种契约性的情形(a contractual situation)。 本文在后面所援引的一个仲裁案件中,奥地利最高法院最后也认为,国际商会仲裁院某仲裁庭在奥地利作出的,没有依任何国家的法律,而是依公平合理原则(尽管没有当事人的授权)作出的裁决没有超越仲裁庭的权限。
由此可见,对于友好仲裁这种类型的仲裁的精确含义或者说仲裁庭权力的确切范围,目前并无一致的观点。所以,当各方当事人在预期会涉及这方面的问题时,他们通常可能会希望在仲裁协议中通过对仲裁庭的特别授权而澄清仲裁庭的权力范围这一问题,以避免卷入不必要的耗费时间和精力的诉讼中。这一点可以通过1979年国际商会仲裁院的一个著名和典型的案例加以说明。
在该案中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未经当事人授权,仲裁庭非依任何国家法律作出裁决,是否超越了仲裁庭的权限。而奥地利和法国各级法院对该问题的不同定性,一波三折的判决,令当事人耗去了几年的时光,使当事人完全没有享受到仲裁制度快捷、费用低廉的优点。如果当事人的仲裁协议明确授权仲裁庭可作为友好公断人或可以依公平合理原则裁决,至少法国公司可能没有机会以仲裁庭没有得到授权,超越权限为由提出上诉(注:该案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适用现代商人法或商人习惯法是否需经当事人授权?目前,一般认为不需要特别授权。一些国家的仲裁立法及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或示范法对此已有明确规定,例如1985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28条第4 款规定,在所有情况下,仲裁庭应根据合同的条款作出裁决并应考虑适用于该交易的贸易惯例。这说明仲裁庭对是否适用贸易惯例有自由裁量权。1998年德国新仲裁法即民诉法第1051条第4款、1986年荷兰民诉法第1054条第4款、法国1981年民诉法第1496条第2款均有类似的规定。)。
因此,在长期合资或合作的的国际合同中常会见到授权仲裁员作友好公断人的条款,这种条款又称为公平条款(equity clause)。但是,对于这种授权条款的效力,不同国家的立法与实践目前仍存在着差异,并没有为所有国家的法律制度所承认或熟悉。一般而言,大陆法国家多在立法或实践中对此持肯定态度,而一些英美法国家对此持否定态度,或者态度不明朗(注:韩健著:《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二、有关国家的立法与实践
(一)英美法国家的有关立法和实践
在1996年前,英国的立法对此态度不明,但司法实践中基本上经历了从反对到放松的过程,直至为1996年的《仲裁法》所肯定。
早期反对的主要理由是,其法律制度使法院没有可能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按公平与善良(ex bono et aequo)作出判决。英国法官只能按照法律(被推定为在任何时候都能提供正确的解决方法)作出判决。而这条规则同样适用于国内仲裁,仲裁员在应适用的实体法是英国法的情况下,必须严格适用法律。英国法院在五六十年代的有关的案件中阐述了下列观点:仲裁员和法官不能有两套不同的法律;仲裁员的职责是根据当事人的法律权利(according to the legal rights of the parties)处理提交给他的争议,而不是依据他所认为的公正和公平的标准来处理争议;不能允许仲裁员适用不同的标准,例如仲裁员或公断人个人对于抽象的公正或公平原则的理解。到了七八十年代的有关判词表明了英国法院对友好仲裁的否定态度有所放松。在1978年的一个判例中,法院认为,当事人授权仲裁员以友好公断人的名义处理他们之间争议的条款(amiable compositions clause or equity clause)是完全合理的,并没有剥夺法院的权限,但其有效性仅限于在技术性和严格解释方面去漠视法律(disregard of law)。但在1978年前英国法院曾多次撤销基于“公平”(equity)作出的裁决(注:韩健著:《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在1988年的一个案件中,大法官塞尔伯恩(Selborne)指出,毫无疑问,在面对使仲裁员有权作为友好公断人去漠视所有的法律问题上,法官会相当的犹豫不决。友好公断人这一词语可以被合理地赋予至少是如下的效力:他们不严格遵守法律规则,并因而作出了裁决,这最多只不过是导致不规则(irregularity)。1992年的一个判例又重申了仲裁员应严格依照法律的观点。直至1996年《仲裁法》第46条(1)(b)明确规定了如果当事人同意,仲裁庭应按照当事人同意的或者仲裁庭决定的其他考虑来处理争议。从文字上看,该法全面承认了当事人友好考虑的仲裁协议的效力,但实践中仲裁员是否可以完全漠视英国法律的规定,而求得自己认为衡平或友好的结果尚待以后案例的发展来提供佐证。
而在同属于普通法系美国的情况却大不相同。早在1875年的判例中,美国的法院就明确承认,仲裁员可以漠视严格的法律规则或证据规则,并按照他们自己的公平观念来处理争议,除非当事人提交时对此有限制。美国法院这种相当开放的观点是基于契约自由原则。按照美国法院的观点,仲裁协议是解决争议的一个合同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当事人创设了自己的法庭,选择了自己的法官,除了有限的审查权或上诉权外放弃了一切,省却了证据规则,允许他们自己选择的法官按照自己对公正和公平的认识来处理要解决的问题。1997年《美国仲裁协会国际仲裁规则》第28条第3款也规定,除非当事人明确授权, 仲裁庭不可以作为友好公断人或根据公平原则裁决。
(二)大陆法国家的有关立法与实践
意大利民诉法第114条明确规定, 当争议涉及的为当事人有权放弃或有权和解的权利,并且当事人共同要求法庭时,法官可以在初审和上诉审中按照公平(equita)原则处理争议。根据民诉法第882条, 经当事人授权仲裁员也有权按照公平原则处理争议。
法国1981年新民诉法第1474条规定,仲裁员依法仲裁,除非仲裁协议授权他们作为友好公断人。在国际商事仲裁中,根据第1497条的规定,如仲裁协议授权仲裁员, 仲裁员可作为友好公断人裁决案件。 另据第1482条第2款的规定,当仲裁员为友好公断人时, 当事人不得向上诉法院对仲裁裁决提出异议,除非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明确保留了此项权利。1987年,巴黎法院在一个案件中认为,如果当事人已经明确表示如果存在于当事人之间的实际情况需要,则处理争议不仅应适用成文规定,而且为了取得公平结果也应调整法律,也应授予仲裁庭友好仲裁的权力。在1988年的一个判决中,法院认为,原则上,友好公断人可以不严格按照法律作出裁决。
德国1923年的一个判例指出,经当事人同意,允许仲裁员在某种程度上不适用法律是正确的。1998年德国新仲裁法(德国民诉法典第10册第1051条)明确规定,只要当事人明确授权,仲裁员就应依公平与善良或作为友好公断人作出裁决。当事人直至仲裁庭作出裁决前都可以如此授权。
瑞士法也允许依公平与善良作出裁决,而且法院享有广泛的权力。瑞士民法典规定,只要成文法规定提及了法院的自由裁量权或考虑有关情况的权力,法院就不仅有义务适用成文法的规定,而且还应考虑公平的问题。瑞士国际私法第187条也明确规定经当事人授权, 仲裁员可以按照公平原则作出裁决。
1986年荷兰民诉法典第4册第1054条规定,如果双方当事人授权, 仲裁庭可作为友好公断人作出裁决。
比利时法律规定,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仲裁员必须依法裁决。
西班牙法律规定,仲裁员有权依公平原则裁决,除非当事人明确表示必须依法仲裁。
1958年《纽约公约》对此无明确规定,但1961年《关于国际商事仲裁的欧洲公约》第7条第2款规定,如果双方当事人明确授权或决定,而且根据适用于仲裁程序的法律允许这样做时,仲裁庭可作为友好仲裁人进行仲裁。国际上拟定的适用于国际商事的仲裁规则多数也承认,只要双方当事人同意,仲裁庭可进行友好仲裁。例如具有广泛影响的1985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28条第3 款就明确规定,如果当事人明确授权仲裁庭,仲裁庭可作为友好仲裁人或依公平与善良原则作出裁决。
由此可见,具有罗马法传统甚至是德国法传统的国家是承认友好仲裁的,普通法国家中的美国,以及英国新的仲裁法也都是承认友好仲裁的。上述这些国家基本上也都是仲裁制度相当发达的国家。
三、友好仲裁的必要性及对仲裁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
那么,赋予仲裁员或仲裁庭作为友好公断人进行仲裁的权力,或者说承认当事人要求仲裁员作为友好公断人协议的效力,其必要性何在?这是否是对法律公正的违反?应该说仲裁员可以不依严格的法律作出裁决是公平的需要。公平就是公正,但并不是法律上的公正,而是对法律公正的纠正。因为全部法律是普遍的,是针对大多数情况的,它并不能涵盖所有的情况,适应于一切情况。但是,这并不能说是法律或立法者的过错,而在于事物本身的性质。因此,纠正法律的过于简单或补充规定的漏缺就是正确的。所以公平就是公正,并优于由于普遍而带有缺点的公正。纠正法律普遍性所带来的缺点是公平的本质(注:一般认为公平的概念是罗马法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概念,最早由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参阅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中译本,第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页。)。 而考虑到这种授权条款对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影响,允许仲裁员以友好公断人身份处理案件的国家,在立法上均明确规定了必须经双方当事人授权,而比利时则进一步从时间上对当事人的授权作出限制,即只能在争议发生后才可以授权仲裁员进行友好仲裁,以使有关当事人能预知自己授权的后果,防止当事人在没有认清争议的性质和重要性之前就盲目地协议友好仲裁。而在国际仲裁中则必须依法仲裁,不能进行友好仲裁。因此承认友好仲裁也可以说是契约自由原则在仲裁中的体现。而仲裁当事人之所以愿意授权仲裁员这种权力,主要是基于友好和商业关系的考虑,这也是这种授权条款常见于长期的国际合资和合作合同的原因。
虽然经当事人授权,仲裁员可以在公平的理念下享有自由裁量权,但这种权力受到一定的限制。首先, 强制性规定(mandatoryprovisions)不属于仲裁员自由裁量的范围,也就是说,仲裁员不能置所有法律规定于不顾,即使仲裁员认为它与公平冲突。其次,一般认为,自由裁量权仅限于实体法(substantive law), 而程序法是完全排除在外的。例如德国仲裁法和荷兰仲裁法等均是在适用于争议实质的规则的条款中(rules applicable to the substance of the dispute),规定允许当事人为此种授权的。另有学者认为,在法院诉讼中情况的确是如此。至于仲裁程序,如果当事人的协议应被如此解释时,该限制是正确的。而在其他一些情形下,那些仅仅旨在保护一方当事人,并没有涉及公共利益的程序性规定如果看起来太苛刻,不能被排除,可以不予适用;这在当事人没有要求仲裁员适用程序法时是可以的。一个中间的情形是当事人指示仲裁员适用某一特定的程序法,除非其违反公平。例如,即使超过了法定的程序性的提交申诉或答辩文件的最后期限一天,仍允许提交。
仲裁员友好仲裁的其他实例有:
1.如果根据应适用的法律,有关缺陷的通知应在8天内发出。 有关当事人虽然在8天内用传真发出了通知,但传真效果不好,然后在8天期限之后又发了一份清楚的传真,如果仲裁员被授予了依公平与善良裁决的权力,并且如果他认为尽管第一份传真不清楚但确实是及时的,则仲裁员可以决定第二份清楚的传真是及时。
2.如果仲裁时效为1年,当事人在时效过后第1天才提出申诉,如果仲裁员被授权依公平与善良裁决,仲裁员可以认为申诉是可接受的。
3.一根据合同必须交货的卖主,遇到买主拒绝受领货物。为了使货物的风险转移给买主,应适用的法律要求买主必须履行某些正式的手续,但卖主履行的手续不全。如果法官或仲裁员被授权依公平与善良处理案件,可以使卖主免于承受未完全履行手续的后果。
四、立法建议
我国《仲裁法》第7条规定,仲裁应当根据事实,符合法律规定, 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虽然从字面上看,该规定使用了“公平合理”,但此处的公平合理似乎尚不能理解为允许进行友好仲裁。1998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53条规定,仲裁庭应当根据事实,依照法律和合同规定,参照国际惯例,并遵循公平合理原则,独立公正地作出裁决。从这段文字来看,似乎也不能得出可以不依严格的法律规则,而依公平与善良原则裁决的结论。在实践中,一般认为,此处的“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通常是指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或无明文规定时,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解决纠纷,而不是指仲裁员在有法律规定但适用严格的法律规则会导致严重不公平结果的情况下,不适用法律规定而根据其所认为的公平的标准处理纠纷。这种笼统地规定仲裁实体问题法律适用的做法可以说是中国的特色,而其他国家的立法或有关的国际公约或示范法一般均对仲裁实体问题的适用作出了相当具体明确的规定,一般是首先规定允许当事人意思自治,选择适用于其争议的准据法,其次如果当事人没有指定应适用的法律,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适用仲裁庭认为合适的冲突规则所确定的国家的法律,如1985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28条第2款的规定。 二是仲裁庭直接适用它认为是适当的法律规则(rules of law)或与争议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规则,如法国、荷兰和德国等的有关规定。并且,紧接在这种规定之后,就是有关友好仲裁问题的具体明确的规定,而后再是规定在所有情况下(包括友好仲裁)仲裁庭应考虑有关的贸易惯例。而我国的《仲裁法》并没有专门就法律适用问题作出明确详细的规定,只是在总则的有关规定中,将“符合法律规定”与“公平合理”简单地排列在一起,而根本只字未提当事人授权的问题,因而可以说与国际上通常允许友好仲裁的规定尚相差甚远。而如果说1998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的规定较《仲裁法》的规定更为详尽,增加了依照合同规定和参照国际惯例外,但其规定方式却与《仲裁法》的规定方式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是将几个更多方面的内容简单地合并在一起。这种规定所产生的一个后果是,仲裁庭在决定法律适用的时候,无具体的章法可循(注:实践中,实际上在我国仲裁庭一般是在当事人没有法律选择时,直接适用与争议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这种高度概括的原则性的规定的最大的缺点是缺乏可操作性(当然其优点是可做灵活的解释),特别是在遇到双方当事人授权仲裁庭作为友好公断人进行裁决时,仲裁地在我国的仲裁庭不能明确地判定自己是否可以不依严格的法律规则裁决。如果仲裁庭根据我国上述规定,得出自己可以以友好公断人的身份裁决,并因此作出裁决。而败诉一方不自动履行裁决,胜诉方在我国有关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法院又该依据什么判断仲裁庭是否有此权限?我国法院是否会对非依严格的法律规则作出的裁决的效力予以否定?我国法院在实践中还可能会遇到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机构非依严格法律规则作出的裁决的问题。
笔者认为,首先我国《仲裁法》应借鉴国际通行的立法例,在相关章节专门规定有关争议实质的法律适用规则(即使由于友好仲裁本身的复杂性,对其地位暂不明确)。其次,在该规定中,应考虑增加有关友好仲裁的内容。因为我国的《仲裁法》既然如此强调“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而实践中友好仲裁又具有纠正不公平的作用,为何不干脆借鉴其他国家通行的立法例,对友好仲裁的问题作出明确的肯定?具体可拟定为:如果双方当事人明确授权,仲裁庭可以作为友好公断人或依公平合理原则解决纠纷。当然,如果不作出明确的规定,或许可通过司法判例来得到清楚的解释,但我国的仲裁实践中似乎尚无友好仲裁先例的报道,这或许是由于友好仲裁对于我们而言仍相当陌生,不为我国所熟悉,其本身的内涵也尚多歧义,仍有许多方面尚需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但毫无疑问,随着国际商事交往的日益频繁与密切,商事仲裁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实践中一定会遇到友好仲裁的问题。本文对友好仲裁问题进行研究的目的旨在抛砖引玉,以期引起立法者、仲裁实务者和研究者对此问题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