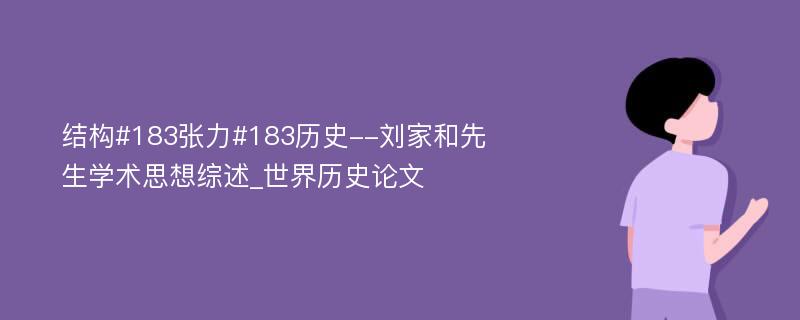
结构#183;张力#183;历史——刘家和先生学术思想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思想论文,结构论文,历史论文,刘家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409(2007)01—0032
一、引言
刘家和,1928年12月生,江苏六合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1952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同年分配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1955—1957年间,曾到东北师范大学从苏联专家进修世界古代史。1979年以前,主要从事世界古代史教学、研究工作;1980年至今,转以中国古代史为主兼治世界史,同时从事中外古史比较研究工作。曾先后主编两本《世界上古史》(教育部指定高校文科教材)和一本《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教育部推荐研究生用参考教材)。另著有《古代中国与世界》(1995)、《史学、经学与思想》(2005)及论文数十篇。曾参与的集体著作、译作尚有多种。
刘家和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历史学家。他在古代希腊史、古代印度史和中国先秦秦汉史、中外古代历史文化比较以及史学理论等领域,皆有精深的研究。他的研究皆关乎古代历史文化的重大问题。例如,关于斯巴达的“黑劳士”制度、印度早期佛教的种姓制度观、《书·梓材》中的“人历”、“人宥”等问题的研究,是探讨古代世界的社会阶层问题的;关于《诗·大雅·公刘》所反映的史事、楚邦的发生和发展、三朝制、宗法制等的考证,是讨论古代国家产生的途径和特点的;至于他集中讨论的中国古代文明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及其关系问题、中国古代王权神化、“轴心期”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中国古典史学形成的过程、古代世界的人类精神觉醒等,本身就是重大的学术课题。上述这些是20世纪50至90年代初的成果。最近十几年来发表的论文,大多集中在中国古代的史学、经学等领域,是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中,从精神层面进一步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比较研究的力作,特别是关于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地位、中国的通史传统与西方普世史传统的比较、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和发展、先秦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萌生、战国时期的性恶说、《左传》中的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春秋公羊学所表现的史学的悖论和历史的悖论等项研究,集中反映了他的研究兴趣和理论深度,也是在世界背景上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高水平成果。总之,所有这些工作,是他立志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中去研究,为写出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历史,写出有中国史在内、并给中国史以应有地位的世界史的重要步骤。刘先生发表的论文皆以选题精准、考证精当、分析精细、思考精深而著称。他的许多学术观点,特别是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及其辩证关系的观点,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以广度和深度而论,刘先生的学术成果是非常丰厚的。取得这样丰厚的学术成果,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勤奋和毅力,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在这勤奋和毅力的背后,更有着对真善美的真诚信仰和不懈追求,有着对研究方法的理性自觉,还有着对这两者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反省。这种反省理所当然应该纳入“学术思想”的范畴。在提升学术质量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认真学习刘先生的学术思想,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作者有幸跟随刘先生学习多年,但深知,要想很好地理解刘先生学术思想的精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篇文章反映了作者现在的认识水平和程度,理解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尚祈批评指正。
二、关于历史的学习与研究的关系
什么是研究?历史研究应该怎样进行?对于打算认真研究学术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世纪之交,刘先生在为《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撰写引论时,积半个多世纪学术研究的经验和思考,对这个问题作了精辟的解说[1](P1~24)。
(一)关于学习与研究的关系
刘先生把学习与研究的关系看作学术活动的内在结构之一种,通过两者之间的张力关系来理解研究的意义。他考察了中国传统典籍,对汉语“学习”和“研究”这两个词的含义进行了分析。指出,广义地说,“学”字的意思里包括研究。狭义地说,“学”字有知道(被教会)、记住和仿效三层含义,这三层意思都反映着人的受教过程。“习”字则有反复地做的意思。概括起来,由“学”和“习”两字组成的“学习”一词,表示的就是由“学”而开始获得知识,在反复的“习”中达到切实的把握。
“研”字本指以石将物磨为粉末,引申义就成了对事物进行精细的分解。“究”字的意思是穷、谋,即穷极究竟、远虑深思的意思。“研”、“究”二字之间是有某种内在联系的,“研”是彻底的分析、分解,“究”是彻底的探求。彻底的分析(研)是彻底的探求(究)的准备,彻底的探求(究)是彻底的分析(研)的完成。由彻底的分析而彻底的探求,这就是研究的过程。
由此可见,学习重在继承,研究重在创新。
那么,重在继承的学习,怎样才能过渡到重在创新的研究?或者说,从学习过渡到研究何以可能?这是刘先生发现并试图解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刘先生认为,实现这个过渡的关键就在“温故而知新”。所谓温故,就是“学而时习之”。它可以产生双重的效果:一方面,把所学知识牢固地记了下来,另一方面,在不断地复习中逐渐了解到所学知识是通过何种途径得来的。或者说,温习的结果,既得到了具体的知识,又得到了产生此知识的方法。如果说,人们通过前者所把握的只是具体的“事”,那么,通过后者所把握的就包括了一般的“理”了。当人们试图用所得知的方法或“理”去进一步探讨新事物时,“研究”就从这里开始了,“新知”的门也就从这里打开了。当然,要做到以上这一点,那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思”。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罔的意思是蒙蔽,也就是无知。学的时候没有用心思,也就无从研究,当然也就没有任何创新。在中国的学术传统里,学习与研究或温故与知新,既有明确的区别,也有重要的联系,这种联系的纽带就是“思”。学习或继承的阶段要会思,研究或创新的阶段更要会思。
刘先生进而指出,由学习过渡到研究,从思维层次来说是从重肯定到重否定的发展。中国有“学问”二字,“学”为什么必须继之以“问”?因为如果无问,学就不能发展。朱熹曾说过,会读书的是能疑,怎样疑呢?用他的话说就是“读书,须是看着他那缝罅处,方寻得道理透彻。若不见得缝罅,无由入得。看见缝罅时,脉络自开。”[2](162) 学了以后要会提问题(即疑),问题从何而来?要从事物的内在矛盾——“缝罅”中去发现。客观的事物或书中所说的事物,为什么会有“缝罅”可被发现?黑格尔说得清楚:“凡有限之物都是自相矛盾的,并且由于自相矛盾而自己扬弃自己。”[3](P177) 所谓“缝罅”,就是客观的普遍存在的矛盾。中国古代学术传统所重视的“疑”、“问”不是单纯抽象的否定,而是有分析的具体的否定,或者说是兼容否定与肯定的扬弃。
由此可见,学习是为研究打基础,作准备,而研究是学习的目标与发展。研究的成果又成了新一轮学习的对象,从而引起新一轮的研究,如此运行不已,就构成了人类文化的不断进展过程。
(二)关于历史的学习与研究之关系
历史学习和研究的关系就是历史学学科领域内的学习与研究的关系,它符合学习与研究关系的一般规律,当然也有自己的表现方式和问题。刘先生从以下两方面来揭示两者的关系。其一,记忆与理解的关系。刘先生认为,历史学的学习不能不从记忆开始,但是要作研究,又不能只靠记忆,而是要由记忆而理解,由理解而提出问题,只有在提出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历史学的研究才得以实现。
关于记忆,有一种偏颇的看法,以为历史课本从小学到大学的变化,就在于知识含量的不同,学生水平的区分也就在于记忆的多少,形象地说,就是“一杯水”和“一桶水”的区分,知识记忆量的水平变成衡量学生业务水平的唯一标准。这样理解问题,其实是把历史学习的方法一例变成了死记硬背。这种观点有见于知识量的区别,无见于知识质的区别。一桶水虽比一杯水多,但终有尽时,历史知识的一时之多,也总有其老化之时。真正好的历史记忆要靠真正好的历史理解来支撑。记忆能力与理解能力是成正比的。
在刘先生看来,理解对历史学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历史学的资料都是前人记忆的成果,有些是无意中记忆下来的,但这样的记忆一般都不能保持很久,因为它未必有意义;而大多数都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记忆下来的。人们有意识的记忆又主要发生在以下两种情况下:一种是,人们深切地理解到该事件或过程对于自己的重要意义,从价值系统认识到记忆此事件或过程的必要性,于是产生了极大的注意力;另一种是,人们对于该事件或过程的内在结构和外部关系都有深切的理解,从知识系统具备了记忆此事件或过程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今天所能接触到的前代的史料,都是前人根据自己的理解而记忆下来的、他们认为最需要记忆也最清晰的事件或过程。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或过程太多而且太纷繁,人们不可能也不必要把它们全记忆下来,于是前人就根据自己的理解去作选择取舍;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或过程都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去加以考察并评述,前人又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解释,因此,我们就不得不透过前人的理解去认识前代的客观历史过程。
另一方面,我们今天学习前代历史,一旦从记忆的阶段进到理解的阶段,我们作为认识主体也就从被动的接受转到了主动分析状态,我们自然也必然会按我们的理解去认识并分析前代的历史。可是,在我们的理解与前人的理解之间,通常会有相同或相通的方面,不如此就会发生我们与前代历史文化之间的断裂;同样,通常也会有不同或疏离的方面,不如此就不能有历史的发展。因为在前人与我们之间必然存在着理解上的异同,所以历史学研究中总不断会有问题的出现。研究总是从问题开始的,而研究成果所达到的水平是与研究者所能提出并解决的问题的深度密切相关的。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学问的大小是和他所掌握或记忆的历史资料的量成正比的,一位历史学家学问的深浅是和他所提出并解决的问题的深度成正比的。前者所涉及的是量的问题,后者所涉及的是质的问题。
其二,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刘先生认为,治史学,从学习到研究,不能没有传承,或传统(tradition),也不能没有创新,或革新(innovation)。在学习历史学的时候,比较地着重于传承,在研究历史学的时候,则更着重于创新。
在学术的传承与创新之间,具有一种相反相成或对立统一的关系。历史学的情况也是如此。真正的历史学上的创新,正如历史过程中的创新一样,是植根于传承之中的。在历史学的传承中,成果与问题同时积累下来,而创新则是这两种同时并存的积累的必然继续。因为,没有问题的积累,就没有创新的需求;而没有成果的积累,就没有创新的实际能力。真正的历史学上的创新必须有对于传承中问题的破,如不深于传承,就不知问题究竟何在,即使知道问题的大概所在,也不能真知其深层的症结所在,从而也就不能真知往何处破,更无从破到应有的深度。当然,创新不止于破,更重要的还是在于立。传承所积累的条件使我们有可能达到新的高度,彻底抛弃了传承的成果,人们也就无从创新。而传承从本质上说是人类文化生命的延续,而文化生命本身像人本身一样只能在不断的新陈代谢中维持下去。没有新陈代谢,没有推陈出新即创新,传承就只能是不断弱化或萎缩下去的苟延残喘,其结果就是最终消亡。真正的传承过程,就是活泼泼的推陈出新的过程。[4](P10~15)
三、关于古史研究方法的三种关系[5](P107~124)
刘先生指出,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方法同样有着若干内在构成及其张力关系。
(一)关于文字之学与哲学思考的张力关系
刘先生以为,必须将文字之学同哲学思考结合起来,使之形成张力,然后加以把握和利用。不仅如此,还必须有形成这种张力的自觉,没有这种自觉,就会总是徘徊在某种理解古书和分析历史的较低的水平上;有了这种自觉,就可以用睁开了的文字训诂之学的眼睛去促进哲学的学习自觉性,又用睁开了的哲学的眼睛去促进文字训诂之学的学习。这样,张力就不仅是一种使我们感到两头吃力的离心力,而是可以成为一种使我们收其两头相互促进之功的向心力。“宏观”和“微观”这两个相反的东西,互相构成张力,就像拔河一样,既是要离开的又是相吸引的,内部是相通的,实际上是相反相成的。[6](P15~18)
刘先生的学术研究,一方面可以说是在宏观的视野下,考察微观问题,另一方面又可以说是深入微观问题以求达到宏观的理解。这就需要从哲学和文字学两个方向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到历史现象的内部,在张力中理解和把握历史现象的本质。本文以他2002 年发表的《论通史》一文为例略加说明。 该文首先对西文general history、universal history、global history、ecumenical history、total history等和中文“通史”一词逐个进行了词源考证,发现, 那些西方词汇都是用来表示带有普世性或区域群体性的历史的,并不强调时间上的古今贯通。而在中国古代,“通”与“达”互训,有“达到”的意思(《说文解字》);“通”的反义词是“穷”,《易·系辞上》有“往来不穷谓之通”[7](P82) 句。“通”字本指空间的由此及彼,而空间上的往来不穷又是在时间里进行的,因而也就变成了时间上的连续不断。“通”字用于时间中运行的历史,主要是指时间上的连续而言。接着,刘先生又从哲学上进行阐释。他借鉴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指出作为西方史学传统之渊源的希腊罗马史学是实质主义的,柏拉图认为,知识(episteme)是对永恒不变的实质的真知实见,而对应于变化不居的现象的感性只能有意见(doxa)而已。因此,希腊人的历史有待于历史事件目击者的作证,结果只有当代的、当地的历史,这与柏拉图信奉的永恒不变的实质是完全不同的。柯林武德指出,希腊人看到了世界万事在变,于是就追求其背后的不变的实质,经过抽象获得的是“实质”,这“实质”本身是抽象的“一”,其内部没有对立方面,这种形而上学的“一”,当然是反历史的。古代中国思想家并非不追求现象背后的本质,不过他们寻求的不是抽象的、无差别的“一”或永恒不变的实质,而恰恰相反,是变中之常。《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7](P78) 刘先生根据《周易折中》所言“一阴一阳,兼对立与迭运二义。对立者,天地日月之类是也,即前章所谓刚柔也;迭运者,寒来暑往之类也,即前章所谓变化也”[8](381),指出,中国人的解释认为,万物并无抽象不变的实质,也非抽象的无差别的“一”,而是“一阴一阳”组成的“道”或本质,其中包含着对立,与希腊的“实质”相反。唯其一阴一阳,这样的道或本质就不能不变,也就不能不更迭。按中国人的理解,道兼体用,自其体而观之,道是对立的统一;自其用而观之,道又是迭运和不断运动的途径。“继之者善”,迭运不穷自然为善。“成之者性”,道(大一)运成物(小一或具体的一),即成此物之性,个性犹有道之一体。因此,中国古人依据通达的意思而著通史,而希腊人则凭借实质主义而著普世史或当代史。至此,文字考证和哲学思考这两端便贯通起来,形成张力,而问题也就在张力中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当然,这种理解在中国和西方史学传统上有着确实的历史证明,文章也已给予充分的交代[9]。 这是刘先生对中西历史文化最根本的特质所做的一次成功的比较研究,不仅对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就是在哲学和文化研究上也同样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在这之前,刘先生在《对于中国古典史学形成过程的思考》一文中对司马迁天观念的解释,在《儒家仁礼学说新探》中对“克己复礼”一句的解释,以及在其他一些文章中的研究,就已经体现了这种治学精神。[10]
(二)关于历史的内在理解与客观分析的张力关系
刘先生指出,所谓的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第一层意思是说,在阅读历史著作时,要透过著作理解作者的思想和精神;第二层意思是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理解历史的时代精神。如果缺乏这两种理解,那么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就只能是支离破碎的和肤浅的。现代人能够对于已成过去的历史有内在的理解吗?是能够的。因为历史是现实生活的渊源,和我们的文化生命有着内在的联系,本国的历史文化尤其如此,所以我们必须也能够把它作为一种活体来理解或体验。那么,又为什么必须有对于历史的客观的分析?因为从另一方面来说,历史又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外在于我们的客观存在。作为历史学的研究者,当然应该也必须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加以认真的分析或解剖。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与客观分析二者之间实际也存在一种张力,它们的方法和任务各不相同,但是又能互相促进。因此既要做好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又要做好对于历史的客观分析,并且使二者互相促进,形成张力。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不是凭某种直觉而发生的领悟和体验。要达到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首先必须弄清楚有关材料的文字训诂,确切把握文献的含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逻辑的分析,弄清文献的内在理路。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客观分析,没有这样的分析,所谓内在的理解就会失去可靠的基础,因此需要的是二者的相辅相成与相得益彰[6]。
刘先生常说,研究历史就仿佛在与历史人物——往往是第一流人物——进行对话。这些人物或是历史活动的主角,或是历史活动的记录者和研究者(在历史记录和研究的历史活动中也是主角)。这种对话就是内在理解。为了使对话顺利地开展,首先必须读懂材料。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进行客观的分析。刘先生的许多文章都可以作如是理解。以下试以他的一篇短文《“岂非天哉”的三重解读》为例予以说明[11](P100~101)。
刘邦出身布衣,毫无凭借,但在秦末大起义中,却能三年亡秦,五年灭楚,一统天下。司马迁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中评论说:“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12](P760) 刘先生早年读此,以为“岂非天哉,岂非天哉”就是司马迁歌颂刘邦的话,刘邦自然就是大圣了。稍后,读《高祖本纪》、《项羽本纪》等篇,联想到这句话,便产生了疑问:司马迁笔下的刘邦起兵前原是那样一个贪婪、无赖之辈;起兵后却因有胆识而被推为沛公。楚汉相争时期,目睹父亲妻小落入项羽之手而无动于衷。打败项羽后当上了皇帝,得天下为私产,自然踌躇满志、得意忘形。所有这些,怎能当大圣之名?既然如此,那么太史公何以用“岂非天哉,岂非天哉”来评价刘邦呢?在读到司马迁专门叙述刘邦病重时的一段对话时,刘先生又有所悟:“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于是高祖谩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赐金五十斤罢之。”[13](P391) 原来司马迁是借刘邦自己的嘴道出, 所谓“岂非天哉,岂非天哉”,是说他之得天下不是凭借人力,不是凭借自己的道德才能,而是靠了运气(天命)啊!再后来,继续读《史记》,发现司马迁在写战国魏亡时说“天方令秦平海内”,魏是没有办法支撑的[14](P1864);写秦的兴起和统一“盖若天所助焉”[13](P685)。为什么这样说呢?据《六国年表》可知,六国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之间战斗不休,结果不是实现了六国的利益,而是在客观上为秦灭六国扫清了道路,这正合了孟子所说的“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15](P383)。秦灭六国,废诸侯,本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结果却为后来者扫清了道路,这也是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的天命啊。“岂非天哉,岂非天哉!”正是由此而来的,这里的天命就是指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啊!读到这里,刘先生有了更深的理解:战国秦汉之际,正值历史巨变时期,旧贵族习气适应不了新时代,而刘邦则没有贵族习气,他的流氓习气恰恰成了他能克敌制胜的条件。从时代精神来看问题,司马迁所言的“岂非天哉,岂非天哉”,正是对刘邦之所以为“大圣”受“天命”的解释。这样,刘先生对“岂非天哉”的理解,经过了正、反、合或否定之否定的三个阶段,既完成了客观分析的一个循环,也对刘邦何以成就帝业和司马迁何以“成一家之言”达到了双重的内在理解。
(三)关于逻辑论证与历史论证的张力关系
刘先生在多年的学术研究中认识到,古代中国人和西方人在对待思想和论证方法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态度。中国人习惯于历史的论证:你说一个道理,要拿出证据来,关键是举出事实例子来,所谓无征不信。先秦诸子都是拿例子说话的,即通过故事讲道理,如孔子所言:“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16](P3297)。其中当然有逻辑,但主要是拿故事做论证。换句话说,中国传统认为真理不能从静态中把握,只能从动态中把握,所以最好的论证就是历史的论证。但希腊人的传统不是这样的,希腊哲学家认为历史的证据是不能证明永恒真理的,因为它昨天是这样的,今天可以不是这样的,所以必须作逻辑的论证。总之,中西文明之分,不在于一方有理性、有哲学,而另一方则没有。双方都有高度发达的理性,是其所同;而西方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逻辑理性上,中国的发展则主要表现在历史理性上。在西方古代文明的理性结构中,逻辑理性居于主导地位,而在中国古代文明的理性结构中,则历史理性居于主导地位。毫无疑问,两者各有所长。不过,对于中国人来说,必须学习西方学术传统里的逻辑的自觉性。只有学人之所长,才能补己之所短,从而才有可能把经过取长补短的中国文化贡献于人类。
刘先生的学术论文从多方面体现出逻辑论证和历史论证形成张力的特点。以《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为例,该文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语源、定义和理论上说明为什么历史比较的功能在于明同异。第二部分则从一多关系来说明世界历史与比较研究的同一性。第三部分则就世界历史的具体问题展开论述。前两部分虽间或涉及具体的史实,但那只是论证时选用的论据,总体上看,这两部分的论证是从“同异”、“一多”的逻辑联系探讨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的关系的。后一部分则引述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说明问题,表现了历史论证的特点,并与前两部分相呼应,使逻辑论证与历史论证形成了张力关系,取得了较好的论证效果[17]。《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一文,虽主要是历史的论证,但全文在谋篇布局和论证的程序和结构上则有着强烈的逻辑精神。是逻辑论证和历史论证相结合并形成张力的典型[18]。2005年与陈新博士合写的《历史比较初论:比较研究的一般逻辑》一文,一方面从可公度和不可公度的矛盾关系及概念的种属关系的角度出发,论证比较研究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以法国学者布洛赫《封建社会》关于封建制度的比较研究为例,说明比较研究在经验上的可行性。是逻辑论证和历史论证相结合并形成张力的又一成功例证[19](P67~73)。刘先生探讨理论问题的文章一方面能够做到突破经验,达到理论的高度;另一方面,又能够与历史相互印证和发明,得到经验事实的支持;探讨历史问题的文章则能够做到选题定位准确、层次和结构分明、行文路数清晰可辨,论证合乎逻辑,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些都得益于他对逻辑论证和历史论证的张力关系的自觉。
四、关于历史的比较研究
刘先生是历史比较研究的大家。他之所以能在比较研究上取得丰硕成果,除了拥有深厚的中外语文功底及丰富的中外史学知识,还与他对比较研究有着清醒的理论自觉和深刻的理性思考分不开。在他看来,历史的比较研究之所以可能,不仅是一个经验的问题,更是一个理论问题。经过他的论证,历史的比较研究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经验性的实用型的学术门类,而是有着坚实的理论性前提条件和研究自觉的学科,究其原因,就在于他指出了内在于比较研究中的结构与张力关系。
(一)上世纪90年代的理论总结
1996年,刘先生发表了题为《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的论文,对历史比较研究何以可能的问题作出了回答。在《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引论》中,对相关问题也作了阐述。
1.同与异——世界历史的内在结构之一
刘先生指出:比较研究的基本功能在于明同异,包括共时性的比较,即不同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等之间在同一历史时期中的同异,和历时性的比较,即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等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同异。同异是历史的比较研究赖以实现的前提。因为,很明显,历史时期相同,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之间的比较才是有意义的,而同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与其自身没有比较的价值。这就是说,无异之同不具有比较研究的条件。历史时期不同,同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的前后比较是有意义的,而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集团之间就没有比较的价值。这就是说,无同之异也不具有比较研究的条件。总之,有相同,才能比其异同;有相异,才能比其同异。根据这个道理,可以推断,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之间,虽然一般说来不具有可比性,但是,只要从一个相同的角度去看,其间仍然是可以比较的。
2.一与多——世界历史的内在结构之二
如果把历史看作是世界历史,那么,它的比较研究还与它所具有的一与多的关系有关。这是因为,首先,世界历史是由多而一的历史。所谓世界历史,就不是地区史、国别史,但却是包含着许多的地区史国别史的历史,没有这许多的地区史国别史,也就不会有世界历史。不过,世界历史也不是各个地区史国别史的简单相加,那样加起来的仍然只不过是地区史国别史的总集或汇纂。用算术的方法加在一起,所得到的只能是某一个多数,而不可能是一。可是,世界历史作为全世界的历史,它必须是一个整体,也就是说,必须是一。如果把各个地区史国别史名之为小一,那么世界历史就是大一,大一由诸多小一集合而成。
3.一多与同异的关系——否定的、抽象的世界历史
要把小一变为大一,就不能是简单的加法,那样只能是量变,结果只能是多,而不会成为大一。要形成大一,就必须有质变,必须对小一有一个否定或扬弃的过程。这个否定或扬弃就是抽象的过程。所谓抽象,就是从许多现象中舍弃了它们的特殊性而抽取其一般性,从而在舍取并行的过程中达到了由特殊而一般、由多而一的境地。如上所说,诸事物各自的特殊性即是其相互之间的异,而诸事物的一般性亦即其相互之间的同。所以,不辨异同就无从进行抽象,而无比较研究,就无从明辨异同。可见,比较研究的明异同,恰好在方法上构成了世界历史所需的辨一多的必要条件。
世界历史又是一中涵多的历史。世界历史必须首先视为一个整体,进一步就必须了解这个整体是怎样构成的。因为,如果满足于由抽象达到的一,那么这个世界历史的一也就成为抽象的无差别的一或者纯粹的一,这个一必然像黑格尔的逻辑起点的纯粹的有(Sein)一样,一方面是无所不包,同时在另一方面又是一无所有的。所以它必然会直接地转化为无。也就是说,它的内涵接近于零了。内涵接近于零的世界历史就不成其为历史,它不可能作为实际的历史存在,也不具有存在的价值。
总之,没有对各个地区、国别的历史中抽象出同而加以概括,我们就只能看到世界各地区各国别的杂乱无章的一大堆事情,就没有世界历史;同样,如果把世界历史看作是抽象的一,其内涵等于零的一,那么整个世界上的事情又变成了一大口袋马铃薯。从外表看,这个口袋(抽象)是一,而从其内容来看,它们仍然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多。
4.一多与同异的关系——否定之否定的、回复具体的世界历史
如果要把世界历史看成有机的一,那么势必要把认识再深入一个层次,由抽象再上升到具体,从同再看出异来,看出那些各异的部分是怎样既互相拒斥又互相渗透地构成为有机的一体的。
怎样才能使认识深入一个层次,从而由同中再看出异来?这就需要比较研究再深入一个层次。只要有了比较研究的同中见异,也就有了世界历史的多样统一的活生生的一。可见,历史的比较研究在方法上又可以成为世界历史所需的明一多的充分条件。
在实际的世界历史研究中,时常可以看到这种认识上的三个阶段:开始时看到的都是异,经过比较又发现了不同国家之间原来在甲方面有相同之处,在乙方面又有相同之处,以至有多方面的相同之处。于是认识就达到了由异而同、由多而一的阶段。再进一步,人们不能满足于抽象的一,就又经过比较而认识到世界正是一个多样统一的有机整体,这样就完成了对世界历史的一次完整的认识过程,当然这样的认识过程实际是需要不断深入进行的。而全部这样的认识过程都必须也必然是在比较的研究中实现的。
5.关于比较研究的限度问题
刘先生指出,历史比较研究也是有其局限性的,它的局限性就在于其自身离不开有意识的角度选择。既有角度的选择,就必然有视阈的规定性,而规定即否定,在选定视阈以外的,自然就是被忽略了的。因此,如果不是清醒地认识这种局限性的存在,就必然会把自己一时比较研究所得视为绝对真理,从而陷于一种盲目自信的状态。世界历史可以选择的比较研究的角度是难以限定的。随着条件的变化和发展,人们会不断发现新的比较视角,所以,历史的比较研究不是可以一次完成的,世界历史也不是可以一次写定的。
(二)新世纪的新进展
2005年,刘先生与陈新博士合写了《历史比较初论:比较研究的一般逻辑》一文,再次对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根据进行了讨论,再次回答了历史比较研究何以可能的问题。
刘先生认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历史比较研究的作品,这些研究主要是期待揭示比较对象之间的异同与本质特征,人们把比较看作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专业历史研究法。但是,历史比较研究作为人文学科内比较研究的一种,它也应该遵循一般比较研究的逻辑。或者说,历史的比较研究在逻辑上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过去,人们有一种乐观的信念,认为比较研究自然就是可能的,所以对此没有提出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科学哲学领域内出现了有关不可公度性的讨论。美国的库恩(T.Kuhn)提出,“范型”(paradigm)之间存在“不可公度性”(incommensurability)。“不可公度性”是否就等同于“不可比较性”?经过长期争论,库恩本人也承认,“不可公度性”并非完全等同于“不可比较性”。此问题争论至今尚未终结。对于这一讨论,刘先生经过审慎的了解和思考,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比较是不可公度性与可公度性的统一。这个说法可能理解起来比较抽象,刘先生用这样一个通俗的比方来加以说明:比如比较的对象完全相同,例如数字3、3、3……,它们之间有同无异,这样,比较就失去了意义;再如比较字母A、B、C、……,它们之间有异无同,比较同样失去了意义。假若是3A、6A、9A……等一系列比较项中,3是公约数,A也是公约数,以3A公约以后,1、2、3、……就不可公约了。这当然是最简单的比喻,如果以法国年鉴学派学者布洛赫的比较研究经典之作《封建社会》中对于“封建主义”的讨论为例,也可以有助于问题的理解。在布洛赫看来,欧洲不同地域的“封建社会”所以能够比较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即依附农民,附有役务的佃领地也就是采邑等,这些似乎就是欧洲封建主义的基本特征。但是,欧洲封建化的程度并不是全部一致的,节奏也不完全相同;最重要的是,任何地方都不是完全封建化的。由此可以看出,研究中世纪欧洲范围的封建主义,必须同时揭示其中的异与同,而研究本身是从现象之异中抽象出同,没有对异的感知,就不可能有对同的抽象。所以,比较研究中,如果可公度性意味着“相同”的话,不能由比较对象之间局部要素的可公度性推导出整体的可公度性。同时,比较研究中,比较对象的可公度性与不可公度性会随着比较者设定的比较范围或概念层次而发生变化。可见,历史的比较研究正是在可公度性与不可公度性之间的结构张力关系中进行的。
五、对历史的敬意
刘先生之所以能在历史研究中取得丰厚的成果,之所以能对历史研究做如此深刻的反省,与他在内心深处秉持着对历史的敬意有关,也与他对这份敬意,对它的内在结构及其张力关系,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深刻的反省有关。
(一)对历史之敬意的内在结构——尊敬与肃敬
刘先生曾不止一次回忆起少年时代在沦陷区的经历:对日本侵略者及其宣传的强烈反感和厌恶,对祖国历史文化的真挚的热爱,英文课上老师讲《最后的一课》(The Last Lesson),他和班上的同学们都流下了眼泪, 这些都深深印在了他幼小的心灵上。抗战胜利后,他考上江南大学,听钱穆先生讲要对中国的历史持有敬意,深受触动。工作后教外国史,发现对外国史也应怀有同等的敬意,敬意是可以超出国界的,于是对历史就有了一种美好的感情。“文革”中,目睹历史遭到践踏和滥用,对历史应持敬意更有了强烈的愿望,并由此对敬意的“敬”字有了新的理解。所有这一切,使他对历史的敬意从一种美好的感情,上升为理性的理解。
1993年,刘先生发表了一篇访谈文章[20](P24~31),系统地表达了关于对历史的敬意的理解。
在刘先生看来,敬意也是有着结构、张力和发展阶段的。敬,《说文解字》解释:“肃也”,肃又是“持事振敬也”、“战战兢兢也”;《释名·释言语》:“敬,警也。恒自肃警也”。据此,刘先生认为,敬既表示尊敬的感情,又表示严肃的态度。由此看来,即使对日本的历史也应怀有敬意,尤其在研究日本历史的时候,敬意是不可缺少的。于是,在刘先生那里,敬字就有了两种含义:一种是感情上的尊敬,一种是理性上的肃敬。继而,刘先生又对这两种含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思考,并认为敬意及其内在的结构关系与确立史家的人格有着必然联系。
(二)尊敬与肃敬之张力即辩证关系——史家人格建立的三阶段
史家如何建立自己的学术人格?或者说,史家如何才成其为史家?刘先生认为须经过以下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首先,治史时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感情,彻底超越感情而达到太上忘情的地步是绝然不可能的。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在从事一项历史研究或撰述之前,必定在精神上处于孔子所说的愤悱状态,并对这种愤悱状态保持敬意。这可以说是事情发展的第一阶段。到了事情发展的第二阶段,前一阶段居于主导地位的感情必须经由理智感的渠道而让位于理性。经过第二阶段的富有客观的、理性精神的研究,历史上的真伪和是否问题弄得更清楚了。于是事情的发展进入了第三阶段。这时候,史家的自信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油然而生,作为史家的人格经过否定阶段以后重新达到肯定阶段,达到了确立。史家对于自身的敬意,既包括了对自身成绩的喜悦与自重,又包括了导致这种成果的严肃的、客观的精神,达到了尊敬与肃静、感情与理性的统一。史家对历史的敬意,表现在对历史过程的崇真黜伪上,表现在历史价值的是是非非或善善恶恶上。是非善恶的感情以理性的判断为基础,而理性的判断明确规定了更高一层次的感情。这也是感情与理性的统一。总之,我们的史学研究在开始时难以无情,深入时又不能不重理,而最终则要求情理结合。有了这样一个正—反—合的循环,可以说,史家的人格才可以真正建立起来。
刘家和先生的学术成果一向以冷静、客观、深刻而著称,表现出鲜明的理性色彩,其实,在这鲜明的理性色彩的下面,非同寻常的激情涌动却从未停止过,这就是他对祖国、对人类、对真理的深情之爱和对历史研究的崇高使命感,在他那里,理性和激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形成了很好的张力关系,表现在对历史的敬意上,就是从尊敬到肃敬,再从肃敬上升到更高层次的尊敬,在建立史家人格的实践中树立了典范。
六、结语
刘先生的学术思想有着一以贯之的精神,那就是努力探索并牢牢把握历史及历史研究的内在结构及其张力关系。在刘先生看来,历史是在内在结构的张力之间发展的,这不但是看到了事物的是(正)的一面,还看到了它的否(反)的另一面,不但看到是(正)与否(反)的两面,还看到了从是(正)到否(反)的变化或发展的第三阶段,所谓张力就是关于这个阶段的一种形象的比喻。
黑格尔把有和无的统一称作“变易”(Das Werden,英译作becoming)[3](P195、197),这变易又可指代从正到反到合或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其实这种变易是理性的展现和逻辑的推演过程,是脱离时间的运动。不过,对理解事物发展的内在根源和动力,黑格尔的这个三段式(triadic process,又译作“三一式”)却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刘家和先生的学术思想,尤其是对历史及其研究方法的内在结构和张力的阐释,恰恰表现出对这个三段式的深刻领悟和批判理解。他常说,历史学家是研究历史的,其实,历史学家自己也是历史的,他的研究也是历史的,他应该时刻意识到自己和自己的研究的历史性或局限性,并在克服和突破局限中不断进步。刘先生积累丰厚,思考精深,却从不轻言发表,世之所传,不及其学十分之一;对于他发表的成果,同行赞叹难以企及,而刘先生却总是感到不足。这固然与他追寻以往历代大师的足迹,充分发掘条件,努力做出不负于时代的创新成就的志向有关,更是他自觉到学术研究的历史性,自觉到个人研究的局限性,并努力克服和突破局限,追求不断进步的精神的自然流露,展现了一位历史学家不断自我反省、自我否定(扬弃)和自我突破的心路历程。
结构——张力——历史,作为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在历史领域的生动表现,反映了刘家和先生学术思想的内在特质,是他确立史家人格的根本途径,也是史学研究应有的真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