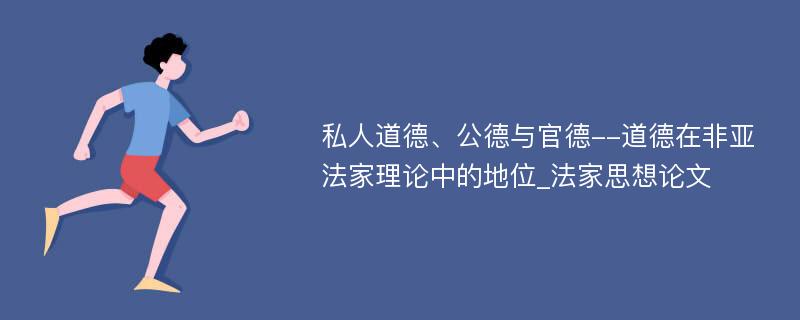
私德、公德與官德——道德在韓非子法家學說中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私德论文,法家论文,公德论文,道德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爲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子認爲儒家的仁義道德“可以戲而不可以爲治”(《外儲說左上》)①,治理國家要靠嚴刑峻法、厚賞重罰,不能依賴道德,故歷來被視爲與“德治主義”相對的“法治主義”的代表,並被貼上“非道德主義”的標簽。如有學者指出:韓非的“法治”學說只認法,不要德,在極端誇大法的地位作用的同時,否定道德的功能和作用,從而否定了道德本身。②另一方面,也有學者不同意這種看法,認爲細讀《韓非子》可以看出,“非道德主義”的解讀未必符合韓非思想的實際。③因此,韓非子究竟是不是“非道德主義者”?道德在韓非子法家思想中究竟有没有、以及有什麽樣的地位?這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在探討之前,有必要首先明確一下概念:即本文所要探討的道德,就是我們現在意義上的道德(ethics,morality),而不是先秦諸子文獻中,比如《老子》所說的“道德”。說《韓非子》書中有《老子》意義上的“道德”觀念,這完全不成問題。因爲韓非子明顯從《老子》那裏繼承了“道”與“德”的思想,正如已有學者指出的,在韓非子思想體系中,“道”與“德”或“道德”甚至還是“法”的形而上的終極依據。④而立“道”垂“德”也是韓非子所謂“明主”的定義之一。⑤然而,《老子》意義上的“道”與“德”與我們今天所說的道德儘管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繫和淵源關係的,但又不完全是同一個概念。⑥此外《韓非子》文本中出現的“德”字,有時僅僅意指“獎賞”(如《二柄》篇“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這也跟我們今天所說的道德無關。爲了保證論題的明晰,有必要先明確一下,我們這裏討論的問題,不是《韓非子》書裏有没有先秦意義上的“道”與“德”的概念的問題,而是在韓非子思想中道德的價值和地位的問題。具體來說,也就是相對于外在的、基于工具理性而設計的制度和法律之外,個人基于某種價值理性自覺地以道德準則來對自己的行爲進行自律,這樣一種東西在韓非子思想中有没有地位?如果有的話具體表現在哪裏?
仔細閱讀《韓非子》,我們不難發現,韓非子並不是個没有道德價值觀的人,道德在他的法治學說中並非没有地位。從終極目標上說,韓非子的法術主張最終也是爲了“利民萌,便衆庶”,“以齊民萌之資利”(《問田》),使“百姓利其澤”(《主道》)。這跟儒家的“仁政”理想並無二致。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韓非子以民衆福祉爲君主應當順從的最高法則,這就足以看出韓非子理論是有政治道德的。⑦即使對儒家的一些道德範疇,韓非子也並非根本否定。韓非子雖然說過:“君通于不仁,臣通于不忠,則可以王矣”(《外儲說右下》)。但那只是强調制度設計要達到即使在君不仁、臣不忠的最壞情况下也能運作的程度,以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而不是縱容君不仁,臣不忠。其實韓非子對于“忠奸”有著鮮明的道德立場。《韓非子》書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反“奸”禁“邪”,認爲只有“忠勸邪止”纔能使一個國家“地廣主尊”(《飾邪》)。“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而“以尊主御忠臣”是建立功名的必要條件(《功名》)。又如韓非子《難一》篇曾批評“桓公不知仁義”,表明他並非根本否定“仁義”本身,只不過反對那種虛假做作的“仁義”,認爲“仁義”不在于表面上做出禮賢下士的姿態,而在于是否真正把天下國家和人民放在心上。“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忘民不可謂仁義”。(《難一》)。總之,韓非子並非從根本上否定包括仁義忠信等等範疇在內的道德價值。
但是韓非子跟儒家在道德問題上的確有一個明顯的不同,就是韓非子似乎已經區分了私德與公德的不同領域。“私德”是指涉及私人生活領域的道德,往往與個人信仰、宗教觀念、修身養性、自我完善有關,也包括家庭內部的倫理道德。“公德”是涉及社會公共領域的道德,是不具有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等熟人關係的人們在公共交往領域應當遵守的道德,包括各種職業道德。而從政者的政治道德,顯然也屬于“公德”範疇。也有人將“私德”稱之爲“宗教性道德”,把“公德”稱之爲“社會性道德”。⑧
梁啓超在《論公德》一文中曾說:“吾中國道德之發達,不可謂不早。雖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闕如。”⑨如果僅就以孔孟儒學爲代表的古代倫理學而言,梁啓超的這個說法大致不錯。儒家倫理學的一個特色就是提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通過家庭這個環節,把個人與天下國家連爲一體,形成公私一貫、一條鞭到底的倫理道德觀。其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就是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關係爲紐帶的熟人社會。君臣關係只不過是這種家庭、朋友倫理的延伸。但是這種社會基礎在戰國時期國家政體(state)初現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已經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改變,基于血緣紐帶的宗法制社會出現了解體與鬆動,非血緣的社會政治組織關係開始發展起來。⑩因此那種公私不分的倫理道德也暴露出它的矛盾和悖論。例如《孟子·盡心上》所討論的“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的案例,《韓詩外傳》卷二所載石奢的故事,卷十所載申鳴的故事,都表現了孝親的私德倫理與維護公義的公德要求之間的矛盾衝突。(11)
韓非子顯然看到了這種社會結構變化帶來的倫理道德上的矛盾衝突,因此在他的政治學說中區分了私德與公德的領域;私德不屬于政治領域,而公德則屬于政治領域。在韓非子看來,儒家的一個錯誤就在于將非政治的私德標準直接運用于政治領域。(12)而韓非子則認爲私德不值得提倡,甚至還應該限制。而公德,特別是表現在君主和官吏身上的官德,則是必不可少的,需要加以提倡。特別是在私德與公德發生衝突時,則提倡公德優先。這是韓非子道德觀與儒家道德觀的一個重要區別。
例如,儒家提倡“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對揭發父親罪行的兒子加以誅殺,而對出于孝親考慮而在戰場上當逃兵的兒子,卻給予獎賞,因爲這符合“孝”的道德。韓非子則認爲這是“私德”與“公德”不分,其結果必然是“令尹誅而楚奸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五蠹》),破壞了公共領域的道德。與此相反,《外儲說右上》記載楚太子犯法,廷理依法制裁,而楚莊王也能支持廷理對太子的制裁。這個故事不僅肯定了廷理的執法嚴明,更贊賞了楚莊王克服父子間的私愛、以法度爲重的公德,這種品質得到了韓非子的贊賞。
此外,道家提倡淡泊名利,潔身自好,遠離世俗的清高的道德,寧願“或伏死于窟穴,或槁死于草木,或饑餓于山谷,或沉溺于水泉”(《說疑》),也要保持自己的道德節操。這種道德,純屬一種個人追求,是私德,韓非子認爲完全不值得提倡。又比如被稱爲“俠”的一批人,勇于私鬥,願爲朋友兩肋插刀,甚至不惜“以武犯禁”。這符合“俠義”的道德精神。但這也屬于個人道德追求,是私德。韓非子認爲不僅不值得贊譽,如果“犯禁”觸犯法律還應該加以制裁。
公德與私德領域的切割,在《外儲說左下》所述的“外舉不避仇”的故事中也有形象的表達:晋國的趙武舉薦自家的仇人擔任中牟令,趙國的解狐也曾舉薦仇人擔任國相。而當仇人得知後前往拜謝時,解狐卻引弓而射之,表示私仇如故。不忘家族私仇,也是儒家提倡的一種倫理道德,與孝有關。儒家經典《禮記》裏面就有“父之仇不共戴天”的說法。但這屬于“私德”,不應當運用于公共事務。而身處公職,出以公義,唯才是舉,公正地推薦人才,則屬于公德。趙武、解狐作爲朝官,“外舉不避仇”,“私仇不入公門”,公歸公,私歸私,界綫清晰,因而受到韓非子稱贊。
但是韓非子並没有在一般意義上推動一種全民公德,他所提倡的涉及公共領域的道德,主要體現爲對君主和官吏的道德品質要求。我們可以把它稱之爲“官德”,也即爲官者的職業道德。
對韓非子政治學說的一個誤解,就是認爲他的學術是爲君主專制獨裁服務的。但實際上,韓非子的法治學說其實也包含不少對君主進行約束的內容。如果我們把君主也看成是國家政體中一個不可缺少的職務,那麽這個職務也是有其職業道德要求的。《韓非子》書中對君主的約束,大多就是著眼于對君主職位的職業道德要求。
韓非子雖然没有像儒家那樣寄希望于君主成爲“聖王”,但認爲君主作爲最高政治領袖至少不能讓人民“絶望”。也就是說作爲一國之君,應該具有起碼的道德素質,遵循基本的政治道德規範,保持民衆對自己的信心,不能讓民衆在自己身上看不到希望。韓非子認爲“民之望于上也甚矣”(《難一》),人民對君主的期望是很高的,君主的道德和行爲不應使民衆“絶望于上”。像桀紂那樣讓人民“絶望”的君主,韓非子與儒家一樣持否定態度。
韓非子對君主個人的私生活本身並没有道德評判,但是他强調一點,即君主在朝廷上必須隱藏自己的個人喜怒和好惡,“無見其所欲”,“去好去惡”(《主道》)。因爲作爲君主,在公共場合顯示自己的好惡,底下的人就會投其所好,給奸臣以可乘之機,影響政事的公正。要求君主隱藏自己的喜怒好惡,不可能由法律來規定,只能是一種基于職務要求的道德自律。
又比如韓非子曾說過:“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外儲說右上》)這往往被人們理解爲擁護君主獨裁。但實際上這裏所謂“獨斷”是有特定上下文的,具體是指“不聽左右之請”,即防範君主的親屬和身邊小人對法制的干擾。比如君主身邊的侍者、宦官、後妃、佞幸、俳優侏儒等等,君主跟這些人如何相處,屬于“私德”範圍。但如果聽信這些人的私下請托,讓他們干預政治,則是私人關係侵入了公共領域。如果被他們忽悠得團團轉,失去了自己的主見,那就好比《內儲說下》一則故事中所描寫的那個燕人李季了。君主如果“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那麽士人就會去巴結君主左右的小人,“費金璧而求入仕”(《外儲說左下》),從而腐敗官場風氣。韓非子强調,君主對于自己身邊的“小人”,包括“人主所甚親愛”的人,只可以讓他們安于規定的職分,而不可以跟他們討論公務,不可以把跟群臣們討論的國事泄露給身邊“小人”。甚至君主連睡覺都最好“獨臥”,“唯恐夢言泄于妻妾”(《外儲說右上》)。因此,這個“獨斷”,可理解爲對君主作爲最高政治領袖的一種道德自律,好比我們今天要求領導幹部在做决策時要獨立作出公正裁决,不聽家人、親朋、故舊等等的游說、托請,不讓公務受到私人關係干擾。這與專制無關。至于在公共决策方面,韓非子倒是曾活用老子“不敢爲天下先”的思想,主張“議于大庭而後言則立”(《解老》),也即君主要首先充分聽取大臣們的意見,讓他們充分議論,然後再做决策。
又比如韓非子要求君主不要去直接插手具體事務。老子就曾告誡人主不要代司殺者殺、不要代大匠鑿。韓非子繼承並發展了老子的這一思想,認爲君主不可以自以爲聰明,不應該“多事”,在具體事務上直接插手。無論是賞罰的實施、官吏的舉拔任免,韓非子都一再强調君主要通過“法”與“術”讓“有司”(有關部門)去實施,不要憑自己的好惡和個人的小聰明直接插手。這也是要求君主要道德自律,不以私心和個人好惡干擾“法術”的運行和“有司”的獨立工作。
對于一般大臣官吏來說,也有他們應該遵守的職業道德,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明于公私之分”,做到“清廉、方正、奉法”(《奸劫弑臣》)。
韓非子認爲人都是自私的,都是趨利避害的,做事情都是圖回報的,君臣之間“主賣官爵,臣賣智力”(《外儲說右下》);“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禄以與臣市”(《難一》),是一種以利相交的買賣契約關係。因此制度的設計就是要基于這種人性論所决定的利害關係。但這不等于說韓非子就是提倡“自私”,也不等于說韓非子認爲有了基于利害關係的制度,就不需要提倡良好的道德了。恰恰相反,《韓非子》書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講“公私有分”,“必明于公私之分”(《飾邪》),“去私曲就公法”(《有度》)。無論君主還是大臣官吏,都不能“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孤憤》)。
韓非子認爲在人臣身上,既有“私心”,也有“公義”。“私心”是人的本性,“公義”則有賴于後天的道德培養。在這一點上韓非子的看法跟他的老師荀子有相似之處。“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污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飾邪》)英明的君主和好的制度,可以促使人臣“去私心行公義”,反之則會使人“去公義行私心”。
韓非子所謂“去私”也不是叫人完全没有爲己的私心,而在于劃清私與公的界綫,不能利用公權力來謀私。這在“公儀休不受魚”(《外儲說右下》)的故事上表現得很明顯。公儀休爲相,自己喜歡吃魚卻不接受別人拿魚來賄賂,堪稱道德廉潔奉公守法。但從公儀休自己的邏輯來說,他並非完全“無私”,而是認爲必須在公與私之間劃一條清晰的界限,纔能持久地保證自己應得的那份“私”。腐敗不腐敗並不在于一官員有没有私心,而在于他是不是有意無意混淆公與私的界綫,利用公權力來謀私。
與此相關,韓非子認爲作爲官員,不應該有太多的“私交”。官場上許多腐敗現象,都是從“私交”開始的。因此韓非子强調“故人臣處國無私朝,居軍無私交”(《愛臣》),痛斥官場上一些人只知道“奉禄養交,不以官爲事”(《有度》),“群臣持禄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三守》)。即拿了薪水不幹職務本身所要求的正事,卻忙于結交私人關係。在官場上,這種“私交”不僅引發腐敗,而且掩蔽官場罪行。韓非子敏銳地指出這一點:“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有度》)。
此外,《韓非子》書中涉及的官德的內容還有以下這些方面:
爲官者應該公平正直。“天下公平”(《守道》)是韓非子的社會理想,公平是法律所要求的精神,而堅持公平正直也是一種道德品質。韓非子認爲法應該體現公平與平等的價值,明確提出“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的可貴思想。但是,把公平的原則寫在法律裏還是相對容易的,而要使之在現實中得到落實,仍然有賴于執政者自身公平正直的道德品質。《外儲說左下》引孔子曰:“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從我們的現實經驗也不難理解,法的公平,往往有賴于爲官者的正直,纔能落到實處。因此爲官者本人是否具有公正、不偏黨的職業道德,也是十分重要的。
爲官者應恪守信用,信守承諾,說話算數。韓非子曾說君主對臣下要“恃勢而不恃信”,“恃術而不恃信”(《外儲說左下》),但這並不等于說“信”本身不是一種良好的、值得鼓勵的道德品質。他的意思只是說不能指望所有的大臣都守信。但守信本身,不論對于君主還是大臣,都應有的道德品質。尤其是對人民必須講忠信:“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難一》)《外儲說左上》强調“明主積于信”,並以“晋文公之攻原”、“吳起須故人而食”、“魏文侯會虞人而獵”、“曾子殺彘”等一系列故事來說明恪守信用的重要性。《說林下》記載樂正子春不願爲魯國送給齊國的贋品讒鼎背書的故事,說明國與國之間也應講誠信。齊魯之間既非父子兄弟,也非朋友,樂正子春仍然堅持對齊國要講誠信,這已經超出了“朋友有信”的私德,進入了公德領域。
爲官者應當各守其職,既不失職,也不越職。如《外儲說左上》引鄭簡公謂子産曰:“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根據所處的職位,該做的事一定要做到並且做好,不該做的事就不要去做。自己的所作所爲要與所處的職位相稱,如《二柄》篇一則故事所表明的,“典冠者”不應該去做“典衣者”的事。又如《外儲說右上》所述孔子禁子路擅愛魯民的故事,即表明爲臣的不應該越出本分,去做不屬于自己職責範圍內的事。這與儒家提倡的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的態度有相通之處。當然,這可能會導致臣下對君主的盲從以致失去自己的是非:“順上之爲,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有度》)但這作爲一般官員在常規狀態下的職業道德,也未可非議。不過在一些特殊或極端情况下,例如這個“上”或“主”明顯是在作惡,或者出現了主上的命令與“法”相違背的情况,臣下還要不要順從?此時恐怕就會出現道德取捨上的兩難:是遵守服從命令的職業道德,還是依據道德善惡的內心判斷?在這種情况下,可能就需要援引儒家“從道不從君”的更高原則了。
總之,韓非子並不是一個没有道德價值觀的人,道德在他的政治學說中是有一定地位的。在終極層面上,他的道德觀與儒家並非根本對立。這種道德價值構成了他的社會政治學說的前提。韓非子與儒家等其他學派不同之處,在于嚴格區分私德和公德兩個不同的道德領域。對于像儒家所提倡的家庭內部的孝道,道家提倡的個人的清高,俠客所奉行的私人之間的仗義,這些私德在韓非子看來不僅不值得提倡,有時還應該禁止。但是在社會公共事務領域的公德,特別是君主和官吏的官德,則是必須的,應該加以提倡和鼓勵。如果說私德往往以宗教信仰或個體信念爲基礎,那麽公德則更多有賴于社會法制與規則作爲保障。因此,公德的建構與通過制度性的“法”和程序性、技術性的“術”來治理國家不僅並行不悖,而且是相得益彰,相輔相成的。
就國家治理的工具而言,韓非子顯然認爲制度性、程序性的“法術”纔更重要,而道德本身並不是個有效的工具。道德的價值需要藉助“法術”這個工具纔能得到實現。高尚的道德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品質,按照他的老師荀子的觀點,道德之善不是天生的,不是人性的本然,因而在現實中也不是必然的。治理國家不能指望某種不必然的東西,而必須依據必然的東西,這就是跟據人的“好利惡害”的本性,用厚賞重罰、嚴刑峻法來治理。特別是在法制不完善、社會秩序混亂的局面下,光靠空口白說,呼唤道德,並不能從根本上解决問題,使社會得到有效治理。在韓非子看來,良好的道德也有賴于完善的法制環境,“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安危》);“安則智廉生,危則争鄙起”(《安危》)。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只有在合理正義的規則的引導下,良好的社會道德纔會生長。(13)
官吏的道德品質問題,也跟他們所處的政治環境和制度環境密切相關。韓非子認爲没有一個臣天生是“忠”的,“忠”的品質有賴于政治環境,也有賴于君主本人的品質,“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群臣忠;君懦而暗,則群臣詐”(《難四》)。例如在官吏的選拔和任用方面,如果有一套公平而規範的制度,而君主也能像韓非子所說的那樣,“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有度》),公正而透明地“論之于任,試之于事,課之于功”,那麽官員也就會“公政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難三》);“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飾邪》),從而使官場逐漸形成良好的道德風尚。相反,如果制度不健全,領導者用人隨心所欲,任人唯親,不守法度,那麽要求下屬恪守道德,廉潔自好,難度就比較大。
但另有一點也值得注意,即雖說完善的法制有利于良好的道德風氣生長,但不能簡單理解爲在制度上直接對道德進行物質獎賞。《用人》篇曰:“明主厲廉耻,招仁義。”表明他認爲君主應當提倡仁義廉耻的道德。但他又曾强調“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奸劫弑臣》),也就是說不贊成官方對個人的“仁義”道德品行進行獎賞。官方只應當獎賞實質性的功勞,而不應當獎賞個人的道德。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爲道德之所以道德,就在于它是個人的自覺自願的行爲,不是爲了其他目的。官方獎賞道德,只會誘發一些人爲了得到獎賞而僞善,那樣道德也就變味了。《韓非子·解老》篇在解釋《老子》“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時說:“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可見他對“仁”作爲一種道德品質本身是認可和肯定的,同時他又認爲“仁”德在本質上是不應該求回報的。因此,如果政府對“仁”進行物質利益獎賞,導致人們爲了得到這種獎賞而僞裝“仁”,其結可能反而在本質上把“仁”給毁了。因爲道德如果失去了內在自覺與真誠,純粹是受外在功利誘惑,恐怕就在本質上背離了道德。
①周勛初等:《韓非子校注》,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下引《韓非子》正文均出此版,僅括注篇名。
②朱貽庭、趙修義:《評韓非的非道德主義思想》,《中國社會科學》1982年第4期。
③錢遜:《韓非的道德思想》,《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1期。
④許建良:《韓非“德則無德”的道德世界》,《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6年第9期;吳凡明、曾建平:《韓非的道德思想與法律發生學》,《井岡山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
⑤如《安危》篇曰:“堯無膠漆之約于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于後世而德結。能立道于往古,而垂德于萬世者之謂明主。”
⑥例如我們不能僅僅依據韓非子說過“聖人爲法國者,必逆于世而順于道德”(《奸劫弑臣》)之類的話,就證明韓非子認爲治國要靠道德。參見白彤東:First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er·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2011(1).
⑦A.P.Martinich.The Sovereign i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Hanfeizi and Thomas Hobbes,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2011(1).p.71-72
⑧田超:《公德、私德的分離與公共理性建構的二重性——以梁啓超、李澤厚的觀點爲參照》,《道德與文明》2013年第3期,
⑨同上,第29頁。
⑩有學者認爲這一時期的社會轉型有點類似歐洲中世紀向現代化社會的轉型,而韓非子則可視爲最早的“現代”思想家,參見前引白彤東文,p.4-13;但這種轉型在中國雖然出現得很早,卻也很不徹底,以至于時至今日我們都很難說它已經徹底完成了,參見郭齊勇主編:《儒家倫理争鳴集——以“親親互隱”爲中心》,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11)關于這個問題學界已有很多討論,參見《儒家倫理争鳴集——以“親親互隱”爲中心》。
(12)參見前引A.P.Martinich文,P.65.
(13)宋洪兵:《如何確保社會的道德底綫——論法家道德-政治哲學的內在邏輯》,《哲學研究》2009年第12期,第4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