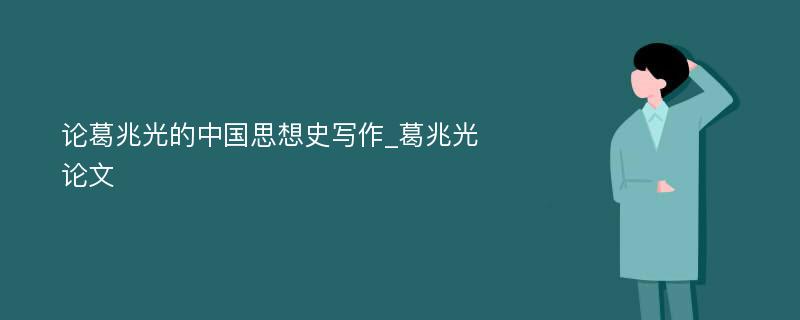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写法漫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写法论文,中国论文,思想史论文,葛兆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初读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第1卷为《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2卷为《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以下统称“葛书”,引文出处仅注卷次、页码)是在1998年的5月。当时,我对儒家仁学的思想内涵很感兴趣。所以,一拿到刚刚出版的葛书第1卷,我就迫不及待地翻到书中专门讨论“仁”的部分(见第179-181页),试图从这部时新的著作中得到一些更新的启发。却不料葛书对“仁”的内涵仅从“仁者爱人”层面作解,连众所周知的“克己复礼为仁”这一维度都不顾及(注:葛书此节在论“仁”前,虽然也谈到了“礼”及礼与仁的关系,但未涉及“克己复礼为仁”这一层意思,所以该节最后称孔子以仁释礼,是“依赖于情感和人性的自觉凸显来实现人间秩序”,可问题是:这种情感和人性的自觉是否有其不可逾越的限度呢?对于这个问题,各人观点上自然可以见仁见智,不过,像“克己复礼为仁”这样的基本材料是不可忽略的。),而且书中还引述某个时髦学者的“考证”,称“仁”的“本义当是‘心中想着人的身体’”——果如此,则“仁者”的“本义”岂不当是“心中想着人的身体的人”?——我想。于是,就把读这本书的计划搁置了下来。2000年年底,葛书又出了第2卷,我犹豫再三,过了四五个月才买了一本,放在书架上。直到最近,在书店看到葛书的《导论:思想史的写法》也出了单行本,影响似乎越来越大,我才下了决心,要去啃啃这部长达119万字的思想史大著。
不过,说实在的,直到开始写这篇小文章的时候,我还是没有读完精装的葛书两卷本。因为我读书一向有一个习惯,碰到疑惑不解的问题,往往要去查其它书中的说法。这回看到葛书劈头第一句“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把思想史看作唯一的历史”(第1卷第2页),我的心里就咯噔了一下。再看紧接着这一句的下文“这一说法曾经受到重视,也曾经招致批评,不过,如果我们把它理解成只有思想的历史的传统仍在今天延续,我们也许会对这种不免过分的说法表示同情”,说了一大通,也没有说到被指为科林伍德所说的这一说法的出处,心里疑惑倍增。于是就去翻何兆武先生译的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的中译本,好不容易才在《历史思想的范围》一节找到了这么一段话:“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思想过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第1卷第224页)对照葛书第1卷第7页倒数第2行中的一句“如果是这样,那科林伍德所说的一切历史都只是思想史就真的成立了”,可见葛书是把科氏的这段话当作“这一说法”的依据的。但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葛书的三种表述与科氏的表述虽然只有几个字甚至一个字的差异,所表达的意思却有相当大的出入:科氏原文("All history is the history of thought")本义是强调思想是历史事件的内在方面,强调内在的思想过程在历史过程中的核心意义,而不是说一切历史都只是思想史(因为历史中除了内在的思想层面,也有外在的行动、事件),也不是说作为专门史的思想史是唯一的历史(要不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恐怕也可以反过来转换成“当代史就是唯一的历史”之类的离奇说法了),更不是指什么“只有思想的历史的传统仍在今天延续”(此语全然不通,因为过去时代的物质文明成果亦仍在今天延续)。由此可见,直正“过分”的并不是科林伍德原来的说法,而是葛书对科林伍德观点的曲解,以及随着这种曲解而来的那种自作多情的所谓“同情”——如果要给这种同情加上一个名目,那它也只能说是一种“曲解的同情”或“同情的曲解”,而不是时人称道的那种“理解的同情”或“同情之了解”。
事实上,在葛书中,类似于这样的建立在误读和曲解基础上的“同情”或批评在在多是。如其导论引言中对冯友兰的一段话的误读(下详)以及对侯外庐的一个说法的批评,都是非常明显的例证。侯外庐1957年在为《中国思想通史》修订版所写的新序中,对其著作涉及的范围做了一个这样的说明:
“这部《中国思想通史》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一起编著的,所涉及的范围显得比较广泛,它论述的内容,由于着重了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说明,又显得比较复杂。”(注: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第7页引文。)
按照通常的理解,这段话的意思是很明晰的,并没有什么令人费解之处。可是,葛兆光在引了这段话后,却这样写道:
“在这里,思想史的思路反而有些混乱,‘思想史’的内容既包括了‘哲学’、‘逻辑’和‘社会思想’,又包括了‘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在这些词语内涵和外延都不够清楚的表述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思想史的困境,除了可以理解的当时的情景之外,思想史与哲学史、思想形态史、逻辑学说史等等的界限不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应该追问:思想史真的是可以包容哲学、意识形态、逻辑学说乃至政治、法律、科学的一个‘大历史’吗?如果是这样,那么科林伍德所说的一切历史都只是思想史就真的成立了,但是,又有谁能写出这样包罗万象的思想史呢?”(第1卷第7页)
只要稍通文墨、略知逻辑的人,恐怕都能看出:在这段话里,葛兆光对侯外庐原文的本义作了怎样的曲解!如果说,葛兆光对科林伍德的那个说法的曲解,主要是通过在转述中改变原文本义的方式进行的,因而表现得比较隐晦曲折,那么,他对侯外庐的原文本义的曲解,却是通过明目张胆地偷换概念的手法直截了当地完成的。侯外庐说“《中国思想通史》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一起编著的,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强调的是通史的综合性,是思想通史对各种思想(包括“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等等)的历史的包容性,这并不意味着他要把思想史当作“可以包容哲学、意识形态、逻辑学说乃至政治、法律、科学的一个‘大历史’”;侯外庐说他的思想通史“论述的内容,由于着重了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说明,又显得比较复杂”,这后半句话强调的也只是他的思想史的阐释框架,是思想史内容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关联(所以需要“着重”“说明”),而并不包含葛兆光所说的他要把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都统统“包括”在思想史的“内容”之中的意思。所以,葛兆光最后的那个石破天惊的“追问”,针对的恐怕只能是他自己,而不应该是受到他无端曲解的侯外庐和科林伍德。
在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第1卷《导论》中,除了对他人观点的曲解以外,我们还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空穴来风的说法。如其《引言》第二段中称:
“回顾现代学术史却可以发现,在近代中国,思想史这一名称似乎没有哲学史这一名称受青睐,或许,三分之一是因为西洋的‘哲学史’的现成范式给予转型期中国学术的方便,三分之一是因为‘哲学’一词的西洋意味在二十世纪前半期对中国学术的诱惑和挑战,还有三分之一是由于大学学科的划分中有哲学一系,因而需要相应的教材。……所以,翻开二十世纪的学术著作目录,以‘思想史’为名的著作似乎还没有以‘哲学史’命名的著作多,而且也不像哲学史的撰述,曾经经历过相当完整的过程,积累过相当成熟的经验。”(第1卷第3页)
葛兆光这样说,自然是为了凸显他的思想史写作在今天的意义,但是,在他的书中却根本找不到支撑他的这种说法的统计数据,相反,他在第六页的一个注里提到的通史性的中国思想史著作的数量就比他在正文中列举的中国哲学史著作要多得多。而且,这还不包括断代性的思想史以及各种分门别类的政治思想史、宗教思想史、学术思想史之类,也不包括八十年代以来新出的中国思想史著作,以及各个时期的海外学者写的各种中国思想史著作。当然,如果把中国所有大学哲学系所用的各种大同小异的中国哲学史教材都算进去,中国哲学史著作的总量或许是要超过各种中国思想史著作的总量,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是说明“思想史这一名称似乎没有哲学史这一名称受青睐”,还是说明思想史写作“不像哲学史的撰述,曾经经历过相当完整的过程,积累过相当成熟的经验”呢?如果说是前者,我想这一定是个笑话,如果说是后者,那也与事实不符。因为,“哲学史”本来就是“思想史”中的一个门类,只不过前者局限于哲学的范围,而后者则涵盖了整个思想领域而已。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学者胡适、冯友兰等人之所以以“哲学史”而不是“思想史”命名自己的相关著作,并不是因为“哲学”这个名词的西洋意味对他们产生了什么诱惑,而是因为他们研究的范围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而并没有涵盖整个思想领域。葛书中说:“很久以来我一直有一个很顽固的观念,我觉得用哲学史(History of Philosophy)来描述‘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如果不对西洋的哲学概念加以修改,严格沿用西洋哲学现成术语的内涵外延,多少会有些削足适履,如果不对中国的思想和知识进行一些误读和曲解,多少会有些圆枘方凿,所以,中国古代的知识和思想是否能够被‘哲学史’描述,实在很成问题。”(第1卷第5页)这话看起来很深刻,其实却只是一种无的放矢的鹦鹉学舌之辞,既没有金岳霖区分“中国哲学的史”与“在中国的哲学史”(注:金岳霖:《审查报告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中华书局,1961年新1版。)的意义,也曲解了葛书中这段话前面所引的冯友兰的那一段话的本意。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开头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可见,他在撰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材料是有选择的,而并没有像葛书中说的那样是“用哲学史(History of Philosophy)来描述‘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注: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第5页引文。)事实上,这也是任何人都不可能这样做的,因为,谁都知道,“哲学”这个概念并不能涵盖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学问,“哲学史”这个名称也不能涵盖包括思想史在内的各个历史学科,即使在“辩证法上高山”、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一切学问的年代里,也没有哪个哲学妄人声称要把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全纳入哲学的范围,或者曾经出现过“哲学音韵学”或“音韵学哲学”之类的名目。这是一个方面,也就是葛书所说的“名称”方面。
而从另一个方面(也就是葛书所说的思想史撰述的过程和经验方面)来看,葛书的说法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1、从历史渊源上来看,如果不计名目,而重实质,承认学案之类为学术思想史著作,那么,我们就得承认中国思想史研究有一个比中国哲学史研究更早的、更深厚的本土传统。2、即使仅仅从现代学术的范围来看,中国二十世纪的思想史研究也是“曾经经历过相当完整的过程,积累过相当成熟的经验”的。虽然以思想史为名的著作比哲学史著作出得晚,但是,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无论在规模、格局上,还是在成就和影响上,与哲学史撰述相比,它们都并不逊色。中国哲学史方面,胡适、冯友兰和任继愈的著作都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光就影响而论,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和李泽厚的三部中国思想史论著肯定不亚于它们,而从学术价值上来看,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则各擅胜场。至于海外学人的有价值的研究著作,更是不胜枚举。(注:事实上,光葛书两卷征引书目中提到的思想史论著就有数十种乃至上百种,可见作者还是对前人的思想史撰述经验还是有所取法的。)对于这些思想史著作的撰述经验,明智的思想史写作者是不会等闲视之的。更何况,哲学史研究本身就属于思想史研究的范围,哲学史著作的撰述经验,也同样可以为思想史研究者借鉴甚至取法。若不然,岂不是要“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吗?3、中国当代的思想史研究,虽然与哲学社会科学其它学科一样,长期笼罩在意识形态的阴影下,但是,它的发展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即使在文革时期,中国思想史研究也仍然以一种政治化的扭曲的形态(如所谓“评法批儒”)存在着,甚至隐然具有某种显学的位置,这与许多其它学科的凋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在文革以后,思想史研究也并没有随着其它学科的复苏和兴旺而相形失色,而是一直产生着相当大的影响,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思想史研究更是由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热中的一个重心转而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包括葛兆光本人在内的一些八十年代的学术新秀,就是在这种热潮中从其它领域转而进入思想史研究领域的。这是一个事实。那么,这个事实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是说明思想史研究冷落,还是说明它非常热门?是说明中国的思想史研究缺乏自己的学术传统,没有形成像哲学史研究那样可资参照的研究范式,甚至没有积累足够的经验教训,可以让有志于“重写”各种历史的时新学者们有所借鉴,还是说明某些学人自身知识准备不足,还没有真正找到思想史研究的门径呢?我想,这个问题是很值得深思的。
二
作为《中国禅思想史》等书的作者,葛兆光在思想史写作方面,并不是一个新手,他对思想史研究和写作的思路,还作过很多的思考。对于他的思想史撰述方面的一些“新的思路”,他自己显然是比较看重的,(注:要不然,也不会在《读书》上连篇累牍地讨论“思想史的写法”,并将其作为所著《中国思想史》的“导论”,还在后记等处一再提及。)许多评论者对他的《中国思想史》表示肯定,也往往着重于这一方面。(注:如在葛著《中国思想史》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朱维铮等人就盛赞其创意。而葛剑雄虽对其成就有所保留,但对其思路仍然比较肯定。他推荐《中国思想史》为“长江读书奖”候选著作,也是基于这个理由。)但是,从《中国思想史》第1卷导论及书中其它部分的有关论述来看,葛对思想史的理解和他的那些自以为新颖的研究撰述思路恐怕都是很成问题的,甚至是相当混乱的。在此,我们不妨首先看看他对思想史本身以及思想史与哲学史关系的理解。
在葛兆光看来,思想史的面目是模糊不清的,与邻近其他学科的界限也是不确定的。他在《中国思想史》第2卷《导言》开头这样写道:
“至今,思想史仍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领域,它的中心虽然清楚,但是叙述的边界却相当模糊,致使它常常模糊不清,也无法像它的邻近学科那样清楚地确立自己的边界,比如它与宗教史、学术史常常关注相同的对象,以至于它们总要发生‘领土争端’,比如它与社会史、文化史常常需要共享一些知识和文献,于是它们又总是要产生‘影像重叠’,比如它与政治史、经济史常常要建立一种相互诠释的关系,于是它们又总是要‘互为背景’,甚至产生了谁笼罩谁、谁涵盖谁的问题。这导致了它作为学科的基础和规范难以确立,就好像一个历史上四处游牧的部落在诸国并峙的地界乍一定居,很难立即确立它的领土和法律,也很难约束它的国民越界犯境一样。”(第2卷第2页)
后头又写道:
“……无论在实际的写作中,还是在学科制度化的建制中,还是在公众的理解视野中,‘思想史’仍然面目不清,实际上它依然面临一些窘境,仅仅是我现在关注的,就包括以下一些问题:第一,思想史究竟其意义在于确立历史上值得表彰的思想‘道统’,还是叙述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实际上,这个问题也就是追问,思想史到底属于思想,还是属于历史?第二,如果是后者,那么它所否应当确立它叙述的对象,在思想的历史中不仅有精英和经典,而且有普遍的、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在支持着社会生活,不仅有思想天才辈出的时代,还有思想凡俗平庸的时代,那么后者是否应当也纳入历史时间加以考虑?第三,如果要描述一个涉及范围更广泛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那么,思想史如何避免自身的漫无节制,并确实处理好它与社会史、政治史的互为背景问题?第四,思想史如何处理它与文化史、学术史的畛域冲突,换个方式来说,就是思想史有无必要划出一个明确的边界,以避免它与文化史、学术史之间的领域重叠?”(第2卷第4页)
在这里,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葛书原文,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避免断章取义之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两段话比较清晰而又系统地表明了葛兆光对思想史与其它学科关系的思考以及他对思想史学科定位的困惑。不可否认,作为一个正在重写思想史的学者,葛的上述言论都是有感而发的,也是经过了他自身的实践与反思的,并不是一些空泛的门外之谈或理论上的纸上谈兵,因而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严格地从学理上对这些言论进行分析,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上述说法的立论基础是相当薄弱的,其推论也是没有多少逻辑依据的。
众所周知,思想史的本义就是思想的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它诚然属于历史学的范围,但是,在历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之中,它与其它分支学科(如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等)的区别却是通过思想这个主题而体现出来的,更确切地说,是因为它以思想的历史进程作为特定的题材领域和研究对象,所以,它必然要从历史的角度探究思想的意义。对于思想史研究来说,思想价值和历史价值都是同样值得关注的。在思想与历史的归属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此其一。其次,既然思想史既属于历史,也属于思想,那么,它在“确立它叙述的对象”的时候,就必须兼顾历史与思想这两个方面的价值,确切地说,就是必须兼顾一种思想在历史上的外在影响和它自身在思想上的内在价值,而不能仅仅依据一种思想在历史上的外在影响确定它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更不能把平庸的东西与思想经典放在同等甚至更加重要的地位。其三,诚如科林伍德所言,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思想的领域是没有边界的,无论政治、经济、社会,还是灵与肉、有与无,一切事物(包括实体与空无)都是思的对象,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学科也都涉及到人的思想过程,并且必须以把握历史上的人的思想作为前提,因而,这些学科与思想史之间一定有着许多交叉重叠的领域。这是很自然的。但是,这种交叉并不意味着特质的消融,更不意味思想史没有自己确定的边界。正如其它学科也并没有因与思想史的交叉关系而消融掉自己的特质、取消本学科一样,学科分际始终是存在的。即使处理相同的原始材料,各个学科的方法和侧重点也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把握思想的特点是把思想因素分别纳入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进行描述,那么,思想史的特点就是把一切思想材料纳入思想自身的进程中进行描述。在思想史中,任何一种历史材料,都必须纳入到思想的历史进程中显示出它的意义,正如在政治史和经济史中,任何一种历史材料都必须纳入到政治或经济的历史进程中一样,这是思想史与其它学科的根本区别,也是学科分际之所在。不同的学科处理同样的题材,这谈不上有什么冲突。思想史要明确自己的学科定位以及与其它学科的分际,但要避免它与文化史、学术史等邻近学科之间的“领域重叠”,却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
至于说到“思想史究竟其竟义在于确立历史上值得表彰的思想‘道统’,还是叙述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我想,这个问题与“思想史到底属于思想,还是属于历史”的涵义应该是有所不同的。因为,无论思想史的意义在于“确立历史上值得表彰的思想‘道统’,还是叙述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它都必然要涉及思想与历史两个方面。而“叙述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与“确立历史上值得表彰的思想‘道统’”这两个目标也并不是截然不可相容的。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虽比较注重哲学方面,并隐然以儒学为道统,但其道统的确立却是在对思想的历史过程的叙述中展开的;又如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从当时流行的思想范式出发,比较注重确立中国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的“道统”,但是,他们也同样没有离开思想的历史进程来确立什么道统。更何况,注重思想的内在价值和理路,并不意味着就是要确立历史上值得表彰的思想道统。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著就很注重阐发各家思想在哲学或政治学上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它们并没有明显地确立某种思想作为道统,更没有把确立历史上值得表彰的思想道统作为自身意义之所在。事实上,在我看来,思想史的意义恐怕既不在于确立历史上值得表彰的思想道统,也不仅仅在于叙述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而是要在对各种思想的历史过程的叙述中,展示思想的“内在理路”和“外缘影响”(注:这两个概念都出自余英时。葛书对余内在理路说似有所辩证,其实却是以偏概全。参阅葛著《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第55-56页及余英时著《论戴震与章学诚》增订本自序(三联书店,2000年)。),确定思想的历史意义和内在价值。在思想史研究和撰述中,历史的尺度和思想的尺度是统一的,也是不可偏废的。作为一个思想史家,不但要努力获得对过去思想的真实的历史的理解,而且也要尽可能地对过去时代的各种思想的价值作出深入的分析和准确的评价。如果因为思想史属于历史而忽视它在思想上的归属,忽视从思想上把握各种学说的内在价值,甚至无力对平庸之作与思想经典的价值差别作出说明,那就不可能真正把握思想的历史进程。
葛兆光认为:“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可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因此,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的世界’,而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第1卷第13页)葛兆光提出“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的世界”这个概念,无疑是为了与“精英和经典的思想”分庭抗礼,但是,他对一般知识和思想的内涵的表述,却带有非常浓厚的精英化的色彩,如下面的这一段话:“我所说的一般思想,是指的最普遍的、也能被有一定知识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对宇宙间现象与事物的解释,这不是天才智慧的萌发,也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当然也不是最底层的无知识人的所谓‘集体意识’,而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作为一种普遍认可的知识与思想,这些思想与知识通过最基本的教育构成人们的文化底色,它一方面背靠人们不言而喻的终极的依据和假设,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理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起着解释与操作的作用,作为人们生活的规则和理由。”(第1卷第14页)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葛所说的“知识”和“思想”,与没有受过教育的底层民众是不相干的。底层民众拥有的关于农耕、渔猎以及气象之类的知识,在葛兆光的视野中,似乎并不属于知识的范围,因而也就没有被纳入他的思想史撰述的内容之中。不仅如此,葛兆光还认为“思想可能是少数天才的奢侈品,而知识却是所用受教育者的必备物”(第1卷第33-34页),这就基本上排除了在没有受过教育的底层民众中产生知识和思想的可能性。而事实上,人们都知道: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底层民众,与其它社会阶层(包括知识阶层)一样,也有一个自己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尽管与受过教育的其它社会阶层(尤其是专门从事知识生产的知识阶层)相比,他们的知识范围相对比较狭窄,思想格局显得比较小器,信仰形态也不免有些粗鄙,但是,从整个社会的“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构成以及对他们自身生活经验的适用性等方面而言,他们所拥有的这些知识、思想和信仰的价值却是别的知识、思想和信仰所不可代替的。如果把他们这一部分的知识、思想和信仰排除在外,那就不可能从整体上把握社会的“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构成,更不可能得出一个什么知识、思想和信仰的“平均数”来。对于这一点,过去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家如侯外庐等人其实比葛兆光认识得清楚,尽管他们的著作在葛兆光看来,都属于注重精英和经典的思想史的范围,但是,他们并没有像葛兆光那样,在知识和思想方面表现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教授对于没有受过教育的底层民众的傲慢与偏见,更没有出现葛的这种表面非精英而实质上却非常精英化的自相矛盾。这是一个方面(即对“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构成的理解)的问题。
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所谓“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方面的内容究竟应该如何纳入思想史撰述之中,恐怕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因为,思想史作为专门史,毕竟是以思想为研究主体、以思想发展为叙述的主要线索的,所以,它必然要把历史上的那些能够推动思想进展的精英人物以及那些能够集中体现一个时代的思想深度的经典之作作为关注的重点,而把其它方面的内容作为次要方面或背景材料。这也是过去许多思想史(特别是思想通史)之所以成为“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的原因所在。葛兆光不满于这种思想史撰述传统,试图撰写“思想的另一种形式的历史”,把“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作为思想史关注的对象,作为一种尝试,倒也未尝不可。可问题是:他对“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范围的界定却很不明确,更谈不上真正地把握古人的知识结构、以及这种结构与思想内容、价值倾向及信仰世界的关联。如果按照上面所说,一般思想只是受过教育的人认可的思想,那它在教育不普及、受教育者占少数的古代社会就不可能具有“一般性”。如果按照他在导论中的另一处的说法,把“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构成与影响分为“启蒙教育的内容”、“生活知识的来源”和“思想传播的途径”这三个方面(见第1卷第23-24页),那么,思想史又要怎样才能容纳如此庞杂的内容呢?思想的深度与广度、思想的背景与主体的关系究竟又应该怎么处理呢?从目前我们看到情况来看,葛书在这些方面的表现恐怕是不如人意的,也是与其初衷不相符的。即就“一般知识”的范围而论,葛书中涉及的知识领域也是比较狭窄的,不要说像涂尔干等人那样把握知识的“原始分类”,就离孔老夫子所说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也还差得很远。尽管作者按照专题形式对章节目录作了一些设计,并且“很费心思地在通常的思想史叙述中插进一些关于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章节”(第1卷第23页),但是,在总体上,葛书所处理的思想材料与过去一些思想史著作并无多大区别,论述的重点也仍是经典思想家的著作,只不过写法上作了一些变化而已。如果说这种变化有什么意义,那也无非是比较讨巧、别致一点,并没有达到转换范式、“重写”思想史的目的。
三
说到历史著作的“重写”,这里恐怕有必要对两种情况作一些分辨:一种是作者自己过去写过一种或数种,后来又另起炉灶,按照新的观点和方法,再写一部同类著作。如冯友兰早年以《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成名,中年写过《中国哲学小史》和《中国哲学简史》,晚年有了新的心得,又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这种情况大概可以算作狭义上的“重写”。还有一种情况是作者自己过去没有写过同类著作,但对他人著作不满意,于是写了一部,试图推翻前人定论,为后人树立新的范式,这也可以说是广义上的重写。八十年代以来学界流行的各种“重写”(包括重写中国文学史、重写中国思想史、重写中国文明史等等)的尝试,大多属于此类。后一种重写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也不难,不过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尺度太宽。不像狭义的重写有作者自己以前的同类著作可以作为对照,广义上的重写是与他人的同类著作相比较,作者自己过去没写过,现在无论怎么写,只要写出了一种,都可以说是“重写”。这是一个问题——对“重写”结果的评价和判定问题。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过去的研究成果和撰述经验。狭义上的重写者虽也往往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但因为自己过去毕竟作过相当的研究,写过同类著作,对过去的经验总不免有所凭借,纵或观点刻意求新,附会新说,在基本材料的处理和基本方法的运用上总不至于离谱太甚。而广义上的重写者则不同,他们以前没有尝到过这方面的甘苦,现在又急于出新,力图表现得不同凡响,这样就有可能会忽视前人研究成果和撰述经验,对学术传统缺乏尊重,甚至暴露出基于无知的傲慢与偏见。这个问题在葛书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作为一部追求“个人性”的标新立异的思想史论著,葛书在写法上下了相当大的功夫。有时候,为了突出自己的新写法的意义,他还不惜将其与传统的写法以至于学术著作的基本体例规范机械地对立起来。如他对按人分章的教科书模式的贬低,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思想史写作本不只有一种模式,按人分章论述的教科书只是一种。而且,好些教材的学术水准也并不比专著低,如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史》、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都是教材,可不妨碍它们成为名著。葛兆光不明就里,非要与那种平庸的千篇一律的教科书争一日之短长,而且在“讲法”和写法上纠缠不清(详见第1卷第59页),这除了说明自己的专著脱胎于讲稿以外,究竟又能说明什么呢?再者,按照常规,篇幅较长的著作一般都要分章列节,可是,葛兆光却声称章节妨碍思想的连续性,认为:“当思想史的结构被写作中的思想史安排为若干章节时,前一‘思想史’即真正存在于历史中的思想的历史就被隐没,而代之以后一《思想史》即写作者理解视野中的思想的历史,于是,章节就把历史切割开来,连续性在这些章节中消失了,而思想就被思想史家分块包装起来供读者任意采撷和阅读。”(第1卷第57页)在这里,葛兆光对章节表现出了一种非理性的恐惧,不过他的著作同样也分了章节,只是较为侧重专题而已。这种侧重专题的做法其实并不新鲜。胡适、冯友兰的两部中国哲学史中,就包括许多专题论述,并不都是按人分章的。葛书批评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的写作范式,可是,侯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注:此书写于1942年,1944年出版,今有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此书为《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的雏形。)就基本上是按专题撰述的,只要把此书的目录与葛书第1卷前几章的目录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两者在专题形式上的相似之处。而且,侯在思想史学上的主要贡献是把思想史建立在社会史基础上,在揭示思想与社会的关联方面,正是后学者如葛兆光等辈的前驱。它如以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亦有可循之例,如李济、张光直等对上古史的研究,就运用了人类学方法。葛兆光对此应该非常了解,可是,他在谈到人类学对上古的理解时,却偏偏只提及不熟悉中国历史的欧洲人类学家的研究,并且由此引出一个石破天惊的问题:“需要追问的是:第一,欧洲的人类学家真正考虑和了解了中国上古的世界图景吗?……至少我们相信中国的上古思想世界并不是世界其它地区早期思想的复制品”(第1卷第83页),似乎有哪个欧洲人类学家真的把中国的上古思想世界当成了世界其它地区早期思想的复制品似的。这种说法,说到底不过是虚设了一个低能的假想敌,以显得自己的平庸识见的高明而已。
葛兆光对中国思想史研究传统和撰述经验的忽视,不但体现在他对著作体例和研究方法的理解上,而且也体现在他所说的写作形式上。众所周知,任何一种思想史著作,都包括考证、述学、评价三个方面。其中,史料考证是第一步的工作,按照胡适的说法,“哲学史最重学说的真相,先后的次序和沿革的线索。若把那些不可靠的材料信为真书,必致(一)失了各家学说的真相;(二)、乱了学说先后的次序;(三)乱了学派相承的系统。”(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年2月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重印本,第11页。)所以,凡是严肃的史家,莫不重视史料的考证。可是,葛兆光却认为,“《思想史》在形式上可以有三种写法……第一种是‘确立事实’……;第二种是‘真理评价’……;第三种是‘追踪旅行’……”(第1卷第52-53页),把考、述、评三要素人为地割裂开来,试图撇开考证和评价,以所谓“追踪旅行”的方式撰写思想史,(注:葛书对其“追踪旅行”法作了这样的表述:“第三种是‘追踪旅行’,一些思想史家自信可以重建古代思想史的思路,他们尽可能体验古人的心情,尽可能理解思想的脉络,顺着时间的流逝,一一陈述思想的转换和衔接,他们‘顺着看’历史,想重新跟着思想的历史走一路。”(第1卷第55页))却“自信可以重建古代思想史的思路”,这只能说是一种异想天开的想法。要知道,“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注: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引自《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09页。)不“确立事实”,不进行“真理评价”,光是去搞什么“追踪旅行”,最多也只能对思想史获得一些浮光掠影的印象而已,又谈何“重建思想史的连续性”呢?况且,文献考订,著作系年,本来就是治史的基本功。今人没有过硬的考据功夫,在考证方面需要藏拙,在写法上需要避开考证以扬长避短或避重就轻,这都可以理解。但是,如葛兆光所说:“过去那种一定要把某种思想的发明权按照著作人分配,著作人一定要按时代先生列入章节的写法,常常为了著作者的真伪和先后,耗去相当大的精力,而且很可能把蔓延几代的思想皴染过程算在了一个人的身上。”(第1卷第60页)“在我写的这部中国思想史中,我按照我的理解寻找思想史的连续性脉络。在这部书中,没有按照人来设立章节,……也没有特别精确地把某种思想或某种说法算在某个思想家的年代,可能年代尺度是比较宽泛甚至宽大的,我总是只在比较长的时间段中描述着思想史的流程。”(第1卷第65页)一部以“个人性”相标榜的思想史著作居然可以忽视前人思想的“发明权”,从模糊的印象中重建思想史的连续性,而这种不重考据的随意性的写法,居然可以与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相契合,这只能说是一种以短为长的奇思异想而已。
葛兆光不但忽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传统和撰述经验,而且对于前人的重要研究成果也缺乏应有的重视。虽然葛书正文脚注颇多,引证颇丰,书后的“主要徵引书目”中又列了数百种文献,同时还做了“主要人名索引”,在形式上显得很符合学术规范,也很有文献基础,但是,对于一些关键性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作者却表现得相当轻忽甚至无视。例如:商周之际及商周两代的文化异同,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近世史家中,王国维、郭沫若、邹衡、许倬云等持“迥异说”,徐中舒、严一萍、张光直等持“微殊说”,两说并立,相持不下,至今未有定论。(注:参见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第1章绪论,人民出版社,2000年。)此乃学术史常识,葛兆光自然也应该知道。可是他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却把前一种观点当作学界的定论或成见,而把后一种观点当作自己的另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的印证和注脚,(注:请看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第1编第3节第一部分第一、二两段(第104-105页)的行文:“长期以来,思想史家对于殷商两代的思想与文化有一个很顽固的印象,即西周对于殷商来说,是一个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时代。……其实这并不可靠,……所以,我也一直有个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殷商其实是中国知识、思想和信仰的主流,而西周本来是西隅小邦,后来的发达只不过是继承了殷周的文化,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一样……”——在这里,另一种观点是作为对葛说的印证而带出来的。)这就难免给人造成著者力排众议、独特异见的错觉。而且,即使对前一种观点,书中的介绍也是很浮泛的。如对傅斯年和许倬云等人指出的周人克商后天命观的变化,尤其是“天命靡常惟德是亲”的观念的形成,(注:请看许倬云《西周史》第3章“克商与天命”,此书八十年代初版,1994年出版“三联版”增订本。)作者就没有注意到,所以,在论证“西周的思想世界与殷周的思想世界,实际上同多而异少”(第1卷第107页)这个观点时,作者就只能泛泛地举出三点“祭神祀鬼”方面的内容(即:“其一,各种祭祀大体上还是继承着殷商的传统,……其二,对象征性的厌胜、禁忌仪式,包括今人看来极其迷信、极端残忍的仪式,周人一样信奉敬畏,……其三,对‘帝’或‘天’的尊崇依然与殷商相似……”)作为依据。殊不知这三点依据即使成立,也只能说明殷商文化的某种连续性,并不能说明殷商之际文化思想观念没有产生剧变。更何况,前人研究已经指出,“由自然天发展出的天神,其性质当然不能与祖宗神的帝相同”,(注: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三联书店,1994年,第106页。)葛兆光不明此理,不知前人研究的精微之处,却想当然地以为“‘帝’的语源意义是生育万物,很可能以‘帝’这个字来表示生育万物的‘天’,是很早就有了的”(第1卷第91页),把“帝”与“天”混为一谈,谈来谈去也只能谈出一些庸常识见,又谈何重写殷周之际的思想演进史呢?
在我看来,葛兆光的所谓“重写思想史”,其实质无非是套用一些时髦的现代名词和流行的西学观念,如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福科的知识考古学及所谓后现代历史学之类,对中国古代思想传统重新进行叙述和阐释而已。换成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用“历史记忆的发掘充当思想资源和意义重新诠释的方式”。(注:原文为:“我以为用这种历史记忆的发掘、充当思想资源和意义重新诠释的方式,似乎可以综合影响和选择的交互作用。”(第2卷第29页),此处“发掘”与“充当”之间的“、”似不合语法,其意殊不可解。)如其《中国思想史》第1卷第二编第十节“语言与世界:战国时期的名辩之学”,从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对语言与世界关系的论述出发研究战国时期的名辩之学,对其做出新的阐释,这显然是一个新的视角,其新意是显而易见的。但问题是,这种富有新意的现代化的阐释实在离古人的思想实际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先秦诸子关注的焦点并不是抽象的思辨性的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而是与现实社会秩序密切相关的名与实的关系问题。尽管名与实的关系中也蕴含了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但是,人们当时关注这个问题的侧重点与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关注语言与世界关系问题的侧重点显然是很有区别的。比如说,葛兆光归纳的“语言能否真正切实地说明或如何说明世界?人们能否通过或怎样通过语言来调整世界的实存状态?人能否或如何超越语言而直探世界本身?”(第1卷第291页)这样三个问题,一看就是从现代西方语言哲学中引申过来的,而不是从先秦诸子的名实之辨中自然生发的。葛书中按照“对于语言的态度”,对孔墨老庄各系及惠施、公孙龙诸家进行分类,认为孔子及其后学“坚信语言可以说明世界”,老子基本上“不相信语言”,庄子一系“怀疑和蔑视语言”,如是所云,虽不无根据,却也有过度阐释之嫌,而且显得有些隔。兹举一例,即葛书对孔子“正名”的阐释:
“坚信语言可以说明世界的是孔子及其后人(注:按:“后人”一词不妥,当为“后学”。),他们关心的中心是社会,他们格守着传统的语言系统,希望社会秩序稳定在原有的语言系统上。所以,他们固执地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名’和‘实’的关系是天经地义的,是天然合理的,这种‘名’所确认的是一个合理的‘实’的世界,任何‘实’的变化都不应该改变‘名’的秩序。……孔子所谓的‘正名’就是希望通过对‘名’(语言)与‘实’(世界)关系的调节来整顿社会秩序,维护旧时代的‘名分’与新时代的‘等级’的一致性。在他们的心目中,尽管‘名’与‘实’并不一致,但是‘名’对于‘实’的规定性和调节性是必须肯定的,‘名’有永恒而稳定的意义,尽管时间流逝,世事转换,但‘名’决不可以变异。他们希望以这种‘名’维持传统的秩序的稳定和延续,而改变了的世界应当去将就这种秩序,换句话说,他们维护的是旧的语言系统对世界的规范和确认,而拒绝为世界的改变而改变语言系统,所以孔子有一句老话叫做‘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第1卷第293页)
这里,我们不妨对照一下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中的解释。在胡适看来,《论语·颜渊》中关于君臣父子的那一段对话很好地说明了“孔子注意到思想混乱与道德乖谬之间,失去‘正名’与树立道德法则及生活和谐的不可能性之间有不可分的联系。因为思想瓦解状态的必然结果是一切权利义务的崩溃,是社会及国家各阶层或阶级的一切正当关系与义务的完全消灭”,孔子所说的正名,“并不就是文法学家或辞典编纂者的任务,而是我所说的思想重建的任务。它的目的,首先是让名代表它所代表的,然后重建社会的和政治的关系与制度,使它们的名代表它们所表示的东西。可见正名在于使真正的关系、义务和制度尽可能符合它们的理想中的涵义。这些涵义,无论现在已变得如何含糊不清,仍然可以通过适当的研究和名的真正‘明智’的用法予以重新发现和再次确立。当这种思想重建最后生效时,理想的社会秩序就必将到到来”。(注:胡适:《先秦名学史》,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28-29页。)在先秦名学研究上,胡适1917年用英文撰写的《先秦名学史》实乃开山之作,葛书中相关章节虽无一语道及胡适此书及其观点,但有关论述与胡适此书的思路(甚至行文次序)颇有相近之处,所以可以对照着看。比如说关于孔子的“正名”思想,葛兆光与胡适一样都是从与社会秩序相关的层面阐释的,但葛的新说胶着于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只是强调儒家学说的保守性,而无视其理想的超越性,不如胡适的旧说妥帖,较有理据,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情境较相契合,亦可与他本人及我们所亲历的二十世纪中国“当代史”相印证。可见,思想阐释的关键并不在于观念、方法与视角的新奇与否,而在于原典解读和逻辑推理、义理辨难的功夫。在后一方面,时下的许多学界名流与胡适那一辈的差距是不可以道里计的。虽然他们现在提起胡适的学问,总不免有些轻薄,如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第2卷后记中,就调侃胡适写书只有上卷没有下卷的“那种只顾开辟新领域的气派”,(注:原文是:“我不是只写上卷不写下卷的胡适之,那种只顾开辟新领域的气派我学不会也没有资格学……”(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后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57页)。)殊不知胡适治学有乾嘉之风,颇重资料考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后,本来还想接着写中古与近世部分,但因为工程浩大,故先从资料长编与专题研究入手,写出了《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戴东原的哲学》、《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章实斋先生年谱》及《胡适禅学案》(为后人所编)等著作,(注:参阅吕实强:《胡适的史学》,耿云志编:《胡适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哪像现在一些时新学者,连基本资料都没有搜集好,原典都没有读通,就率尔操觚,撰写大部头的通史通论,以至于出现各种常识性的错误,犹以思路创新自诩。
有论者称:“葛兆光的《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1卷》讲思想史的知识,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区分,抛开思想历史中的义理辨难,算是文献史家作思想史的新路子。”(注:遇资州:《九十年代中国学术思想丛书漫议》,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年2月号,第51期。)此语褒贬之意,颇令人不解。因为:(一)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本来就很讲究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况且,思想史以研究思想的历史为务,对思想的义理辨难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又岂能轻易“抛开”了事?抛开义理辨难的“《思想史》”还能称为真正的“思想史”吗?(二)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并不以文献考据见长,尽管葛本人出自古文献专业,但是,从本文上面的相关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对文献考据是不那么注重、用力的。所以,以“文献史家作思想史的新路子”来表彰他,恐怕也是一种误解或错位。而在辞章方面,作为学术文本,我看葛书恐怕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如措辞随意,用词不当,概念表述不清,有时甚至逻辑混乱,不知所云,且常漫无边际地驰骋想象、抒发感想,显得像是读书随笔和抒情散文的混合体,而不是规范性的学术著作。如第1卷第一编第二节《卜辞中所见的殷人观念系统》中的这一段文字:
“对于祖先的重视和对于子嗣的关注,是传统中国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念,甚至成为中国思想在价值判断上的一个来源,一个传统的中国人看见自己的祖先、自己、自己的子孙的血脉在流动,就有生命之流永恒不息之感,他一想到自己就是这生命之流中的一环,他就不再是孤独的,而是有家的,他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在扩展,生命的意义在扩展,扩展成为整个宇宙。而墓葬、宗庙、祠堂、祭祀,就是肯定并强化这种生命意义的庄严场合,这使得中国人把生物复制式的延续和文化传承式的延续合二为一,只有民族的血脉和文化的血脉的一致,才能作为‘认同’的基础,换句话说,只有在这一链条中生存,才算是中国人。”(第1卷第95页)
在这段典型的抒情文字中,除了一些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以外,只有那种浮光掠影的印象和大而无当的感慨,即使把里面的“中国人”换成其它国家的人,话也照样可以这么说,意思也照样含混得很。而这样的文字在葛书中却是经常可以看到的,如所谓“宇宙是古代中国思想世界的意义和价值的来源”(第1卷第128页),“古代中国的人们最容易感受并且最能笼罩一切的,后来的中国人最容易习惯而又时时不离的,可能就是作为空间与时间的天地”(第1卷第45页)之类,都是一些大而无当的空泛之辞或不知所云的废话而已,经不起概念分析和义理辨难,甚至经不起文字语法上的推敲。试问:宇宙既然可以说是古代中国思想世界的意义和价值的来源,为什么不可以说它是古今中外一切思想意义的来源呢?人生宇宙之中,又有谁能离得开时间与空间呢?天地只是空间形态,又如何能“作为时间”呢?葛兆光在“以理工著称的清华大学”工作多年,对自然科学多少懂得一些,如今却在这种最基本的科学常识问题上犯迷糊,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以上所述,大多是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尤其是第1卷导论)中出现的问题,同时也涉及这些问题在葛书正文一些篇章中的表现,并不是对葛书的全面评价。葛书全文洋洋119万言,想必有其优长之处,足可为人称道。不过,既然他特别强调“思想史的写法”以及他的新写法的重要性,且亦以写法之新奇而引人注目,笔者在此以他关于写法的论述作为评论的主要对象,当亦不为过矣。当然,除了对写法的论述以外,更值得关注的是按照这种写法写出来的东西,是这种东西的实质性内容。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写法,在总体上给中国思想史研究究竟有没有带来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没有通盘研究,不敢遽下断语。不过,我想,在回答这个总的问题的时候,本文上面提到的各方面存在的具体问题恐怕是不容回避的。
而在上述这些问题之外,恐怕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是葛书对实质性问题的表面化处理。如在谈到“卜辞中所见的殷人观念系统”时,作者这样写道:“第一,引起我注意的,首先是殷商时代人心目中神秘力量的秩序化。”“第二,值得注意的是卜辞中所表现的祖灵崇拜及其与王权结合产生的观念的秩序化。”“第三,值得注意的还有祭祀与占卜仪式中所表现的知识系统的秩序化。”(第1卷第90-102页)而在谈到西周时代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变化(就与殷商时代的比较而言)时,他又这样写道:“西周时代,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切都在进一步合理化与秩序化过程中。”(第1卷第125页)葛兆光欣赏福科的知识考古学,对话语、权力与秩序的关系特别关注,他从秩序化角度把握卜辞中所见的殷人观念系统,固然不足为怪,不过,他把“一切都在进一步合理化与秩序化过程中”作为西周时代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却恐怕是太流于表面,而没有触及到殷周之际的实质性变化,如其他研究者所说的天命观的变化、神权观念的演化以及礼仪制度和宗法制度的变化等等。(注:参阅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我想,这或许正是作者过分注重思想史的写法而相对忽视义理辨难、忽视思想的实质性研究的结果吧。
标签:葛兆光论文; 思想史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中国思想史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哲学史论文; 历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