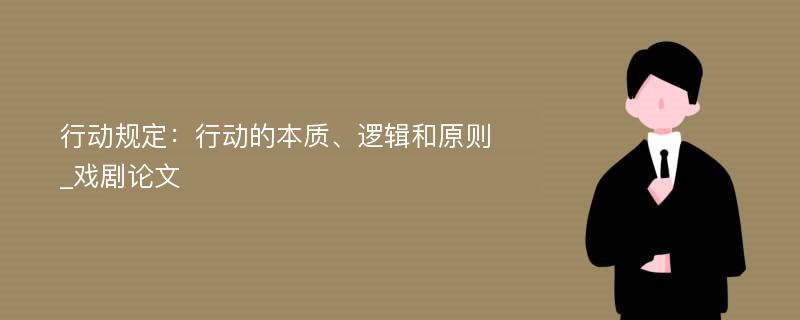
动作规定:动作的本质、逻辑与原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作论文,逻辑论文,本质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8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95(2013)03-0079-08
冲突是动作的本质。无论是戏剧动作还是电影动作,都要求前后统一,相对集中,流畅合理,动机明确,富含意义与冲突发展。在这里,冲突性是动作的最本质的要求。所以我们说,冲突是动作的本质,是动作得以存在的依据,更是动作得以发展的基本理由。动作的第一基本原则,就是冲突性原则。动作的本质意义是建构和组织冲突。所以,冲突是动作的核心意义所在和存在意义所在。
一、冲突:电影与戏剧的动作本质
冲突是一切叙事艺术的内在规律。在戏剧理论中,甚至冲突被认为是戏剧艺术的本质特征——“戏剧的本质”,其最早源自于法国戏剧理论家布伦退尔在《戏剧的规律》中的说法。其实,伏尔泰很早就提出,每一场戏必须表现一次争斗;黑格尔也是把“各种目的和性格的冲突”看作是戏剧的“中心问题”。一般认为,冲突是构成故事情节的基础与展现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实际上,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动作才是构成故事情节的基础和展现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等于是说,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同样,没有冲突也就没有电影。黑格尔说:“因为冲突一般需要解决,作为对立面斗争的结果,所以充满冲突的情境特别适宜于作剧艺的对象。”“只有当情境所含的矛盾揭露出来时,真正的动作才算开始。”[1]“每一个动作都有许多先行条件,所以很难断定真正的开头究竟从哪一点起。不过就戏剧动作在本质上要他齿及一个具体的冲突来说,合适的起点就应该在导致冲突的那一个情境里,这个冲突尽管还没有爆发,但是在进一步发展中却必然要暴露出来。”[2]
冲突是一切戏剧的主要力量,冲突也是一切电影的主要力量。“冲突是一切戏剧的主要力量;外在冲突在戏剧中是最感染人的因素;内在冲突则给予喜剧与悲剧以庄严并使其特征显著。一个剧本,只有当它一面离开闹剧的边缘,另一面又离开情节剧的边缘时,才会成为一部伟大的剧作;只有当它把外在冲突与内在冲突结合在一起时,它才会在舞台上与文学领域中获得成功。”[3]
戏剧总包含着冲突在内,电影也总包含着冲突在内。“事实上,一般对戏剧的认识便是:它总包含着冲突在内——角色与角色间的冲突,同一角色内心诸般欲望的冲突,角色与其环境的冲突,不同意念间的冲突。”[4]
戏剧的核心是冲突,电影的核心也是冲突。“一个环境,一个困难的问题或一个艰险的处境出现了,你必须与之冲突、斗争,以求得解决。所以戏剧的核心是冲突。一男一女在路上谈笑而过,没有人注意他们。如一男一女在路上相骂以至相打,大家便会围上来看看。因为它有冲突,有戏剧性冲突了。”[5]
“戏”,就是冲突。这是我们大家早已明确的问题了。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戏”,对于剧本创作的主题思想来讲,恐怕就是指戏剧的冲突是否真实、尖锐、复杂,有没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有没有典型意义。“戏”,对于一个导演来讲,最重要的,恐怕是如何把戏剧的冲突更鲜明、更强烈、更真实地表现出来,他应当抓到展开戏剧冲突的关键:情节。抓住了情节,戏剧的结构、节奏就容易掌握了。抓住了情节,人物的性格就容易把握了。抓住了情节,才有“戏”。“戏”,对于演员来讲,恐怕最重要的是表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纠葛中的各种复杂的思想感情。[6]
所以,电影与戏剧一样,“首先是一种叙事(讲故事)的媒介,通常的故事都包含着戏剧冲突,它们本身就是以正在进行着的文化冲突为基础的”[7]。这是电影性与戏剧性的动作冲突的共性。
最早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开始,人们就冲突性质与内涵的解释展开了不懈的追寻,但却众说纷纭。黑格尔强调“各种目的和性格的冲突”;布伦退尔把戏剧冲突看作是意志冲突,即人的意志与神秘力量和自然力量之间的冲突;劳森则把戏剧冲突的内涵引申为社会性冲突;而有些戏剧理论家主张戏剧冲突是人的性格冲突。在当代戏剧中,更有人主张用“抵触”代替“冲突”,即人物之间的冲突并不采取对抗的行动,而是和平的方式,如退让、妥协、容忍等,因而表现出的是一种抵触的方式,认为这是矛盾发展复杂多样的表现。
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冲突的性质与内涵主要表现为意志冲突和性格冲突两种。“人物之间的意志冲突是戏剧冲突最具体的表现,是一切冲突中最富于戏剧性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意志冲突包括正反面人物之间的意志冲突,也包括正面人物之间或反面人物之间的意志冲突。只要意志发生冲突就能构成戏。”[8]“一出没有性格的戏,就是一出没有一切真实性的戏,因为人之所以有这样或那样行动的动机,都归结于他的性格。”[9]
这也是戏剧的动作冲突与电影的动作冲突的共性——动作性的共有特性。
冲突,Conflict:To be in or come into opposition,对立或形成对立。《美国传统英语双解词典》:Conflict,Opposition between characters or forces in a work of drama or fiction,especially opposition that motivates or shapes the action of the plot.冲突,戏剧或小说中人物或势力间的对立,尤指推动或影响故事情节的矛盾冲突。冲突,它来源于拉丁文conflitus,可译为分歧、争斗、冲突,等等。在艺术中,冲突就是表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以人的内心的矛盾关系的特殊艺术形式。据此,我们认为,构成动作冲突的根本是关系,是人与人、人与物和人自身内心的关系的差异——关系的平衡与不平衡形成的矛盾冲突,因此,冲突的基本逻辑是关系逻辑,冲突的基本哲学是差异哲学。黑格尔就曾这样说过:“由于剧中人物不是以纯然抒情的孤独的个人身份表现自己,而是若干人在一起通过性格和目的矛盾,彼此发生一定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形成了他们的戏剧性存在的基础。”[2]249差异是冲突的源头和基本形态:动作冲突的基础是差异的结果。差异:外在形态的差异,本质性格的差异,内心世界的差异,行为动机的差异,等等。
惟其如此,我们说,冲突是关系的冲突,是人与人、人与物和人自身内心的差异关系的改变和重建。换句话说,冲突是关系平衡的打破与再次求得平衡的一个运动过程。美国的戏剧电影理论家约翰·霍华德·劳逊曾将电影冲突的特性说成是“运动中的冲突”,认为“电影在表现冲突时,为了争取达到某些可以理解的特定目标而进行奋斗的自觉意志,也必须具有足够的强度以能将冲突发展到危机点”[10]。劳逊对电影冲突的这种说法无疑是精到的。差异这种关系的平衡与非平衡,包括了人类所具备的一切精神与感情,展现了人类精神与感情关系的多样性:动机、意志、目标、欲望、性格、力量、命运,等等。
其实,冲突既然是人与人、人与物和人自身内心的关系的改变和重建,那么,关系的多样性,必然导致关系改变和重建的多样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冲突的性质是多样的,而也正是人类对存在世界的这种无穷多样性,对生存世界的这种无尽选择性,以及对精神世界的这种无比丰富性,人的“关系”的存在才会如此丰富多样。
泼拉斯就戏剧说过这样一句话:“突出性格的唯一方法是:把人物投入一定的关系中去。仅仅是性格,等于没有性格,只是随意堆砌而已。”[11]关系和关系的改变与重建,不仅是人物性格塑造的前提,也是情节赖以展开和发展的基础。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故事情节的单调和人物性格的单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关系的单调和单薄。所以,虽然一般认为,性格冲突是主要的冲突,但我们也不排除,意志冲突、欲望冲突、能力冲突、理念冲突、命运冲突、目标冲突甚至力量冲突,都可作为冲突性质的一部分。
有些学者认为,冲突展开的条件,根本上在于人物的性格,因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赋予了冲突展开方式的多样性。这种说法就一般意义上而言是对的,但不能绝对化。我们更注重的是人的关系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换句话说,对冲突而言,人物关系的独特性和丰富性要大于人物性格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所以说,人物依据与情境依据,性格依据与意志依据,事件依据与偶发依据,大事依据与小事依据,都可以说是冲突形成、展开和爆发的条件及依据。俗话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冲突运用与设置的高下好坏,与冲突的类型与依据,并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
其实,既然冲突是关系平衡的打破与再次求得平衡的一个运动过程,对抗和抵触就都是这一运动过程中的一种方式,进攻、斗争、坚持和退让、妥协、容忍等,仅仅是方式的差异罢了。
冲突的目的是制造动作的张力,正是因为冲突的存在,才使动作充满了张力。所以,无论是意志冲突、性格冲突,还是欲望冲突、理念冲突,都是因差异性的对比形成动作的动力和张力,然后才奔向高潮,直至矛盾和危机的解决——人与人、人与物和人自身内心关系平衡的打破与再次求得平衡的动作的最终完成。换句话说,张力是冲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关系平衡的打破与再次求得平衡的一个运动临界状态,所以张力构成向度性冲突。
冲突的基本模式可分为:选择结果型: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冲突目的/动机/目标,最终只能达到/实现其中一个。回避结果型: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冲突目的/动机/目标,最终只能回避/避免其中一个。选择回避型:对一种冲突目的/动机/目标,既想达到/实现又想回避/避免。
依据冲突的力度和强度,可分为:主要冲突与次要冲突,贯穿冲突与阶段冲突,大冲突与小冲突,铺垫性冲突与爆发性冲突,递进性冲突与解释性冲突等。
依据冲突的类型,则可以分为:铺垫性冲突、解释性冲突、递进性冲突、阶段性冲突、关键性冲突、逆转性冲突、爆发性冲突等。
一般讲的“突转”,可看作是逆转性冲突,“发现”可看作爆发性冲突。
动作的断裂是关系差异的放大和极致化的结果,其表现为强刺激冲突。因此,对影像动作来说,没有差异的动作断裂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产生不了动作的推动力和张力,不能驱使动作向前发展。劳逊曾提出:“戏剧的基本特征是社会性冲突——人与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个人或集体与社会或自然力量之间的冲突;在冲突中自觉意志被运用来实现某些特定的、可以理解的目标,它所具有的强度应足以导使冲突到达危机的顶点。”[10]213“由于戏剧是处理社会关系的,一次戏剧性冲突必须是一次社会性冲突。”[10]207讲的正是本质上的冲突与社会的关系。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通过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才能真正认识人的本质。更重要的是,只有把社会的矛盾集中凝聚在人物性格的冲突上,才能构成引人入胜的戏剧冲突。所以,不管是人与人、人自身内心的冲突,还是人与物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社会矛盾或危机的反映,也必须具有社会意义。但需要注意的是,社会意义并非是社会重大事件或重大矛盾的同义词。
这就是:冲突的存在形态并不是生活的自然形态,而是经过艺术的选择、集中、加工、概括和提炼后的冲突形态,因为生活中存在的人与人、人与物和人自身内心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它是散漫和凌乱的,而且往往还与非关系的人与物纠缠在一起,所以只有经过艺术的梳理与加工,它才有可能成为艺术中的冲突。
然而,正是因为戏剧与电影在媒材(艺术用材)和技艺上的区别——艺术的选择、集中、加工、概括和提炼的区别,才造成了两者在冲突形态、展开与解决上的差别。可以这样说,虽然戏剧动作与电影动作的本质都是冲突,冲突的基础也都是关系的差异矛盾,但在表达上却并不相同。
其一,在动作冲突形态选择上的不同。
冲突在戏剧与电影中的形态方式,都可以分为三种:外部冲突,即人物之间的冲突;内部冲突,即人物自身的内心冲突;人外冲突,即人与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之间的冲突。在戏剧中,动作的冲突由于受到“表演动作”的舞台限制,基本上都发生在人与人之间,或者是人物自身的内心冲突之间。但在电影中,冲突却可以发生在人与非人之间——与大火、龙卷风、火山、地震、陨石及其他任何非人类的冲突。并且因为影像的“无所不能”的特点,在表现人类与存在世界之间的矛盾关系方面的冲突,更是“如鱼得水”,将戏剧动作所不能也不允许的方面,展现得无以复加。所以,我们说,在动作的冲突形态选择上,戏剧是有限的选择,电影却是无限的选择。以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为例。《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取材于《丹麦史》、《悲剧故事集》和一个失传的哈姆雷特旧剧。通过麦王子哈姆雷特揭露其叔父克劳狄斯毒死父王,盗娶母后,篡夺王位的故事,表现了人与人的冲突。《哈姆雷特》于1603年以前首演后,就被改编成无数的其他艺术样式,如舞剧、广播剧,甚至中国戏曲的各种地方剧种,如越剧《王子复仇记》。电影被发明后,先后已被改编成的较成功电影,就有包括中国电影《夜宴》在内的不下数十部影片。
但对一些人与自然的冲突为主题的电影科幻片、灾难片、神怪片,甚至战争片来说,如《后天》、《2012》等,就很难改编成戏剧在舞台上演出。这就是戏剧与电影在动作冲突形态选择上的不同。例如世界级动画大师宫崎骏的动画世界,除了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矛盾外,如《天空之城》(1986)、《萤火虫之墓》(1988),在其感官世界中最叹为观止的就是表现人与自然(存在世界)的矛盾关系。在《风之谷》(1984)中,描写了一个被人类几乎毁灭的世界;在《幽灵公主》(1997)中,表现了一个被贪婪的人类因没有节制的开采铁矿而导致世界被毁灭的悲剧。显而易见,宫崎骏对自然——人的存在世界的敬畏,展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不平衡关系的这种冲突,只有在造型影像的世界中,才得以实现。
其二,冲突在动作变化上的差别。
冲突的解决引发的是动作上的转变——突转(激变)与渐变。突转,一般指剧情向相反方面的突然变化;发现,则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这是两种戏剧性的表现技法。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提出,突转与发现是情节的主要成分。在实践中,发现通常与突转相互联用或同时出现,以此造成情节的激变。例如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由于报信人无意之中透露真情,俄狄浦斯才发现自己的罪孽,由此导致剧情急转直下,最终弄瞎双眼,自我放逐。激变/突转是戏剧动作的最主要的形态和功能之一,有些戏剧理论家甚至将之称为戏剧艺术的本质。英国戏剧理论家威廉·阿登尔就认为,戏剧是一种激变与突转的艺术,小说则是一种渐变的艺术。
我们可以将之稍作扩展:如果说,戏剧是一种激变/突转的艺术,小说是一种渐变的艺术,那么,电影就是一种激变与渐变交叉结合的艺术。
其三,动作冲突在特征上的差异。
戏剧动作的冲突特征主要体现在情节性与言语性上,电影动作的冲突特征却主要体现在身体性与(身体)延伸性——外部动作上。就这种意义上说,电影的动作冲突充满了视观性,不仅将冲突的发生、高潮与解决都放在外部动作上,其动作的力度、幅度、强度和速度,都是戏剧动作所无法比拟的。譬如电影的环境与景色的描写——用影像表现,其与文学和戏剧舞台描述的最大差别就是动作性:电影影像的环境和景色,其动态的画面和运动性的构图,本身就带了很强的动作张力。特别是电影动作片中的“动作”,可以说是影像动作的最极致的表现——力度、幅度、强度和速度上的极致。可以这样说,动作片中的“动作”,如飞车追杀,是冲突上力度、幅度、强度和速度上达到极致的呈现:用极致手段造成平衡状态被破坏后的极致动作。飞车追杀从关系的高度紧张,到爆发式的平衡关系的被破坏,再到车毁人亡或追杀失败而形成新的平衡,过程中的动作强度越强,时间越长,幅度越大,速度越快,则动作冲突的张力就越大,动作的紧张度也就越高。动作的这种正比例关系,大概也只有电影的影像动作才能做到,这也正是电影艺术的魅力所在。
电影《黑客帝国》中的飞车追杀场面,可以说是个典型案例。在《黑客帝国2:重装上陈》中,为了表现双方力量的势均力敌,摄制组专门花了300万美元“制造”了一条高速公路,在这条短短的高速公路上,一切飞车的绝技全部“亮相”,飞车“动作”的速度、幅度、强度和力度,可说是“影无前例”,而且整段公路飞车追杀戏,时间超过14分钟,时间之长也是“影无前例”——全剧的矛盾冲突,因动作的紧张刺激而达到了最高潮。
二、视点:电影与戏剧的动作辩证
任何艺术都是叙事的艺术,“因为叙事是一种跨媒介的属性:除了电影叙事之外,许多艺术媒介的作品都有叙事。叙事性作品包括一些舞蹈、音乐作品和绘画以及几乎所有的连环画和文学”[12]。每一个叙事从定义上都是被叙述的叙事,即被叙述性地呈现的,而叙述性的呈现在概念上就必须有一个叙事者存在,因为叙事就是讲故事,讲故事就要求有一个故事的讲述者。
这就是叙事视点——叙事的动作视点,叙事的基本动作逻辑。“在一部叙事影片中(并不是所有的影片都会讲故事),视点(point of view)非常重要,视点表明是谁在讲故事。”[13]毋庸置疑,叙事人在讲述故事,在讲述或显示“动作”,对电影和戏剧的叙事来说,是基本一致的。但由于电影是镜头的影像叙事,戏剧是表演的戏像叙事,媒介属性的不同导致了电影与戏剧在视点叙事上的差异。“在电影哲学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我还没有提及,但是我现在将细致地考察它:最广泛地讲,这个问题涉及电影叙事和其他叙事性艺术中叙事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电影是否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叙事,并以此区别于其他艺术?或者,在电影和其他艺术的叙事能力之间是否有着强烈的相似性?”[12]199
这就是,在一定意义上说,电影的叙事视点是“给定的”,因而是不固定的,戏剧的叙事视点是“非给定的”,反而倒是固定的,两者表现出了决然相异的差异性。有一点需要说明,对电影是否存在“叙事人”,电影学界却一直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左的观点:对称论题观点的“有”与不对称论题观点的“否”。
对称论题的观点认为,电影与一切艺术样式,甚至文学相同,存在着叙事者,即讲故事的人,它包括叙事者,暗含的作者以及代理人,来传达情节和观点以及与故事的关系。“对称理论家认为,在这两种媒介中(指文学与电影),这些结构特征是一样的,而仅仅是叙述的交流模式不同——电影用显现叙事,文学以讲述叙事。”[12]199
不对称论题的观点认为,叙事者在文学中是无处不在的,然而在电影中却难以找到。“电影叙事并不是以文学叙事的方式来传达的。不对称理论的解释,可能从两种媒介的不同交流模式方面来提出,因此与对称观点不同,不对称观点认为交流模式确实影响叙事的结构特征。”[12]200认为因媒介的不同而导致电影不存在“叙事者”。
贝利斯·高特甚至讨论了电影中三种“暗指的作者”(叙事者作为不可见的观察者、叙事者作为向导和叙事者作为图像制作者)的不可能性。“暗指的作者”指的是“暗含的电影叙事者”。“这种叙事者被认为是把电影作为整体来叙述,而不是明确出现在画外音中或作为角色出现在电影中。既然他们把电影作为整体来叙述,而他们的声音却听不到,他们就被认为是视觉叙事者,以某种方式制作便于我们观看的景象或图像。相信这种实体的人常常认为,即使有一个明确的叙事者,这样的暗含叙事者也能找到;暗含的叙事者站在明确的叙事者背后,控制后者从中现身的故事。”[12]200所以,“作为电影叙事的一般说明,叙事者作为图像制作者,连同另外两种模式,都应该被摒弃。”[12]206贝利斯·高特否认电影中“暗含的电影叙事者”普遍存在的理由,是“因为电影是视听媒介,而小说是词汇媒介”,所以作为“暗指的作者”的“视点”在电影中是不可能存在的,而这种“视点”的存在,只能是荒唐和愚蠢的。
这是因为,“假定一个镜头是从一个房间的天花板拍摄;那么,我就必须虚构地被粘在天花板上。我如何到那里,我又如何待在那里呢?如果一个镜头从外太空拍摄,我就必须虚拟地待在那个点上。我是否要想象自己穿一件使我继续活着的太空服飘浮在外太空呢?当一个镜头片段从一个地点的镜头变到完全不同的地点的镜头时,我是否想象我有力量瞬间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而且在其他情形下,似乎我必须想象不仅是荒唐的东西,而是全然矛盾的东西:比如,如果一个电影中的谋杀被表现为不可见的,那么我必须想象我看到了不可见的某事。”[12]203很显然,这种解释缺乏足够的理由与依据。
其实,讲故事的人——“叙事者”,在电影中屡被质疑,在戏剧中却鲜被提及,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电影摄影机与放映机的存在,并进而造成了电影与戏剧在动作叙事视点上的差异。“电影中,总有一个片头字幕以外的角色,这就是摄影机。在摄影机表现得无所不在的时候,它的行为很像一个无所不在的作者。”[14]所以,我们说,正是因为“摄影机”的存在,摄影机镜头成为了电影的叙事人视点:叙事者的“眼睛”作为影像动作叙事的视点——电影的叙事“眼睛”。可见,视点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摄影机的位置有关。“我们要了解摄影机拍摄动作的不同方式,也就是不同的电影视点(cinematic point of view)。”[15]
换句话说,由于电影的影像是摄影—放映镜头的呈现,所以,在电影中,叙事者的讲述必须通过“镜头”的显现。因此,叙事者在电影中实际上“化”成了摄影和放映的“镜头”——“镜头”就是电影叙事者。而观众在观看电影时,观看的视点只能是“镜头”给定的视点,在这里,观者的眼睛与镜头是“重叠”的,它只是将摄影——放映的镜头所“见”重复了一次。“摄影机从哪个位置、通过何种‘眼睛’观看动作?”[15]116从这一点引申出去的是:一部影片无论有多少拷贝,在多少影院放映,观众的前后左右的座位有多少差异,观众所“见”是完全一样的,是镜头所“见”,也是叙事的动作视点——叙事“眼睛”所见;影片的后期剪辑和数字化生产所发生的影像的呈现,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是摄影——放映的镜头“模拟”。
从这种意义上说,叙事者作为不可见的观察者、叙事者作为向导和叙事者作为图像制作者的说法,都是可行的,是对电影“叙事者”的不同理解与解释而已。
与电影相比,戏剧则是完全由演员当场表演的“代言体”叙事,观众的眼睛不需要经过“镜头”的“重叠”:同一个动作在舞台表演时不可能用不同的视点“表现”,因为没有“镜头”的中介,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同一个场面可以使用一个或多个视点来表现。”[13]311对电影是来说是常态,是基本的表现手段之一,对戏剧来说则是难以置信的。“在小说中,叙述者往往就是作者的代言人;但是在电影里,叙述者却很少是电影创作者的代言人,叙述者往往是一个角色,通常是故事中的主要角色。”[16]
博格斯和皮特里在《看电影的艺术》一书中,将电影的动作叙事视点分为四种:客观视点(摄影机作为旁观者)、主观视点(摄影机作为动作的参与者)间接主观视点和导演诠释视点。其实,导演诠释视点始终“隐藏”在客观视点和主观视点之中,而间接视点则是客观视点与主观视点的互为转换过程而已。正如贝·迪克所说:“小说和电影中的第一人称叙事之间是有区别的。在一部影片中即使用第一人称叙述,它也用第三人称来表现戏剧性的情节。影片中的‘我’在简短的引进之后,就开始展现戏剧性的情节,于是这个“我”就变成一个‘他’或‘她’了。在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始终是一个有意识的叙述者,因为他或她总是说‘我’。在影片中只在叙述的开头和结尾有一个有意识的‘我’,因为此其间的一切都是戏剧化了的。”[14]586而真正需要提及的是“自身”视点,这是电影声画结合产生的特有视点。
在一定意义上说,客观视点也称作全知镜头,主观视点也称作主观镜头。客观视点(全知镜头)将摄影机当作一扇窗,“窗户外边的观众看里面的人物和事件。观众能够看到那些动作,好像它们在一定距离外真的发生了一样,但观众并不能参与进去。”[15]117所以,客观视点(全知镜头)又被称作“物理视点”,“物理视点,通过它我们看见场景,即所见,它可以零视点,不与叙事中的任何人物相关或者内部视点(通过某人物来看)。”[17]客观视点不让观众卷入影像动作中,意在强调动作的“纪录性”,“好像摄影机仅仅在尽可能直接地记录故事人物和动作而已。”[15]117其目的是让观众忘掉摄影机的存在。
但在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即使是客观视点,摄影机位也可能“站在”一个人类所无法实现的位置或角度的观看,譬如房间的天花板,几千米的地下,甚至人体的内部,这也是与戏剧的“全知”观看不同的视点观看。“尽管经典分镜力求采用理解故事的最佳视点,观众仍然不可能真正全知,因为剪辑、取景和场面调度都会参与抑制和控制故事的信息流。因此,不单需要通过观众的全知目光,更需通过影片叙事而去营造悬念,激发观众对故事进展的兴趣。确实,叙事者对观众视点的引导可以成为影片主要戏剧性视觉元素。”[18]
在这种意义上说,客观视点(全知镜头)实际成了“叙事者”的代言者。
主观视点,或称主观镜头,也被称作“内部视点”,热奈特称作内部聚焦,若斯特称作内部视点化。这种手法是将摄影机放在影片中某个人物的位置,使观众感到眼前所见的是该人物的视角观看范围。“主观视点提供的是参与动作的剧中人物的视点,并带有人物的主观情绪。”[15]118所以,主观视点或称主观镜头,实际观者是以影片中的角色的“眼睛”来观看,其实就是角色的视点。“一般而言,这个视点通过摄影机的运动得到保持,迫使观众观看剧中人物看到的东西,感觉自己仿佛成为了人物一样。”[15]118主观视点(主观镜头),与客观视点不同,是将影片中的角色当作了“叙事者”的代理人——从角色的视点来叙事,它不仅“迫使”观者卷入角色,甚至“迫使”观者卷入视点的动作之中,从而带来电影特有的观看“异样”感。
“自身”视点是用电影的特有的影像手段,通过自身的视点来“观看”自身角色,是一种主观视点中的再视点——视点中的视点,实际上是以自己的视点来观看自己的身体。在这里,声音与动作的分解,使声音成为叙事的视点,来观照动作的角色。
这是因为,在电影中,制片、剧作者、导演、演员、剪辑等,作为影片的创作者,创造的代理人“叙事者”,几乎不可能不显身。譬如小说《格利佛游记》中的“叙事者”格利佛,是作者斯威夫特“叙事”的代理人,小说是靠格利佛的航海日记构成的。放在电影中,如果格利佛不出现在画面中,就构成角色不在场的客观视点或主观视点——要么成为“全知”的客观视点,这时影片创作者与代理人“合二为一”;要么成为主观视点,依格利佛的视点看其他人物动作与情节。而如果格利佛出现在画面中,则构成角色在场的客观视点或自身视点——前者是影片创作者与代理人“合二为一”的“全知”视点,后者是主观视点中的再视点,格利佛要观众透过他自己的视点来“观看”格利佛:代理人是如何通过展开情节叙事的,“往往有一个暗含的电影叙事者,我们通过他的眼睛看到情节”[12]200。
我们以影片《肖申克的救赎》为例①。瑞德是影片的主角之一。我们“认识”瑞德这位影片的角色,及他在影片中的动作,是通过多元的视点来完成的:客观视点、主观视点和自身视点。客观视点,作为无所不在的摄影机呈现的是:瑞德作为剧中人(角色/表演者),作为被叙述者出现在电影画面中。主观视点,我们通过影片中的其他在场角色“观看”瑞德,譬如银行家安迪,或者假释官眼中的瑞德,甚至是其他角色“嘴”中(言谈)的瑞德——这时的瑞德是作为被叙述者而不出现在电影的画面中。
自身视点,瑞德被获得假释后,有异端克服心理障碍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通过画面与声音的紧密结合,视点从主观到客观视点的转换来完成的,实际上画面上的瑞德动作与身体,是他自身叙述的结果——瑞德作为叙述者(讲故事的人),用画外音在讲述他自己的情况,但他作为剧中人又出现在电影画面中,观者也知道他作为剧中人存在,这实际上是一种主观视点的再次内视化。最后,他找到了安迪为他留下的礼物,并克服了假释后的心理危机,找到了安迪。两个朋友最终相遇。
又如在影片《假如爱有天意》②中,通过角色(梓希)在场“讲述”的客观视点,转换到角色在场的主观视点,最后成为角色在场的自身视点——从梓希的视点“观看”她与尚民的自身恋情。当然,“在整部影片中始终保持纯粹的主观视点几乎不可能”[15]118,所以,都是几种视点的交叉、融合与结合。而这种多向度的视点,增强了电影叙事的力量——强度、深度与表现力,“这种手法大大引发了观众的认同感,重现了对摄影机最初的认同(我们认同摄影机的眼睛,它同时也是人物的眼睛)。”[17]19
在电影中,视点更确切地说来自“被观看者”。摄影机展示给观众的往往并不是场景中某个特定的人看到的东西,因为摄影机设置的视点只是为了营造一种视觉的真实感而已。[19]例如影片《莫扎特传》③通过剧中人萨列里的视角和夹叙夹议,向我们展现了这位把优美与纯净带给人间的音乐大师短暂而充满华彩的音乐人生。这一独特的富有表现力的叙事视点,将这位“上帝所钟爱的人”的多重性格和才华横溢却不谙世事的不幸遭遇,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当莫扎特脸色苍白地躺在床上,竭尽全力对萨列里随口谱写《安魂曲》,而萨列里虽然使出浑身解数,尽全力抄写,却仍然跟不上莫扎特喷涌而出的天才旋律,使影片冲到了悲剧高潮,更表达了上帝的“公平”:上帝给予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天才与痛苦是等量给予的。
不管是戏剧还是电影的“叙事者”——剧作者还是导演,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藏匿在舞台或者影片的每个角落中,通过某些不易觉察的方式表白内心。在很多时候,这种表白是没有“视点”的表白,我们甚至找不到“表白”的叙事者。所以,“认知视点,即所知,有时又叫做叙述视点。”[17]70但由于戏剧与电影在动作与身体的显现上视点表达的不同——戏剧是单元的,电影是多元的,使戏剧的戏像动作,戏像身体,与电影的影像动作——影像身体,具有了两种完全不相同的美学途径与美学效应。
注释:
①《肖申克的救赎》,编剧弗兰克·达拉邦特、斯蒂芬·金,导演弗兰克·达拉邦特,主要演员摩根·弗里曼、蒂姆·罗宾斯。美国,1994年。
②《假如爱有天意》,又译作不可不信缘、缘起不灭、爱有天意。编剧、导演郭在容,主要演员孙艺珍、曹承佑、赵寅成、李基宇等。2003年,韩国。
③《莫扎特传》,编剧Peter Shaffer、导演米洛斯·福尔曼,主要演员默里·亚伯拉汉、伊丽莎白·贝里奇、汤姆·赫尔斯。美国,198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