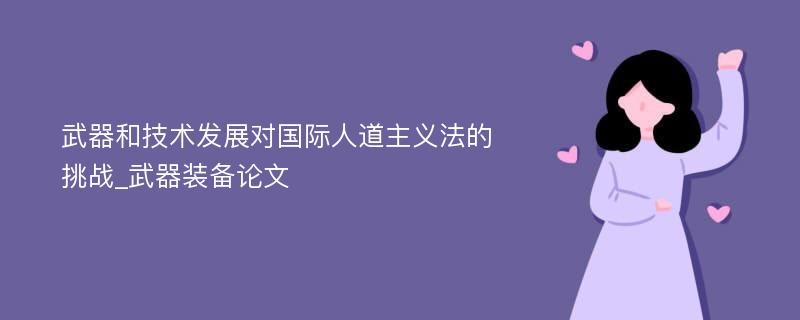
武器和技术发展对国际人道法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发展论文,人道论文,武器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5815(2005)01-0070-04
国际人道法必须随着可能转变为对人类敌对使用的任何科学的发展而发展。面对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和作为它的物质形态的新式武器的不断涌现以及由此引发的世界新军事变革,肯定和分析国际人道法对武器和技术的控制,认识武器、技术发展对国际人道法的挑战,探讨强化对新武器、新技术的国际人道法控制,是摆在世人面前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
一、国际人道法对武器、技术的控制
国际人道法不仅仅是为战争受害人提供直接救护和保护的法律,它还包括限制作战手段和方法的内容。在历史上,限制作战手段和方法的法律,是通过海牙公约发展起来的,被称之为“海牙法”;直接保护战争受害者的法律,是通过一系列日内瓦公约发展起来的,被称之为“日内瓦法”。过去有一个时期,把国际人道法仅仅限于“日内瓦法”的范围,占了主导地位。今天再坚持这样的观点,已经不合时宜。[1]其一,一些海牙公约自身就包含着人道保护的规则。比如,两次海牙会议订立的《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其中第一编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就是专门规定保护战俘、病者和伤者的,第二编中的第27条,规定了对宗教、艺术、科学和慈善事业的建筑物、历史纪念物、医院和病者、伤者集中场所的保护;第三编规定了对被占领区居民的保护。其次,限制作战手段和方法,目的是减轻战争灾难,实现战争中的人道要求。《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规定一切限制作战手段和方法的规则,都是“出于在军事需要所许可的范围内为减轻战争祸害的愿望而制订的”。避免使用超出“军事需要所许可的范围”的作战手段和方法,防患于未然,是对受到或可能受到战争伤害的人员和财产最好的救护和保护。再次,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的1977年附加议定书,已经把所谓“海牙法”和“日内瓦法”这两个法律分支联系起来,整合为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就是现时通称的国际人道法。对此,国际法院在应联合国大会要求提供的“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是否合法”的咨询意见中说得很清楚:“传统国际法上所称呼的‘战争法规和惯例’,部分地以1868年《圣·彼得堡宜言》和1874年布鲁塞尔会议为基础,是人们在海牙进行编纂(包括1899年和1907年海牙公约)的结果。‘海牙法系统’,更准确地说,《陆战法规和惯例的章程》规定各方交战行为的权利与义务,并限制其在国际武装冲突中杀伤敌方人员所使用的手段和方法。除此之外,还有旨在保护作战部队的伤、病员和不参加敌对行为,即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法系统’(1864年,1906年,1929年和1949年公约)。这两个武装冲突中适用的法律体系互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逐渐发展成为今天被称之为‘国际人道法’的单一的、复合的法律体系。”
时至今日,我们没有理由再坚持把限制作战手段和方法的内容再排除在国际人道法之外。
国际人道法对作战手段和方法的限制,主要是通过对武器和技术的控制来实现的。武器本身就是技术的物化,把武器用于作战,既是技术的应用,也是应用的技术。因此,国际人道法一开始就十分注意对武器和技术的控制,而且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重视武器和技术的控制。
国际人道法对武器、技术控制,开始时主要着眼于禁止现有武器的使用。1868年《圣彼得堡宣言》,放弃使用任何轻于400克的爆炸性弹丸或是装有爆炸性或易燃物质的弹丸;1899年海牙会议的三个宣言,禁止从气球上或用其他新的类似方法投掷投射物和爆炸物,禁止使用专用于散布窒息性或有毒气体的投射物,禁止使用在人体内易于膨胀或变形的投射物;1922年和1925年签订关于在战争中使用潜水艇和有毒气体的条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都是这一思路的产物。以后,国际人道法对武器、技术控制,由禁止现有武器的使用到禁止其发展、生产、储存及销毁。1972年《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1993年《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1997年《关于禁止使用、存储、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是这一发展的积极成果。国际人道法对武器、技术控制,同时还向着过去和未来的方向发展;向着过去,解决遗留武器的危害问题。“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了销毁遗留化学武器。“特定常规武器公约”规定,停止敌对行动后清除、排除、销毁雷场、雷区、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特别是2003年通过的“关于战争遗留爆炸物的议定书”,提供了解决所有在冲突后仍然威胁平民居民的爆炸性弹药的法律。向着未来,未雨绸缪,解决新武器、新技术超出“军事必要”的伤害问题。1977年《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是一个这方面的成果。更为重要的,是1977年“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36条,它规定了对“研究、发展、取得和采用新的武器、作战手段和方法”进行合法性的审查。上述简要的叙述表明,国际人道法对于武器和技术,从战中、战后和战前三个时间维度,从使用、销毁和研发生产三个环节,进行了全面控制。普及国际人道法,研究国际人道法,实施国际人道法,发展国际人道法,不应当排除、而应当十分重视对武器、技术的控制。
二、武器、技术的发展对国际人道法的挑战
有控制就有反控制。这种反控制的国家行为集中表现为,或拒绝参加相关条约,或虽然参加条约而不遵守甚至退出条约,或利用国际人道法的空白,逃避、对抗国际人道法的控制,发展为国际人道法基本精神所禁止的武器、技术。比如,美国并无以地雷作为自卫和防御武器的需要,却不参与渥太华禁雷公约;虽然具有绝对的核优势,仍然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为保证对导弹袭击的绝对战略优势,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保证拥有对其他任何国家进行导弹射击的绝对战略优势,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日本虽然参加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但至今并没有多少履行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行动,而按条约规定,它应当在2007年前将这些遗弃化学武器处理完毕。“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议定书”把研发新武器、新技术的合法性规定为各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而各缔约国是否履行此项义务、是否正确行使该项权利,是大有问题的。比如,把外空军事化合法吗?国际社会的主流看法,认为它违背国际人道法的基本精神。独占外空武器技术研究和发展绝对优势的超级大国,就不这样认为。它不仅提出、而且努力完善“太空战”理论和构想,研发外空武器系统,就是要“抢占外空,控制地球”。国际人道法控制武器、技术的发展,而武器技术又总是超出国际人道法的控制而不断发展。武器、技术的发展强劲地冲击着国际人道法:
武器、技术的发展冲击了国际人道法的基础。全部国际人道法,就其实质来说,就是平衡和协调满足“军事需要”与避免“不必要痛苦”这一对矛盾,为这对矛盾运动提供恰到好处的基本原则、规章和制度。武器、技术的发展无情地打破了原来已经达成的平衡和协调,极大地加深和激化了这一对矛盾。它使“军事需要”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战争以消灭敌方的军事人员和物资为“军事需要”,而武器、技术的发展,要求注重打击敌人的信息节点,从结构上破坏其整个军事系统。它带来了许多新的更为严重的“不必要痛苦”。即以这些年亮相战场的贫铀弹来说,它带来的灾难就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后果十分严重深远。武器、技术的发展还使得满足“军事需要”与避免“不必要痛苦”这对矛盾更加难以协调。精确制导武器、先进侦察手段的运用等等,固然使得打击的精度更高,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破坏和平民伤亡;但高技术武器的超常毁伤威力,陆、海、空、天、电磁“五维一体”的作战样式,又使区分原则更加难以施行、避免“不必要痛苦”更为困难。
武器、技术的发展,扩大了军民两用的技术与装备的范围,科学家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将成为决定性的军事力量,冲击着国际人道法原来的调整范围。信息技术越来越成为武器系统乃至整个军队的支撑和主宰技术,随着作战对信息系统依赖程度的增加,民用信息系统在战争设施中的比重将不断增大,大量非军人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各类专业人才,将为战争提供至关重要的服务。这样一来,原先已经清楚的军事目标和民用物体、战斗员和非战斗员的区分,现在又成了十分严峻的问题,重新摆到了国际人道法面前。
武器、技术的发展,使国际人道法出现了许多空白。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军事领域兴起的“新军事变革”(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实际上就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引发武器装备质的飞跃,将导致作战样式、作战空间、作战指挥、作战理论、军队编制乃至整个军事思想、国防建设的全方位变革。已经面世的和即将面世的大量新武器、新技术、新作战方法、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战争中的人道问题,超出了国际人道法原有的规范体系。它要求国际人道法与时俱进,发展和完善自己的规范体系。
武器、技术的发展挑战国际人道法的控制,同时也推进国际人道法的发展。国际人道法与武器、技术的发展,就是在这种控制和反控制,挑战和应战的相互作用中,交织前进的。当前,武器、技术的发展,向国际人道法提出了全面而深刻的挑战。国际人道法如果不能发展自身而将其控制在现代社会“人道要求”的范围内,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如果能够深刻洞察并自觉接受挑战、恰当应对这些挑战,即将获得新的全面发展。避免前者,争取后者,这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三、强化对新武器、新技术的控制
国际人道法必须直面武器、技术发展的挑战,强化对新武器、新技术的控制。惟其如此,才能防止武器、技术的发展造成超出达到合法军事目的所不可避免的伤害,避免“不必要的痛苦”,一如既往地给武装冲突受害者以法律保护,满足当代武装冲突中的人道要求。
国际人道法强化对新武器、技术的控制,首先应该落实新武器、新技术的审查机制。如果说《圣彼得堡宣言》只是正式提出审查新武器、新技术的话,那么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则已经建立了对新武器、新技术的审查机制。该议定书第36条规定:在研究、发展、取得或采用新的武器、作战手段或方法时,缔约一方有义务断定,在某些或所有情况下,该新的武器、作战手段或方法的使用是否为本议定书或适用于该缔约一方的任何其他国际法规则所禁止。本条所建立的审查机制,其审查主体是缔约国自身;审查对象和范围,是缔约国“研究、发展、取得或采用”的一切武器、技术,而不论它们在世界范围内是未研发的还是现有的;审查实施时机是新武器、新技术“研究、发展、取得或采用”的各个环节,而不是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审查的标准,是第一议定书的相关规定和适用于缔约国任何其他国际法规则。(注:对第一议定书第36条的具体分析,请参看伊莎白·达斯特,洛宾·科波兰,里可·伊索,未来战争与新式武器?—关于国家审查作战手段和方式合法性的义务[M].国际人道法评论(2002-2003).)应该说,在这个审查机制中,审查对象无所遗漏,审查时机和关键环节恰到好处,审查适用的法律全面清楚,如果正常运行,可以保证新武器、新技术的符合国际人道法的基本精神。但事实上,这个机制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是因为,第一,审查的主体是研究、发展、取得或采用新武器、新技术的缔约国自身,自己审查自己,岂不难哉!更何况绝大多数缔约事实上并未对第36条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并没有在国内建立新武器、新技术的审查机制。第二,即使少数在国内建立新武器、新技术审查机制的国家,在实施审查的时候,并没有能够严格适用第一议定书的相关规定和应当适用的其他国际法规则这个标准。更为糟糕的是,这个机制本身对于出现上述两种情况没有制约和补救措施。为了强化对新武器、技术的控制,从机制上着眼,应该进一步完善新武器、新技术的审查机制,并真正让它运行起来,发挥作用。
强化对新武器、技术的控制,还应该更多地关注和推进军备控制的进程。这里说的军备控制是指以条约的形式限制武器系统——武器本身及其指挥控制、后勤保障和相关的情报收集系统——的研制、试验、生产、部署、转让、使用。它不包括裁军,也不包括单方面的和强制性军备限制,如单方面采取的军备控制措施、对战败国实施的强制性军备限制措施等。军备控制主要关注军事的稳定性,包括危机的稳定性和军备竞赛的稳定性,而并非是武装冲突中的人道要求的满足,它与国际人道法的目的不同,实施和监督机制也不一样。因此,把国际军备控制与国际人道法混为一谈,甚至把军备控制纳入国际人道法,并不妥当。但是,国际军备控制与国际人道法在内容、实施和发展上,具有互相重合、互相保障、互相促进关系,是不争的事实。比如,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和禁雷公约的签订,既是军备控制的成果,也是国际人道法的发展。总结和运用这方面的经验,把国际人道法对新武器、新技术的控制与军备控制对武器系统研制、试验、生产、部署、转让、使用的限制紧密联系起来,以国际人道法的基本精神推进军备控制,借助军备控制强化国际人道法对新武器、新技术的控制,具有广阔的前景。
强化对新武器、技术的控制,最好是立法先行,未雨绸缪。通过事先制订国际条约以禁止研制开发不符合国际人道法精神的新武器、新技术,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1977年《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是这方面的一个良好开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鉴于2001年《生物武器公约》审查会议加强其执行机制的失败,于2002年9月发出“生物技术、武器和人道”的公开呼吁,努力促成通过一个“关于防止为敌对目的滥用生命科学的政治宣言”,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步骤。同样,中国在1985年、2000年和2001年,分别在日内瓦以裁谈会文件的形式表达了旨在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主张和建议,2002年,又在裁谈会上和俄联合其他国家提出《关于未来防止在外空部署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国际法律文书要点》的工作,也是事前立法,防止迫在眉睫的外空军事化非常重要的努力。
立法先行,制订国际条约以禁止研制开发不符合国际人道法精神的新武器、新技术,国家的态度当然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但民间的作用绝不可忽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生物技术、武器和人道”的呼吁,不仅仅是指向政治当局和军事当局,也指向科学、医疗、工业团体和一般民间社会,动员所有社会团体和成员,特别是与生物技术直接有关的团体和成员,共同努力发展符合国际人道法的生物技术开发、运用的规则。一些非政府组织在日内瓦联合成立“防止生物武器计划”组织,希望通过民间力量,加强对国际生物领域的监督,防止生物研究被用于军事用途,这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呼吁完全一致。现代民主社会,国家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通过做好民间的工作推动国家,大有作为。
发挥民间的作用,还可以采用组织民间编纂法典的形式来实现。这方面近期的一个突出事例,是《圣雷莫海上武装冲突国际法手册》的面世。由于“考虑了最近的国家实践、技术进步以及相关领域的法律影响,尤其是《联合国宪章》、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航空法和环境法”,[2]此手册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却很有助于形成普遍接受的、调整海上武装冲突的国际法,并且已经起到了法律工具的积极作用。当然,禁止研制开发不符合国际人道法精神的新武器、新技术,与重述海战法的情况不同,不能设想组织民间编纂这方面的法典能起到《圣雷莫海上武装冲突国际法手册》相同的作用。但是,通过这种方式,对于签订禁止研制开发不符合国际人道法精神的新武器、新技术的条约,能够起到一定程度地推进作用。
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美妙无比的福音,但如果无节制地将其滥用于战争,则构成对人类的巨大的威胁。国际人道法是控制武器技术在战争中滥用的法,是在接受武器技术发展的不断挑战中丰富完善起来的法,面对高新技术和高、精、尖武器引发的新军事变革,应该通过完善和落实新武器、新技术的审查机制,通过推进和借助军备控制,通过事先立法,强化对新武器、新技术的控制,消除这种威胁。这样,国际人道法将随着可能转变为对人类敌对使用的任何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防止武器、技术的发展造成超出达到合法军事目的所不可避免的伤害,满足当代社会对武装冲突中的人道要求。这是国际人道法的价值所在,生命所在,也是世界人民对国际人道法的期盼。
收稿日期:2004-11-02
标签:武器装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