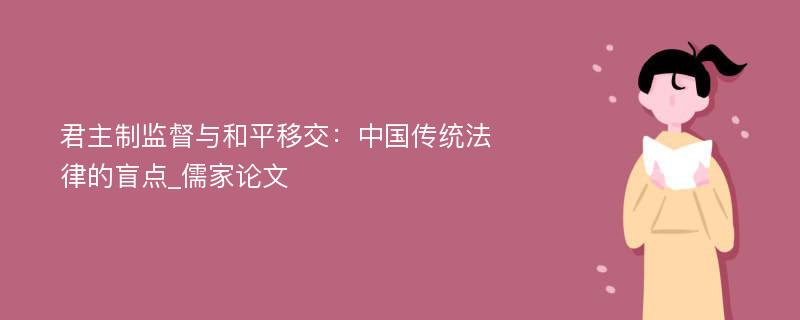
君权监督与和平转移:中国传统法学的盲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君权论文,盲点论文,中国传统论文,法学论文,和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新儒家”的学者牟宗三先生曾把中国传统政治学说的特征总结为“有治道无政道。”此说对我们认识中国传统法学说也有特别的启示意义。中国传统法学说实在也是一种“有治道无政道”的法学说。因为在古代中国,政治学说与法律学说本来就是浑然不分的。
所谓“政道”,就是关于政权问题的理论。从法律角度看,主要是关于权力合法性问题、权力的合法正常更迭问题、权力的分工与监督制约问题等等的理论。所谓治道,就是关于行政管理对象及管理方法问题的理论。从法律角度看,主要是关于具体事务的立法及执法问题的理论。在法的领域,政道相当于根本法理问题,治道相当于具体法律问题。
就中国政治法律史而言,所谓“政道”,应包括以下问题:君权或国家的起源、性质及更替、君权与吏权的关系,国家权力的分类及功能,国家机构的构成与运作,国家的决策程序或机制,国家的纠错机制等等。这些问题是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学说讨论得最少的问题。这是一个天生的盲点或缺陷。
一
“政”是什么?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学说中的“政”不外两重含义:一是“政令”或“法令”。孔子云“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注:《论语·为政》),老子云“以政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注:《尹文子·大道下》)都是此意。二是“政事”或“行政活动”。孔子云“为政以德”,“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注:《论语·颜渊》)孟子说“善政得民财”,“无政事则财用不足”,(注:《孟子·尽心》)讲的是行政手段或活动。这两种含义合起来,就是权力或国家根本大权。“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注:《论语·季氏》)权力发而为政令,行而为政事。或者说,政令、政事的源泉为政权。
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学说所关注的,几乎只是政令、政事问题,很少讨论政权问题。一代又一代贤人哲士们喋喋不休地讨论的,只是应当如何王霸并用、赏罚分明,如何理冤恤民,如何施行德教,如何从严治吏、循名责实,如何亲贤远佞、选用贤才,如何兼听纳谏,如何仁政爱民,如何发奸止叛强化治安,如何提高行政效率,如何有效贯彻政令法令,如何惩治贪污,如何止讼息讼……等等具体“治道”问题,实在很少涉及政权合法性的取得及更迭、政权的性质、最高权力的监督制约等等根本的“政道”问题。
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学说对这类“治道”问题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几乎每一个在历史上留下文字的人都曾参与过“治道”问题的讨论,留有这类言论。甚至最鄙薄政治的老子、庄子及其追随者也不例外。如老子就曾向君王们提出过“治大国若烹小鲜”、“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治人事天莫若啬”(注:《老子》第57章、59章、60章。)的具体政治谋略性建议;庄子就曾提出过“礼又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以道观能而天下之官治”(注:庄子“天运”、“天地”。)等具体政策性建议。关于具体政治法律问题即“治道”问题讨论如此之多,说明了中国古代政治中的弊病蠹害十分严重,迫使人们不断谋求改善“治道”,谋求治病之良方。人们反复不休且愈来愈多地讨论“治道”,说明政治行政中的种种弊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语云:“射不中的,反求诸身。”讨论政治问题的人们本应如此。“政者治之体,治者政之用。”当“治道”方面出了问题时,重要的是应该反省“政道”方面的利弊得失,不能老是在“治道”之内打转转。归根结底应讨论决策机构的构成、决策机制和程序、权力的根本制约机制等等是否有缺陷,应筹思如何使之更科学更完善,以期缩小“治道”上失误的可能性,然而由于历史和文化模式的限制,我们的先贤先哲们并没有这样的思维模式,而是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这另一条路就是“为政在人”。“为政”即“为治”。“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注:《中庸》)“有治人无治法。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注:《荀子·君道》)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就一切政治弊端即一切“治道”方面的问题所作的最权威的原因归纳。即是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认为,一切政治弊端的最大的、最终的根源,在于用人不当。“君子者,治之源也。源清则流清。”(注:《荀子·君道》)这样把人的作用强调到极处,特别是把贤人君子的道德楷模作用及其“为政以德”(为政时一本至公,无奸私之心)之效果夸大到极处,实在是走上了一条与古代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古希腊罗马人虽然也注意寻找贤君贤相贤吏,但更重视政体或制度的调整,以期有效约束掌权者,使其不得姿意妄为。所以早在公元前八至四世纪,就产生了特有的“民主制”和“法治制度”,国王和皇帝由人民公举,公民大会可以直接投票立法,元老院或公民大会可以迫令元首去职并改选他人。我们呢?虽然在设置机构和官吏时也曾有一些牵制、互监之考虑,但绝大部分心力用在对官吏及官吏候选人的道德净化上,期望达到一个几乎永远也达不到的目标——“人人皆可以为尧舜”,(注:《孟子·尽心上》)“(惟)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注:《孟子·公孙丑上》)
为了这一目标,中国古代哲人贤士们费尽了心智。但除了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亲贤远佞”、“赏罚分明”、“振肃纲纪”、“慎选举、严督察”之类的主张之外,他们并没有多做什么。后代贤哲们比前代贤哲们在理论深度上也没有进步多少。历代王朝的决策者或当家人们也费尽了心机,于是,撤换“道德卑下”者,任用“道德高尚”者,对官吏及官吏候选人进行道德教育以提高其品德水准,便成为世世代代周而复始的简单循环,结果一切依然故我。甚至,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端在这个循环中不断加深或恶化:中央集权不断走向极端,皇权不断膨胀,权力滥用愈来愈严重,腐败不断加剧。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为政在人”、“用贤去奸”之说也于事无补。昙花一现的法家虽然提出了“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注:《慎子·威德》)和“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注:《韩非子·用人》)的精彩主张,但很快被儒家正统的口诛笔伐所淹没,没什么大影响。况且,实际上,法家的这些主张虽貌似“离经叛道”,为儒家所不容,但却与儒家有着内在的一致:政治制度和法律,充其量只是一种弥补治国者为政者才智不足(所谓“中”、“拙”)的手段或工具,是“法术”或“政术”,并不是可以弥补或因应人们道德不足、制止官吏腐败的治国大道。法家自己也承认他们把制度和法律强调到比道德更重要的地位是不得已,是权宜性的,是为了“救世”。(注:郑相子产云其铸刑鼎的动机是“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左传》昭公六年)。如此是说,若“侨有才”,若要虑及子孙后代之事,则不必“铸刑书。”韩非子亦云其尚法是为了“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人民“无死亡系虏之患”(《韩非子·奸劫弑臣》)。这似乎是说,若非此应急之需要,则不应如此尚法。)在他们心目中,“任法”仍是不得已的下策。既然“任法而治”都是不得已之策,那么当然不会去讨论一个极为重要的政理或法理问题了。
于是,一个最最重要的问题——权力能腐蚀人;若非外力的有效制约,道德高尚的人也会被腐蚀,也会变得腐败;如何从体制或根本制度上尽可能有效地防止或降低这种腐蚀、腐败,使道德卑下的掌权者也无从姿意妄行——几千年来一直被人们忽视或回避了。我不知究竟是什么缘故。要我们的祖先提出“三权分立”、“以权力制约权力”、“人民监督政府”的主张当然是苛求;但是,踏上“完善法律制度以防腐败”的思考路径应该是可能的。
可惜,我们的祖先一直未能进入这条思路。他们没有或很少去从制度体制是否有根本缺陷的角度去寻找种种“治道”方面弊端的内在原因。几千年里,他们一直把一切弊政腐败的原因归结于人的道德堕落。直到清初的黄宗羲,才开始接近从制度方面去找原因的思路,但又后继无人,未形成较大社会及政治影响。黄氏认为,制度好应比人好更重要。制度不好,即使有贤能之人,仍无法依据此制度建功立业利国利民;若制度好,则不管有无贤人都不要紧。“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网罗反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注:《明夷待访录·原法》)其实,始创制度及后来讨论政治制度体制得失的人们,原本就是应该从“万一不幸”的“其人非也”之处着眼,首先考虑制度本身的严密,不要在制度上留下太多的漏洞或给贪腐官吏提供太多的方便。一旦实践中出现弊端,首先就应想到制度本身有弊端。一切考虑,都应以“小人”为基本参照物:每立一制度,应先考虑到若不完备严密,若不有效制约,“小人”将会如何假借之以徇私舞弊。以“君子”为参照物,一切均往好处想,结果便不能不是“以君子始,以小人终”,只能看到“小人乱政”的局面不断重演。“完善制度以减阻腐败”的思路与此正好相反:“以小人始,以君子终”。
二
关于“政道”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确讨论得太少了。这当然不能全怪他们。在专制集权的高压统治之下,文人学士们若要谈政治,除了歌颂当世君主“英明圣哲”及论证其权力为“天授神与”没有危险以外,谈论其他任何“政道”问题都有危险,甚至掉脑袋。所以,当看到政治行政中的种种弊端时,人们只能抨击贪官污吏,只能祈求国君从严治吏,振肃纲纪,只能劝君主“亲贤臣远小人”或“任用贤能”,只能劝为官者“为政以德”、“奉公走私”。下级贪吏贪腐了,责任在上级;众多官吏贪腐了,责任在中央、在皇帝。这个思路是他们常有的。但追到了中央、到了皇帝头上时怎么办?这就叫许多哲人一筹莫展了。“至圣先师”如孔子者,只能说:
“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事君……勿欺之,而犯之。”(注:《论语·先进》及《宪问》)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注:《论语·泰伯》)
“三谏之而不听,则逃之。”(注:《礼记·曲礼下》)
这是一种消极的做法。“止”就是“不仕”,弃官。“隐”和“逃”都是消极回避: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但孔子总算还主张“三谏”“犯之”,反复批评建议三次。这算是消极中的积极可贵态度。这考虑改革制度本身了吗?没有。只是考虑人,只认为君主听谏便是一切弊端解决之道。
孟子是古代中国最有“民主”精神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态度比孔子激烈: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注:《孟子·梁惠王下》)
“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注:《孟子·万章下》)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注:《孟子·尽心下》)
孟子比孔子显然进了一步,设计了“易位”途径来解决政府腐败问题。这比孔子的“隐”、“逃”办法当然好一些。但是,其所发明的“易位”办法是什么?没有新的,不过是“汤武革命”式的暴力推翻,这有些似似于西哲卢梭等人所言人民对暴政有“反抗权”。但是,若昏暴之君抗拒革命则如何?若因“革命”战争弄得天下生灵涂炭又如何?孟子并没有考虑。实际上,他还是没有考虑“完善制度以减阻腐败”的课题,没有考虑即使不用革命诛伐这种代价高昂的手段也同样能实现政治革新、腐败遏制之目的的方式、程序问题。今人看到这里不免为古人惋惜:既然“民比君贵”,人民比政府重要,为什么不能为“贵君”设计出一种可行的有保障的监督约束政府(包括君王)的机制或制度以减阻其贪污腐败呢?为什么不朝这方面想一想呢?
荀子似乎比孟子更进了一步,他似乎开始接触到了政权合法性问题:
“世俗之为论者曰:桀纣有天下,汤武篡而夺之。是不然。……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桀纣去天下也,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禽兽之行,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故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弑君。汤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纣者,民之怨贼也。”(注:《荀子·正论》)
在荀子看来,“汤武革命,应天顺人。”他们取得政权,并非从桀纣处夺得,而是人民“归而往之”地形成。桀纣本无政权,或者说通过人民“怨而叛之”的方式剥夺了其政权。政权的合法性在于人民拥戴。汤武杀桀纣,不是叛臣杀元首,而是代表人民诛杀早已没有政权合法性的“怨贼”(这与孟子观点一致)。在这里,荀子也接近“一切权力属于(或来自)人民”之命题的边缘。但他就是未跨过这一步。既然人民“归而往之”便可使其政权具有合理合法性,那么政权不就属于人民吗?荀子不会这么想。他可能仍认为政权来自“天”。天通过人民“叛”、“归”的形式褫夺了桀纣的政权,改授给汤武。荀子不知有没有想过:若桀纣这种拥有强权(不是合法的政权,而只是军队警察等暴力工具)的“怨贼”不许人民“怨而叛之”,抗拒汤武“吊民伐罪”式的讨伐,使得人民“血流漂杵”、“千里无鸡鸣”,那又该怎么办?实质上已无道德合理性或自然法合法性的政权,怎样才能做到不用流血战争即可剥夺其人定法上的合法性?怎样使“万民归之”的合道德合自然法的政权不流血地获得无可争议的人定法上的合法性?
法家比儒家在此一问题上的态度更保守。他们主张,即使君主残暴昏庸(即最高权力腐败),臣民们也只有受着,不得进行革命:“人主虽不肖,臣不侵也。”(注:《韩非子·忠孝》)既然如此,当然就更谈不上设计正常的和平的权力约束和交替程序了。
西汉初年,这种问题的讨论还曾进行过。景帝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上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否学者莫敢言受命放杀者。”(注:《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列传》,二者记载略有异。)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明显的一次涉及现政权合法性的讨论。关于汤武是“受(天)命”还是“篡弑”,自《易传·系辞传上》“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的标准结论作出以后,自春秋战国到汉初,除法家外,几乎没有人还疑这一结论的正确性,亦即没有人不承认讨伐暴君,以武力夺取政权的权利。但到了汉景帝时,这一问题竟成了跟“马肝”(古人认为马肝有毒,不能吃)一样的危险问题,不许讨论。因为这种问题只要一讨论,就涉及到现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也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最两难的问题之一:否认汤武革命,等于否认现政权的合法性,因为每一王朝均系推翻上一王朝即“革命”而建立;肯定汤武革命,又等于承认现在及将来的人们有推翻本朝政权的权利。所以,当辕固生“联系本朝夺权实际”地说到:“照你这么说,难道高帝(刘邦)灭秦夺权错了吗?”这一“上纲上线”使黄生马上噤若寒蝉。照说,景帝应该支持辕固生,因为他赞成汤武革命。但他两方都不支持,而是下令禁止讨论,并宣告此一问题为“马肝式问题”(有毒问题)。
其实,正是这种“马肝式问题”才是政治法律学说所最应讨论的问题。可惜,几千年里的中国思想家们,就是因为未食此“马肝”,所以一直不知“政道”特别是政权合法性、政权合法约束、合法更替之机制等等“味道”,使中国政治法律学说的天然缺陷千年依旧。从汉以后,泛泛地赞扬汤武革命,赞扬本朝革前朝之命是可以的,但绝对不要在讨论此一话题时联系本朝腐败的实际。董仲舒就是显著的例子:
“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在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注:《春秋繁露·尧舜汤武》,有人认为此语非董氏语。见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221页。)
董子不敢说“汉若无道,后人亦伐之。”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任一王朝无道,都免不了有人讨伐并取代。要想不被“伐”,只有两条路:一是保持政治开明廉洁,使人无“伐”的借口,或没有人民愿意追随某人而“伐”之。二是实在要“伐”,就用“文伐”,不要“武伐”,用和平的,正常的程序实现对政府的改良或更替。从前者出发,应该探索出对权力或官员的有效监督制约机制,使其想腐败也腐败不到那里去,未到严重腐败时即已被罢免。从后者出发,应探索出政权的和平转移程序,使失德的元首及其追随者不得不和平地交出权力,使有德的问鼎者不必大动干戈而只需和平地动用民意,使下台的政权要人及其家人们得保首领不被滥杀。只要从这两者的任一角度稍微用心地探讨下去,中国的政治学、法学,进而中国古代的政治,就不会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副模样。
三
政府改革是“政道”的关键,政府最高权力的变更又是政府改革的关键问题。如果不敢讨论这一问题,那么结果只能是:一方面,建立一个“凡君皆圣皆贤”的假想前提,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君主身上,一切改革设想以不触及“圣上”利益为前提。一切政治管理活动的结果,如有功,“君任其誉”;如有错,“臣任其咎。”除了谏官制度下偶尔有人“犯颜直谏”对国家最高权力的决策起点纠误作用(且是无制度保障的,听不听则要看君主的情绪如何)之外,对最高权力的构成、限度、行使,最高决策的产生与颁施等等方面的根本问题,几乎无人敢问津。在传统中国政治中,政治就是君政,一切国家机构均不过是君权的工具。既然“君主无过错”,出错总是臣下的错,那么只能把全部的心力用到诸如“官吏是否称职”、“政策措施是否恰当”、“怎样提高为政者品德素质”等等具体“治道”问题上,归根结底又集中到“用人”问题上,用人问题几乎成了“治道”的全部。荀子的观点最有代表性:“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注:《荀子·君道》)“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故法而议,职而通,无隐谋,无遗谋,而百事无过,非君子莫能。”(注:《荀子·王制》)贤人君子的作用既然如此神奇、如此重要,当然就没有必要去斤斤计较于“政道”问题了。荀子在这里贬低的表面上仅仅是“良法”的作用,实际上是否定了探讨“政道”的必要性,因为“政道”探讨的目的正是为了寻求“良法”。(注:荀子所谓“良法”,既然必赖君子才可实现,一旦有小人掌之必乱,这其实并不是“良法”。良法应能使小人无法纵肆其恶志。否则,即有恶法。)从荀子以后,虽然朝朝代代均有人讨论改革政府机关、消除弊政的问题,但大多是蔽于“用人”之一曲而不知返,在“亲贤远佞”、“退恶进德”的圈子内反复循环,很少有人从追求良法的角度去探讨权力的分工制约、决策过程的科学化等“政道”问题。
另一方面,对国家最高权力(君权)的构成、变更、使用等等若欲有所建言的人,既不能从“政道”之“本”上去考虑或议论,就只能将计就计地借“天威”对君主提出一点忠告,讲的“天命无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等等大道理,以期感动“天听”,使君主回心转意。“惟有德者可以得天命”也好,“非圣人莫能有天下”(注:《荀子·正论》)也好,都是对君主进行的无可奈何的道德规劝。这些规劝,起不了多大作用,反过来却更有利于皇权的进一步膨胀:既然君主的道德条件如此重要,那么只要眼下可以认定皇上“有德”时,就必然要主张“一切权力归皇上”,主张强化皇权,主张最高权力不受制约。种种政治弊端,人们往往将其归固于皇帝良善的诏命未被下级认真贯彻执行,因而认为只有强化皇权才能消除弊政。他们不知道,权力越集中,越容易发生腐败,此乃铁的规律。万一不幸是“无道”者为君,我们当如何?若不能对当世君主而主张用“汤武革命”,那么就只能寄希望于“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恶,天能罚之。”(注:《墨子·天志中》)说白了,就是要大家“听天由命”。因为“天罚”只能通过天灾异变的方式显示,只能在天灾人祸的大动乱中使其不暇自救而自我灭亡(对当世君主用汤武革命的办法“致天之罚”、“代天行罚”之道路,后来已被儒家正统学说所堵死)。几千年来,竟然没有一个人设想用不靠暴力,不指望天威的和平化、程序化、制度化的有保障的途径去完成对最高权力的变更、改造,这真是怪事。人们设想的最理想权力转让程序是“禅让”,然而毫无制度保障,仅系于个人品德,且最应当将权力转让出来的人往往是最不愿意禅让的人。于是我们的政治史就只能陷入从开明君主到昏君加天灾人祸、王朝覆灭又到新王朝建立并渐渐走向昏亡的周而复始的轮回,只能听任这种周而复始的改朝换代战争对生产力成就进行一次又一次毁灭性摧残!我当然不是说理论的失误带来了这一切,但都不能不承认,“政道”的盲点或致命缺陷,阻塞了我们探索避免此种轮回之制度的道路。直到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才从西方引进了“人民革命”、“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新理论,中国的“政道”才为之一新,中国的政治法律思想才为之一新。直到今日,因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学说的全面确立,中国才有可能真正跳出那可怕的数千年轮回。
结语
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学说在“政道”方面的盲点或天然缺陷很多,我这里仅仅涉及一个方面,即最高权力的监督制约及和平更替。这是“政道”之中最关键的问题。(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学说在“政道”的其他方面的缺陷,我当另为专文研究。)从这一盲点或缺陷,我们能够看出些什么呢?
我想,这反映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学说的幼稚、肤浅:有“说”无“学”,有“论”无“理”。只有“政道”的深入探究,才有可能使我们的政治学法学进入有“科学”或“学理”的境界。第二,反映了“神权政治论”对政治学法学的致命障碍。一方面神化君权或神化君主的结果当然是不得讨论最高权力的制约更替问题。这与古希腊罗马即确立的世俗政权理论大异其趣。另一方面,笃信“天报”、“天讨”、“天罚”,寄望于不可定之天数,必然会在完善政制、约束权力的人为努力方面自我松懈。第三,反映了以农立国的内陆型东方专制主义统治强权的极端性。在其他文明类型或政治类型里都或多或少允许或想压制也压制不了的根本政理讨论,在中国却能有效地禁止数千年。至于这种有效的强大的压抑机制(也可能是欧洲古代或中世纪一些暴君所神往的机制)如何能在中国形成并长期存续,这又是另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
标签:儒家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孟子·尽心上论文; 汤武革命论文; 政治论文; 君主制度论文; 孟子论文; 法律论文; 国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