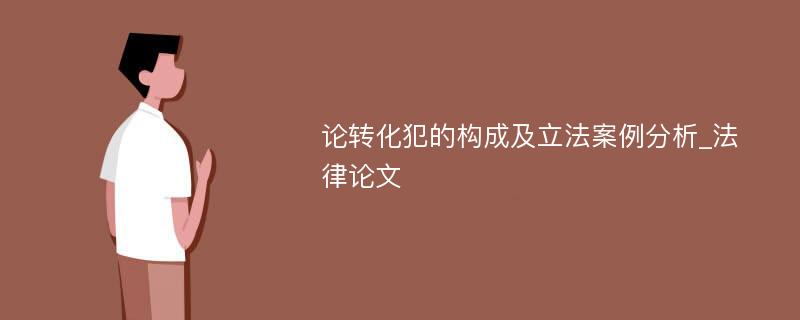
论转化犯的构成及立法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什么是转化犯,刑法理论界有多种表述,主要观点如下:(1)指某一违法行为或者犯罪行为在实施过程中或者非法状态持续过程中,由于行为者主客观表现的变化,而使整个行为的性质转化为犯罪或转化为更为严重的犯罪,从而应以转化后的犯罪定罪或应按法律拟制的某一犯罪论处的犯罪形态;(注:参见杨旺年:《转化犯探析》,载《法律科学》1992年第6期。)(2)指行为在实施某一较轻的犯罪时,由于连带的行为又触犯了另一较重的犯罪,因而法律规定以较重的犯罪论处的情形;(注:参见陈兴良:《转化犯与包容犯:两种立法例之比较》,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4期。)(3)指行为人在实施某一较轻犯罪(基本犯罪)后,由于其特定的不法行为,而使轻罪转化为某一重罪,法律明文规定以转化后的重罪定罪量刑的犯罪形态;(注:参见赵嵬:《论转化犯》,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7年第6期。)(4)指由法律特别规定,某一犯罪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另一种更为严重的犯罪,并应当依照后一种犯罪定罪量刑的犯罪。(注:参见王仲兴:《论转化犯》,载《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笔者认为,在以上定义中,定义(1)认为转化犯的含义涵盖了由非罪向罪的转化,这样,转化的罪质可以不变,即犯罪量的增加也可以成立转化犯,这势必扩大了转化犯的范围,不甚妥当,因为本来的一罪就不存在转化问题。定义(2)认为转化犯的成立是由于“连带的行为又触犯了另一较重的罪名”,这显然没有把转化犯与牵连犯从根本上区分开来,而且这里的“连带行为”语义模糊,容易导致误解,连带行为并不能包括转化犯的其他转化条件。定义(3)也认为是“特定的不法行为”导致了罪的转化,与定义(2)有同样弊端。笔者基本赞成定义(4)的表述,但在用语上需略作改正。即转化犯是指行为人在实施基本罪的危害行为过程中,由于出现特定的犯罪情节,而使基本罪的性质发生改变,转化为某一重罪,并且按重罪定罪量刑的犯罪形态。
根据转化犯的定义,结合我国新刑法的规定,笔者认为转化犯具有以下构成特征:
第一,行为人实施了基本罪的危害行为,这是转化犯的前提条件。转化犯是相对于基本罪已经成立而言的,没有基本罪存在,也就无所谓一罪向另一罪的转化,如果行为人实施一般的违法行为,在发生一定条件之后,构成某一犯罪,这只是犯罪的成立问题,而不是犯罪的转化。只有从一种罪质向另一种罪质的转化,才是转化犯研究的对象。由于我国刑法尚未出现过失犯罪向其他罪转化的立法例,理论界一致认为转化犯的基本罪只能是故意犯罪。有学者进一步强调必须是基本罪的犯罪行为已达未遂或即遂状态,才有可能产生转化犯。笔者认为,如果行为人实施基本罪的预备行为,构成基本罪的预备犯以后,一旦加入法定的转化条件,则可以向重罪的预备犯转化。例如,携带凶器,准备实施抢夺他人财物的行为,应当根据新刑法第267条第2款的规定,以抢劫罪的预备犯定性,如果仍然定抢夺罪的预备犯则有违刑法总则对预备犯的规定,也不符合本条的立法精神。纵观新刑法对转化犯的规定,关于基本罪危害行为的罪状描述有以下形式:(1)“犯前款罪……”;(2)“有前款行为……”,或者“……有前款行为的……”;(3)犯……罪(具体罪名)……”;(4)重复描述基本罪的犯罪行为;(5)因与基本罪处于同一款,故省略了对基本罪行为的描述。
第二,增加了新的犯罪情节,这是转化犯的转化条件。“情节”作为刑法术语是指表明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是否具有人身危险性,以及社会危害和人身危险程度轻重的主客观事实情况。表明转化犯构成特征的情节具有以下特点:(1)它超出了基本罪的构成范围,是基本罪自身不能包容的因素,具有相对独立性;(2)它与基本罪危害行为又密切相关,没有基本罪的危害行为,它的存在便完全具有不同意义;(3)它也不同于基本罪的量刑情节,因为它的出现改变了基本罪的性质,使基本罪发生质的变化;(4)当这里的情节属于不法行为时,它不能独立构成犯罪,否则就成了两个罪结合成一个新罪的结合犯了。新刑法对转化犯构成特征的规定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行为人在实施了基本罪的危害行为之后,又实施其他违法行为;(2)被基本罪包容的危害行为造成了特定的犯罪结果;(3)采用特定的犯罪方法实施基本罪的危害行为。由此可见,那种认为转化犯的转化条件仅限于“特定的不法行为”的观点(注:参见赵嵬:《论转化犯》,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7年第6期。)与我国刑法的具体规定不相符合,是不够全面的。
第三,法律明文规定转化为某一重罪,并按重罪定罪量刑,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转化犯是由基本罪加上特定的犯罪情节转化而来的,故相对于基本罪来说,转化犯属于重罪。这样,转化犯的罪名也就不同于基本罪的罪名。这种罪质的不同,决定了单纯因量的增加而使一般违法行为转化成犯罪的情况不属于转化犯。
此外,认识转化犯的构成特征时,我们不能忽视转化前的基本罪与转化后的转化犯之间应有的联系:(1)法律评价的对象相同,即转化犯的行为人就是犯基本罪的行为人。因此,新刑法第393条规定的“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法第389条、第390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这不属于转化犯立法例。本条规定的基本罪是单位行贿罪,主体为实施行贿的单位,与因(单位)行贿而取得违法所得的个人,二者不是同一评价对象,故这种情况不属于由单位行贿罪转化而来的转化犯。(2)从客观方面看,基本罪的危害行为是转化犯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主要内容,这一点前文已有论述。象危害行为一样,基本罪侵害的对象也是转化犯的侵害对象,但由于增加了新的犯罪情节,二者侵犯的客体发生了显著变化。(3)基本罪的罪过形式决定转化犯的罪过形式。我国刑法规定的转化犯的基本罪都是故意犯罪,转化犯也都为故意犯罪。但二者的故意内容有所差别,比如对危害结果的认识、对行为违法性的认识、以及追求的犯罪目的等,都有一定的不同,而且后者的主观恶性明显比前者要大。(4)关于犯罪形态的联系。故意犯罪过程中的预备、未遂、既遂形态实际上是反映犯罪客观方面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指危害行为在犯罪构成过程中的发展程度。由于转化犯的危害行为以基本罪危害行为为主要内容,因此其基本罪犯罪形态对转化犯的犯罪形态有重要影响。首先,基本罪是预备或未遂形态时,如果成立转化犯,则只能呈现转化犯的预备或未遂形态。例如,行为人盗窃、诈骗、抢夺未遂以后,又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应以抢劫罪未遂论处。其次,基本罪为既遂形态时,并不意味转化犯一定既遂,这取决于转化条件的具体内容。如果转化条件是发生特定犯罪结果,那么转化犯就是既遂形态;如果转化条件是特定不法行为,那么转化犯是否既遂还取决于不法行为是否已经得逞。例如,行为人私自开拆、隐匿邮件成立既遂之后,又图谋窃取财物但因被人发现而未得逞,这时,只能定转化犯的盗窃未遂。
转化犯的构成特征决定了它与结果加重犯是不同的。结果加重犯是指实施基本犯罪的危害行为,过失导致发生基本构成要件以外的重结果,从而对此规定较重刑罚的犯罪形态。转化犯与结果加重犯都是相对于某一基本犯罪而言的,在处罚上都较基本罪为重,尤其是当转化犯的转化条件是特定的犯罪结果时,更应当注意二者的区别。笔者认为,二者的主要区别是:(1)主观心理态度不同。结果加重犯的行为人对重结果的出现一般是持过失的心理态度,重结果的发生是他所不希望的,在其故意内容之外;而转化犯的行为人对重结果的发生或其他转化条件均持故意的心理态度,而且多为直接故意。(2)与基本罪的关系不同。结果加重犯虽然出现了超出基本犯罪构成的重结果,但并未改变基本罪的罪质,故仍应以基本罪的罪质定罪;而转化犯则改变了基本罪罪质,转化条件使基本罪不能涵盖已经具有的社会危害性,法律必须规定新的重罪与之相适应。(3)处罚的根据不同。处罚结果加重犯直接根据法律特别规定的法定刑,而处罚转化犯的依据是转化后所犯罪的法定刑,在罪状中的表述一般是“依照本法第×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或者“依照本法第×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这样,对有的转化犯应在重罪的法定刑内从重处罚,这也是与结果加重犯有所不同的。此外,除了基本罪为故意罪的结果加重犯之外,新刑法还规定了过失罪的结果加重犯,如第131条重大飞行事故罪、第139条消防责任事故罪、第330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等,而转化犯的基本罪都为故意罪。结果加重犯的存在须以重结果的发生为要件,重结果发生了,无论基本罪的犯罪行为是既遂还是未遂,均成立结果加重犯既遂形态,故结果加重犯无未遂可言,而转化犯不仅可能出现未遂犯,还有可能出现预备犯,对此前文已作论述。
新刑法约有十余个条文规定了转化犯。笔者选择以下有代表性的条文在此予以分析,并阐述个人看法。
第一,新《刑法》第241条第5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又出卖的,依照本法第240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这是关于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向拐卖妇女、儿童罪转化的规定。其转化条件是出卖被收买的妇女、儿童。有人认为,该条规定不属转化犯而应为数罪,理由是“其出卖行为显然又触犯了拐卖妇女、儿童罪。”(注:参见赵嵬:《论转化犯》,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7年第6期。)笔者认为,该条第5款规定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在主观上不以出卖为目的,否则依据第240条的规定就已经构成了拐卖妇女、儿童罪,而不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这里的“出卖”行为也不属于第240条第2款规定的“贩卖”行为。因此,该款规定的“出卖”行为不能独立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第241条第2款的规定,行为人在收买被卖的妇女后,又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后一行为已独立构成了强奸罪,但只按重罪即强奸罪定罪处罚,这属于吸收犯的立法方式,而不符合转化犯的构成特征。
第二,新《刑法》第247条、第248条规定了“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的转化犯。类似的规定还有第292条第2款规定的“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333条第2款规定的“有前款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以上四个法条规定的转化犯都是以致人伤、亡的犯罪结果为转化条件,导致此结果出现的危害行为都可以被基本罪的犯罪行为所包容,即无论是刑讯逼供、暴力逼取证人的证言或殴打、体罚被监管人,还是聚众斗殴或以暴力、威胁方法强迫他人出卖血液,这些基本罪的犯罪行为都包含着对受害人人身的伤害,它们与受害人的伤亡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与此有别的是第238条第2款规定的“……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这是否为转化犯的立法例呢?笔者认为,非法拘禁的危害行为与上面四种基本罪的危害行为具有不同的特点,非法拘禁本身不应包容故意伤害行为,因此,第238条第2款前段对非法拘禁致人重伤、死亡的,规定为结果加重犯,而该款后段又另行规定“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情形,这里的“使用暴力”致人伤、亡的行为和结果不仅超出了非法拘禁罪的犯罪构成,而且足以独立构成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因此,非法拘禁,并且使用暴力致人伤、亡的,成立事实上的数罪,加上二罪之间并无牵连关系,对事实上的数罪以重罪论处的,属于吸收犯的立法例,而不是转化犯。还有人认为第289条前段规定的“聚众‘打砸抢’,致人伤残、伤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也属于转化犯的立法例。笔者不同意这一观点,理由是聚众“打砸抢”本身不能构成独立罪名,它只是故意伤害罪的特殊形式而已。如果不发生“致人伤残、死亡”的结果,聚众“打砸抢”行为就不能构成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而只是一般违法行为。同样地,如果不发生“毁坏或者抢走公私财物的”情况,也不能构成抢劫罪。
第三,新《刑法》第253条第2款规定了“犯前款罪而窃取财物的,依照本法第264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的转化犯。这一立法例来源于原刑法第191条的规定。由于当时的规定是依照贪污罪从重处罚,故不少学者认为它是结合犯的立法例。(注:参见吴振兴著:《罪数形态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页以下。)新刑法颁布以后,情况有所不同,对这里的“窃取财物”如何理解,有必要加以探究。笔者认为至少应当区分以下几种情况分别对待:(1)如果窃取的财物数额不够较大的,依照该款规定,应在第264条规定的第一个档次的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罚。根据前文所述转化犯的构成特征,这种情形属于典型的转化犯。(2)如果窃取的财物数额较大的,就出现了独立的数罪情形。当前罪与盗窃罪具有法律上的牵连关系时,即为了盗窃财物而私折邮件就成牵连犯,这时本款规定的则属牵连犯立法例;若二者并无牵连关系,比如行为人出于好奇心理私折邮件之后,再生谋财的念头,窃走有关财物,但依本条规定,仍只定盗窃罪,而不实行数罪并罚,这就属于吸收犯的立法例了。
第四,新《刑法》第267条第2款规定了“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转化犯。有学者认为这一规定是“一种法律推定”。(注:参见陈兴良著:《刑法疏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9页。)笔者认为,携带凶器实施抢夺对他人的人身安全构成更严重的威胁,给被害人维护自身权益增加了精神障碍,这一条件足以改变一般抢夺行为的性质,使一般抢夺罪转化为抢劫罪。
第五,新《刑法》第269条规定了“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转化犯。类似规定在日本刑法中被称为事后强盗罪。在我国台湾,一些学者则称之为准强盗罪,之所以称为准强盗罪是因为这种犯罪不完全符合标准强盗罪的构成特征,还有的台湾学者称准强盗罪为追并犯,即“乃原罪依法律之特别规定,因与犯罪后之行为合并,变成他罪”的犯罪形态。(注:参见陈朴生著:《刑法总论》,台湾三民书局1978年版,第270-271页。)其追并犯的概念与我们所称转化犯是从相同角度进行定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