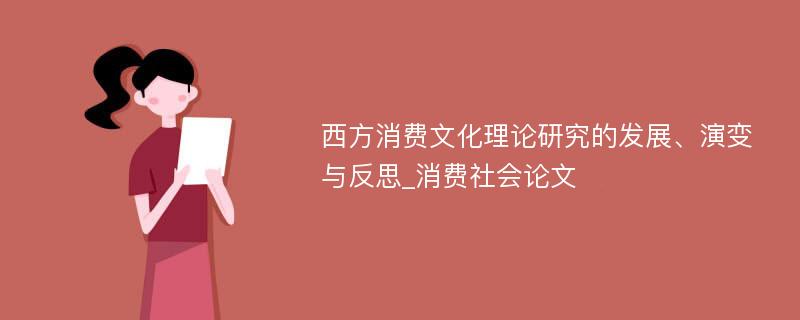
西方消费文化理论研究的发展、演变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传统社会视域下的消费文化研究
消费既是西方社会巨大转变的原因,也是西方社会巨大转变的结果。[1] 在西方社会变迁过程中,消费是一种决定性的社会和历史的力量,这是西方消费文化研究普遍认可的观点。消费文化史是理解整个西方消费文化研究的主题,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如布罗代尔(F.Braudel)、费瑟斯通(M.Featherstone)、坎贝尔(C.Campbell)、威廉姆森(R.Williams)等代表人物,都采用广泛的历史观点对消费文化进行研究。
正如西方工业革命在推动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一样,消费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地位同等重要,并且相互影响,研究消费形态与西方社会变迁之间的重要联系,成为消费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而其起点至少回溯到15世纪。消费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必须从社会变迁的多重视角,进行历史省察。
工业社会固然是消费文化研究的重点,但是消费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古典经济学家将消费作为其经济学说的重要内容,威廉·配第、亚当·斯密、李嘉图、魁奈等人对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节制消费,奢侈性消费等展开了多方面的探讨。从十八世纪开始,商人、企业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就开始以类似的主要消费理论为依据,忙于辨认欧洲和北美的一系列消费革命。许多西方史学家将社会风尚和日常消费作为论述的重要内容,如卡洛.M.奇波拉(Carlo M.Cipolla)主编的《欧洲经济史》一书中,论述了1750年至1914年欧洲的消费结构、习俗和风尚对消费的多重影响。[2] 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一卷)中,集中讨论了欧洲前工业化时期的日常消费,如一日三餐的面包、饭桌上的菜肴、饮料、住宅、服装与时尚等等,将15到18世纪的欧洲消费文化史作为物质文明的核心内容进行详细探讨。[3] 为消费文化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严密的分析思路。
在消费文化研究中,仅仅把消费作为某一时期各消费链融合作用的结果是不够的,消费研究必须同社会和文化史研究结合起来,与许多具体的研究相互借鉴。因此,必须抓住历史细节,避免笼统地泛泛而论。[4] 弗兰克·莫特(Frank Mort)的观点代表了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看法,将消费文化与文化分析、人文地理、商业史、社会史等结合起来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其中马克迅·贝格(Maxine Berg)和亨利·克利弗德(Helen Clifford)主编的《消费与奢侈:1650至1850年的欧洲消费文化》,是近年西方消费文化史研究的一部代表作。该书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考察消费者及其交往的私人和社会公共空间的文化维度,结合艺术、科技、经济和物质文化史,集中讨论英、法、荷兰等国在食品、饮料、奢侈和时髦商品、艺术收藏品等的消费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丰富文化意义,从奢侈与必需,新奇与模仿,公共与私人消费空间,过剩、品味和时髦,身份认同与自我展示等五个方面,全面展现了1650年至1850年欧洲消费文化的发展历程。[5] 在物的文化传记中,历史的沉淀更能反映其文化内涵。
在消费文化史的研究中,研究个人消费如何受到群体的影响,往往采用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凡勃伦(T.Veblen)提出的炫耀性消费理论,对中世纪以来有闲阶级的生活与其他社会阶级的区分,对浪费、虚荣、代理有闲、代理消费、奢侈等概念进行探讨,[6] 使消费的社会意义表现得非常广泛,为现代西方消费社会理论奠定了基础。在十六世纪初,西欧是一个社会阶层界定严格且地位组织非常清楚的社会,因而个人的消费行为大都是由其在整个社会阶层中的位置所决定。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晚期,正如威廉姆森所认为的那样,阶级已正在失去主宰的地位,由生活方式及其他影响力取而代之。而消费的角色有助于规范和界定社会流动性。麦克法伦(A.Macfarlane)认为物品在整个社会流动中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守门人的角色,例如一个拥有几世纪珍贵物品的家庭,将会取得高贵显赫的合法性地位。米勒(M.Miller)认为消费性物品可以作为那些期待别人的生活方式的人们的一种所谓的“文化人门之物”。同时,十九世纪以来的消费民主化,影响着阶级的概念与实践。在消费行为上,麦克杰克(N.Mckendrick)等人认为,从十八世纪开始,西方社会的消费形态从以家庭为重心转变到以个人为重心,成为消费史研究的焦点。[7]
消费不但是日常生活所必需,在阶级社会,它是观察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对象。一些政治学者对奢侈消费观念的历史演变和社会影响进行多方面探讨,进而进行政治学分析。如克里斯托弗·贝里(Christopher J.Berry)对奢侈的概念进行了历史考察,从古典到现代社会的变迁中,奢侈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巨大变化,奢侈与需要和欲望密切相关,独有的奢侈品的形象是通过先声夺人增加消费的一着棋,在奢侈的“古典范式”中,意味着对美好生活的破坏,但是,随着奢侈的“去道德化”,其推动消费的正面意义不断扩大,政府对待奢侈的态度,影响着社会政策和秩序。[8]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消费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从文化地理和区域的角度,对消费文化史进行分析和论述,是近年西方消费文化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例如美国学者多南德·凯特力特(Donald Quataert)对16到20世纪初期奥拓曼帝国的消费史的研究,[9] 拉切尔·波拜(Rachel Bowlby)对美国十九世纪的区域消费文化的研究,[10] 麦克杰克·呢伍(Mckendrick Neil)对英国十八世纪商业化社会与消费社会产生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11]这些研究文献,从不同角度对国家和区域消费文化的历史变迁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察,对消费文化史的比较研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一些地区遗留下来的考古材料,展现了其物质消费的发展历程,通过对一些日常消费品的使用及流行过程,可以洞察到物质消费文化的历史变迁以及对社会经济文化交往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如尤兰达·考特尼尔(Yolanda Courtney)对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带的酒店的不均衡分布的考察,对酒店集中地带的经营模式进行深入研究。酒店标识牌作为领取物品的信用标志,在伯明翰地区广泛流行,引导着一种新的消费方式,而标饰品成为消费者信赖的物品,成为一种文化模式。[12] 这种酒店标牌的空间维度,反映了传统的消费习性和地区市场交易网络的牢固性。通过对酒店这一具体的消费场所的全面分析,可以了解到当时英国经济交往过程中,消费信用所发挥的重要功能,酒店的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消费习惯之间的关系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酒店标牌对金属贸易和地区经济交往方式发挥着显著的作用。
英国考古学专家简尼·韦伯斯特(Jane Webster)通过对1800年以来赫布里斯群岛地区居民对进口瓷器的消费态度的论述,说明当地人对传统的木制品有着固执的偏好,他们坚守着固有的消费习惯,对瓷器采取抵制和歧视的态度,这种外来经济生活变化所采取的方式,说明他们的生活不是简单的抵制,而是与英国大陆之间的消费方式存在“拒绝适应”的根深蒂固的观念。[13]
二、从现代到后现代的消费文化研究
罗斯托认为现代化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是在“工业化”的推动下才完成的。罗斯托在1960年发表了《经济发展阶段:非共产党宣言》,根据经济指标把所有社会的发展都分为五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的大众消费阶段。这五个阶段是根据英国工业革命的分析而总结出来的。[14] 而产业革命的发展,始终以生产与消费的连接为前提的。产业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消费革命,罗斯托认为在高额的大众消费阶段,其特点是消费已经超过基本需要,进入高层消费阶段。但是,在经济起飞阶段,西方社会的消费文化,已经成为主导西方社会生活的重要力量,以福特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标志着20世纪初大众消费社会的出现。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过渡,反映了西方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工业化加快了消费的步伐,消费的形式更为多样化,消费社会成为消费文化理论的基本研究对象。
消费进入西方社会学讨论的主题,应是肇始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地对抗着,它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15] 这种禁欲主义推动了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对绅士和贵族而言,仍然保持着以快乐为取向的生活方式,他们对奢侈品的消费需求,是推动工业革命的动力。韦伯的论述,为消费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
正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言:“现代社会的文化改造主要是由于大众消费的兴起,或者由于中低层阶级从目前为奢侈品的东西在社会上的扩散。”[16] 这种始于上世纪20年代的大众消费方式,与技术革命紧密相关,技术彻底改变了社会习惯和生活方式。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到典型的“消费社会”。福特主义倡导“一天工作8小时,挣5美元”,这种大规模、标准化的生产,使工人的生产劳动和家庭生活完全割裂开来,工人的生活必须依赖于商品。而后福特主义所采用“灵活积累”的新控制模式,在劳动力市场、劳动过程、产品及销售方式等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加快了生产和消费的节奏,消费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生产者主体在向消费者主体转移,经济的中心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消费也由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变。“消费社会”成为西方现代社会的代名词。对“消费社会”的分析和反思,成为当代西方消费文化理论研究的重心。
西莉亚·卢瑞在分析当代西方消费文化时指出:“消费文化是20世纪后半叶出现在欧美社会的物质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17] 随着“丰裕社会”的出现,对物的文化意义的分析,成为研究消费文化的重要环节。以鲍德里亚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在西方后现代理论背景下,运用当代符号学理论体系,对“消费社会”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鲍德里亚在他前期的三部著作《物的体系》、《消费社会》和《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生产领域扩展到消费领域,在此过程中,他对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产生怀疑,将符号学与政治经济学评判结合在一起,展开对“消费社会”的深入研究。
在对物的本质的研究中,鲍德里亚认为,必须把物从其功能性中解放出来,从日常的物进入到“人的行为及关系系统”。消费已不是单纯的需要的满足,消费的前提是物必须成为符号。消费是一个系统,它维护着符号和组织完整,因此它既是一种道德(一种理想价值体系),也是一种沟通体系、一种交换结构。[18] 符号消费其实是消费者的一种“自我实现”,或是为了体现“自我价值”的消费,也包括“炫耀”因素在内。消费体现的并不是简单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现代社会中,符号价值可以不受使用价值和劳动价值的约束,一件商品可能劳动量很低,但是符号价值很高,符号消费在当代社会具有神奇的地位,富裕、富有其实只是幸福的符号的积累,极大的丰盛意味着只有浪费才具有意义,商品只有在破坏时才显得过多,而且在消失中才证明财富。在符号消费过程中,破坏成为后工业社会决定性功能之一。符号价值理论的提出,构建了当代消费文化理论的基本框架。
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对分析消费史上一些夸耀消费,有很大帮助。但是鲍德里亚片面夸大了符号消费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对作用,对具体的消费实践和消费产生的政治话语重视不够,他在消费文化的分析中完全采用符号学的理论,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对使用价值和劳动价值之间的关系视而不见,对消费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过程缺乏充分的认识和理论上的提升,从而使他的符号消费理论存在严重缺憾。
显然,消费文化研究不能局限于消费的符号学分析,一些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将物的意义与消费的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物质商品不但有用,而且有意义,还可以作为社会关系的标志。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和经济学家巴龙·伊舍伍德研究的消费文化,已经跨越了商业系统。他们通过商品在宗教仪式中的功用的讨论,说明了商品可以作为社会地位的标志,商品之所以产生意义,是因为每个人都积极参与到特定文化中。马歇尔·萨赫利斯(MarshallSahlins)则用人类学上的图腾崇拜概念来分析消费,他认为被生产的物体是现代社会中的图腾,而消费者群体就相当于传统社会中的部落。例如,服饰可以被视为传达了每一类人所固有的属性,而这些属性又是区分他们的基础。阿尔琼·阿帕多拉(Arjun Appadurai )认为:物体的两种发展轨迹,即文化传承和社会历史,需要深入探讨,物体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增添分量和权威,因此,可以对事物的社会方面进行叙述性研究。[19] 正如道格拉斯所言:“消费的实际功能在于它有社会意义”,“物品就是仪式的附件;而消费是一场仪式,其主要功能是让一系列进行中的事件产生意义。”[20] 道格拉斯对消费的社会意义作了深刻的评述,但是对消费实践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秩序方面的塑造作用,并没有展开深入的讨论。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对鲍德里亚和道格拉斯等人的观点进行了综合,在《区分:鉴赏判断的社会批判》一书中,他提出了鉴赏趣味标志社会等级的观点,认为“品位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相反,社会方式决定个人的品位。”人们在消费实践中的鉴赏力是由“习性”所决定的。习性是一个持续的,可转移的性情体系,它结合以往经验,任何时候可作为人们认识、评价事物和行为的基础,它使人能够完成无限多样化的工作,凭借类似的机制从而解决相同问题。[21] 习性与一个人的家庭、群体、人体的等级和身体经营密切相关,是文化和日常生活实践的有机统一,它并非是静止不动的,它可以由不同社会群体所采取的策略之互动所决定。
布尔迪厄对习性的论述,将消费文化的分析置于广阔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探求影响习性的社会因素,对扩大消费文化的社会空间话语,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研究品位对社会再生产的意义时,布尔迪厄研究了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之间的关系,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并非对等的关系,文化资本具有自己独特的、独立于收入或金钱之外的价值结构,它相当于转化为社会权力的能力。如果单纯根据收入来判别品味等级,就会忽视文化与经济的双重运行原则。[22] 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同时他还提出日常消费与审美消费之间是同源的,艺术鉴赏与日常生活是息息相通的。这些论述,进一步深化了西方消费文化理论,对理解社会文化商品的经济与生活方式的生活空间,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
在商业社会,消费的指向逐步由“生产者主体”向“消费者主体”转移,研究消费者行为成为心理学学派的重点,“在一般人成为富足成熟的消费者之前,消费行为在整个消费者心理的发展脉络中已经发生根本的转变,”[23] 消费者的需要,商业广告和品牌对消费心理具有重大影响。流行观念与消费者的心理状态相关,“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会很有魅力地刺激、消耗人们的心理状态之故。”[24]
将消费文化理论运用于具体的购物经验,是一些西方学者近年来对消费文化进行个案研究的重要题材,当代西方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电视、报纸、新潮艺术和超级市场等,与后现代主义的形形色色的理论体系,将消费活动拖入现代性游戏和无限的折磨、狂喜和梦幻中,在对后现代社会的反思和评判中,消费文化成为全面展现当代资本主义特征的主流话语,有关这方面的成果层出不穷。
从政治学的视角研究消费文化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一个新的热点,这种“从文化帝国主义与多元主义的观念,来界定消费的性质,或者认为高能量、高度市场化的消费文化是会将文化帝国主义、霸权化加以制度化。”[25] 一般认为,跨国公司在西方消费文化的扩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西方国家以广播和电视为手段,以广告对发展中国家的消费文化进行“同化”,对消费者实行引导和操纵。消费主义文化的广泛流行,使发展中国家固有的文化传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从而放弃了对西方主流话语的抵抗。一些学者通过具体的材料证实了西方消费文化的征服过程。如斯嘉尔·卡沙(Sjur Kasa)论述了美国牛肉和汽车进入东北亚地区的过程,尽管长期以来受到传统消费模式的强烈抵制。但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美国的贸易政策极大地改变了这些地区的消费环境,“美国化”的消费文化逐步得以流行。在全球化进程中,跨文化和伦理差异对消费者和商人的选择风格仍然有不可忽略的影响。[26] 阿汉哈德·贾迈尔(Ahmad Jamal)对全球化与伦理、种族文化冲突及其对商业销售和人们的消费选择的影响,进一步作出了文化学和人类学的解释。[27] 在以物为中心的全球化过程中,消费文化无疑成为全球性的文化问题。
三、对西方消费文化理论的批判性反思
西方消费文化研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与演变,取得了令人炫目的成就。对西方消费文化理论的价值作出客观性的评述,有利于引导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消费文化研究。
尽管西方消费文化研究借鉴了许多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但是,其主要是借鉴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事消费文化研究的学者也以哲学和社会学家为主体,在研究视域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消费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行为,但是消费文化研究在借鉴经济学研究成果方面十分欠缺,特别是消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运用得不够。如消费函数理论、消费调控理论、消费的易变理论等等。消费文化的形成过程,本质上是一种“传播”过程。离开了传播学的研究,对媒介消费文化就无法理解透彻。作为与文化研究最临近的消费文化研究,在运用现代西方文化理论方面也有不深入之处,对社会潮流、审美风格等当下问题关注不够,影响了其文化含量。另外,由于对后现代理论的崇拜,过分强调宏观研究,对微观的日常生活研究不够,范围过窄,过多地依赖于冥想,使其理论哲学的色彩过浓,显得表面化和破碎化,缺乏说服力。这在后现代消费文化理论研究中尤为突出。
当代西方消费文化理论以“消费主义”为中心,极力鼓吹消费至上,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但是在消费符号的操纵下,人成为消费的机器,在“物化”的过程中丧失了自我,丧失了道德伦理,直接导致了人的异化,西方消费文化理论对因过度消费导致人的异化不但视而不见,还鼓吹为人性的解放和现代文明的标志,显然对西方社会病的形成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消费主义”在盲目消费的同时,给自然环境和资源造成极大的破坏。由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影响,西方消费主义迅速蔓延全球各地,如果不加以认真鉴别,将是一场文化灾难。某些国家的“文化霸权主义”,必须坚决予以抵制和批判!
与西方消费文化理论缺乏批判精神相反,马克思在研究消费问题时全面地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拜物教”,进而批判了消费异化和人的全面异化。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理论,理应成为西方消费文化研究合理吸收的重要学术资源。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西方消费文化研究向来与马克思主义水火不相容,使西方消费文化理论脱离了社会实际,脱离了人际关怀,脱离了阶级分析,在对西方社会的畸形发展过程中,反而充当了说客,这种社会责任意识的缺失,是西方消费文化研究的又一重大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