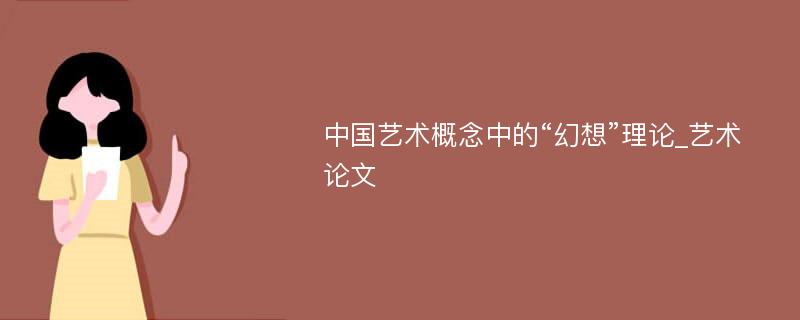
中国艺术观念中的“幻”学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说论文,中国艺术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9)06-0032-11
清画家戴熙论画每有惊人之语,他说:“佛家修净土,以妄想入门;画家亦修净土,以幻境入门。”这个“以幻境入门”,为画道一大因缘,也是中国艺术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反映了中国艺术独特的思想,这一思想至今仍然有价值。它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幻觉——幻觉主要指人心理中出现的虚假感觉,而中国传统哲学和艺术论中的“幻”则是一个有关存在是否真实的问题。
佛教从幻相、幻有、幻化三个方面看“幻”的特点。从性土说,一切法(包括可见的事象和大脑中的概念)都元实体性,都是由因缘和合而生灭,所呈现的是假相,这叫“幻相”。故幻是与“真”相对而言的。从存在形式上说,万事万物以及人们的心念,都是幻的存在,不是真有,而是假有,佛教称此为“幻有”。幻有是相对于“无”而言的。从万事万物的产生过程看,一切显现的现象,都是幻象,就像魔术师点化一样,所以称“幻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幻是虚,是相对于“实”而言的。这种幻化现象,既是一种“乍现”——刹那刹那,忽生忽灭,都无暂住;又是一种“诈现”——以不真实的面目来迷惑人。
在这三方面中,幻相侧重于假而非真,幻有侧重与无而非有,幻化侧重于虚而非实。反映了佛家哲学在幻方面的思想脉络。本文讨论中国艺术观念中的幻问题,就想以此为线索,来展示中国艺术家在其中的独特思考。不是理出一个像佛学的思路,而是以佛学此方面的观点为线索,对中国艺术论这方面已然形成的观点作一整理。
一、幻化:关于变幻的思想
中国哲学强调变化,宇宙即大化流行,它是生生不息、变化无穷的。在中国哲学看来,天地间是一个气的世界,万事万物都在阴阳二气的氤氲中浮沉,变化由是生焉。
变化的思想是儒家哲学的精髓。《易传》将《周易》古经中的朴素变易观,上升为一种贯彻天地人伦的至理,所谓“《易》者,易也”——《周易》就是一部谈变易的书。《易传》中所概括出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等,成为中国哲学的重要思想。而《易传》强调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也落实在变化上。变化思想是儒家哲学的重要基础。如宋明理学“生、仁一体”的学说,就是奠定在《易传》变易哲学基础上的。
但是,中国哲学还有另外一种思想,认为变化是一种幻象①,“变化”或许应叫“变幻”更确切,变即幻,变化是虚妄的事实。
《庄子·大宗师》中讲了一个故事:“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怕小舟丢失,将它藏在大壑里;怕山丢失,将它藏到大泽里。以为这样就可以保全,然而半夜里(此指冥然不觉),却有个大力士将他背走。这大力士就是变化。郭象注云:“夫无力之力,莫大于变化者也。”宇宙不主故常,才生即灭,一只看不见的巨手在拨弄着世界、改变着世界。
熊十力先生在《新唯识论》中曾引此作为他翕嗣成变思想的重要依据。他认为,本体即为大用,必有一翕一闢,由此开合之机,便生出生机变化。儒家由此变易的思想,“悟得人生有无上底崇高的价值,无限的丰富意义”,而释道两家却持“空幻的感想”,消极对待大化流行的节奏,儒家则“自有改造的勇气”。② 但他论证变化思想,却举庄子此一寓言,认为“极有理趣”。他以为庄子这段话强调的就是变化:“变化的力,是能揭天地以舍故趋新。故的东西,绝不会有暂时停住,忽然已是新起的事物了。天地万物,无时而不迁改,世间瞬时创新,而人或见为旧,舟和山,瞬息变易,而人或视之若前。”③
熊先生这一判断并不准确。庄子所表达的思想,与儒家的变易哲学完全不同。庄子通过这个故事,不是说明世界的变化意,而是说明变化是虚妄的。正因为世界变化如斯,新新顿起,密密畴移,所以这世界是虚幻不可把握、也不可与之俱走的。庄子哲学的落脚点不在变化,而在虚妄不实。熊先生的观点,与郭象之说倒是相似,郭象就是肯定世界的变化性的。郭象的理解也与庄子有较大的差异。
庄子藏舟于壑的论述有这样的背景:“鱼相与处于陆,相啕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犹有所遁。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很显然,庄子是要“忘”,从理性、知识的分别中走出,相忘于江湖,回到世界之中,从而“藏天下于天下”——融入世界之中,而不是站在世界的对岸,将世界当作自己的对象,自己似乎不在世界中。对于变化也是如此,人的生命就是一个变化过程,如果执着于这样的变化,人就永无安宁之时,顺应自然,才是根本之道。庄子哲学强调悟道的最高境界是不生不死、不将不迎,就是与物同化,不以物易己,不被外物所奴役。也就是说,变化是表面的事实,人不能为变化的表相所迷惑。《秋水》中说:“万物一齐,孰短孰长?道元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满,不位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是所以语大义之方,论万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宇宙的变化,是一幻化的过程,以短暂之人生,随幻化之世界,必然流荡难返,虚妄不实。庄子由此建立他的生命意义理论。
佛教哲学不讲变,而讲幻。大乘空宗讲中空幻有,尤其是中观学派的空幻思想对中土影响甚大,龙树上承阿含与般若思想,提出的“俗有真空,体虚如幻”的中观思想,成了佛教空幻思想的代表。佛教强调,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如《金刚经》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维摩诘经》说:“一切法生灭不住,如幻如电,诸法不相待,乃至一念不住,诸法皆妄见,如梦如焰,如水中月,如镜中像。”僧肇在解释此语时说:“诸法如电,新新不停,一起一灭,不相待也。弹指顷六十念过。诸法乃无念顷住,况欲久停!无住则如幻,如幻则不实,不实则为空,空则常净,然则物物斯净,何有罪累于我哉!”④ 生生灭灭世界的虚妄不实,是佛家哲学的基本观点。
释道两家都不否定事物变化的特点,但又不肯定变化的实体性,都认为变是幻——我们看到的世界的变化,只是其表面,是虚妄的;我们对这样的幻象的执着,就是妄见,是颠倒见解。人生的烦恼、生命的枯竭往往都是由对幻象的执着所造成的。两家通过幻的辨析,示人以解脱之法。所以,释道两家有关变的思想,不是变化哲学,而应是一种“幻化哲学”。
儒家斥这种幻化学说为虚妄之见,如张载《正蒙》说:“释氏语实际,乃知道者所谓诚也,天德也。其语到实际,则以人生为幻妄,以有为为疣赘,以世界为阴浊,遂厌而不有,遗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诚而恶明者也。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故语虽似是,观其发本要归,与吾儒二本殊归。”又说:“释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灭天地,以小缘大,以末缘本,其不能穷而谓之幻妄,真所谓疑冰者与!夏虫疑冰,以其不识。”而当代哲学研究中,一提到佛道的幻化哲学,总会给它戴上消极的虚无主义的帽子。其实这样的学说并非没有理论价值,它所带给中国文化的,并不都是消极的东西。儒家的变化哲学,由天地无一息不变的学说中导引出昂奋的进取思想;而释道的幻化思想,却促进人们在流荡变易的世界中思考生命的价值。
释道的幻化哲学对中国艺术和审美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生命的不可把握,人生乃百年孤独之里程,促使艺术家去聆听生命深处的微妙呻吟;变化是表象,万物生灭如流光逸影,促进中国艺术家在形式之外追求真实的生命意义;而释道幻化哲学视知识为赘痈、人生为痛苦,故取超脱之道路,也为强调生命安顿的中国艺术和审美生活提供了理论支持。
在中国艺术中,有一种变化为虚幻的思想。如八大山人有一幅《鱼鸟图》长卷,今藏上海博物馆,是八大晚年的重要作品。在八大绘画思想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起手处,画一拳怪石,上蹲两只鸟,中段画一条鱼,略大,画的尾部在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着一小鱼。画有三段题识,其中第三段谈“善化”,其云:“东海之鱼善化,其一曰黄雀,秋月为雀,冬化入海为鱼,其一曰青鸠,夏化为鸠,余月复入海为鱼。凡化鱼之雀借以肫,以此证知漆园吏之所谓鲲化为鹏。”
八大山人这幅画表现的就是“善化”——善于变化的思想。八大用艺术的方式,来说明变化的不确定性和存在的虚幻本质。这幅画画的是“鱼鸟互转”的故事,《庄子·逍遥游》中,说一条名为鲲的大鱼,化而为名叫鹏的大鸟,八大通过这个人所共知的故事,表达的却是与庄子不同的思想旨趣。庄子强调的是无待的逍遥,而八大强调的是存在的幻化。这幅画告诉人们,世界的一切都是“善化”的,画的是鸟,却又是鱼,画的是鱼,却又是鸟,以前是鱼,现在是鸟,现在是鸟,又将变成鱼。从名上说,它可以说是鱼,又可以说是鸟,它是非鱼非鸟。曾经有海外学者从生物性转化的角度来理解这一问题,是对这画的误解。这幅画中,有关于名和实两方面的质疑。就名上说,此之谓鱼,彼之谓鸟,然而鸟将变鱼,鱼将变鸟,其名将何定?就实上言,物皆处于大化流转之中,没有一个定在,何能言实?形虽有而无质,名虽名而未名,名实皆不能定,故而为妄,所描绘的只是一个虚空世界而已。
明代画家徐渭也喜欢在幻化的世界中追求真实的意义。他有《旧偶画鱼作此》诗,从云林的画写起,诗中说:“元镇作墨竹,随意将墨涂。冯谁呼画里?或芦或呼麻。我昔画尺鳞,人问此何鱼?我亦不能答,张颠狂草书。迩来养鱼者,水晶杂玻璃,玳瑁及海犀,紫贝联车渠。数之可盈百,池沼千万余。迩者一鱼而二尾,三尾四尾不知几。问鱼此鱼是何名?鳟鲂鳣鲤鲵与鲸。笑矣哉,天地造化旧复新,竹许芦麻倪云林!”⑤ 云林画中的竹,画的像芦(当是芦苇)又像麻,他自己画中的鱼,是此鱼又是彼鱼,物之形态没有一个定准。是他们画不像?当然不是,因为“天地造化旧复新”,世事轮转何能定,一切都是虚幻的。青藤《仿梅花道人竹画》说:“唤他是竹不应承,若唤为芦我不应。俗眼相逢莫评品,去问梅花吴道人。”⑥ 也说的是这个意思。
在中国艺术观念中,还有一种将幻化的世界颠倒过来的思想。幻化的世界是虚妄的,如将此幻化现象视为实有,就是颠倒见解,是与真理相反的妄见。正像《维摩诘经》上所说:“虚妄分别孰为本?答曰:颠倒想为本。”人生的一切烦恼都来自这样的妄见。中国艺术论中也有类似的观念。
唐代以来中国艺术史上有关于“雪中芭蕉”的争论,王维曾作《袁安卧雪图》,画雪中芭蕉,此图曾藏北宋沈括家,沈括认为此图“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难可与俗人论也”。⑦ 对其中所透露出的思想大加赞赏。芭蕉乃易衰之物,从自然的时序上说,不可能出现雪中芭蕉的事实。王维这样画,是一种颠倒时序的做法。
为什么要颠倒时序?其中深藏的思想正与传统幻化哲学有关。他的这一画法,直接根源是佛家思想。佛经中有“火里生莲花”等说法,莲花怎么可能在火里绽放?这也是一种颠倒见解。明李流芳合二事云:“雪中芭蕉绿,火里莲花长”。⑧ 错乱的物理观念反映的是对妄见的颠倒,将原有的看似正常实是颠倒的秩序再颠倒过来。
这种思想在后代产生很大影响。徐渭《蕉石牡丹图轴》,是一幅大写意作品,画芭蕉、英石和牡丹花,上有题识数则,记录一次癫狂作画的经过。初题说:“焦墨英州石,蕉丛凤尾材。笔尖殷七七,深夏牡丹开。天池中漱犊之辈。”又识:“画已,浮白者五,醉矣,狂歌竹枝一阕,赘书其左。牡丹雪里开亲见,芭蕉雪里王维擅。霜兔毫尖一小儿,凭渠摆拨春风面。”旁有小字:“尝亲见雪中牡丹者两。”在右下又题云:“杜审言:吾为造化小儿所苦。”
“为造化小儿所苦”,意指人生无常,人生如一场戏,世界背后似有一只无情的手,翻云覆雨,颠倒东西。青藤在醉意中要跳出颠倒的世相,不为幻术所迷,在酣然狂放之中,解脱性灵。题诗中所说的“牡丹雪里开亲见,芭蕉雪里王维擅”,将王维的创造引到更加荒诞的地步。雪中不可能有牡丹、芭蕉,青藤却说,亲自见到雪中有两朵牡丹,这些胡言乱语,颠倒了时序,颠覆了规矩。徐渭曾画有《梅花蕉叶图轴》,画大片芭蕉叶铺天盖地向上,几乎遮却画面的中段,芭蕉叶中伸出一段梅枝,上有淡逸的梅花数点。右上题云:“芭蕉伴梅花,此是王维画。”用荒诞的表达,颠倒既有的秩序,表达追求真实生命的见解。
清代艺术家金农曾画有《雪中荷花图》,并题云:“雪中荷花,世无有画之者,漫以己意为之。”⑨ 雪中荷花本是禅家悟语,元画僧雪庵有《罗汉图册》,共十六开,今藏日本静嘉堂,其后有木庵跋文称:“机语诗画,诚不多见,而此图存之,亦如腊月莲花,红烟点雪耳。”金农说:“慈氏云:蕉树喻己身之非不坏也。人生浮脆,当以此为警。秋飙已发,秋霖正绵,予画之又何去取焉。王右丞雪中一轴,已寓言耳。”又云:“王右丞雪中芭蕉,为画苑奇构,芭蕉乃商飙速朽之物,岂能凌冬不凋乎。右丞深于禅理,故有是画以喻沙门不坏之身,四时保其坚固也。”芭蕉易坏,雪中元荷,画雪中芭蕉和荷花,表达的是不为幻化所惑的思想。
由此可见,幻化思想是把握中国艺术宋元以来发展的不可忽视的角度。
二、幻有:关于形式即幻象的思想
中国艺术在两宋之后,形成了“形式即幻象”的思想。艺术形式是幻象,没有实在意义。如画家画一物,并不是为了表现这个物。作为形式构成因素的山水花鸟等等,可以说是花鸟山水,因为它们有山水花鸟之形,但又可以说不是山水花鸟,因为画家根本不是要将它们当作山水花鸟来看,只是借助于它们的形式来表达心中的感觉。如你看云林,只停留在疏树、空亭上,你就得不到云林;看八大,分辨他画的是什么鱼、什么鸟、什么花,你就不可能懂得八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山水花鸟等都是幻象,都是指月之指,登岸之筏。正因此,中国画发展才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山水花鸟,梅兰竹菊,无数人画过,但我画又有何妨!形式即为幻象,关键是心灵的传达,水墨胜过丹青,一角一边,都是一个完整的叙述,单柯片石,可以上掩唐宋巨手,一切都是“幻景”。唐代禅宗大师南泉指着牡丹花,对弟子们说:“时人看一株花如梦幻而已。”不少中国艺术家也有这样的思路。这里谈中国艺术论中三个相关的说法。
第一,求于骊黄之外说。
古代审美与艺术观念中,有一种“求于骊黄之外”的学说。倪云林《临王漫庆墨竹轴》云:“以中兄长家藏澹游竹石二帧,真有天真烂漫出乎笔墨町畦之外之逸韵,因篝灯下戏效之,虽不能摹形似,亦颇得骊黄牝牡外也。”清戴熙转述苏轼的一则画事说:“东坡曾在试院以殊笔画竹,见者曰:‘世岂有朱竹耶?’坡曰:‘世岂有墨竹耶?’善鉴者因当赏于骊黄之外。”东坡将“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作为他所提倡的文人意识的关键内容,意思就是“求于骊黄之外”。苏轼评张旭书法时说:“世人见古德有见桃花悟者,便争颂桃花,便将桃花作饭吃,吃此饭五十年,转没交涉。正如张长史见担夫与公主争路,而得草书之法,欲学张长史,日就担夫强求之,岂可得哉!”⑩ 在苏轼看来,艺术也是一样,就像灵云悟桃花,与桃花并无多大关联,你如果盯着桃花来思考,永远不得入门。元天如惟则禅师论扬补之梅花时说:“补之能为梅写真,梅华又为翁传神。翁比梅华更清绝,眼光烁破珊瑚月。”(11) 画中一枝梅花,却不能当梅花看。倪云林有诗云:“爱此风林意,更起丘壑情。写图以闲咏,非在象与声。”(12) 戴熙自题画云:“山色本无色,泉声非有声。顿觉眼耳妄,根尘何自生?”(13) 在他们看来,画中出现的山林风色,都是幻,不是实有;执着于山林的风色,都是妄见。绘画的妙处在声色之外。
明代画家陈淳(字白阳),在中国绘画史极负盛名,他不仅是中国花鸟画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在山水、书法方面也有独特的贡献。王穉登云:“天才秀发,下笔超异,画山水师米南宫、王叔明、黄子久,不为效颦学步,而萧散闲逸之趣宛然在目。一花半叶,淡墨倚毫,而疏斜历乱,偏其反而,咄咄逼真,倾动群类,若夫翠辨竹寻、葩分蕊析者,俗工之下技,非可以语高流之逸足也。”(14)
白阳不是“翠辨竹寻、葩分蕊析”——斤斤于形式者。北京故宫藏白阳《仿米山水长卷》,白阳自题云:“人恒作画曰丹青,必将设色而后为专门,而米氏父子戏弄水墨,遂重名后世,石田先生尝作墨花枝亦云当求于形骸之外,画亦不可例论与!”北京故宫又藏其《花觚牡丹图》,白阳自题云:“余自幼好写生,往往求为设色之致,但恨不得古人三昧,绝烦笔研,殊索兴趣,近年来老态日增,不复能事少年驰骋,每闲边辄作此艺,然已草草水墨,昔石田先生尝云:观者当求我于丹青之外,诚尔,余之庶几。”在这两处题识中,白阳转述了吴门宗师沈周的话:“求我于丹青之外”、“当求于形骸之外”,这是吴门画派的重要原则。白阳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由丹青而水墨,由形似而草草笔致,由驰骋纵横而淡逸平和,去画史纵横习气,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白阳视绘画形式为幻有。北京故宫藏白阳的《墨花钓艇图册》,画梅、竹、兰菊、秋葵、水仙、山茶、荆榛、山雀、松枝及寒溪钓艇,共十段。前九幅都是花木,最后一幅却画寒江之上,清流脉脉,一小艇于中闲荡,和前面的内容似乎不协调。白阳将它们束为一册,有自己的考虑。末幅上他有题识说:“雪中戏作墨花数种,忽有湖上之兴,乃以钓艇续之,须知同归于幻耳。”这是一次雪后墨戏之作,伴着漫天大雪,他率意作画,为竹,为梅,为点点花朵,为雪中的青松,江山点点,山林阴翳,在他的笔下翻滚,在他的心中流荡,他画着,画着,意兴遄飞,外在的形象越来越模糊,有形世界的拘束渐渐解脱,他忽然想到着一小舟,带他远逝,遁向远方,遁向空茫的世界。由此他得出,一切有形的存在都是“幻”,花木是幻,小舟是幻,一切的存在都是幻,不是不存在,而都是流光逸影,都是不断变化过程中的环节,生生灭灭,无从确定,都是幻有,虽有而无。一如北宋法演禅师所说的:“以相取相,都成幻妄”。(15)
白阳、青藤、云林、东坡,乃至宋代以来的很多艺术家,将形式看作幻象,否认形式的实在性。东坡的枯木怪石、云林的疏林空亭、青藤的雪中莲花等等,这些形式都是一个幻象,是一个昭示存在的非确定性的刺激物,它们通过不合规矩和美感的存在方式,说明世界的存在并非由你感官所及就能判断,一切对物象的执着是没有意义的。如云林寂寥的疏林空亭,它们的存在,就说明不存在,或者说是非真实的存在。我们不可能从疏林空亭的具体空间结构、色彩特点等,获得这幅画的确实意义。
这种形式即幻象、求于骊黄之外的思想,与传统艺术理论中的一些观念看似相同,其实大异其趣。传统艺术论中类似的观点大约有三:一是象外之象的理论,这是意象言关系影响下的理论,要有象外之意,形式是表意的,意决定着形式存在的价值。如我们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能发现东篱南山之外的意义。二是形神理论,从汉代以来形成的中国艺术的传神理论,强调以形写神、以神统形、传神写照,这是人物品藻中形成的观点,后来影响到人物画,在顾恺之那里,神特指人的眼神,并由眼神发而为人的内在精神。唐宋以来,这一理论又发展成与韵味说等相联系的观念。三是韵味说。这一学说自六朝时形成,后来成为中国艺术批评的重要标准,强调艺术要有超越形式之外的意味,如所谓余味说、韵外之致说、含不尽之意如在象外、诗罢有余地等等,都属于这方面的观念。
上述三种观点的共同性在于,它们都强调艺术意义的根本不在形式,而在形式之外的因素;艺术形式是受神、韵、味等决定的;成功的艺术创造应该是形式和神韵、意味等的统一。可见,这些观点中都没有对形式本身的否定,形式的实在性并没有受到质疑。而两宋以来文人意识影响下出现的形式即幻象说,是对形式本身的超越。
第二,形为影子说。
徐渭曾提出:“舍形而悦影”(16) 的观点。他题《画竹》诗说:“万物贵取影,写竹更宜然。”又有题《牡丹画》诗云:“牡丹开欲歇,燕子在高楼。墨作花王影,胭脂付莫愁。”他的意思是,他画一枝竹,不是追求如何画像,而是醉心于表现一个影影绰绰的形式。他画牡丹,要为牡丹画影,淡去色彩,在外形上只取其梗概,似是非是。
“舍形悦影”说是中国艺术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形是具体的,影是虚幻的,舍形而悦影,要以虚幻的表达取代具体的形式。中国艺术论认为,好的艺术形式不是现实世界的模本,而是对这一世界的超越,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幻象;一个确实的存在,会引起人物质之想,而一个“影”的存在,若有若无,可以使人从具体的物质形式中逃脱。
中国艺术重影,不是重视物质意义上的影子,如光影、月影、花影、鸟影,而是强调存在的若有若无的特征,强调一切存在皆非定在的思想,突出生命的不可把握的特点。在道禅哲学看来,外在的世界是虚而不实的,如同影子一样。前面我们所引南泉所说的:“时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庄子也曾将人的生命比喻为与影子竞走的过程。他曾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害怕自己的影子,就拼命地跑,但影子也随着他跑,最后这人累死了。庄子感叹到,你为什么不到大树下面,大树下不就没有影子了?这大树下就是他所说的自然天全之道。庄生化蝶的故事也强调现实世界如影如梦的特点。中国艺术喜欢影,强调“舍形而悦影”,通过虚幻的形象,表达对世界、对生命的看法,也受到道禅哲学的影响。
中国美学追求镜花水月的美,是传统哲学幻有思想的体现。不坐实,不粘滞,飘渺无痕,如苔痕梦影,如空花自落。严羽说:“盛唐诸公,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澈玲珑,不可凑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中国画家将“寒塘雁迹,太虚片云”(沈灏《画麈》)作为绘画的最高境界,如孤鸿灭没,若隐还现,寒潭雁行,去留无迹。董其昌说:“摊烛作画,正如隔帘看月、隔水看花,意在远近之间”(《画禅室随笔》),也在申述此旨。
八大山人有“画者东西影”的说法,这是他关于绘画的一个纲领性学说。绘画是空间艺术,绘画中需要表现一定的空间形态,必须呈现具体的、物象。但八大山人认为,画中所画的“东西”——形象,应该只是“东西”的一个“影子”。从形式特征看,我们无法复制一个与外在世界完全相同的物体;我们所见外在的“东西”,其实只是一个幻相。所以八大认为,我们在绘画中表现的形式,只能是“东西”的一个影子。更重要的是,通过绘画中影影绰绰、似像非像的形式,能帮助人放弃对法的执着,把握实在的意义世界。
这里再以陈白阳为例。白阳于1536年作墨花图册,其自题云:“嘉靖丙申春二月,淹留累日,独坐静寄庵,戏作墨花八种,灯下戏题八绝句,以形索影,以影索形,模糊到底耳。”(17) 此卷墨花写意影影绰绰,似花非花,白阳明显在追求影的妙处。“以形索影,以影索形,模糊到底耳”,可以说是晚年白阳绘画的重要特点。
白阳以花鸟见著,其实他的山水也别有风味,今见其很多山水作品,多为“模糊到底”之作。他曾作《云山图卷》,今藏北京故宫,显示出他从二米山水中脱略出的一家风味。米家山水重视气化氤氲的感觉,以此来表现宇宙间气韵流动的节奏,而白阳却从云山墨戏中转出幻有的思想。米家山水重气,白阳山水重幻。这幅《云山图卷》得镜花水月之妙。画以淡墨染出一痕山影,以荒率之笔匆匆勾出山林屋舍等轮廓,风物悠远,烟水迷离,极有分致。上有石天禅师所书“画外别传”四大字引首。这四个字真可谓对白阳绘画的妙评。他的画超越法度,境界高逸,似流光逸影,其妙处当在画外求之。石天禅师并有题跋云:“撇却金针玉线,倒拈无孔笛,吹彻古轮台,所谓无佛处称尊,高扬师子吼。”“撇却金针玉线”,意思是不以色貌色,以形写形。“无孔笛”和在“无佛处”得之,意思都是强调法外求妙,所谓画外别传是也。北京故宫藏白阳《雪渚惊鸿》长卷,并书谢惠连《雪赋》,作于1538年,是白阳晚年的作品,引首有白阳所书“雪渚惊鸿”四字,既是此画之题,也道出了此画的风味。这幅画将雪渚惊鸿的不粘不滞特点表现得非常好。夏日画雪,画心中之雪,招高天之凉意。画雪渚惊鸿灭没之状,皑皑白雪中,有山村隐约其问,寒溪历历,雪坡中有参差芦苇,一片静谧澄明,高天中有飞鸿点点。给人以雪梦生香的感觉。
唐寅为吴门画派中的天才画家,晚年他受佛学影响很深。李开先《中麓画品》说:“唐寅如贾阆仙,身则诗人,犹有僧骨。”他号六如居士,取《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之意,六如意为人生就像梦、幻、泡、影、露、电,都是形容生命短暂而不可把握。梦取非实;幻取非真;如大海一沤,忽起忽灭;如影恍惚,似有还无;如晨露历历,见阳光就干;如飞点过隙,一闪即无。他的画就带有梦幻空花的色彩。
他的《桐阴清梦图》,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画一人在青桐树下坐而人眠,上面唐寅题有一诗:“十里桐阴覆紫苔,先生闲试醉眠来。此生已谢功名念,清梦应无到古槐。”画南柯一梦的故事,但南柯一梦的主人是梦到槐安国,娶了漂亮的公主,当上南柯太守,醒后才知是一场大梦。唐寅说他对这种功利之梦不感兴趣,他做的是桐阴下的清梦,他要梦到一个清净的世界去。唐寅的画中有很多表现滔滔人世皆梦幻的内容。如《葑田行犊图》,画一人骑在牛背上归来。有题诗云:“牧犊归来绕葑田,角端轻挂汉编年。无人解得悠悠意,行过松阴懒着鞭。”又有《雪山会琴图》,画大雪下,诸友人会聚一室,弹琴寄意。有题诗云:“雪满空山晓会琴,耸肩驴背自长吟。乾坤千古兴亡迹,公是公非总陆沉。”这两幅画以及题诗表达了人生如梦幻的思想,一切都不可挽回的逝去,一切的喜怒哀乐都随历史的风烟淡去,他画中的一痕清影,突出的是他的醒觉。1520年,他曾画有《落花诗意图》,画面简单至极,两只春燕,一朵落红,飘飘零零,形简而意丰,那是人生的叹息。
第三,无迹可求说。
严羽论诗提出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观点,本是禅语(18),这是一个在中国艺术论中影响深远的观点,就是不露痕迹,禅宗所谓不粘不滞、元住无相是也。
为什么要淡去“迹”?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世相,如苔痕梦影,当然无法形之于“迹”,一滞于“迹”,就表达不出这一特点。如南宋石溪心月《墨梅一题序》:“顷在四明同清凉范长老游大梅,或索和华光师墨梅十题,题曰悬崖放下,曰绝后再苏,曰平地春回,曰淡中有味,曰一枝横出,曰五叶联芳,曰高下随宜,曰正偏自在,曰幻花灭尽,曰实相常圆。首尾托物显理,偕位明功,以形容禅家流工夫。从入道应世,至于得旨归根边事。无准于实相常圆,着语云:黄底自黄青底青,枝头一一见天真;如今酸咸都忘了,核子如何说向人?予愧短乏,哦晃非素习,不得已亦勉强思量。到思量不及处,果幻花灭尽耶?墨梅无下口处耶?”(19) 北宋僧人华光善画梅,其画梅法影响甚大,其“幻花灭尽”思想,就是要淡去一切痕迹,画一物,则忘一物,因为物不是物。元初明深禅师善画,有题瓶梅诗云:“折来斜插胆瓶中,数点半开春意融。疏影横斜窗漏月,暗香浮动户来风。既无根本那能实,徒有标姿总是空。莫待弃情时节至,只今便作朽枯容。”(20) 虽有美姿,总是空空,总是幻象。
传菩提达摩所作《无心论》说“夫至理无言,要假言而显理。大道无相为,接鹿而见形。”艺术也是如此,不能不托之于相。如在绘画中,下笔就有凹凸之形,一点水墨落入纸中,打破了一片虚无,从“无”的深渊突出出来。所以,凡有形之象,不可无“迹”,但高明的艺术表现是要尽量淡去“迹”的束缚,似有若无,似淡若浓,使其迹象虚幻,像倪云林那样,远山变成了一痕,长河变成了一抹,所谓一痕山影淡若无,一抹清流无踪迹。像八大山人那样,一只鸟儿虚化为似有若无的形状。
受这一思想影响,中国艺术产生了一些特别的形式感。正是受此思想影响,中国绘画从总体发展趋势上说,渐渐淡去了穠丽的色彩。由丹青而水墨,就受到是“解得色染皆虚空”哲学的影响,不光是材料变化所带来的。徐青藤《枯木石竹》说:“道人写竹并枯丛,却与禅家气味同。大抵绝无花叶相,一团苍老莫烟中。”青青翠竹,郁郁丛林,都没有了踪影,淡化为一团苍老暮烟中。青藤这方面的咏叹很多。他题《芭蕉墨牡丹》诗云:“知道行家学不来,烂涂蕉叶倒莓苔。冯伊遮盖无盐墨,免倩胭脂抹瘿腮。”又题《雪牡丹》诗云:“银海笼春冷茜浓,松煤急貌不能红。太真月下胭脂颊,试问谁曾见影中?”再有《画红梅》诗云:“即使胭脂点,犹成冷淡枝。杏花无此干,铁树少其姿。挂壁纷红雪,闱春在锦池。元由飘一的,娇杀寿阳眉。”《画百花卷与史甥题曰漱老谑墨》云:“世间无事无三昧,老来戏谑涂花卉。藤长刺阔臂几枯,三合茅柴不成醉。葫芦依样不胜揩,能如造化绝安排。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拨皆吾五指栽。胡为乎,区区枝剪而叶裁,君莫猜,墨色淋漓雨拨开。”《水墨牡丹》云:“腻粉轻黄不用匀,淡烟笼墨弄青春。从来国色无妆点,空染胭脂媚俗人。”在这里牡丹失去了胭脂之色,变而为又黑又丑;红梅的胭脂点,化而为冷淡枝;他没有兴趣去依样画葫芦、涂抹百花争艳的形貌,而重视大千世界内在的意趣。在墨色淋漓中,一切缛丽的色彩、动人的形貌都不存,因为一切色相都是乍见之影;一切色相的摹绘都只能取媚俗人。
中国书法也受到这无迹思想的影响。如唐初智永之书,有浓厚的禅味,前人评其书,认为其妙在收束之处,不粘不滞,自有腾踔无迹之意。清何绍基评其《千字文》说:“笔笔从空中来,从空中住,虽屋漏痕,犹不足以喻之”。唐草书大家怀素亦得无迹之妙。如其中年以后所作《论书帖》,极受佛学思想影响,结体允稳,风流飘逸,真有仙人啸树之美。而元倪云林之书法,也有不落风尘之味,波澜不惊,不疾不徐,从容推行,似落非落,后世画人多仿其作。
三、幻相:关于幻的真实性问题
中国艺术突出幻的表达,最终是为了追求“真”。因为,幻即虚妄,即假,假即非真。中国艺术论强调幻,是与对人的真实生命关注密不可分的。我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来理解这方面的思想。
第一个层次是幻而非真。绘画界曾经有关于“写真则不真”的讨论。古代人物画叫“写真”,为人物取影。然而,在很多画家看来,这样的“真”,其实是虚而不实、假而不真的。通过画人物,怎么能够得到“真”?只能得到“幻”。苏轼《赠写真何充秀才》说:“此身常拟同外物,浮云变化无踪迹。问君何若写吾真,君言好之聊自适。”世界在流荡,人生如幻境,何以能写出人之真,只有出一个幻象,只能聊以自娱罢了。这就像南宋无准师范题一个僧人的草虫画所说的:“似则似矣,是则未是;若是伶俐衲僧,不作这般虫豸。”(21) 清戴熙曾为他的朋友太常仙蝶画像,并赠诗云:“瞬息几千年,天空任去来。果然是仙客,何必守瑶台。冷暖不逾节,交游殊爱才。人间梦幻耳,此相岂真哉!”其中也谈到了世事如幻、写真不真的观点。
中国艺术家以自己的切身体验,诠释由幻及真的思想。倪云林《为方厓画山就题》诗中写道:“我初学挥染,见物皆画似。郊行及城游,物物归画笥。为问方压师,孰假孰为真?墨池搵浥滴,寓我无边春。”他开始学画,模仿外物,觉得一切都是真的,后来他悟出,他所描绘的外在色相世界纵然再真切,其实也是假的,所以他后来的画,色彩没有了,外在具体的形式也虚化了,越来越淡逸,越来越不像了,看起来他的画是渐渐“假”了,其实,他离“真”却越来越近。
清傅山有诗曰:“天下有山遁之精,不恶而严山之情。谷口一桥诞危岸,峰回虚亭迟曜形。直瀑飞泻鸟绝道,描眉画眼人难行。觚觚拐拐自有性,娉娉婷婷原不能。问此画法古谁是,投笔大笑老眼瞪。法无法也画亦尔,了去如幻何云成。”(《题自画山水》)他的画“觚觚拐拐”,而不是“娉娉婷婷”。为什么他这样做?因为他“了去如幻何云成”,万法都是幻象,他以丑陋、古怪的表达,消解外在的障碍,使“自有性”彰显,由假而即真。金农喜欢画梅,梅花有香,他总是说这是“空香”——是幻而不真的,汪巢林也善画梅,金农常与他交换这方面的看法。他有《画梅寄汪士慎》诗云:“寻梅勿惮行,老年天与健。山树出江楼,一林见山店。戏粘冻雪头,未画意先有。枝繁花瓣繁,空香欲拈手。”(22) 他要赠给朋友一缕空香,以这幻而不实的形式,共期真实的生命呈现。
第二个层次是非幻非真。在中国一些艺术观念看来,如果有真幻的心念,进而屏弃虚幻,追求真实,并不能得到真,因为这是一种分别的见解,一分别,就会导致心灵的执着,一执着,就不会有自由的创造。要追真去幻,还必须忘却真幻,超越真幻的分别。戴熙说:“以不动求动,以无声求声,实以有形求无形,是真是幻,非真非幻,故作秋声图漫题。”(23) 强调一相不着,非幻非真。
徐渭《书倪元镇画》题诗云:“一幅淡烟光,云林笔有霜。峰头横片石,天际渺长苍。虽赝须金换,如真胜璧藏。偏舟归去景,入画亦茫茫。”这里的“虽赝须金换,如真胜璧藏”二句,并非说所见云林画是赝品,相对于外在世界来说,云林的画是“赝”——是不真的,只是一个幻象。青藤诙谐地说,云林的笔头似乎有霜,经他笔头一过滤,这世界的一切似乎都染上了萧瑟的意味。但这萧瑟的世界,却“如真”,表现了“性”的真实。青藤曾说:“物情真伪聊同尔,世事荣枯如此云。”(24) 看是真,却是伪;虽是伪,却是真。世界本来运转就是如此,荣枯更替,无有终息。要在不为表相所迷惑,在世界流转的幻象中发现生命的真实。
第三个层次是即幻即真。唐玄觉《永嘉证道歌》说:“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幻身即是法身,幻相即为真相。这样的思想,正是中国很多艺术家的思路。
戴熙有论画语道:“实境亦幻境,独游真闭关。江山风月外,何处不浮山。”“佛家修净土,以妄想入门,画家亦修净土,以幻境入门。夫幻妄乌可用焉?不知识解明通后,随处皆成真实,又何幻妄之非真实也。”随处即真,即幻即真。幻,既是对执着的否定,也是对“真”的肯定。戴熙认为,“识解明通”(将妙悟)后,幻也是真实。
我们可以以假山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取“假山”之名,意为不真之山,它是“假”的“山”。假山是为了满足人们山林之想而创造的,假山是山的替代。唐人姚合《寄王度居士》诗论假山有云:“无竹栽芦看,思山叠石为。”将山林之景缩于庭院之中,以尽卧游之趣。假山是作为真山的替代形式而发展起来的。虽然是山的替代形式,但假山毕竟不是真山,它是“假”的山。
假山是否没有真山“真”?深通园林假山之妙的袁枚说:“常州杨青望《南涧晚归》云:‘岳寺风声起暮钟,残阳归去兴尤浓。停车欲认登临处,忘却西南第几峰。’陈郁庭《造假山》云:‘历尽嶙峋兴愈浓,归来犹自忆芙蓉。阶前叠石呼僮问,认是曾游第几峰。’两首相似,俱有羚羊挂角之意。”(25) 游山林归来,又见假山,假山没有真山大,假山没有所游的山“真”,这样的假山还有什么意味?明人谢肇淛就曾对此质疑道:“假山之戏,当在江北无山之所,装点一二,以当卧游。若在南方,出门皆真山真水,随意所择……又何叠石累土之工所敢望乎?”又说:“然北人目未见山,而不知作,南人舍真山而伪为之,其蔽甚矣。”(26) 他将假山称为“伪”——是不真的。这样的观点难称允当。北人做假山并非因为北方无山,北方之山多矣。他没有看到假山的独立艺术价值,将假山仅仅当作真山的替代品。如果假山不是为了让人体会山的高耸远大,而是表现人心灵的体验,山居庭院中有这样的假山在,更能唤起人们对生命的把玩,流连于真山与假山之间,玩味于实有与空灵之境,于羚羊挂角处寻生命的真义,这样的假山存在不但是可有可无,更给人带来无穷的意味。
假山胜过真山,如果说这样的话,很多人恐怕不会同意。其实这正是中国传统艺术的观点。董其昌说:“以径之奇怪论,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绝不如画。”山水画高于真山水在于笔墨的精妙,笔墨不是纯然的形式,而是表现心灵的语言,艺术家用心灵照亮了山水,假笔墨而表达出来。纯然的山水是外在的对象,是与人的心灵无关的存在物。而山水画是一段心灵的轻歌,是人的生命光辉照耀的世界,当然要高于一般的存在物。假山之妙也是如此,它虽然是对真山的隐括,但却是艺术家的创造,是艺术家心灵浸染的结果,僵硬的石被艺术家的生命之光照亮了。一片假山,呈现的不仅是对大千世界的概括形式,更是人的心灵的创造、生命的体验,假山是“韵人纵目、云客宅心”的体现。
中国的假山艺术,就是对“山”的真实意义的发掘,也是对世界真实意义的发掘。虽是假山,却将山的灵魂出落出来,艺术家以几块石头来雕刻心灵,通过心灵的浸染,将石头变成了活物。此正是真山所不可比也,所以说虽假却真。在这个意义上说,假山,不是假的山,而是真正的山。王世贞《弇山园记》中说的“世之目真山巧者,曰似假。目假者之浑成者,曰似真”正是这个意思。这正是即假即真的思路。
收稿日期:2009-04-18
注释:
① 本文对“幻象”与“幻相”二词有所区别。幻象,指虚幻的存在形式。幻相,则是从性上说明存在的非真实性。
② 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熊十力全集》第三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
③ 见前揭,第134页。
④ 僧肇:《注维摩诘经》,大正藏第38册。
⑤ 徐渭:《徐渭集》,卷五,徐文长三集之五。
⑥ 徐渭:《徐渭集》,卷三七,徐文长逸稿之八。
⑦ 关于王维此画所引起的争论北宋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其中多有批评王维犯常识错误者。如明谢肇淛《文海披沙》卷三说:“作画如作诗文,少不检点,便有纰缪,如王维雪中芭蕉,虽闽广有之,然右丞关中极寒之地,岂容有此哉?”钱钟书认为此说“最为持平之论”(见《谈艺录》附说二十四)。面在近现代的画学研究中,也有类似此论者。如俞剑华谈到此时说:“画家偶一为之,究非正规。”(《中国画论类编》上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44页。)也有误解将芭蕉置雪中为表达生意之说,如文徵明画《袁安卧雪图》,有跋云:“赵松雪为袁道甫作《卧雪图》,老屋疏林,意象萧然,自谓颇尽其能事。而龚子敬题其后,以不画芭蕉为欠事。余为袁君与之临此,遂于墙角作败蕉,似有生意。又益以崇山峻岭、苍松茂林,庶以见孤高拔俗之蕴,故不嫌于赘也。”(汪石可玉《珊瑚网》卷三十九)
⑧ 《檀园集》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 金农:《冬心先生杂画题记》《美术丛书》第三集第一辑。
⑩ 《东坡题跋》卷四,言张长史书法。
(11) 《天如惟则禅师语录》卷五,补之梅,卍新纂续藏经第70册。
(12) 倪云林:《清閟阁集》卷二。
(13) 戴熙:《习苦斋画絮》卷九。
(14) 《吴郡丹青志》,逸品志。
(15) 《法眼禅师语录》卷下,大正藏,第47册。
(16) 《徐渭集》卷二十,徐文长三集之二十。
(17) 《式古堂书画汇考》画卷卷五。
(18) 羚羊挂角:出自禅宗,《景德传灯录》卷十七:“(道膺禅师谓众曰:)如好鬣狗,只好寻得有踪迹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迹,气亦不识。”又卷十六:“(义存禅师谓众曰:)我若东道西道,汝则寻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你向什么处扪摸?”
(19) 《石溪心月禅师杂录》,《续藏经》第28套第1册。
(20) 《天目明本禅师杂录》,卍新纂续藏经第70册。
(21) 《题僧画草虫》,《无准师范禅师语录》卷五,续藏经第26套第5册。
(22) 《冬心先生画梅题记》,《美术丛书》三集第一辑。
(23) 《习苦斋画絮》卷二。
(24) 《杂花图限韵》,《徐渭集》卷九《徐文长三集》之九。
(25) 《随园诗话》卷十四。
(26) 《五杂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