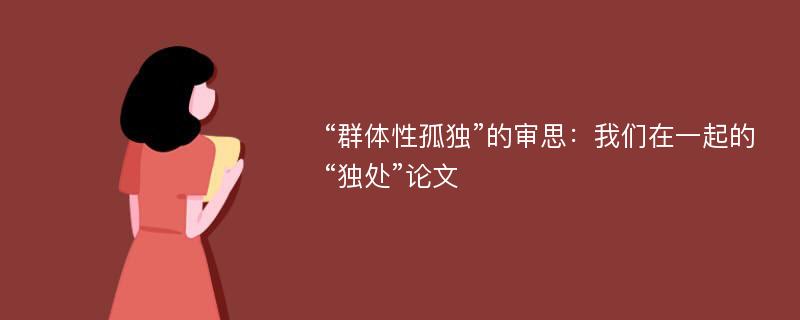
“群体性孤独”的审思:我们在一起的“独处”
□ 林 滨 江 虹
摘 要: “在一起的独处”称为“群体性孤独”,即身体近在咫尺心却远隔天涯。人际关系建立便捷与人际关系实质萎缩成为群体性孤独的一体两面,揭示出人们深陷于与其社会性本质相悖的“在一起”的时代问题。“群体性孤独”是个体与共同体之关系这一经典命题在互联网时代的延续与凸显。本文直面群体性孤独的问题,并不是如何消除个体的孤独,而是避免我们在一起的“独处”。对关系的自识与反思,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在一起。”
关键词: 群体性孤独;个体化;网络;社会性
一、“群体性孤独”的本质厘定:现代人的社会性存在的危机
雪莉·特克尔在她的著作《群体性孤独》中描述了这样一种场景:“家人在一起,不是交心,而是各自看电脑和手机;朋友聚会,不是叙旧,而是拼命刷新微博、微信;课堂上,老师在讲,学生在网上聊天;会议上,别人在报告,听众在收发信息。所有这些现象都可以归结为‘群体性孤独’(Alone together)”[1]。显然,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我们对上述情景并不陌生,且常常置身其中,切身体验。“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在你身边,你却低头玩手机”——这句流行语,说出的是我们相似的感受,反映的正是群体性孤独的特质,即我们“在一起”的“独处”。它包含两个值得关注的重点:“在一起”指的是人们共处于同一个时空场域;“独处”指的是人们之间并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机联系,没有真正被看见。一言以蔽之,即身体在场,心却远离。“群体性孤独”现象一旦成为日常生活中普遍性的存在,那么,以回归生活世界、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和发展的哲学则必须予以直面和审思。
皇窑景区本着“立足景德镇、走出江西省、面向中国、放眼全世界”的发展目标,参考GB/T 24421—2009《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系列国家标准,遵循“分块负责、齐头并进,先建立、后细化整合”的标准化工作方针和“简化、统一、协调、优化”的标准化原则,突出陶瓷文化创意特色的相关内容,建立覆盖全景区的服务标准体系。
1.变化:从时间到空间向度的凸显
孤独从来不是现代人的专属,作为个体生命的本真性存在,自古有之。只是孤独的存在形态呈现出从时间向度到空间向度的凸显,演化为一种新型孤独——群体性孤独。比较之下,就个体生命存在的时空维度而言,古人的孤独更倾向同时间发生关系,恰如屈原的咏诵“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陈子昂的叹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没有高楼、水泥和鸽子笼的生存环境,让古人对时间更敏感——时间似乎同他们更具直接性。古人被时间浸染,易逝却不舍,漫长而又短促,所谓‘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於我归处’(《诗经·浮蝣》)。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正可以被认作孤独意识在中国历史上的继往开来”[2]。时间性的孤独既意味着光阴易逝、人生苦短,诚所谓“少壮几时兮奈老何”(刘彻);也意味着面对时间的绵绵不绝,人的形单影只万难变更,正所谓“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苏轼)。如果说,古人在时间维度的孤独是一种心灵深处的孤绝意识的话,那么在空间维度上孤独则大都是源于物理空间的阻隔,有着类似“西出阳关无故人”之叹。不过在同一时空场域,古人面对面的交往,往往则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或“把酒言欢”的共情共鸣。但当世界历史开启从地方市场到世界市场再到全球化时代之后,世界恍如地球村,天涯若比邻,借助快捷的交通工具,我们甚至可以做到上午在香港喝早茶,傍晚在伦敦喂鸽子,曾经相隔的万水千山不再是人们见面的屏障。但历史发展却又呈现出孤独在空间样态的吊诡:物理空间的阻隔消失,心灵的阻隔却在建立,此消彼长导致我们即使在一起,但依旧孤独。这种孤独不再是离群索居、与世隔绝的形单影只,也不是茕茕孑立、孤苦伶仃的无助寂寞,而是表现为身处人群之中游离的眼神、热闹中的突然沉默和狂欢后的落寞,是一种“在一起”的孤独。“孤独者并不生活在万里之外的孤岛上,孤独者生活在我们的中间”[3]。因此,现代人的孤独更攸关于空间,是社会空间的空缺,而不再是自然界空间的阻隔,是“社会的空间”在定义现代人的孤独,它让孤独发酵为多倍的孤独。
走廊联通其他成片的耕地和其他绿地,形成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廊道。同时,使用耕地、基本农田代替当前河流、道路两旁的绿化带,不仅不会削弱其绿化效果,还可以将田园风光、村落与城镇景观展现出来,增加意境。
2.序位:“界面”高于“见面”
这种群体性孤独症候在社交网络时代更为凸显。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强有力地改变着人的活动社会时空结构。由于时间“碎片化”和“分流”,空间“去地域化和集中化”,加上互联网媒介所搭建的社交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遍运用,人与人之间交往在时空向度上实现了共时共在,在线在场,所谓的“分开”和“独处”此时都失去了其原初的意义。网络技术以虚拟的方式将远隔天涯海角、相互分离的个体“链接”到一起,从而实现了跨越物理空间的互动,扩展了人们“在一起”的实质性空间。但与此同时,相聚在一起的人们却很少专心地与身边的人相处。虽然他们身处同一个空间,但内心却又渴望同时“在别处”——借助掌媒连线到他们并不在场的任何地方,同身处异地的人时刻保持联络。由此,“人群中的沉默”这种令人尴尬的现象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从社会联系的意义上来说,社交平台给孤独的人群缔造了一个紧密互动的空间,扩展了人们彼此之间的接触,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疏离似乎被互联网所消弭。但事实上,孤独个体通过互联网媒介所搭建的社交网络并未生成他们所渴求的亲密关系。相反,人们沉迷于对技术的依赖之中,其闲暇时间基本都被电脑、手机等现代新设备所占据,“界面”正在取代“见面”,正如图克尔所言,“我们上网是因为我们繁忙,但结果是花在技术上的时间更多,而花在彼此之间的时间更少。我们将连接作为保持亲近的方式,实际上我们在彼此躲避”[4]。因此,即使我们在真实的物理空间共在,但借助掌媒却可以随时抽身而退,进入界面的世界,我们内心既没有走进对方心灵的需要,也不会专注聆听和敞开倾诉,深陷“在一起”的独处。
3.特质:“容器人”的样态
互联网为孤独的大众提供了逃避的场所,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个体排遣孤独、渴望联系的需求。网络时代的远程技术可以实现个体同时与多个其他主体展开交往,形成一种点对面的共时性的广泛性联系。这就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场景中脱离出来,穿越到无限延伸的时空旋涡当中,以此来推进社会关系网在更为广大和纵深的意义上的拓展和延伸,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的社会性交往需求,弥补了现代人心灵的空虚与寂寞。今天的人们不再面对面交流,更多地通过网络化的远程登录,在由文本、照片、视频、声音等符号构造出来的数据流中进行沟通,即便他们此刻同在屋檐下。因为这种远程在线交流,既满足我们对于身体隔离与建立联系的需求,同时也避免了现实交往中有可能出现的尴尬与失误,从而大大增强了我们对社交的控制权以及能够最大限度管控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但同时我们也发现,这种在线社交已显露出某些危机,我们越发远离客观真实的世界、亲近技术世界,“人与人的交往简化和抽象成‘机’与‘机’的交往”[10]。现代人对网络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殊不知,恰恰是网络技术阻断了我们真实、亲密关系的建立,由此加强和深化了人的孤独体验。
二、“群体性孤独”的原因分析:个体化时代的生存境遇与网络技术的界越
1.个体化时代的生存境遇:自由而孤独
人生而自由且孤独。柏拉图在《会饮篇》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人类在很久以前都是“双体人”,两个脑袋、四只手、四条腿,但因为人类的傲慢自大,宙斯就把人劈成了两半,于是,人类终其一生都在苦苦寻找自己的另一半,由于被劈开的人太多了,找到另一半就成了很难的事情,但是孤独的“半人”依旧执着寻找[6]。“半人”这种不完整的状态隐喻着个体永远是残缺的、孤独的,以及人类一直想从孤独中走出来的渴望与焦虑。因此,孤独,乃是个体的存在方式,但与他人合为一体或在一起,也是个体与生俱来的诉求。人类最初的孤独源于人与大自然的分离,人与自然从浑然一体状态转变为分离状态,成为“类”存在,“此一‘类’就成了无家可归的‘被抛者’”[7]。这是人类最初的孤独体验。为了克服这种孤独,人类走向了马克思所言的“人的依赖”阶段,因为个人力量的渺小与生存环境的恶劣注定个人对共同体的直接依赖,离开共同体他就无法生存,这时孤独升级为对与群体隔离的恐惧。然而随着历史向前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人类逐渐摆脱共同体的束缚,开启了个体化进程,而这一过程本身就伴随着日益增长的孤独。
所谓的“个体化”是指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不再以家庭、宗教、阶级等既定的社会身份,而是“个人作为社会关系体系中的一个基本单元,作为社会行动过程中的一个实体单位”[8]来创造自己的生活,它表现为个人的独立性、独特性和主体性的不断凸显和增强。个体化进程的本质是个体从社会中逐渐地“抽离”或“脱域”,其中的一个后果便是个体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既往各种共同体的庇护和支持,变得愈加孤立,每个人除了自己之外找不到其他的立法者,沦为自由的孤独患者。正如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指出,“原始关系”给予人们安全感与归属感,一旦人们从整体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也就意味着他必须孑然孤立地应付一个未知的新世界,这个世界与个人相比是强大且具有威胁性的,这时候人便产生无助、孤独和无权利的感觉[9]。所以,个体化进程一方面是自由的获得和增长,另一方面是孤独的日益加深。自由而孤独,既是个人的体验,也是群体的困境,是我们每一个现代人所不得不面对的“命运”。就此而言,孤独是人类在自我寻求过程中必经的一次生命体验,在这个境遇之中,一旦个体无法用丰盈的自我和强大的内心回应孤独本身所提出的要求和挑战,难免会对孤独产生恐惧,转而逃避孤独。
2.网络技术的界越:身体的“缺场”取代了“在场”
群体性孤独的特质及吊诡,不仅显示了现代人孤独的独特样态,更重要的是昭示了现代人的社会性存在危机,即我们不知道如何真正在一起。正如有学者指出,现代文明的终极问题是“我们如何在一起”的问题。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得知:“我们”是人类文明共同的基因,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真谛,我们必须且只能“在一起”。无疑,人类有许多路径“在一起”,如经济、政治、法律、制度等等都是让人们在一起的方式,“在一起”已然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普遍图景,然而,这些都是外在的“在一起”[5],缺乏精神与情感的深层次沟通和有效互动,呈现出“在一起”的内部贫瘠与匮乏。对此,日本学者野牧亦有同感,他用“容器人”这一概念来描述现代孤独个体的社会形象:在以电脑、手机为主的媒介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现代人的内心世界就像是罐状的容器——孤立与封闭,虽然他们渴望与外界接触以此摆脱孤独状态,但每一次的碰撞都仅停留在容器外壁之间的碰撞,无法深入对方内部,每个人其实都还生活在自己的“气泡”中,由此造成即使相互碰撞的双方也无法建立深刻、亲密的社会性关系。因而,现代人的孤独不再是仅指时空隔离产生的精神落寞,更是指向在一起“独处”所呈现出来的生存困境:一面是人际关系连接极度便捷,一面是人际关系实质极度萎缩。
今年11月6日至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上海期间强调,经济强国必定是海洋强国、航运强国。要有勇创世界一流的志气和勇气,要做就做最好的,努力创造更多世界第一。
社会交往是人的社会性的诉求与人的本质形成的重要方式,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交往是在主体间的交互体验中生成的并不断建构的过程,是具身行动者之间的协调过程,既包括了主体与他人之间的情绪感人、情绪共鸣,也包含了身体姿势、面部表情和语音语调等方面的协调[11]。有学者把这种“亲临而在场”视为“最接近跨越人与人之间鸿沟的保证”[12]。然而,“远程即时在场”的网络技术通过消解时间和空间从而解构了“此刻当下的在场”,使得实体性的身体交往被边缘化。“它们由于将‘在场’时间与它的此时此刻相孤立从而杀死了它,为的是一个可换的别处,而这个他处已不再是我们在世界上的‘具体在场’的他处,而是一种‘离散的远距离在场’的他处”[13]。远程技术在线交流通过文本、照片、声音等这些符号化身来代替缺席身体呈现在其他人面前,用电子义肢——客户端、数字装备来拟代人的生物感官,从而直接隔开了我们与他人的直接碰触,破坏了在场的此在性,也取消了肉身主体“在场”的必要性。维希留指出,正是技术对人类身体的“内殖民化”,导致我们越发远离客观世界,亲近技术世界;沉迷于网络在线的“此时”,而不顾及“此处”,也就是相聚地点的空间[14]。另一方面,由于网络技术支持重新编辑、美化等功能,个体往往是有选择性地呈现自我,是经过主体包装和加工后重新塑造的“网我”,即“拟态人”。这就导致个体是在由键盘和显示器建构起来的数字化形象的幻象中与他人进行交流,这既让互动失去了真实性,也增加了诠释的难度。因为符号式交流无法真正传达和体现人的言谈举止与喜怒哀乐,反之,在一定程度上,它削减了交往中的人性因素。特克尔在论述网络技术引起人的社交异化问题时总结道:“数字技术用在线联络代替了面对面交谈,把复杂鲜活的人际交往化约为简单高效的连接;把借助身体展演的自我呈现变为虚假失真的自我表演;把亲密关系弱化为仅仅是联系;网络亲密滑向网络疏离。结果是人们希望技术助其从现实关系中解脱,实际却加剧了交流的不确定感和人的孤独体验”[15]。
显然,通过远程技术个体可以与外部世界随时保持一种虚拟的联系,这种看似个体与社会的疏离被虚拟时空所消弭的交往实践,并不意味着能生成人的社会性。从伦理意义上看,生活在一起的人们缺乏传统共同体成员之间那种有机联系。个体化社会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人们不再是观看、注视他人,而是将目光只投向自我本身,一切都成了映衬自我的镜中风景,“一旦‘我’从‘我们’中浮现出来,相对于‘孤独的心灵’而言,‘亲密的形式’的价值和意义随之降低,虚拟空间中亲密关系不可避免地疏离起来”[16]。社交网站充斥着无所顾忌的宣泄和不在乎他人的言说,却很少有人在倾听。当个体通过互联网将自己的真实情感表达出来后,却发现无人对此回应和给予关心,失落和孤独被重新唤起,并猛然意识到远程登录即时在场的背后仍旧横亘着不可逾越的心灵间隔。“社交网站在制造短暂的‘伪集体欢腾’之后,又将个体重新推向空虚和孤独”[17]。
3.“伪集体欢腾”:无法真正“看见”彼此
根据纱线的牵引力公式,将含有突出物的纱线受到牵引力分解成正常纱线受到的牵引力F0和突出物受到的牵引力F′,即:
反思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从“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主体性走向主体与主体“共在”的主体间性,为我们寻求自我与他者之间理想的关系样态、孤独个体得以可能共同生活的伦理基础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事实证明,简单的“主体——客体”或“主体——中介——客体”的认知模式,只有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时才行之有效,一旦拿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就会面临“他人不是客体”的尴尬。因而,从理论上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在于在面对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必须从“主体——客体”或“主体——中介——客体”的认知模式,转为‘主体——中介——主体’的认识模式[25]。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否认个人主体性,事实上,主体间性是主体性的伴生物,“人的个体性和个体化在促生着人的联合和社会性的结合”[26],而个体自我的确认又是在主体间的相互观照中获得,这既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也是海德格尔口中的“此在本质是共在”。
三、“群体性孤独”的克服路径:我们如何更好地“在一起”
抓住群体性孤独产生的内在原因,才是解决问题的致思理路。毫无疑问,个体化进程带来的个人主体性原则的确立标志着人的一次重大解放,个体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与独立。然而,在这个成就背后,还潜伏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危机,即随着“自我”成为“中心”和“绝对实在”,“我”从“我们”中逐渐分离出来,社会团结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亲密关系面临破裂的危险。“在社会性的华丽外表里头是孤独者的恐惧与空虚的灵魂”[21]。现代个体表面上看起来认同社会性,但在其内心世界并不存在他者,他者直接消失在“我”的同一性和自主性之中,因此也就不可能生成有机的社会关系。“孤独者始终无法超出自身,寻找到一个和其他个体共同构成的扩大的自我,这个孤独者无法理解共同生活的必要性,也因此无法摆脱自己的恐惧”[22]。这种恐惧的根源在于个人主体性内蕴和遵循着“对象化”的逻辑,“对象化逻辑”是把自我确立为“唯一”主体,把自我之外的他者统一视为“客体”的这样一种“主客二元对立”的逻辑[23]。在这种“对象性”逻辑统治下,人与人之间关系不可避免成为一种互为对象性关系,每个人都把他人视为工具性存在。雪莉·特克尔也指出,在互联网时代的人们可能遭遇到的风险是,彼此之间开始把对方当作实用性的客体去接近,并且只愿意接近那些对我们而言实用的、有趣的和舒适的部分,我们满足于用物化的方法看待彼此。显然,这种互为对象的对待方式“既粉碎了旧有的‘连续性’的形式,也损害了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关系”[24]。因此,我们需要诉诸社会关系的实践转向,从“向外求”转为“向内求”,也就是说,从向外寻求社会与集体的关系,转为向内寻求自己对这些关系的重新看法,通过反思而不是一味、盲目寻求社会支持解决群体性孤独的问题。无论是对自我还是对他者、社会的关系,只有经历了独立的自识与反思,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在一起独处”的社会性困境。
1.人与人关系:走向主体与主体“共在”的主体间性
群体性孤独的形成,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从外在现象归于网络技术造成的“身体的缺席”,从内在本质则源于个体化进程中个体自由与孤独的生存境遇。前者是网络世界所带来的技术与人的发展问题,而后者关乎人的个性与合群问题,二者共同造成个人与共同体关系在现代的发展和危机,“一方面是个体在呜咽和呐喊,另一方面是类整体、共同体在召唤”[19]。就此而言,群体性孤独是对“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张力的延续与深化。孤独个体之所以要聚集“在一起”,是因为个体发现了自身与他人之间的必然性关联;聚集“在一起”的个体依旧孤独,缘于他们在互动过程中并未生成有机的效用关系。“如果说基于生活实践的智慧创造出了一个相互依赖、相互融入的大家‘在一起’的世界”[20],那么,如何真正地、更好地“在一起”,从“机械团结”走向“有机团结”则是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因此,就群体性孤独问题的核心意向而言,我们不是讨论如何消除个体的孤独,而是解决“在一起”的“独处”,即我们如何更好地“在一起”,探求个体如何在自我寻求过程中塑造自身对他人的社会性情感,缓解和克服由关系疏离而带来的孤独,从而重新构建起共同生活的可能。
现代人企图借助网络世界“集体欢腾”来阻止孤独感的迫近,可是,事实却是相反,它让我们陷入群体性孤独。对此,美国著名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一针见血直指真相:融入群体的个体被舒适的温暖包围,从精神分析象征来看,他就像回到了子宫,这使得他暂时摆脱了孤独,但这是以放弃他作为独立本体存在为代价的,把自己完全融化于外界权力之中,从而丧失了发展他自身的内在资源、力量和方向感,以及以此作为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关系的基础,而后者正是使他最终战胜孤独的东西。所以,对于丢失了内在自我的现代人来说,无论他们怎样抱团取暖、相互依靠在一起,都无法躲避孤独,甚至会变得更加孤独[18]。
(7)超细无机吸声棉喷涂技术。既保证了保温、吸音隔声的效果,又具有良好的防火性能,还保证了良好的视觉效果。
从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认知转为与他者共在的思维认知,它意味着应抛弃实用的“对象性逻辑”,而把人们之间的“相互承认”“相互需要”作为促进人们在一起生活的社会基本价值。社会团结与社会生活统一的可能性存在于社会成员间的民主商谈和对话过程中[27],特克尔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认为重拾面对面交谈有助于人们走出在线的孤独。与虚拟网络世界“容器人”封闭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呈现方式不同,强调“相互承认”“对话”的主体间性交往内蕴着一种开放性和能动性:每个个体之间彼此分享经验、尽可能相互理解,以至构成相互间的交流与融合,从而促成意义世界的生成。这是主体在重新理解自我与他人关系基础上、从内心深处所触发的心灵碰撞,它既保持了个人主体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同时又超越了其隔绝性和孤立性,从而使得分离个体实现新一轮共同生活得以可能。无疑,交往实践是主体间性得以实现的客观基础,个体需要在实践层面走出离群索居的生活,重返具身性交往空间,再现“自我”与“他者”的主体间性对话,建立真正的社会交往。
2.人与网络技术关系:建构主体的技术理性
直面群体性孤独产生的外在原因,对网络技术的辩证认识与合理运用也是克服群体性孤独不可或缺的。在当今时代网络社交已经成为人们主要的交往实践活动,由于在网络交往过程中,我们并未在与他者的交会中生成丰富的主体间性关系,反而在每一个依赖技术个体周围建立不让他者靠近的壁垒。更进一步说,在“身体缺场”的虚拟符号交往之中,并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他者”,网络交往中也就几乎没有主体间性的参与,因此也就必然造成更加彻底的孤独。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网络技术所引发的社交革命对人类交往的自由发展意义深远。因而,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人的社会性生成,以及如何理解当代网络交往的伦理困境,这是需要我们加以追问和反思的。换言之,真正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技术能对人做出多少改变,而是人面对这种改变对自我与技术关系的反思。“技术的存在并不是决定人们的依赖行为的根本力量,而在于作为技术使用主体的人对于技术所采取的行为的过程中,亦即主体的技术理性本身”[28]。这就需要我们促使技术角色的合理回归。
那么,合理的技术角色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考察技术的发展历程,便会发现技术是在对解决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基础上完成自身发展。也就是说,技术是以人的需要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是人类实践发展的产物,那么技术的运用就必须充分体现满足人的发展需求这一根本目的的人文特性。在这里,需要明确的是,造成群体性孤独的网络技术本身并不是没有人文因素,只是这种因素被其他物遮蔽了。所以,要想消除群体性孤独、促进人的主体性的和谐发展,就必须回到技术本身,重新建构具有人文关怀的技术发展观。这就要求技术一方面要继续发挥其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作用,为人的存在和发展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要求技术必须在人文关怀的基础上适度控制自身的发展,以此减轻技术的负面效应,使其朝着人类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这就意味着在技术发展中要兼顾技术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保持两者之间必要的张力。唯有如此,技术才能充分发挥联结人们在一起的桥梁作用,人也因此重获主体性与社会性。
网络作为一种“不在场”的显现,已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环境的一部分,让现代个体摒弃互联网是不可能的,因而在处理人在虚拟网络世界与现实生活世界中活动的各种关系时,应秉承“人网共生”“虚实和谐发展”的理想与追求,既要充分发挥赛博空间在促进人的主体间性交往方面的积极作用,也要主动参与线下面对面的交谈,以此来弥补线上交往由“身体缺场”所带来的不足,在真诚理解和谈话中构建互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用真正的“在一起”来疗愈孤独的人群,建立更好的生活。
参考文献:
[1][美]雪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M].周逵,刘菁荆,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序言.
[2]敬文东.感叹诗学[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84-85.
[3]张国旺.孤独个体的共同生活:自然社会的“自然”与“社会”[J].社会,2016(6):36.
[4]Turkle Sherry.Alone Together: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NY:Basic Books.2012:281.
[5]樊浩.我们如何在一起[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
[6]柏拉图.会饮篇[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7]郭春明.孤独意识的时代凸显与现实关切[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9.
[8]郑杭生.品味社会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98.
[9][美]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M].刘林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
[10]吴伯凡.孤独的狂欢——数字时代的交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334-335.
[11]何静.生成的主体间性:一种参与式的意义建构进路[J].哲学动态,2017(2).
[12][美]约翰·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M].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388.
[13][法]保罗·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M].陆元昶,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5.
[14]卓承芳.维希留速度政治学视野中的身体、空间[J].中外文化与文论,2016(3).
[15]刘婷.在线社交中的身体悖论[J].新闻界,2018(10):
[16]张兆曙,王健.制造亲密:虚拟网络社区中的日常生活——以人人网SNS人际互动平台为例[J].青年研究,2013(6):62.
[17]王建民.互联网时代的个体自由与孤独——社会理论的视角[J].天津社会科学,2013(5):78.
[18][美]罗洛·梅.人的自我寻求[M].郭本禹,方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9][26]王晓东.生存论视域中主体间性理论及其理论误区——一种对主体间类存在关系的哲学人类学反思[J].人文杂志,2013(1):20,21.
[20]赵旭东.后文化自觉时代的物质观[J].思想战线,2015(3):7.
[21][22]黄涛.现代自然社会中的“孤独者”[J].读书,2016(3):131,132.
[23][27]贺来.社会团结与社会同一性的哲学论证——对当代哲学中一个重大课题的考察[J].天津社会科学,2007(5).
[24][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0.
[25]郭湛.论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3).
[28]张军锐.颠覆与重构——数字交往时代的主体性研究[D].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1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发展分享经济的社会环境与社会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6ZDA082)、教育部人文教育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研究”(项目编号:JJD710016)]
林滨: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虹: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珑玲
标签:群体性孤独论文; 个体化论文; 网络论文; 社会性论文;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