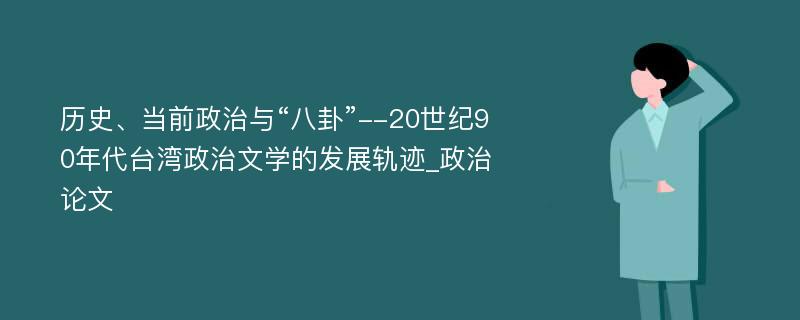
历史、时政和“八卦”——90年代台湾政治文学的发展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时政论文,轨迹论文,年代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的台湾经历了政治上变动最为激烈、快速的年代,相应地,也成为“政治文学”空前繁荣的年代:解严、强人消逝、反对党建立、“统”“独”等议题摆上了桌面。进入90年代后,“解严”所释放的政治能量已渐衰减,“政治文学”自然也有着相应的潮起潮落,但80年代所开启的一些议题或主题,则延续下来,且有深化的发展。
“统”与“独”仍是90年代台湾文坛不能回避的议题。其中较集中、明显的对抗有:1995年间台大教师陈昭瑛得到陈映真、王晓波、林书扬等呼应的、与若干具有“独”派倾向的高校外文系教师围绕“本土化”问题的论争;1997年因纪念乡土文学论战廿周年引发的由原乡土文学分裂的“统”“独”两阵营的对峙;以及1998年陈映真、吕正惠等对于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判。
近年来台湾分裂主义政治思潮的突出倾向是“亲日仇华”。它一方面将国民党(包括随同国民党到台湾的“外省人”)视为“外来”“殖民者”,宣扬只有脱离中国,才能结束被殖民的命运;另一方面则为日本的50年殖民统治涂脂抹粉,试图以此斫断台湾民众固有的中国情结和民族认同。台湾当局的头面人物公开宣称“国民党是外来政权”,被列入中学教科书的《认识台湾》更以大篇幅强调日据时期“日本现代化带来的光明面”……,都是这一思潮的典型表现。文坛可说是这一社会政治思潮的重灾区之一,部分作家舞文弄墨,为这一思潮推波助澜,他们遭到正义人士的批判和谴责是必然的。如针对张良泽在《正视台湾文学史上的难题》一文中鼓吹设身处地、以“爱和同情”重新解读40年代的“皇民文学”作品,陈映真等深刻地指出:所谓“皇民化”运动的本质和目标,乃是要“彻底剥夺台湾人的汉民族主体性,以在台湾中国人的种族、文化、生活和社会为落后、低贱,而以日本大和民族的种族、文化、社会为先进和高贵,提倡经由‘皇民练成’……从而彻底厌憎和弃绝中国民族、中国人的主体意识,把自己奴隶化,对天国输绝对的效忠。”那种想要高攀“皇民”而对自己体内流动着的毕竟只是台湾人的血而感到绝望的情意结,陈映真等称之为“精神的荒废”,并指出:“只要没有经过严峻的清理,战时中精神的荒废,总要和现在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陈映真:《精神的荒废》)这就挑明了当年的“皇民”“皇民文学”和现在的美化、正当化等日本殖民统治的“台独”言论某种内在的联系,这种批判无疑具有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意义。
围绕“历史”(特别是近百年来的台湾史)展开的论辩延续到80年代后期。这期间,一些倾向于“独”的作者往往热衷于写“二二八”,企图藉此证明“族群”矛盾由来已久,以此挑起所谓“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关系问题。而与“统”派有较深渊源的作家则致力于50年代白色恐怖史的发掘和书写,从阶级斗争而非族群矛盾的观点,准确地反映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和人民革命斗争历史。值得一提的,一些原住民作家致力于抗日历史题材的创作,如游霸士·挠给赫的小说集《天狗部落之歌》、瓦历斯·诺干的组诗《Atayal》等,对于美化、正当化日本殖民统治的社会思潮,是一个有力的反诘。
90年代中期“时政小说”的崛起,使台湾政治文学的发展有了一个较大的转折。它的着眼点从“历史”转到了“当前”,主题从揭示政治“压迫”转到揭示政治“乱象”。此前近十多年来的“政治文学”,从稍早的“牢狱文学”、“人权文学”到后来的“二二八小说”、“白色恐怖史”作品,其主题均在揭示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而所谓“时政小说”未必触及政治压迫问题,而是直接取材于当前政治人物行迹以及刚发生、正在发生、臆测中即将发生的政治事件。如1994年前后,在“台独”思潮高涨引发两岸关系紧张的局势下,台湾出现了《一九九五闰八月》等一批揣测大陆武力攻台情景的畅销书籍,即属此类。
在时政小说上用力最著的当数张大春。他于1994年发表的《没人写信给上校》揭示了统治机器种种内幕和弊端。小说以真实事件“尹清枫命案”及其牵连的军购弊案为故事背景,于案件发生后一个月即在报上边写边载,随着媒体对若干线索和案查过程的披露,同步甚或超前地设想案情发展始末和真相,其虚构几达乱真的地步,号称“小说破案”。更具轰动效应的则为稍后为台湾高层权力集团写“外传”的《撒谎的信徒》。小说主角李政男其实写的是李登辉,民进党候选人彭明敏以彭明进的名字代替,蒋氏父子则原名原姓地出现在小说中。作品着重描写李政男知遇蒋经国而爬上权力的颠峰,却从来是一个平庸、懦弱、见识短浅的无能之辈。光复之初,他虽曾参与“耕耘社”的活动,其实只是一个无理想信仰、无意之中的卷入者。但在遭受情治部门的追查监禁时,他矢口否认自己的这段历史,甚至检举了同伴,逃过一劫,成为一个地道的撒谎者和背叛者。作者由此达成了对当前台湾频频上演的政治闹剧和庸劣政治现象的揭露和嘲弄。小说单行本于1996年3 月所谓“总统”选举前夕推出,除了戏谑捣乱之外,显然也带些直接影响选战的意图。
无独有偶,差不多同时出版的、同样牵涉选战的还有知名小说家王定国的《台湾巨变一百天》和宋泽莱的《血色蝙蝠降临的城市》。前者以日记的形式,冷眼观看并逐日记下“大选”前一百天发生的政治事件、政治人物的言行,并加上作者个人对当下台湾政局的感喟。出现在书中的均为真人真名。后者则结合魔幻写实的手法、19世纪浪漫派小说风格和大众连载小说的文体,着笔于选战热潮及黑金政治,以血色蝙蝠附身的黑社会青年彭少雄兴衰起灭的经历为主轴,描绘出国民党、在野党之间彼此斗法、互挖疮疤,跟黑道携手往来的政治怪象。这两位作者在政治理念上本来都有偏向,但这两部作品不再聚焦于统独问题而是对选举过程出现的弊端和各党派政治人物的龌龊表现加以揭露,反映出台湾社会的混乱景象,正如王定国所写的:“当各种传媒不断谈论国民党是不是外来政权时,我并不在意”,令他感到焦虑和痛心的,是那“政乱民不安”的社会现状:“社会治安败坏,金融风暴一直依靠国本救急救穷,族群的对立至今无解,人道的精神荡然无存,在这么个灰暗、无助的轨道崩溃中,选总统有什么鸟用?”(《台湾巨变一百天》)
“时政”文学到了近两年,又有了新的变化,这就是所谓“八卦”的兴起。这种作品由具一定知名度的人物(一般为政治或媒体人物)所写,用于呈露个人的私生活,或揭发、影射其他具知名度者的隐私。具轰动效应的有:《黄义交爱情故事》、《男谎女爱——邱彰的离婚档案》、《何丽玲》等等。像李昂的小说《北港香炉人人插》,有影射陈文茜(时任民进党文宣部主任)之嫌,也为人认为属此。至于徐璐(第一个访问大陆的台湾记者)自剖其6 年来遭受性暴力侵害的心路历程的《暗夜幸存者》,则被视为一本原本可能被渲染成“八卦”的书。
对“八卦”书,有学者对其作正面意义的解读,认为其中有“女性的声音藏在其间”,表明作者“要从伤口的治疗,想厘清自己的人生”。但这类作品总是和时政有所关联。它不像一般人写回忆录,须经过较长时间的沉淀,而是具有“即时性”,通过对政治人物的“曝光”对现实政治产生影响。这种作品的盛行,本身也有其社会政治文化的意涵。台湾有学者认为:美国八卦所以当道,是因为大众对政治有很强的犬儒态度;台湾一般人目前对政治也有很强的犬儒态度——当八卦变成一种市场的主流价值时,就与当时社会大众对于政治和政治人物的幻灭有关;一般人对政治人物失望的居多,所以要看他们不好的地方,“这种政治名人的八卦,甚至变成人们的一种武器,用于拆穿政治人物的假面具。”另有学者认为:透过这种书,我们开始对政治有另一种想象的空间,政治人物拥有权势,是很多人从小的梦想,只是难以实现,现在我们看到这些人的光圈的背后,其实与我们凡夫俗子差不多,甚至道德比我们凡夫俗子还差,这是一种补偿作用(董成瑜:《“八卦,八卦,人人爱乎?”座谈记录》)。“八卦”并因其迎合了某些读者的窥密心理而经常和商业炒作联系在一起。
从“历史”的关注到“时政”的介入再到“八卦”的流行,台湾政治文学的主流逐渐转向一种对社会乱象的无可奈何的反映,相应地,它中间曾夹杂着的某种偏狭的本土意识、分离意识乃至“台独”论调,趋于软化和淡化。其原因,除了“台独”论调本身理论上的贫瘠、非正义性、以及其教义性与现实可能性的矛盾外,似乎也是一种与现实政治和社会思潮发展相契合的必然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