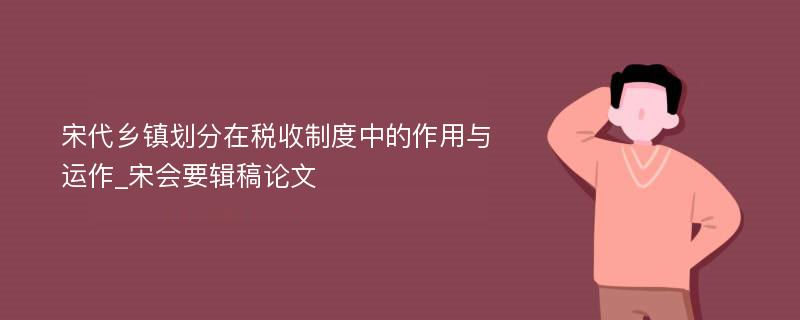
宋代乡司在赋税征收体制中的职权与运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赋税论文,职权论文,宋代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代,乡是实现国家财税职能的最基层机构,乡司(注:本文的乡司、乡书手以及书手、乡书、乡胥、乡典等,都是指相同的事物。)则是以乡为单位配置的实现国家财政职能的专业人员。鉴于目前国内对宋代乡司及宋代县乡赋税征收体制的研究尚未有专门论述,本文拟对宋代县乡赋税征收体制中乡司的职权与运作进行一些初步探讨。
宋代乡司在县乡赋税征收体制中主要承担各类版籍和赋税簿帐的编制、书算等财税稽核方面的运作,即宋人通常所说的造簿帐,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编制、推排五等版籍
五等版籍,又称五等丁产簿,或简称版籍、丁产簿,是宋代以乡为单位的乡村户籍资产总帐,也是宋代州县衙据以划分税户纳税等级并分摊税役的根本依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之14载:“(熙宁)七年七月十九日。司农寺言:曲阳县尉吕和卿请,五等丁产簿,旧凭书手及耆户长共通,隐漏不实,检用无据”。《作邑自箴》卷四载:“造五等簿,将乡书手、耆、户长隔在三处,不得相见。各给印由子,逐户开坐家业,却一处比照。如有大段不同,便是情弊”。都指明乡书手与乡村基层政权头目耆、户长等共同负责编制五等版籍。这是乡书手的主要职责。
与编制五等版籍相关联,随着乡村税户田产物力的升降增减,乡司也还同时负责五等版籍中税户等第的“推排”。每逢闰年,负责造五等版籍的乡司书手根据税户资产的升降增减、丁口的新进病退等情况进行推收、核实及重新登记,并登录于官司版籍簿帐上,用以编排厘定税户户等,并据此重新摊派税役(注:《宋会要辑稿》食货69之25。)。推排每隔三年举行一次,对税户变动不定的物力、丁口等进行核查跟进,确保国家税役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尤其是南宋承宋金战乱之后,土地关系混乱,推排更是稳定乡村基层统治秩序,维持政府财税收入的必要措施,“是以绍兴以来,讲究推割、推排之制”(注:《宋史》卷131 “食货志·役法下”。)。可以说,州县版籍簿帐的合理、可靠,端赖乡司的推排是否办理得公正、平允。
基于乡司在编制和推排五等版籍中的职责,他们在承办买卖、逃亡、户绝等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的同时,实际上也就取得了决定税户纳税等级(户等)和处置税户承担税役课赋数量的权力。这些职责和权力,既赋予乡司维护乡村赋税征收体制正常运转的重任,也给了他们假公济私,舞文作弊的可乘之机。乡司在编制和推排五等版籍时,往往不依法办事,借机中饱肥私,“比年乡司为奸,托以三年一推排方始除附,乃使久年系籍与疾病之丁无时销落,新添之丁隐而不籍,皆私纠而窃取之。致令实纳之人无几,而官司所入大有侵弊。兼有十数年不曾推排处”(注:《宋会要辑稿》食货69之31—32。)。由此而造成“推排”失据,州县五等版籍与实际情况严重脱节的现象。五等版籍失去了准确性和可靠性,县乡赋役征收体制也因此而陷于混乱之中。胡太初在总结为县之道时说,“今之作县者,莫不以催科为先务,而其弊有不胜言者,最是乡胥走弄,簿籍漫漶。不惟驱督不登,县受郡之责;抑亦逼抑过甚,民受官之害”(注:胡太初《昼帘绪论》“催科篇第八”。)。乡司编制、推排五等版籍的职权,不仅关系到县乡赋税征收体制的运转,亦是宋代地方稳定,乡村民事成败的关键。
二、编制税租簿帐
税租簿、税租帐是县衙以乡为单位登录所辖各乡主客户丁数、税租总额、各税户税租额及盐钱屋税麴货等税额的会计帐册(注:参见《庆元条法事类》卷47“税租簿”、卷48“税租帐”。);由于两者是县乡征收夏秋二税及其他杂税的具体依据,所以又被称为二税版籍。宋政府明确规定每年由乡司书手负责写造本乡税租簿帐,并签名画押。县令佐审查毕押字用印,送州审查后于县令佐厅置柜收鏁(注:《宋会要辑稿》食货69之17—18。)。
二税版籍的内容,包括本县及所属各乡去年原纳税总额,当年新增收税额及逃绝户应开阁减放税额,当年实纳税总额,以及各税户应纳税额等(注: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69之17—18、《庆元条法事类》卷47“税租簿”。)。由于二税版籍建立于五等版籍之上,乡司书手依据五等版籍写造夏秋税租簿,这就意味着各乡、各户的纳税额取决于乡司书手之手,意味着县乡赋税征收体制运转的起点掌握在乡司书手手中。
为保证税租簿帐的准确可靠,宋政府对乡司书手写造税租簿帐立有条法禁约:“诸典卖田宅,应推收税租,乡书手不于人户契书、户帖及税租簿内亲书推收税租数目、姓名、书押令佐者,杖一百,许人告”(注:《宋会要辑稿》食货69之24。)。尽管有严格的法规和严厉的惩罚,但是乡司照样利用其写造税租簿帐的职权从中牟利。南宋初,“州县旧管税额,往往自兵火后来,簿籍不存,多是旋行括责,于十分内以分数立额。后来归业人户,虽业多,止是隐落,或州县自用,或乡司欺盗,走失合纳常赋”(注:《宋会要辑稿》食货70之129。)。 这既反映出乡司侵吞公赋,同时还可以看出,乡司书手的职责所带来的实际权力,已使他们成为县乡赋税征收体制中举足轻重的角色,成为掌握政府公赋来源的关键人物。
三、注销税租钞和结算上报
宋代县衙征税,税户纳税都有一整套的规章制度。首先,在起征赋税前一百天,把上税季的征税簿帐及有关变动的资料由县送州,经州核实认可后,送返县司,形成当年的税租钞,这是本税季征税的原始依据。然后,州县官司于起催前两月,分遣役人将“凭由”(注:“凭由”约相当今天的缴税通知单,其上需注明税户隶属之乡耆都甲、明细税目、纳税注意事项等。)散发给各税户,以便税户预先备齐应纳钱物。再后,州县令佐备同样格式的县钞、户钞、监钞、住钞等赋税“四钞”,作为正式的纳税凭证分送县司、税户、监司及仓库。完成这些必备的税务程序后,才开始起征赋税(注:参见《庆元条法事类》卷47“税租簿”、“拘催税租”。)。从赋税征收机制来看,“户钞,付民执凭”,约即现今之纳税收据单,税务官吏在税户赋税纳讫时,应在该户户钞上加盖印信,并付给税户收执,故又称为“朱钞”。“县钞,关县司销簿”,用以致送县府的催理单位,俾使官府得以在税租钞帐上注册批销。“监钞,纳官掌之”,乃呈送上级监司,供作稽核存查之用。“住钞,仓库藏之”,俾使藉以盘存出纳。显然,这是一套甚为完备的赋税受纳制度。
税租钞是县司本税季赋税征收的底帐。按宋代条法规定,在收税过程中,乡司负责税租钞的注销及结算存档。“依法:输纳官物用四钞。县钞付县;户钞给人户;监钞付监官;住钞留本司。及税租钞,仓库封送县令佐,即日监勒分授乡司书手,各置历,当官收上日,别为号计数,以五日通转。每受钞,即时注入,当职官对簿押讫,封印置柜收掌”(注:《宋会要辑稿》食货70之142。)。也就是说,一方面, 当税户依法定期限将应纳钱物输官了毕,仓场税务官吏在该户户钞上加盖印信,形成“朱钞”,并交付税户收执,作为该税户已完税的凭证。另一方面,当州县仓库收到税户缴纳的钱物后,即将已完税之县钞封送县令佐,县令佐当天分授给对应各乡的乡司书手。乡司每收到县令佐分授的县钞,应即时在税租钞中予以注册批销,这才算是该税户真正意义的完税。
此外,当法定纳税期限结束时,乡司还须完成以下两项工作:其一,在本税季结束时对各税户的纳税情况进行清理核实;其二,对本乡纳税总数及剩欠数等进行统计结算存档,并将县乡税租钞上报本州,以了结该税季的税务程序(注:《庆元条法事类》卷47“受纳税租”。)。这样,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看,各税户及各乡的完税与否,全靠乡司在税租钞中的注销结算认定。因此,就宋代县乡赋税征收体制的运转过程而言,乡司既是启动者,又是完成者。宋代称乡司为“知首末乡胥”(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1“治推吏不照例禳祓”。),无疑反映了这一现实。这也表明,宋代县乡的征税,完全掌握在乡司手中,乡司的地位相当于县下各乡的征税总管。
赋税“四钞”的功用在于建立健全的税赋受纳制度,严格稽核出纳正误,防止伪冒舞弊,并在发生纠葛时作为相互参照的依据。同时,税户在取得朱钞作为纳税凭据后,亦可免除重叠追呼的骚扰。从具体操作的角度来看,“四钞”制度的成败,关键在于乡司是否在税租钞中如实地销帐。宋政府为预防乡书手舞弊求赂而对乡书手的注销税租钞有严格的禁约:“诸销税租簿,吏人、书手受县钞或取到监、住钞而不即时勾销,至毁失者,虽会恩仍勒停”(注:《庆元条法事类》卷46“受纳税租”。)。乡司“若不以监、住钞销凿,辄取户钞或追人户赴官呈验者,各杖一百。因而受乞财物,加本罪一等”(注:《宋会要辑稿》食货70之142—143。)。但由于乡司在征税过程中正处于州县征税与税户纳税两者间枢纽的有利地位,其编制税租簿帐和注销税租钞的职责又赋予他们决定税户应纳与实纳税租数额的权力,所以无论禁约条款如何严厉,却难以避免乡司在税租钞的注销结算存档等征税各环节中的营私舞弊。有关乡司“不即据钞销簿,方且藏匿以要货赂”(注:《宋会要辑稿》食货70之141。),甚或“二税之输,簿厅(乡司)不即凭官钞销簿, 异时按籍而追,至有已输而枉被扰者”(注:陈襄《州县提纲》卷4 “追税先销钞”。)的记载,史不绝书。如此,非但“四钞”之征信功能为之丧失,抑且破坏了完整的税务程序,阻滞了县乡赋税征收体制的正常运转。
四、推收税租
宋代以田产为征收赋税的主要依据。税户典卖田产,赋税应随田产而转移,并在官方的税租簿上加以过户,是为推收税租。宋户部条法规定:“诸典卖田宅,应推收税租,乡书手于人户契书帖及税租簿内,并亲书推收税租数目并乡书手姓名。税租簿以朱书令佐书押”(注:《宋会要辑稿》食货11之18。)。可见推收税租也是乡司职责之一。
推收税租又称“推割”,“凡百姓典卖产业,税赋物与力一并推割”(注:《宋史》卷178“役法下”。)。 即人户因田产买卖交易而发生私有财产转移时,过户田产所纳的税役,也应一并过割。推割与推排不同:推排每隔三年才举行一次,是定期的全面税役清查程序;而推割由于是与田产交易一起进行,所以是随时随地的不定期的赋税转移手续。从两者之间的关系来看,三年一次的推排实行得如何,端赖平日的推割能否及时准确。就宋代县乡赋税征收体制而言,推割既是掌握税户物力升降实况的首要关键,又是推排制度好坏成败的前提和基础。
宋代法律规定,私有田产的交易转移,须完成必要的手续。首先,由买卖双方议定价格,交付钱货田产并订立契书。其次,应向官衙“投税请契”,了纳契税,以取得官府的公证。再次,买卖双方持契书同赴官府“对行批凿”,当面证对税役转移,官府加以按验后,由乡书手代表官府在税租簿帐上办理推割手续,将卖方出售田产所附带的赋税数额转入买户名下。如此才算备妥了完整的手续,官府才予以认可,契约才发生法定效力。
然而,由于推割仅是个别的赋税转移,官府虽有诸如“凡质贸田业,印契之际,须执分书或租契,赴官按验亩角税苗分数之实,勒户案人吏并乡书手即时注籍”(注:《宋会要辑稿》食货11之18。)之类的立法,并多次严申“应人户典卖田产,依法合推割税赋”(注:《宋会要辑稿》食货10之15。)。但由于对频繁的单个推割缺少有效的监督措施,因而乡司往往不依法办事,由此造成推割不实。典卖田产者多是贫民,具有收购田产能力的则多是乡豪权贵,他们利用贫民迫于生计而亟求鬻售田产的窘困,“嘱托乡司承认些少税役,暗行印押契赤批凿簿书”(注:《宋会要辑稿》食货61之64—65。),买产少过割或不即过割,而贫民田产虽已过户,赋税却犹挂于户下。推割不实,不仅助长了偷税漏税的颓习弊风,而且使贫困下户身陷产去税存之困境。
推割不实则推排失据,州县版籍簿书就不可能精确,而一旦公家之税租簿帐丧失了可靠性,征税体制亦随之而陷入混乱。对此,正如陈襄所言:“是以财赋走失,不可胜言。而差役无凭,习以成风,恬不为怪。更加数年,则有赋者亡产,有产者亡赋,不可稽考矣。”(注:陈襄《州县提纲》卷4“整齐簿书”。 )可见推割不实在县乡赋税征收体制中普遍存在,并且已成为宋代税制的一大弊害。
五、编排和点派差役
差役的编排和点派,是宋代县乡赋役征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官府根据五等丁产簿来排定每年度的差役,因之五等丁产簿也被称为差科簿。如前所述,五等丁产簿(差科簿)的操作完全由乡司一手负责,因此,每年度差役的编排和点派,实际上也完全是由乡司掌握。南宋法规规定:“今后诸县差大小保,必令本县典押及乡书手于差帐同结罪保明,编排既定,令丞同共点差其合执役之人,即时给与差帖,截日承受管干。如有不实不公,却许照条限越诉,许行改正。本县典押并照差役不当本条与乡司并行断勒,永不收叙”(注:《宋会要辑稿》食货66之30。)。可见编派差役也是乡司的职责之一。
南宋之役法,实质上是差役而非募役。所谓“募法未尝不存,而未尝不强差也”(注:叶适《水心文集》卷3“役法”。)。 名义上有募法存在,实行起来却是强差,既征敛免役钱,又勒差乡户充役。这不但加重了生产者的负担,而且也破坏了乡村的正常生产秩序,实为宋代乡村一大弊害。
更何况掌握差役编排的乡司并非循良之辈,“大抵一乡役次,乡司、役案,梦寐知之,不便从公与之定差,盖欲走弄以其私,追逮一人,则有一人之费。不伐其谋,何惮不为”(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3 “比并白脚之高产者差役”。)。更加重了役法对生产秩序的破坏。胡太初说:“今之乡司差役,率是受赂,甲诉不当,则转而差乙,乙诉不当,则转而差丙,此风尤不可长。使前之所差非,则乡胥岂得无罪,前之所差是,则今岂应改,而至于再,至于三耶。”(注:胡太初《昼帘续论》“差役篇”。)可以看出,编排点差乡役的职责,为乡司大开鲸吞蚕食之路,成为蠹害乡里的手段。而处在此种情况下的差役,或由于“乡司受情,增减物力,定差不当”(注:《宋会要辑稿》食货66之21。),凭借职权任意增减物力;或由于“乡司同以物力高强人户匿在小保,及故有隐落差互,意在邀求”,借编排差役而乞觅骚扰;往往因此“致惹词诉”(注:《宋会要辑稿》食货14之28。),诱发出许多是非难辨的役法诉讼之争。于是,民间兴讼纠役,牵连瓜蔓,以致叶适有“今天下之诉讼其大而难决者,无甚于差役”之叹。连政府都不得不承认:“比年以来,乡司、案吏于造簿攒丁差大小保长之际,预行作弊,致争讼不已,使已役之人久不承替,破荡家产,深可矜恤。”(注:《宋会要辑稿》食货14之22—23。)乡司掌握差役的编排点派,不仅严重妨碍了农民的正常生产,摧毁了农民的生计,抑且破坏了乡村经济的正常发展。尤其是当纷乱不堪的役法与物力多少、户等高下纠缠在一起时,“其计较物力推排先后,流水鼠尾,白脚歇替之差,乡胥高下其手,而民不惮出死力以争之”。更直接影响到乡村基层社会的安定,严重动摇了宋王朝的统治的根基。
六、乡司的其他职权
除以上几种主要职责外,其他与县乡赋税征收体制中户籍、赋税、役法有关的各类财税事务,大都也在乡司的职责范围之内。
宋代和预买绸绢,本以“务优直以利民”(注:《宋史》卷175 “布帛”。)为目的。但随着宋政府财政开支的剧增,逐步转化成正式的赋税,因此其摊派的依据和买册,往往与五等版籍和二税版籍一起由乡司负责编制。绍兴时臣僚言;“和预买随正税绢均科,诸郡多寡不同。其和买多于正税额至一倍去处,近年又缘乡司走移人户家业,每年增添。谓如今年着一匹,明年着一匹一尺,又次年着一匹一尺五寸之类。其逐年上供之额,元不曾增添,止是乡司取受,将形势上户或公吏之家偷落减免,却均人概(该)县人户名下补数。”乡司可以“走移人户家业,每年增添”,足见其负有编制和买册及决定各税户和买数额的职权。当然,如同乡司负责编制税租簿帐一样,和买册既由乡司写造,诸如“逐年上供之额,元不曾增添,止是乡司取受,将形势上户或公吏之家偷落减免”之类“乡司持此为走弄之弊”的现象,自然又成为令政府头疼困扰的棘手问题。
因灾伤或战乱而适当蠲免赋税,也是宋代县乡赋税征收体制的内容之一。其中检视核实灾伤轻重,呈报应蠲免赋税数额,亦属乡司的职权范围。绍兴时,江浙等路都转运使张公济说:“人户田苗实有灾伤,自合检视分数蠲放。若本县界或邻近县分小有水旱,人户实无灾伤,未敢披诉。多是被本县书手、贴司先将税簿出外雇人,将逐户顷亩一面写灾伤状依限随众赴县陈过,其检灾官又不曾亲行检视,一例将省税蠲减,却于人户处敛掠钱物不赀”(注:《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16—17。 )。可见乡司有视灾荒轻重呈报蠲减赋税的职责。当然,乡司书手借灾伤荒歉为名,一面向上级呈报,“一例将省税蠲减”;一面私下征税,“却于人户处敛掠钱物不赀”,以致“朝廷蠲减之数,徒为虚赐耳。”(注:《宋会要辑稿》食货70之89。)这样,既增加了税户的负担,又损害了政府的威信,严重削弱了宋政权的统治基础,于国于民都不利。
七、结语
宋代乡司的法定职掌,就其专业性质而言,仅仅是负责县乡财税的统计和会计工作而已。然而,倘若从宋代县乡赋税征收体制的运行来考察,就不难看出,乡司实际上控制了县乡赋税征收的全过程。从编制、推排五等版籍,编制两税版籍,编制和注销税租钞,推割税租直到乡役的编排点差,和预买绸绢的编册摊派,灾情蠲免的检视上报等,无一不经乡司之手。因此,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考虑,乡司的这些职责,无疑使其掌握了县乡赋役征收的实权,扮演着县下各乡征税总管的角色。所谓“县道财赋,本源全在簿书;乡典奸弊,亦全在簿书”,“知首末乡胥”的说法,正揭示了乡司这一角色的重要性。
乡司有恃无恐地在各类版籍簿帐及课征赋役中营私舞弊,史书所载,触眼皆是,不足为怪。问题是为什么乡司舞弊的现象屡禁而不绝。笔者以为,其关键在于乡司处于县衙征税与税户纳税的枢纽地位,是宋代乡村管理体制及赋税征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由于两税法之后以资产为对象的赋税征收愈益复杂化和专业化,有关赋税征收的户等、田产、物力的排定,赋税的推收及税役的认定等,都集中于乡司一身,使他们获得了掌握征收乡村赋税全过程的权力。这既使他们成为实现州县财税职能的关键人物,又给他们营私舞弊提供了舞台。宋代,乡司虽身处县府的尾闾末端,是县胥吏的最底层,但在与自己管辖的乡里的直接交涉中,他们却是主导的一方,扮演的是主角;他们既是县司依赖的对象,又是乡村税户不得不屈从甚至依赖的对象。正是这种中间枢纽的地位和掌握征收乡村赋税全过程的实权,使乡司成为宋代乡村管理体制及赋税征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更进一步来看,乡司的职掌虽然只是县衙对全部乡村实施管理中的财税稽征部分,但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中国古代的乡村管理体制既是以户籍征税徭役为主,这些职掌也就势必使乡司成为宋代乡村管理体制中的关键人物,进而导致宋代基层社会的“吏强官弱”。宋代乡司的职责与运作,不仅关系着宋代县乡赋税征收体制的运转,亦影响到农村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和乡村基层社会的政治安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