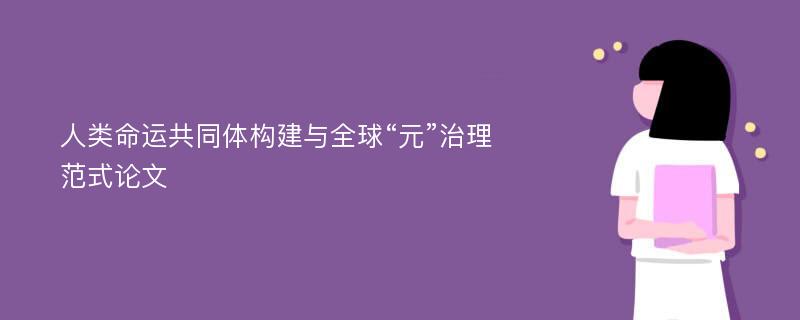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与全球 “元 ”治理范式
□吴畏
摘要 :西方基于不同理论框架和体系的全球治理研究,除了针对如何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经验社会科学研究路径即工具主义路径外,还有一条指向全球化的未来构想和构型的反思性研究路径,即建构主义路径。通过与全球化的历史、现实、发展和前景密切联系起来,全球治理的视阈在与“国际社会”、“国家社会”、“世界政府”、“世界共同体”(或“全球共同体”)、“全球民间社会”等概念的界定、探讨和阐发中不断得以扩展。同时,由于治理本身所蕴涵的基本逻辑,如治理模式、治理类型、治理结构和元治理等,在欧盟的建制和实践的启发下,发展出一些新的概念,如多层次(元)治理、多尺度(元)治理和多空间(元)治理等,全球治理的建构主义研究路径凸显出更为重要的意义。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不能仅仅把它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可能更为重要的是把它当做全球化的一种理想构型。循此思路,需要论证的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怎样作为超越西方的“世界共同体”或“全球共同体”和“全球民间社会”这些概念的一种未来世界构型,并且怎样作为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治理的“元”治理范式。
关键词 :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治理; 元治理; 全球民间社会; 全球共同体
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构建有着世界历史进入全球化时代的深刻背景,二者之间存在着有待探讨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内在关联。虽然全球治理目前主要被当做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工具性概念,但是还可以把它当做指向全球化时代的未来世界构型的建构性概念。因此该问题在于阐发它作为建构性概念所需的全新的理念基础。在西方,全球治理的视阈在与“国际社会”、“国家社会”、“世界政府”、“世界共同体”或“全球共同体”[注] 本文把“世界共同体”与“全球共同体”看做是基本内涵相同的概念,尽管西方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语境当中分别使用这两个概念。本文在不同的地方涉及西方学者使用这两个概念之处都与作者原文保持一致。 、“全球民间社会”等概念的界定、探讨和阐发中不断得以扩展。已经有论者,在欧盟的建制和实践的启发下,提出了适用于全球治理的一些新概念,如多层次(元)治理、多尺度(元)治理和多空间(元)治理等。这些概念的提出表明把全球治理从工具性概念转换到建构性概念的演进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不应当仅仅被当做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而是应当在更为广阔的意义上把它当做全球化的理想构型。一方面这是因为它能够超越西方的“世界共同体”或“全球共同体”和“全球民间社会”的理论和实践逻辑;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可以现实地解决多层次(元)治理、多尺度(元)治理和多空间(元)治理等所无法解决的实践难题。
一、全球化的内在逻辑与全球治理的主要问题
如果把全球化作为一个经验事实来看待,一方面,它带来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生活质量提高、产品的极度多样性、文化相得益彰、为解决世界性问题增进相互理解和提升合作层次等积极后果;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国家利益分化加剧、不平等日益增加、霸权主义盛行和对国家主权和民族认同的削弱等消极后果。全球治理概念应运而生,并被寄予以此能够在新的理论和实践框架内使人类走向美好未来的期望。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把握全球化的实质和发展趋向,就必须追问它的内在逻辑,而要以全球治理作为解决问题并开辟未来的基本路径,就要弄清楚全球治理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全球化的内在逻辑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历史逻辑(或资本主义逻辑),全球化可以看做是劳动分工、商品市场、资源交换、科技创新、人际交往在全球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展。全球化使得当代世界的发展呈现出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多维度进程。全球化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首先是在全球层面上资本无限制的流动和市场力量无约束的统治,其次是全球化带来了信息和人员无节制的流动。因此,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全球化究其本质而言就是相互联系和时空压缩,体现为多中心、多形式、多时相、多尺度、多因果的历史过程[1]225-230。但在关于全球化的内在逻辑的探讨当中,存在着三个既可以做出经验论证同时又可以做出反事实论证的问题。第一,全球化的主体是什么?第二,全球化的动力和机制是什么?第三,哪些事物和问题被全球化?因此,要对全球化做出比较明确的定义,选择理论框架就十分关键。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历史逻辑框架之外,关于全球化的理论说明至少还出现了两个值得关注的逻辑框架:一个是社会空间理论,它是把空间观念与社会理论紧密关联起来的一种松散性理论,尽管它还没有形成一种确定的形态;另一个全球性理论,它指的是那些超越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范围的关于未来世界构想的宽泛理论,在其名下也有多种理论形式。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与稳定性,选取Cronbach的α信度系数法对量表的信度进行检验。一般认为,总量表的信度系数在0.8以上,分量表的信度系数在0.7以上,则量表的信度较好[14]。利用SPSS 22.0中的可靠性分析模块,对回收的102份有效问卷进行信度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社会空间理论关注如何从人类生活方式的立场来理解全球化。如果把空间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基本构型,那么人类的生活空间早已不再是局限于特定的地域空间。不仅物质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已经超越了地域的限制,而且交往生活和精神生活更是几乎可以不受地域的限制,所以人类生活空间在结构上和组织上的形成和变化主要取决于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发展和变化。全球化带来了人类境况(human condition)很多基本方面的变革。人类被置于趋向于全球性的社会网络当中,生产体系和市场在世界层面上相互协调,媒体形象和资讯企及地球上的人民大众,信息化允许远距离的互动,物质的和符号的交往暗示着时空压缩[2]291-323。舒德(Jan Aart Scholte)就认为,区别于用国际化、自由化、普遍化和西方化等概念来描述全球化,全球化可以定义为社会生活的重新空间化,或者全球化指的是社会空间本质的转变[3]84-86。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空间在结构上和组织上的重构又是如何可能的呢?即究竟是在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社会的基础上来重构?如果社会空间重构遇到不可克服的难题,又是何种力量对这种重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呢? 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往往又必须回到全球化的体制建构和保障机制问题上。例如,全球化是否最终需要服从于民主原则和制度的世界公民(world citizenship)和全球政体(global polity)。
所谓的全球性理论,可以根据对全球化的不同理解、从多种不同的理论框架来立论。首先,它可以是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可以明显区别于康德的世界主义。约瑟夫(Jonathan Joseph)就认为,全球化观念应当聚焦于关于社会世界和行动者本质的预设。大多数全球化理论最终要接受一定的世界观,并与一种特殊的社会联结(social conjuncture)和组织社会生活很多方面的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影响相匹配[4]107。更为普遍的看法是全球化正在形成新的世界体系,即把世界构想为一个系统,以及把世界人民构想为被赋予平等权利和责任,以及决策者必须对其负责的个人的单一选民(a single constituency)。这样一来,就需要建立世界体系的社会整合和治理的制度机制,它包括市场、政府组织和共同体。国际市场和跨国企业作为主要根据交换原则来运行的制度,民族国家、国际组织和超国家联合体作为主要根据合法性权威原则来运行的制度,集体性运动和认识共同体作为根据团结原则来运行的制度[5]291-323。
其次,全球性理论可以是一种政治理论。传统的国家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似乎已经无法适用于说明全球化对全球政治的影响。巴布(B. Ramesh Babu)认为,全球化可以被视为国际相互依赖得以深刻变革(在质和量上)以至于国际政治变成全球政治的一种现象和过程。在实践上,民族国家所面临的每一个主要问题/挑战已经变成了一种全球问题/挑战,除非在全球或至少在国际或区域层面上来处理,就不可能有可行的方案[6]180-193。这似乎又必须预设某种全球政治的实质性建构(全球政体或世界政府)之可能性。因此,卡布雷拉(Luis Cabrera)认为,被重新构想的广义世界政府之必要性在于,在其名下可以企及的三个有益目标。第一个是安全。创立世界政府的目标是能够保证个人免于大规模暴力的威胁,包括常规战争、恐怖主义,特别是核战争。第二个聚焦于作为确保全球正义或者被更广泛地被理解为全面的个人权利的全球整合。第三个关注全球政治正义或者使合适的民主参与成为可能。更具包容性的超国家治理似乎得到广泛的支持,但这明显与全球政府的倡议者寻求主权的整合和让渡的方式不能等同起来[7]471-491。
2.1组间总有效率对比 研究组银屑病患者总有效率经评定为92.5%,对照组经评定为57.5%,组间具统计学差异(P<0.05);研究结果如表1所示。
(二 )全球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西方学者所论证的世界共同体和全球民间社会这两种未来世界的基本构型当中,都包含着对人类的发展前途和未来命运的某种关切。世界共同体概念与全球民间社会二者的本体论预设实际上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别,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观点看,它们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世界共同体更加强调世界人民之间的普遍性的价值认同和法律约束,而全球民间社会则偏重于强调他们之间的道德规范和自主合作,二者基本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是在全球性关系当中并通过它所形成的异质性的共存方式。在全球共同体这一概念当中,它既是作为一个全球性共同体(a community of the global),即抽象单一性的观念,又因为存在着不可还原的分裂或内在的差异化,从而是一个具体多样性的观念[24]173。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共同体的理念基础和基本逻辑是“共同体”这一概念,因此把世界共同体作为比较对象,才能准确阐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实质和建构逻辑。
世界主义被认为是揭示世界的政治秩序之伦理、文化和法律基础的一种思想,同时它又是一种普遍主义,被当做应对全球挑战甚至是全球治理的一种政治哲学和方法。世界主义价值观预设了对国际体制和组织的领导的必要性。赫尔德(David Held)认为,我们所面临的全球挑战最好在世界主义法律框架下去应对,并有三个支持理由。第一,世界主义价值在国际和全球政治领域很多重要方面的发展中发挥着建制作用,这又与构架核心的普遍的公民和政治原则密切相关。第二,全球化所造成的“命运叠加共同体”(overlapping communities of fate)之世界、由跨越社会边界和部门的相互交织和相互依赖关系所构成的世界,在密集的网络和过程中跨国家地把人们的命运联结起来。第三,如果由此引起的复杂和迫切的政治问题得到解决,不是通过市场和地缘政治的机制,而是通过商议、负责任和民主的机制,那么世界主义法律秩序可以被看做为国际性地和全球性地解决那些问题确立了一个公正的和包容的政治框架[17]535-547。世界主义法律框架无疑是对全球化所导致的当代世界多边主义秩序的不充分性进行理论反思而做出的新建构,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它是作为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世界共同体的必要条件吗?如果不是,世界共同体也仅仅意味着一种未来世界构想。
七八十年代,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小时候,我一觉醒来,常常听到忙碌了一天的父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小声嘀咕:老母亲的哮喘不知有没有复发?弟弟妹妹们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啦?“唉!写封信问问吧。”谈到最后,他们总是以这句话结束。那时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一封省内普通信要十天半月才能收到。父亲读过几年私塾,能自己写信,但家中的小叔们没念过书,写信、读信都得请人帮忙。尽管这样,父母也只有依靠书信和亲人传递消息,寄托彼此的思念。
其次是全球治理的模式困境。全球治理的困境首先源自于对治理样式或类型的理解与运用。就公共治理而言,幕利门(Louis Meuleman)区分了治理的三种“理想类型 ”(governance styles)样式或“模式”:层级治理、网络治理和市场治理。这些理想类型首先是理论建构,在现实当中,会出现三者不同的混合形式[11]3。罗兹则把层级、市场和网络看做是三种治理结构[12]47。三种治理样式(styles)或治理结构各自都有清晰的并相区别的内在逻辑。例如,层级治理的核心价值是权威,因此输出必须是权威的和合法的。同感和信任是网络治理的核心,因此结果被期望以共识为基础。市场治理建基于竞争和价格,这使得最好的结果是最具竞争力的和最便宜的产品成为它的逻辑[13]49-70;51。全球治理的另一种逻辑是为了更好地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因而就可以被视为广义的或全球范围的公共治理。三种治理样式或治理结构总会具有某种程度和某种范围的实用性。但是三种治理类型要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可能,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特定文化作为治理行动者的共同性精神条件,甚至可以认为治理类型本身也就是文化类型。因此在文化多元主义的背景下,无论是为了解决全球问题,还是为了更好地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全球治理都会面临在特定社会当中盛行的价值、态度、信念、导向等不同文化类型之间深刻的内在矛盾和冲突。
关于全球化的未来前景,根据不同的本体论预设和理论框架,西方学者提出了世界共同体(全球共同体)和全球民间社会两种基本构型,而世界政府(或全球政府)这一传统概念,由于全球化所展现出来的各种复杂特征和不确定迹象而被边缘化。这两种构想的思想渊源和历史逻辑并不相同,前者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后期的宇宙学,后者可以追溯到启蒙时期的社会理论。在全球化条件下,它们首先都是关于未来世界政治秩序的理想构型,同时它们都预设了威斯特伐利亚型民族国家的存在和发展这一前提。
全球治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表明了全球治理与全球化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的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一种可能的出路是,不能简单地把全球治理看做是更好地解决全球性问题和提供全球公共物品,而是应当超越传统公共治理和国家治理的视野,着眼于在全新历史发展条件下,建构一个更可持续、更加协调、更加稳定、更高层次的全球共同体。
这背后,我以为与法国人对待博物馆、对待历史的态度有关。漫步于巴黎街头,处处都是古迹文物,处处都是历史,但处处也都是当下人的生活。在这里,历史是鲜活的,是被延续的。博物馆里的每一件文物,仿佛都是活生生的,并没有人为切断,你可以畅通地与之对话,用你的生活经历建构你自己的历史叙事。除了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卢浮宫所展现出来的气魄与度量,我想除了高科技的保护措施之外,也与法国的国民素质自信有关。整个参观的过程中,欧洲面孔都表现出了较为优雅的素养,没有大声喧哗,更无人真的去触摸那些触手可及的藏品。我想,正是这种优良的公民素养,才增强了其诸多制度安排和生活方式的“底气”。
二、作为全球化理想构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一个社会(或社区)的首先责任是满足其成员的基本生存需要包括生理的、社会的、情绪的和精神等方面的需要。具体来讲就是"驱动即需要"。这是生物决定论的说法,即用生物性的内在区里来谈需要,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就是如此。他从人类动机的角度,将人的"需要"分为五大类,按照由下至上的等级依次分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及爱的需要、受人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西方学者认为老年人需求主要集中在物质需求、医疗需求和精神需求。高校教师退休后有一定的经济来源,能够提供生活的基本保障,物质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但其医疗需求和精神需求满足程度则因人而异。
(一 )全球化未来前景的两种基本构型
再次是全球治理中的国家悖论。在全球治理的理论探讨当中,一直存在着谁是真正的和可行的治理者的争论,是像设想的世界政府这样的超国际组织或机构,或者是全球民间社会,还是民族国家?全球化似乎预示了前面两种超越国家或独立于国家的全球性组织或建构的可能性,但全球化实际造成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民族国家的国家观念、利益和认同的强化。这就是全球治理中的国家悖论。这种悖论其实在“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的英国学派那里就给出了明确的暗示。他们认为,可明确研究的对象是“国家社会”(society of states),而不是“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14]423-441,即把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机制(尽管对于权力平衡是如何实现的会有不同说明),反对世界社会和世界系统理论把国际社会看做是由具有某种自组织和自规制性质的各种规则和规范来自发地、主动地和积极地管治的。英国学派的一个著名观点是:“政治权威的多样性——国家社会——是实现作为整体的人性善的最好安排”[14]427-428。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治理的国家悖论的另一种现实情况是“全球地方化”(glocalisation)。全球化作为一种整体运动,伴随着超国家整合、次国家分裂和新的相互联系出现等现象,形成了三种新的联接方式:全球与国家的联接、国家与次国家的联接、地方与地方的联接,它们超越了国家间、国内(intrastate)等传统范畴[15]180-193。换句话说,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可能处于既有存在的必要,又有多余的嫌疑的两难境地。
世界共同体是由国际法律师麦克杜格尔(Myres McDougal)及其密切合作者社会科学家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在二战结束时明确提出来的概念,他们用这一概念指称“真正代表和包容所有的主要文化系统”的一种共同体。后来的研究者根据全球化的发展变化,对这一概念基于不同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实践论和价值论做出了不同的阐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阐述都把世界共同体概念紧密地与全球治理联系起来。西方关于如何构建世界共同体主要依赖于两种历史上所形成的观念资源:一种是国际主义,另一种是世界主义,并根据全球化的实践进程做出新的说明或注入新的内容。从反思国际主义的路径来构建世界共同体,旨在解决以国家之间和政府之间的合作为基点的国际主义路径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以联盟、条约和协定为主要形式所建立的、保证参与各方安全和利益的国际体系的脆弱性和临时性问题如何解决,另一个是独立国家之间通过外交关系的彼此交往和相互作用的领域、层次和范围如何适应和满足全球化的发展变化要求。入江昭(Akira Iriye)认为,要超越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去建构全球化时代的未来世界——全球共同体,就必须充分重视、发挥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这一建构主体的力量和作用[16]10。但是这个全球共同体到底是指什么,他似乎又把它与国际社会等同起来了。
“哈尼染”,在哈尼语里是哈尼族的意思,同时,“染”字也表示了李高明所从事的美发专业。公司Logo则是李高明自行设计,早在多年前,李高明就开始打了一些基础。Logo的整体是一个哈尼族老妇人的头部,帽子部分则是李高明自己名字艺术化的简写。离开得越久,李高明对家乡、对哈尼族越有感情。
全球民间社会虽然是一个含混的和有争议的概念,但是它包含着关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和世界的现状、发展和未来的描述性和规范性内容。从当代的国家和世界状况来看,可以对全球民间社会做出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的定义:它是处在家庭、国家和市场之间,并超越国家的社会、政体和经济限制来运行的观念、价值、制度、组织、网络和个人的空间[18]3-22。当然在这种界说和论证当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哪些行动者和组织被认为是全球民间社会的一部分,国家或者由其主导的国际组织和机构是否应当包括在内。如果排除后者,似乎就只有非政府组织和市场行动者符合要求,甚至连由国家或政府来参与建构的像欧盟、WTO、联合国都不能算,当然建国运动(分裂民族主义)及其组织也被排除在外[19]303-324。所以,从全球民间社会的建构主体的现实基础来看,它目前在经验上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因为这些行动者至少目前还不能完全摆脱国家、身份、道德和信仰等因素的制约。
从当代的国家和世界发展来看,全球民间社会被解读为在“世界政府”、“世界共同体”和“国际社会”之外全球化的一种发展前景。全球民间社会概念被用来意指目前民族国家体系所发生的变化,并被设想为将来可以取代这个体系的一种新的社会实在。海恩斯(Volker Heins)认为,全球民间社会理论不是要接受民间社会是作为国家的反平衡的自由主义观念,也不能像韦伯那样把政治上的非国家力量封闭在国家边界内,它最终建基于描述和接受非国家世界对于国家世界的优先性这一政治本体论[20]159-171。但是这样需要预设非国家世界对于现代政治的一般性,这种一般性基于怎样的观念或原则才能合理地推导出来,海恩斯以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的“信心政治”(politics of faith)观念为基础进行了论证。巴特尔森(Jens Bartelson)进一步把它明确为:全球民间社会概念,在它提供了一个真正的跨国模本替代物的意义上,可以用来为在新兴的世界政体中实行政府权威进行辩护[21]371-395。也就是说,全球民间社会在基本建制上要预设世界政体,而不是世界政府的可能性。
如果在一般意义上,全球民间社会指称的是,“为承认人们平等的道德价值、他们的积极能动性和那些对于他们的自主和发展是基本的东西,而做出职权范围规定的伦理空间和政治空间。”[22]465-485,那么全球民间社会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未来世界的社会形态,而不仅仅是政治形态?不少论者给出了关于它的人性论和道德论的论证。法尔科(Richard Falk)提出了基于人类普遍情感的一种自然主义的论证,他认为:“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拓展了共同体的意义,放松了主权与共同体之间的联系,但是要建立起对人民(更宽泛的‘我们’)的苦难和渴望的强烈认同感”[23]。这种人类普遍情感还必须转化为一种具有全球性的、超越了国家的普遍道德,才能维系全球民间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赫尔德就指出这种道德的实现形式:“道德关怀的最终单位是作为个体的人们,不是国家或其他的人类联合的特殊形式”,同时,“人类属于在其中每个人值得平等的尊重和对待的单一道德王国”[22]465-480。
首先是全球治理的实践难题。在超国家的、具有统一性的政治、法律、经济和文化系统尚未建立的情况下,除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可以在全球治理当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之外,还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商议式全球治理,其中也存在着全球治理的实践难题。首先来看由政要、企业家、学者和民间组织领导者共同参加的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简称WSSD)所遇到的全球治理的实践难题。对于WSSD而言,主要问题在于:它在何种程度上,并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全球发展?政治决策能否引导在全球化的世界当中的事件进程?或者,全球化实际上导致了一种新的无政府状态和控制缺失?斯劳特(Steven Slaughter)认为,长远思考这种商议机制的意义,需要考虑三种部分相互依赖的因素或观点:一是影响权力一般分配和人们意愿导向的“权力”,二是不同行动者、国家、组织和企业之间的“相互理解”(创立共同规范和共同体制),三是作为一种心灵的心理状态的“希望”[9]94-107。其次来看作为商议式全球治理的论坛“G”系统(如G8及后来的G7,G20)。它是以成员国或政府以及主要国际组织为参与主体的、在国际法的规范协定之外成立、没有执行秘书处和预算、独立于成员国的行动能力的论坛系统[10]71-90。对于基于多边外交的论坛“G”系统而言,实践有效性也是其最大问题。尽管每一次会议都会围绕彼此关心的重大多边或全球问题(如经济、政治、安全、环境等)展开对话,进行公开辩论,但一旦遇到重大分歧就会无果而终。2018年的G7和G20就是例证。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超越世界共同体
在全球治理的诸多定义中,韦斯(Thomas G. Weiss)给出了一个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定义:全球治理是帮助所有的行动者(国家、政府间组织、民间社会、跨国公司和个人)确认、理解和处理跨边界问题的非正式的和正式的价值、规范、程序和制度的总和[8]35。根据这种定义,他认为全球治理所面临的主要困境在于存在着五个方面的“全球治理隔阂”(global governance gaps),即知识、规范、政策、制度和服从的隔阂[8]128。这里从全球治理实践的三个方面来更为全面地说明全球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共同体都承认共同体是包含特殊性的普遍性统一体。世界共同体理论假定在一个更大的社会整体中,普遍性和特殊性是暗中相互包含的范畴[25]171-172。这意味着,共同体的普遍形式和特殊形式在时间上是共同构成的,也是相互渗透的;也意味着在所有人的普遍共同体与构成它的个别共同体之间存在某种同构性;还意味着个人之间的所有社会关系以及他们所身处的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嵌套于所有人的普遍共同体。世界共同体理论仍然局限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关系的逻辑论证,把人性论、理性论等当做共同体具有普遍性的主要依据,没有说明共同体的普遍性条件和现实基础是如何形成的,虽然世界共同体假定,在全球层面上某种社会形式已经存在,也存在着不依赖于主权国家的政治权威的某种形式[25]21。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则把全球化所造成的世界各国在很多方面所形成的日益全面和深入的相互关系作为立论基础,而不是首先预设某种普遍性先验地存在,并认为共同体的特殊性是由每个参与者的活动方式和结果所产生或构成的,它们不具有静态的固定性质。因此,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普遍性寓于特殊性当中,并且以特殊性的充分发展为条件。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整合现存的各种形式的共同体。共同体对于任何个人来说,首先是一种单独依靠个人而无法实现的共同生活方式。世界共同体建立于这种观念:根据共有一系列的自然能力和共同的星际栖居地,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而构成了一个单一共同体[25]171-172。这是关于共同体形成的一种自然主义论证。共同体是由共有各种价值、生活方式,认同群体及其实践,认为彼此是群体之一员的一群人所构成。共同体有不同的形式,如宗教共同体、伦理共同体、民族共同体、道德共同体或语言共同体,等等,不仅如此,共同体还存在于不同的层次。这些共同体得以建基的基本观念显然不可能都由这种自然主义来说明,甚至可能是与之相矛盾和相对立的。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通过建构一种普遍性信念和整合性道德来整合现存的各种共同体形式,而不是简单地取消、代替、重构这些共同体形式。这种普遍性的信念的来源在于,人类发展历史表明,构建面向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的共同体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即使今天一些条件还不具备。这种普遍性的道德的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首先,成员之间必须要有团结;其次,不存在系统性剥夺或(某些形式的)系统性非正义[26]172,尤其是在缺乏有效的全球权威和共同的文化认同的条件下。
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用实践方式来解决世界共同体所遇到的价值实现悖论。世界共同体必须建立在一些普遍价值体系的基础上,但是推行这些价值的努力很可能会遇到基于其特殊性背景的抵制。当下难以形成融贯的共同体观念恰好是共同体概念成功地民族化(国家化)的结果,因而,理解这种民族化(国家化)是怎样发生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共同体之普遍化概念和特殊化概念之间所出现的紧张关系,这也隐含着怎样来化解这种紧张关系[25]171-172。这种情况促使我们反思共同体的基本条件是什么?特殊共同体的特征被广泛地相信是建立在“同一”和“他者”的辩证关系基础上,因此解决同一与他者的矛盾是通过形成某种认同来实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通过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构型来定义的发展性观念,因此它需要思考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共同体建构逻辑,暂时搁置现实的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因为国家能够产生区别于民族共同性的实质性爱国主义认同,因此一种观点认为,通过建构新的全球政治制度来产生全球多民族爱世主义(global multinational patriotism),它不同于全球民族的观念(及其与文化霸权主义相关的意蕴)[27]57-58;63。如果谋求某种程度或方式的全球政治整合是可能的,跨民族共同的价值实现悖论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需要做的工作就在于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必需的既具有整体性,又可能为每一个人都能接受的核心价值观念。
全球化深刻影响着当代世界基本格局,并改变着每个国家的未来发展前景。全球化的未来走向在不同的理论框架内分别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知。在西方,“全球共同体”或“世界共同体”概念和“全球民间社会”概念逐渐取代传统的“世界政府”、“国际社会”、“国家社会”和“世界社会”等概念,成为正在探索的全球化未来理想构型的核心论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概念都蕴含着以全球化及其当代后果为基础的全球治理的内涵。虽然习近平根据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发展愿景而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但我们不应当把它与“全球共同体”或“世界共同体”和“全球民间社会”割裂开来。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没有设定先验的普遍性原则,而是基于对全球化的实践逻辑(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社会空间化、治理普遍化)的认知来重新思考人类的整体性的未来发展可能实现方式,因而应当被当做超越“全球共同体”或“世界共同体”和“全球民间社会”的全球化未来的一种全新理想构型。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元治理”范式
由于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从根本上解决在当代的全球治理理论和实践当中存在着三个主要问题:全球治理的实践难题、全球治理的模式困境,以及全球治理中的国家悖论,因此一方面需要在现有的世界体系框架内卓有成效地创新治理模式,另一方面寻求新的全球“元”治理范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可以避免世界政府、全球民间社会和民族国家哪个才是真正的全球治理者这一根本争议,另一方面也无需否认民族国家发展自己的国家观念、国家利益和民族认同的现实意义,而是应当关注、引导和动员各种不同的治理主体如何形成共同愿景并承担共同责任,根据实践合理性这一原则来实施全球治理这一没有终点的宏大渐进工程。这又需要促进全球民间社会的形成、发展和完善来打开全球治理的实践空间,以超越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方式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全球“元”治理新范式。
(一 )全球民间社会作为全球治理的实践空间
贝克尔(Gideon Baker)和钱德勒(David Chandler)认为,全球民间社会理论家们涵盖了不断增长的广泛视角和观点,尽管它们之间存在差异,但大多数的路径聚焦在绑定于民族国家的“公民权利”旧形式与一种新形式的道德和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断裂[28]2。实际上,如果从全球治理的角度上看,一方面,全球民间社会这一概念逐渐改变了把全球治理看做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工具性概念的传统做法,例如,罗西诺(James N. Rosenau)在全球治理概念提出之初就提出:由于问题存在于全球范围,例如,环境污染、货币危机、腐败、艾滋病、恐怖主义、大众移民和毒品交易等,所以治理必定发生在全球尺度上[29]167-200。另一方面,全球民间社会概念由于蕴含着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等限制的一些构想,也把全球治理拓展为人类如何面向未来的空间性概念。
潜供电流是影响较高电压等级输电网重合闸成功与否的主要因素[9-11]。对于10 kV配电网同杆并架线路可能会因为潜供电流存在影响重合闸动作。
全球化给每个民族国家及其社会形态带来了两个方面的深刻影响:一方面,在全球层面上资本无限制的流动和市场力量无约束的统治,对一个国家自主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产生了侵蚀效应;另一方面,全球化所带来的信息和人员无节制的流动,对一个民族的政治意识和国家认同产生了瓦解效应。因而一些论者据此设想了一种全球社会[注] “全球社会”概念泛指是一个更大的社会整体,而不是单个个人或个别社会的总和(参见Jens Bartelson, “Is There a Glob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2009, 3, pp.112-115)。它与全球民间社会概念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无须预设或包含任何社会的构成方式和机制,如道德、权利、法律和政体等。 或全球民间社会正在形成。基于此,贝克尔和钱德勒认为,全球民间社会理论提出了三种面向未来的目标或理想,从而打开了全球治理的实践空间。首先,它使得政治共同体得以扩展,即国际政治不再被视为受制于国家狭隘民族利益的政治空间,而是被视为不断对关心更普遍人类利益的非国家行动者开放的政治空间。其次,它把全球民间社会的行动作为世界政治的主要决定因素,在新自由主义的“历史的终结”的决定论面前,重新强调了人类能动者。再次,全球民间社会的出现预示着可以超越国家边界来拓展民主,在那里可以构想决策不断地“向上”脱离和超越基于民族国家的民主制度的控制[29]4。
全球民间社会理论对于全球治理而言存在着三个方面明显的缺陷。第一,这种理论把全球治理的空间拓展局限于社会政治领域,或者说只涉及三种基本治理模式中的网络治理,而把在全球治理中一直起重要甚至是基础作用的层级治理和市场治理排斥在理论视野之外。第二,这种理论不能从实在论的立场理解和认识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当代演进和发展,尤其是没有把狭隘的民族主义、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重新出现和可能盛行所导致的反全球民间社会的因素纳入理论视野,因此一旦出现上述情况,它就只能意味着基恩(John Keane)所设想的“普世统治”(cosmocracy)[注] 基恩所提出的新词“cosmocracy”(普世统治),是由拉丁语的kosmos(意为世界、秩序、普遍的地方或空间)和kratō(意为统治或掌控)所构成,它是一种理想类型。它以最简洁的形式描述了制度化权力的一种类型,即背离所有以前的管治形式——从亚里士多德试图发展城邦类型学,持续到今天区分威斯特伐利亚国家,后现代和后殖民国家,或者现代、后现代和前现代国家的不同做法。参见John Keane, “Cosmocracy and Global Civil Society”, in Gideon Baker and David Chandler (eds.), Global Civil Society: Contesting Futur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p.30-31. 的终结,或者说全球民间社会不能真正作为全球治理的有效场域。第三,在这种理论当中,民族国家的多样化、个性化发展总是被预设为不能主动适应或满足全球民间社会的发展需求,甚至总是以其对立面的方式出现,因此这实际上否定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相联结、相契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由于存在这三个缺陷,全球民间社会给全球治理所拓展的实践空间充满了不确定性,也无法包容各种丰富的、具体的治理实践形式。或者说,全球民间社会只是为全球治理打开了一个单向度的空间。
(二 )全球治理的实践范式转换
全球治理的实践范式转换首先表现为全球元治理概念的出现。全球元治理概念显然是把元治理的基本概念拓展到全球治理的领域而形成的,其中一个关键的推动因素就是欧盟的建制与实践。杰索普认为:元治理由对复杂性、治理和治理失败等问题感兴趣的几个西欧学者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并被整合进几个理论和政策范式。它的定义中包括:自组织之组织、自规制之规制、自调控之调控、治理网络内似博弈互动的结构化和行动者之间影响整个系统参量变化的互动。就其最基本的和一般的(也是折中的)意义而言,它意味着“治理之治理”(governance of governance)[30]106。元治理作为实践范式,是对所有的治理形式和与之相连的政策趋于失败(市场失败、国家失败、网络失败,或信任消失)的回应,并以力图重新设计它们为导向,或者因为一定的社会力量希望重新平衡不同的治理模式而出现。元治理出现在很多场合和尺度上,当治理问题或力量的动态平衡促使努力改善治理或改变对观念利益或物质利益产生策略选择性的影响[31]8-32。因此如果把元治理看做是对社会协作的层级、网络和市场形式混合体的治理,那么它可以被视为是在竞争性治理、权威性治理和合作性治理之间的协商过程。故此元治理是一个位于三种主要治理样式之上的概念,它通常采取多视角的、通盘检视(helicopter view)的方法。
欧盟的建制与实践推动了把元治理的视野从公共部门改革和国家治理拓展到超民族国家的综合性共同体构建。为了科学说明这种共同体的构建逻辑,多层次(multi-level)元治理、多尺度(multi-scalar)元治理、多空间(multi-spatial)元治理等概念相继出现。多层次元治理概念出现在超越一个独立国家的组织架构(超国家架构)问题上,用来探讨欧盟以国家形态出现所发生的更一般的变化。对欧盟而言至少存在着两个层次的失败,一个层次是运用特殊治理机制的特殊治理努力的失败,另一个层次是一种治理模式的总体性失败。因此,对应于三种基本治理(或协调)模式,我们可以区分三种元治理的基本模式和一种总体模式。首先,存在着对个别市场的反思性重设和(或)对两个或多个市场之间关系的反思性重置,通过调整其运作、嵌套、连接、嵌入、脱嵌或再嵌入,也存在着“市场中的市场”。其次,存在着对组织的反思性重设、中介组织的创制、组织间关系的重置、组织生态(在很多组织共存、竞争、合作和共同进化的条件下对组织进化条件的组织)的管理。再次,通过对话和商议,存在着对自我组织条件的反思性组织。最后,存在着共振或“元治理”。这涉及管理在流行的协调模式当中的复杂性、多元性和缠结的层级。不幸的是,因为任何实践都容易失败,元治理和共振也有可能失败[32]69-70。
杰索普在探讨欧盟建制与成员国的相互关系时使用了多尺度元治理: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区域委员会、成员国在欧盟元治理政体当中各自扮演不同角色。关于欧盟政策制定的多层次治理概念,只是把握了从政府到治理的转变,而不是从政府到元治理的转变[1]。用来探讨制度类型、政治实践和政策过程的多尺度元治理概念强调:第一,在这些类型、实践和政策涉及的、受其影响和(或)由此推动的层次、规模、领域和场域的不可还原的多样性;第二,包括像在“网络国家”和“网络政体”等观念当中所表明的重要的水平和横向联结,以及多层次治理所隐含的纵向联结在内的,与治理相关的政治关系复杂、缠结和交织的本质;第三,元治理作为权衡政府和其他治理形式以创造协调政策形成、政策制定和完成所必要的多样性、灵活性、适应性之反思艺术的重要性;第四,可能涉及(超出了政府的不同层级和欧盟作为行政、政治和经济空间的限定的)这些制度和实践的行动者的多元性和确实的异质性[33]220。
多空间元治理概念从更为一般的和普遍的相互关系和交往关系的角度来思考共同体的建构逻辑。空间包括社会产生的网格和社会行动的范围,它们划分和组织物质的、社会的和想象的世界,并且根据这些划分引导行动。空间可以是治理的场域、对象和方式,并且根据导向行动与各种空间想象相联系。这是因为,第一,被继承的空间构型及其机会结构是治理得以成立、竞争和调整的场域;第二,在空间产生于安排、控制、重组和提升物质的、社会的、符号的边界、界限、边际和阈限的意义上,它是治理的对象。这些安排不限定在通过疆域化所确定的那些;第三,空间可以是治理方式,当它依据“内部”、“外部”、“跨越”和“阈限”的空间来界定行动范围,以及通过各种各样的时空技术在行动者、行动和事件之间型构可能的联结。第四,因为没有行动者能够把握地理—社会—空间的关系的所有复杂性,这迫使他们通过(框定他们的理解、导向、直接的空间规划或其他规划的空间方面的)空间想象来看待空间[31]8-32。
对原始单炮记录(图2)进行τ-p变换,以消除直达波等干扰,提纯面波信号(图3)。τ-p变换参数选择如下:
全球治理的元治理逻辑,既不同于公共治理的元治理逻辑,又不同于国家治理的元治理逻辑,它不仅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而且是以建构共同体为导向的。虽然全球治理能否以及有没有必要建立起类似欧盟的、政治、政体和政策具有某种统一性的机构和组织,仍是一个问题,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做全球“元”治理的根本指向。在反思多层次元治理、多尺度元治理和多空间元治理概念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把关切人类共同生活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治理的“元”治理范式。这是因为,首先,这是共同体在当代世界真正现实主义的构建方式,符合全球化的历史演进逻辑;其次,它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超越传统的二元论范式(如普遍—特殊、国家—社会、个人—社会、理想与现实)提供了新的论域。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不同共同体形式的整合问题,以及价值实现悖论都可以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但有差异的治理实践当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参考文献 :
[1]Bob Jessop.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cale and European Governance”,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05, 96(2).
[2]Alberto Martinelli. “Markets, Governments, Communities,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003, Vol. 18(2).
[3]Jan Aart Scholte. Globalisa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 2nd edition,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4]Jonathan Joseph. The Social in the Global :Social Theory ,Governmentality and Global Politic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5]Alberto Martinelli. “Markets, Governments, Communities,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003, Vol. 18(2).
[6]B. Ramesh Babu. “Genuine Global Governance: Hegemony to Legitimacy”, South Asian Survey, 2017, 21(1&2).
[7]Luis Cabrera. “Global Government and the Sources of Globoscepticism”,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5, Vol. 43(2).
[8]Thomas G. Weiss. Global Governance :Why ?What ?Whither ? Cambridge and Malden, MA: Polity Press, 2013.
[9]Henri Vogt. “Possibilities of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Age of Globalisation”, Forum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2003, 30(1).
[10]Steven Slaughter. “The Prospects of Deliberative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G20: Legitimacy, Accountability, and Public Contest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3, 39.
[11]Louis Meuleman. Public Management and the Metagovernance of Hierarchies ,Networks and Markets , Heidelberg: Physica-Verlag, 2008.
[12]R. A. W. Rhodes. Understanding Governance :Policy Networks ,Governance ,Reflexivity and Accountability , Buckingham ·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7.
[13]Louis Meuleman. “The Culture Dimension of Metagovernance: Why Governance Doctrines May Fail”, Public Organization Review, 2010, 10.
[14]Chris Brown. “World Society and the English School: 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erspective on World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1, 7(4).
[15]B. Ramesh Babu. “Genuine Global Governance: Hegemony to Legitimacy”, South Asian Survey, 2017, 21(1&2).
[16]Akira Iriye. Global Community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7]David Held. “Restructuring Global Governance: Cosmopolitanism,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9,37(3).
[18]Helmut Anheier et al.. “Introducing Global Civil Society”, in Helmut Anheier, Marlies Glasius and Mary Kaldor(eds.), Global Civil Society , 200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T. Olaf Corry. “Global Civil Society and Its Discontents”, Voluntas , 2006, 17.
[20]Volker Heins. “Global Civil Society as Politics of Faith”, in Gideon Baker and David Chandler (eds.), Global Civil Society :Contesting Futures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21]Jens Bartelson. “Making Sense of Global Civil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6, 12(3).
[22]David Held. “Cosmopolitanism: Globalisation Tame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3, 29(4).
[23]Richard Falk. On Humane Governance :Toward a New Global Politics , Cambridge: Polity, 1995.
[24]Henrik Enroth. “Community?”, in Henrik Enroth and Douglas Brommesson(eds.), Global Community ?Transnational and Transdisciplinary Exchange , London and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Ltd, 2015.
[25]Jens Bartelson. Visions of World Community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6]Andrew Mason. Community ,Solidarity and Belonging :Levels of Community and Their Normative Significance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7]Luke Ulas. “Global Community as a Response to the Cosmopolitan Solidarity Problem”, in Henrik Enroth and Douglas Brommesson(eds.), Global Community ?Transnational and Transdisciplinary Exchange , London and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Ltd, 2015,
[28]Gideon Baker and David Chandler. “Global Civil Society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 in Gideon Baker and David Chandler (eds.), Global Civil Society :Contesting Futures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29]James N. Rosenau. “Change, Complexity, and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Space”, in Jon Pierre (ed.), Debating Governance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30]Bob Jessop. “Metagovernance”, in Mark Bevir(ed.) The SAGE Handbook of Governance, Sage, 2011.
[31]Bob Jessop. “Territory, Politics, Governance and Multispatial Metagovernance”, Territory, Politics, Governance, 2016, 4(1).
[32]Bob Jessop. “Multi-level Governance and Multi-level Metagovernance”, in Ian Bache and Matthew Flinders(eds.), Multi -level Governance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33]Bob Jessop. State Power :A Strategic -Relational Approach , Cambridge: Polity, 2007.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a Paradigm for Global Meta -governance
WU Wei, HUST
Abstract : Western global governance studies based on various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systems have two approaches,one is empirical social science approach focused on tackling global problems,i.e. instrumental approach,another is reflective approach directed to the imagination and configuration for the future of globalization,i.e. constructive approach. By relating to the history,reality, development and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the horizons of global governance are widened in terms of the definition,explor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for concepts such as ‘international society’, ‘society of states’, ‘world government’, ‘world community’(or ‘global community’),and ‘global civil society’. The basic logics of governance,such as governance model,governance style,governance structure,and meta-governance,evolve into some new concepts,such as multi-level(meta-)governance,multi-scalar(meta-)governance,and multi-spatial (meta-)governance,in the light of constitution and practice of European Union. So constructive approach makes mor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he studies on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should not be only regarded as Chinese project,but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regard it as the ideal configuration of globalization. What need to be done is to argue,how it is possible for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o be the configuration of world future by transcending ‘world community’(or ‘global community’),and ‘global civil society’,and how is it possible to be a paradigm for global meta-governance.
Key words :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global governance; meta-governance; global civil society; world community
中图分类号 :B0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023(2019)01-0007-10
DOI: 10.19648/j.cnki.jhustss1980.2019.01.02
作者简介 :吴畏,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治理哲学研究”(15BZX019)
收稿日期 :2018-12-20
责任编辑 吴兰丽
标签: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 全球治理论文; 元治理论文; 全球民间社会论文; 全球共同体论文;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论文;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