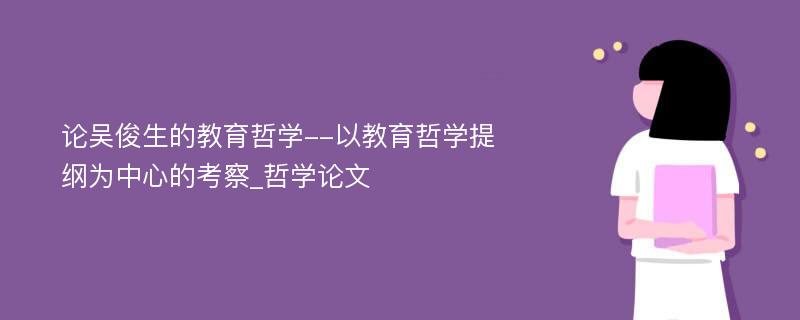
吴俊升教育哲学管窥——以《教育哲学大纲》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大纲论文,中心论文,吴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对教育哲学有些兴趣的人,大抵对吴俊升及其《教育哲学大纲》都不陌生。但是,也许是时过境迁,也许是政治因素,很少有人真正认真对待吴俊升及其《教育哲学大纲》在中国教育哲学史上的地位。即便有些教育哲学著述有所涉及,但也多是观点概述,寥寥评析。在这里,我们祈望走进他的学术生涯,以《教育哲学大纲》为支点,理出若干线索,从而“管窥”其教育哲学探究的主要思想和基本理路。
吴俊升(1901-2000)一生涉足学术、教学、行政、出版等多方面的工作,但都没有离开教育领域。早年在如皋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后在东南大学获学士学位。1928年,与夫人倪亮同赴法国,秋季注册进入巴黎大学,师从涂尔干(Durkheim,E.)的嫡传弟子福科内(Fauconnet,P.),继续研修教育理论,最终以《杜威教育学说》(La Doctrine Pédagogique de John Dewey)为论文,取得文科博士学位。1931年秋,任北京大学教授,后兼任教育学系主任,直到1936年冬休假赴美考察。其间,出版了专著《教育哲学大纲》和《德育原理》(均为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翻译了法国哲学家拉朗德(Lalande,A.)的《实践道德述要》(Precis Raisonne de la Morale Pratique)(中华书局1935年版)。1938-1944年,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1945年,任中央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并兼正中书局的总编辑。1949年以后的二十年,他主要在香港新亚书院进行教学和管理工作,其间也曾短期在台湾从事教育行政和出版工作,以及在美国大学或学会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1969年7月,正式从新亚书院退休。尽管诸事纷扰,但是他始终不忘关切和从事教育研究的事业,继续发表了一些有关文化教育的论著①。
在吴俊升的众多著述中,《教育哲学大纲》无疑是至为重要的一本。这本书是他根据自己在北京大学主讲“教育哲学”课程时编制的讲义增订而成的,脱稿于1934年,1935年1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列入“师范丛书”;同年3月增订后再版,改归“大学丛书”。1943年,在重庆再版,并增加了“渝版自序”;1948年,又在上海重版,同时写了一篇简短的“沪重版自序”。1973年,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增订本,附有“台湾增订版自序”,并在原有两编(“绪论”、“教育哲学的根本问题”)的基础上,新增“教育哲学的新页”一编,分别简述“存在主义与教育”和“分析教育哲学”,相应地在“参考书要目”中补充了一些新的论著。1985年,时值该书出版五十周年,吴俊升特别写就了《〈教育哲学大纲〉问世五十周年自叙》,这篇“自叙”最初发表在《东方杂志》第19卷第1期,后又在《教育哲学大纲》重版时辑入。七十多年来,这本书广受欢迎,行销不止,是我国大学“教育哲学”课的重要参考书,也是商务印书馆印行时间最长的“大学丛书”之一。它之所以有如此持久的影响力,不仅在于其内容的广泛、持论的公允,更在于它所开创的独特的教育哲学体系②。
所谓教育哲学,在吴俊升看来,不外是确认哲学和教育的关系,探讨教育所根据的哲学的根本原则,并对这些原则在教育的理论和实施上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批评性的分析③。在研究的方法上,教育哲学主要有两大派别:一派是“在教育以外寻求一种哲学,把这种哲学自外应用到教育上来,决定教育的理想”,由此教育哲学成为一种应用哲学。另一派“不主张从外方将一种哲学应用到教育方面来,而希望教育自身能产生一种哲学”。后一派的主张尽管可以提高教育哲学的地位,但是离开一般哲学,教育哲学便无从建立,所以他认为,比较接近事实的,还是前一派的观点。即“我们要检讨一下哲学思想史和教育思想史,便可见到每个时代的教育思想,都是当时的哲学思想的反映,而教育哲学家的系统,无非是他本人的哲学系统演绎而成。这种事实,可以证明教育哲学终是哲学的应用,要研究教育哲学非从哲学下手不可。”④由此可见,抛开一般哲学谈教育,是无所谓教育哲学的。他在探讨教育哲学时,始终没有离开这种立场。
从这种教育哲学的定位出发,教育哲学又该有怎样的体系架构呢?20世纪30年代,教育哲学仍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有关教育哲学体系的建构,仍处在探索之中,甚至没有取得基本的共识⑤。吴俊升综合当时教育哲学的各种尝试,提出作为应用哲学的教育哲学,不外采取三种研究程序:第一种略近于“哲学之教育的应用”,即“以哲学里与教育有密切关系的各个主要问题,如心灵论、知识论、社会哲学及道德哲学等等为纲,以各派哲学对于这些主要问题的解答为目,然后评述各派哲学对于此等主要问题的解答,在教育上所生的影响”;第二种略近于“各派教育哲学之体系”,即“以各派哲学如自然主义派、理想主义派、实行主义派、社会主义派、个人主义派等等为纲,以各派对于教育有关系的各个主要问题的解答为目,然后评述此各派哲学体系在教育上所生的影响”;第三种略近于“教育之哲学”,即“以教育本身的根本问题如教育本质论、目的论、方法论、价值论、课程论为纲,以和此等根本问题相关涉的各派哲学的解答为目,以期阐明何派哲学,对于教育本身何种问题,有何主张,有何影响,最后更就教育上的实际结果,加以批评”⑥。
这些研究程序,虽在结构和体系上各有特点,但在研究目的上都是为了探究教育的哲学根据。相比较而言,吴俊升更倾向于第一种程序。尽管这种程序有偏重哲学的系统而忽略教育本身体系的嫌疑,但是他认为,这种体系更适合当时中国教育学系的学生,因为他们“对于哲学大概是缺少很高深的修养的”,“为他们讲教育哲学,若是不先从浅显处把教育的哲学基础指示清楚,然后再回到教育本身的问题,恐怕教学的结果不是只讲过‘教育’,根本未接触到‘哲学’而成为教育学的重复品,便是‘哲学’和‘教育’两方面的观点都牵混不清”。⑦
吴俊升在综合考虑之后,按照第一种研究程序,组织《教育哲学大纲》的框架和体系。第一编“绪论”概述教育哲学的学科性问题,第二编“教育哲学的根本问题”分述“心灵论与教育”、“知识论与教育”、“道德哲学与教育”、“社会哲学与教育”。就其结构和观点而言,这本书主要是以杜威教育哲学“折衷”各派主张:在心灵论上,以自然主义“折衷”实体论、原子论和唯物论;在知识论上,以工具主义“折衷”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在道德哲学上,以实验主义“折衷”快乐主义和康德主义;在社会哲学上,以民主主义“折衷”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黄济先生认为,这种“体系是比较完整的,而且在内容上丰富方面,可以说是居所有‘教育哲学’专著之冠。”⑧
不仅如此,吴俊升采取的这种研究程序和体系安排,在当时的教育哲学著述中,不仅中文著作没有先例,而且外文著作也不甚完备。只是在《教育哲学大纲》问世五年后,也就是1939年,美国教育哲学家布鲁巴克(Brubacher,J.S.)才在《现代教育哲学》(Modern Philosophies of Education)一书中采用了类似的体例;1961年,莫里斯(Morris,V.C.)在《哲学与美国学校》(Philosophy and the American School)的理论部分,也以本体论、知识论、价值论为纲,以各派哲学的解答为目,最后归结到教育的应用上。至于国内的教育哲学研究者,主要采用后两种研究程序(特别是综采二者)⑨,只有少数将第一种研究程序纳入教育哲学的写作中⑩。从这种意义上说,《教育哲学大纲》为教育哲学的体系建构开辟了新的路径。
诚如前述,这本《教育哲学大纲》在观点上与杜威教育学说有内在的关联。有关杜威教育学说的研究,实际上也构成了吴俊升教育哲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主题。在他的著译中,也以有关杜威的研究为最多。
吴俊升与杜威教育学说的接触,是在进入南京高师以后的事情。1919年,杜威在南京高师讲学,但是吴俊升入南京高师时,杜威已经在北平讲演了,他“未能赶上”。但是,杜威讲演的文字都在报纸刊出,他都有阅读。而且,当时南高汇聚了许多杜威的信徒,他们使用的教材和教授的内容,也多是杜威的思想。杜威的五大演讲以及他的《民主主义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思维术》(How We Think),对他都有至深的影响。他深切地感受到,“从前在如师所学的传统的教育理论和方法,都不免陈旧,应该放弃。”这时,他已经“开始成为杜威教育学派的一个信从者”(11)。
对杜威教育学说的这种兴趣,很快就转化为一种严肃的研究。1925年,吴俊升在《教育杂志》第17卷第1号上,发表了首篇有关杜威教育学说的研究论文:《杜威的职业教育论》。在法国读书时,在福科内的提议下,他对杜威教育学说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并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杜威教育学说》(文末附有所译杜威的《我的教育信条》)。在法文中,这是第一本比较完备地介绍杜威教育学说的著作。1931年,这篇论文在Les Presses Modernes出版。1932年,由热拉尔塔(Reralta,A.J.)节译,载于乌拉圭国家出版部的《教育全书》(Enciclopedia de Educación)。1958年,该书又在巴黎沃仁哲学书局(Librairie Philosophique,J.Vrin)再版,列入《哲学史丛书》(Bibliotèque d'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对他来说,这是与《教育哲学大纲》同等重要的著作。
应该说,这篇论文为吴俊升后续的杜威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至于他在《教育哲学大纲》、《德育原理》、《教育概论》(12)等著作中都在不同程度上融合了杜威教育学说,而且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杜威教育学说的论文。在这些著述中,吴俊升首先注重对杜威教育学说的“同情式”理解,要求回归杜威的文本本身,将杜威教育学说与其追随者的观点区分开来,将杜威教育学说与其实施区分开来,特别是将杜威教育学说与“新教育”或“进步教育”运动区分开来,从而避免将追随者的“误解”和实践者的“变形”归咎于杜威教育学说本身。他说,“杜威的教育学说,实是体大思精,面面顾到,并没有有丝毫偏颇的地方。他总是以较高的概念统摄教育方面个性与社性、训练与兴趣、权威与自由、心理组织与论理组织、理论与实践、纯理与实用种种的对立而折衷至当的。可是,他的门弟子,阐述和实施他的学说,却不免有偏重个性、自由、兴趣、放任、心理主义、活动主义、狭隘的实用主义的趋势。……我觉得这些以杜氏学说为标榜,而所实施的并不是他的主张,一方面固然对于教育本身有害,一方面也是对于杜氏本身欠公道。”(13)
尽管吴俊升对杜威教育学说倍加推崇,但是他并不“盲从”杜威,而是主张在“同情式”理解的基础上,对杜威教育学说采取一种批判性的态度。所以,他说自己“仅为杜威学说之研究者,而非其追随者”(14)。早在南京高师附中任教时,他就意识到“杜威一派教育学说的限制”。特别是当时受杜威学说影响,在“新教育”名义下实施的教育,往往偏重儿童一端,他感到有必要“从社会的观点,来加以批判,并重估其价值”,因此在《大公报》的教育副刊发表《重新估定新教育的理论与实施的价值》一文,反对“新教育”对“旧教育”的矫枉过正,认为“新旧教育的原则,仅是程度的差异,并非是非的绝对,应该随着教育的实况而互相折衷,互相均衡”。在当时的氛围下,这种批判是冒大不韪的,以致“《教育杂志》编者不敢发表这篇论文”。同样,在《教育哲学大纲》中,他虽以杜威教育学说为“折衷”,但决不是简单附和杜威教育学说而没有批评和补正,而是试图以“社会的观点”来平衡杜威及其追随者的“个人的观点”。(15)在这些论述中,吴俊升以当时杜威教育学说在实施中逐渐走向极端,从而主张“以社会权威来平衡个人自由;以义务观念来平衡兴趣主义;以为求知而求知,来平衡为做而求知;以教育为生活准备,来平衡教育即生活”。(16)但是,到了20世纪中期,杜威教育学说在美国及其他国家遭遇挫折,饱受批评,吴俊升觉得其中不少批评是缺乏根据的,因而又再发表了《杜威教育思想的再评价》(载新亚书院《学术年刊》1960年第2期)一文(17),为杜威教育学说进行辩护。他认为,杜威教育学说尽管要求一些先决条件(如教师),存在一些内在困难(如教育目的、教材、方法方面),但是杜威的思想仍然把握着现代教育运动和潮流的正确方向,代表着促进教育现代化和人道化的新趋势(18)。正是有了这种独立而公允的批判态度,吴俊升才能做到“始而对于他的学说,在实施上发生缺点,加以批评;继而在他的学说,受到不公正的攻讦时又加以辩护”。(19)这为他在国际杜威研究领域赢得了声誉。
除了直接研究杜威教育学说之外,吴俊升还在杜威生平行谊和著述的整理方面颇有贡献。他研究杜威数十年,常常感到缺少一种详备的杜威传记,记叙杜威生平行谊和思想渊源,因此重拾早年在《杜威教育学说》首章叙述杜威生平和著述的工作,将平日积累的杜威生平和著述资料加以整理,终在1961年完成了《约翰杜威教授年谱》初稿,1971年进行了增订,后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增订约翰杜威教授年谱》(1983)。这个编年长谱,综采其他杜威传记的优势,为研究杜威思想的渊源和演变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另外,在整理杜威著述方面,吴俊升颇为看重的一项工作是,还译杜威在华的全部演讲。1964年,他应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East-West Center)的聘请,研究杜威对中国思想与教育的影响。杜威当年在华讲演,原来的英文手稿或讲演大纲,俱已散佚。吴俊升在夏威夷大学与克洛普顿(Clopton,R.)教授一起,将杜威在华的全部讲演还译成英文。这些英文译稿,一直存在夏威夷大学图书馆。其中,有三册已经出版:一是《杜威在华演讲(1919-1920)》(John Dewey,Lectures in China 1919-1920),1973年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二是《思想的类别》(Types of Thinking),1984年在纽约哲学文库(Philosophical Library)出版;三是《杜威在华演讲(1919-1920)——论逻辑、伦理、教育和民主》(John Dewey,Lectures in China 1919-1920 on Logic,Ethics,Education and Democracy),1985年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出版(该集另有吕聪明博士助译)。在整理这些讲演的基础上,吴俊升还写就了一篇报告论文《杜威在华演讲及其对中国思想和教育的影响》(Dewey's Sojourn in China:His Lectures and His Influence on Chinese Thought and Education)(20),认为在西方教育学家中,杜威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是最大的,也是最全面的。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杜威的访华讲演与其中国学生的传播展开的,不仅触及了教育理论的更新,而且表现在教育实施中采取的各种新改革和新举措上,包括改订教育宗旨、采用美国学制、制定儿童中心课程、推行新教学法、成立实验学校、提倡学生自治等等(21)。
值得一提的是,吴俊升曾经三次拜访杜威,既就杜威著述请益,又咨询杜威有关当时中国教育问题的看法。第一次是在1930年秋,时逢杜威在巴黎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经福科内引介,在杜威住的旅馆内拜访他,主要是请杜威指示博士学位论文纲要,同时就《我的教育信条》译成法文,征得杜威同意。第二次是在1937年春,在杜威的寓所,与拉特纳(Ratner,J.)(22)一同与杜威晤谈,向杜威提出了两个问题:“在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情形之下,教育上应该注重的是世界主义还是民族主义?”“教育上是否可以施行强制作用(Constraint)?”杜威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第三次是在1945年6月,与邱椿、朱启贤同谒杜威,希望了解他对中国教育的看法,以及他对赫钦斯(Hutchins,R.M.)的批判、“名著计划”及自身理论的妥当性的意见。这三次晋谒,尽管时间很短、谈论有限,但是吴俊升从这些交谈中,感到杜威不仅是伟大的“经师”,而且是伟大的“人师”。在他看来,“从西洋教育史上考察,没有一个教育家有类似他的博大精深的教育学体系的。也没有一个教育家在教育实施上发生过如他这样伟大的影响的。也没有一个教育家以他的本身伟大的人格施教,如杜威这样诚恳而一致的。他的教育理论与实施,如得着适当的了解,依然是世界教育界的指南针。”(23)
正是有了这些持久的关注、公允的批判和深度的接触,吴俊升对杜威的理解尤为“入里”。20世纪初叶以来,杜威俨然成为我国教育界的一种“现象”,但是真正懂得杜威的,也许屈指可数。当年,由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进而“笔伐”杜威的实验主义(24),“师生三代”共牵连;孟宪承先生就曾感喟,中国真正懂得杜威的,大概“两个半”。据推测,一是胡适,另一个即是吴俊升。至于“半个”,那是孟先生的自谦。(25)云云。这种推断,是大致也不为过的。
对于《教育哲学大纲》的体系安排和观点评析,吴俊升自己是满意的,以至于在历次重印和修订中,他也一直维持初版的体系和观点,只是做了极少处的文字修正。但是,这本书主要是评述西方教育哲学的内容,而没有述及中国教育哲学的问题。这不能说不是一种“缺憾”,吴俊升一直心中耿耿。为了弥补这种“缺憾”,他在“渝版自序”和“《教育哲学大纲》问世五十周年自叙”中,试图对中国教育哲学的问题做些解答。寻求适合中国的教育哲学,实也成为他教育哲学探究的重要方向。
在求学和从教初期,吴俊升对时代风向和教育思潮非常敏感,这种集中敏感体现在他对中国教育现状的“逆势”批评上。当时中国充斥了各种教育思潮,进行着各种教育尝试,但是他感到这些理论和实践,“纷纭变化,没有重心,引起矛盾冲突与幻乱和失去效力,”(26)所以提出“中国教育需要一种哲学”。在他看来,这种哲学不一定就是形而上的意义,而是指导实践的最高原则。就像经济、政治活动一样,教育的实施也需要统整在一个或数个原则之下。事实上,当时东西方的发达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教育哲学。中国教育在采取新式学校制度以前,也有自己的哲学,如“中学西用”;只是在采取新式学校制度之后,失去了统一的哲学。首先,当时的教育偏重“怎样教”、“怎样训练”的方法问题,而对“教什么”、“训练成怎么样的一个人”等问题关注不够。其次,教育方法和制度“轻易模仿和轻易纷更”,以致摇摆不定。再次,在教育理论和实施中存在各种矛盾,如文化传递上中西之争、德育上公私之别、教育社会化上的社会观冲突等。吴俊升认为,这些问题的背后,都与缺少一种教育哲学的指引有关系,因此中国亟待建立一种教育哲学,处理这些教育理论上的分歧和教育实践上的冲突。
既然如此迫切,那么怎样寻求适合中国的教育哲学呢?吴俊升认为,这种教育哲学,必定涉及宇宙观、人生观、社会观等根本问题,又必定与中国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要求相应合,而不能由教育界本身单独进行决定。他说,中国教育的哲学“应该由全国的哲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科学家、教育家……一齐起来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和现在的需要,作一番综合的考察,先确定一种普通哲学。这种哲学,在其内容上,应有一种明确的宇宙观、人生观和社会观;在应用上,应该可以顾及经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艺术、教育各方面,而作为最高的指导原则。然后教育学在根据这种普通哲学,演绎出几项指导原则,为理论和实施的基础,而这些指导原则,便构成我们所需要的教育哲学。”(27)显然,这种方向和路径,与吴俊升所持有的“教育哲学作为应用哲学”的观点是一致的。
吴俊升的这些主张,不久便激起了一场争鸣。例如,张君劢认同由哲学演绎出教育哲学的观点,但是他认为,适合中国的教育哲学在建构上还面临着两点困难:第一,与欧洲教育的情况不同,当时我国教育与哲学是分离的,因此哲学难以成为我国教育的南针,推进我国教育的变迁;二是我国教育缺少一贯的精神,常在各种思想和制度中彷徨无主。要克服这些困难,建立中国教育哲学,最终需要在各派哲学之间、在各时代文化之间实现大综合(28)。另一位学者姜琦则不同意吴俊升指示的建构中国教育哲学的路径,相反认为这种哲学只能在教育界产生,因为教育哲学是一种特殊的哲学,就像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等一样,具有自己的特殊对象——教育事实;而对于这种事实,只有教育家自己才能够看得清楚而捉摸其真意义。否则彼此越俎代庖,凡所产生的种种特殊哲学,都不免隔靴搔痒,难算是真正的各个特殊哲学。(29)而且,姜琦、崔载阳等人认为,当时中国教育已经蕴含着一种哲学(即“三民主义”),而无需外求。
这些积极的回应,也让吴俊升进一步感到问题的重要性。他意识到,不能只满足于提出问题,还需要寻求明确的解答,真正为中国教育寻找一种恰切的哲学。因此,1943年,在《教育哲学大纲》的“渝版”自序中,吴俊升就尝试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面对两次世界大战,他深切地感到,无论是德国的极权主义,还是英、美的民主理想,都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教育哲学:德国要改变极权主义,走向民主主义;英、美要维持民主主义,同时克服个人主义的积弊。至于我国教育,从清末以降,先是与德国教育相近,奉行爱国主义的精神,主张“发愤图强,牺牲小我,效忠国族”;后又转向“崇尚个人自由”、“憧憬于国际主义”,与英美教育旨趣相同,但是这种教育哲学却使中国成为组织松散、“解除武装”的国家,后来又渐渐矫正过来。在吴俊升看来,当时中国还是一个“组织没有完成的国家”,“个人的思想和行动还是太嫌散漫自由”,加之国家“缺乏国防和军备”、人民“太重私利”,因此中国教育固然不能放弃民主主义的理想,但是也“决不能忽视组织与训练,也决不能放弃国家民族的本位”,因为只有养成守纪律、负责任的国民,才能具备民主的条件,只有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才能在国际上成为“一个有力的单位”。所以,他说,我国教育哲学既不能采取极权主义,也不应完全模仿英美式的民主主义,而要“以折衷于善群与修己、组织与自由、训练与兴趣、民族与国际之间的一种健全社会哲学为依归”(30)。建立这样一种合理的、自主的教育哲学,应该成为我国教育哲学研究者的使命。这种主张在当时乃至在今天,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吴俊升认为这种“健全社会哲学”就是“三民主义”。末了,他希望,《教育哲学大纲》能够为建立中国教育哲学提供一种参考。
上面只是从教育哲学方面,简要勾勒吴俊升所做的一些富有开创性的探索。正是通过开拓教育哲学的新体系、推进杜威教育学说的发展、寻求适合中国的教育哲学,吴俊升确立了他在中国教育哲学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甚至可以说,有关中国教育哲学的回顾和反思,都不能绕开吴俊升及其《教育哲学大纲》,都需要在不同程度上回应他探讨的一些问题。然而,在中国大陆教育界,吴俊升在教育学术上的贡献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期待,从历史的角度迎来新的局面。
本文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瞿葆奎先生的指导。在他的函请下,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杨深坑先生惠寄了大量有关吴俊升生平和著述的资料,主要有《教育与文化论文选集》(1972)、《文教论评存稿》(1983)、《庚午存稿》(1994)、《教育生涯一周甲》(1976)、《增订江皋集》(1986)、《教育哲学大纲》(增订本,2001),以及司琦、徐珍编的《吴俊升先生暨夫人倪亮女士年谱》(1997)。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①其中结集出版的有《教育论丛》(台湾中华书局,1956重版,该书1939年在上海中华书局初版)、《教育与文化论文选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文教论评存稿》(台湾正中书局,1983)、《庚午存稿》(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等,同时编有《增订约翰杜威教授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还翻译杜威的《自由与文化》(Freedom and Culture)(台湾正中书局,1953)等。此外,吴俊升也酷爱文学,吟唱诗文,除了自传体的《教育生涯一周甲》(1974年连载香港《中华月报》,1975年台湾《传记文学》分期刊载,1976年由传记文学出版社印单行本)之外,还自印《江皋集》(1966,《增订江皋集》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6年版)、《庚午酬唱集》(1971)、《庚年酬唱续集》(1982)等。有关吴俊升生平和著述,可参见吴俊升:《教育生涯一周甲》,传记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国立”教育资料馆主编,司琦、徐珍编:《吴俊升先生暨夫人倪亮女士年谱》,台湾三民书局1997年版。
②吴俊升:《教育哲学大纲》,台湾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教育哲学大纲》问世五十周年自叙”。
③吴俊升:《教育哲学大纲》,台湾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9页。
④吴俊升:《教育研究的检讨和展望》,载《文教论评存稿》,台湾正中书局1983年版,第191—192页。
⑤1933年,邱椿在为姜琦《教育哲学》所作的序中,依凭自己的研究和了解,罗列了当时有关教育哲学的十种讲法:(1)阐明哲学与教育的关系,其中又有两种:一种是讲明哲学中几门学科和教育的关系,另一种是讲明各家的哲学与其教育思想的关系;(2)叙述近代各派的教育哲学;(3)陈述各国教育之哲学的基础;(4)研究教育哲学问题;(5)讲述一派或一家的教育哲学;(6)探讨教育价值;(7)研究历代教育哲学变化的规律;(8)陈述教育的根本原理;(9)批评现代的教育;(10)发表个己的教育哲学。见姜琦:《教育哲学》,群众图书公司1933年版,“邱序”。
⑥吴俊升:《教育哲学大纲》,台湾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8页。
⑦吴俊升:《教育哲学大纲》,台湾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自序”。
⑧黄济:《教育哲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302页。黄先生认为,“心灵论与教育”、“社会哲学与教育”部分,可以独立成为教育心理学和教育社会学。这是可以商榷的。事实上,吴俊升并不是简单地从经验的(empirical)层面描述心理或社会的现象和结构的。
⑨例如,姜琦:《教育哲学》,群众图书公司1933年版;陆人骥:《教育哲学》,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林砺儒:《教育哲学》(开明书店,1946);张栗原:《教育哲学》,三联书店1949年版;陆有铨:《现代西方教育哲学》,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王坤庆:《现代教育哲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
⑩例如,傅统先、张文郁:《教育哲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二编“分论”(包括“价值论与教育”、“伦理学与道德教育”、“认识论与教学”、“美学与美育”);黄济:《教育哲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三编“教育哲学的基本问题”(其中涉及“知识论与教学”、“道德论与道德教育”、“美学与美育”、“宗教与教育”等)。值得注意的是,与吴俊升的《教育哲学大纲》不同,这两本还整合了另外两种研究程序。
(11)吴俊升:《教育生涯一周甲》,第17页。
(12)与王西征合编,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13)吴俊升:《杜威先生会见记》,载《教育与文化论文选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86—387页。
(14)吴俊升:《教育与文化论文选集》,第2页。
(15)这种“社会的观点”,主要来自涂尔干和福科内。有论者认为,这本《教育哲学大纲》受“康德哲学”的影响,似乎缺乏充分的根据。毋宁说,这本书的观点直接受杜威哲学、涂尔干社会学的影响,更为合理。
(16)吴俊升:《教育生涯一周甲》,第61页。
(17)1961年3月,该文又以《杜威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再评价》(A Re-evalu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of John Dewey)为名,发表在美国《教育论坛》(The Educational Forum)。
(18)吴俊升:《杜威教育思想的再评价》,载《教育与文化论文选集》,第316—318页。
(19)吴俊升:《教育生涯一周甲》,第113页。
(20)这篇报告的节写《杜威在华演讲及其影响》(Dewey's Lectures and Influence in China),收录在博伊斯顿(Boydston,A.)主编、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杜威著作导读》(Guide to the Works of John Dewey)中;1971年10月,这篇报告又以中文在《东方杂志》刊发;1983年,在《中国文化季刊》(Chinese Culture Quarterly)第24卷第2期发表。
(21)吴俊升:《杜威在华演讲及其影响》,载《教育与文化论文选集》,第354—359页。
(22)拉特纳编有杜威的《旧个人主义与新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Old and New)等论文,集为《现代世界中的智慧》(Intelligence in the Modern World)(1939),以及杜威的《我的教育信条》(My Pedagogic Creed)与其他五篇论文,集为《今日的教育》(Education Today)(1940)。
(23)吴俊升:《杜威先生会见记》,载《教育与文化论文选集》,第397页。
(24)瞿葆奎编著:《教育学的探究》,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18—520页。
(25)金锵:《殚精研究,锐意发明——忆孟宪承教授的治学精神》,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年第4期。
(26)吴俊升:《教育生涯一周甲》,第64页。
(27)吴俊升:《中国教育需要一种哲学》,载《教育与文化论文选集》,第53页。
(28)有关讨论可参见吴美瑶:《待完成的教育哲学体系——重建1934到1937年中国教育哲学发展史上的一段论争》,载《教育研究集刊》2005年第51辑第3期。
(29)张君劢:《中国教育哲学之方向》,载《东方杂志》1937年第34卷第1号。
(30)姜琦:《中国教育需要那一种哲学》,载《教育杂志》1935年第25卷第1期。
(31)吴俊升:《教育哲学大纲》,台湾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渝版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