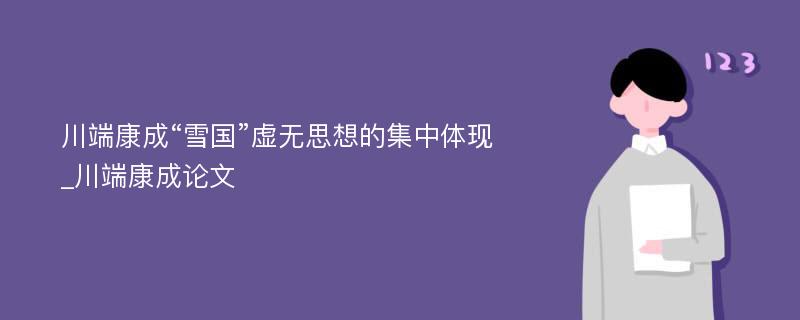
川端康成虚无思想的集中体现——谈《雪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川端康成论文,虚无论文,集中体现论文,思想论文,雪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一个作家,无论他怎样独辟蹊径,都不可能不受时代潮流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也不可能不受民族传统文化的制约。川端文学的支撑点,正是建立在日本古典文学传统和西方现代派艺术表现手法等基础上。川端康成在继承和创新的自觉结合中,开拓了一块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川端康成的名字,是与日本传统的美联系在一起的,他把东方传统的“悲”、“无”、“美”作为核心成分组构起来,赋予它“超然”的特质,表现了川端式的虚无思想,别具一种哀婉、细腻、幽美的格调,与西方现代派虚无思想遥相呼应,显示出东西方虚无思想相似中的差异。
一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雪国》思想主题的理解也是如此。有人认为它表现了日本传统的女性美和自然美;有人说它表现了复杂悲悯的深沉情感;也有人说它赞颂、同情驹子执着纯洁的爱情和美好的心灵,鞭挞了岛村颓废的生活态度和虚无思想。我们知道,对于作品的思想,只有深入作品,并对其艺术本身的艺术逻辑进行分析,才能得出客观准确的结论。
川端本人曾直白:“我的作品中新感觉成份并不浓厚”,①但他的《雪国》还是带有明显的新感觉派特色。新感觉派看重的是人的感觉经验和意识。在他们看来,外在的事实并不重要,因为客观世界纷繁多样,它的本来面貌是根本无法真正把握的,并反对传统小说精心编织情节,认为传统小说歪曲了生活的本质,现实主义用虚假的真实欺骗读者。所以新感觉派独辟蹊径,以主观感觉映象代替对事物的客观描写,不太重视人物、情节和结构,作品只有感觉赋予人与事物的“形态”与“景象”,以及由此构成的情境,作家对生活含义的基本理解,就寓于这种情境之中。这种艺术手法显然带有西方现代派的影子,又融汇了东方文化传统。
在《雪国》中,感觉的主体是岛村。作品以平静的语调记述了坐食祖产的游闲者、舞蹈家岛村三去雪国的经历。岛村初到雪国,结识了单纯而又执着、对生活满腔热情的驹子。无论是学三弦,还是记日记,抑或是对待爱情,驹子都是一丝不苟的。驹子一往情深,爱上了过路游客岛村,而岛村却认为驹子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岛村第二次去雪国的路上,遇到了美丽的姑娘叶子。叶子“近乎悲哀的美”使他为之销魂,但叶子却一心扑在行将就木的行男身上,沉浸在幻境般的爱情世界里。岛村第三次去雪国时,行男已经死去,岛村一面跟驹子虚无周旋,一面倾心于美丽的叶子。正当岛村准备与叶子同道返回东京时,叶子却坠身火场,安详地死去了。
在这个充满感伤气氛的故事中,驹子的形象是十分动人的。作为艺妓,在世俗的意义上,她是谈不上纯洁的,但她心地的善良,执着的追求和对岛村的一心一意而让岛村觉得她“洁净得出奇,甚至令人想到她的脚趾弯里大概也是干净的。”她本不爱师傅的儿子行男,但为了给行男治病,却毫不犹豫、也毫无怨言地做了艺妓。虽是在屈辱的环境下成长,经历了人间的沧桑但没有湮没在纸醉金迷的世界,而是承受着生活的不幸和压力,挣扎着生活下来。驹子对生活的认真和热爱,甚至表现在细微末节上。记日记,做读书笔记都使我们不难看出她的求知欲望、顽强毅力和对正常人生的渴望和追求。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练出的技艺比一般艺妓高出一筹。虽然这是职业的需要,但对驹子来说,又是她“顽强求生的象征。”驹子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还表现在她对纯真爱情的渴望上。驹子同岛村邂逅之际,便把全部爱情倾注在岛村身上。不顾自己的得失,把自己的身心都依托给对方,她这种对爱情的态度是坦荡的,也是纯真的。她对岛村的爱恋,实际是对朴素生活的依恋——她只是渴望过正常的生活,她所追求的只是一个普通女子的正当权利。从作者赋予驹子的形象可以看出,川端康成对笔下的这个人物是抱有同情的,正如他自己曾经表白过的:“作者深入到作品中驹子这个人物的内心之中,对岛村却不大顾及。”②但如果就此来断言,《雪国》的思想主题是表现对驹子的赞美和对岛村的批判,却显然有些欠妥。虽然在作品中驹子与岛村的生活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这种对照却构不成对岛村的鞭挞,相反的却构成了对岛村虚无思想的肯定,因为《雪国》中所有对驹子的描写和同情,都是经由岛村的感觉屏幕显现的。而全篇的情境设置,恰恰是对岛村那种虚无人生观的印证。
岛村生活态度中的虚无主义是显而易见的。他从来不看西方舞蹈,却热衷于“凭借西方印刷品来写西方舞的文章”,他到雪国寻欢逍遣,是在空虚的自我放任中寻找寄托,以求“得到一种心灵上的慰藉。”对于岛村来说,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当人们抱有非现实的想法徒劳无益地追求它们的时候,才对它们感到“一种虚幻的魅力”,他不辞辛苦地登山是如此,对驹子和叶子的追求也是如此。在岛村的感觉里,驹子的肉体的现实的美,一旦被占有就失去了它的魅力,以往的追求“如同一场梦”,叶子的精神的非现实的美,则始终是不可企及的。川端康成有意识地安排追求纯真爱的驹子和追求虚幻爱的岛村之间的相互对立,以及叶子的猝然假死,使岛村对她的爱构成“非现实世界的幻影”,最终导致悲剧的结局。岛村是日本三十年代持消极遁世的人生态度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作者通过这个形象表现的显然是:美是虚无的,对美的追求是徒劳的,人生不过是一场虚幻的梦。
如果说川端的虚无思想在岛村身上主要是通过意识活动来表现的,那么在驹子身上则是通过具体的、生动的形象来表现出来的。驹子是作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显示出生活的“徒劳无益”。在作品中,驹子对生活的全部奉献与追求都落了空——她卖身为妓为行男治病,但垂危的行男照样很快地死去;她练得一手好琴,却没有机会在舞台上一显身手,只能供酗酒者作乐之用。作品中着墨最多的,也是最可悲的,是她对爱情的执着追求自始至终寄托在不可信赖的岛村身上,而岛村虽然也不是玩弄驹子,但却一面“反觉得她的存在变得更纯真了”,一面同情地感到驹子的生活态度是一种徒劳。即使是后来岛村一心想摆脱她的时候,驹子对岛村仍是一往情深。川端有意无意地经常把驹子这种可以观照的外部活动与岛村的意识活动放在一起映照,使岛村从旁观者的身份去注视驹子的行动,发出“徒劳”,“完全是一种徒劳”的叹惜,这种对照无疑是在告诉读者,命运就是这样。在这种情境设置中,作者越是将驹子对生活的追求描写得纯洁、执着,这种追求的“徒劳无益”就愈在读者心里引起震动,“徒劳”这个词由岛村的口与心重复了十余次,绝不是偶然的。作者企图以此在读者心中唤起共鸣。
行男这个人物,似乎只是一个简单的道具而已,但他的存在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是联结驹子与叶子感情线索的交接点。驹子和叶子与他的感情纠葛,把作者埋下的伏笔绷紧,随时准备把读者引向一个虚无的空间。他成为表现作者虚无思想的死亡的象征。
如果把《雪国》看作一支凄婉、感伤的乐曲,那么悲观与虚无就是它的主旋律,它表现的是川端“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徒劳”的心声。
二
川端是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他力图追求新的感觉,新的生活方式和对事物的新的感受方法。他以锐利的目光搜集,灵敏的神经感触,继承古典文化传统,借鉴西方艺术表现手法,不断探索,创造出具有东方特色的现代派文学。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川端的虚无思想在《雪国》里得到最充分最集中的体现。驹子对生活的执着追求、真诚奉献,统统归于幻灭,让读者从这个形象上领悟到“人的生存和追求是一种徒劳”的思想。岛村为了排除心里难以忍受的苦闷寂寞,在神魂颠倒的幻想中寻找自我价值,而现实生活对他来说已毫无意义和魅力。在他身上显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自我意识的破灭,以及忧郁、伤感和无所作为。行男一出场就生命垂危,他人的帮助,自身的挣扎都挽救不了死亡的命运。行男的死似乎在显示,年轻的生命在大自然面前无能为力。这三种虚无思想的表现形式在西方现代派文学中都有所反映,虽然他们身上反映了东方的色彩,但还不足以代表川端虚无思想的典型特征。
叶子作为一个与驹子相对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是一个透明的幻影,是灭我为无的超脱象征。与驹子对现实生活的执着相反,叶子的生与死都是力图超脱世俗的。行男未死时她沉缅于精神上的爱;行男死后,她沉浸在悼念中。她似乎总是生活在超脱尘世的幻境中。叶子是位非常纯朴的少女,“从没有赴宴陪过客”,同岛村接触也“充满了警惕”的神色,最后因为生活无着,才祈求岛村带她到东京当女佣。最后通过一场大火,摆脱了世俗的缠绕,安静地完成了“内在生命的变形”而归于虚无。叶子在《雪国》中既是“悲”的象征,“无”的象征,也是“美”的象征。作者从描写叶子超凡的美开始,以描写叶子脱俗的美告终,结尾调动雪的纯洁、火的神圣、银河的壮丽,为叶子的死——摆脱尘世达到解脱的虚无——创造出一个凄美无比的意境。川端通过岛村的思想写出驹子现实中的光和热,虽然有某种魅力,但一经得到就变得索然无味,只有叶子这种超然的美、虚幻的美,才使他感到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他对驹子的美常带着怜惜的心情去俯视,对叶子的美始终怀着赞叹和向往。在川端看来,死不是终点,而是生的起点,是最高的艺术,最美的表现,因而他没有把叶子的死看作是生命的完结,而看作是生命的延续,是新生命的开始,以此来表现叶子形象的纯洁性和完美性。
驹子和叶子在作者的感觉上实际是一体的。驹子是叶子的实体,叶子是驹子的精灵。驹子的精灵有着向上的追求和纯粹的美感,实体的驹子却陷入了艺妓的不可自拔的泥泽。篇终的大火,烧掉了驹子的精神追求,因为这种追求本身就是一种美的悲剧。所以当驹子抱着叶子的身体时,“仿佛抱着自己的牺牲和罪孽一样”。结尾处,岛村要离开了,无论肉体的驹子还是精神的驹子对岛村来说都是一种“美的悲剧”,一种“徒劳”,况且那“一群汉子连推带掇地”把他推到一边,要接过“叶子抱走”,这种无奈与凄凉,使岛村无限悲哀,于是岛村只好从现实走向感觉,让荡眸的泪水“哗啦一声向他的心坎上泻下来”。
川端这种超然的虚无思想的形成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年幼时亲人接二连三的逝去,冷酷的客观现实使川端在意识里铭刻下“孤独感”,定下了感伤忧郁的人生基调。是年迈的祖父相依为命这种凄怆而单调的气氛,使幼年川端康成的感情不免染上些许悲凉的色彩,在他幼稚的心灵里投下了寂寞的暗影。眼瞎耳背的祖父去世后,川端失去了家庭的温暖以及爱的象征。他漂泊无着,开始把生与死融为一体,对死的世界产生了生的感情,认为生即死,死即生。情场的多次失意,心中留下了苦闷、忧郁和哀伤,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使他感受到了人与人,幻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产生了一种胆怯和自卑,而且自我压抑、窒息和扭曲,更加深了他对虚无冥想的迷恋,强化了他对人生悲观的看法。尽管他保持着对艺术顽强执着的探索精神,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不可能不在川端的内心留下阴影。同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日本,由于战争和物质方面的畸形发达所造成的各种社会矛盾,经济萧条、劳资冲突等,使社会陷入动荡之中。敏锐的川端在这种现实中感到一种无法排遣的空虚和悲愁,更加深了他早已埋在心底的虚无思想的印记。20世纪以来的日本虽然承受了西方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潮的冲击,却始终保持着较浓厚的宗教气氛和封建性质。佛教和老庄哲学很早就影响着日本,从中演化而来的东方传统虚无思想,则是一种以逃避现实来反抗现实,在幻想中肯定人生,给人以希望力量的人生观。它渗透着东方的历史,尤其是文学。如果说,东方传统的虚无思想还不能主宰年轻时代的川端的思想,那么从饱经沧桑,历尽挫折而处在精神危机中的川端,东方传统的虚无思想则另有一种魅力。曾经像驹子一样对待生活、又像驹子一样理想破灭的川端,自然地在东方宗教里找到了使他超脱的最佳途径。难怪川端自己说:“我相信东方的古典,尤其佛典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学。我不把经典当作宗教的教义,而当作文学的幻想来敬重。”③川端晚年自杀,除了他生活、生理上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他那种超然的虚无思想。他自身的生活经历使他感到人生的孤独,生死的无常,以为生是徒劳,死是绝对的,抱着一种无法逃避的虚无感和死的宿命感。
正因为如此,曾经受到西方近代文学洗礼的川端,感觉到东方传统的宗教比西方传统的宗教更优越。他从“轮回”的思想出发,对于死产生了生的感情,而过去已有的生即死,死即生的信念更加坚定起来,升华到视死如生、视死为尽善尽美的境界,以“死的形式”达到“生的超脱”,使现实生活中极度痛苦的人生在这种超脱的境界里愉快幸福地生存下去。这种“超然”的东方传统虚无思想特质,为西方现代派虚无思想所不具备的。
川端康成自己也曾强调:“有的评论家说我的作品是虚无的,不过这不等于西方所说的虚无主义,我觉得这在‘心灵’上根本是不同的。”④作者在此特别强调的是心灵。西方虚无主义者在心灵中否定一切价值,而川端康成却抱着一种空灵的态度,有虚的一面,也有“灵”的一面。在他看来,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镜中花”。作为花的实体它是无意义的,作为花的美感它是有意义的,何况东方所承受战争的创伤和经济危机的打击没有西方那么沉重,人们的心理和精神也没有西方人那样扭曲异化到绝望的程度。所以川端文学总在虚无的思想下暗藏着一种希望之光,在叶子身上就体现出生死如一,安详坦然,心平气和地走向超然境界的东方精神。
虽然川端的文艺观点和艺术手法与西方现代派有许多相似之处,甚至主题也在表现虚无,但他精神和艺术的根基却仍在东方。川端曾反复强调:“我们的文学虽然是随着西方文学的潮流而动,但日本文学的传统却是潜藏着的看不见的河床”。⑤“我接受西方近代文学的洗礼,自己也进行过模仿的尝试。但我的根基是东方人,从十五年前开始,我就没有迷失自己的方向。”⑥川端继承和发扬了东方古典文学传统,吸取了西方精华,使两者水乳交融,不断创新。含蓄、深沉的人物,寓情于景的淡淡的伤感,清静、幽美的背景,轻快、和谐的叙述层次,行云流水般的有向结构,这些都表现了川端自己独特的东方艺术特色,有别于西方现代派作品更多表现强烈的变态,异化的人物(比如卡夫卡《变形记》中人群变成了犀牛群;尤奈斯库《秃头歌女》中一连打二十九下的时钟和《新房客》中窒息于物质之中而不自觉的房客),以及叙述上强烈的跳跃,布局上的陡险峭拔。
川端反社会的虚无思想带有笼统性、绝对性,它有很大的破坏作用;但对资本主义社会给人造成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的形象表现和其潜在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现实生活的客观意义上的否定,又有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⑦
注释:
①转引自《川端康成评传》,中国社科出版社,1989年版。
②《川端康成全集》第六卷后记,新潮社,1977年版。
③⑥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④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⑤川端康成:《日本文学之传统》,转引自《川端康成评传》,中国社科出版社,1989年版。
⑦文中摘录,除说明出处外的均摘自《川端康成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