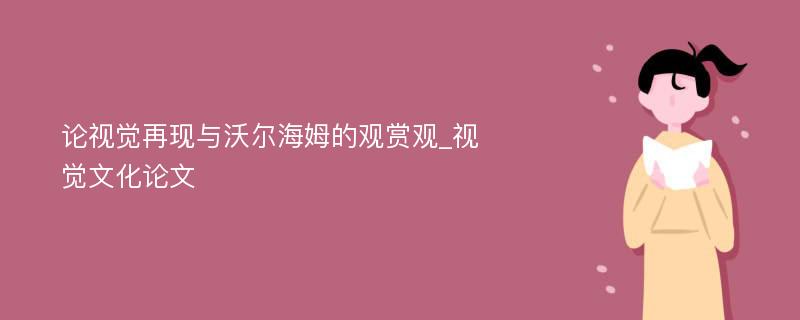
论视觉再现与沃尔海姆的观者之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沃尔论文,海姆论文,视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Representation,这个词国内一度译为“再现”,而近十多年来,“表征”这一译法则迅速取而代之。一个术语译法的转变,所代表的自然是理解方式上的一种巨大转变。对representation来说,所谓“再现”,它的最初意义与柏拉图所开始的模仿说有关,其核心在于强调图像与所模仿之物的外观上的相似性,从而让事物呈现眼前。就威廉斯对“representation”与“representative”的词源及其意义变迁的讨论来看,该词获得这种意义与14世纪欧洲对古典艺术的理解,以及19世纪对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理解都有关,结合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之前国内艺术界对现实主义的关注,那么选择“再现”便恰当地表达了representation的这一层含意。它所要表达的是一个图像与它所模仿的事物之间在视觉上的某种天然联系,这便是看上去相似。而今更为流行的“表征”译法则源自于文化研究路径,它发展了representation“代表不在场的事物”(威廉斯406)这一脉的含意,意在强调图像或文字符号的社会性,展现意识形态系统、观念系统、知识体系等建构表征系统的过程,进而揭示出其背后所掩盖的权力关系。因而按照斯图尔特·霍尔的理解,所谓“表征”不是指被模仿之物与再现之表象的相似性,而是指两个表征系统:一是物与概念系统的相似性;二是概念系统与符号之间的相似性(霍尔15-19)。在文化研究所阐述的这一层意义下,原本“再现”一词所指的基于感官相似的特征被置换了,取而代之的是符号学视野下建构的,或是有待解码的相似性。从“再现”向“表征”语意的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前者基于直接的、直观的而又基础的知觉经验,它提供的貌似是私人生理体验,但就如当年的经验主义研究一样,这种私人感官体验却提供了某种可期待的普遍性和稳定性;而后者则是社会性统合的,它不可能只隶属私人事务,但对知识体系、社会体制及意义系统的祛魅及解构,则赋予它无可回避的不确定性与人为性。在representation这两种译法的演进中,我们是否能够看到从现代性发展出的“否定性原则”的胜利?或许。但这种否定性原则是否是学者们思考“再现”或其他问题的唯一方式?那则未必。在此问题上,理查德·沃尔海姆对再现理论的创造性阐述在美学及艺术领域内极为著名。沃尔海姆以及分析美学视野下的再现问题与上述表征问题的不同之处在于,在新的再现理论那里,同时涉及了两个因素——视知觉与文化体系,而且现代再现理论的特点在于:无论是对直观感官经验可能性的讨论,还是对文化体系预先规定视觉经验之现象的洞察,都渗透到了对视知觉本身的研究之中。尽管早在模仿说时,视觉经验就已是再现观的重要因素,但当分析美学重提再现,并聚集于视知觉方面时,这时的“再现”便已是一个现代问题。 一、贡布里希与视觉再现问题的提出 当然,沃尔海姆并不是在此新视野下讨论“再现”的第一人。说到现代视觉再现问题的提出,我们不得不首先提一下学界业已很熟悉的贡布里希。 再现成为一个现代视觉问题,这是从何时开始的?与模仿说相应、追求视觉逼真的再现理论持续了很久,直到20世纪上半叶,随着照相术与现代艺术的出现,存在于“视觉真实”观念中的问题才日益被发现,按照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里所指出的那样,这时人们发现:他们实际所见的与他们所知的并不相同,在印象派与立体主义的冲击之下,“再现”越来越脱离了“模仿”的视域(512-18)。与之相应的则是瓦尔堡学派、格式塔视觉心理学等在视觉性研究上的发展,在此语境下,对“再现”的讨论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其中的开创性著作便是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在书中,贡布里希对视知觉的特殊性以及艺术再现的特征性的新发现,对分析美学的再现问题的讨论产生了极大影响,成为之后再现论争的话题与重要资源之一。 贡布里希的视觉再现观中有三个关键词:图式(schema)、制作(making)与匹配(matching)。其中图式是贡布里希指出的一直为传统再现观所遮蔽的“真相”。图式是艺术家创作不可或缺的出发点,是视觉范例、视觉框架,是再现的程式,它表现为我们所知的艺术风格。“我们的知识往往支配着我们的知觉,从而歪曲了我们所构成的物像”(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中译序”6)。贡布里希所强调的艺术家视觉再现中的图式/程式因素已极为接近霍尔的表征概念,按照贡布里希对之的理解,从光线到色彩的转变也同样也是一个编码/解码(代码传递)的问题,这也是再现图式的关键所在。当然,贡布里希的图式还限制在风格—视觉经验的议题之下,未延伸到更宽泛的社会文化领域,但拓展似乎也只是一步之遥。 就贡布里希的“图式”本身来说,他由图式出发所欲讨论的是视知觉的心理学问题,是在先的视觉图式如何影响了人的生理器官、影响我们的眼睛,从而影响了人们解读可见世界的能力。视觉经验是被建构的,贡布里希正是在此意义上反驳了罗斯金的“纯真之眼”。然而,贡布里希的“再现”毕竟不像“表征”那样跳出视知觉的直观感性领域。从制作到匹配的过程中,艺术家首先从其所知的观念/图式出发去观看,但他不会被限制在图式下,而是根据已知图式与现实的不匹配,从而通过不断试错,找出更令人满意的、可匹配的视觉图式。那么,这里有一个疑问便呼之欲出了:最终匹配的依据是什么?贡布里希并不完全赞成视觉主观性的观点,在他看来“存在着真正的视觉发现这种东西,也存在着检验它的方法”(《艺术与错觉》392)。贡布里希的答案是艺术家所见的“视觉”客观现实。那所谓的视觉现实又是什么?我们在这里应该感激贡布里希将他的讨论停留在视知觉的心理学,而不曾走得太远,因为这停留或许会比“表征”为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与思虑的空间。贡布里希介绍了两种解释这种“实际所见”的心理学观点,一种是“先天主义者”的,一种是“经验主义者”的。但他并没有真正选择一个定论,而只是指出“因为不管由于禀赋还是由于早期的学习,我们无疑具备非凡的能力,能够解释从外部世界向我们连连袭来涌入的线索,并且能够根据空间和光线的种种可能的构型来测验它们的一致性”(《艺术与错觉》395)。从而,贡布里希在此问题上的不置可否蕴含了有关视知觉问题的两个相反的立场(而这是以往我们研究者通常所忽视的)——视知觉既被知识、图式所建构;但同时也是直观与直接的视觉经验,有其生理上的先天基础。 正是贡布里希所揭示的视知觉的貌似矛盾的特征赋予了“再现”理论较之于模仿再现观及表征观更复杂的内涵。尽管并非所有的讨论者都赞成贡布里希将再现看作视觉错觉的观点,比如沃尔海姆就相当反对贡布里希的错觉说,在《艺术及其对象》《绘画作为一种艺术》(Painting as an Art)等多部文献中都对之有过专门的驳斥。但是贡布里希所建构的视知觉理解模式却奠定了其后讨论再现问题的基础。我们可以注意到,现今围绕着视知觉的被建构性与其先天知觉能力的争论极为热烈。而在此问题上,沃尔海姆所做的视觉再现研究便被公认为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进展。 与贡布里希一样,沃尔海姆同样关注视知觉既被外在惯例所建构,但同时也具备一定的先天知觉能力这一特征。他对贡布里希的视知觉观的发展表现在三点:首先,他从贡布里希及其他早期视觉再现研究者所关注的“艺术家”转向了“观看者”,这一对视觉经验者身份的转换令沃尔海姆得以跳出对贡布里希理论中艺术创作“图式”的限制,从而更贴近“看画”这一视觉经验本身所可能带有的特征。其二,视觉经验者身份转变的优势在于:观看者视觉经验较个体艺术家可以更为多元,观者既可不再受制于图式但又可以相关于图式。这就允许了对视知觉探讨的更多可能性。沃尔海姆可以进一步跳出绘画文本的限制,从而发现“看进”这一观看再现性图像时所产生的特殊视觉经验形式,即他对“看进”经验的双重性的揭示,在这种观看经验下,观看者既能把握到作品所要再现的主题,又能注意到媒介及形式本身。正是对看进双重性的坚持,让沃尔海姆认为贡布里希分析中所采用的错觉画其实不能纳入“再现”的范围,因为在错觉画中,观看者会忽略媒介的因素。①其三,如果说贡布里希的视知觉观点更侧重“图式”的那一面,那么在沃尔海姆这里,他则是在承认视知觉之被建构性的情况下,集中讨论了视知觉所具备的先天知觉能力的那一面。 二、沃尔海姆:观者之看与艺术家之眼 视觉再现,在沃尔海姆这里,它是因其对观者之看的讨论而绽放异彩的。如果我们对他的相关重要篇目加以梳理,我们可以看到沃尔海姆的“观者之看”立场在再现问题中的日益明晰。从1968年《艺术及其对象》中对视觉经验“看似”特性的发现;到1976年《看似、看进与图像再现》中通过用“观看适于再现”(seeing appropriate to representations)来代替“再现性观看”(representational seeing)来令其见解更清晰化;②再至1998年的《论图像再现》中对“适当经验”与“恰当的观者”的分析;直至2003年《是什么令再现性绘画真正可见?》中对“适当经验”的反思与进一步澄清。或许有人会指出,笔者似乎遗漏了他极为重要的《绘画作为一种艺术》中对观者之看的讨论。其实在这本书中,沃尔海姆主要从另一角度讨论了这一问题,那便是艺术家作为观看者的视角。沃尔海姆的这一做法并不是偏离了话题,而是对他所关注的“观者”身份的限定,他/她不是随意的观看者,而是通过看图像再现,与艺术家实现了视觉经验交流的欣赏者。 总的说来,依笔者之见,沃尔海姆发展其“观者之看”立场的关键一步便在于他将“再现性观看”发展到了“观看适于再现”(seeing appropriate to representations),这一变化突出了其理论的三个要点:其一是将视觉经验锁定在了观看者的视觉经验上;其二则是他相应所提出的“适当经验”为考察艺术家与观看者之间的视觉交流提供了一种可能性。“适当经验”一词的引入一方面肯定了艺术家意图及外在文化惯例在一定程度上对视觉经验的规范性,就这方面而言,视觉经验因而有其被建构性的一面;另一方面,沃尔海姆也借“适当经验”来表明视觉再现过程中,视知觉自身所具有的先天知觉能力的基础性作用,因此观看者可以在无须知晓艺术家意图及外在惯例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实现与艺术家的视觉交流。 首先,这涉及将视觉经验锁定在观看者的视觉经验。这种理论上的聚焦是随着沃尔海姆对“再现”之理解的发展而展开的。 在最初的《艺术及其对象》中,沃尔海姆对其所讨论的与“再现”有关的视觉经验的归属是含糊的。不过从他所举的例子看,他这里已经开始关注观看者的视觉经验。沃尔海姆改进了一个个案,并对之进行了评论,这比较形象地体现了他关于视觉再现的初步立场,我们可以看到,在其中后来极为著名的“看进”观在这时已经初具雏形。 沃尔海姆通过以下这个例子,例证了包括贡布里希在内的以往再现说的一个特征——即图像所具有的再现属性是让形象(figuration)或是图形成为另一物的再现,在这种“再现”观之下,观看者会忽略画布/媒介本身的存在: 假设年轻绘者们被要求将一个蓝色块点到一块白画布上,然后去观察这块蓝是如何陷到(似乎如此)白色后面的。在原有的例子所用的“放”的感觉和修改的例子当中给我们的“陷”的感觉,都以基本的形式告诉了我们将某物视为一种再现或者某物具有再现属性的观念。照此而论,如果我们准备接受艺术品不能是物理对象的观点,因为它们具有再现属性,那么,看上去好像我们就会接受这样的引导,将陷在白后面的蓝看做是某种具有刺激本质的东西,从而否定了画布的物理性。(沃尔海姆16-17) 当画家看到蓝陷入白背后之时,他是看不见画布本身(即书中所说的物理对象)的。或者说,从例证中艺术家绘画的目标来看,他们希望作品在观者眼中能产生上述效果。在这样的眼光下,图像的再现属性与画布的物理属性不可能相容,沃尔海姆这里所针对的是贡布里希的错觉说所陷入的误区——在著名的鸭兔图中,在把那个形象仅看作是鸭(或兔)的头部,却没有丝毫视觉辨识上困惑的那一阶段,观看者是意识不到画布本身的形式特征的,因为一旦意识到这一点,观看者就会困惑于那究竟是鸭还是兔。 在批评上述“再现”说的情况下,沃尔海姆坚持视觉再现经验的特殊性在于:看见作品之再现内容,以及看见作品之媒介及其形式特征——即“一方是在画布上把看到的色块看成是陷在画布后面,另一方则坚持放到画布上的两个色块都是物理对象”(沃尔海姆17)——这两种视觉注意力并不彼此冲突。沃尔海姆在这里发现了观看行为本身的特殊性,并将同时看到这二者的观看称之为“再现性观看”(representational seeing),这也就是他所说的“看似”(seeing-as)是再现的依据。不过,沃尔海姆在《艺术及其对象》中有关“再现性观看”的说明是比较简略与含混的,他此时并没有明确在理论上提出视觉经验的双重注意力这一见解,因而,“再现性观看”尚处于提出问题而未及详察的阶段。而且,他这时也还不曾明确地将视线转到观看者,尤其是艺术家作为观看者的特殊立场之上。 关键性的转变发生在第二阶段,即以《看似、看进与图像再现》一文为代表的阶段。从术语的变化上说,沃尔海姆此时多采用“观看适于再现”一语来代替“再现性观看”。其表述上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在于,“观看适于再现”一语更适于指宽泛意义上的视觉经验形式,而不必绑定观看再现性绘画时的视觉经验。而在我看来,这种改变将原本的名词式表述变化为一种关系项的表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视觉再现实现过程中,艺术家视觉经验与观看者视觉经验之间的潜在关系。当然沃尔海姆最为明确地指出他视觉再现的考察中心是观看者经验,并把艺术家列入观看者之列,这则发生在《绘画作为一种艺术》之中。 其次,在《看似、看进与图像再现》及之后的文章中,沃尔海姆颇强调一个与“观看适于再现”有关的概念,即“适当经验”。该概念与他在这一阶段所提出的另一核心观点“看进”相呼应,也涉及对于视觉经验的两个层面上的理解,即上文我所提到的艺术家意图及外在文化惯例规范视觉经验的一面;以及视知觉自身所具备的先天知觉能力的那一面。 第一,就艺术家意图这一方面而言,沃尔海姆一般视之为观看重要的、但未必是必须的参照物。在《看似、看进与图像再现》中,他指出了“正确标准”的问题,“使观看适于再现唯一的东西就在于:对其正确标准的适用,而这种标准就来自于再现制造者的意图:我们通常称再现制造者为‘艺术家’”(沃尔海姆173)。这里首先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意图”指什么?他在《绘画作为一种艺术》中将意图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从广义上说,意图包含了欲望、思想、信念、经验、情感等这些心理层面,以及绘画传统与相关知识等外在内容;而从狭义上讲,意图则是指艺术家创作之时的心中所想(Wollheim “Painting” 8)。对于此二者,从沃尔海姆对适当经验的理解来看,他是兼而取之的。同时也需要注意的是,当沃尔海姆提出“正确标准”时,他所指的是一类特殊的视知觉与意图之间的关系,也即,是只与审美与艺术有关。 相应的,沃尔海姆在之后的《论图像再现》中则提出了视觉再现最低限度的“适当经验”(appropriate experience)以及“恰当的观者”(suitable spectator。)的概念,在他的说明中,观看者从外部语境中所获取的艺术家意图等相关信息对于建构其“适当经验”来说显然是重要的: (一)如果一幅画再现了某物,那么就会有一种关于那幅画的视觉经验,这一经验决定了它这么做。我称这一经验为一幅画的“适当经验”。(二)如果一个恰当的观者看着一幅画,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将有适当的经验。 恰当的观者是一个有着合适的敏感性、具备恰当的信息、如果必要的话,还被恰当地唤起的观看者。敏感性和信息必须包括对所再现之物的一种识别上的技巧。“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是指,除了观看条件外,观者还必须获得针对手头任务的所有资格。至于“恰当地唤起”,它意在预先阻止一种可能的疏忽,并压制所有过于一般的前见。(Wollheim “On Pictorial” 217)从这一角度来看,无论是“标准”还是“适当”都意味着视觉再现中的视知觉的筛选性。这种筛选的标准的构成成分与意图一样极为丰富,即需具备足够的知觉能力与充分的知识储备。 第二,“适当经验”所强调的另一面则与上一点恰恰相反。沃尔海姆尽管在多篇文章中提及艺术家意图的重要性,甚至有些时候,艺术家意图还是他讨论观者之看的出发点,但他从未被此限制过,对观者之看的讨论总是越出艺术家意图的视野,而回到看的视知觉本身,尤其是视知觉自身所包含的先天知觉能力的那一面。 在1976年所提出的“观看适于再现”中,我们可以留意到这一特征。在看一幅再现性画像时,观者的视知觉能力相对于艺术家意图便起到了一种非常独特而更为重要的作用,沃尔海姆认为这才是根本性的。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视觉再现依赖于观看本身而非通过刻意了解艺术家意图来实现,即使是对于“恰当的观者”也是如此。 很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当某个正确标准适用于“观看适于再现”之时,为了看到某一适宜的再现,[……]在观看这幅图像所再现的东西的时候,他并不需要通过首先意识到(现在或曾经的)艺术家的意图来做到这一点。相反,他可以(艺术史家常常这样做)从他真实观看的方式中推出观看再现的正确方式,或者他可以从图像里所可见的东西中来重构艺术家的意图,而且,对一位拥有了相关技巧和信息并具有理性自信的观者来说,这完全是合法的。(沃尔海姆175)他的这一想法更为清晰的陈述是在《论图像再现》中,对于一个可能缺乏特定识别技巧与适当经验的观者来说,他可以通过观看本身,并通过图像再现对他的视觉激发来获得这种经验与技巧。具体来说,也就是通过观看再现性图像,在“视觉上意识到事物或那种事物的经验”(Wollheim “On Pictorial” 219)。并且,“视觉上意识到”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惯例性的,沃尔海姆将之视为对图像再现起决定作用的经验,因而他再现的视知觉包含了很大的直接知觉的成分。正因此,沃尔海姆反对惯例说或符号再现论对观看再现行为中对知觉方面的否定态度。当符号再现理论假设,如果不掌握规则与技巧就无法把握再现时,这种对惯例系统与符号系统的过分关注会令观者远离知觉。比如一位观者可能因某些信息或惯例而“知道”再现性图像再现了什么,但他其实并没有在画中“看”到。 在我看来,沃尔海姆通过“适当经验”所提出的这第二层面的特征对于他的视觉再现理论是尤其重要的。因为它彰显了沃尔海姆对视觉再现之本质的根本立场:“再现是知觉的(Representation is perceptual)”,这是他在1998年《论图像再现》一文中的结语。或者,我们也能在他在提出“观看适于再现”时所指出的“一种更广泛的知觉类别”一语中体味一二,沃尔海姆借此充分地传达了他对再现中视知觉类型的理解。 因而,所谓的“适当经验”首先要求人们的视觉拥有一种强大的直觉力(strong intuition)。在后期的《是什么令再现性绘画真正可见?》中,沃尔海姆承认,他对“适当经验”的解释“太不恰当,太不敏感了,太用滥了”(Wollheim and Hopkins 132),这似乎一下子推翻了他早先的理解。但在我看来,这不如说是沃尔海姆对“适当经验”的进一步清晰化。“适当经验”在这篇文章中更为明确了其视知觉的特殊性质。沃尔海姆把“适当经验”重新划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的适当经验就是他所说的“看进”,他称之为实质性的经验;而广义的适当经验则称为结构性的经验,是指“通过我们在凝视再现之时,看到了什么,或更准确地说,正确地看到了什么”(Wollheim and Hopkins 132)。我们这里姑且不谈“看进”,而来看广义的适当经验,沃尔海姆又将之区分为一般层面与特殊层面,③无论是一般层面还是特殊层面,这种广义的适当经验都强调了一点:视觉再现得以实现的过程中,观者的(或是他们被再现性图像所触发的)视觉经验的绝对重要性及基础作用,就像沃尔海姆常说的那样,在再现中,“看”比惯例与知识更重要。在我看来,这广义的适当经验其实是对“最低限度的适当经验”更确切的表述。它表明了在再现问题中,沃尔海姆日益明确地关注于视知觉本身,关注于能够更好地研究这一视知觉属性的观者之看的这一问题。 在了解沃尔海姆的“观看适于再现”所彰显的上述三个特征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来思考他转向观者之看,并提出“适当经验”的用意何在。理解这一点便涉及到沃尔海姆对再现性图像的观看者的限定——这是一类特殊的观看者,是与艺术家在视觉经验上得以交流的观看者。在这一策略下,沃尔海略或许有意识地回避了一个问题,即观者之看的无限多元与偶然性,因为他实际讨论的是审美交流中的艺术家及观者的视觉经验。 就此而言,“观看适于再现”暗示着视觉再现问题中一种旨趣与目的的存在:视觉再现中的视觉交流何以可能?换而言之,一般不同时在场的观看者与艺术家,他们的视觉经验的交流何以可能,其基础何在?这一答案就暗藏在视觉再现的本质——知觉——中。在提出这一观点时,沃尔海姆预设了视觉经验交流的基础:即可以分享的人类普遍视觉能力。 有些心理因素来自于艺术家深层心理,某些因素在绘画历史与传统之外是不可想象的,但意识到以下这点很重要:如果那不是为了艺术家所持的某种更深远而又极重要的信念,没有什么因素能对艺术家的工作方式产生影响;没有什么因素可以导致他这么画而非那么画。这些信念与人们如何知觉绘画成果有关,而艺术家必须相信,当一个独特的意图在其作品中得到实现时,那么,一种拥有恰当知觉和恰当信息的观看者将会倾向于在揭示这一意图的绘画作品前具有经验。换而言之,一种更为夸张但又相当合理的方式是说,所有艺术,或者说至少是所有的伟大艺术,都假定了一种艺术家与受众都共享的普遍的人类本性[……](Wollheim “Painting” preface 8) 当阅读到《绘画作为一种艺术》序中的这段话时,我们或能理解:在考虑“观看适于再现”、“适当经验”的过程中,沃尔海姆为何会思考艺术家作为观者的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这是沃尔海姆思考视觉经验之交流可能性的最鲜明的一次尝试。从以上沃尔海姆对视知觉性质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复杂性:视知觉可谓是艺术传统、文化符号体系、个人深层心理等因素融汇而成的后果。但视觉再现最低限度也是最基本的先天知觉能力却使不在场的双方有交流的可能性。而沃尔海姆将艺术家视为观看者的立场就体现了这样的一种努力。 该立场最鲜明地展现在《绘画作为一种艺术》的第二章“观者看到了什么”中,沃尔海姆开篇便指出艺术家既是作品的创造者,也是观看者,而且其创造者的身份是建立在他身为观看者的立场之上的。因而,他把艺术家的创造过程总结为“既用眼画”又“为眼睛画”,也就是说,艺术家绘画是为了生产出观看者头脑中的特定经验,艺术家在看画中发现他作画的可能方式,以特定的方式去标记他的画布,以便观看者能看到艺术家想要再现的是什么,即让图像能被眼睛所接受(Wollheim “Painting” 44)。在此立场下,画家尽管是在绘画,但他通过图像分享愉悦、传达意义、并提供理解的目的其实更为依赖他作为观看者的身份。换言之,艺术家是依赖于他作为观看者的状态获得了视知觉的能力,其中之一便是“看进”的能力,这样他才能再现事物(Wolllleim “Painting” 44)。“结果再现的艺术家必须至少让自己做到这一点:以特定的方式来标记画布,以确保观看者不仅能识别,而且还能看进图画中,看到图画所要再现之对象。这一需求促使艺术家必须竭力凭借其知觉上的信念”(Wollheim “Painting” 52。)反言之,观者看画,如果他完全不顾图画所引发的视觉经验,传达的信息,那他的观看也与对图画的理解无关(Wollheim “Painting” 42)。就此而言,沃尔海姆所关心的再现的视觉经验便是一种交流的经验,这与著名的罗兰·巴特纯偶然性与个人性的视觉经验“刺点”(punctum)截然不同,而这种不同显然源自于他们在视觉经验及交流之可能性看法上的根本差异。 综上而言,无论是艺术家之眼还是观者之看,最终都汇聚到视知觉这个核心上来,并予以其不同于传统刺激—反应论模式下刻板的知觉涵义——即视知觉作为生理与文化互相渗透后的一个综合体。一方面所谓的“正确标准”在关注艺术家意图之时,提出了“恰当的观者”的要求,从而倡导了多少带有些惯例论色彩的文化阐释建议。但另一方面,这一理论却又从不会将自身简化至一种符号学问题,沃尔海姆看到了往往被忽视的另一面:“对绘画的审查,将从其自身处提取出理解它所必须的信息。这是一种自引导操作”(Wollheim “Paintings” 89)。在因个体、文化、社会、种族、性别、阶层等因素而广泛存在着种种差异的视觉经验中,这种视觉的“自引导操作”,也就是观看者自身所固有的“看”的能力,为视觉经验的可交流性提供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基础。就此而言,当沃尔海姆接过贡布里希的话题,从观者之看的角度来思考再现问题时,视觉经验的交流便包容了既多元又基础的可能性,这可以说是当代视觉再现及视觉研究中最为可贵的贡献之一。 注释: ①“看进”是沃尔海姆的再现理论中的另一核心概念,此处限于篇幅无法详细展开,将另设单篇论述。 ②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沃尔海姆在《看似、看进与图像再现》中强调“观看适于再现”,以澄清其“再现性观看”一语所可能带来的涵义上的含糊,但他在之后的文章中仍大都习惯采用“再现性观看”这一表述。“适于再现的观看是一种更广泛的知觉类别(perceptual genus),因为我使用了‘再现性观看’这个术语,我现在意识到这个术语容易造成混淆,但我还坚持使用它。”参见沃尔海姆:“看似、看进与图像再现”,刘悦迪译,《艺术及其对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73。 ③在一般层面上是指,当思考图画再现某物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时,其答案是由站在画之前所具有的经验的一般本质决定的。在特殊层面上,对于一幅画实际上再现了什么的问题,这是由这幅画所引发的经验的特殊内容决定的。See Wollheim and Hopkins."What Makes Representational Painting Truly Visual?" 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