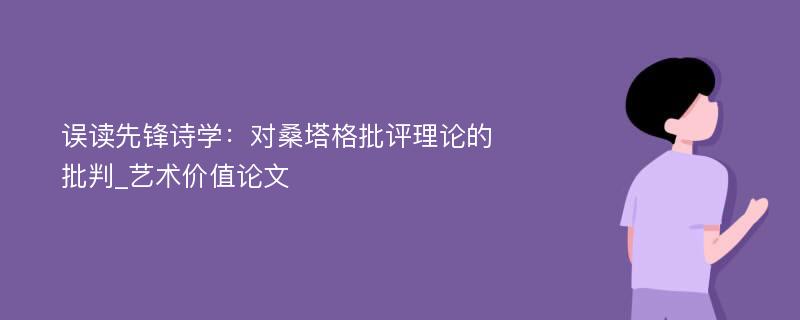
被误读的先锋诗学——桑塔格批评理论之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诗学论文,先锋论文,误读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11-0105-07
无论出自赞成还是反对,作为批评家的桑塔格都被当作20世纪60年代美国文化运动的标志性人物。的确,从《反对阐释》到《关于“坎普”的札记》,总是以一种“好战”姿态出现的桑塔格让人领教了她敏锐的艺术感知力。这种倚重掠轻、化怪异为神奇的勇力,以及隐匿了性别的傲慢文风,进而是她“改进世界”的冲动和行动,都使这位在20世纪文化转型时曾颇受关注与争议的人物,成为先锋派诗学的突出代表。然而1996年,距《关于“坎普”的札记》发表32年之后,桑塔格却这样表白自己的困惑:这些(指她本人早期的)文章所表达的情趣判断或许已经成了主流。然而支持这些判断的价值观却仍然没有得到光大。① 她的困惑是当代社会关于艺术价值的困惑,更确切讲,是对于艺术理想因何被快速商业化的困惑。这使桑塔格成为理解当代先锋派批评的一个生动案例。通过对桑塔格诗学困惑的分析与梳理,能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更清楚地认识当代批评理论的贡献与局限及其对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
一
要说清桑塔格的困惑,首先要从她反对阐释开始。桑塔格提出反对阐释,其意在反对以理性主义为主导的艺术批评,绝不是不要意义,更不是拒斥思想。在《反对阐释》中,她明确表示她反对的不是“最广泛意义上的阐释”,不是尼采所说的“没有事实,只有阐释”意义上的阐释,不是作为理解的阐释。② 她觉得尼采这句话是正确的,只表明她承认“事物就是事物,而人只是人”③,但不表示她鼓吹人因此就放弃抵达事物本身的努力。她亦不反对尝试寻找一件艺术作品的某种意义的可能性,她反对的是某些艺术批评方式,尤其是当时以理性主义为主导样式的批评现状。
具体地说,桑塔格反对“一种阐明某种阐释符码、某些‘规则’的有意的心理行为”,反对从作品整体中抽取一系列因素,并将它们转换成预设好的“对等物”。更确切地讲,桑塔格着力反对的是以内容为指归的解读艺术品的做法,她认为,具有明确的内容指向性的意义会使艺术品失去了本来的面目,因而是对艺术品的伤害。桑塔格决意要将通常认为内在于艺术品的、能被概念化地予以归纳提取的思想内容抛出艺术品之外,让艺术品从这种内容中独立出来,进而摆脱历史、政治、道德等抽象观念对艺术的围困。她甚至认为,“艺术中另有一种深思熟虑的使用思想的方式:把思想当作感觉的刺激物。持这种立场,并不意味着这些艺术家希望摆脱思想。而是意味着,思想、包括道德思想,以一种新的方式被提出来。思想可以作为一种装饰、道具、感觉材料来起作用”④。
这种转换了功用的思想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将思想从道德层面转移到美学层面;第二,暗示艺术从文学主导的状况中跳脱出来,表达人类行为的最宽广的可能语境,至少是比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艺术所提供的语境更宽广的一种语境,并反对那种对世界进行道德化的做法。由此可见,桑塔格提倡“逃避阐释”,这是反对阐释的一个策略。她将诸种现代的乃至后现代的艺术流变,例如“戏仿”、“抽象艺术”、“装饰性艺术”以及“非艺术”都理解为对内容指向性阐释的有意识的逃避。
桑塔格心目中艺术的理想风格,乃是外表统一、明晰,来势快疾,所指直截了当,她用“透明”一词概括“艺术中最高、最具解放性的价值”,即体验事物本来的那种明晰。可见,桑塔格的确反对人类刻意给万物“设想出一种共有的深度”,这里的“深度”就是指诸多在艺术批评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和思想观念。桑塔格反对动用这些观念进行艺术批评,因为与用感性体验的复杂而深微的人性相比,文化和思想的观念就显得“太笼统,太抽象,也太巧于辞令”,太容易“转眼就化作警句格言”,太“易于迅速衰败了”。
因此,直指意义的内容说,或依仗文化思想观念的内容说,作为一种不恰当的理解艺术的方式,极易阻碍艺术对事物本身明晰的整体性的理解。不仅如此,好战的桑塔格批判以内容为中心任务的阐释是怯懦的和僵化的,在她看来,不仅是艺术,甚至我们的这个世界都“已足够贫瘠了,足够枯竭了”,反对“阐释”就是“去除对世界的一切复制”。她说,“阐释使艺术变得可被控制,变得顺从”,好像艺术在强大的“阐释”面前被迫沦为奴隶,而反对“阐释”就是将艺术作品从这种奴隶的境遇中解放出来。她从读者或批评者的角度提倡保持艺术批评的活力和创造力,并热切地赋予真正的批评以勇敢探索与挑战的姿态:既然“真正的艺术能使我们感到紧张不安”,这种不安是对意义暂时空无的不安,而真正的批评就是在对意义的焦虑中完成艺术的发现功能,即寻求作品显现的关于世界的某种可能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对阐释就成了一场战斗。这场战斗是针对保守的学院派的,如果具体到人,就是当时美国著名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这位当时纽约知识分子圈里的重要人物坚持认为,人文研究“需要一种既是历史的、又是政治的和道德的意识和活动”,批评家要“通过学术交锋,与他所处时代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政治和文化运动保持对立的关系,而在社会改进中起到他的作用”。⑤ 但在年轻的桑塔格看来,正是像特里林这样高踞象牙塔顶的教授们,以他们的“文化修养”和“内行人”的地位维护着传统的内容说在艺术批评中的主导作用,以“文化”的名义将艺术创作和批评束缚在对传统“修补翻新”的境况中。
这就是桑塔格诗学所体现的先锋性品格,这种批评理论与注重作品的思想内涵、强调艺术的伦理效果的传统批评的分庭抗礼显而易见。但因此而将之纳入奉行解构主义立场的后现代批评阵营却未必恰当,因为事实证明,桑塔格对特里林的不满并不是针对他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而是反对他作为一个批评家对艺术价值的理解。无论如何,艺术不能揣着什么“观念”去经营,它应该是具体的,是一堆数不清的动作和细节,是那些一直被认作“表面”的东西,是生命本身的表现。桑塔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引用柯克托的名言:“风格是灵魂。”如果说她的确接受一种“价值虚无”,那指的是固有的价值体系在生存论意义上的虚构性或存在论意义上的非自在性,她并不否定价值本身。
她愤怒地把尤内斯库作为向固有观念屈服的艺术家的例证,直截了当地说:“与布莱希特、热内和贝克特比起来,尤内斯库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一个次一等的剧作家。”其根本原因是尤内斯库拒绝把语言当作一种交流或自我表达的工具,这归根到底缘自他对生活的冷漠,甚至是对人类的厌恶,更不能容忍的是他又以文化诊断的时髦的陈词滥调来掩盖这种厌恶感。桑塔格认定尤内斯库很多时候都在扯淡,根本不愿勇敢而严肃地思考。在她看来,当尤内斯库说“我相信使我们彼此隔绝的东西只是社会本身,或者,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是政治本身而已”时,他只是在表达他的反智主义,而不是表达一种关于政治的立场。⑥
桑塔格如此严厉地批评尤内斯库,主要是因为这位戏剧家对思考这件事本身是冷漠、甚至厌恶,他仅仅复制了一些时髦的观念,又混乱地毫无节制地利用奇思异想出来的戏剧语言。不严肃的态度只能让他的戏剧成为“带有先锋派感受力色彩的消遣性”的剧作,这才是真正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的毒害是双方面的:一个旨在“利用”某个观念的作品恰恰会虚化这个观念,同时,这个作品也将因为无法指引探索某种可能性而丧失价值。桑塔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反对创作者或批评者让艺术去阐释思想的。她亦是在这个基调上,阐述个体趣味的等效与自由。
审美的自律是桑塔格反对阐释的理论潜台词。但她更希望每个个体,尤其是从事艺术的个体,真正将艺术视为一种探索的行动而不仅仅是一个答案。她预设了这样的命题:个体的就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她事实上仍然是在宏大叙事的模式里论证问题。不仅如此,她甚至向往艺术像在巫术胎里的状态,那时艺术作品就是正在做的事本身,没有人探问它说明了什么,更用不着艺术为自己作一番正当性辩护。
二
正是本着这个理想设定,桑塔格指出通往新意义的新路径,她用欧文·豪最先提出的“新感受力”来命名,并以理论与评论两种方式阐述她的新感受力理论。在桑塔格看来,新感受力首先表现为艺术手段对科技成果的吸纳。那些不同于文学书写方式的音乐、电影、舞蹈、建筑、绘画和雕塑,全都大量地、自然而然地、不觉尴尬地吸纳科学和技术的因素,这些艺术和实践是新感受力的核心所在。⑦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说桑塔格意欲打破艺术与科学的界限(尽管她认为两者分享同一种文化)是不甚妥当的,其实,她仅是指出新感受力作为感性的新形式的特征之一:物质性,或准确地讲,诉诸物质的形式感。
她在评论《马拉/萨德/阿尔托》时,很具体地阐述了新感受力的物质性。她不仅指出当代戏剧中舞台压倒了文本,还进一步直接将导演的艺术看作一种物质的艺术。在这种艺术中,导演要对付演员的身体、道具、灯光和音乐,这种不可穷尽的材料方面的创新性以及对感官的持续不断的关注,是对新感受力物质化特性的最好描述。她进而重申了在《反对阐释》中语焉不详的关于艺术要追求表面性的主张。她坚持观点是次要的,进而通过将思想本身作为一种和装饰、道具一样的感觉材料来解释“表面化”的含义。她认为,艺术中另有一种深思熟虑的使用思想的方式:把思想当作感觉的刺激物。持这种立场,并不意味着希望摆脱思想,而只是意味着,在名副其实的艺术作品中,思想(包括道德思想),以一种新的方式被提出来。但桑塔格并非仅将思想移到美学层面来表现它形式上的丰富性,她的目标是将思想置于本体论层面,即将思想作为某种具有丰富性的物质化的戏剧材料来对待。
桑塔格提出新感受力的第二大特质是非情感性,或情感的间接性。她坚持艺术体验与日常情感的间离,强调新感受力不是日常感受力的延续,而是对日常感受力的拓展,它们不在同一个层面上。桑塔格反对艺术感受诉诸心理体验。她指出,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那些超越了心理描绘的戏剧,并引用阿尔托的话:戏剧情节并非在社会的层面上展开。更不是在伦理和心理的层面上……这种让人物去谈论情感、激情、欲望和冲动这些具有一种严格心理顺序而且其中每一个词都将抵销无数示意动作的心理过程的顽固倾向……是戏剧失去其真正的存在理由的一个原因。⑧ 这个主张具有鲜明的超现实主义理论背景,作为一种推崇即兴的偶然的自发的创造,超现实主义主张戏剧是表演艺术,是动态效果。
如果说,桑塔格在通过反对阐释来表达对艺术以个性、偶然性拒斥概念与逻辑的主导地位的希望,那么,她同样通过间离日常情感呼吁新感受力,来引领自我从貌似安全的必然可知性世界疏离出来。因此,新感受力维护的美感是冷漠的,是由“与情感直接呈现的艺术相对立的那种反思的艺术”提供的。正是在反思性的艺术中,艺术作品的形式以突出的方式呈现出来。⑨ 至此,桑塔格反对内容指向性的阐释找到了具体的批评落脚点——新感受力是对形式的警觉。此警觉表现为材料与形式的意图交叉、错位,甚至相对、相反,因此新感受力要求的艺术形式常表现为反形式。比如,布莱希特将一个热的题材置于一个冷的框架中,而阿尔托用最极致疯狂的手法表现最冷静的思考。就效果而言,这是为了延宕情感的发生,并使行动保持神秘性,而这神秘性又正是超现实主义所推崇的,是人在审美中积极探索、不断克服焦虑之后获得情感最大化的源头,更是对古典悲剧效果最近似的实现。
但深入来看,桑塔格反对在审美过程中动用日常情感,而且最终她没有明确将审美体验指向情感,这是问题的关键,是她的审美理论被划入后现代文艺思潮的主要标志。在大框架上,她的确努力寻找新感受力背后的精神支撑,并试图建起二者的联系。具体地说,她要在物质性的感受力与精神性的人之间确立某种等效性,作为艺术让人重获完整性的一种表现。而她建议的方式是通过性和情的中间物——色欲。⑩ 完成这个论证,她分了两步。第一步,真正的艺术引导人体验均衡宁静的状态。她这样描述一部伟大的作品带给人的最终反应:“冷静的、宁静的、沉思的,神闲气定,超乎义愤和赞同之上。”当活跃的艺术体验最终归于平和安宁,这种艺术体验同时是一种疏离性体验。但问题是这个体验并不完全是情感的体验,确切地说,只是情绪的变化,仍然停留在物质层面。因此,桑塔格强调的审美体验的确包含回归本能的过程性因素,正是在此意义上,她接受马尔库塞将审美当作一种感性的低级机能,并将自由首先定义为肉体能量的释放性满足。但是,这种自我从世界疏离出来的平和安宁的身体体验并不是艺术独有的,它仍然带有鲜明的物质性和消费性。桑塔格也显然不满意马尔库塞对感性审美的这种理解,她并不认为感性只能是低级的,以放松为最终目的的。恰恰相反,从她的批评实践看,她赞美严肃、困难的现代艺术。特别是从《关于“坎普”的札记》的文思和措辞看,她几经周折,却执意将某些“腐朽的”趣味拔高到严肃的现代艺术范畴,一如她把某东西说成“有趣”,其最终目的是“暗示挑战旧的赞美秩序”。(11)
更为关键的第二步是,她在《论风格》中就反复强调艺术是意志的激发或振奋。这种支撑傲慢的新感受力的意志“藐视行动的后果和判断的后果”,即不说“美”或“善”,而只说“有趣”。在桑塔格看来,这种先锋派的不计后果的行动本色完成了从审美判断到生命自决的跨越,正是自由意志的体现。而这种自由意志因为能“刺激和加深我们对我们周遭无比广阔和全面、既无生命又充满活力的现实的感受”(12),而使我们重返现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鲜活的现实可以藐视关于美或丑的判断,甚至比政治、历史更深远。她在《不灭:为维克托·塞尔日辩护》的结尾,摒弃逻辑的书面语言这样写道:“勇敢……和淡漠……和感官愉悦……和活生生的人间……和怜悯,怜悯一切——所有这些,依然不灭。”(13)
这说明她清楚地意识到,艺术感受仅达到超脱的体验是不够的,事实上在她看来,感受是感情的外化,就像她同意“面具就是真理”一样,她认为诉诸感官的感受和它们激起的情感是同一样东西。桑塔格亦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以“艺术色情学”(erotics of art)取代艺术阐释学的。这样,从审美返回现实,桑塔格遵循了美即是善的原则,超越了先锋派诗学。也正因此,在随后到来的娱乐业时代里,她对先锋派新感受力的价值失效倍感困惑。
三
桑塔格的困惑是,她的新感受力理论中的物质性被商品化的流行文化大肆利用,成为注意力经济在文化中的最大卖点,进而,商业价值又将审美感受力背后的精神因素一并作为可复制的无差别的商品要素被物质性地外化了。无论是感受力的物质性要素,还是精神性要素,都失去了个体性依托和内心真正的自由,而这是桑塔格竭尽全力维护的艺术的最高价值。作为先锋派诗学的一个代表,桑塔格注定要领受时尚的祭礼,注定要目睹一个个更劣质的尤内斯库的出现,目睹每一次商品交换都是一个相同的陈旧故事的独特而单调的重复。(14) 那么,导致桑塔格在新感受力的物质性和精神性之间苦心经营的桥梁断裂的原因何在?最主要的原因是,她的审美理论有个强大的哲学及意识形态背景,这使她原本鲜活的审美主张因为打上太深的时代政治烙印而显得滞重。
首先,桑塔格的困惑有整个晚期现代性的大背景,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陆思想界对启蒙、对理性的反思。一方面,人类通过启蒙把自身“从一系列顶着‘神话’和‘自然’的幌子出现的强制性力量和限制中解放出来”(15);另一方面,事实证明理性并不能打消人对日常生活意识全然不透明的力量和过程作出恐惧和绝望的反应,相反,在以理性支撑的现代经济和管理社会里,个人的理性和判断力越来越衰退。当某些早已被启蒙证伪的假想的永恒实体或原则一旦被用来服务于现代的大规模操作,个人便失去了真实生命的最后一星火花,没有什么理智之途可以折回。(16) 这就是《启蒙辩证法》试图解释的,法西斯在民主高度发达的欧洲盛行的原因,也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审美主义兴起的一个理论准备:既然理性最终颠覆了自己,既然理性已被它自己认定无法在主体与物之间承担语境和中介的作用,(17) 那么,就让审美不仅成为对理性的修正,更作为人性尽善尽美的形态。
同样的逻辑也出现在马尔库塞的审美理论中。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的德国哲学家到了美国,用他的新弗洛伊德激进主义助推了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新文化运动。他的美学理论就是将艺术自由的前两层含义放到一个压迫与反抗的战斗性的叙事文本中,再用政治中的自由概念期待艺术自由的概念,将审美理论转换成一个具有讽喻性和乌托邦色彩的政治理论。诺埃尔·卡罗尔就批评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的审美理论将复杂的社会矛盾极端简化为感性和理性的戏剧性冲突,并一味夸大艺术以自由意志战胜现代理性社会的压迫是不恰当的(18)。这样做就把审美置于悖论的境地,即审美要以自律的姿态背负政治赋予的功能。关于这一点,韦尔施在《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中质疑了作为特殊体系的现代艺术怎样为整体获得意义的有效性。他明确指出,负担过重对于美学并没有好处,它给失效准备好了道路。(19) 而桑塔格的困惑正在于对“失效”的不解。
我们看到,在桑塔格的审美理论中,艺术自由分别被用于三个不同层面。其一,指艺术要自律,要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和空间,具体表现为趣味的自由。其二,指艺术让人体验自由的生命状态,但这个超脱的状态不表现为一种惰性,而是积极地面对生活。这两个层面的自由对应到康德的审美经验中分别表现为经验所支持的无利害的自由以及想象力和理解力不受概念支配。第三个层面可以涵盖前两个,指一种开放的态度,是深层的内心的自由。尽管第三个层面的艺术自由的意义是桑塔格所有审美理论的起点与归宿,但由于它的包容性削弱了战斗性,使得好战的桑塔格更愿意强调前两层意义。而更严重的是,在压抑与反抗的审美政治化模式的干扰下,内心的自由被外化为政治上的人的自由。
1965年,在《论风格》里,她为德国女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展示的“灵气、优美和感性的复杂动态”所震撼;与批评界以“纳粹美学”对这两部影片所作的定性不同,她坚持认为一个艺术作品可以扮演纯粹形式的角色。但九年之后写《迷人的法西斯主义》时,尽管她依然坚持这两部片子或许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纪录片,她却反感流行文化将里芬斯塔尔塑为一座文化丰碑,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背后推动力部分肯定是由于她是个女人的事实。为此她并不掩饰对大众文化的失望,明确表示:真实的情况是,在高雅文化中可以被接受的,到了大众文化里就不能被接受,只提出无关紧要的道德问题作为少数人的一种特质的那些趣味,一旦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便蜕变为一个让人腐败的因素。趣味是语境,而语境已经发生了变化。(20) 这里所说的趣味就是艺术自律观的集中体现。对于艺术自律的反驳,卡罗尔的评价言简意赅:“在受到交换价值和工具理性、利益动机和表演原则支配的资本主义和极权主义社会里,这种趣味通常无法实现。”(21) 桑塔格所指的“趣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生命意志里最轻盈敏捷的触角,这种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对批评家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它没法统摄生命意志的全部意义,它无法充分地体现艺术品格和关怀,因而它总表现得异常脆弱,不仅自己无形,还极易被利用。
然而,假如把桑塔格写《论风格》时的战斗意志考虑进去,我们就会发现,她所用的“趣味”一词里更包含艺术作为否定力量的意义和对人的自主的展望。“艺术和自由,恰似普罗米修斯的火,只能被偷来,用来反对现存秩序。”这是1946年毕加索不愿回电纽约现代美术馆支持“艺术自由”时说的一番话,他又进而说了以下的话:“要是有朝一日允许艺术畅行无阻,那是因为艺术已经被淡化,显得软弱无力,不值得为之奋斗了。”(22) 1965年的桑塔格显然全心领会着毕加索的前一句话,而1974年的桑塔格必定会为毕加索的后一句话动容,因为她确实看到了在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推动下,大众文化披着“现代艺术”的外衣“畅行无阻”,但永远失去了个体探索力量,开放的精神亦变成了犬儒的态度。
桑塔格接受席勒的艺术游戏说,希望艺术战胜“责任和天命的严肃认真”,从而使人在实现其生命主体时成为真正的人。但事实是,当代人的确告别了严肃和真诚,却依然没有自己。尤其令她愤懑的是,她曾经以某些特殊的“趣味”反对教益先行的批评原则,然而,当这些趣味通过大众媒体被流行文化作为时尚观念吸纳之后,却比她曾反对过的那些传统观念更快速地衰败,而她倡导的新感受力亦在娱乐的气氛中,摆脱不了《启蒙辩证法》早已批判的结局——成了技能而不再是创造力。于是,问题还是要回到艺术自由的含义上。理想的批评是让艺术品是其所是,也即让艺术得到充分的自由,这是艺术自律的目标。桑塔格显然支持这一点,并且认为自律的艺术必定是负责任的。
所以有这样的结论:“自由意味着责任。当人们认识到事物正是其所是的时候,他们便是自由的,也因而才是负责的。”(23) 显然,她写下这段话,就是将艺术的自由和人的自由放到一个因果链上,即通过艺术的自由来实现人的自由。并且,在她看来,两个自由同时实现这的确是理想状态,但事实上,艺术以审美的方式为人的“是其所是”提供一个实践的领域,这个领域是乌托邦性质的,无法大规模地现实化。因为,既然自由不能仅是不受限制意义上的自由,那么全然的自由就不是生命的常态,就像全然的压迫亦非常态一样。
尽管艺术要以复杂而深微的生活本身作底色,但真正的艺术亦非某个生活常态。“顽童”毕加索在1946年已足够老,不再为要求一个抽象的“自由”概念在他人(别的艺术家们)的生活里实现而站出来抗议,艺术自由归根到底只能代表个体内心的开放。因此,即便要为艺术而“战斗”,那也是一个人的战斗。桑塔格对当代艺术批评的价值,正在于她强调了艺术批评的个体性——艺术选择与判断的过程就体现了批评主体内心深处的自由,就是对各种事物真正的理解、好奇和容纳,这才是艺术滋养人的地方。
所以,桑塔格的诗学困惑不仅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具有普遍性,而且体现了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性转型的先锋派诗学的一种文化张力。人们在事过境迁之后进行思想盘点时,可以从中认真汲取一些有益的经验。先锋派诗学怀抱着将生活艺术化的革命理想,希望通过艺术的自由品质唤回人的自由精神。既然行动是情感的外化,那么艺术亦是一种行动。比之情感,行动与感受更亲近;比之创造,行动与复制、模仿更亲近。最后的情形是,懂得艺术(用艺术思维)并能享受艺术的人可能越来越多,甚至从事艺术事业的人可能越来越多,但是艺术创造却越来越少了。(24) 进而,在将艺术的个体价值泛化为普世价值的过程中,先锋诗学又因其感受力中的物质性元素,在主观和客观上为商业化操作提供了素材。正是在充分商业化的进程中,它被市场的各个环节蓄意甚至恶意地误读,生活艺术化的理想被艺术生活化的事实取代。
但是,作为一个批评家,桑塔格始终是一个倾听自己内心真实感受的人,她的困惑最终由她自己的艺术批评实践得到解答。当她对记者说,“没有‘主义’,弥赛亚不会降临”(25) 时,她坚持作家要有立场;当她面对波兰作家访问团,不忍听那被仇恨情绪歪曲的言论,说“我们美国人也是孤立的”(26) 时,她强调哪怕是最正义的立场都不能作为说昧心话的借口。她想当然地要求听众和她一样分清正义和真理的区别,她的想当然是因为她相信人尚能被艺术滋养,尚能体验幸福的感觉,这是她与当今那些欢欣雀跃地宣布“终结”的诸位后现代论者的最大不同,亦是她备遭误解却又一再被人真诚地谈起的原因。
然而即便如此,桑塔格诗学里的先锋派特质依然构成当今现实世界里“某种较好、要求较高的标准”。这个标准的第一条就是行动。如果桑塔格作为一个已然逝去的当代西方知识分子对别处亦冠以此称谓的人群有所裨益的话,那么她的意义主要不在于她说了什么,而在于她如何是、如何成为一个作家。在她的批评生涯里,“行动”意味着永远基于“个人的”自我超越,意味着去体验那“令人激动不安的”美,去讲出真相,去捍卫自由的现代性。对于今天仍在现代性之路中艰难探索的中国文论界来说,桑塔格诗学思想的这种品质所具有的参照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桑塔格诗学思想所确立的第二条标准是现实感。从1964年的《反对阐释》到2002年的《关于美的辩论》,桑塔格始终致力于探索从美学返回现实的路径。她说:“从一生深刻而漫长地接触美学所获得的智慧,是不能被任何其他种类的严肃性所复制的。”(27) 因为美带来的智慧无外“多元”二字,而这个“多元”必须在直面充满诸多无法克服的互相矛盾的现实之时才真正配得上“智慧”这顶桂冠,才能一举剥去那些篡夺性的口号式的大概念的伪装,露出它们反人类的本质,才真正注释了“生命之树长青”的意义。对于今天越来越热衷于自说自话地高谈阔论的中国文论界,桑塔格的这种精神尤其让人回味。
注释:
① [美]桑塔格:《三十年之后……》,见《重点所在》,第325页,陶洁、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② [美]桑塔格:《反对阐释》,见《反对阐释》,第6页,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本文第一部分未注引文皆引自该文。
③ [法]罗伯·格里耶:《快照集 为了一种新小说》,第118页,李奇志、余中先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
④ [美]桑塔格:《马拉/萨德/阿尔托》,见《反对阐释》,第198页。
⑤ [美]迈克尔·赫尔方:《伊甸园之门》“序言”,第3页,方晓光译,见[美]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⑥ [美]桑塔格:《尤内斯库》,见《反对阐释》,第139、140页。
⑦ [美]桑塔格:《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见《反对阐释》,第346页。
⑧ [美]桑塔格:《马拉/萨德/阿尔托》,见《反对阐释》,第195页。
⑨ [美]桑塔格:《罗内尔·布勒松电影中的宗教风格》,见《反对阐释》,第208页。
⑩ 参见[英]R.W.费夫尔:《西方文化的终结》,第169页,丁万江、曾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11)(12) [美]桑塔格:《关于美的辩论》,见《同时:随笔与演说》,第7、11页,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13) [美]桑塔格:《不灭:为维克托·塞尔日辩护》,见《同时:随笔与演说》,第89页。
(14) [英]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第322页,王杰等译,柏敬泽校,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5)(17) [美]劳伦斯·卡洪:《现代性的困境——哲学、文化和反文化》,第296、293、295页,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6)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反对自己的理性:对启蒙运动的一些评价》,见《启蒙运动与现代性》,第373页,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8) [美]诺埃尔·卡罗尔:《超越美学》,第87页,李媛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9) [德]沃尔夫冈·韦尔施:《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第131页,洪天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0) [美]桑塔格:《迷人的法西斯主义》,见《在土星标志下》,第97—98页,姚君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1) [美]诺埃尔·卡罗尔:《超越美学》,第82页。
(22) [法]弗朗索瓦兹·吉洛、卡尔顿·莱克:《巨匠与情人》,第211页,周仲安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23) [美]桑塔格:《戈达尔的〈随心所欲〉》,见《反对阐释》,第239页。
(24) [英]R.W.费夫尔:《西方文化的终结》,第128页。
(25)(26) Sohnya Sayre,Susan Sontag:The Elegaic Modernist,p.1,p.19,Chapman and Hall,Inc.1990.
(27) [美]桑塔格:《关于美的辩论》,见《同时:随笔与演说》,第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