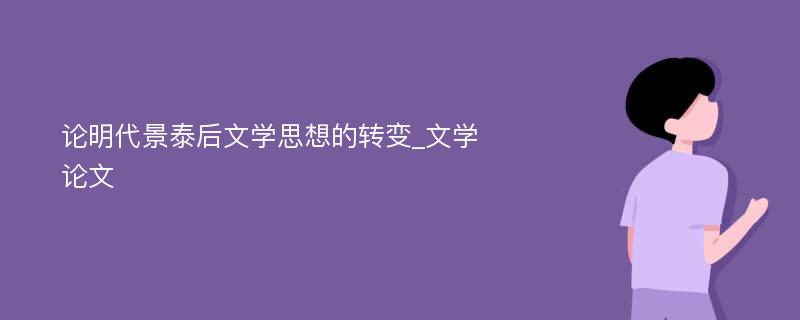
论明代景泰之后文学思想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景泰论文,明代论文,思想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0-0104-11
论明代文学与文学思想者,以台阁体文学为有明文学思潮之始。其后或接以李东阳,将之视为弘治后期兴起的复古文学思潮之先导;或接以李东阳,而将之视为一独立流派,即所谓茶陵派者①; 或直接接之以前七子的复古思潮,而将台阁文学思潮至前七子复古思潮的百馀年间,看作台阁文学思潮发展的三个阶段。自台阁文学思潮全盛之永乐朝,至弘治后期复古思潮的兴起,文学思想潮流究有何种变化,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提出,在台阁文学思潮全盛之后,有一个文学思想缓慢转变的过程。从景泰至成化末、弘治初的四十馀年间,存在着一个文学思潮的过渡期。这一过渡期时段的设定,自上限言,是景泰之前台阁文学思潮的主要人物已离开文坛。自下限言,是这一过渡期的一大批作者如李贤、岳正、柯潜、韩雍、卞荣到成化末已先后离世;少数活到弘治初的作者,如张宁、王越、陈献章都已到晚年,文学观念并无明显的变化。弘治八年(1495),李东阳领袖文坛②,开始了文学思想发展的又一个段落。
一
景泰后文学思想转变之一重要表现,是台阁文学思潮失去了它生存的条件,与它的领导核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我们都知道,台阁文学思潮产生之基础,是政权的力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皇帝的意旨。早在这一思潮奠基的洪武朝,它就与政权密不可分。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制礼作乐,严格等级关系;以程、朱理学一统思想,强化思想管制。以统一的思想标准选拔人才,如规定标准的《五经》注疏本为教学与科举考试的依据;又命刘三吾删去《孟子》中不利于皇权绝对权威者共八十五章,重编为《孟子节文》,以之为录取人才之思想标准。他亲自撰写《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颁示全民,每户一本,人人读,且作为学校课本。此一种之思想统制,在历史上亦属罕见。对于士人之政策,则是既用又压。一方面,他善用人才,礼聘名士,与廷臣诗酒倡和,营造君臣和睦之气氛。今存他与廷臣倡和的诗就有三十三首之多。同时他又残酷杀害稍有过失或不为所用的士人,如高启、王彝、陶凯、李仕鲁等的被杀,宋濂、刘基的死于非命等等。严格的思想管制与对待士人既用又压的政策,以及士人有限的生存空间,就是明初文学思想发展的环境。朱元璋还亲自整顿文风,前后七次诏谕文风改革,甚至动用刑罚,廷杖文辞繁琐的大臣。他主张文章要实用,文辞要平实,反对骈丽,反对繁辞;要尊典谟、崇古训。他通过政策导引和日常言行,规范了文学走向。在政权力量的干预下,自然也便形成了颂美、追求平和雅正、表现雍容典则开国气象的文学思想主流。洪武朝此种文学思想,事实上已为永乐之后台阁体文学思潮的全盛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永乐朝在政权上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巩固,大一统的思想文化环境也随之进一步强化。朱棣一登帝位,就严令遵太祖之旧制,“礼乐制度,咸有陈规”。永乐三年(1405)他对将到文渊阁读书的新科进士说:“然当立志远大,不可安于小成,为学必造道德之微,必具体用之全;为文必驱驰班、马、韩、欧之间。如此立志,日进不已,未有不成者。”[1](卷三十八,P643) 他已经给为文定下了班、马、韩、欧的偶像。此类偶像,特别是欧阳修,后来一直成为台阁体作家推崇的对象。永乐十八年,时为太子、后来的仁宗皇帝朱高炽过滁州,登琅琊山,访醉翁亭,对随行的杨士奇谈了他对欧阳修的崇敬之情。《明太宗实录》称:“盖皇太子为文章尤善修,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独修有雍容和平气象;尤爱其奏议切直,尝命刊修文以赐群臣,且谕之曰:‘修之贤非止于文,卿等当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1](卷二百三十,P2231) 黄瑜《双槐岁钞》也说:“仁庙潜心经学,礼重宫寮,文仿欧阳,诗尚《选》体。宣庙承之,天资颖异,制作如《广寒殿记》之类,虽巨儒莫及,诗歌词理尤纯粹。”[2](P63) 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皇帝都极其喜欢欧阳修,看重其忠君之心与其文风的雍容和平气象。永乐一朝,编《四书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进一步强化程、朱理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大规模编纂《永乐大典》,不仅丰富了文化积累,也培养了一大批文化精英。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的皇帝,也都跟朱元璋一样,喜欢作诗,常与廷臣倡和。当然,从他们现存的诗作看,那水准实在不敢恭维。但是自其导向言,则似不应忽视。这三朝,可以说是有明皇权统治的极盛时期。国力的强盛、思想的一统、文化的繁荣,给台阁文学思潮的高度发展准备好了一切条件。这时,以杨士奇、杨荣、杨溥、胡广、金幼孜、黄淮等为代表的一批台阁重臣,便出来引领文坛,形成台阁文学极盛的局面。台阁文学思潮的核心,是正统儒家的文学观,主张传圣人之道与鸣国家之盛,提倡典则雅正、和平温厚的文风,强调服务于政权。我们以往研究古代文学思想,不注意朝廷的文化政策,不注意皇帝的文学观念,而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台阁文学思潮从奠基到极盛,就是一个显例。这一思潮产生的重要基础,就是皇帝个人的意愿与政权的力量。而此一思潮之得以推行,则有赖于台阁重臣如三杨们所形成的领导核心。
台阁文学思潮的兴起与政权有密切的关系,而其衰落,亦与政权关系甚大。政局巨变,思潮的核心人物退出文坛,继任的台阁重臣台阁文学观淡化,为此一思潮衰落之主因。
台阁文学思潮的主要人物胡广死于永乐十六年(1418),金幼孜死于宣德六年(1431),黄淮死于正统十四年(1449),作为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台阁重臣、也是台阁文学思潮灵魂人物的三杨,于正统五年(1440)、九年(1444)、十一年(1446)相继去世。三杨与黄淮,虽然活到正统朝,而他们的影响已减弱,他们事实上已相继退出文坛。此时的政治局面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统六年宦官王振开始弄权。三杨死后,大权完全落到王振手里。正统十四年,在王振的耸动下,正统皇帝朱祁镇亲征瓦刺,兵败土木堡,全军覆没,二十四岁的朱祁镇被瓦刺俘虏。皇帝被俘,国之大辱。之后郕王继位,是为景泰。景泰一朝,政局安危与皇位更替带来种种的矛盾,使皇帝无暇亦无心顾及文事。且景泰皇帝不久又荒于女色,甚至召妓女入宫。而大臣则“皆全躯保位,无报国忠”。[3](卷三,P75、P72) 景泰皇帝在位才七年,数年前已从瓦剌放回的朱祁镇于景泰七年复辟,是为天顺。皇位的争夺开始了大规模的报复,景泰朝的重要阁臣商輅、萧鎡被除名为民,江渊被谪戌,王文与于谦被杀,朝政震荡。成化朝又是宦官汪直专权,廷臣多依附于他的门下,“堂堂翰林,相率拜内竖之门”。[3](卷四,P99) “当是时,朝多秕政,四方灾伤日告。”[4](卷一百六十八,P4524) “成化秕政多,一坏于汪直,再坏于李孜省,传奉满朝,贪谀成风。”[3](卷四,P103) 廷臣党分南北,进退任情,相互争斗。当时的重要阁臣万安、刘吉、彭华、尹直人品都不好,“阁老乃为内臣轻鄙,时事可知”,万安还向皇帝进房中术。“惟万、刘蟠踞凡二十年,至弘治始罢。揆地浊秽莫甚此时。”[3](卷四,95) 景泰、天顺、成化三朝君臣之间,已不再像永乐、洪熙、宣德三朝那样和谐相处,也不再谈文论艺。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已失去台阁文学思潮赖以生存的基础:已经不是颂美、“鸣国家之盛”的环境了。
与政局变化同步,重要阁臣亦失去对台阁文学思潮的影响力。景泰、天顺、成化三朝,入阁预机务者十九人。他们中有的虽仍持台阁文学观念,但既无新意,创作上亦无甚成就,不具备文坛盟主之资质,如陈循、商輅、彭时、萧鎡、刘定之。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人看作台阁文学思潮之馀响。此种馀响,亦文学思潮过渡期之一特征。他们有的人,人品差,为朝臣所轻鄙,文亦无可言者,如万安、刘吉、陈文、彭华、尹直、徐有贞。有的没有文集或者有文集而没有传世,如王文、江渊、许彬、王一宁。薛瑄入阁不足四个月,他以理学名世,诗虽写得不错,但属邵雍体,与台阁体异趣。值得注意的是李贤、岳正、刘珝和虽未入阁预机务而为翰林学士、掌院事的柯潜,他们的文学思想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他们的文学观念,渐渐地从台阁文学思想中淡化了出来,从重功利转向重性情趣味上来。在他们身上,出现了文学思想转变的迹象。
李贤(1408—1466)是天顺、成化两朝入阁预机务的重臣。他在为杨溥的文集作序时虽然也还提到文章的政教之用,提到文章的台阁气象,但是,他在《行稿序》中,却特别地提到诗的性情趣味:
诗为儒者末事,先儒尝有是言矣。然非诗无以吟咏性情,发挥兴趣。诗于儒者似又不可无也。而学之者用功甚难,必专心致志,于数十年之后,庶几有成。其成也,也不过对偶亲切,声律稳熟而已。若乎辞意俱到,句法浑成,造乎平易自然之地,则又系乎人之才焉。[5](卷七,行稿序)
这段话有几层意思。一是“诗为儒者末事”。这是先儒之言。二是他认为要吟咏性情与发挥兴趣,还需要诗。在这一点上,他没有强调诗的政教之用。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也反映在此后诗歌题材的选择上。三是诗必须做到辞意俱到、句法浑成,达到平易自然的境界。这第三点,就关系到诗的艺术特质问题了。在《跋赵子昂书陆士衡〈文赋〉》中,他特别从艺术的角度肯定了《文赋》的价值所在:
文章虽为末技,不专心致志则不得其妙。观陆士衡《文赋》一篇,虽曰形容才士作文之趣,实写其平生肆力文章之功,非望空想像亿度而为之也。其用心之劳可知矣。虽然,圣贤之文则异于是,何也?有是理则有是文,无是文则是理有缺,苟有所作,不为无用之空言;况摅发胸中所蕴,一气流通,如风行水上自成文耳。所谓有德者必有言,非末技也。末技云者,词章之文,士衡所赋是也。然造其妙者亦寡矣。若士衡者,顾岂可少也哉
在这里他说了三个问题。一是说,《文赋》是陆机的创作经验之谈,非凭空想像之说。我们都知道《文赋》谈的是一系列的创作问题:物感、想象、灵感、构思、语言的表达力、写作技巧等等,是文学自觉意识的出现、文学创作长期艺术经验积累之后的产物。它强调的是文学的艺术特质,与功利说是完全不同的。二是说,圣贤之文与《文赋》所说的不同,不同就在圣贤之文是理与文一气流通,是一体的。虽说有德者必有言,但如果没有文,理就无从表达,文同样很重要。三是他把圣贤之文与词章之士之文分开来了。先儒说文章是末技,李贤认为,末技做得好也不容易,因之陆机《文赋》自有其价值,不可少。
显然,在李贤的观念中,功利说淡化了。他开始重视文学的艺术特点了。
岳正(1418—1472)也曾入阁预机务,他也有儒家先道后文的传统观念,但是,他的文学思想中,更多地带进了庄子的重自然、重性情自然流露的思想。他所理解的此种自然流露的性情,与杨士奇们所追求的“性情之正”的性情,已经不同了。他在《九日感怀诗序》中说:
人之于忧乐,有可已者,有不可已者。可已者以人,非忧乐之真也;不可已者以天,忧乐之真也。[6](卷四)
“以人”,是说人为的忧乐,非出于本性之真。他解释说:“嗟乎,世之人未尝无忧乐也,穷则慽慽于贫贱;达则衍衍于富贵,所以为忧乐者,率以人也。”人的自然本性为物欲所遮蔽,所忧所乐,皆出于人为,而非自然纯净之本心。而所谓“天”,则是指性之本然。此一种之思想,实来自庄子。③ 岳正认为,只有出于自然之本性,没有外在的束缚,才会有真性情的表达。此种出于本然之性的忧乐之情的发泄,才会是不可已已的。岳正这篇序,是为陈缉熙写的。他说陈缉熙的感怀诗“感时序之易流,叹年龄之将迈,抑郁懣结之怀,其能已乎!是故风木势变而死者勿作,可忧也;时命方蹇而生者勿显,可忧也;鹡鸰载分而兄弟勿守,可忧也;摽梅云实而伉儷勿时,可忧也。忧于心,宣于声音,成于言辞,畅于节奏而为歌诗,亦固宜矣。”[6](卷四,九日感怀诗序) 为生死亲情而忧而乐,为人生际遇而忧而乐,皆人性不可抑止之本然,故不可以已已。天顺中他左迁钦州同知,在诗作中就流露出了感伤失落的情思,如《夜雨呈同志》:“雨中灯火夜堂深,无限闲愁损客心。献玉不逢经双刖,屠龙学得破千金。生逢邓禹应相笑,老学南阳祗漫吟。满目风尘双短鬓,为谁萧索不胜簪。”[6](卷二) 岳正在创作中反映出来更多的是个人内心的感喟。他的万物相感相生、万物一体的思想,更多的是庄子的影响,而非程、朱理学的路数。
成化十一年入阁预机务的刘珝(1416—1490)也有片断类于台阁文学观的论述,但多无新意。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反对复古。在《马先生文集序》中他说:
文岂易言哉!弗遭其时弗文也,弗养其气弗文也,弗克其学弗文也。粤自造书契以来,世有升降而文与之俱。宋不唐,唐不汉,汉不春秋战国,春秋战国不三代唐虞,如老者不可复少,势不得然也。[7]
他是从论气与论世开始的,世不同且人异气,则文自然不同,故不可能回到古代。在趣味上,他崇尚平淡自然,而非台阁体的雅正典则。
柯潜(1423—1473)在理论表述上崇尚台阁文学观,而在创作实践上反映的却是纯情的文学思想倾向。他的诗作不多,但大体皆深情细腻。他的两首《无题·和义山》,是这方面的例子:“翠袖湘裾立晓风,绛纱窗外画阑东。伤心玉笛声初断,回首瑶台信未通。满地淡烟芳草碧,一簾残雨落花红。年来但守芳心在,两鬓从教似短蓬。”“人在蓬莱欲见难,重门花落又春残。惊回远梦莺犹语,题就长箴砚已干。云母屏前香缕细,水晶簾外雨声寒。箧中旧制双纨扇,愁拂尘埃强自看。”④ 或者因为是和诗,故有义山之哀艳细腻,但他其他的一些诗作,也有与此类似的情调,如《闺情》二首、《三月晦日作》、《棠梨白头》、《睡起》等等,红情绿意,深情微婉。另外的一些诗,则写得清新流利,嘉靖时的康大和论柯潜诗,称:“其为诗冲淡清婉,不落畦径,庶几登陶、谢、王、孟之堂。”[8] 他的诗歌创作倾向,与他所提倡的敦厚和平典则雅正之音的理论,与台阁文学思想观念显然是不同了。
台阁文学思潮的基础是政权的支持,景泰后此种支持已不复存在。台阁文学的生存环境是盛世,景泰后环境亦已发生巨变,已无可颂美之太平景象。台阁文学思潮的领导核心是台阁重臣,景泰后的台阁重臣,有的虽仍有台阁文学观念,但已失去影响力;有的台阁文学观已经淡化,文学思想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倾向。台阁文学思潮的领导核心已不复存在,这一思潮的衰落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
文学思潮更重要的变化反映在创作实践中。这时的大多数士人,已经没有了前辈台阁作者三杨们那样对于朝政的热情。他们虽亦在官任职,但心态已经与朝廷有了这样那样的隔膜。他们的吟咏,也便从鸣国家之盛转向了个人喜怒哀乐、个人得失、一己感悟的发泄,转向了私人生活情趣的抒写。他们有的在论及文学时,虽亦提倡崇圣宗经,但着眼点则在独抒个人情怀。他们的创作倾向,已然是不知不觉地发生不可否认的变化了。
张宁(1426—1498?)是此一时段留下文论较多的一位。他论文杂取政教文学观与独抒情怀的观点,但他的创作则极重抒情。他曾出使朝鲜,沿途写了不少诗。他说所见景物,“其间留连悲啸之情,盖有出于吊古询风之外者,虽余亦既知之矣。然兴发成章,政自不能不尔也”。[9](卷十三,登太平馆楼六十韵) 留连悲啸之情,既已逸出吊古询风之外,自己亦知此种之感情非身为使者所应有,而情之所发,却不能自已。他似乎极重视悲苦之音。他说:“气满志得者,虽有所著,多不能胜寒微之士。彼交于物也深,则其达于天也必浅。理趣之妙,固非贪荣乐富者所能与也。”[9](卷二十,冰蘖稿跋) 这段话值得注意的是交于物深而达于天必浅和理趣之妙两处。交于物深而达于天必浅,就是庄子所说的嗜欲深者天机浅,意谓若摆脱利欲之纠缠,则可达到与道泯一之境界。此一种之人生境界,是非功利的。在《物外心诗文卷序》中,张宁也有类似的言说。他提到“富贵若大梦,功名撚指间,吾何以此而挠吾心哉!恒当遨游于湖山风月,托兴于书画文字,寄跻于斯而不泥于斯,人知之嚣嚣,人不知亦嚣嚣,世上事与我了不相涉,物外期可久也云尔而已”。[9](卷十四) 这说明庄子的物不撄心的思想已经对他产生了影响。这与他的台阁前辈严守程、朱理学的人生理念,已经大异其趣了。而此种思想正是他非功利诗歌创作的基础。他所说的理趣之妙,自创作之思想渊源说,来自宋人之诗歌理念。而从他在其他地方的论述看,则此一“理趣”,似更近于宋人严羽所说的“兴趣”。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的“兴趣”,是指“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一种诗歌境界,强调的是诗的艺术的特质。与理趣说相联系,在《西湖百咏诗序》中,张宁也提到了诗的言外之趣。他说:“然善作者,言多隐约微婉,非因辞逆志,体事得情,茫然声韵之末,终无以达其本旨。”[9](卷十七) 这同样是从诗的艺术要求上说的。此种诗歌理念,与台阁体文学观的强调政教目的,侧重点是很不同的。他的创作实践与上述他对于诗的理解相一致。他存诗1176首,其中题画诗482首,八景诗(写八景诗为此时之时髦)103首,寄、赠、酬、送别诗110首,其馀695首为倡和、登临、感悟、寿丧贺挽等作。他的古体诗写得很好,如《记事》、《送刘廷信兄归闽》、《癸卯寓杭,戏写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图,潦草,为婢子所笑,因题与女玉祥收为刘氏清话》、《诗送友人刘宗大》诸作,娓娓而言,流易生动,与台阁体的典则雅正情调完全不同。他的不少诗,常有一缕淡淡愁情,如《夜行舟中闻笛》:“白露青枫夜色寒,何人吹笛向江干?风廻浦溆滩声合,月落关山客梦残。金殿几时闻旧吹,画楼何处倚危栏。天涯早已难为听,况复怀人泪不干。”[9](卷九) 《除夕风雨,卧病郡斋》:“萧萧风雨到闲廷,愁病相兼酒易醒。身外功名何潦倒,眼前儿女尚伶仃。清霜客鬓随年白,芳草云山入梦青。底事夜深眠不得,自烧银烛看医经。”[9](卷九) 有些诗写日常生活甚至入于香艳,完全背离了台阁体的最基本的观念。《舟中与徐文海叙旧,追赋旧事三首。词虽婉媚,意实经常,总不能效丽则之言,然亦非香奁体也》之一、二:“龙髻盘云翠作翘,绣鞋尖小束轻绡。鳞鸿附託芳心许,弟妹传呼小字娇。彩凤竟分萧史伴,黄花瘦减易安腰。无端却忆朱簾下,手劈云香待月烧。”“曾将玉杵捣玄霜,红叶无情逝水长。明镜已孤鸾凤影,罗衣空染蕙兰香。东风梦觉空凝涕,秋月诗成欲断肠。唯有谢家兄弟在,时时相见一凄凉。”[9](卷九) 所谓“总不能效丽则之言”,意谓此种曾经有过之香艳往事,实无法用典雅之言辞表达。他自辩说非香奁体,其实这个辩说是不能成立的,从用词到意象,与香奁体并无区别。写这类诗的还有丘吉等人。拿这类诗与台阁诗人的作品比,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二者的差别。创作倾向是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了。
此一时段另一位独抒个人情怀,诗写得很好的人是王越。王越(1426—1498)以儒官拜将。虽然他一生征战边陲,但他从不正面写征战。他写边塞生活的诗也不多,且涉及边塞生活时,亦少写边塞生活之风貌,而以传达一己之感觉情思为主。他存诗656首,⑤ 其中涉及国家、朝廷的诗作是少数,其馀多为登临、咏怀、感悟人生之作。有的诗写得很重情,如《新秋写怀寄定襄》二首之一:“西风黄叶又经秋,浪迹何时得暂休!万里胡天双倦翼,十年宦海一虚舟。炎凉世态谁青眼,辛苦人生自白头。赢得双肩吟骨瘦,天教收拾杜陵愁。”[10](卷上,怀友) 把边塞生活写得如此的无奈与失落,“倦翼”言已经疲惫不堪,“虚舟”言仕途之难以预料。一位屡建战功的将领,何以有如此之失落与感喟,这或者与他私交宦官汪直而受到指责有关。汪直当时权倾朝野,王越与其有所来往,但亦并未助其为孽。在复杂的政局中,人际交往的复杂性远非后人所能想象。正直与邪恶、是与非,亦远非判然划线所能解决。王越还是一位较为正直的人,竟因与汪直的交往而备受指责,史臣曾为此发为感慨。这也是他在许多诗中发牢骚的原因。他写世事的无奈:“既然如此且如此,无可奈何将奈何?只好醉翻双老眼,看人平地起风波。”写对人世险恶的感慨:“自古论交重读书,于今翻为读书迷。既推下井还投石,才送登楼便去梯。”翻为读书迷,迷,迷误,意谓误信书上道德仁义之言说,现实并非如书上之所言。现实是人心险不可测。他眼中的社会,已非盛世。对于这个社会,他已无颂美之心。他只有失望与伤感,有一种对于人生的感悟,如:“已知世事只如此,借问古人安在哉!”“将来世事应难料,已往年光竟不同。”“莫把青灯照歌舞,五侯亭馆半丘墟。”⑥ 有时他也在诗中表现了超脱的人生态度:“爱饮村醪懒赋诗,此中真趣有谁知?教成白鹤如人舞,买箇黄牛当马骑。池草涧边春意足,衔云洞口夕阳迟。吟成独坐空庭久,正是纱窗月上时。”[10](卷上,自咏) 他有一些小诗,写得有如南宋杨万里辈的诗那样清新小巧,那样的富于生活小情趣,如:“一箇小茅亭,人间境自清。巧云涵画意,幽鸟做诗声。”“结茅如斗大,终日自徘徊。窗破蝇钻入,门虚犬撞开。”[10](卷上,小亭杂咏五首之三、四) 一位惯于沙场征战的将领,何以对人生有如此的失望与落寞的心境,除了上面提到的因与汪直交往而备受指责、因而气愤不平之外,这背后的因由也仍然与政局有关。 “土木之变”的阴影,一直存留在这位将领的心头。直至天顺八年(1464),那是朱祁镇已复辟的八年之后,王越还为此事感伤不已。这年正月朱祁镇死,秋天,王越登上古云中城楼,写下了《登云中城角楼次古人韵》二首,当时他正以副都御史巡抚大同,面对发生过耻辱事变的边关发为感慨:“都将十五年前泪,洒落桑乾水共流。”十五年前,就是正统十四年,是皇帝朱祁镇被瓦剌俘虏的国之大辱的年份。在这首诗里,他说“青山不管兴亡事,白日长含天地愁”,说“谁有雄才能破虏”,说“谁是先忧范仲淹”。在他的心中,朝廷之上,已经没有人为国分忧,没有人能为国尽力了。这使他有无限的伤感,在潇潇暮雨中沉浸于对朝政失望的心绪中。[10](卷上) 一位有名的将领,有如此的心态,并非仅仅是他个人性格与个人遭际的问题,说到底还是整个的政局所形成的一种环境、一种氛围、一种普遍的心态的影响。
同是名将而且诗也写得很好的郭登(?—1472),面对其时的局势,也有类似的心态,如《暮春登大同西北城楼同仰寺丞瞻潘御史洪赋》:“满地飞花春已阑,溪风山雨更生寒。浮云蔽日终难散,腐柱檠天恐未安。西北兵戈犹扰扰,东南民庶半凋残。先朝遗老惭无补,独对西风把泪弹。”[11](P2337) 王越登楼是“土木之变”的十五年后;郭登登楼是“土木之变”的当年,那时他正以都督佥事充参将守大同。皇帝被俘之后,瓦剌曾带着这位被俘的皇帝来到大同城下,要叫开城门。守城的正是郭登,他负国重任,拒绝开门,但内心却有一种强烈的失望与彷徨。对于朝廷中奸侫误国的不满,对自己无力回天的不安,“腐柱檠天”之喻,就是这无力回天的心境的流露。在郭登的诗里,有时对朝政的不满还表现得十分激烈。五古长篇《枭》[11](P2330) 借对枭的凶残和上帝的纵容影射朝廷的是非不分。此种不满,也反映在他的咏物诗里,如《蝇》:“眇形才脱粪中胎,鼓翅摇头可恶哉!苦不自量何种类,玉阶金殿也飞来。”[11](P2344) 此诗作于郭登谪戌甘肃时,讽刺的可能是借着朱祁镇复辟而祸乱朝政的石亨辈。《棋》:“看来总是争闲气,笑杀旁观袖手人。”[11](P2342) 讽刺的也还是天顺复辟之后朱祁镇不问是非,杀戮、更换大批朝臣;朝臣中又明争暗斗,不从国家安危着想。他所说的“争闲气”指此。从谪所放还,他对当时的政局,仍然失望,而且带着深沉的伤感,如《保定城中偶成》:“寒窗儿女灯前泪,客路风霜万里家。……独醒空和骚人咏,满耳斜阳噪暮鸦。”[11](P2339) 我们把王越、郭登上述诗的情调拿来与台阁体作者同类诗相比,就能看到此时在创作倾向上的变化。台阁体的代表人物杨溥《东征》诗:“搀枪耀齐分,龙御勤六师。出门驰马去,不暇告妻儿。亲友送我行,欲语难为辞。死生岂不恤,国事身以之。”[11](P2186) 金幼孜《早发禽胡山》:“六师严号令,车骑肃前征。塞云月中暗,胡尘雨后清。沙鸡随箭落,野马近人惊。咫尺闻天语,常依御辇行。”[11](P2189) 同样写边塞,杨溥们的诗表现的是壮大、信心。他们的诗写得并不好,但是情调却是明朗的。他们强调的是要表现“性情之正”。这个“性情之正”,就礼乐说,是有节。最早是《礼记·乐记》的有关论述。后来程明道与朱熹,对此都有引说。“性情之正”也被引申到心性的存养上来。永乐朝编写的《性理大全》,也提到性情之正。此一种之思想,正是其时推行程、朱理学以规范士人思想之一要求,亦台阁体作者抒情之一准则。台阁体重要作者于此都有所论。杨士奇论杜甫,就说杜诗之所以好,是“一由于性情之正”。[12] 杨荣与杨士奇他们在东郭草亭宴饮赋诗,他提到此次倡和之诗,表现的是性情之正。而此种性情之正,是为了使人识见盛世之气象:“意之所适,言之不足而咏歌之,皆发乎性情之正,足已使后之人识盛世之气象者,顾不在是欤?”[13] 金幼孜也有这方面的论述,他说:“大抵诗发乎情,止乎礼义。古之人于吟咏必皆本于性情之正。”[14] 台阁文学思潮之重要人物视性情之正为诗歌抒情之一准则。这个准则与修身去欲、情而有节,与鸣国家之盛是一体的。而景泰之后的四十馀年间上引柯潜、张宁、王越、郭登们的诗,则既没有表现盛世之气象,感情的抒发或悲慨、或牢骚不平,亦并非发而有节之情。他们的抒情特点,已经有违于性情之正的准则。诗歌的创作倾向是不知不觉地变化了。
三
景泰后文学思想的转变,还与思想领域的变化有关。此时思想领域的重要变化,是儒学中出现了由理学向心学发展的一支。被视为由程、朱理学向阳明心学发展中间环节的白沙心学的出现,打破了程、朱理学在思想领域一统的局面。这不仅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也影响着文学思想、文学创作倾向的变化。
白沙心学对文学思想的影响,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由理入心,由外在言说而入于心灵,归于本真,在创作中表现真性情。而在审美趣味上,则是由典则雅正而转为纯任自然的明净之美。
陈献章(1428—1500)是主张通过个人的修持而至圣的。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白沙学案”中说:“故有明儒者,不失其矩矱者亦多有之,而作圣之功,至先生而始明,至文成而始大。”[15](P79) 献章论由修持而至圣人:“夫人之去圣人也,远矣。其可望以至圣人者,亦在乎修之而已。”[16](重修梧州学记,P79) 他所说的修持,就是修心:“天道至无心,比其著于两间者,千怪万状,不复有可及。至巧矣,然皆一元之所为。圣道至无意,比其形于功业者,神妙莫测,不复有可加。亦至巧矣,然皆一心之所致。心乎,其此一元之所舍乎!”[16](仁术论,P57) 天道无心,是说天道自然而然运行,非有意为之。圣人无意,是说圣人顺自然之道,无意于改变之。而心止于一,“一”就是无欲。“一者,无欲也。”[16](《复赵提学佥宪》三,P147) 道在心中,心中所存止的道,就是本然之道,无欲之道。要体认此一存于心中的本然之道,就要去欲。去欲要通过静坐悟入。他说:“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方有商量处。”[16](《与絮克恭黄门》二,P133) 他说他二十七岁从吴与弼学,读古圣贤之书,但不知从何处入手。直到回白沙,终日静坐,“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涣然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兹乎!’”[16](《复赵提学佥宪》一,P145) 他通过静坐呈露的心之体,是本真,是随处体认得来的天理。悟得此心,处事也便皆合于圣人之道。
但是,他通过静坐所悟入的这个圣人之道,其实有着相当多的庄子思想的成分。他在送张廷实的序中,赞许张廷实说:“盖廷实之学,以自然为宗,以忘己为大,以无欲为至,即心观妙,以揆圣人之用。”[16](送张进士廷实还京序,P12) 去欲,是儒家思想修持的要点;以自然为宗,忘我,则是庄子的思想。在庄子那里,我既忘我,于万事万物无所系心,也就不存在欲的问题。在与贺克恭的信中,他也提到修持的最高境界就是物我两忘:“接人接物,不可拣择殊甚,贤愚善恶,一切要包他。到得物我两忘,浑然天地气象,方始是成就处。”[16](《与贺克恭黄门》十首之十,P135) 他崇尚自然之道,说:“宇宙内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动自静,自阖自闢,自舒自卷;甲不问乙供,乙不待甲赐;牛自为牛,马自为马;感于此,应于彼,发乎迩,见乎远。故得之者,天地与顺,日月与明,鬼神与福,万民与诚,百世与名,而无一物奸于其间。”[14](与林时矩,P242) 天地万物,都顺其自然,不要人为地干预它。这正是庄子的自然之道。我们在陈献章的诗里,可以找到大量关于这方面思想的描述,如《观物》:“一痕春水一条烟,化化生生各自然。七尺形躯非我有,两间寒暑任推迁。”[16](P683) 万物自然运行,我与万物为一体,我亦非我。又如《题庄子泉》:“闲看千丈雪,飞下玉台山。争知白沙子,不是南华仙!”[16](P540) 我既非我,彼亦非彼,则我亦是彼。这正是《庄子·齐物论》所说的“物无非彼,物无非是”之意。又《饮酒》二首之二:“君莫停杯我为歌,我今忘我是谁何。”[16](P471) 亦此意。我既非我,我已忘我,则我本为虚。道也是虚。《赠陈頀湛雨》二首之一:“君若问鸢鱼,鸢鱼体本虚。我拈言外意,六籍亦无书。”[16](P524) 《示诸生》二首之一:“无我无人无古今,天机何处不堪寻。风霆示教皆吾性,汗马收功正此心。水火鼎中非玉液,鸳鸯谱里失金针。道人欲向诸君说,只恐诸君信未深。”[16](P494) 我既与万物为一,则我与万物皆泯于一,故言“无我无人无古今”。风霆示教,原是儒家的传统说法,意指天地无私,化生万物,圣人则之,以之为教。此处却渗入庄子与物泯一的思想,以风霆示教为己之性,意指我既已泯一于大化之中,则物性亦我性。我于诸君,亦当以道之本然为教。我之修心亦如是,悟入于本然之性,则法本无法。我于诸君,亦无金针可度。诸君也只有悟入自得。与道为一,与万物为一体,是他的思想的核心。《对竹》二首之二:“窗外竹青青,窗间人独坐。究竟竹与人,原来无两个。”[16](P516) 以万物为一体,性之本然本无任何之系累,无任何之干扰,《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三则上曰:“天地之大,且不我逃,而我不增损,则举天地间物既归于我,而不足增损于我矣。天下之物尽在我而不足以增损我,故卒然遇之而不惊,无故失之而不介。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烈风雷雨而弗迷,尚何铢轩冕尘金玉之足言哉!”[16](P55) 这就是庄子所说的“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意思。我便是无所系念的本然之我。凡所言说,皆我的本然之心。在《送李世卿还嘉鱼序》中,他说与世卿在白沙:“朝夕与论名理。凡天地间耳目所闻见,古今上下载籍所存,无所不语。所未语者,此心通塞往来之机,生生化化之妙,非见闻所及,将以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非敢有爱于言也。时时呼酒与世卿投壶共饮,必期于醉。醉则赋诗,或世卿唱,予和之;或予唱而世卿和之,积凡百馀篇。其言皆本于性情之真,非有意于世俗之赞毁。”[16](P16) 本于性情之真,是指不受外物干扰的自然的真性情。这也是他的诗文创作的理念。在《夕惕斋诗集后序》中他说:
受朴于天,弗凿以人;禀和于生,弗淫以智。故七情之发,发而为诗,虽匹夫匹妇,胸中自有全经。此《风》、《雅》之渊源也。而诗家者流,衿奇眩能,迷失本真,乃至旬锻月炼,以求知于世,尚可谓之诗乎?[16](P11)。
此一思想甚有价值,是说诗不是做出来的,是情有所动,不得不发的产物。此一种之情,指人性自然禀赋之七情,是“受朴于天”的本真之情。他反对迷失本真,反对人伪。人伪是巧智伤真,自诗而言,是只注重技巧。他认为只落在技巧工夫上,于诗有害:“诗之工,诗之衰也。……率吾情盎然出之,无适不可。”[16](认真子诗集序,P5) 从此一基本思想出发,他在评论诗歌发展史时,甚至有极端的说法:
魏晋以降,古诗变为近体,作者莫盛于唐。然已恨其拘声律、工对偶,穷年卒岁,为江山草木、云烟鱼鸟粉饰文貌,盖亦无补于世焉。若李、杜者,雄峙其间,号称大家,然语其至则未也。[16](夕惕斋诗集后序,P11)
他之所以认为李、杜尚且未至,是轻其“技”。在《与王乐用佥宪》中,他也有类似的论述:
夫诗之盛莫如唐,然而世之大儒君子类以技目之,而不屑效焉,则所谓诗之至者,果何人哉?仆于此道,未尝一得其门户。寻常间闻人说诗,辄屏息退听,不敢置一语可否。问其孰为工与拙,罔然莫知也。比岁闻南京有庄孔旸者,能自树立,于辞不一雷同今人语,心窃喜之。稍就而问焉,果出奇无穷。及退取陶、谢、少陵诸大家之诗学之,或得其意而亡其辞,或得其辞而遗其意,或并辞意而失之。盖其所谓夙生晕血,终欠一洗之力,而又惧其见讥于大儒君子。终所谓技,不可旷岁月于无用,故绝意不为。凡学于仆者,亦以是语之,而无有疑焉者矣。[16](P154)
庄孔旸就是庄昶。他的诗与陈献章的诗当时被称为“陈庄体”,以其创作倾向相似之故。在这里献章说庄昶能自树立,不与人同。说自己受到庄昶诗论的启发,以之衡量陶、谢、杜诗。他说他未能理解陶、谢、杜诗之好处,乃知“技”之无用,故绝意不在“技”上下工夫。
不重视技而重视感情的自然发抒。他反复论述诗之本体是情:“若论道理,随人深浅,但须笔下发得精神,可一唱三叹,闻者便自鼓舞,方是到也。须将道理就自己性情上发出,不可作议论说去,离了诗之本体,便是宋头巾气也。”[16](次王半山韵诗跋,P72) 他重诗之感情自然抒发,同时主张诗应该有韵味,辞气应该自然。在《与汪提举》中,他提出了风韵问题:“大抵论诗当论性情,论性情先论风韵,无风韵则无诗矣。今之言诗者异于是,篇章成即谓之诗,风韵不知,甚可笑也。情性好,风韵自好;性情不真,亦难强说,幸相与勉之。”[16](P203) “性情好”,就是指本真的自然秉赋之性情。任受之于天的真性情自然呈露,也就能有好的风韵。所谓好的风韵,就是表现在诗中的诗人的气象。他所追求的是物我两忘、浑然一体的天地气象,是一种平和的胸襟韵味。所说的论诗先论风韵,从风韵看性情,也就是从诗中所呈现的诗人胸襟气韵,看其性情之真假。重诗的感情特征,重神韵,重自然的特点,也就与宋人严羽的诗学主张有了相通之处。他接受了严羽的“诗有别材”说,和严羽一样,他对于诗的理解,也重在妙悟。这悟入说,与他修持的静坐说是相通的。
与他的诗歌主张相联系,他在创作上追求一种自然的明净的境界。自诗中所表现的情思言,是平静悠然,所谓“百感交集而不动”。[15](P78) 不动,是诗情兴发感动之后复归于平静,由此种平静之心境自然说出,有时是心中幻象,有时是一种直感,毫无雕琢痕迹。由直感而生心象的,可用他的一首诗来形容这类诗境形成的过程:“江云欲变三秋色,江雨初交十日秋。凉夜一蓑摇艇去,满身明月大江流。”[16](《偶得示诸生》二首之二,P631) 外物之不断变化,心必有所感,而我于外界此种不断之变化中,自思得之,所感复归于平静,“凉夜一蓑摇艇去”,我自回归于无所系念之我,于是有所悟入,展现“满身明月大江流”的境界。这满身明月、大江,就是我有所感之后生发的心中幻象,是一个澄明的心境的影像。又如《睡起》:“天地蜉蝣共始终,十年痴卧一无穷。道人试画无穷看,月在西岩日在东。”[16](P612) 十年修持悟道,“无穷”指谓道。“痴卧”者,谓本在道中而不觉,睡起忽有所悟:道就在日升月落中。道无形,日升月落就是道之象,道在万物之中。
他的大多数诗,则是直感,没有任何的尘杂干扰,有所感即直接说出。这些诗表现的是他超脱世俗的平淡自然的情趣。陈献章存诗2030首,⑦ 表现的多是此种境界。《题闲叟》:“前村烟火熟朝炊,正是先生睡足时。身带江山人在画,目穷今古世争棋。花边击鼓诸孙戏,竹下扶筇一鹤随。应笑书生闲未得,白头忧世欲何为!”[16](P413) 《舫子》:“此身天地一虚舟,何处江山不自由。六十一来南海上,买船吹笛共儿谋。”[16](P588) 《偶成》:“墙角经春卧短筇,千秋塔骨不如公。科头坐转茅簷日,闲看蛛丝荡午风。”[16](P546) 《春中杂兴》三首之二:“小雨如丝落晚风,东君无计驻残红。野人不是伤春客,春在野人杯酒中。”[16](567) 《赠张叔亨侍御》:“天下原无事,劳劳我有心。相携沙上语,山月二更深。”[16](P515) 昔人论白沙诗,称其脱略凡近,意谓其境界之脱俗。也有人称其诗自《击壤》来。白沙诗因其由理入心,心中原有所悟,将此所悟直接说出,也就有似理语,或从此一点,以之比同于《击壤》。其实,白沙诗与《击壤》是不同的。这不同,就在于其中有情趣。朱彝尊说“然白沙虽宗《击壤》,源出柴桑”,[17](P182) 正是看到了白沙诗的自然情趣。
陈献章创作倾向的意义,就在于从感情上与朝政疏离,从而将文学完全带离了政教附庸的地位。这不仅完全背离台阁文学思潮之基本要求,且也深刻而内在地影响了晚明文学思想的发展。正如他的哲学思想是阳明心学的先声一样,他的文学观念、创作倾向,也可以看作晚明重个人情趣的文学思潮的先声。他的文学观念与晚明文学思潮的联系,亦从心学之发展开始。既然受朴于天,回归本真便是题中应有之义。回归本真之一开放点,存在着重自我、重个性之通道,感情观也就存在着七情本有之解读空间。此一点后来王阳明有进一步之表述:“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认得良知明白。……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谓之欲,俱为良知之蔽。”[18](P111) 良知为性之本然,七情流行俱是良知之用,只是不要“有所着”,“有所着”便是欲。何者为“着”,何者为“不着”,他并没有明确的度之界定,因之也就失去约束的意义。而且,既认七情为性之本然,也就为任情而行留下了可能。白沙与阳明在七情问题上留下之此一模糊空间,到了晚明,便被完全放开,无所约束,走向纵欲了。⑧ 此种思潮反映到文学上,就是求真,重情。没有偶像,不尊唐,不尊宋,不尊汉魏六朝;亦喜唐,亦喜宋,亦喜汉魏六朝,自己喜欢就是好,不喜欢就不好。 “各任其性耳。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19](P193) 一切以情之真假为依归。晚明重情思潮之产生,原因固甚复杂,但回归自我,把文学带离政教之用的路径,却不能不说与前此的回归真情说有关,尤其是白沙所主张的受朴于天的性之本然之情。当然,白沙所理解的性之本然之情是去欲的纯净之情,是明净心境的产物。而晚明重情思潮所表现的情,却复杂得多,既有纯情,亦有纯欲,亦有情欲一体者。但同样回归性之本然,在此一点上与陈献章、王阳明是一脉相承的。
四
台阁文学思潮的全盛,推动的主要力量是政权。景泰之后,文学思想开始转变,也与政局有关。“土木之变”以后,台阁文学思潮已经失去它的政治基础。台阁重臣的台阁文学观已经淡化,这一思潮的领导核心也已失去他们作为领袖的影响力。创作实践中出现了新的倾向,从鸣国家之盛转向了私人生活情趣的抒写。更为重要的是白沙心学的出现,打破了程、朱理学一统的局面,由理入心,追求心灵的本真,在文学创作中表现真性情,在审美情趣上由典则雅正转向纯任自然的明净的美。文学思想的这一转变,说明台阁文学思潮已经退出主流地位,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
这是文学思潮发展的一个过渡期。台阁文学思潮退出主流,下一个大的文学思潮即复古思潮还没有到来。这一过渡期有如下特点。
一是思想的衔接。文学思想的演变是缓慢过程的渐变,而不是突变。在这个过程中,台阁文学思潮并没有立刻消亡,它的存在虽然已非主流,但也还存留在有的人身上,直到成化后期,也仍然有秉持台阁文学观念者,如丘濬等。台阁文学思潮的一些观念,遗存的时间就更长,不惟如前述景泰后四十馀年间李贤、岳正、刘珝、柯潜们身上有,下一时段的李东阳、程敏政、邵宝们也还有。虽然在他们身上,表现的程度深浅不尽相同,但承传却是明显的。这些存留下来的观念,大多是儒家传统文学观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如政教之用、表现性情之正等等。
一是新的文学观念的开启。作为过渡期,既有台阁文学观的承传,也有新观念的出现。这四十馀年间最为重要的新观念的开启,就是重性情的文学观特别是陈白沙的文学观的出现。重情文学观衔接后来的重情说。下一时段的李东阳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说人不能无所动情,情动则必有所发抒,于是有诗,说情之发动不可止。白沙主情之自然流露,反技巧,东阳亦谓以法模拟,必失天真兴趣,“求其流出肺腑,卓尔有立者,指不能一再屈也”。[20](P531、534) 后来的复古派也提出重情说,虽然他们由重情而走向复古。抒发真情是从我,复古是从他,从抒发真情到模仿古人,初心与路径背反。这正是复古派的悲剧。不论后人如何为之辩说,在文学的历史长河上,他们的创作并无大的成就,已然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他们之提出回归真情,却是台阁体思潮的必然反拨,是景泰开始的重情说的自然发展。
此一时期既有台阁文学思想的遗存,又有新观念的出现。交叉错落,没有形成有系统的新的理论主张,没有共同追求的新的文学创作倾向。它只是两个大的文学思潮之间的一种过渡。它之后是李东阳,再之后才是前七子掀起的复古思潮。它只是文学思想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但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注释:
① 最早提出茶陵派者为四库馆臣。在顾清《东江家藏集》提要中说:“其诗清新婉丽,天趣盎然;文章简炼醇雅,自娴法律。……在茶陵一派之中,亦挺然翘楚矣。”在黄佐《泰泉集》提要中说黄佐“然在茶陵宗派消歇之馀,七子议论方兴之会,独能力追正始,不失雅音,犹为不惑于歧趋者焉”。有的地方,虽未明言何人属茶陵派,但可作茶陵派理解者,如在石珤《熊峰集》提要中说“路诗文皆平正通达,具有茶陵之体”,在郑岳《山斋文集》提要中说郑岳“犹恪守茶陵之矩度”,在吴宽《瓠翁家藏集》提要中说宽“以之羽翼茶陵,实如骖之有靳”。此数处所说“茶陵”,可理解为指东阳个人,也可理解为指茶陵派。陈田《明诗纪事》承其说,如论邵宝,称:“在茶陵诗派中,不失为第二流。”然亦有持不同看法者,如朱彝尊《明诗综》论石珤,就说:“近见东南文士,有推少保诗为北方之冠者,又或谓得长沙之指授。俱未尽然。其诗颇类明初江西一派。”他引陈卧子论李东阳:“文正网罗群彦,导扬流风,如帝释天,人虽无预宗派,实为法门所贵。”意谓东阳在当时之地位,有如帝释天之尊严,然相从者亦无预于宗派。在东阳周围,是否存在一个茶陵诗派,应该从文学观念、创作倾向和各人在当时不同时段之影响诸方面考虑。此一问题远较想象为复杂。
② 李东阳在翰林修撰和翰林侍讲期间,虽在交往中颇富文名,但是他的影响的扩大,是在成化二十二年(1486)为顺天府乡试考官之后。而真正成为文坛领袖,则是弘治八年他入阁预机务之后。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提及此一点时说:“李东阳当国时,其门生满朝,西涯又喜延纳奖拔,故门生或罢朝或散衙后,即群集其家,讲艺谈文,通日彻夜,率岁中以为常。”后人把李东阳看作成化文坛的领袖,是不确的。
③ 《庄子》卷六《秋水》:“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 (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90页)这是说,万物处于自然的状态,不要去干涉它、改变它,这就是“天”;岳正数次提及庄子,可证他接受庄的思想影响,与三杨们是不同了。
④ 原诗四首,今存二首,见《竹岩集》补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存世的《黎阳王太傅诗文集》存诗474首,《黎阳王襄敏公疏议诗文辑略》存诗476首,去其重复,共得诗656首。
⑥ 依次为《结屋》、《怀友》、《辞朝归》、《榆林灯下独酌》、《李汉章东山书屋》,均见《黎阳王太傅诗文集》卷上。
⑦ 李明君又从地方文献中辑出“逸诗”52首(见其刊于广东文史馆《岭南文史》2006年3期之《陈白沙诗辑逸》)但此52首中,有17首已收在《陈献章集》中,李先生失检。所谓逸诗,有的只是题目不同,如《题画》,《集》作《题和靖画》;《弘治二年冬子长命书是目应之》二首之二,《集》作《梅花》;《阅周溪图赠刘肃庵主》六首之一、二、三、五,《集》作《阅周溪图作,赠刘景林归呈尊甫翁肃庵程乡令》,之四、六,《集》作《东白张先生借予藤蓑不还,戏之》;《与华山范规小酌》,《集》作《是夕范生小酌》;《舟泊金洲》,《集》作《金洲石》;《访山家》,《集》作《访山家次韵》;《寄题吴处士黄冈书屋次湛民泽韵》,《集》作《寄题小圆冈书屋和民泽韵》;《赠蔡亨嘉还饶平》,《集》作《次韵世卿赠蔡亨嘉还饶平》;《游峡山》,《集》作《石门次林缉熙韵》。
⑧ 此一问题之内在理路远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我在拙著《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已有论述,此处不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