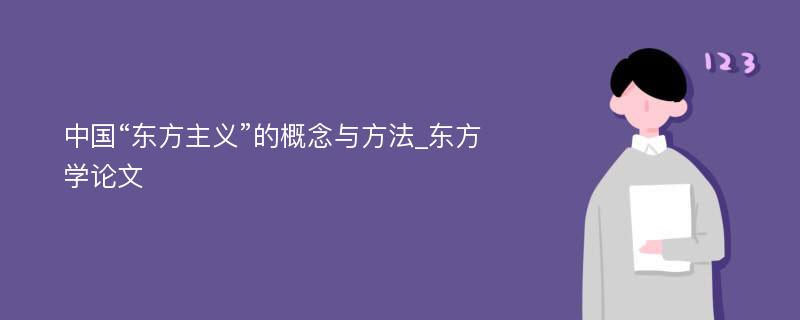
中国“东方学”:概念与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方学论文,中国论文,概念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3)02-0001-07
一、东方/西方;东方学/西方学
中国的学问,按空间范围,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是“国学”,研究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其核心是汉字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即汉学;第二是“西学”或“西方学”,是研究欧美(西方)的学问;第三是“东方学”,研究除中国以外的东方各国的学问。当然,在国学与东方学之间,也有交叉重叠的部分,例如关于中国与东方各国历史文化关系的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特别是跨境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其中有一些已经积淀为一个国际性的学科,如蒙古学、藏学、敦煌学、丝绸之路研究等,在一定语境下也可以划归为“东方学”的范畴。
在上述三种学问中,国学(中学)和西学(西方学)是众所周知的,以至于在许多中国学人的意识当中,除了国学,就是西学。这种意识集中反映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文化”、“中西学术”、“中西比较”等约定俗成的词组、命题与表述当中。相比之下,东方学虽然早就有丰厚的历史积累,但“东方学”这一概念却使用不多,缺乏学科自觉,这恐怕也是中国学术文化界盛行已久的“中西中心主义”的一种表现。东方学意识的缺失,主要是因为许多学人习惯上以“中国”代替“东方”,认为中国的“国学”就代表了东方学,或者覆盖了一大部分的东方学,在某些人看来,或许剩下的部分就不太重要了。另一方面,“印度学”、“日本学”、“朝鲜—韩国学”等学科,在大多数情况下又各自为政,还未能有效地整合为更高层次的东方学。
在中国传统的学术史上,因为缺乏“东方、西方”的世界观念,而没有产生出类似于欧美的东方学这一概念,也没有东方学的学术自觉,然而中国的东方学却有着悠久的传统。汉魏时代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历代文献对中国周边国家(包括西域中亚各民族、印度、波斯、日本、朝鲜、东南亚等亚洲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文化的记载,六朝至唐代的义净、玄奘等对印度与西域的游历与记述,明代以后的《日本考》等著作,都可以视为中国“东方学”的基础和渊源。清末民初佛学复兴时期,康有为、章太炎、苏曼殊、梁启超对印度的评论与研究,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对日本的介绍和研究,都使中国东方研究进入了实地考察与文献互征的近代学术状态。进入20世纪后,在欧洲学术文化的影响下,“东方”、“东方文化”这样的概念在中国学术界被大量使用。1920年代,中国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关于东西方文化优劣问题的大论战,也推动了此后的人们对东西方文化分野的重视。1950年代,我国曾翻译出版前苏联学者写的《东方学》、《古代东方史》等著作,虽然书中充斥着意识形态论辩色彩和阶级决定论,但对中国“东方学”学科意识的推动是有益的。1950~1970年代以东西方冷战为背景,以“第三世界”理论为基础的所谓“亚非拉”问题的评论研究,也有很大一部分与“东方学”领域相叠合。到了20世纪,我国学术界出现了一批有成就的堪称“东方学家”的学者,如章太炎、梁启超、周作人、陈寅恪、徐梵澄、丰子恺、吴晓铃、饶宗颐等。
但是,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东方研究”,就大陆地区而言,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间成熟和发展起来的,并且在国别研究和分支学科两个方面得以展开。在国别研究方面,埃及学、亚述/巴比伦学、印度学、东南亚学、中东学、中亚学、藏学、蒙古学、日本学、朝鲜/韩国学等学科概念都被明确使用,不仅成立了以“××学”为名称的学会及研究机构、教学机构,而且出版了以“××学”为名称的学术杂志、书籍等。中国的印度学研究历史最为悠久,学术底蕴丰厚,日本学则具有较大的关注度,成果也最多,朝鲜/韩国学后来居上,阿拉伯学、伊朗/波斯学及中东学稳步推进,蒙古学、藏学得天独厚,东南亚学不甘示弱。在这些分支学科领域中,出现了一批新的著译等身的东方学家,如古代东方史学家林志纯,东方艺术专家常任侠,印度学家季羡林、金克木、刘安武、黄宝生,阿拉伯学家纳忠、仲跻昆,波斯学家张鸿年,朝鲜学家韦旭升,日本学家周一良、汪向荣、梁容若、叶渭渠、严绍璗、王晓平等等。在分支学科方面,东方哲学、东方文学、东方美学、东方艺术、东方戏剧等在各分支学科中,学科意识较为自觉。其中,中国“东方文学”的学科意识最为鲜明和自觉,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学术史。中国东方研究会自1983年成立,迄今已经有近三十年的活动历史。期间,许多大学中文系开设了东方文学课程,以“东方文学”为题名的专著、教材以及相关著作已有上百种,论文数千篇。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的《东方文学研究集刊》也在连续不断编辑出版中。延边大学等大学设立了专门的“东方文学”二级学科博士点。这些都表明,东方文学在中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可观的东方学分支学科。
但是,尽管我国已经有了丰厚的东方学的传统积累,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与欧美的“东方学”、日本的“东洋学”或“东方学”相对应的“东方学”学科建制与普遍的学科自觉。世界许多文化大国都早已成立了的“东方学会”、“亚洲学会”之类的学术团体,至今在我国也没有出现。在这种情况下,长期以来,各个分支学科的研究就相对缺乏东方学的整体感和学科归属感。因此当务之急,是以东方学这一学科概念,将已经有了丰厚积累的东方各国问题的研究以及东方研究的各个分支学科统合起来,使各分支学科突破既定学科的视阈限制,以便打造与世界东方学接轨的更宽阔的学问空间和学科平台,使中国的“东方学”与“西方学”、“国学”三足鼎立,形成一个完整的、协调的而不是顾此失彼或厚此薄彼的学科体系。这样一来,国学、东方学、西方学就可以成为在世界学术背景下确立的三个“集群学科”的名称。这三个“集群学科”是在世界学术文化的大背景下,在空间区域上划分出来的、置于“一级学科”之上的跨学科的学科。在学科划分上,现在我国在学术体制上只有“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三级学科”的划分,当“一级学科”寻求更高的学科依托,探索跨学科的、区域性、整体性研究的时候,往往就需要归靠在或依托在国学、西学、东方学这样的集群学科上。就东方学而言,假若没有“东方学”的学科观念以及学术团体、学术体制,那么印度学、日本学、阿拉伯学、东南亚学、朝鲜/韩国学等,就像五指不能握成拳头、甚至连相互间的交流都缺乏平台。只有建立东方学,才能适应21世纪中国与东方各国新型的国际关系与文化关系的需要,才能使我国的东方研究与英、法、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东方学并驾齐驱。为此,就需要在教育与教学体制上逐渐改变“英语至上”的做法,充分尊重多语言、多民族、多国家、多元文化的世界格局,重视东方各国语言文化的学科建设与教学,为中国东方学的繁荣发展创造必要的基础和条件。
二、“东方学”与“东方观”及“东方观念”
任何一个学科都有自己一整套学科概念和术语,这是构成学科体系的基本要件。东方学也不例外。在中国的东方学学科理论建构中,除了上述的“东方学”这个学科名称及与此相对应的“西学”、“国学”等学科概念外,还涉及学科内部的相关概念,主要是“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东方观”及“东方观念”等。这些看上去似乎明明白白的概念,却因为种种原因而变得似是而非,因此有必要加以辨析。
在西方,那些关于东方国家的描述和议论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思想观念,被称为“东方主义”(Orientalism);那些研究东方的学者、思想家,以东方国家为题材、对东方加以描写的作家与艺术家们,则被称为“东方主义者”(Orientalists)。的确,站在“西方主义文化”的立场上,较多地关注东方、描写东方、谈论东方,就是“东方主义”或“东方主义者”。这显然是“东方主义”的原本含义,因为站在西方及“西方主义”相对立场上看,东方学家们对东方世界的关注与研究,是对东方世界的弘扬,所以属于“东方主义”。这个词早在1920年代,就被日本学界所使用,并且有所讨论。例如,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在1926年发表的系列评论《饶舌录》中,将弘扬东方文化的印度的泰戈尔和中国的辜鸿铭,看成是“东方主义”的代表人物。谷崎润一郎及当时日本人所理解的“东方主义”应该说是“东方主义”的本义。事实上,在西方学术史及思想史上,“Orientalism”这个词原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
然而近几十年间,那些生活在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的阿拉伯裔的学者、评论家们,却在与“Orientalism”这个词的本义正相反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如贾米拉的《伊斯兰与东方主义》、提巴威的《说英语的东方主义者》、希沙姆·贾依特的《欧洲与伊斯兰教》、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等著作,都在西方人的一些“东方主义”作品里看出了想象东方、歪曲与丑化东方,特别是歪曲、贬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反东方的或者“非东方主义”的倾向。但他们在表述这一看法的时候,却仍然依照西方学者已有的习惯,将这些倾向称为“东方主义”,直到1997年萨义德的《Orientalism》出版,一直都是如此。而国内一些学者也照英文直译为“东方主义”,在著书作文时频频使用“东方主义”一词。于是,在汉语语境中,“东方主义”这个词的字面含义与实际含义之间就形成了严重的悖谬。
众所周知,“主义”一词,是日本人对英文词缀“ism”的翻译,“主义”传到中国后,对中国现代的语言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主义”这个词在汉语中,其词性已经发生了变化,它既可以像英文的“ism”那样作为接尾词,也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名词使用,如五四时期胡适提出的著名的主张“多研究点问题,少谈点主义”,这里的“主义”就是作为独立的名词使用的。同时,在汉语的语境中,“主义”作为结尾词,其含义是正面的、肯定的。凡主张一种观点、推崇一种学说、肯定一种制度,便称之为“某某主义”。“主义”是一种主张、一种理念,例如“霸权主义”是对霸权的主张,“个人主义”是对个人权力和利益的诉求,“自由主义”是主张自由的,“资本主义”是主张资本利润与自由市场的。依此逻辑,“东方主义”也应该是主张东方的,是对东方的正面肯定、弘扬与坚持。但是事实上,“东方主义”指的却是西方人站在自身文化价值观立场,乃至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立场上对东方形成的一系列浪漫化的想象和一整套观念与看法。在特定条件和特定语境下,这些想象、观念和看法中,也含有一些本来意义上的“东方主义”,即肯定和弘扬东方的倾向,但总体上却不是“主张”东方,而是对东方文明与东方社会做出的否定性评价,是把东方“他者化”,把东方作为西方文明优越的一种反衬,从而具有“西方中心论”,即“西方主义”的“反东方主义”倾向。因此,无论是从汉语中“主义”一词的约定俗成的词义,还是从上千年西方人的东方观、东方观念来看,用“东方主义”这一概念来指称西方人的东方观,都是错位的、乖戾的,甚至是悖谬的。就萨义德的《Orientalism》一书的中心主题而言,作者所评述的也不是西方的“东方学”研究(Oriental studies)史,而是西方人的东方观念,是西方人为了与自身对照,在关于东方的有限知识基础上,站在自身文化立场上形成的,对于东方世界的一种主观性印象、判断与成见;实际上,萨义德所描述和着力批判的,是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中那些“西方主义”,或者说是“反东方主义”的观念与倾向,而不是“东方主义”的倾向,准确地说,是西方人的“东方观”,是西方人关于东方的观念。这样说来,综合萨义德的全书基本内容,把“Orientalism”译为“东方观念”或“东方观”也许更为合适。
笔者在这里要说的,重点不是萨义德那本书的译名问题,而是因为这里涉及了“东方学”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东方学”到底是什么?“东方学”与“东方研究”是什么关系?“东方学”与“东方主义”、“东方学”与“东方观”或“东方观念”是什么关系?既然有了所谓“东方主义”倾向,那么有没有与之相对的“西方主义”?如果有,那么应该怎样看待东方学中的“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两种对立的思维倾向,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进一步对这几个重要概念加以辨析。
首先,是“东方学”与“东方观念”(东方观)两者之间的关系。
“东方学”与“东方观”、“东方观念”之间具有相当的联系性,又有很大的区别。区别在于,“东方学”是一个学科概念,“东方观念”是一种思想概念。“东方学”与“东方观念”之间的关系,是学术研究、学科与思想形态之间的关系。作为一门科学研究的东方学学科,强调的是对某些具体问题、具体领域的深入研究,注重研究的实证性、客观性和科学性。例如,18-19世纪的英国的威廉·琼斯,法国的商博良、安迪格尔、德·萨西,德国的马科思·韦伯等人,他们都是严格意义上的东方学家,分别对东方语言、东方文学、东方宗教、东方历史文化等做过专门的、深入系统的开创性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系统的东方观或东方观念。
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思想家、评论家、旅行家、宗教家而言,他可能没有专门的东方学研究实践,但总是要发表他对人类、世界,包括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的评论,在构架其思想理论体系时将东方世界纳入其视野,并提出自己关于东方的看法,这就形成了他们的“东方观”。这样一来,“东方观”或“东方观念”就呈现出复杂的形态。有时表现为以东方研究为基础的较为客观科学的形态;有时则是一种在他人的东方学研究的基础上所发表的对东方问题的评论观点和看法;有时则是与科学的东方学研究无关的关于东方的想象、成见乃至偏见;有时则是这几种情况的复杂交错的状态。
要进一步加以区别的话,“东方观”与“东方观念”也有不同,“东方观”是零碎的、片断的、个别的,而“东方观念”则有一定的系统性、普遍性。当“东方观”积累到一定程度、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流行的或主流的看法之后,便发展为“东方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爱尔维修、布朗热、孟德斯鸠的“东方专制主义”论,黑格尔的审美三形态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世界精神”论,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美国学者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与治水理论等,都形成了系统的东方观念。“东方观念”一旦形成,也会对“东方学”研究产生持续不断的影响,长期以来西方主流东方学渗透着根深蒂固的“东方观念”,其表现出来的“西方主义”偏见就是很好的例证。
因而,在东方学的理论建构中,应该认真清理“东方学”与“东方观”、“东方观念”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对东方学的内涵和外延做出明确的界定。广义上的东方学史或东方研究史,当然应该分析、评述东方学家的“东方观”或“东方观念”史,但是,非东方学家的“东方观”和“东方观念”只能是背景性、附属性的。在严格的学术层面上,东方学史应该是东方研究的学科史和学术史,它与作为思想史的“东方观念史”是有区别的。相应地,“东方学”的历史与“东方观”的历史在写作上也应属于两种不同的学术理路,前者属于学术史的范畴,后者属于思想史的范畴。例如,我们要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东方的思想观点加以研究,准确地应该表述为“马克思主义东方观”;当我们在构架《东方学概论》之类的概论性著作的时候,应该将西方国家、东方国家(包括中国)的东方学研究成果作为基本材料,对东方学家的学术成果做出全面评述,而不是仅仅评述西方的东方学家。同时,根据研究的需要,也可以把那些非东方学家的东方观包括进来,但是那应该是次要的。
三、东方学的方法
对学术研究而言,所谓研究方法,不仅是具体可操作的行为规则,也是一种基本思路。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方法,东方学作为一门学科,当然也不例外。但东方学作为一个学科,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上又具有自己的规定性,因而方法论上也应该有自己的某些特殊性。而且在东方学的不同历史阶段,研究方法也应该有所变化。当“东方学”这门学科在19世纪的英、法等国开始兴起的时候,所采用的主要是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三种基本方法。地下考古发掘解决的是包括古代遗址、各种文物在内的物质层面上的东方学资料问题;民俗学的方法主要是通过田野作业,深入某种文化的基层,对地上文物、相关的人与事加以采访调查和收集资料;语言学的方法要解决的则是文献的识别、阅读和翻译问题,它与比较故事学的研究一道,直接导致了欧洲比较语言学学科及研究方法的诞生。欧洲东方学家们的考古学、民俗学和语言学的方法,为东方学的研究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现代学术也有相当的启发。王国维提出的地上文物与地下文物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就与东方学的研究方法密切相关。
但是,我们今天的东方学研究,与19世纪的东方学相比,其历史阶段、学术环境和研究宗旨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就古代东方研究而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而且考古发掘涉及国家主权,不能像19世纪西方列强的考古学家那样随便闯入。中国的东方学家所能做的,就是关注相关国家考古发掘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古代东方语言识读的基本问题大部分已经解决,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将相关文字材料译成中文。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今天中国东方学的研究方法不同于欧洲古典东方学的研究方法。事实上,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几位有成就的东方学家,如季羡林、饶宗颐、王晓平等先生的研究,已经为中国东方学的研究方法做了很好的示范,对此加以总结和发挥,就可以解决今天的东方学方法及方法论问题。
笔者认为,中国的东方学研究,应该采用三种基本方法:第一是翻译学的方法;第二是比较研究的方法;第三是区域整合和体系建构的方法。
首先是翻译学的方法。
翻译学的方法是东方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东方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中国的东方学属于中国的学术,所有其它国家的文字材料都必须首先转化为中文,才有可能在汉语语境及中国学术文化的平台上进行。对于东方古代文献而言,翻译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文字的转换问题,翻译本身就是一种研究,这是古典文献、古典作品翻译的一个显著特点。由于古典文献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浓缩和积淀,蕴含了多侧面的丰富知识与思想信息,翻译古典文献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转换的过程,也是翻译家站在自身文化的立场上,去理解、探究、阐释对象文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研究的过程。这一点应该为更多的学生、学者所体会与认识。纵观中外东方学研究的历史,有成就的东方学家首先是古典文献及古典文学的翻译家,例如,英国及欧洲东方学的奠基者威廉·琼斯一生的学术活动,都把古代东方作品翻译成英文作为主要事业。他翻译了印度的梵语文学经典《沙恭达罗》、《牧童歌》、《嘉言集》,翻译了波斯诗人菲尔多西的长篇史诗《列王纪》、涅扎米的长篇叙事诗《蕾丽与马杰农》和《秘密宝库》以及哈菲兹的抒情诗,翻译了古代阿拉伯的《悬诗》,还翻译了中国《诗经》中的有关诗篇。琼斯对古代印度、波斯、阿拉伯的评论与研究,都是建立在这些翻译之上的,这些翻译为英国的印度学、波斯学、阿拉伯学奠定了基础。同样的在中国,从汉末六朝到唐代的持续不断的佛经翻译,也为中国现代的印度学、中亚学奠定了基础。到了20世纪,季羡林对《罗摩衍那》、《沙恭达罗》的翻译,徐梵澄对《奥义书》和《薄伽梵歌》的翻译,金克木、黄宝生等对印度古典诗学与文论的翻译以及对《摩诃婆罗多》的翻译,纳训对阿拉伯《一千零一夜》的翻译,张鸿年等波斯学家对《列王纪》等波斯古典诗歌的翻译,饶宗颐对“近东开辟史诗”的翻译、周作人对《古事记》及江户文学的翻译,钱稻孙、杨烈、李芒对《万叶集》的翻译,丰子恺、林文月对《源氏物语》等物语文学的翻译,还有刚问世的《日本古典文论选译》(两卷四册)等,都是中国东方学的成果,都具有很大学术价值。许多东方学家用了大量的心血和时间从事翻译工作,这不仅为他们个人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使东方各国的古典文献作品突破了语言壁垒而进入汉语语境,进入了更大的“东方学”的学术平台。可以说,没有翻译,就没有“东方学”的形成。东方学者除了自己的专攻之外,要对其它东方国家有所了解,自然就需要借助翻译。没有翻译,只能是各自为政的国别研究,而不会出现真正的东方学。
到目前为止,东方古典文献及古典作品的汉语翻译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最重要的文献大部分都已经有了中译本。这是否意味着翻译及翻译学的方法在今后的东方学研究中就不那么重要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古典作品的翻译有一种译本往往是不够的,首译本具有开创性意义,它在翻译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但恰恰是因为它第一次翻译,就可能存在种种缺憾,因而出现能够超越首译本的译本,是必要的和值得期待的。另一方面,东方各国尚有很多没有汉译本的古典作品,例如,印度现存十八部“往世书”至今仍然没有汉译本,各种古代民间故事集也缺乏全译本。阿拉伯的古典诗学及文学批评据说很发达,但是至今只有区区三四万字的翻译。日本出版的各种《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只是选本,尚且有上百卷之多,我们仅仅译出了其中的小部分。其中“渡唐”物语《浜松中纳言物语》和《松浦宫物语》,中世“战记文学”经典《太平记》,松尾芭蕉与谢芜村、小林一茶等人的“俳文”,《日本灵异记》和《砂石集》等“佛教说话”,都有极大的文学价值与文献价值。古代中东、东南亚各国的翻译情况也是如此。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翻译、尤其是东方经典作品的翻译,仍然是东方学的基础,也是东方学不可绕过、不可回避的基本途径和方法。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当我们强调“作为东方学之方法的翻译”的时候,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途径和手段。对于一位学者而言,翻译是研究的基础,建立在亲手翻译基础之上的研究是最为可靠的、也是最值得人们信赖的。但是假如一个学者只做翻译而很少做研究,那就令人遗憾了。
第二,是比较研究的方法。
比较研究是所有现代科学和学科都通用的方法,但对东方学来说,特别需要比较的方法。看看中外东方学的历史,那些东方学大家无一例外都是比较研究的专家,他们的学术发现更多地依赖于比较。例如,正是运用了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英国的威廉·琼斯发现了印欧各民族语言之间的深刻而广泛的联系;正是运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琼斯发现东方各民族诗歌的某些共通性,以及东方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异同点。中国的东方学家也是如此。比较就要有比较的资本。对于中国的东方学而言,比较研究的资本首先是国学。没有国学的底蕴和修养,没有对国学的某一领域、某些课题的深入了解和研究,就不可能展开有效的比较研究,比较方法的运用就无从谈起。事实上,一个好的东方学家几乎都是一个优秀的国学家。上文提到的季羡林、饶宗颐、王晓平等东方学家几乎全部可以称之为国学家。比较方法的运用,使他们打通了国学与东方学之间的界限。
近三十多年来,由于比较方法在东方学中的大量运用,使得研究成果大量出现,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可以称之为“比较东方学”,是东方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比较东方学”中最突出的是中日比较、中印比较、中韩/中朝比较等。可以预料,“比较东方学”今后还将有更为广阔的研究前景。
第三,是区域整合、体系构建的方法。
“东方学”本身是一个整合性的概念,它是由东方各国的国别研究组成的,是以各国别、各语种的研究为基础的。因而,东方学分支学科较多,学科领域很庞大、很庞杂。从实践上说,除了特殊时代极个别的天才人物,像威廉·琼斯那样的人物,没有面面俱到的“东方学家”,也没有人是所有分支学科的行家里手。但是,东方学并非要求一个学者全面而又深入地研究东方各国的历史文化问题,而是要具备东方学的学科意识、学术眼光以及必要的学术修养。要求在从事东方学的某一分支学科研究的时候,不能只是孤立地就事论事。例如,研究印度问题,必然与东南亚问题、中国问题联系在一起;研究日本问题,也必然与中国问题、朝鲜问题,乃至印度佛教等问题联系起来;研究阿拉伯伊斯兰问题,必然与东南亚海岛各国问题,中国回族与西北部历史文化问题联系起来;研究中国的藏学、敦煌学,也必然与印度研究、西域研究联系在一起等等。更有一些问题本身是跨国界的,因而必须使用“区域整合”的研究方法,例如季羡林先生的《糖史》以及他对造纸术、丝绸及其文化传播问题的研究,王晓平先生的《佛典·志怪·物语》这样的选题,都必须突破国别研究的孤立性和局限性,寻求区域的相关性和联系性。这种国际跨界、区域整合的方法是一种以揭示“传播—影响—接受”为主要宗旨的历史文献学的方法,它主要依赖于历史实证、典籍考据、文献解读等手段。
如果说“区域整合”是以揭示研究对象之间的事实联系为目的,那么,“体系构建”则是一种理论构拟的方法,就是要在某些研究对象之间建构一种超越事实之上的精神联系,从而产生出含有思想素质的新的知识形态。对于东方学研究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凡是以“东方”为定语的各学科的研究,例如“东方历史”、“东方宗教”、“东方哲学”、“东方美学”、“东方文学”、“东方艺术学”等,都需要有体系的构建。以“东方文学”的研究为例,东方各国文学之间是有着深刻历史联系的,因此,研究东方文学就必须采取国际越界的方法,揭示他们之间的事实上的传播与影响的关系。但是仅此还不够,还要在更高的层面上为东方文学构拟出一个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固然必须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但同时它主要是逻辑的、思想的产物,因而是“超事实”的并非纯客观的东西,是作者对研究对象的整理、提炼、综括和诠释,因而带有“理论构拟”的性质。再以“东方美学”的研究为例,倘若只是把东方各国的审美意识、审美思想评述出来,那是远远不够的。既然称为“东方美学”,就不能仅仅是东方各国美学的简单相加,否则只写国别美学史就够了;而且既然称为“美学”,就不能把东方美学史写成“审美意识史”。要发现和提炼一系列概念、范畴,要为东方美学建立起理论体系或理论谱系。
[收稿日期]2013-01-06
标签:东方学论文; 东方主义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