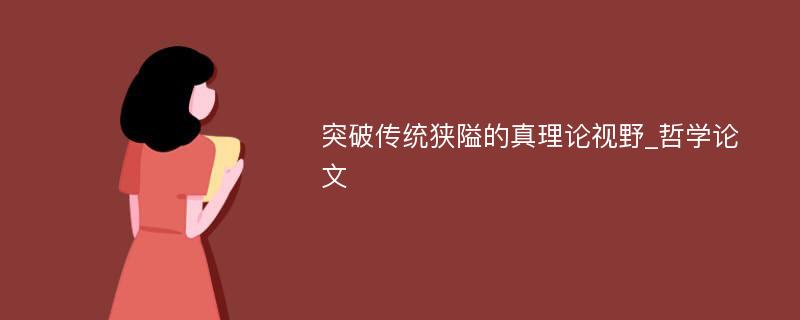
突破真理论的传统狭隘视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狭隘论文,视界论文,传统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问题的提出
自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以来,关于真理问题的研究已有相当进展。为了推动研究更加深入,现在,我认为有必要提出下面这个问题进行思考,这就是:哲学应当怎样去探讨真理的问题,或者说,哲学应当探究的究竟是何种真理问题?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在我看来,是因为它直接关联着对于人类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的理解,即人们不懈地追求真理,究竟是在追求着什么、要去追求什么?
在以往的哲学中,我们的目光主要盯在科学认知真理上面,仅限于从认识论去谈论真理,而且把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真理性归结为主体对客体本性和规律的正确反映,仅祗强调主观应该符合客观的单面关系。这个方面当然也是需要的。主观对客观本就有着肯定性的关系。正确反映对象的本质和规律也是人类活动获得成功的必备的前提和条件。然而问题是,哲学探讨的真理问题是否应该仅仅限制于认知性的科学真理,科学认知真理能否认作就是人类活动追求的最高真理?更进一步说,人类孜孜以求真理,为真理前赴后继、奋斗牺牲,难道就是仅仅为的认同客体、符合客观、适应外部世界、实现客观本性,此外还有没有更高追求的真理目标?或者换一种方式说,符合于外界对象,是否可以认为就是人类理性活动的最高本质、唯一功能和终极目标?
当着思想局限于狭隘的理论范围之时,对这里所提的问题我们可能会感到很怪异;而一旦回到现实生活的广阔天地,我相信我们就会立即体验到,原来哲学理论所论说的那种真理实在太过狭小、不敷现实使用,很难反映出生活的真实。而这点,在我看来,或许就是我们的哲学理论远离了生活、因而也为生活所冷落的一个重要表现和原因。
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真理”通常既是一个很神圣的字眼儿,同时又是运用得十分广泛和普遍的概念。它并不是只有一种涵义。人们经常是在不同的意义上去运用真理一词,这里既包括认知性的真理,也包括其他意义上的真理。因此可以说,在生活中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真理概念,它反映了现实的人们是具有多方面的不同追求的。
真理,如果从它的普泛而非学理的意义说,无非就是指真实之理或实在存在之义。在这里,真实是与虚假相对待的,实在是与虚幻相对待的。有真实是因为有虚假;有了真实与虚假,就需要去分辨真假,于是产生出求真的活动。
在现实生活中,真假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个认识问题、观念活动问题。理性和观念有着真假的分别,这没有疑问;对象和存在,甚至人的生活本身也同样都有真假、实幻的区别问题。人们在现实活动中,经常会把假存在当作真存在去对待,把假对象当作真对象去处理,拿假问题当作真问题去进行争论。当然也会把真的当作了假的。生活亦如此。人们正在过着的生活,不一定就是真实的生活。人们往往不得不去过着一种虚假的生活,而且经常把它当作了真实生活,或者把真实生活看成虚假的生活。这只要想想某些官场和商场逢场作戏的生活,再想想“文化大革命”那些年代神话般的生活状况,就会理解这里说的一切。这类真假问题也需要去分辨。辨别这类真假的意义决不亚于辨别真假观念的意义,甚至应该认为更加重要、更有意义(虽然这两类真假问题经常是联结在一起的,却也不是完全相同的一回事)。
事情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样的“真”存在于何处,它究竟是个什么?显然,这只能是对人而言的真、为人而有的真。这样的真既不可能存在于人们生活之外的世界里,也不可能仅与客体相关而与人的主体状态无关。人们通常所说求真、讲真、叫真,以及“要为真理而奋斗终生”这些话,决不仅仅是要使自己去适应或符合于外在的客观、客体和对象的意思,它们具有的内涵明显都超出了科学认知真理的那种意义。一种需要并值得人们为之奋斗终生、甚至不惜贡献生命而去争取的真理,是一个神圣而伟大的目标,其中必然体现着人们的某种理想和追求,寄托着人们对于未来莫大的美好期望。这样的真理,只能属于人自身创造本性的实现,不可能仅仅是回到事物已有的预先规定。
从这种观点去理解人的“理性”,我们会同样地看到,它的本质也不是仅仅趋同于客体、仅仅符合于客观的对象。人们需要认知客体,是为了超越客体;人们需要反映客观,是为了突破客观。理性的本质应该说是双重性的,它对对象的肯定性关系只是作为环节而蕴涵于对于对象的否定性关系中的。引导人们突破物的局限,超越自然规定的限制,在人和物之间建立起以人为主导的统一联系,这才是人们所以需要理性和理性应当发挥的真正的和基本的功能。理性与对象的统一关系,从这一意义说就不会是单面的符合关系,必然是双向的互适关系。即使就单纯认知性的“反映真理”来说,例如科学总结出的规律和原理,它也不只是单纯地反映对象的客观内容,其中也已对象化了人的本质内容,那种所谓的客观性,只能是为人而存在、为人所有的客观性。所以当科学把事物的本性转化成为理性特有的普遍性的形式,这就意味着使它超越了事物的客观存在,突显了事物对人而有的意义,并在事物和事物、事物和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可由人支配和运用的联系,人们通过这一中介就能创造出自然界本来没有的存在。理性的这一本性,以往的某些哲学家已经意识到了,在他们关于理性的理论中,已不再局限于认知理性、理论理性的传统观念,同时还提出并研究了实践理性、价值理性、审美理性等范畴;即使单就理论理性而言,也不再理解为单纯表象客体,而是加进了某种先验的成分和内容,这部分称为先验理性。康德就是这类哲学家的突出代表。
这就是人的现实生活和实际活动向我们昭示的情况。哲学本是来自于生活的,理应去表现生活、理解生活、说明生活、批判生活、引导生活。哲学的真理论是教人分辨真假、追求真理的专门性理论,它应当具有宽广的视野和高超的意境,全面去表现生活中的求真活动,不仅要说明实然性的、手段性的、理论性的真理活动,也应说明应然性的、目的性的、实践性的真理追求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决不能够也不应该把自己的视野仅仅局限于某一种真理的问题上面。
二 真理的人性本质
真理问题是人所特有的问题。唯人才需要去辨析真假,才会去追求真理,动物世界是不存在这样麻烦的问题的。这个事实说明,真理是表现着人性、属于人的存在方式,无论真或假,都是人的本性的体现。
哲学属于人的自我意识理论。哲学讲真理当然也就只能从人性出发,必须体现出人的特有本性。
人的本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来就是实践性。人是一种实践的存在,以实践为生存本性的存在。
实践本性意味着,人是一种自我创造性的存在。人一方面是自然存在,在这一意义上,人同其他自然存在一样,必须依赖自然而生存,并且要受到自然规定的影响和制约;人同时又是一种反自然的存在,在这一意义上,人又超越了自然的限定,制造出自己独特的生存活动和存在方式。人在自身的创造性活动中,通过本性外投的方式,在把自身本质对象化于外部存在的同时,也就使对象人化,把自然事物变成了“为我的存在”。据此我们可以说,由于人的出现便颠倒了自然的乾坤,人的本性也就是颠倒的自然本性。
人的如此本性充分体现在真理性质之中。
如果我们去探究“人为什么要去追求真理、人追求真理究竟是在追求什么?”这类问题,我们就会发现一种看起来十分矛盾的现象:人之所以需要追求真理,这意味着人能制造一种假理,而且人也总在那里不断制造着假理;由于人经常为假理所诱导,又为假理所迷惑,常常是假中有真真中有假、假假真真真假难分,所以才需要去追求真理、分辨真假。
如果再进一步追问,人又为什么要去制造假理,造了假之后还要费力求真,给自己凭添如许的麻烦?这显然不会是仅仅为了要去消除假理便去制造假理。先造假理再去消除假理,这个行为本身说明,“假理”一定也是人的生存方式所需要,对于人的生存生活有着某种用场;否则,人是不会允许发展这种能力、从事这样无谓的行为的。人从制造的假理中去求取真理,这同时也说明,由此所求得的真,决不会像过去所了解的那样,仅仅是为了使人的行为能够顺应、符合于客观、客体的需要。因为,道理很明显,如果仅仅是为了使人的行为顺应自然、符合客观,那就不如让人回去做动物,没有必要先造假理再去求真地多此一举。
人是一种很奇怪的存在,人的行为常常是看起来自相矛盾的。其实,这正是人之为人的本性。人的这一切矛盾行为,从人的实践本性会很容易理解。归根结底来说,所有这一切矛盾行为都是根源于一点,即人不能满足于自然提供的现成的存在和条件,不会甘心仅仅顺从自然本性所规定的生活。人需要的一切,虽然须以自然条件为依据,但它只能凭靠自己的劳动去进行制造。这就是人的实践本性。而制造的行为,按其固有本义便是一种无中生有的活动,实际也就是把真的变假、假的变真的活动。这就是为什么人需要去制造假理,然后又必须去追求真理的根本缘由。人所追求的那种真理只是人自己的创造活动的产物,并不是什么既有的现成存在;作为这样的真理当然也就只能从消除人所制造的假理中去求得,它决不是客观本有的什么既定之理。所以从这一意义说,真正表现人之为人本性的,与其认为求真的行为,不如看作造假的本领更能说明问题。
人所制造的假理,人们从它能够引出真理,也就能够由它走向虚幻。不会使人陷入虚幻的东西,也不能引人进入创造境地、超越客观自然的限制。从根本上说来,这就是人所特有的“主观性”的作用。主观性对人具有两重性的作用,它像一把双刃剑,既是发挥创造性的利器,也是可能伤害自己的凶器。过去从原苏联引进的哲学教科书只看到它伤害自己的一面性质,因而必欲连根拔除而快之。从这种观点出发,进而便把真与假、实与幻的关系看成绝对对立的。按照这种观点,真是真,假是假,二者界线分明;真是客观性,假是主观性,二者互不相容。于是,在这种理论里,人们追求真理的活动便被归结为追求客观性、排除主观性的活动,区分客观性和主观性也就成为判别真理与谬误的根本界线和尺度;哲学,特别是它的真理论的功能因而就变成只是教人如何“一切从客观出发,不能从主观出发”的理论。
这在现实生活中,当然是完全行不通的。实际生活中我们不但排除不了主观性,还得时时处处去依靠主观性、发挥主观性的作用。这既是人的生存活动本性,也是人作为人的生活的本有内容。试想,在人们所创造的劳动产品里,有哪一件不是主观性物化的结果?即使是一块天然的石头,当着把它变成人的对象时,例如南京的雨花石、安徽的黄山石,人们也往往要赋予它以某种主观性的精神内核,什么“童子拜观音”、“猴子观海”、“寒江独钓”、“秋风落叶”等等,如此才感到心满意足。在人的生活里,主观性与客观性总是纠葛一起难解难分的。问题只在于如何去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它们之间如何建立一种适于人的发展状况和要求的关系,而决不在于简单地排除主观性的问题。所以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出了“为主观性正名”的问题(详见《哲学研究》1987年第10期《论哲学观念的转变》一文)。
同样道理,为人所有的真与假、实与幻的关系也不是一种简单地否定关系和排斥关系。事情往往是这样,真中有假假中有真,假的可以变真真的也可变假;正所谓真变假时假即真、假作真时真亦假。如果不是这样,人就失去了创造能力,也就不再是人。
按照这样的理解,人的求真就不简单是一种认知活动,而且是一种实际的创造活动,人所追求的真理也不单纯是为了适应自然、认同客观,而是贯注着人的理想、追求的一个创造性目标。为此,我们就不能不去调整、改变过去从单纯认知真理所形成的那种真理观念和理论框架。我们宁可把真理问题理解得复杂一些,以便思考得更加深入,切莫过于简单化。
三 走出传统科学理性框架
过去,我们对真理问题理解得很狭窄、过于简单化,可以说基本上是按照直观认识论所了解的科学认知本性去理解真理问题的,追究其原因,我以为主要同下面的两个情况有关。
第一个情况。对真理的这种理解是由于沿袭传统观念,特别是近代以来把人假定为理性存在、以科学理性充当楷模的这种哲学观念所造成的。
近代自结束宗教神学的独断统治之后,便掀起了理性的复兴运动,随之科学得到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理性逐渐取得了支配地位。由于理性被科学化,“科学”便成为一切理论的标准模式,其他种种意识形式都不能不向科学理性靠拢、看齐,于是形成科学技术理性支配文化形态的时代。
科学化的这种倾向,在哲学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它不但影响到哲学理论的形式方面,还渗透进哲学理论的内容之中。在那一时期,一些哲学家甚至认为哲学只是科学思想及其成果的一种综合理论,把哲学变成仅仅是科学的附属物。另一些哲学家虽然竭力维护以往哲学的至尊支配地位,他们也难以摆脱科学思想的影响,只能按照科学方式称哲学为凌驾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理论。
哲学的科学化影响至今也并没有完全消除。在从原苏联引进的教科书里,我们就能看到大量的这类影响印迹。教科书里的许多基本哲学范畴,如物质、运动、时空、规律、因果、必然性等等,当初是从科学概念直接搬运过来的,至今对它们的所谓哲学解释,体现的仍然主要是科学(而且是那一时代的科学)的观点,例如“规律”的理解就基本是如此。另外,适应科学的要求,教科书也把哲学理性化,重视认识理性的意义,不重视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像意志、情感、目的、欲望这些范畴都未给予应有的地位,有的干脆被排除在了哲学理论之外。教科书讲述哲学理论的方式,也基本是摹仿、照搬科学理论的论述方式。首先给出命题、原则、结论,然后引用大量的经验事例去予以证实,哲学变成了如列宁曾经指出过的“实例的总和”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真理”被看成单纯追踪客观性的活动,哲学的真理论被归结为认知性的科学真理论,就是顺理成章、毫无奇怪的事情了。
哲学作为世界观理论,同其他一切意识形式和知识部门都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并需要不断借助其他意识成果以充实自己的内容。哲学在一个时期趋向神学化、在另一个时期趋向科学化,这在哲学和人类意识成长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哲学毕竟只是哲学,既非神学也非科学,它具有自己特有的对象和任务,也有自己特有的理论形式和研究方法。如果说在过去,哲学和科学都还发展得不够成熟,出于反对宗教神学统治斗争的需要,哲学和科学彼此联手相互借助,哲学直接吸纳大量科学内容因而使自己科学化具有相当理由的话;那末在哲学和科学都已发展成熟的今天,哲学仍把自己看成“科学理论”,无论是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或是科学之下的科学亚种,就都是不适当、有违哲学本性的行为了。今天的问题是,需要克服任何把哲学非哲学化的倾向,不论是神学化的倾向还是科学化的倾向,这样才能保持并发挥哲学自身固有的本性、职能、价值和功用。
所谓克服哲学的非哲学化倾向,更深入一步去说,这个任务的实质就是要使哲学更全面和更完整地去反映和把握人的本质,以便由此推动人类逐步做到如马克思所说,“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页)。从这一意义上说,任何非哲学化的倾向,包括神学化和科学化等倾向在内,都是对人的本质的某种片面化和抽象化理解的表现。克服哲学的非哲学化倾向,其实就是当今时代人们所倡导的“人文精神”的实质和内涵。
我们在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完成的是克服哲学神学化倾向的任务,那时以来,还遗留下消除哲学科学化倾向的任务有待完成。要实现这一任务,就要从真理标准问题深入真理自身的实质和本性问题展开讨论。现在已到了应该把这个问题提上研究日程的时候了。
四 克服直观认识理论局限
现在谈第二个情况。马克思本来已为我们走出狭隘的科学理性框架、克服直观认识理论的局限,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和方法基础,这就是马克思确立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然而遗憾的是,从原苏联学者起始包括我们在一个长时期都并没有认识这点,我们面对珍贵的宝藏,却不知怎样去派它的用场,以致使它长期埋没发挥不出作用。
过去,我们虽然承认“生活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应该说我们并没有认真和彻底地去贯彻这点。实践在教科书中仅仅被安插在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位置上,我们以为这个最终审判官的位置是具有最高权力的位置。可是这样一来,就使它只有在认识和真理既经形成之后才能行使职权和发挥作用。而在认识本性和真理本性的阐释中,我们沿用的仍然是直观认识论的观点,从摹写论去理解认识本性,从客观性去说明真理的本性。认识和真理的本性既然已经定型,审判官在“秋后算账”中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呢!只能去为直观认识理论充任“轿夫”的作用,顶多也只是一票否决权的作用。由于我们没有改变认识的直观本性,却又要求实践去进行验证,关于怎样从实验去检验认识与对象符合与否的问题就成为一个观题,我们很难说得清楚,人们也总要提出这样那样的疑问,如效果如何证明符合,真理“标准”究竟是实践还是客观事物等等问题就是由此生发出来的。
按照这样的理解,以往我们所讲的“真理”,实际不过是客观存在、客观对象、客观本性的一种“代号”;因而“服从真理”在我们的哲学中也就变成只是去顺应存在的客观事物、服从既定的先在本性。这里体现的原则,同200年前被马克思批评为直观认识论的原则,如霍尔巴赫所说:“人是自然的产物,存在于自然之中,服从自然的法则,不能超越自然,就是在思维中也不能走出自然;人的精神想冲到有形的世界范围之外乃是徒然的空想”,于是他呼吁“呵,人呵!……放弃那些空洞的希望……让我们服从必然罢……让我们听命于自然……顺着自然为你划就的必然的道路放心地走去吧……”(《自然的体系》上卷,第10、315页)有什么差别、能有多大差别?它怎能与马克思创立的实践观点以及由此决定的认识理论相容呢?
如果我们把认识真正放到了实践基础上,把它理解为实践活动的一个环节,那么,认识本性以及真理本性所表现的首先就应当是实践的本性。实践本性是一种创造活动的本性。从这一意义说,人的认识活动就应看作是感性实践的一种理性预演活动,看作是先行于感性实践的“精神实践活动”。它决不仅仅是顺应、认同、表象、摹写既定对象的活动。从这种观点去认识,人所追求的真理,在它身上所体现的统一性就决不只是单纯趋向客观性的那种客体本有的统一性,而应是以人的方式所建立的人与客观、人与对象、人与世界的新的更高的统一性,这样的真理必然是体现着人的理想和追求的真善美的统一体。
这两种情况说明,我们沿袭的传统真理观念必须实行根本变革,这既是当今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彻底坚持和贯彻马克思的实践观点的需要。
真理观和价值观是哲学理论中最富敏感性、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部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适应时代、历史和实践所发生的变化,我们对价值观的问题比较注重,展开了广泛地讨论,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这是非常必要的。价值观与真理观在哲学理论中紧密相联、很难拆开。如果说价值观涉及的是人们的思想和追求问题,那么真理观则是关联人们更高和更深层次的理论信仰和信念问题。不改变传统的真理观,关于价值观的许多问题都不可能彻底解决。随着价值观问题讨论的日益深入,现在已把真理观的问题提上日程,需要我们去展开研究和讨论。这种研究对当前重建人们的思想和信仰具有十分重要和迫切的意义。
本文主要是提出问题,意在推动思考和研究,至于一些问题的具体答案,只能在讨论中由大家去共同作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