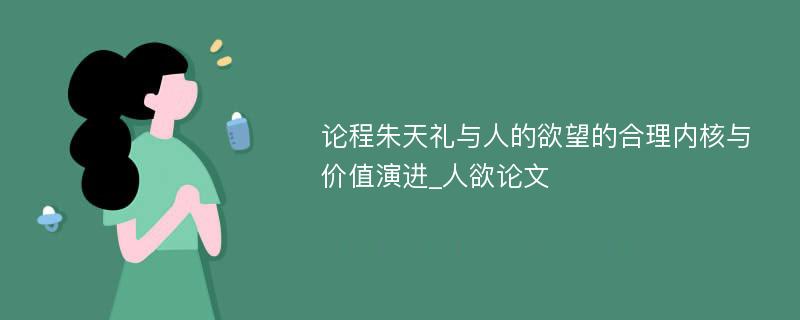
论程、朱天理、人欲之辨的合理内核及其价值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理论文,内核论文,人欲论文,价值论文,论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在程、朱的观念体系中,人的一切正常合理的生理欲求因符合天理而得到肯定,超过正常合理之度的欲求即为人欲,亦即私欲,必须加以摈除。因此,天理与人欲之间的对立实质是公与私、正与邪的对立,就形而上的层面言之,“存天理、灭人欲”是一个包含合理内核的命题。然而,在实践层面,程、朱将名教纲常等伦理要求视为天理的真实内容和永恒表现形式,从而使这一极富合理性的命题变成吃人、泯灭人性的工具。从道德到非道德、合理到不合理的这一价值嬗变,并非程、朱个人历史和思维的局限性使然,而是整个儒家理论体系固有缺陷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关键词 程颢 程颐 朱熹 程朱理学 天理 人欲
天理、人欲之辨是程(程颢、程颐)、朱(朱熹)理学的核心内容,对其能否作出准确、全面的理解和把握,直接关系到对程、朱理学的总体评价。本文拟就此一述己见,妥当与否,望不吝赐教。
一
在二程和朱熹的观念体系中,天理和人欲是一对正相对立的范畴,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构成了人这一物类所特有的存在方式,而矛盾斗争的结果则使人的生命活动具有了不同的价值和意义。
在程、朱看来,天理、人欲之间矛盾、对立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生人之初。依照他们对万物生成的解释,万物之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理和气。理是“生物之本”,气是“生物之具”,理、气相合始成万物。人作为万物中之一物,它的生成也是如此。单纯的“理”不可能成就有血有肉、活生生的现实的人,必须有“气”作为它的载体,作为它的挂搭、安顿之所,也即是说,必须理、气相合才能成人。程、朱认为,所谓“人欲”正是产生于这个理、气相合而成人的过程之中。如朱熹说:“盖缘这个天理须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朱子语类》卷一三)由此说来,人欲的产生,天理、人欲的对立归根到底是根源于气禀。因为天理是本来就有的,而人欲则是禀气而后生的。有了气禀,才有了人欲,才有了天理和人欲的对立。当然,在程、朱看来,如果禀气清明纯粹,则自然是浑然天理而全无人欲之害。然而,天理的安顿不可能总是恰好,真正恰好的只有极少数“生而知之”的圣人,而就大多数人的气质来说,并不是天理的理想安顿之所。此正所谓:“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所以从总体上讲,“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这似乎正应了那句著名的格言;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禽兽。
天理和人欲既然是敌对的双方,那么它们之间争战的激烈程度和残酷性也是可想而知的。二程把二者形象地比喻为交战中的两人,说:“有人胸中常若有两人焉,欲为善,如有恶以为之间;欲为不善,又若有羞恶之心者,……此正交战之验也。”(《二程遗书》卷二下)一人代表天理,是善;一人代表人欲,是恶。欲为善,则有恶从中作梗;欲为不善,则有善在背后牵制。天理和人欲就是这样互相对立,决不相随。朱熹的揭示和描述则较二程更为简捷明了。他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天理人欲,无硬定底界,此是两界分上功夫。这边功夫多,那边不到占过来。若这边功夫少,那边必侵过来。”(《朱子语类》卷一三)在朱熹看来,天理和人欲之间如同两军交战,势不两立,彼此消长。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天理存,人欲就亡,人欲胜,天理就灭。二者之间决没有中立而不进退的道理。所以朱熹认为,对于人欲,决不可姑息迁就,要“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之”,克得一分人欲,便就复得一分天理。只要立定脚跟,坚韧不拔,终有取胜之时。此即所谓:“存天理,灭人欲。”
二
说起“存天理,灭人欲”,有一个问题在此必须分辨清楚,即程、朱所谓“人欲”的内涵到底指的是什么?这是我们正确评价程、朱天理、人欲之辨的关键所在。对此,现代人常常习惯性地或者想当然地把这一概念直接诠译、转换成“人的欲望”一词,把它看作是对人的自然属性的称谓。然而事实上,相对于程、朱的原意来说,这一理解实在带有很大的偏差。在此,我们不妨先看看程、朱本人的表述。《二程遗书》卷一八说:“且譬如椅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温暖,无所不为,然后夺之于君,夺之于父,此是趋利之弊也。利只是一个利,只为人用的别。”“利”即“欲”也。二程认为,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是人皆有之、不可或无的天性,它本身没有什么不好,因此,对于它我们只可称之为“利”或“欲”,而不可称之为“人欲”。因为“人欲”只是不好,只是恶,它是趋利之弊、求欲之过,也即是对于“利”的过分要求,这种要求已不满足于自身在社会伦理规范(与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限度内的合理所得,而只从“自家躯壳上头起意”,不顾他人的合理利益,强取豪夺,损人利己。这样,原本正当的“欲”便就流而为不合理的“人欲”了。所以,同样是“利”,同样是“欲”,用得好与不好、当与不当,性质大不相同。用得不好、用得不当,就是“人欲”。那么,用得好、用得当呢?朱熹说,那就是“天理”。《朱子语类》卷一三载云:“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朱子)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显然,朱熹与二程是一脉相承的,他也认为,像饥而欲食、渴而欲饮之类是人所不能无的,因此,对人来说,欲望本身存在的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问题的关键只在于欲望的限度,在于对欲望的追求是否已经超过了合理的界限,是否损害了别人的正当利益。例如,同是饮食之欲,在界限之内的就属天理,在界限之外的则是人欲。对于天理、人欲之间的这种微妙的不离不杂的关系,朱熹沿用了南宋学者胡宏(二程的再传弟子)的一种说法,称之为“同行而异情”。他说:“如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佚,圣人与常人皆如此,是同行也。然圣人之情不溺于此,所以与常人异耳。”(《朱子语类》卷一○一)也即是说,同是行口目耳鼻四肢之欲,但圣人和一般人不同,圣人心中始终有个尺度,以尺度为准,只求合理;而一般人则不然,常沉溺欲中而不能自拔,伦理道德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就是个人的一己私利能否得到满足,所以其行止情状自然与圣人迥异。再比如,同是好乐、好勇、好货、好色之主,如果能“循理而公于天下”,就是天理;如果“纵欲而私于一己”,便就是人欲。由此可见,天理、人欲虽然性质正好相反,然而却是彼此联结在一起的,或是天理,或为人欲,关键只在一个度,在度以内是天理,一不留心跨越这个度便就成了人欲了。此正所谓:“天理人欲,几微之间。”所以朱熹常把人欲比做贼,乔装打扮,神出鬼没,人们必须时时提防、细心体察,做到有纤毫人欲,便能识得破,捉得住,否则必生错乱乃至是非混淆、黑白颠倒。
勿需再赘,由以上的阐述中,我们不难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第一,决不可把程、朱所谓的“人欲”等同于今天一般所谓的“欲”。在程、朱的观念体系中,“人欲”一词有着特定的内涵,即专指“私欲”。“欲”包括“人欲”,但不等同于“人欲”,“欲”中还有“天理”。因此,对程、朱而言,所谓“灭人欲”,并不是要从根本上灭绝人的一切生理欲望——因为它不该灭也灭不掉,而只是要通过对过分的、不正当的欲求的摈除,把人人生而具有、不可或无的生理需求恢复到合理的界限之内。正因为如此,所以朱熹反对笼统地谈“禁欲”、“无欲”,他认为佛教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在于“欲驱除物累,至不分善恶,皆欲埽尽”。他讥讽佛教的“无欲”主张是“终日吃饭,却道不曾咬着一粒米;满身著衣,却道不曾挂着一条丝”,荒谬可笑。由此可见,程、朱对“人欲”的界定显然不同于今天我们于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一概念时所赋予给它的内涵。对此,如果缺乏明辨,无疑会对我们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程、朱的天理、人欲之辨造成很大的障碍。
第二,与第一点相关联,决不可把“天理”和“人欲”的对立归结为“理”和“欲”的对立。因为“欲”和“人欲”在程、朱这里并不是内涵和外延相等的概念,亦即二者并不是一个东西。程、朱认为,天理和人欲之间的对立实质上是公与私、正与邪的对立。朱熹说:“人只有一个公私,天下只有一个邪正。将天下正大底道理去处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处之,便私。”(《朱子语类》卷一三)而公正即是善,私邪即是恶。所以,天理和人欲的对峙与交战归根到底是一场善与恶之间的持久较量。
明确以上两点之后,我们再来反观程、朱的天理、人欲之辨就会发现,在形而上的层面,或者说从原理上讲,“存天理、灭人欲”并非是一个不合理的命题。天理只是善,当然要存;人欲只是恶,不能不灭。天理胜,则成其所以为人;人欲胜,则与禽兽无异。所以二程义正辞严地说:“存不得天理,更做甚人!”朱熹也是语重心长、严辞以告:“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其实,程、朱千言万语,其良苦用心也正在于此。
三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存天理、灭人欲”作为一般命题的这种合理性却最终被程、朱所赋予给它的具体历史内容湮没和窒息了。本来,名教三纲作为一套与君主专制制度相适应的价值规范,是一种最缺乏人性、最没有理想性的伦理要求,因而是应该被超越和否定的。但是,历史和思维的局限性却使程、朱偏偏把这种需要被超越、注定要死亡的伦理看成了“天理”的真实内容和永恒的表现形式。因此,在程、朱这里,名教三纲就是天理自然,不得僭越,不容亵渎。这样一来,问题就严重了。君纲、父纲自不必说,单是“夫为妻纲”一条,在历史上就不知枉送了多少人的青春性命。在程、朱眼里,男尊女卑是“常理”,夫唱妇随、唯命是从是“常道”。男人可以休妻再娶,而女人则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即便是寡妇,即便是贫穷无托、有冻馁之忧者,也决不可再嫁。为什么?因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下)。正因为如此,所以朱熹大力提倡所谓“节烈”。据朱熹曾任知州的漳州《府志》记载,仅漳州一地,自宋以来一直到太平军入漳之前,就有“烈女”4498名。其中有所谓“节烈”、“节孝”、“节德”、“贞节”、“苦节”;有所谓“婆媳同孀”、“三世苦节”、“五世节妇”;有所谓“夫亡投井”、“自缢”、“绝粒”等等。凄凄惨惨,令人不寒而栗。所以,清代思想家戴震的一句“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的控诉,引发了后世人的普遍共鸣。“存天理、灭人欲”这一原本极富合理性的命题,到头来却变成了杀人、吃人、泯灭人性的工具,实在是可悲、可叹!
不过,说到底,程、朱的局限性并不仅仅是程、朱个人的,而是属于整个儒家的。程、朱天理、人欲之辨在操作层面上所表现出来的对人的权利与尊严的无知和冷漠,恰恰是儒家理论体系固有缺陷所必然导致的结果。纵观儒学发展的历史,人的权利对儒家学者们来说,一直是一个懵然无觉的思维盲点。在他们的观念中,只有人格的平等,而无人权的平等。因此,在儒家的理论和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极不相称的情形贯穿始终:一方面,他们高举“人皆可以为尧舜”、“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旗帜,为唤醒人性的自觉、人格的尊严和平等而高歌呐喊;另一方面,他们又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卫道士,为不平等的现实政治提供了一整套冠冕堂皇的理论说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诚然,我们并不怀疑,从主观愿望上讲,以仁为己任的儒者们的一切努力,都旨在使人性的光辉和人格的尊严在现实中得以充分地展现和真正地树立起来,然而,问题的关键却在于,没有人权的平等,人格的平等便失去了真实的基础,到头来,它要么被悬置挂空、胶窒固塞于主观之内而不能广被天下、博施济众,要么则向下坠落,扭曲变质,最终沦为一种戕害人性、自我陶醉的精神鸦片。具体到程、朱的天理、人欲之辨来说,他们虽然能够在内涵上对“存天理、灭人欲”作出圆融无碍的解释,从而确立起这一命题在逻辑上或理论上的合理性,但在外延上,在实践层面上,权利平等观念的缺乏却使他们无法把这种合理性真正落实下来。在他们所倡导的三纲伦理中,建基于权利不平等基础上的不合理要求被当成了“天理”而加以颂扬和维护,而属于人的基本权利范畴的合理需要则被当成了“人欲”而要求人们“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于是乎,在他们这里,善与恶之间、道德与非道德之间便失去了一以贯之的价值判准而变得似是而非、价值混乱。其实,从历史上看,由儒家理论上的这一盲点或局限所造成的价值失准,一直在影响、制约着历代儒者去进行公正合理的道德判断,程、朱所谓“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判断是如此,就是孔子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判断也同样是如此(参见拙作《论墨家伦理观的真髓及其价值——从儒、墨比较谈起》,《齐鲁学刊》1991年第三期)。从道德到非道德,从合理到不合理,这种价值上的嬗变,显然不是儒者们的主观所愿,但也正因为如此,对此一过程的懵然不知和不觉,才恰恰是真正可悲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