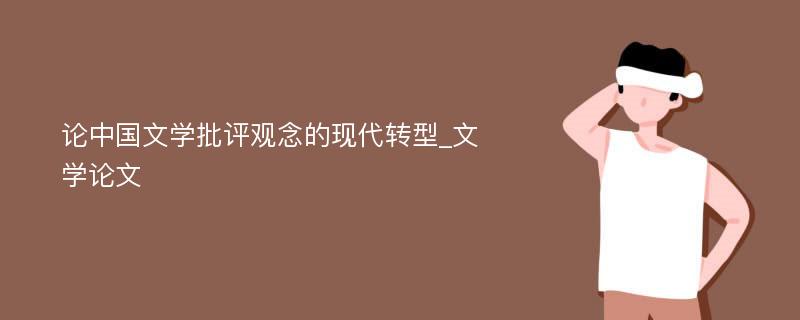
论中国文学批评观念的现代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中国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舶来品的“文学批评”一词本身所包含的文学观念及其内涵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观念有着明显的差异,传统的“诗文评”如何转变成了今天的文学批评?对于中国古代文论而言,有“诗文评”是否就等于有文学批评学?关于文学批评的本体、性质、标准、目的、功能、特征、作用等问题的理解在近现代之交的中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或转型?这些问题,对寻求中国文学批评的科学建构和创新发展而言,都是我们必须正视的。
一、契机:批评的自我反思
中国文学批评观念的现代转型首先表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本身的反思上。这是认识论上的深化,是转型发生的首要契机。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强调整体直观式的感觉判断,即对整个艺术作品的个性、精神风貌作整体直觉把握,作辨味批评,用简略而又精确的审美术语或概念对艺术作品的美感特点加以描述,力求把握创作主体的“机心”,而力图避免破坏艺术作品传达给接受者的美感趣味,而且,评价作品时往往不作逻辑分析,而是依赖于评论主体的丰富想象力和审美经验,在直观感悟中求得一种整体性把握。中国批评家往往疏于作进一步的知性分析,不是“不能说”,而是点到为止——“不必说”,条分缕析式的肢解在古人看来只会破坏美感趣味。这种批评方式有别于西方注重知性分析、注重逻辑演绎与推理的批评方式,使得中国古代的艺术批评与鉴赏具有强烈的艺术意味。这种对待文学批评的基本态度在近代以来仍然得到承续,比如,佚名的《读新小说法》一文就是典型的一例。这篇文章称新小说宜作“史”、“子”、“志”、“经”来读,又认为没有格致学、生理学、地理学等知识结构不可以读新小说。至于新小说何以宜作史、志、子、经等类型的书来读?文章缺少理论的绵密分析;对于缺少格致学、生理学、地理学等知识结构不能读的原因也缺少逻辑剖析;文末最后一段充斥的是各种判断句,这种判断的标准是什么,亦缺少由辨到证的基本分析过程,它要求的只是高明的感悟能力。而这种批评在进入民初以来,通过西方文学批评的对照,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或反思。如朱希祖在《文学论》中就从学科的角度来批评传统的文学观念说:“吾国之论文学者,往往以文字为准,骈散有争,文辞有争,皆不离乎此域;而文学之所以与其他学科并立,具有独立之资格,极深之基础,与其巨大之作用,美妙之精神,则置而不论。故文学之观念,往往浑而不析,偏而不全。”①
这种反思还渗透到对传统中国文学批评家的批评态度上。如傅斯年结合当时中国的剧评情形批评说,当时中国戏评界要么“不批评”,即或批评,也是“不在大处批评”,“少见过论到戏里情节通不通,思想是不是,言语合不合的”,结果“评戏变成捧角了”。② 在郭沫若眼中,文学批评界充斥的是“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鄙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视文艺批评为广告用具”。③ 这些人“不是做些无理的谩骂,便是献些不虞的赞辞”。④ 茅盾也认为:“我国素无批评主义,月旦既无不易之标准,故好感多成于一人之私见。”《〈小说月报〉改革宣言》对于传统中国文学批评家的态度,一些批评家还提出了自己的改进主张。如郭沫若就提出正确的批评态度应该是:“不要匿名,不要怕事,不要顾情面,不要放暗箭。我们要大胆虚心佛情铁面,堂堂正正地作个投炸弹的健儿!”⑤
这些反思甚至渗透到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术研究中。在郑振铎看来,传统文学批评中的文体分类意识就大有问题,像《离骚草木疏》附在集部,诗话夹杂在别集和总集中,理学家的性理之文与朴学家的考证之文列入文学的,比比皆是。⑥ 基于此,研究者们把改进中国文学批评的途径投向了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如朱光潜在《中国文学上未开辟的领土》一文中就提出要“把研究西方文学所得的教训,用来在中国文学上开辟新境”⑦ 以重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设想。
这些反思促使当时人们把眼光投向西方文学批评。如茅盾曾坦陈:“我们现在讲文学批评,无非是把西洋的学说搬过来,向民众宣传。”⑧ 朱自清在《诗文评的发展》一文中说得更直接:“若没有‘文学批评’这个新意念、新名字的输入,若不是一般人已经能够郑重的接受这个新意念,目下还是谈不到任何中国文学批评史的。”⑨
二、向路:批评观念转型的展开
在西方文学批评理念的影响下,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观念的转型与变化表现得越来越清晰。这种转型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清晰看出:
(一)批评义界的嬗变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对“批评”一词的界定是非常宽泛的,称谓也不尽相同。大致有如下几种:(1)“观”。它带有文学接受活动中的“欣赏”的含义,但又并非是一般的欣赏,还带有研究、审察、评论之义。如春秋时代有所谓的“观乐”、“观舞”。《左传》中记载的季札观乐活动以及观乐后所发的感叹及评述,实际是一种音乐艺术批评。刘勰在《知音》篇中提出的著名的“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要求从文学批评过程的各个环节和批评实践的具体问题出发,对许多文学问题作出评论,实际上是确立了六种文学批评标准。(2)“说”。如《孟子·万章上》中所提到的“说诗”。这其中,“说”是解说、诠释,实际上也就是诗歌批评。(3)“诂”。如汉代董仲舒有著名的“诗无达诂”论。诂,表面看有用今言释古言之义,实际也包含解释、评论之义。(4)“评”。它来自东汉以降的人物品鉴活动(如《世说新语》中就曾记录了许多“论者”对人物的“评”语),并逐渐从政治、道德领域泛化到整个文化领域,也进入到文艺批评领域。(5)“品”。“品”作为批评概念的确立,首归钟嵘诗歌批评著作《诗品》。《诗品》以纯艺术鉴赏态度三品论诗,置品级,辨流派,溯渊源,改变了传统的以史证诗、以意逆志、注重真善而忽视审美的批评方法,开创了以审美鉴赏为中心的批评方法之先河。唐代司空图也曾以二十四品论诗的风格,创立了独具风貌的诗歌风格美学。清代袁枚则有《续诗品》32首以传世。刘熙载的《艺概》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被看作集诗品、文品、赋品、词品、曲品、书品于一炉的品评大制。到明代,随着戏曲的兴盛,戏曲批评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像吕天成的《曲品》、祁彪佳的《远山堂剧品》和《远山堂曲品》都是名作。(6)“批”、“批点”、“批评”。它们的出现与戏曲、小说等文体的兴盛密切相关,“批评”、“批点”、“评点”成为文学批评的代名词,像李卓吾、金圣叹都是有名的评点大家。(7)“笺”。“笺”既是“评”,又是“解”,即解释。“笺”与“注”不同,按清代浦起龙《读杜心解·发凡》的说法,“注与解体各不同:注者其事辞,解者其神吻也。神吻由事辞而出,事辞以神吻为准。”“解之为道,先篇义,次节义,次语义。语失而节紊,节紊而篇晦;紊斯舛,晦斯畔矣。而说者每喜摘一句两句,甚或一两字,别出新论”;“注列句下,解附篇末”。浦起龙所说之“解”也就是“笺”。
从古代文学批评对“批评”一词的义界与称谓看,其涵义往往是多义、模糊甚至歧义的,同时涉及学科领域的交叉。如“品”字,往往在艺术中的绘画、音乐、文学、戏曲等各门类中通用;“诂”、“笺”则同历史学、语言学等领域有密切关联,因而缺乏从文学领域自身对文学批评进行的准确界定。当西方文学理论传入中国后,对此进行甄别、比较或者重新解释,似乎就成了当务之急。而这样的工作我们在民初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述中可以大量看到。比如,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在引述西方文学批评定义的基础上对“文学批评”作了界定。他说:“诗文之有评论,自刘勰、钟嵘以来,为书众矣,顾或研究文体之源流,或第作者之甲乙,为例各殊,莫识准的。则以对于‘批评’一词,未能确认其意义也。考远西学者言‘批评’之涵义有五:指正,一也;赞美,二也;判断,三也;比较及分类,四也;鉴赏,五也。若夫批评文学,则考验文学作品之性质及其形式之学术也。”⑩ 罗根泽也曾对“文学批评”一词作过较为严密的考辨。他认为“文学批评”是英文literary criticism的译语。criticism的原意为裁判,后来冠以literary为文学裁判,又由文学裁判引申到文学裁判的理论及文学的理论。文学裁判的理论就是批评原理,或者说是批评理论。所以狭义的文学批评就是文学裁判,广义的文学批评,则于文学裁判以外,还有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如果说“文学裁判的理论”这一内涵来自于西方,那么他对广义的文学批评的性质的认识则来自于他对中国文学批评特质的认识。他认为对“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必需采取广义,否则就不是真的‘中国文学批评’。”(11) 在罗根泽看来,中国文学批评本来就是广义的,侧重文学理论,不侧重文学裁判,其原因是:从批评著作看,刘勰的《文心雕龙》“其目的不在裁判他人的作品”,而是“论文叙笔”,讲明“文之枢纽”,其他的文学批评书,也大半“侧重指导未来文学,不侧重裁判过去文学”;从批评主体看,“中国的批评,大都是作家的反串,并没有多少批评专家。作家的反串,当然要侧重理论的建设,不侧重文学的裁判”;(12) 陈、罗二人的界定,都带有明显的西学痕迹。对此,朱自清就“文学批评”与“诗文评”之间的关系坦陈了他的看法:“‘文学批评’是一个译名。我们称为‘诗文评’的,与文学批评可以相当,虽然未必完全一致。我们的诗文评有它自己的发展;现在通称为‘文学批评’,因为这个名词清楚些,确切些,尤其郑重些。”在朱自清看来,“文学批评”这一术语的作用就在于它是一把“明镜”,只有靠这把明镜,才能“照清楚诗文评的面目”,因为,“诗文评里有一部分与文学批评无干,得清算出去”,而这就是朱自清所说的“将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在这一大前提下,再“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才能“将我们的材料跟那外来意念(此外来意念即西方‘文学批评’——笔者按)打成一片,才能处处抓住要领”。(13)
(二)批评性质的认识转变
关于文学批评的性质问题,西方文论史上有种种不同说法。其论争的焦点,按韦勒克的说法,就是“批评到底是一门艺术还是一门科学”。(14) 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实践看,中国人更倾向把批评看作一门艺术,这不仅仅表现在古代文学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更注重批评的灵感、直觉特点,更注重一种整体把握,其批评活动中往往出现大量整体感觉式的审美术语如风神、风骨,韵致、韵味,生趣、生意,气象、气韵,精气、灵气等等,还表现在古代批评家在其批评实践中常常把价值判断作为批评的重点,当然这种判断首先往往是同政治教化和需要相联系的(其次才涉及艺术形式问题),而这种价值判断也不像西方文艺批评那样具有理论上的逻辑性和严密性,更缺少西方文学批评在传达实践中的规范化、系统化、精细化以及细密的知性分析的特点。这一弊端在近现代以来,由于西方文学批评的引入,开始遭到国人的不断质疑。这些质疑不仅导致了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对文学批评性质的诸多反思,也形成了关于文学批评性质的不同见解。
1.文学批评具有科学性
俄国诗人普希金曾认为,批评是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杜勃罗留波夫也指出:“批评的第一个工作(在我们的意义上说)——发现事实,指出事实——就能够十分顺利地、不致引人反感地完成了。接着另一个工作——根据事实进行评判。”(15) 这些都是对文学批评的科学性质的肯认。这种看法对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学者有极大的影响。它首先反映在译介工作之中。比如刘文翮就曾说自己“往年从梅光迪先生学《文学概论》、得温采司特(即Winchester,现译作‘温彻斯特’——笔者按)之《文学评论之原理》。细阅一通,觉其析理周致、主张中和、不滥许新派之主张、不固主先哲之言论。判析今昔有类明决法官,未尝偏听,亦未尝武断也。”(16) 温彻斯特的文学批评著作翻译到中国之后,对中国文学批评家影响极大,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因为他的著作具有一种与传统中国文学批评极为不同的科学性、客观性。景昌极、钱新在温彻斯特所著《文学评论之原理》一书“序言”中就其阅读温氏著作细致描述了自己对中西文学理论著作的不同感受,称其极喜爱温彻斯特的原因就在于它具有“擘肌分理,惟务折衷,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的特点,是一种科学的批评。
这种影响也见之于中国学者对自身的反思与批评中。如词学家龙榆生就曾批评说,中国人治批评之学,往往“但凭主观之见解。又或别有用意,强人就我,往往厚诬古人”,因此,“必须抱定客观态度,详考作家之身世关系,与一时风尚之所趋,以推求其作风转变之由,与其利病得失之所在。不容偏执‘我见’,以掩前人之真面目,而迷误来者。”(17) 从龙榆生批评的立论角度看,针对的主要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但凭主观之见解”而缺少科学的、公允的、客观的批评态度与方法。又如,唐文治对近代陈衍的文学批评特点大加赞赏,他认为陈衍解析文学作品,“譬诸科学家分析法、解剖法,悉中腠理,物无遁形,何其精而入神也”。(18) 而在文学论争盛行的现代文学领域中,这种坚持文学批评科学性质的观点也开始深入人心。比如,在创造社作家眼中,艺术与科学并不是绝对相反的,一个文艺家也应研究科学,减少其不精确的缺点。在他们看来,科学方法的参与对于改进中国文学“批评能力未充实”(19) 的现状大有裨益。由此,他们把文学批评的基本性质与科学的客观性、反思性特点紧密联系起来,如成仿吾在《作者与批评家》中说:“如果我们想肯定作者的一切,只评判他的成绩如何,或想由作品中发见它的意义,那便非没入创作的氛围气中不行,也要这样才能不负作者。批评与赏玩不同点,绝不是一个不没入一个没入,而在批评家于赏玩时能为不断的反省,赏玩家却只是一味赏玩。”(20)
值得注意的是,对文学批评的科学性的肯认,发展到30年代,还成了文学史著述一条重要的学术指标,比如王易在其《词曲史》“序言”中对其编撰意图就作过这样详细的说明:“以科学之成规,本史家之观察,具系统,明分数,整齐而剖解之,牢笼万有,兼师众长,为精密之研究,忠实之讨论,平正之判断……为谈艺家别开生面者。”(21)
2.批评即价值判断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十分重视价值判断,传统的“文以载道”说是这种观念的主要理论支持,“文德”说也从创作主体修养与文学表达之间关系的角度显示了文学批评中的价值判断(德为文之基础,文为德之外化,文的作用在于劝德、教化)。除了这些在内容上侧重于以政治教化、德行、人格来评判文学作品价值之外,另一种价值评判主要是审美价值的判断。比如滋味、情味等是有关作品审美韵味的艺术价值判断;“文采”、“华采”、“壮采”、“神采”等是关于文学艺术作品形式要素或形式美感的价值判断;“韵致”、“风致”等是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关于文艺作品形式美感或审美风貌方面的价值判断;“微妙”、“高妙”等是对作者高明的艺术审美鉴赏和审美创造力的价值判断;“笔力”、“识力”、“魄力”等是对文艺创作活动中主体的审美理解与分析能力、审美传达能力等的价值判断;“浓”、“淡”、“雅”、“丽”等是对作品艺术风格所作的审美价值判断。诸如此类,都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价值判断主要有两种,前者主要关乎政教内容,后者则涉及作品的艺术性及形式问题。这两种价值判断也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政教中心论传统和审美中心论两大传统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局面。
近代以来,把文学批评的性质视为一种价值判断的倾向在批评实践中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价值判断由于西学的引入,增添了新的内容。
首先是关于文体本身的价值判断,如关于小说和戏曲的价值判断较之中国古代视为小“道”就有了明显的改观。蠡勺居士就批评了过去轻视小说的观念,他说:“若夫小说则妆点雕饰,遂成奇观,嬉笑怒骂,无非至文,使人注目视之,倾耳听之,而不觉其津津甚有味,孳孳然而不厌也,则其感人也必易,而其入人也必深矣。谁谓小说为小道哉?”(22) 徐念慈更是认为小说“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23)“是为小说之进步,而使普通社会,亦敦促而进步。则小说者,诚是占文学界之最上乘。”(24) 关于戏曲的作用,近代文学批评家也给了极高评价。(25) 更有论者宣称“戏剧之效力,影响于社会较小说尤大”,原因在于“戏剧者,一有声有色之小说也”。(26)
其次是关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二者价值谁高谁低的判断。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如诗话就被看作“以资闲谈”之物,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就说他作诗话乃是“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像文话、曲话、词话等等大都也是作如是观。到了近代,人们开始发现,文学批评也是一种需要极高禀赋、学识的创造性工作。譬如定一就指出:“良小说得良批评而价值益增,此其故宜人人知之。然良小说固不易得,乃若良批评,则尤为难能而可贵者也。金圣叹曰:‘今人不会读书。’吾亦谓必如圣叹,方是真会读书人。”(27) 好的批评可以使作品的价值得到更充分的展现。如邱炜在《菽园赘谈·金圣叹批小说说》中就说:“明末山人名士,得有钟伯敬、李卓吾辈,竞为批评小说之举……千古小说之灵机,至是乃大畅焉。”(28)
到了现代,文学批评的独立价值已为多数现代批评家们清醒地认识到。如陈嘏在介绍勃兰兑斯的文学批评思想时特别指出:“中国现在,文艺创作固然要紧,但文艺批评更来得要紧。……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上没有位置,世界文学对于中国文学,也一点不生影响。这全然是文艺批评不发达的缘故,没有健全的文艺批评,不能把世界思潮引到本国来,就是本国有了几个创作天才,也很容易淹没的。”(29) 批评史家郭绍虞则结合中国文学现实指出,文学的发达“不仅在创作一方面,更须赖有正确忠实的批评者”,“中国文学正在筚路蓝缕之时,创作方面固须注重,批评方面亦不可忽,为中国文学的前途计,对于光明的指导者,其渴仰的希望为何如!”(30) 对批评之独立品格的殷殷期盼之情溢于言表。
3.批评即解释
在现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将文学批评的性质视作一种解释性活动的观点是相当普遍的,像韦勒克的《近年来文学批评中的科学、伪科学和直觉》、M.H.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术语汇编》都把批评界说为与文学作品的解释、分类、分析、评价有关的研究。在英美新批评家和结构主义批评家那里,这种观点表现得尤其突出,克林思·布鲁克斯的《形式主义批评家》、威廉·K.维姆萨特的《具体普遍性》、I.A.瑞恰兹的《文学批评原理》、罗兰·巴特的《什么是批评》、茨维坦·托多洛夫的《批评的批评》等论著都大致持上述观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考证法、笺注法也具有这种解释性特征,只是没有非常明确的理论上的阐述。近代以来,这种理论上的阐述也极少有人为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近现代之交的王国维的文学批评活动却以批评实践的方式凸现了文学批评的解释性。他的《红楼梦评论》在中国文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根据西方理论来深入、细致、系统和专门地解释了一部中国文学作品,虽然王氏文论思维模式的失误之处在于他设定某个先验的和既成的理论构架,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了单向的阐发,将《红楼梦》作了论证西方文论有效性的理论注脚。这种以先验的理论框架为标准的文艺解读方式,其生搬硬套、削足适履、牵强附会之处也颇为不少,但他的文学批评指向了一种对文学批评性质的肯认,即:文学批评并不是为了寻求文学家的“本意”、“本旨”的一种意义“还原”活动,更是一种意义“生成”的活动——一种解释活动。相比之前的小说理论家们的解释活动而言,王国维的解释活动不仅有理论模型的支持(叔本华的悲剧理论),使其批评获得了一种“理论深度”,而且使中国文艺批评由个人化的感性操作和索隐式的实证,转向某种具有“普遍有效性”的思想性论说,由此扩展了文艺批评的“总体空间”。到了现代,关于文学批评的解释性已有学者明确承认,如梁宗岱即为一例。他说:“……批评家的任务便是在作品里分辨,提取和阐发这种种原素。”(31)
4.批评即自我感觉的记录
古代中国人崇尚直觉思维方式,因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推崇品鉴、活参、点悟、玩味等印象式、感悟式评论,其批评写作往往用语玄妙,类比与典故运用较多,批评风貌上也常常以不落言筌、空灵含蓄为美,这使得整个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都带有印象主义批评的色彩。不过从理论上明确将批评的性质定义为批评家自我感觉或印象的记录的做法还非常少。在近代文学批评中,这种实践上大量运用而理论探讨却甚少的状况也一直保持下来。比如下面一则评论:
新出小说,花样甚多,骋秘抽妍,俱倾于美的方面,足为文界异采。因仿昔贤品诗之例,而为此品。
《银山女王》,如师挚《关雎》,洋洋盈耳。
《世界末日记》,如长康画人,传神阿堵。
《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如咀嚼哀梨,爽脆可口。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如牛渚燃犀,怪无遁影。
《孽海花》,如列子御风,凭虚浩浩。
《无名之英雄》,如僧繇画龙,点睛飞去。
《海底旅行》,如倒啖甘蔗,渐入佳境。
《女娲石》,如读《镜花缘》,每辟异境。
《剧盗遗嘱》,如鼓铸洪炉,克肖物状。
《美人黄鹤》,如曹霸画马,骨肉停匀。(32)
这则评论言辞优美,比喻繁多,重视的是个人阅读印象的传达,而不是理性的逻辑的分析。在近代文学批评中,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但当我们寻找这种批评的理论依据或基本解释时,却很难找到。这种状况到了20世纪后得到了明显的改变。特别是唯美主义和西方印象批评传入中国后,理论上的探讨较之近代不可同日而语。
在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中,视批评为印象或自我感觉的记录的这种看法是20世纪唯美主义和印象主义批评的主流看法。像王尔德、阿纳托尔·法郎士、勒美脱尔、瓦尔特·佩特等人都是这一理念的坚定支持者。这种将批评视为“试图用文字描述特定的作品或段落的能被感觉到的品质,表达作品从批评家那里直接得到的反应(或印象)”(M.H.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汇编》)的看法被茅盾、郭沫若、李健吾、林语堂等人所接受,并转变为一种理论上的思考。如郭沫若就强调:“批评没有一定的尺度。批评家都是以自己所得的感应在一种对象中求意义。”(33) 茅盾也说:“请不要误认文学批评家就是‘大主考’!批评一篇作品,不过是一个心地率直的读者喊出他从某作品所得的印象而已。”(34) 李健吾更主张批评是“个人的象征”,他认为真正的批评家“有他不可动摇的立论的观点,他有他一以贯之的精神。如若他不能代表一般的见解,至少他可以征象他一己的存在”。他明确指出:“什么是批评的标准?没有。如若有的话,不是别的,便是自我。”(35)
三、聚焦:批评本体的自觉
上述关于文学批评性质的讨论实际都在不同程度上聚焦到“批评本体为何”这一重大问题。本体意识是事物认识中最为重要的成分之一。按照人类意识发展的内在规律,本体论的探讨尚未出现之前,发生论或功能论层面的探讨往往更多,或者以批评实践本身来作出回答。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其自身实践中就不乏对批评本体的感性体验,甚至有相当多的批评家以其批评实践来回答这一问题。从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实际看,古代文学批评的本体论探讨主要是将对象局限于作品的一种释义学,即批评的主要工作就是释义。孔子开解经之先河,其《论语·述而》确立了崇奉经典、阐述经义“述而不作”的解经学的基本原则。这种观念构成了中国的学术批评与文学批评的“经学”传统。从汉代经学到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一以贯之,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学术或批评共同体,不仅具有形成公认的话语所要求的对于相关学科的来源广泛的文献积累,还在学术宗旨、理论预设、检验方式、批评理念、批评方法等诸多方面形成了一种以明古论今为主导倾向的严谨的实证学术范式和以精详考证为基础的学术或批评阐释系统。像先秦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解诗方法,两汉针对《诗经》和楚辞的解经式批评,特别是经学家们以“美刺言诗”的方法对《诗经》作断章取义的附会解说等,都是极为典型的代表。中国解释学从方法上讲,有疏,有义,或训诂,或正义,最后形成了两个基本的解经向路,如清代学者李兆洛在《养一斋文集·诒经堂读经解序》所说:“一曰专家,恪守一师之法,尺寸不敢违越,唐以前诸儒类然;一曰心得,通之以理、空所依傍,惟求乎己之所安,唐以后诸儒类然。”这两条向路就是所谓的“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这种观念从现代文学批评论的角度看,实际上就是视批评为解释的观念的反映。还有一种观念是将批评本体落脚到作家身上——作家本体论观念。这可以在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班固的《汉书·司马相如传》、王逸的《离骚经序》以及各种有关文学家的“赞”、“墓志铭”、“吊”、“传”等中看到,在这些文学批评中,批评者十分重视对作家身世经历和创作意图的关注,作家自身的遭际、生存环境等往往是批评家重点关注的对象,通过追寻作家身世来探究作家作品的原意,从而对作品作出解释与判断。将作品本身作为批评的核心的这样的一种批评本体论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也有呈现。如“摘句”批评法、小说与戏曲评点、金圣叹的形式批评等,虽然也关注作家本身,但眼光更多放在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审美技巧上。而把读者视为批评的本体的这种看法也常常见于批评家笔端。汉代董仲舒的“诗无达诂”论、清代谭献的“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的说法等等,都可以作为例证。不过批评实践本身与理论探讨本身仍然是有差别的。批评本体论的探讨意味着文学批评学的建立。这一点无论在中国古代还是近代,都是缺少自觉意识的。换言之,批评围绕文学构成一个回声区,它将作品中沉默的不确定的内部世界展示出来。有文学便有文学批评,这一点中西皆然,但对于中国古代文论而言,有文学批评是否就有文学批评学这一问题却鲜有论者论及,因此,茅盾批评说:“中国自来只有文学作品而没有文学批评论;文学的定义,文学的技术,在中国都不曾有过系统的说明。收在子部杂家里的一些论文的书,如《文心雕龙》之类,其实不是论文学,或文学技术的东西。”(36) 而当现代批评家接受了西方的理性思维和逻辑方法之后,这种关于批评本体论的探讨才进入到议事日程,也才有了上述关于批评性质的探讨与争鸣,虽然这些讨论以当代的眼光来看仍然失之肤浅与粗糙,但它依然是一种向现代文学批评理性思维寻求转变与对接的尝试与努力,其意义不可谓不大。即使像批评史家郭绍虞,虽也未曾对“文学批评”作过“义界”,但他认为“文学批评的转变,恒随文学上的演变为转移,而有时文学上的演化,又每因文学批评之影响而改变”,且“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联带的关系”,(37) 却也是关于文学批评本体论的探本之论。如果将眼光投向当代,我们就会发现近现代以来批评家的现代性努力的重要意义。像潘凯雄、蒋原伦、贺绍俊合著的《文学批评学》以及张荣冀的《文学批评学论稿》,都对批评的本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除了将20世纪西方批评方法融入中国传统的批评理论外,这两部著作在批评本体的研究上较之传统思维模式又前进了一步,如果没有近现代以来的有关探讨,很难设想这两部著作的成功。
更为重要的还在于,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传统“诗文评”向现代文学批评的转化与迈进,并非完全是西方强势文论强制同化的结果,而是中国本土文学批评在同化与顺应的运演结构中既把外部环境中新的因素纳入自身发展着的批评机体中,又不断顺应改变着的外部文化与批评环境以获得最大限度的批评适应力的运动过程的产物,它通过文学批评诸视域的调整,通过比较、认同、阐发、互释、互证、整合、重构、修正等诸多方式,以及对不同文化间差异性或不可通约性的深度追问,进入了更为广阔的批评自觉和现代转型中。
注释:
① 朱希祖:《文学论》,《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
② 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新青年》第5卷第4期,1918年。
③ 郭沫若:《海外归鸿》,《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1922年5月。
④ 郭沫若:《编辑余淡》,《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1922年11月。
⑤ 郭沫若:《海外归鸿》。
⑥ 郑振铎:《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文学旬刊》第51期,1922年。见《郑振铎全集》(第6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⑦ 朱光潜:《中国文学上未开辟的领土》,《东方杂志》第23卷11号,1926年6月。引自《朱光潜全集》(第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143页。
⑧ 茅盾:《“文学批评”管见一》,见《茅盾文艺杂论集》(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页。
⑨ 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文艺复兴》第1卷第6期,1946年7月。
⑩ 陈钟凡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1927年版,第7页。
(11) 罗根泽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中华书局,1962年新1版,第8页。
(12) 罗根泽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一),第14页。
(13) 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
(14) R.韦勒克著:《批评的诸种观念》,丁泓等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15) 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449页。
(16) 刘文翮:《介绍〈文学评论之原理〉》,《文哲学报》第3期,1923年3月。
(17) 龙榆生:《词学研究之商榷》,《词学季刊》1卷4号,1934年4月。
(18) 唐文治:《石遗室丛书总序》,见《陈石遗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60页。
(19) 郭沫若:《编辑余谈》。
(20) 《成仿吾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页。
(21) 王易著:《词曲史》(序言),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22) 蠡勺居士:《昕夕闲谈小叙》,《瀛寰琐记》第3期,1872年。
(23) 徐念慈:《小说林缘起》,《小说林》1907年第1期。
(24) 觉我(徐念慈):《余之小说观》,《小说林》1908年第10期。
(25) 陈佩忍:《论戏剧之有益》,《二十世纪大舞台》第1期,1904年9月。
(26) 铁:《铁瓮烬馀》,《小说林》1908年第12期。
(27) 定一:《小说丛话》,见《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4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
(28) 邱炜:《客云庐小说话》卷一,见《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4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
(29) 陈嘏:《布兰兑司(勃兰兑斯)》,《东方杂志》第17卷第5号,1920年3月10日。
(30) 郭绍虞:《俄国美论与其文艺》,《小说日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1921年9月。
(31) 梁宗岱:《谈诗》,见《梁宗岱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32) 邱炜:《新小说品》,《客云庐小说话》卷四,见《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4卷)。
(33) 郭沫若:《批评与梦》,见《文艺论集》(汇校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页。
(34) 茅盾:《“文学批评”管见(一)》,见《茅盾文艺杂论集》(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页。
(35) 李健吾:《答巴金先生的自白》,见《李健吾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44页。
(36) 雁冰:《文学作品有主义与无主义的讨论》,《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1922年2月。
(37)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诗文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