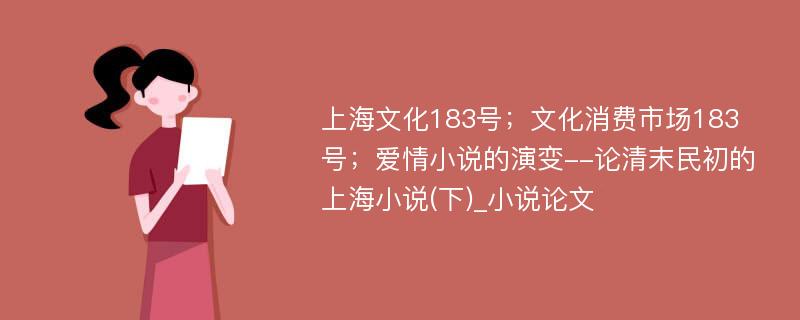
新兴都市上海文化#183;文化消费市场#183;言情小说流变——清末民初上海小说论(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民初论文,文化论文,清末论文,消费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08)10-0088-06
一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西方人及其资本开始逐步撤离上海租界,西式事物的参照作用明显减弱,这限制了新兴都市上海外层带文化的发展,中层带依附内层带文化对整个新兴都市上海产生影响的。上海华洋交界处滋生的“洋泾浜文化”在民初则更立足于华界而发生变化,它的亦中亦西表现出向占上海人口绝大多数的江浙人的吴文化传统返归,在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审美趣味上形成以吴文化为根柢的“海派”特征,这是一种对都市文化消费市场更具有依附性的文化,民初上海小说在这一文化氛围中较之清末发生了明显变化。
民初上海小说的变化,还与辛亥革命后的社会现实相关,主导民初小说这一变化的是南社文人。南社1909年成立,苏州是其发源地,成员以环太湖流域的江浙籍人士为主,这是一个以吴文化为根柢的新型文人团体,反清政治革命态度激烈,在思想文化性格上,又是民初上海“洋泾浜”文化特征的典型体现。辛亥革命成功的意外顺利,南社文人极度兴奋,作为江南有着数百年与满清王朝的对抗传统的后裔,他们自然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自豪与成就感,“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苏殊曼作),是他们中间传颂一时的诗句,既可见志得意满之态,又是他们对“英雄美人”的理想期冀的体现。其时,江南各地的南社分社纷纷成立,知识分子几乎都以南社中人自许。但是,民初中国所呈现的社会图景又绝非革命党人所想象的国泰民安之状,整个国家陷入极度混乱与动荡之中,恰如当时在华的一位外国记者所言:“中国目前所遭受的痛苦或许比全世界其余各地所遭受的痛苦加在一起还要大一些。”① 曾经倾心革命的一代知识分子,表现出“万般无奈的失落和颓丧”——“当年的壮志热血,当年的英风豪气,已经同他们对那场改朝换代的革命所怀抱的希望一样,付诸东流,同归幻灭。这是中国文人第一次集体领受近于绝望的幻灭感。”② 南社文人革命“胜利”后封侯授爵、英雄美人的遥想,很快就被民初军阀当政、政客腾达的现实击得粉碎,最早敏感到“乱世”的降临,发出“呜呼哀哉”的哭声,政治革命激情的迅速消退,一批出生于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年轻的南社文人,自觉向吴文化的小说传统回归,成为民初上海小说潮流的滥觞者。
1912年《民权报》副刊发表长篇骈体小说《玉梨魂》,作者是年初受聘执编该报的江苏常熟人徐枕亚。《民权报》的一批南社青年革命党人,对袁世凯在北京组阁的独裁专制的抨击,态度坚定,言辞锋利,但反袁之激烈掩饰不住内心对推翻帝制以求共和的革命的怀疑与绝望,徐枕亚在《民权报》及其被封后产生的《民权素》,以及他主编的《小说丛报》上,发表了不少凭吊“革命”及“战争”的小说,但在民初上海文化氛围中,这些作品都远不及《玉梨魂》轰动大。《玉梨魂》有作者的经历,写在无锡一乡间小学任教的何梦霞寄住远亲崔家,同时为崔家青年寡妇白梨影之子做家庭教师,何、白二人在相互诗函传递中萌生爱慕之情,怯于礼教又痴情难断,梨影作主让家中进过女校的小姑崔筠倩与何梦霞成婚,由此酿成悲剧:白梨影恋情未断反愈深,抑郁而死;崔筠倩婚后未得所爱也在幽怨中郁郁而终;何梦霞则痛苦难抑出国留学,后回国投身革命军,武昌一役殉国。小说着意渲染三人特别是白梨影陷入迷惘、痛苦之中不得解脱的情感,浸透全篇的浓重的感伤,显然带有作者的现实感触。作者模仿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安排何梦霞出走及捐躯的结局,明显是将故事文本置入现实——“是七尺奇男,死当为国;作千秋雄鬼,生不还家。”③ 显然,这是一种空幻之志。小说面世,唏嘘声不已,1913年出单行本,再版数十次,总销量达数十万册,又被改编成话剧,拍成最早的无声影片。《玉梨魂》产生如此轰动效应,显然不能仅仅从辛亥革命后知识界“近于绝望的幻灭感”去认识,折射出了民初上海的文化氛围,是作者在这一文化氛围中通过对吴文化传统的更新再造所使然。
《玉梨魂》的核心文本是从江南才子佳人小说传统中脱化而出。明清两代一个多世纪里,在《金瓶梅》和《红楼梦》两大奇书之间,江南存在着一个写才子佳人的小说潮。中心则在产生和流行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言情通俗小说的吴地。《玉梨魂》显然对此有所超越,不仅男女主人公皆为受过新式教育的普通平民,也写出他们感情专一如“玉”如“梨”,发掘人物之“魂”。清末上海受启蒙思潮影响的“谴责小说”是通过对吴文化传统的超越出现的,民初徐枕亚在《玉梨魂》中重新摄取吴文化传统资源,更新再造,“才子”与革命相联系而具英雄色彩,“佳人”的情感表现虽受限于“发乎情止乎礼”,但作品的悲剧结局又明显是对此的责问与反抗,这是小说在以吴文化为根柢的上海以至江南轰动和畅销的根源。作为新兴都市上海文化的体现,《玉梨魂》同时又超越了“倡优士子”的传统叙事模式,何梦霞由“士子”衍变而来,已带有郁达夫笔下“零余者”的几分色彩,白梨影这个女子也已不再属于“倡优”,更贴近社会现实人生的实际,——知识者生逢乱世被抛到社会底层与落难女子同病(命)相怜,所感受到的“同是天下沦落人”,这种人生故事经由《玉梨魂》的转换,具备了进入“现代”的可能。几年后创造社作家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出版后,在江南知识青年中激起强烈反响,是可以从《玉梨魂》对吴文化传统的激活,以及对“倡优士子”模式的更新再造中找到一些根源的,甚至十几年后,我们仍然可以在蒋光慈的《少年飘泊者》中发现所受《玉梨魂》影响的明显痕迹。《玉梨魂》还一改清末“谴责小说”通用的传统白话语体,采用江南文人多所偏好的骈散结合的文体叙事,与北京学府中章门弟子同人对“六朝文”的提倡相一致,可以追溯到江南文化结构衍变中知识者对桐城文的普遍厌弃,显示了近现代之交语体变革的路向。
与《玉梨魂》同时或稍后刊载于《民权报》副刊的,还有吴双热的《孽冤镜》和李定夷的《霣玉怨》。吴、李与徐枕亚同来自吴文化中心,又携手供职于《民权报》,这两篇小说的情调、语体皆承续《玉梨魂》,直写儿女私情,更深地触及了传统婚姻制度,明言:“欲普救普天下之多情儿女耳;欲为普天下之多情儿女,向其父母之前乞怜请命耳;欲鼓吹真确的自由结婚,从而淘汰情世界种种之痛苦,消释男女间种种之罪恶耳。……愿普天下为人父母者,对于子女之婚嫁,打消‘富贵’两字,打消‘专制’两字。”④ 与《玉梨魂》相一致,《孽冤镜》、《霣玉怨》也着意于装饰美、感伤美的营造,那种“骈四俪六”、“雕红刻翠”、“哀感顽艳”之格调,分外引人注目。研究者推《民权报》为民初言情小说的发源地,视他们三位为开鸳蝴(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三鼎足”,虽然他们有更宽的创作题材,但对民初小说影响最大的还是这些言情之作,从中可以看出鸳蝴派小说的来龙去脉,也足以显现上海小说民初与清末之不同。清末“谴责小说”不屑于关注人的家庭生活特别是儿女私情,1906年群学社聘请吴趼人担任《月月小说》总撰述,吴所撰发刊词再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却落在“借小说之趣味之感情,为德育之一助”,⑤ 他的小说如《恨海》,把言情题材从明清以来所擅长表现的后花园、烟花巷中解放出来,置入十里洋场的上海不无意义,但对情感悲剧根源的揭示,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相一致,“归罪于社会上旧道德的消灭”。显然,真正体现青年男女的情感生活从道德束缚中解脱出来,获得独立意义表现的,是民初《玉梨魂》、《孽冤镜》、《霣玉怨》开启的言情小说潮流。
二
清末与民初的上海小说,作为新兴都市上海文化的表现,相一致是通过都市文化中层带的报刊出版与文化市场关系得到发展的,但是,与清末小说对报刊出版更具有主导性,通过报刊出版实现对文化市场的不断更新与重建不同,民初小说及其所借助的报刊出版对都市消费性文化市场更具有依附性,为南社文人所开启的言情小说,就是通过都市消费文化市场的膨胀而得到迅速发展的,其表现就是1914年出现的“甲寅中兴”。
“甲寅中兴”作为新兴都市上海内层带文化活跃的表现,是与上海华界民初以来的变化相关的。民国建立后的政局动荡以及战争不断,向相对安定的上海的人口流动再度进入高峰期⑥,主要落脚于华界,至1915年上海人口已超过二百万,带来华人圈的急剧扩大,并向洋人居住的租界渗透,同时,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上海租界的洋人纷纷返国,外资兴办的工商、金融、娱乐业顿显萧条,转手华人,民族工商业从而获得发展,这带来上海华人的工资收入增加,生活水准明显提高,相应地,华人兴办的文化消费市场也迅速膨胀起来。市场机制作用下的文化消费市场的繁荣,推动了以华人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报刊出版业的发展,较之清末,民初上海报刊出版业的发展更是华人资本使然,如1912年史量才买下《申报》全部产权,次年改“隔日报”为“日报”,并更新印刷技术,为满足市场需求,从最初每小时印全张报纸两千份,发展到每小时可同时印刷十二张一份的报纸一万份,⑦ 商务印书馆1914年收回全部日股,次年改用胶版印刷。
1914年上海文学期刊创办之多,作家职业化、作品商品化程度之高,都非清末可比,是上海文化消费市场急遽膨胀的表现。商务与中华书局在资金最为雄厚的出版机构,这一年适应上海文化消费市场的需要,所办期刊《小说月报》和《中华小说界》转向以刊发言情小说为主。开上海言情小说创作之先河的南社文人,1914年创办《小说丛报》、《民权素》、《小说旬报》,发表了吴双热的《花开花落》、权予的《铁血鸳鸯记》、徐枕亚的《雪鸿泪史》、剪瀛的《鸳鸯劫》等,虽叙及刚刚逝去的那场革命,但打动人心的仍然是其中男女主人公“哀感顽艳”的爱情故事。此外,有影响的期刊还有《眉语》、《礼拜六》、《黄花旬报》、《女子世界》等。《礼拜六》似异军突起,可视为“甲寅中兴”发表言情小说最重要的阵地,要与“戏园顾曲”、“酒楼觅醉”、“平康买笑”的都市消费风习相抗衡,以争得更多的读者。该刊推出“甲寅中兴”最具影响力的南社青年小说家周瘦鹃,每期均有他的言情之作一篇至两篇。周瘦鹃是苏州人,肄业于上海民立中学,十七岁发表剧本《爱之花》,一举成名,以创作为职业,言情题材已不同于南社前辈,紧贴都市生活,人物以学生、教师、画家为主,还有其他各类普通都市市民,他从这些都市青年男女的家庭日常生活中不断发现或苦涩或僵化的情爱关系,择取出来,着意渲染,衍成悲剧,诸如小说《真假爱情》、《恨不相逢未嫁时》、《此恨绵绵无绝期》、《画里真真》等,均发表于1914年。他创作与翻译并行,小说以短篇见长,写法上有赖于对“欧美名家短篇小说”的翻译,所译小说结集成书卖中华书局出版。周瘦鹃出身贫寒,少年成名有赖于包天笑的帮助,他的出现,是民初言情小说题材转向直接描写都市生活的标志。包天笑亦是苏州人,是上海文坛上不多的经历贯穿清末民初的南社作家,他办报办刊编国文教材,有多方面的成就,但影响最大的是著、译小说。清末译有《迦茵小传》、《空谷兰》、《梅花落》等言情之作,受到读者欢迎,又译述教育小说《馨儿就学记》、《孤雏感遇记》等,颇得好评。他清末创作的短篇《一缕麻》,虽意在揭露指腹为婚的野蛮性,却写出了“美人儿”对“丑男子”的由恨变爱,突出了情的“圣洁”,因而民初又被改编为剧本,搬上了舞台。包天笑是“甲寅中兴”不可或缺的作家和编者,1915年担任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发行的《小说大观》主编,该刊创季刊之始,每期字数在三十万字以上,三百数十页,是当时小说界最为厚重之刊。⑧ 由于他的声望,当时第一流的言情小说名家姚雏、陈蝶仙、许指严、范烟桥、周瘦鹃、程小青、张毅汉、毕倚虹等的新作均发表在该刊,他自己则每期都有长篇连载或短篇新作。《小说大观》以其刊发的切合读者阅读口味的长篇言情之作,适应并推动了消费性文化市场的发展。
对于“甲寅中兴”得到更大发展的言情小说,可以与清末小说相对比来认识。首先,清末小说特别是“谴责小说”,较少考虑市场机制作用下的文化消费效应,是对上海阅读市场绝大多数读者的吴文化口味的硬性剥离,以改变以“欢场”为中心的文化消费趋向,这显然与维新思潮的影响分不开,民初言情小说是在维新思潮影响弱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自觉向吴文化传统回归,以满足文化消费市场的需要,体现了市场经济主导下的文学创作与文化消费的双向推动作用。其次,“谴责小说”之“命意在于匡世”,指陈社会时弊,是与世俗化的社会生活相脱节的,民初上海都市化程度的提高,更体现在市民的世俗生活的独立上,即休息与劳动截然分开,《礼拜六》即抓住了这一特点,刊发言情之作以满足读者休息时的“消闲”需求,由此发展起来的武侠、侦探、滑稽、历史、掌故等不同类型的小说,几乎无一不贯穿着言情,以调动和丰富读者“消闲”中的文化消费兴趣。再次,清末“谴责小说”的“揭发伏藏,显其弊恶”,却“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⑨ 这限制了小说艺术表现的空间,民初小说转向言情,更注重小说艺术本身,如周瘦鹃、包天笑等兼擅翻译,在小说创作中采用并实验西方小说技法,提高了言情的艺术表现力。还需要看到,言情小说的兴盛虽以市场为依托,却对上海都市化发展中商品经济的恶性膨胀带来的污秽,即机谋计算充斥,人性之恶张扬,不无针砭。过渡淫染于商业铜臭的都市人,精神和情感生活倍显空虚、乏味,而寻求通过文学中的非现实的情爱故事填充,也不无保留精神生活领域一块“纯净”之地的意愿,让心灵在非现实的情爱故事中得到“净化”,这为言情小说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所以,言情小说写哀情、苦情、怨情、悲情、惨情、痴情、奇情、幻情、侠情、谐情、趣情……,虽名目凡多,但突出的是一个“纯”字——“言情小说中男女两方不能圆满完聚者”,“内中的情节要以能够使人读而下泪的,算是此中圣手”。⑩ 而使我们看到,言情小说塑造人物,多将“情”与“欲”相对立,以突出“情”的圣洁。
但也显而易见,民初以至“甲寅中兴”发展起来的言情之作,并非是从民初社会人生的精神和情感状态体验中升华出来的,难以与都市人的社会生活相统一,在写作和阅读层面多属于“画饼充饥”,只能在非现实的“虚幻故事”中得到瞬间心理自适,而根本无法从中汲取直面都市社会人生的思想、精神和情感因素,这限制了言情小说发展的可能。所以,民初言情小说创作中更有意义的作品,是与清末相联系的,即承续“谴责小说”言指社会的精髓,寻求情的社会意义。这一倾向萌发于清末,曾朴在他创作的社会小说《孽海花》中就注重融会言情因素,吴研人1906年执编《月月小说》时,所写作品多属言情之作,着眼点在凸显情的社会意义,包天笑则进一步在小说中将社会与言情融于一体,但真正标志“社会言情小说”出现的,是李涵秋。李涵秋是江苏扬州人,清末跻身文坛开始小说创作,成名于民初,是将清末“谴责小说”传统带入民初言情小说创作的最有力度者,所著《广陵潮》完稿于1919年,但部分章节1914年在《大共和日报》副刊连载,即已发生影响,1915年有出版机构为他发表的这些章节出版了单行本。《广陵潮》是一部写家族命运的长篇小说,作家找到了社会与言情的契合点——家族,将扬州结有姻亲的云、伍、田、柳四家的盛衰荣辱,置于清末民初的历史变动中,四家两代人的恩爱纠葛、悲欢离合,与辛亥风云、民初社会动荡、洪宪称帝、张勋复辟以至“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系,使读者在观赏市井生活中,通过一对对青年男女的情爱关系的波澜起伏,触摸到历史的进程,悟出人物命运的一些社会意义。(11) 所以,继《广陵潮》之后,出现了《歇浦潮》、《人海潮》等效仿之作,但在社会与言情的结合上显然都无法与《广陵潮》相比。
三
但是,1912年至1916年,是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思想文化领域最“灰暗”的历史,(12) 民初言情小说转向以都市市民为接受和表现的对象,较之清末“谴责小说”既缺乏外在思想文化力量的支撑,更缺乏作家自身的自主性与和独立性,是依附于都市消费文化市场的变化而变化的。
这与民初以来以南社为主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直接相关,政局混乱,理想破灭,他们痛感自己在这个社会中已一无所用,在一片悲悯声中,认为自己无须再保留曾经有过的那份“庄严”与“神圣”,不再具有精神上的追求与操守,他们写小说、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混日子”或“谋钱财”,所丧失的必然是创作的严肃性,这样,当他们转向以都市市民为接受和表现的对象时,人生观与价值观也开始向市民倾斜而世俗化,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欲望。纯粹为市场经济所驱动的文学,使文学的生产与消费商业化,即文学创作这一纯粹的个体精神创造,蜕变为作者、读者、出版商共同参与下的商品交换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消费决定生产,一部作品一旦畅销,市场机制迅速将作品类型化,投入批量生产与制作以赢利,导致作品的文学性根本丧失,带来劣品、伪作的泛滥。这在清末即已出现,民初上海文化消费市场的恶性膨胀,这种现象伴之以“炒卖”显得更为突出。徐枕亚为《民权报》写《玉梨魂》时,不求稿酬,写得十分认真,作品畅销后,他在《小说丛报》任主编,当时报社资金亏损,他又写出《雪鸿泪史》在《小说丛报》连载,托言作品是重金购得的《玉梨魂》主人公何梦霞的日记,日记体虽显新颖,但小说内容不过是《玉梨魂》的花样翻新,了无新意,生硬地添加了许多主人公的诗词书礼,赶制中为充数甚至抄袭了他人的作品,这显然已经与市场经济中的商品营销方式并无区别。(13) 被称为“掌故小说大家”的许指严,早期作品《南巡秘记》、《十叶野闻》等大都写得严肃,有史料依据,因而畅销,但他后来也钻进市场的“生意眼”,为“解决经济拮据”,与世界书局合谋伪造一部《石达开日记》,登广告说如何觅得原稿,“居然一编行世,购者纷纷,曾再版数次”。(14) 李定夷的《霣玉怨》畅销后,在不到十年时间里,竟有四十七八部长篇小说问世,不少作品内容雷同,更有一些偷梁换柱之作,如他的笔记体历史小说《民国趣史》(上海国华书局1915年出版),不过是从报刊上摘录各种并非全都真实的奇闻轶事,然后从中分出“官场琐细”、“试院现形”、“裙衩韵语”、“社会杂谈”等的不同,分章将这些材料一一罗列,便拿去出版。清末谴责小说家李伯元、吴研人等借助于报刊上的新闻故事写小说,还要有所斟酌、取舍,写入小说还要从立意出发有所增删、修改,民初小说摘取报刊材料则不分良莠,只要是有刺激性、趣味性,标榜“实录”,原样植入小说,这样拼凑出来的作品,很难说有什么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只能是一种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市场行为。
民初上海小说较之清末的蜕变,更主要缘于为商品经济驱动的消费文化市场的恶性发展。1915年,“外国人经营的娱乐业日渐衰退,这与民族资本家及其他人士日益增长的娱乐需求之间的矛盾暴露出来,所以一批投机商人和流氓头子乘机创办了以赢利为目的,并力求适合中国口味的娱乐场所,如大世界、新世界、新新公司、先施公司、天韵楼、劝业场等一批大型游乐场所相继建立,新式剧场如大舞台、笑舞台、共舞台、天蟾舞台等也纷纷建立”,(15) 这些都市文化市场中最具刺激性与消费性的“欢场”,其繁盛景况较之1897年李伯元办《游戏报》时的上海滩,有过之而无不及,清末在维新思潮影响下上海文坛所发生的变化迅速消退,文坛热点和中心重新向“欢场”回归。相应地。“甲寅中兴”时一批十分活跃的期刊,1916年后纷纷停办,如当初与“戏园顾曲”、“酒楼觅醉”、“平康买笑”一类都市消费风习相抗衡的《礼拜六》,1916年4月出至百期宣告截止,同年同月,《民权素》出至第十七集叫停,中华书局所办《中华小说界》该年6月停刊,此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停刊的,还有《眉语》、《小说时报》、《妇女时报》、《余兴》、《小说海》、《春声》等曾经十分畅销的期刊。清末上海的报、刊分流在这个时期也发生逆转,一些期刊更是依附于“欢场”创办,如郑正秋主编了附属于新世界游乐场的《新世界》(1916年2月创刊),孙玉声主编了附属于大世界游乐场的《大世界》(1917年7月创刊),周瘦鹃主编了附属于先施公司的《新施乐园报》(1918年8月创刊),此外还有《劝业场日报》、《新舞台报》、《新丹桂笔舞台日报》、《花世界鸣报》、《上海花世界》、《笑舞台》等,上海各大报副刊,如《申报·自由谈》、《新闻报·快活林》、《时报》副刊《小时报》等,也加盟其中,民初文人、报人,受经济利益驱使,少有不染身其间,为之捧场的。(16) 《新世界》打着“文明开化”的旗号,先后举办三次“花国选举”活动,哄动一时,(17) 在规模和影响上远超过1897年《游戏报》为妓界的“开花榜”。这反映了从清末到民初形成的新兴都市上海文化,在根柢上具有的商业性与消费性,1904年的“癸卯大观”对以“欢场”为中心的文化消费倾向的冲击与改变是有限的,1914年的“甲寅中兴”,是在都市文化消费市场膨胀的基础上形成的,由此所导致的,必然是纯粹以赢利为目的“欢场”重新成为文坛热点与中心。
民初承续清末最富有意义的社会题材创作,正是在文化消费市场的恶性发展中,蜕变为文人争相卷入的披露社会“黑幕”的热潮。“黑幕”原本不过是填充小报一角的花哨新闻,以披露“某生”、“某女”的淫、盗之事为能事,用以满足读者猎奇索秽的趣味,增加报纸销量。《时事新报》1916年9月1日创办黑幕征答专栏,宣称“本其救世之宏愿”,认为“有一种不良之社会,即有一种可惊之黑幕”,发起“黑幕大悬赏”,(18) 一时间,应者云集,“黑幕”成为文人及报刊出版竞相依附的文类,以至“家弦户诵,径走翼飞,行销之广,且远过于稗官家言”,(19) 由此而有“黑幕小说”的兴盛。发起于1916年而在1918年达到鼎盛的“黑幕”写作,仍然为南社文人所主导。1918年3月中华图书集成公司出版发行的《中国黑幕大观》(路滨生编辑),纂集170位作者的黑幕笔记742则,内分16个门类,诸如政界黑幕、军界黑幕、学界黑幕、商界黑幕、报界黑幕等等,王纯根为该书所写“序”打出“救世”的旗号,但书中所披露“黑幕”,无疑是在为他所说的“世教衰微,道德堕落”推波助澜。王纯根也编有《百弊丛书》,指责别人编“黑幕”贻害社会,自己照编不误,内容鄙俗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是在1918年,徐枕亚组织一些南社文人编有《人海照妖镜》,可谓“黑幕”集大成式的丛书,书分四集,“色海”集中又分出“引诱类”、“窃盗类”、“恫吓类”、“倾陷类”、“薄幸类”、“险毒类”、“狡狯类”、“欺骗类”、“奸拐类”、“蛊惑类”、“贪鄙类”、“淫荡类”等等。从这些细目可见编者的兴致与读者口味,如时人姚民哀所说,这类文章“文行背悖之徒,肆其淫秽之念,以谋斗筲之利,矻世换俗之功未见,而贻害青年已不知凡几矣!”(20)
新兴都市上海文化的商业性与消费性,在辛亥革命后主导上海文坛的南社文人身上有更为突出的表现,这是他们从“言情”之转向“黑幕”写作的根本原因,“五四”人批“黑幕”追溯到言情小说的始作俑者鸳蝴派,(21) 并不为过。鲁迅1915年担任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时,就参与查禁上海32种鸳蝴派小说,后来谈“清之人情小说”,到《红楼梦》截止,把“佳人才子小说”传统之在清末依附上海“欢场”写狎客与妓家,称为“狭邪小说”,认为此类小说自《海上花列传》后,只能是“人情小说”的“末流”,(22) 只字不提民初上海的言情小说,不仅缘于鸳蝴派小说之为文化消费的产物,在他看来,这更是民初中国社会文化现象的表现,即:“凡当中国自身烂着的时候,倘有什么新的进来,旧的便照例有一种异样的挣扎”,而使“许多人渴望着‘旧文化小说’(这是上海报上说出来的名词)的出现,正不足为奇;‘旧文化小说’家之大显神通,也不足为怪”,“至于说他流毒中国的青年,那似乎是过虑。倘有人能为这类小说(?)所害,则即使没有这类东西也还是废物,无从挽救的”。(23) 范烟桥的《民国旧派小说史略》,把“黑幕小说”与鲁迅命名的“谴责小说”相提并论,一并归之于“社会小说”,(24) 这也是时下一些研究者发掘“黑幕小说”意义提出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梳理小说源流,截止于清末,仅在“清末之谴责小说”一章中谈其流变,延及民初,认为在维新思潮影响弱化的背景下,这类“以抉摘社会弊恶自命”的小说的市场化发展,是不可能成为严肃的社会小说的,“其下者乃至丑诋私敌,等于谤书;又或有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则遂堕落而为‘黑幕小说’”。(25) “谴责小说”与“讽刺小说”的根本不同,更是通过其之蜕变为“黑幕小说”表现出来的,前者对所谴责的对象仅仅取“暴露”态度,后者则全然是从消费文化市场出发的肆意“编造”,如包天笑在小说《黑幕》中披露“黑幕小说”写作“黑幕”所言:“上海的黑幕人家最喜欢看的是赌场里的黑幕,烟窟里的黑幕,堂子里的黑幕,姨太太的黑幕,拆白党的黑幕,台基上的黑幕,还有小姐咧,男堂子咧……”那么如何“不必身历其境就得到许多黑幕”?告之,“你要看报时,就留心报上的本埠新闻和那些小新闻,这里头就有许多黑幕在内……譬如报上登了某公馆的姨太太逃走了。这时,他们做黑幕的一个大题目来了。那报上所登不过寥寥三数行,他便装头装脚,可以演长至一万余字,至少也得数千字。全在无中生有,移花接木,加上许多作料。你别小觑那报上所翳寥寥三数行,这便似药房里所卖的牛肉汁一般,只用得一茶匙,把开水一冲,便冲成一大碗。做黑幕的,他就是用这个法子。你想,以上海之大,奸盗淫邪之多,社会之复杂,一天里头总有一条两条够得上做黑幕材料的。这可不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吗?”(26)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社会文化的封闭与怪异,中国国民性的“看客”心理,不仅是“谴责小说”弊病形成的根源之一,更是民初“黑幕小说”滥觞而大行其道的社会基础。“黑幕是一种中国国民精神的出产物,很足为研究中国国民性社会情状变态心理者的资料;至于文学上的价值,却是‘不值一文钱’。” (27) 时值“五四”,“黑幕小说”不能不成为中西文化、中西文学差异与对立的标志性体现,“五四”人批“黑幕”并非仅仅着眼于“小说艺术”,是立足于“立人”而要建立整体反映和表现时代和社会的新文学,这就不能不把其时正盛行的“黑幕小说”作为批判的主要对象。
新兴都市上海文化根柢上的商业性与消费性,使清末与民初上海有明显差异的小说,最终趋于一致。由此可以认识到,为什么1915年出现的《新青年》,从上海转到北京而可能发动“五四”文学革命,为什么立足于北京发动的文学革命要以思想启蒙即改造国民性为先导,而可能使中国文学真正发生变革。这同时也可以说明,清末民初上海通过报刊出版与文化市场关系的不断更新,以及报与刊的分流,为现代小说的萌生所提供的资源,只有经过“五四”文学革命,才可能得到真正继承与发展。
注释:
① 《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里循通信集》上卷,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924页。
② 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117页。
③ 吴双热:《玉梨魂·序》,1914年上海民权出版部版《玉梨魂》。
④ 吴双热:《孽冤镜·自序》,1914年民权出版部版。
⑤ 《〈月月小说〉序》,《月月小说》第1年第1号(1906年)。
⑥ 第一次高峰出现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上海人口增至百万。
⑦ 参见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第451—45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该书这一部分对上海报刊出版业“印刷技术设备的更新”的情况有详尽的介绍。
⑧ 1915年8月创刊的《小说大观》,页数是陈独秀1915年9月创办的《青年杂志》的三倍,售价比《青年杂志》高五倍,却十分畅销,直至1921年6月才停刊。
⑨ 《中国小说史略·清末之谴责小说》,《鲁迅全集》第9卷第282页。
⑩ 许廑父:《言情小说谈》,《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页。
(11) 郑逸梅说:《广陵潮》1914年登载在《大共和日报》后,“涵秋之名大震于沪上,被称之为海内第一流大小说家。《广陵潮》登毕,印成单行本,直至近岁,《中国通俗文艺》还刊布一部分,并有再印全书之计划,可见这书并不以时代的变而失去其价值;书中人物,什九真人真事,足资参考。”郑逸梅:《清末民初文坛轶事·〈广陵潮〉的作者李涵秋》,《郑逸梅选集》第2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3页。
(12) 参见陈方竞:《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
(13) 郑逸梅:《南社丛谈·南社社友事略·徐枕亚》,《郑逸梅选集》第1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8-259页。
(14) 郑逸梅:《南社丛谈·南社社友事略·许指严》,《郑逸梅选集》第1卷第140-141页。
(15)(16)(17) 参见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第464,464-465,465页。
(18) 见1916年9月1日上海《时事新报》的“征稿启事:《黑幕大悬赏》”。
(19) 吴绮缘:《人海照妖镜·序》,徐枕亚主编《人海照妖镜》,小说丛报社1918年版。
(20) 姚民哀:《世界秘史·序》,《世界秘史》,上海图书集成公司1919年版。
(21) 钱玄同1919年1月9日在《“黑幕”书》中斥“黑幕”,就推及“同类之书籍”如“《艳情尺牍》、《香闺韵语》及‘鸳鸯蝴蝶派的小说’等等”,认为“此等书籍,从一九一四年起盛行。四年以来,凡变过几种面目,其实十六两还是一斤,内容之腐败荒谬是一样的”。见《新青年》6卷1号《通信》。周作人在1919年1月12日发表的《论“黑幕”》中。追踪“黑幕”的源头,认为“笔记小说”与“艳情小说”是“黑幕”小说得以产生的根苗。见《每周评论》第4号。
(22) 见《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鲁迅全集》第9卷第339页。
(23) 《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小说世界〉》,《鲁迅全集》第8卷第112页。
(24) 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207页。
(25) 《中国小说史略·清末之谴责小说》,《鲁迅全集》第9卷第292页。
(26) 包天笑:《黑幕》,《小说画报》第14期(1918年7月1日)
(27) 周作人:《再论“黑幕”》,《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