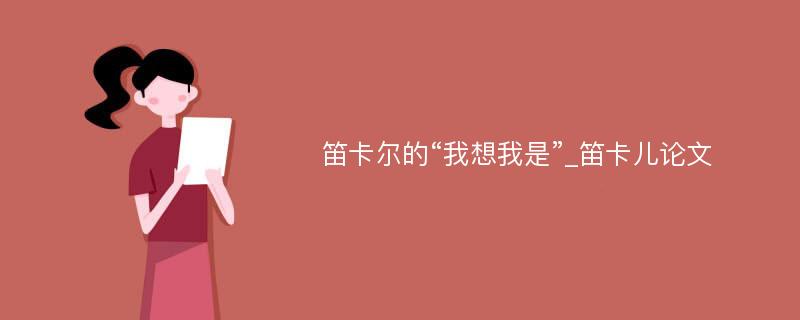
笛卡儿的“我思故我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是论文,笛卡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笛卡儿在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他引入了“思(考)”这一概念,并使它成为哲学的核心问题,从而开创并形成了认识论的研究。他的思想的集中体现就是他的名言"Cogito,ergo sum"。这句话的英译是"I think,therefore I am",德译是"Ich denke,deshalb ich bin",而汉译一般是“我思故我在”。按照我的理解,笛卡儿的这句话,英译和德译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汉译却有问题。它的正确翻译应该是:“我思故我是”。在本文中,我想就这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一些看法。(注:这是继关于海德格尔、巴门尼德、亚里士多德之后,我进行的又一个案例研究。这里有许多背景思想没有展开,但是读者可以参见那些研究。参见王路:《“是”、“是者”、“此是”与“真”——理解海德格尔》,载《哲学研究》1998年第6期;《巴门尼德思想研究》,载《哲学门》2000年第1期;《“是”、“所是”、“是其所是”、“所是得”——关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几个术语的翻译》,载《哲学译丛》2000年第2期;《“是”还是“存在”——读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载《哲学译丛》2000年第3期。)
一
笛卡儿从怀疑出发,包括怀疑各种感觉,进而谈到总有一些东西不能怀疑,特别是进行怀疑的“我”是不能怀疑的,由此得出“我思故我是”这条哲学中的第一原理。罗素说这一思想是“笛卡儿的认识论的核心,包含着他的哲学中最重要之点”(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87页)。一般来说,笛卡儿这一命题主要强调的是思考或思维活动:由于我进行思考,我才怎样怎样。因此,讨论笛卡儿的思想,似乎主要应该探讨他关于“思”的论述才对。在西方哲学著作中,一般也是这样做的。当然,这样的探讨,并不是像看上去那样简单,比如关于这里的“故”究竟是不是推论,就是有不同看法的。(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0-72页)但是,无论怎样,探讨思考总是要与是相联系的,因此,本文的讨论虽然主要不集中在关于思考的问题上,而集中在是这个问题上,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此外,我们过去一直把笛卡儿这句名言翻译为“我思故我在”,因而也很自然地理解为:由于我思维,因此我存在。这样,笛卡儿的思想就是强调精神和物质的关系,而且强调精神先于物质。这里,一个显然的疑问是:如果我不存在,那么我如何能够思考呢?人们会感到奇怪,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像笛卡儿这样的大哲学家怎么会出现问题呢?在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探讨对这句话中是的理解,即这里说的究竟是是还是存在,是非常有意义的。
众所周知,笛卡儿从“我思故我是”这个原理出发,或者说,他从探讨解释这个命题出发,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我是一个在思考的东西。从我思考出发,得出我是一个在思考的东西,无论这种说法能不能成立,有没有毛病,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一结论是自然的。而且,他强调的还是思考,整个思想也是一致的。但是,我的问题是:如果从“我思故我在”出发,那么得出“我是一个在思考的东西”还是不是那样自然?(注:必须指出,“我思故我在”中的“在”与“我是一个在思考的东西”中的“在”,二者的意思是不同的。后者不是一个动词,也是原文中所没有的,因此可以不翻译出来,或者翻译为“进行”,即“我是一个进行思考的东西”。)这里强调的无疑还是思考,但是整个思想还是不是那样一致?
从字面上理解,以思考作为出发点,认为由于我思考,因此我存在,也就是说,有我。再从思考出发,对这个被认为存在的我进行反思,问这个我究竟是什么,因此得出我是一个在思考的东西。这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我的问题是:笛卡儿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笛卡儿的《第一哲学沉思集》共有6章,第2章主要探讨了这个问题。为了清晰准确地理解笛卡儿的思想,我们重点讨论其中两段话。第一段话如下:
引文1:可是我怎么知道除了我刚才断定为不可靠的那些东西而外,还有不能丝毫怀疑的什么别的东西呢……难道我不是什么东西吗?可是我已经否认了我有感官和身体……难道我就是那么非依靠身体和感官不可,没有它们就不行吗?可是我曾说服我自己相信世界上什么都没有,没有天,没有地,没有精神,也没有物体;难道我不是也曾说服我相信连我也不存在吗?绝不是这样;当我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是可靠的。可是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的非常强大的、非常狡猾的骗子,他总是用尽一切伎俩来骗我。因此,如果他骗我,那么毫无疑问我是;而且他想怎么骗我就怎么骗我,只要我思考我是某种东西,他就绝不会使我什么都不是。所以,在对上面这些很好地加以思考,同时对一切事物仔细地加以检查之后,最后必须做出这样的结论,而且必须把它当作确定无疑的,即我是(Ego sum),我存在(egoexisto),这个我常常说出或在心里想到的命题必然是真的。(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3页。其中几处有修改,参见Descartes:Meditationen,Felix Meiner Verlag 1972,S.18;Descartes: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Librairie Philosophique,J.VRIN,1978,p.25)
在这段话中,被我加上黑体的几句话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第一句“难道我不是什么东西吗”,这是笛卡儿从怀疑出发,提出了一个不能怀疑的问题。当然,这还仅仅是一个问题,还不那样确定。第二句“只要我思考我是某种东西,他就绝不会使我什么都不是”,这是对第一句的一个正面回答。而且,这是在考虑了上帝的因素之后做出的回答,因此是非常肯定的回答。也就是说,我是某种东西,即使上帝也不会否定的。第三句“我是,我存在”,这是一个必然真的命题,它是从第二句得出来的。这里的“必然真”显然是借助了上帝的力量。我们只求理解他的意思,不考虑其论证的合理性。
从这三句话,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这就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成分“是”。无论是“我不是什么东西吗”(即“我是某种东西”),抑或“不会使我什么都不是”(即“一定会使我是某种东西”),还是“我是”,都含有一个“是”。想到笛卡儿是在论证他的命题“我思故我是”,似乎这个特点也算不了什么。相反,值得注意的好像倒是另外两个问题。第一,在这三句话中,前两句与后一句是有差异的。从字面上看,前两句肯定是表达了“(不)是某种东西”,但是后一句话只表达了一个“是”。因此,后一句话表达的究竟是“是”还是“存在”?第二,在后一句话中,除“我是”外,还跟有“我存在”,对此该如何理解?它们是同位语吗?是语词解释吗?是递进解释吗?
应该说,笛卡儿的这段话是非常清楚的,不会产生什么歧义。如果它的意思是连贯的、一致的,那么第三句话应该是前两句话的继续,即仍然是要说明“我是某种东西”。在这种意义上说,“我是”应该是一种省略的表达,省略了“是某种东西”后面的成分。我以为,这样的理解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能不能令人信服,似乎还需要论证。也就是说,即使按照上下文可以理解笛卡儿是从一般的“我是某种东西”过渡或抽象到“我是”,我们还要找到足够的证据说明,笛卡儿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省略或抽象。其实,这样的论证在笛卡儿的著作中是不难找到的。同样是在谈论我是什么的时候,笛卡儿说:
引文2:在我有上述这些想法之前,我先要重新考虑我以前认为我是什么……那么我以前认为我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我想过我是一个人。可是一个人是什么?我是说一个有理性的动物吗?当然不;因为在这以后,我必须追问什么是动物,什么是有理性的,这样一来我们就将要从仅仅一个问题上不知不觉地陷入无穷无尽的别的一些更困难、更麻烦的问题上去了,而我不愿意把我剩有的很少时间和闲暇浪费在纠缠这样的一些细节上。(同上书,第24页)
这一段话实际上还没有完,还有很长,不过,这里的引文已经足以回答我们的问题了。
简单地说,笛卡儿省略“是”以后的东西,乃是因为它们会涉及许多非常麻烦的问题,而且,它们并不是笛卡儿主要想回答的问题,“思”才是他要考虑的主要问题。这里,与思(考)相关的主要是思考“我是某种东西”,仅此而已,而这一问题的抽象就是“我是”。所以,完全可以肯定,引文1中第三句话的的确确是前两句话的继续,因而是它们的省略或抽象表达。
在引文1的这句话中,“我是”的后面还紧跟着“我存在”,直观上给人一种印象,这里的“是”的意思就是“存在”。我认为,这样的理解不是不可以的,特别是当西方人这样谈论的时候。但是应该看到,即使这样理解,我们也只能说,这是用存在来解释是,即说是的时候,可以表达存在。引伸一步,说某物是怎样怎样,则可以表示某物存在。问题是,即使承认了这样的理解,“是”本身还是没有更多的含义?“我是”是不是还表达更多的内容?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我是,我存在”乃是一个命题,它是思考和表达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理解,存在当然可以是对是的进一步说明和解释。
笛卡儿在作出身心二元区别之后,再次提出“我到底是什么呢”的问题。在谈论灵魂的属性——感觉和思维——时,他说:
引文3:现在我觉得思维是属于我的一个属性,只有它不能跟我分开。我是(Ego sum),我存在(ego existo),这是靠得住的;可是,多长时间?只要我在思维;因为假如我停止了思维,也许很可能我就同时停止是了。我现在对不是必然真的东西一概不承认;因此严格说来我只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者一个理性,这些名称的意义是我以前不知道的。那么我是一个真的东西,真正存在的东西了;可是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我说过,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还是什么呢?我要再发动我的想象力来看看我是不是再多一点的什么东西,我不是……(同上书,第25-26页。其中几处有修改,参见Descartes:Meditationen,S.20;Descartes: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p.27)
这里,笛卡儿明确阐述了他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思想是与我不可分割的属性,从而正面论证了思维的重要性。然而十分显眼的是,虽然他在这里再次提到上述引文中的第三句话,但是却明确强调“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并且进一步问“是一个什么东西”、“是什么”等问题。如果我们接着笛卡儿的论述往下走,就会看到,他还不断地在问:“我究竟是什么呢”(同上书,第27页),“什么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呢”(同上),并且通过自己的论证说明“比以前稍微更清楚明白地认识了我是什么”(同上书,第28页)。在这样的背景下,难道我们还能够说,笛卡儿谈论的是存在吗?我认为,笛卡儿主要谈论的乃是是,存在乃是关于是的一种解释,一种引伸的说法。用它来理解是,固然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笛卡儿主要是谈论思考,因而谈论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对“我是某种东西”的理解,因为这是人们最直观、最简单、最经常的思考方式,至少在他看来是这样。
二
讨论笛卡儿的思想,即使仅仅讨论他的“我思故我是”,以上论述也是不够的,大概至少还要探讨他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才行。《沉思》除第3章和第5章专门论及上帝的存在外,其他各章均有一些论述。因此,笛卡儿与上帝相关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他的“我思故我是”这一思想,乃是非常值得参照和思考的。
如果按照上文的理解,笛卡儿关于上帝存在的表达应该是“上帝是”。但是我们看到,笛卡儿除了谈论“上帝是”以外,还明确地谈论“上帝存在”。不同之处在于,他一般不大问“上帝是什么”,而总是肯定“上帝存在”,并借助上帝的存在来论证“我”怎样怎样。这里,我不探讨笛卡儿是如何论证上帝存在的,他的论证对不对,有没有道理。我的问题主要是:“上帝存在”与“上帝是”有没有区别。
在笛卡儿的论述中,“上帝是”与“我是”是有区别的。在我看来,这种区别与其说是字面上的,不如说是使用上的。如上所述,虽然笛卡儿也把“我存在”与“我是”并列来谈,甚至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他是用“我存在”来解释“我是”,但是实际上它们还是有区别的,而且这种区别是可以从他论述的方式,特别是从引文1前两句话到第三句话的过渡体会出来的。但是在“上帝是”和“上帝存在”这里,我们却根本看不到这样的过渡,因而一般体会不到它们之间明确的区别。在这种意义上说,“上帝是”和“我是”当然是有区别的。
此外,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笛卡儿有许多关于上帝的本质和上帝的存在的讨论。他明确指出,“上帝的存在不能同他的本质分开”(同上书,第70页),除了上帝以外,他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的“存在是必然属于它的本质的”(同上书,第72页)。因此,“存在性和上帝是不可分的”(同上书,第70页)。也就是说,在一般事物,本质和存在是分开的。而在上帝这里,本质和存在是不分的。针对反对者的一些质疑,特别是像“三角形的存在和本质如何分开”这样的质疑,笛卡儿有如下一段解释:
引文4:必然的存在性在上帝那里真正是一种最狭隘意义上的特性,因为它仅仅适合于上帝自己,只有在上帝身上它才成为本质的一部分。这就是三角形的存在性之所以不应该和上帝的存在性相提并论的原故,因为在上帝身上显然有着在三角形上所没有的另外一种本质关系……说本质和存在,无论是在上帝身上或者是在三角形那里,都能分开来单独领会,这话也不对,因为上帝乃是他的是,而三角形并不是它自己的是。(同上书,第381-382页。其中有两处修改,参见Descartes:Meditati-onen,S.350)
我觉得这段解释有三点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它说明存在性是上帝的一种性质,而且是一种狭义的性质。这样我们就不能在一般意义上理解它。其次,在上帝身上,本质与存在不能分开理解,而在其他东西,则是可以分开来理解的。由于这两点,因而产生了第三点很有意思的结论:上帝的是和三角形的是乃是不同的。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则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三点意思完全可以归为一点:在上帝这里,本质和存在是不分的,而在其他事物,本质和存在是区分的。这与前面提到的笛卡儿的那些论述显然是完全一致的。问题是,这种区分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笛卡儿的思想,我们再看他的另一段话:
引文5:如果“是动物”属于人的本性,那么可以断定人是动物;如果“三角之和等于两直角”属于三角形的本性,那么可以断定直角三角形是三角之和等于两直角。如果存在属于上帝的本性,那么就可以断定上帝存在,等等。(同上书,第152页。略有修改,参见Descartes:Meditationen,SS.135-136)
这是笛卡儿在答辩别人对于《沉思》第2章的反驳时关于自己的论证的一段说明,他是想论证,只要我们认为属于一事物本性的东西,就可以被正确地断定为属于该事物。虽然这段话仅仅涉及与本性相关的问题,而没有直接回答存在与本质的区别与否,但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笛卡儿的有关思想,因为这里的解释是非常具体的。动物是人的本性,因此可以断定“人是动物”;三角之和等于两直角是三角形的本性,因此可以断定“直角三角形是三角之和等于两直角”;存在是上帝的本性,因此可以断定“上帝存在”。这段解释的意思不难理解,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本性与本质虽然近似,却无疑是有区别的。在笛卡儿时代,人们非常清楚来自亚里士多德的传统的本质定义,即属加种差。也就是说,说明一事物的本质需要说出它的属和种差。这里关于本性的说明,显然不是关于本质的说明,因为看不到属加种差。动物显然仅仅是属,而不是种差。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与表达本质相似的表达方式:“是动物”,“是三角之和等于两直角”,等等。以人为例,不管谈论他的本性(“人是动物”),还是谈论他的本质(“人是理性动物”),表达方式都是一样的,即“S是P”。也就是说,本性也好,本质也罢,都要表达为“是怎样怎样”。问题是,对于任何事物都可以这样谈论和考虑,惟独对上帝不行。因为上帝的本性就是存在,所以对它的本性的表述就是一个“存在”。推而广之,上帝的本质也是同样。
有了这里的理解,再看引文4,我们就可以明白笛卡儿的那三层意思是什么了。我们现在倒着分析那三层意思。说“三角形是”乃是不行的,因为这样并没有对三角形有任何说明,也就是说,仅仅一个“是”,还没有说明三角形的本性,因为三角形的本性必须要通过其他东西来说明。而对于上帝,我们仅说“上帝是”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是”在这里既表达了上帝的存在,又表达了上帝的本性。正因为这样,上帝的这种本性与三角形的本性是不同的。因此,说三角形存在与说上帝存在的意思也是不同的。因为说三角形存在并没有表明它的本性,而说上帝存在也就同时表明了它的本性。所以,“上帝存在”中的存在,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即狭义的存在。只有对上帝才能这样说,而对其他事物是不能这样说的。
在笛卡儿的著作中,他用“存在”和“是”来论述上帝,因此他说“上帝是”,“上帝存在”,而且这两种用法确实常常是不分的,意思也是大致相同的。但是,从以上论述我们确实可以看出,这里还是有细微差别的。最重要的一个差别是,对上帝可以说“是”,也可以说“存在”,二者是等价的;或者,对上帝只能说“是”,但是这种“是”乃是在“存在”的意义上理解的;但是,对于除上帝以外的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简单地这样说。
在笛卡儿的哲学著作中,虽然他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进行了许多论述,但是他最主要的成就并不是他关于上帝的论证,而是他关于“我是”的论证。因此“我是”乃是我们考虑的重点。我们既然看到上述差别,自然就会说,“我是”与“上帝是”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与上帝是不同的,乃是上帝以外的东西,因此在“我”的身上,存在与本质是相区别的,“我”的存在与本质或本性并不在于我自身的是,而是需要有其他的说明。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引文1、引文2和引文3的论述是不应该有什么理解上的问题和歧义的。特别是对于引文1中从前两句话到第3句话的过渡的理解,也是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和歧义的。
三
“我思故我是”这个命题强调的是“思”,涉及到“是”,而在具体论证过程中,包含了大量关于上帝存在的讨论。如果没有任何哲学背景知识,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笛卡儿要使用“我是”这样一种方式来讨论他想强调的“我思”?探讨“我思”和“我是”,为什么要涉及关于上帝存在的讨论?这是因为,“我是”的核心不在于我,而在于是,而这个是恰恰就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形而上学乃至哲学的核心问题。而上帝存在,则是中世纪神学和哲学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因此,笛卡儿的“我是”并不是随便说的。他的这个命题以及相关的探讨,是围绕着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进行的,同时也反映出中世纪哲学的强大影响和继续。
在笛卡儿的探讨中,我们看到,最容易令人迷惑和产生问题的地方乃是是和存在的区别。无论是关于上帝与其他事物的区别,还是关于本质和存在的区别,实际上都与是和存在的区别有关。根据引文1、2和3,笛卡儿的思想是清楚的。因此,我们理解的困难显然主要不在“我思故我是”这句话本身,而在于涉及到上帝以后。如果不谈论上帝,大概也就不用区别存在与本质,因此也就不用有那么多相关的讨论,也就不用区别是与存在了。问题是,在笛卡儿那里,谈论上帝,甚至以上帝为出发点,已经成为哲学传统,因此他不得不谈论,必须谈论。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倒是应该考虑一下,从上帝出发,为什么就一定会涉及到存在和本质的区别呢。
直观地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关于存在和本质的区别乃是从关于上帝的表述来的。一般来说,哲学家关于上帝的表述来自神学家,而神学家关于上帝的表述来自《圣经》。上帝告诉摩西的话“我是我之所是”乃是人们知道的关于“上帝是”的惟一表述。从这句话里,人们知道,上帝是什么就是什么,换句话说,人们仅仅知道“上帝是”,因为他说的那个“我之所是”仍然仅仅表明“上帝是”。神学的讨论是从相信出发的,关于上帝是不能怀疑的。因此,根据这个“上帝是”,既不能随便说上帝是什么,又要相信有这样一个上帝,因此这个“是”就成为上帝惟一独特的性质。此外,神学家们还必须从这里出发论证上帝的至高无上性、完美无缺性、全知全能性,等等。因此,必须对这个“是”作出区分。区分的结果就是存在与本质的统一。比如,中世纪著名神学家和哲学家托玛斯·阿奎那认为,“他之所是”是上帝最合适的名字。他说:
“他之所是”是比“上帝”更合适的,因为它使我们可以在第一意义,即他是(esse)的意义上使用这个名字,因为它以一种不加限制的方式表示他,还因为它的时态,正像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但是当我们考虑用这个词表示什么意思时,我们必须承认,“上帝”是更合适的,因为它被用来表示这种神圣的本性。更合适的甚至是“他是他之所是”,它被用来表示上帝这种不可传达的实体,或者表示上帝这种个体实体,如果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东西的话。(St.Thomas Aquinas:Summa Theolo-giae.vol.3.pp.92-93)
表面上看,阿奎那提供了三种理由,说明“他之所是”是上帝的名字,有时候甚至是比上帝更合适的表达。第一是由于它的意思,因为它不表示任何特殊的形式,而只表示是(esse)本身。第二是由于它的普遍性,因为其他任何名字都要么不太普遍,要么至少会增加一些细微的意义差别,这样就会限制或确定原初的意义。第三是由于它的时态,因为它是现在时,而上帝恰恰既不是过去的,也不是将来的。但是实际上,这三种理由不过就是一个理由:用“是”来表达,乃是最普遍、最没有限制的,而这恰恰符合上帝的性质。
问题是,这样的探讨固然涉及上帝,而在神学的讨论规则下,必须这样理解,但是哲学家们毕竟还要探讨哲学问题本身,特别是探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探讨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门“作为是的是”的学问。阿奎那明确地指出,应该知道,正像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第5卷说的那样,是本身乃是以两种方式表达的,“首先它被分为10种范畴;其次它表示命题的真”(Aquinas,St:On Being and Essence.Toronto,Canada 1949.pp.26-27;Aquin,T.Von:Das Seiende und das Wesen,Lateinisch/Deusch uebersetzet.kommentiert und herausgegeben von Franz Leo Beeretz,Reclam 1987.SS.4-5),而“本质则是在是的第一种意义上理解的”(同上,p.27;SS.6-7),即在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范畴的意义上理解的。表述一事物的本质并不意味着断定一事物的存在,也就是说,本质与存在并不意味着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在中世纪哲学家那里,上帝只能表达为“他之所是”,而这种说法“意味着在上帝没有他的本质和他的存在之间的区别”(Maurer,A.A.:Medieval Philo-sophy,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eval Studies 1983,p.114)。因此,他们必须论证,在上帝这里,存在与本质是同一的。这里,我不想探讨这种分析和论证有没有道理,是不是站得住脚,而只想指出,认识这些分析和论证的产生、形成及其影响,对于我们理解西方哲学,特别是理解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方面,这样的探讨及其结果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沿袭了西方哲学传统;另一方面,它又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即神学的强大影响。认识到这样的继承与差异,我们可以真切地体会到西方形而上学思想的发展与变化。
为了理解笛卡儿的思想,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康德关于上帝存在的一段著名论述:
是(Sein)显然不是真正的谓词,即不是一个关于任何某种能够加在一事物概念上的东西的概念。它纯粹是一事物的位置,或是某种自身的规定。在逻辑使用中,它仅仅是一个判断的连词。“上帝是全能的”这个句子包含两个带有对象的概念:上帝和全能;“是”这个小词并没有引入一个谓词,而仅仅引入了使谓词与主词联系起来的那种东西。如果我现在把这个主词(上帝)与它的全部谓词(全能也属于此)合并起来并且说:“上帝是”,或者“这是上帝”,那么我为上帝这个概念没有增加任何新的谓词,而仅仅增加了这个主词本身与它的全部谓词,并且增加了与我的概念相联系的对象。(Kant: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i,Suhrkamp Verlag.Band 2.1974.S.533)
不论康德的论述对不对,有没有道理,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它与笛卡儿的论述显然不同。他们之间的区别有很多,然而较大的差异大概就在于,笛卡儿是从“上帝是”出发,不加怀疑地论证它的合理性,而康德正相反,对“上帝是”这种论证方式本身提出质疑。特别是,康德对中世纪神学的论证方式提出批评,他认为,“每一个时代人们都在谈论那绝对必然的本质,而且人们并不努力理解是不是能够和如何能够思考这样一个事物,而是努力证明它的存在。尽管这样一个概念的名词解释是非常容易的,即它是某种这样的东西,它的不是乃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这样的做法人们丝毫没有变得更聪明,同样看不出怎么可能把一事物的不是看作绝对不可思考的东西,而实际上人们是想知道,我们通过这个概念究竟是不是可以普遍地思考某种东西”。(同上书,S.529)从康德的论述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在探讨“是”这个问题上,康德和笛卡儿的哲学传统无疑是一致的,但是在关于“上帝存在”的问题上,康德与笛卡儿是非常不同的,而且与笛卡儿时代那些批评笛卡儿的人的观点和论证方式也是根本不同的。我想,这里大概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且不论欧洲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也不论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对中世纪宗教神权的反叛,在康德时代,至少笛卡儿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而中世纪就更加久远,因此康德的形而上学研究虽然仍然保留不少上帝存在的讨论,但是宗教的影响已经不是那样强烈,至少不是像笛卡儿时代那样强烈。他的探讨虽然保留了宗教哲学的主要问题,却完全是在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的。
笛卡儿在哲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他的思想具有开创性,提出了思的问题,从而把认识提到哲学研究的首位;另一方面,他的思想也有继承性,探讨的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传统问题,即是本身。因此,理解和研究笛卡儿的思想,不仅应从他的著作出发,还应从哲学史出发。这样,我们不仅会看到宗教神学对哲学发展的影响,也会看到哲学与宗教神学的不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从古希腊到笛卡儿,是之问题的延续,而且可以看到从笛卡儿到康德,以至康德以后的哲学家,是之问题的继承和发展。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非常清晰地体现了一种思想的一脉相承。在这样一种思想背景下,面对海德格尔所说的要回到古希腊,回到对“是”本身的追问,难道还会感到有什么可奇怪的吗?
标签:笛卡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