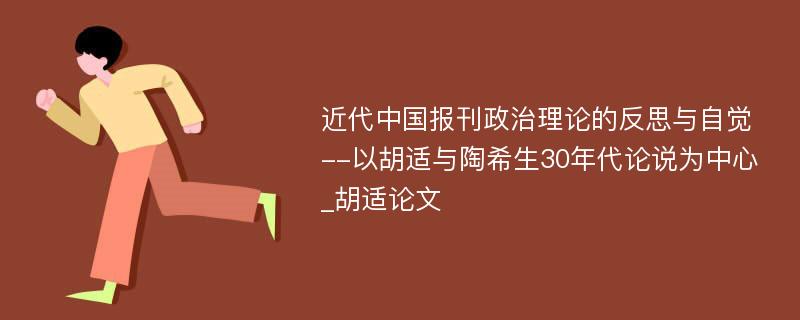
现代中国报刊政论的反省与自觉——以1930年代胡适与陶希圣的一场讨论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政论论文,中国论文,报刊论文,自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公报》“星期论文”是1930年代由胡适、蒋廷黻、傅斯年、丁文江等人担任撰稿人的著名政论专栏,专栏基本上囊括当时最优秀而有公共关怀的一群知识分子,讨论主题涉及内忧外患的中国的各个层面,一直持续到1940年代末期才结束。除了作者群体、媒体文化、思想资源、舆论话题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特征之外,“星期论文”作为公共舆论在论述风格上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其明晰清楚的行文风格和对话商榷的讨论态度,在“星期论文”中很少看到佶屈聲牙的表达,也很难发现强词夺理的“宣传口腔”,也没有文人习气明显的反讽、影射、揶揄等感性措辞,相反,“星期论文”大都是在一种言说者与阅读者人格平等的预设下,用学理的方式深入浅出地讨论问题,几乎没有进行人格攻击式的词汇。
可以说,“星期论文”具有“绅士风度”的学理化公共舆论特色正是作者群精神人格特征的表现,之所以形成这种典范的公共舆论,是因为作者群一方面受到过传统文化的熏染,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大都有名士作风和儒雅性情,文如其人,展示了他们的个性与胸襟;另一方面,这些作者绝大多数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曾经耳濡目染西方文明的精华,浸染过西方经典文化,并且在长期的学院教育中养成了说理的思维方式和讨论的对话态度,因此,以他们为主体的“星期论文”的文风自然就亲切平易,晓畅动人,就好像与读者在谈心一样自然恰当。当然,这也与胡适作为“星期论文”的精神领袖,自觉地提倡一种朴实明白的文风有莫大的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专栏“星期论文”与当时活跃的一份同人刊物《独立评论》的精神旨趣是近似的,而这两个专刊(期刊)的作者群体也是高度重叠的。在1930年代胡适与陶希圣围绕行文风格的问题还发生了一场有趣的论战,通过对这场论争的考察,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捕捉到支撑“星期论文”学院风格的语言基础。胡适在表述方式这个问题上是毫不含糊的。论争缘起于胡适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的一篇题名为《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的评论。胡适在这篇文章里先是概述思想界的一个现象:“现在有一些写文字的人最爱用整串的抽象名词,翻来覆去,就像变戏法的人搬弄他的‘一个郎当,一个郎当,郎当一郎当’一样。他们有时候用一个抽象名词来替代许多事实;有时候又用一大串抽象名词来替代思想;有时候同一个名词用在一篇文章里可以有无数的不同的意义。我们这些受过一点严格的思想训练的人,每读这一类的文字,总觉得无法抓住作者说的是什么话,走的是什么思路,用的是什么证据。老实说,我们看不懂他们变的是什么掩眼法。”①
接着,胡适以陶希圣的文章《为什么否认现在的中国》为例进行分析。他认为陶希圣在文章中使用的“资本主义”概念是用一个抽象的名词来替代近代中国变法图强的诸多历史事实,用有特定内涵的“封建主义”概念来指称整个中国前现代历史,因而造成混沌、笼统和抹杀事实的恶果。而陶希圣认为没有殖民地,就没有资本主义的话语,在胡适看来,就是用连串的名词的排列来替代思想的层次,来冒充推理的程序,因此是作者文风上的懒惰和武断。陶希圣在同一个段落里六次使用语义分殊的“自由”概念,被胡适批评是“滥用一个意义可广可狭的名词,忽而用其广义,忽而用其狭义,忽而又用其最广义。近人用‘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等等名词,往往犯这种毛病。这毛病,无心犯的是粗心竦忽,有心犯的是舞文弄法”。②胡适把这种作文方式导致的后果归纳为“在思想上,它造成懒惰笼统的思想习惯;在文字上,它造成铿锵空洞的八股文章”。③
胡适把这种文风的罪魁祸首归结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字障的遗毒。古人的文字,谈空说有,说性谈天,主静主一,小部分都是‘囊风薄雾’‘捕风捉影’的名词变戏法。”④胡适所沿袭的仍旧是对中国传统文风的弊病的抨击,而不像时人会认为这是食洋不化的产物。最后,胡适针对这种滥用名词和概念的现象提出了诊治对策:“名词是思想的一个重要工具。要使这个工具确当,用得有效,我们必须严格的戒约自己:第一,切不可乱用一个意义不曾分析清楚的抽象名词。(例如用‘资本主义’,你得先告诉我,你心里想象的是你贵处的每月三分的高利贷,还是伦敦纽约的年息二厘五的银行放款。)第二,与其用抽象名词,宁可多列举具体的事实:事实容易使人明白,名词容易使人糊涂。第三,名词连串的排列,不能替代推理:推理是拿出证据来,不是搬出名词来。第四,凡用一个意义有广狭的名词,不可随时变换它的涵义。第五,我们要记得唐朝庞居士临死时的两句格言:‘但愿空诸所有,不可实诸所无。’本没有鬼,因为有了‘大头鬼’‘长脚鬼’等等鬼名词,就好像真有鬼了。滥造鬼名词的人自己必定遭鬼迷,不可不戒!”⑤
这篇文章一发表,马上引来陶希圣的反驳式回应。他在紧接着的《独立评论》第154号从几个方面反驳了胡适对其文风的批评。首先,他认为所谓以偏概全的掩眼法,如一说到西方就是资本主义,一说到中国文化就是八股、小脚、太监之类,如果成立的话,作为批评者的胡适在为文时一样地存在这种以局部事实做整体判断的倾向和表达。其次,他认为用抽象名词代替具体事实并没有错,也是现代社会知识专业化之后无法避免的,不可能通过穷尽罗列概念的方式去进行表达。胡适所谓的语言空泛是因为用抽象名词描述抽象事实所导致。最后,他认为胡适不允许其将近代中国设造船厂、办铁厂等看作资本主义,是因为胡适的“看法是孤立的、散乱的、琐碎与偶然的”。⑥而没有用联系的观点观察社会现象。
从陶希圣的回应文章来看,他巧妙地把胡适对其含糊、晦涩、滥用新名词新概念的行文风格的批评置换成思想方法的讨论,进而从思考问题应有的辩证联系的立场回击胡适,语言表达的争论转换成为思想方法是否妥当的问题。这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击中了胡适实验主义哲学的“软肋”。如论者所指出:“胡适将自然科学实验方法简单地套用到社会研究领域,势必将中国社会复杂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简单化、个别化、戏剧化了。由于他过于偏好对特殊问题、具体问题的个案处理,只进行社会现象的表面观察,而拒绝透过现象作更有价值的深度透视,因而使他对诸社会问题的内在联系显得茫然无知,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实验主义所提供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开药方式的方法显然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问题的脉络所在,从而与迫在眉睫的社会总危机全然隔膜。”⑦
换言之,胡适实验主义的渐进改良方法,是将整个社会看做一个支离破碎的断裂的非整体存在,因而拒绝以普遍联系的方式考察其内在关联,同时也拒绝给社会危机开出一个总体性解决的方案。这似乎是相当理性的实际的态度,但同时也是一种无法召唤民众乌托邦热情的“冷酷的理性”。试想如果没有反封建主义、反帝国主义等抽象名词的社会号召力,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就会丧失一个持久的动力泉源。⑧因此,陶希圣是将胡适对他的文风的批评看作是对其自身实验主义哲学的“语言辩护”,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掉转枪口对准胡适的痛处(也是其最为世人诟病的软肋之一)痛下针砭。
胡适在同期的《独立评论》上发表了《略答陶希圣先生》。胡适坚持认为晚清新政不能冠之以资本主义的名号,而是国家经营的经济实体。这自然牵涉到他们对资本主义概念的认识分歧。胡适如此为其哲学方法辩护:“实验主义的哲学并不反对人用一个抽象的观念来连贯一些现象。但它的主要方法是要人先把那个抽象名词的意义弄得明白。如果‘中国的封建主义’一个名词‘我们尚须研究’,那么,在我们研究的明白清楚之前,不得滥用”。⑨胡适的意思是学者在为文时对自己使用的概念首先自己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同时在写作的时候有一个明晰的界定,并且同一个词语不同的语义不能在同样的文本中混用,如果实在避免不了,则必须作出说明。这些要求确实有利于读者准确地理解作者所试图表达的含义,在1930年代的《大公报》“星期论文”中,很多政论都是按照这种严谨格式进行表达,而一些争论之所以发生除了政治立场或价值立场的分殊外,往往很多情况中是缘于对同一个概念的不同理解所致。
正是胡适的身体力行,保证了“星期论文”严格说理而很少含糊的学院化风格。胡适对语言表达清晰明白的自觉追求,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思维方法的问题,在其思想意识中者更是一个民族自救的根本途径的问题。这从他与陶希圣在私下的通信中可以断定。《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写于1935年5月27日。根据胡适1935年6月3日日记的记载,《略答陶希圣先生》的写作情境是“重检陶希圣兄送来驳我的文章,戏写短文,不满千字”。⑩一个礼拜之后,胡适写了一封长信跟陶希圣详细讨论思想与语言表达问题。他在该信中很坦诚地说到:“此次我借用尊文作例子,实无丝毫恶意,至多只有《春秋》‘责备贤者’之微意,因余人实不足引征也。领导一国的思想,是百年大计,必须以哀矜之态度出之,不可稍存草率。自误是小事,误人误国都是大罪。思想必须从力求明白清楚(clear and distinct)入手,笛卡儿所以能开近世哲学的先路,正因为他教人力求清楚明白。从洛克以至杜威、詹姆士,都教人如此。我们承两千年的笼统思想习惯之后,若想思想革新,也必须从这条路入手。此意我怀抱已久,七年前写《名教》一文,即拟继续鼓吹此意,终以人事匆匆,不能如愿。上月读你答我之文,——《否认现在的中国》——我深感觉你受病太深,而处此浇薄之社会中,绝少诤友肯为你医病解缚。因此,我忍不住作《思想弊病》一文,略指此种方法的缺陷。”(11)可见,胡适在这封信中主要讲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思想关乎国运,必须认真而切实,在思想的时候不可玩弄八卦,不可草率随意,而必须保持谦卑平和、整齐严肃之心态,否则因为思想的弊病而耽误国家复兴则是罪莫大焉。这主要是谈论思想观念的形成与表达应有的科学态度。第二层意思是对中外思想方式做了一个粗疏的划分,认为西方思想自笛卡儿以来直至洛克、杜威等思想家都主张明白清楚,而中国传统思想习惯是笼统含糊的。因此中国思想若想革新,必须从引进和学习西方学者的严密的思想方式入手。这等于在中国式思维方式和西方式思维方式之间做了一个价值判断。按照第一层意思,中国思想是必须革新的,因为它关系到民族国家的命运,而革新的方向按照第二层意思是必然向西方看齐的。这段话第三层意思是说明胡适自己为什么要以陶希圣为例证进行分析和批驳,因为他感觉陶受传统的笼统的思维方式毒害太深,而在“浇薄之社会”,个人自顾不暇或一团和气,不会坦率指出问题症结所在。胡适自认为“诤友”,所以便有义务指出。
陶希圣在6月12日的回信中,首先对胡适作为师长和诤友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表达了感激之情。然后,斩截地表明了痛下决心返朴归真的态度。他说:“从民十七时[起],曾抱决心,扫清过去的口号式文章,从事探讨,多谈问题,少作结论。近来偶作争辩,遂犯旧过,长夜深思,觉得不安。今后当再澄清这‘习气种子’,仍然多谈问题少作结论,以答规劝的盛意,这是至诚,决非‘外交辞令’。”(12)这正是当年胡适与李大钊等论战时所提出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实验主义态度。不过陶希圣并不是完全认同胡适对西方学术与思想的推崇备至,他也为其鼓吹文化的独立自主进行了辩白:“窃念我等对于国民稍负教育责任,在学术界‘自责’是应当的,在教育上则‘格外克己’也有不良影响。‘文化无国界’是在长久的理想上,是学者应当认识的;反之,在国民教育上,‘国界’恐怕还得留下。我以国际主义者转而重视这‘国界’,并不是一时的冲动。”(13)他认为在国民教育方面应该强调民族文化并重视国界,这有助于培养国民的民族国家意识和文化自信心。
对陶希圣的这番辩白,胡适并不赞同。他在当天的回信中,首先批评了陶希圣所谓的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双重写作标准。他坦率地说道:“我们教人信仰一个思想,必须先自己确信它,然后说来有力,说来动听。若自己不能信仰,而但为教育手段计,不能不说违心之言,自弃其信仰而求人信仰他自己本来不信仰的东西,我不信这个方法是可以收效的。依古人的说法,修辞立其诚,未有不诚而能使人信从的。”(14)这就涉及写作者的诚实的问题,即必须对自己的文字负责,自己所宣称的应该是自己所信仰的。胡适的这种写作态度也影响了“星期论文”作为公共舆论的特质,即每篇“星期论文”大都是作者经过严肃的思考得到的信仰,是作者诚实而坦率地书写自己的意见,这就内在地规定了“星期论文”的学理气味浓郁,而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那些不进行推理而盲目地宣传一种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文章,或者那些尖酸刻薄、冷嘲热讽、插科打诨的无聊文字。
自然,之所以能够在1930年代出现这样一个公共舆论的典范,也是在一个历史的进程中慢慢形成的。公共舆论在近代中国刚出现的时候往往是偏激而芜杂的,情绪性的谩骂往往湮没了学理的分析,并且这种谩骂、攻击、无所不用其极的话语方式反而更容易在社会层面获得强烈传播效果,启蒙话语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受众在思维、语言与精神上的高度同质化,这是近代中国公共舆论启蒙的悖论。杨国强在考察清末反满的公共舆论时就指出过:“由排满发为论说,重心在于攻击。由此,义理、辞章、考据都不足以为这种别成一类的文体立规范,攻击能够支配论说,攻击便已自成规范。于是人自为说不仅常常相扦格,而且容易信笔游走而漫无约束……只要事涉满汉,遍无禁忌。古来的士大夫留下过许多界限,而在知识人的手中都成了可以打碎的东西。”(15)
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的作者在讨论问题时显得理性多了,但仍然时时有一些惊世骇俗而经不起推敲的文章。“星期论文”作者之一的张熙若在1919年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尖锐地抨击当时以《新青年》为旗帜的所谓新文化运动的某些弊病。他在该信中指出:“《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今日同时收到,尚无暇细阅,略读数篇,觉其论调均差不多。读后感触是喜是悲,是赞成,是反对,亦颇难言。盖自国中顽固不进步的一方想起来便觉可喜,便觉应该赞成;然转念想到真正建设的手续上去,又觉这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议论,不但讨厌,简直危险。……尝思将来回国作事,有两大敌:一为一味守旧的活古人,二为一知半解的维新家。二者相衡,似活古人犹不足畏。此等维新家大弊,在对于极复杂的社会现象,纯以极简单的思想去判断。换言之,那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发为言论,仅觉讨厌,施之事实,且属危险。适之,这非老张现在退步,不过因为他们许多地方同小孩子一般的胡说八道,心有不安,不能不言耳。”(16)可见,早在15年前,张熙若等一部分知识分子就非常注意政论的文体问题了,并反对那种逞一时口舌之快,而将一些理论的夹生饭生吞活剥地灌输给读者,并指出这样的公共舆论如果仅仅是说说而已都让人觉得讨厌,如果一旦被当局采纳并付诸实践,那么就会流毒甚远危害社会。因此,对于像张熙若这样的学者来说,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意见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是关乎国家社会安危的大事,因此必须是有利于建设的理性的讨论,这个思路也是一直在现代中国公共舆论史里延续的,到了1930年代《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可以说发展到了顶峰的阶段。
胡适在前述给陶希圣的回信中指出只有通过忏悔和自责的方式才可能“创造新国”,“一个民族的思想领袖者没有承认事实的勇气,而公然提倡他们自己良心上或‘学术’上不信仰的假话,——即此一端,至少使我个人抬不起头来看世界。”(17)胡适强调的是说真话,诚实地表达意见,而不能为了一时所谓鼓舞士气的目的,故意夸张本民族的文化或压低西方文化的价值。这种说真话的方式并不代表说话者就不爱国,反而是一种理性的爱国行为的体现。这恰恰体现了马克思·韦伯致意再三的知识者必须保持“智性上的平实的诚实”。胡适是这样为自己辩白的:“请你注意我们提倡自责的人并非不爱国,也并非反民族主义者。我们只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而已。我们正因为爱国太深,故决心为她作诤臣,作诤友,而不敢也不忍为她讳疾忌医,作她的佞臣损友。”(18)
“星期论文”这种论述风格的形成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大公报》以言报国注重舆论的历史传统为“星期论文”的定位奠定一个良好的大报风范;“星期论文”作者群大多数学贯中西的知识结构使其面向公众发言时有清醒的自我认识,注意把道理说得深入浅出,其知识资源大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西学,二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等,三是他们在现实中所耳闻目睹的经验。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星期论文”的作者都有一种讨论和对话的心态,有一种容忍和多元的胸襟,简单地说,他们基本上是比较认同言论和思想自由的,并且认为好的见解是必须通过对话、交流和碰撞才能获取的,正因为这种思想上的共识或默契,他们都反对思想专制和思想盲从。
美学家朱光潜1937年4月4日发表在《大公报》“星期论文”上的《中国思想的危机》从反面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中国的思想界正面临着三个大危机:“第一是误认信仰为思想以及误认旁人的意见为自己的思想的恶习气。”“其次,我们所认为思想界危机的是因信仰某一派政治思想而抹煞一切其它学派的政治思想,甚至于以某一派政治思想垄断全部思想领域,好像除它以外就别无所谓思想。”“思想界的最严重的危机还不在以上所述两层,而在浮浅窄狭的观念因口号标语的暗示,在一般青年的头脑中深根固结,形成一种固定的习惯的反应模型,使他们不思想则已,一思想就老是依着那条抵抗力最小的熟烂的路径前进。”(19)朱光潜的意思很明确,他反对将思想与信仰混淆,思想是个体努力思考以及与别人对话的智慧结晶,是反思性的个体理性,而信仰则是不需要思考的,要求的是虔诚的服从和心灵的皈依。思想最大的敌人是思想的权利被某部分特权人士垄断,而大多数人的思想权利被剥夺,这就可能导致青年人容易形成思维惯性,一种奴性的缺乏思考力的条件反射,这种思考已经不是自由的思想,而是意识形态式的机械反应,是人被极权驯化后的自动按专制思维进行的思考模式。(20)这三者都是与思想的自由品质格格不入的,都是一元的、专制的和充满偏见的,尤其可恨的是这种固执的偏见又是与意识形态的建制化捆绑在一起的,因此这种洗脑是体制性的和日常性的,是制造顺民的有效工具。这自然与“星期论文”作者强调自由思想是背道而驰的,思想不自由成为他们最深恶痛绝的敌人,所以当他们自己在表达的时候就非常注意自觉排除这种思想上的专制,而尽量用一种说理的方式进行论述。
可以说,“星期论文”作为一种公共舆论,其存在本身就与当时存在的国民党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构成了深层的对峙。朱光潜认为要解决这三个危机,至少要做到:“我们应该学会怀疑,不轻下判断,不盲从任何派所谓‘领袖’,从多方面的虚心的探讨中我们会明白每一个问题都可有许多不同的看法,而绝对真理是极难寻求的。是非优劣由比较见出,集思才能广益。思想的最大的障碍是私见武断,而成功的要诀则在自由研究与自由讨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现在所最需要的不是某一种已成的思想(Thought),而是自己发开想,所必需的正确的思想习惯(Thinking habit)。”(21)可以说,“星期论文”正是这样一种自由思想和平等对话的言论实践,这种实践对于现代中国公共舆论的成熟无疑是具有示范性意义的。
陈仪深通过对《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的历史考察,认为以胡适为首的知识群体的言论体现了一种鲜明的“自由主义论政风格”,他将其内涵概括为三个层面:在知识分子内部争论中“容忍异见”,面对统治势力“不畏强御”,针对一般民众的发言“不赶时髦”。(22)基于《独立评论》和《大公报》“星期论文”作者的高度重叠特征,陈仪深的这种论断同样可以用来描述“星期论文”的论政风格,其实也就是当时以《独立评论》、“星期论文”等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的论政风格,这种自由主义论政风格所折射的恰恰是现代中国成熟的公共舆论的话语特征和理性品质。
胡适的论政风格奠定了“星期论文”的特色,在纪念《独立评论》创刊一周年的文章中,胡适曾从一个侧面概括学者论政应有的品格,他认为:“第一是‘成见不能束缚’,第二是‘时髦不能引诱’。现今有许多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不能用思考与事实去打破他们的成见;又有一种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他们不能抵御时髦的引诱。‘成见’在今日所以难打破,是因为有一些成见早已变成很固定的‘主义’了。懒惰的人总想用现成的、整套的主义来应付当前的问题,总想拿事实来傅(附,引者注)会主义。有时候一种成见成为时髦的风气,或成为时髦的党纲信条,那就更不容易打破了。我们所希望的是一种虚心的、公心的、尊重事实的精神。”(23)铲除成见,拒绝时髦,对于一个崇尚自由思考的知识分子而言应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民国,很多知识分子渴求着解除民族危难之法,各种西方思潮如走马灯般在中国知识界传播,大多数思想体系都试图给中国一个整全性的一劳永逸之解决方案。在这种历史情景下,知识分子的表达往往很难规避“成见与时髦”的双重面影。而胡适一直倡导的朴素平易的文风对于建设成熟稳健的公共舆论就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周策纵在纪念胡适逝世25周年时曾经专门指出其语言风格层面的表达特征:“从胡先生作品的风格来说,大凡读过他诗文的人,没有不觉得非常浅显明白,本末条理,通顺流畅。无论你同意不同意他所说的,你总觉得他在说清事理;当然,有时也只是他自己斟酌选择过的事理;但比起许多别人来,他多半还是比较公平的。即使他反对或责备人,作品里却从来不盛气凌人,不生气,不讥讽挖苦,不故意损伤别人的自尊心,不骂人。尽管别人冤枉他,骂他,也不生气,不对骂。这样叙事、说理、分析的文章,在中国是凤毛麟角,非常罕见的。我虽然不完全赞同他主张写诗必须明白清楚,但我充分承认那种明白清楚的诗也自有它的特色和好处。胡先生作品的风格,我也许可以可用‘平情顺理,清浅流丽’八个字来概括。”(24)正是因为胡适的身体力行,以及胡适派学人群的同气相求、遥相呼应,“平情顺理,清浅流丽”的文风也就成为《大公报》“星期论文”论述风格的主要特色,成为作者群体在政论写作中的“集体无意识”式的共识,职是之故,“星期论文”才可能成为1930年代中国式公共舆论之典范。
注释:
①胡适:《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独立评论》,1935年6月2日第153号。
②同上。
③同上。
④同上。
⑤同上。关于胡适的语言风格的研究,可参阅陈平原:《“精心结构”与“明白清楚”——胡适述学文体研究》,台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2年12月第38期。
⑥陶希圣:《思想界的一个大弱点》,《独立评论》,1935年6月9日第154号。
⑦许纪霖:《胡适:社会改造中的理性贫困》,《许纪霖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
⑧格里德曾经在其著作《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对胡适的实验主义哲学提出这样的疑问:“一种不谈终极目的的社会哲学能够提供充分的目的与方向意识?被看作是一种方法论‘变迁媒介’的自由主义是否可以产生伟大事业所必要的热情?照此解释的自由主义在实际中能否从分析转入行动?”,详见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2页。
⑨胡适:《略答陶希圣先生》,《独立评论》,1935年6月9日第154号。
⑩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82页。
(11)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91页。下同。
(12)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第494页。
(13)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第494-495页。
(14)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第495页。
(15)杨国强:《论清末知识人的反满意识》,《史林》,2004年第3期,第20-21页。
(16)张熙若:《张熙若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8-419页。
(17)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第496页。
(18)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第496页。
(19)朱光潜:《中国思想的危机》,《大公报》“星期论文”,1937年4月4日。
(20)思考与个体的道德品质之间的关系,可参阅阿伦特晚年文集《责任与判断》中的《思考与道德关切——致奥登》一文,陈联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1)朱光潜:《中国思想的危机》,《大公报》“星期论文”,1937年4月4日。
(22)陈仪深:《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5月版,第240—251页。
(23)胡适:《独立评论的一周年》,《独立评论》,1933年5月21日第51号。
(24)周策纵:《胡适风格(特论态度与方法)——胡适先生逝世廿五周年纪念演讲会讲稿之二》,台北:《传记文学》,1987年3月第50卷第3期。
标签:胡适论文; 陶希圣论文; 1930年论文; 胡适日记全编论文; 大公报论文; 读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社会舆论论文; 新青年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