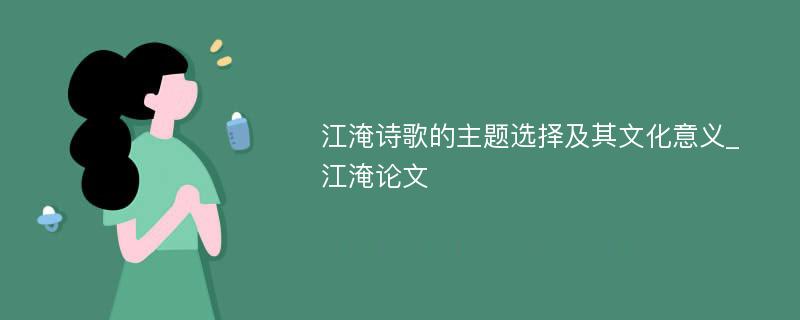
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题材论文,诗歌论文,意义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江淹除擅长拟古题材的诗歌创作之外,还写下相当一部分的游历与赠和之作。无论是哪种题材的作品,都是江淹本人的生活经历、当时的政治局面以及诗坛风向的侧面折射,蕴含着极为丰厚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 江淹 拟古诗 游历诗 赠和诗 文化意义
由于江淹晚年背负“才尽”的恶名,致使长期以来对他的研究远远不够全面和深入。即使在有限的研究中,人们也只是把眼光局限在其“善于摹拟”的作品之上,而对江淹摹拟之外的其他题材的诗歌论之甚少,这与江淹“诗体总杂”的创作实际极不相称。有鉴于此,本文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辑,把江淹诗歌按题材划分为拟古、游历、赠和等几个主要方面,试图对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进行一番考察。
一
在江淹现存的百多首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拟古诗,包括《杂体诗三十首》、《学魏文帝》、《效阮公诗十五首》,计四十六首。可见拟古诗在江淹全部诗作中的重要地位。
关于《效阮公诗十五首》的写作背景与时间,江淹在《自序传》中云:“宋末多阻,宗室有忧生之难,王(指刘景素)初欲羽檄征天下兵,以求一旦之幸。淹尝从容晓谏,言人事之成败。每曰:‘殿下不求宗庙之安,如信左右之计,则复见麋鹿霜栖露宿于姑苏之台矣。’终不以纳,而更疑焉。及王移镇朱方也,又为镇军参军,领东海郡丞。于是王与不逞之徒日夜构议,淹知祸机之将发,又赋诗十五首,略明性命之理,因以为讽。”从这段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江淹的这组诗实际上是借拟古以讽谏刘景素的不轨之谋,其写作时间大致在泰豫元年(472)七月至元徽二年(474)秋江淹随景素镇京口这两年间。
江淹的另一组拟古名作《杂体诗三十首》,据曹道衡先生考证,“似当作于建元末,最迟恐亦在永明初年”。[①]这组诗作前面有作者自序一篇。从《杂体诗序》来看,江淹创作这三十首诗并不是一味地拟古,而是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主要是针对当时理论界存在的部分偏向有意而为。这些偏向包括“各滞所迷”、“贵远贱近”、“重耳轻目”等,这对于当时的主要诗歌形式五言诗的健康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正因为如此,江淹希望通过“品藻渊流”、“商榷”等方式,来表达他对五言诗“通方广恕,好远兼爱”的观点。从《杂体诗三十首》所选诗人的情况来看,江淹的拟作选取了自汉代至刘宋末年的29位作家(第一首为无主名的古诗),其中汉2人,魏4人,晋15人,宋8人。晋宋作家占了绝大部分,这可以说是对“贵远贱近”理论的反动。如果把稍后的《文心雕龙·明诗》中所提及的五言诗作家与江淹拟取的对象作个比较,我们发现刘勰提及的作家中有15位与江淹模拟的对象相同,他们是李陵、班婕妤、曹丕、曹植、王粲、刘桢、嵇康、阮籍、张协、潘岳、左思、陆机、孙绰、郭璞、张华。如果剔除江淹拟作中8位刘宋作家,那么可以更加明确地发现,江淹与刘勰对汉魏晋五言诗的发展成就与代表作家基本上持相同观点。再把稍后的《诗品》与江淹的拟作做个比较,我们发现江淹所拟的29位作家,《诗品》中均有品评,其中11人居上品,13人居中品,5人居下品。从中可以看出江淹在选拟作家时既考虑到艺术成就的高低,又考虑到艺术风格的不同,真正做到了“玄黄经纬之辨,金碧浮沉之殊,仆以为亦各具美兼善而已”。同时还可看出钟嵘与江淹在理论上的某种一致之处。
从《杂体诗三十首》模拟的题材来看,江淹拟作也有较大的价值。我们先把江淹拟取的题材与其后《文选》中确立的诗歌题材做个对照。《文选》中肖统共确立诗歌题材23个条目,其中和江淹拟取的题材完全相同的有咏史、游仙、游览、咏怀;题材大致相似而名称稍异的有述德(怀德)[②]、公宴(游宴)、哀伤(述哀)、赠答(赠别)、行旅(羁宦)、军戎(从军、戎行)、郊庙(从驾)、杂歌杂诗杂拟(杂述);题材之间有内在联系而名称不同的有劝励(言志)、献诗(感遇)、祖饯(离情、怨别)、招隐反招隐(田居)、挽歌(养疾)。根据上述的统计可以看出,《文选》诗歌的立目只有补亡、百一、乐府三类与江淹拟作的题材不能对应,而这三首之间,百一和乐府严格地说来并不是诗歌的题材,而是诗歌的体式。这样,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所模拟的题材的价值就充分体现出来了,他为肖统《文选》在诗歌立目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江淹选择拟古这一诗歌题材进行创作的文化意义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一、发扬光大了拟古诗这一特殊的题材,为拟古题材的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作出了贡献。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辑,魏何晏有《拟古诗》一首,这大概是现存最早的拟古诗了。晋宋之际,从事拟古的作家及作品愈来愈多,著名的有陆机《拟古诗》十二首,谢灵运《拟邺中咏》八首,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等。但这些拟作或模拟一个时期的一批作品,或模拟一个时期的一部分人作品,或模拟某一类题材的作品,在模拟对象的分布及时代的跨度等方面均不及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广泛和长久。当然,就拟作本身的艺术价值而论,鲍照《拟行路难》则明显高出其他拟作一筹,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江淹拟古之作应有价值的理由。相反,肖统《文选》立“杂拟”一目,计录诗六十三首,而江淹《杂体诗三十首》被悉数收入,占收录的全部拟作的一半,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江淹拟古之作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二、用创作实践客观形象地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表达出作者独特的文学倾向。在江淹之前,虽然五言古诗曾出现过建安初期的“腾踊”之势,但这并没有为理论界予以充分的肯定。挚虞《文章流别论》云:“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而约与江淹同时的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也说:“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两人都认为四言诗是“正体”,而五言诗则是四言诗的“流调”。这种观点大概就属于江淹在《杂体诗序》中提到的“贵远贱近”、“重耳轻目”一类。为了扭转这一理论偏向,作为诗人的江淹用独特的形式——模拟前人的作品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文学观点,从创作实践这一角度给五言诗以充分的肯定。江淹的看法对后来钟嵘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钟嵘在《诗品序》中对五言诗的肯定,在品评其他诗人时对江淹的揄扬[③],在具体品评江淹时,说他“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朓”,[④]这些都可以作为江淹文学观点影响钟嵘的侧面证据。三、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钟嵘《诗品》云:“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最早对江淹拟古诗给予高度评价。其后历代评论家对江淹拟古之作间有评论,大都持褒扬之观点,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曰:“拟古推江文通最长,拟渊明似渊明,拟康乐似康乐,拟左思似左思,拟郭璞似郭璞,独拟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汉耳。”严羽在肯定江淹拟作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部分不足。虽然江淹的诗歌创作并不仅仅停留在拟古的层面之上,但后人一提起江淹,对其拟古之作总是津津乐道,江淹也因此在诗歌史上获得了重要的位置。
二
除了拟古之作,江淹诗歌中经常涉及的另一题材是游历。然而这一题材的作品却很少为人提及,大概是由于人们过份看重江淹的拟古之作及辞赋而对江淹集中游历题材的作品有所忽视的缘故。按创作时间的先后划分,江淹的游历之作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江淹赴荆州前所作,如《望荆山》、《秋至怀归》、《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等;二是江淹随刘景素在荆州时所作,如《从建平王游纪南城》、《渡西塞望江上诸山》等;三是江淹被贬吴兴后所作,如《赤亭渚》、《渡泉峤出诸山之顶》、《迁阳亭》、《游黄蘖山》等[⑤]。
综览江淹的游历之作,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江淹诗中描摹的景色不可谓不美,但诗人的心境却始终没有乐山乐水的悠闲。如《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一诗描摹了庐山香炉峰仙境般的景色:“瑶草正翕赩,玉树信葱青。绛气下萦薄,白云上杳冥。中坐瞰蜿虹,俯伏视流星。不寻遐怪极,则知耳目惊。”又如《渡西塞望江上诸山》,诗人从时空转换、动静结合、色彩变更多重角度摹景写意,使诗歌摇曳生姿。然而诗人的心境却是一片萧瑟,如“零泪染衣裳”(《望荆山》)、“尤照忧人情”(《从建平王游纪南城》)、“一伤千里极”(《赤亭渚》)等诗句即为明证。通过对这一矛盾的深入分析,我们就会清晰地看出江淹游历之作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江淹的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据蕴含在江淹三类游历之作中的情感走向来看,大致经历了一个由感伤到忧惧再到怀归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形成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密不可分的。即以感伤的心绪为例,在文通第一次被诬获罪之后,虽然得到了刘景素的赦免,并且很快转为巴陵王休若的右常侍,但他内心的感伤情绪仍然挥之不去,这从他的《望荆山》《秋至怀归》等作品中可见一斑。那么,为什么江淹在景素幕中已有被诬获罪的历史却仍然不以转任休若右常侍为乐呢?这不能不涉及到当时的政治环境。明帝刘彧即位以后,对他的兄弟如休仁休祐休若等并不信任,《宋书·刘休若传》曰:“上以休若和善,能谐缉物情,虑将来倾幼主,欲遣使杀之。”在江淹入休若幕府之前,休若已两次遭到明帝的降职处分,明帝甚至对休若结私瞒上的行径指责说:“孝建、大明中,汝敢行此邪?”因此,休若在明帝朝的政治前途并不光明。秦始七年(471)七月,休若最终被赐死。反之,刘景素在明帝时政治地位呈上升的趋势,一方面景素比较年轻,羽翼未丰,另一方面他是明帝的晚辈,对明帝的统治暂不构成威胁,直到明帝临终前,由于考虑到太子幼弱,才想到对景素的势力进行牵制。由以上分析可见,江淹在赴襄阳休若幕府时的心境是灰暗的,对自己将来的政治前途充满了忧虑,反映到作品中,使得这一时期的游历之作饱含感伤的情调。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说,江淹在他这一时期的游历之作中流露的心绪,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险恶的政治氛围对诗人的影响。换句话说,江淹的游历之作也内包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意义。
江淹的游历之作还形象地描绘了闽地的奇山秀水,为诗国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空。在江淹之前,人们对闽中的了解十分匮乏,在作品中加以表现的更是寥若晨星。西晋张协《杂诗十首》(其八)云:“闽越衣文蛇,胡马愿度燕。”刘宋时的谢灵运在《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中亦云:“闽中安可处?日夜念归旋。”两人均表达了闽越乃蛮荒之地,于此不可久居的想法。即使是后于江淹的谢朓、萧纲等人对闽中的偏僻仍存畏惧心理,“南中荣桔柚,宁知鸿雁飞”(谢朓《酬王晋安》)、“章甫翠履之人,望闽乡而叹息”(萧纲《与湘东王书》)即可为证。江淹在去吴兴赴任前也是心有疑虑的,《被黜为吴兴令辞笺诣建平王》云:“淹乃梁昌,自投东极,晨鸟不飞,迁骨何日?”以致他“眷然西顾,涕下若屑”。然而,一旦江淹踏上闽中的土地,立即被眼前的碧水丹山及珍木灵草所吸引,于是他用五色的彩笔,绘出了一幅闽地山水风光的画卷。如他在《渡泉峤出诸山之顶》中写道:“万壑共驰骛,百谷争往来。鹰隼既厉翼,蚊鱼亦曝鳃。崩壁迭枕卧,崭石屡盘回。伏波未能凿,楼船不敢开。百年积流水,千里生青苔。”在《游黄蘖山》中又写道:“残屼千代木,廧崒万古烟。禽鸣丹壁上,猿啸青崖间。”这里有遮蔽日月的山峰,往来驰骛的山谷,也有百年的流水,千里的青苔;有千代的松木,万古的云烟,也有丹壁上的禽鸟,青崖间的猿猴。真可谓“南州饶奇怪,赤县多灵仙”(《游黄蘖山》)。甚至在诗人眼中,闽中“下视雄虹照,俯看彩霞明”(《迁阳亭》)、“金峰各亏日,铜石共临天”(《游黄蘖山》)的高耸地势,连蜀地峭峻的山峰也望尘莫及,“剑迳羞前检,岷山惭旧名”(《迁阳亭》)就是一个说明。江淹在诗歌中对闽中山水的描绘,第一次使人们通过艺术的形式领略了闽地的真实风貌,加深了人们对边地的了解。同时,江淹的这部分作品也拓宽了山水游历诗歌的题材范围,在引导诗人们把目光投向边远之地的山水景色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我们认为江淹的闽地游历之作为诗国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空,文化意义殊不可抹。
三
赠和之作在现存江淹诗歌中占有一定的比例,有十数首之多。然而同江淹的游历之作一样,江淹这类题材的诗歌也鲜为人重视,这对全面深入地把握江淹诗歌创作的走向与价值极为不利,因此有必要对江淹的赠和之作进行恰当的分析和评判。
据曹道衡《江淹作品写作年代考》,除去《秋夕纳凉奉和刑狱舅》、《当春四韵同□左丞》这两首作品难以考定写作年代外,江淹的其他赠和之作均可考出大致的写作年代。其中最早的一首赠和之作当为《贻袁常侍》,此诗作于泰始四至五年(468—669)。而作于永明三至四年间(485—486)的《郊外望秋答殷博士》可能是江淹最晚的一首赠和之作。从江淹赠和之作的时间跨度上来看,这些作品基本上写于江淹出仕以后的十余年间,这正是江淹仕途蹭蹬心绪复杂的时期。
江淹赠和之作的价值和意义集中体现在艺术表现方面,它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我们知道,元嘉诗风的代表作家是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对于这三家的诗歌风格,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有一段精辟的议论:“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魄。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从这段议论中可以看出,元嘉诗风的优点是讲求典雅、用事、对偶、藻丽,这对革新东晋以来质木无文的玄言诗风无疑做出了贡献。然而元嘉诗风的缺点也因此而并存其间,如酷不入情、顿失清采、操调险急等等。这与诗歌崇尚抒情委婉、丰神绰约的本质特点相去甚远。永明时代,人们明显意识到元嘉诗风的不足而力图新变,据《南史·王筠传》载,谢朓曾提出“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的观点,沈约更是力主“三易”说(《颜氏家训·文章》中:“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他们不仅在理论上提倡平易的诗风,而且在创作实践中也身体力行。江淹恰好处于元嘉和永明这两个时期的中间,客观上具备诗风过渡的时空条件,江淹主观上的努力也使得其诗风的过渡性尤为明显,这一特点特别体现在其赠和之作的创作上。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了解到江淹的拟古之作具有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文化意义,但这究竟还是模拟。认为江淹的拟古之作完全代表其本人的诗歌风格,这难免牵强附会。其实,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早已指明:“(江淹)虽长于杂拟,于古人苍壮之作亦能肖吻,究非其本色也。”而江淹的游历之作在风格上偏重于继承元嘉诗风的古奥与典密,承前的特点鲜明,启后则不甚明了。如《游黄蘖山》就是典型的例证,这不仅体现在该诗的用语古奥晦涩,如“残屼”、“廧崒”等,而且还体现在部分句子即是直接从元嘉诗人的句子中化出,如“禽鸣丹壁上,猿啸青崖间”即是化用鲍照《登庐山望石门》诗中的“鸡鸣清涧中,猿啸白云里。”因此,江淹赠和之作所体现出的诗风的过渡性愈加明晰地显露出来,具体表现为:一、抒情的清婉。如《贻袁常侍》、《卧疾怨别刘长史》、《应刘豫章别》、《池上酬刘记室》等篇采用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手法,曲折地写出诗人与友人间的离情别绪;《寄丘三公》、《灯夜和殷长史》等篇采用比兴手法抒写友情的真挚,笔调婉转,感人至深;“琴高游会稽,灵变竟不还。不还有长意,长意希童颜”(《赠炼丹法和殷长史》)、“戚戚忧可结,结忧视春暮”(《池上酬刘记室》)则采用了顶真的表现手法一吐诗人的忧惧之情。以上这些清真委婉的抒情方式,对诗歌的表情达意起到了烘托映衬的作用,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二、语言的清丽。江淹赠和之作在词语方面较多地采用了叠字和联绵词,如寂寂、永永、猎猎、飒飒、怅怅、戚戚等是叠字;皎洁、踟蹰、佗傺等是双声;烂熳、浸淫、泛滥、萧条等是叠韵。这些词语的使用避免了生涩,使诗歌走上了清秀的正路。在句子方面,他大量采用了对仗的方法,根据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二十九种对》的划分,江淹的赠和之作主要运用了以下几种对仗方法:一是的名对,如“卧歌丹丘采,坐失曾泉光”(《灯夜和殷长史》)、“水馆次夕羽,山叶下暝露”(《池上酬刘记室》)等;二是隔句对,如“昔别楚水,秋月丽秋天;今君客吴坂,春色缥春泉”(《贻袁常侍》)等;三是联绵对,如“铄铄雾上景,懵懵云外山”(《贻袁常侍》)、“猎猎风剪树,飒飒露伤莲”(《应刘豫章别》)等;四是叠韵对,如“浸淫泉怀浦,泛滥云辞山”(《应刘豫章别》、“萧条晚秋景,旻云承景斜”(《秋夕纳凉奉和刑狱舅》)等。江淹运用对仗的手法与元嘉诗人颜延之非对偶不成句的极端做法明显不同,江淹运用对仗一方面是为了增加语言的整饰美和秀丽美,更重要的是为了抒情的需要,这是值得提出的一点。
注释:
①曹道衡《江淹作品写作年代考》,载《艺文志》第3辑。
②括号内为江淹拟作的题材,下同。
③如《诗品》在品评范云、丘迟时,说他们“故当浅于江淹,而秀于任昉”;在品评沈约时,说他“故当词密于范,意浅于江也”。
④陈庆元《江淹“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脁”辨》一文,认为此句当理解为“筋力强于王微,成就高于谢朓”。载《文学遗产》1985年第4期。
⑤关于江淹游历之作的创作时间,可参见吴丕绩《江淹年谱》、曹道衡《江淹作品写作年代考》(见《艺文志》第3辑)、丁福林《江淹诗文系年考辨》《江淹著述又考》(分见《河南师大学报》1987年第3期、《扬州师院学报》1992年第1期)、母美春《江淹诗文系年考辨》(见《南京师大学报》199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