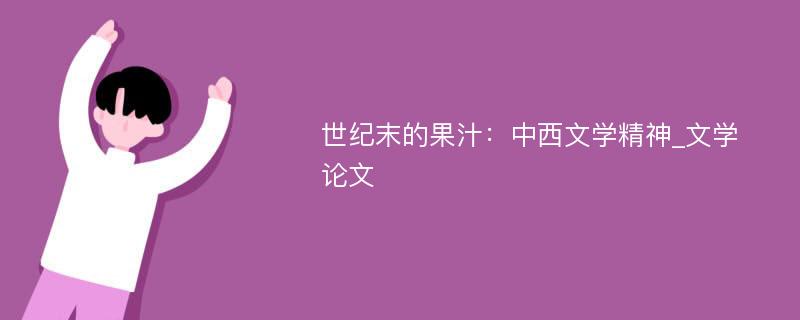
——“世纪末果汁”:中西文学的精神遇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末论文,果汁论文,中西论文,精神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世纪文学回顾
引言:“世纪末”的灵感
20世纪中国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与世界文化和文学广泛联系的基础之上的。百年文学史一定程度上是文学思潮流变史,这其中西方文学思潮又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催化剂。故此,清理中外文学思潮的关系,应该是20世纪文学回顾与反思的题中应有之义。值得注意的是上个世纪之交,人们好作“近三百年的学术反思”,而这个世纪之交则瞩意“百年沧桑”。看来,灵感和机遇都离不开“世纪末”语境。世纪老人季羡林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现在又到了一个世纪末。很多人,特别是对时间推移一向敏感的知识分子,都对即将来临的一个新世纪有所考虑,有所幻想。我现在就常常考虑21世纪的情景。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世纪的转折点并不总是意味着社会发展的转折点,也不会在人类前进的长河中形成一个特殊的阶段,但是世纪末往往对人类的思想感情产生影响,上一个世纪末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1)]虽然季先生没有具体论述上一个世纪末对人们思想感情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但我们确实知道,上一个世纪之交,对于中国近代社会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们的思想、感情、观念、心理以及与此相联的行为和实践,异常丰富和活跃,生动地带有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特征。如果稍微放宽一点,上一个世纪之交,大体可以包括19世纪的最后10年和20世纪的最初30年。这40年的时间,正好是具有268年历史的封建清王朝的最后岁月,也是我国封建君主专制嘛义王朝的末日,同时也是中国人争取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社会进步的艰难斗争的40年。由于新旧世纪的交替同剧烈的社会变革、政治变革、文化变革交织在一起,就使得历史内涵变得更加丰富,更加深邃。诞生在这个时期的中国新文学,也就必然带上了世纪之交的种种文化现象。在这种情境下西方的世纪末思潮适时而入,在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世纪初的梁启超和王国维都敏锐地注意到了这股思潮,在他们的文章中开始出现叔本华和尼采的名字,这使得他们对悲观厌世精神有了极为深刻的自觉。王国维把《红楼梦》看成是“悲剧中之悲剧”,梁启超则得出了“中国文学,大率最富于厌世思想”的认识,并因其“极凄惨,极哀艳”而赞赏《桃花扇》。[(2)]吴趼人干脆在《上海游骖录》中公开提倡“厌世主义”。而《老残游记》中的“沉船之梦”,陈天华《瓜分惨祸预言记》中“万民遭劫,全国为墟,积骸成山,流血成河”就简直是一幅“世纪末日”的图景了。内忧外患,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以至于清末民初的小说“半皆怨史”,虽不能说这是一种“世纪末情绪”,但也至少构成西方世纪末思潮传播和影响的接受心态。作为一种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浓郁的“精神氛围”,我们不能忽视清末民初这种悲观厌世情绪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可以说,正是这种思想资源与西方世纪末思潮的历史汇流,决定了五四启蒙主义不同于欧洲18世纪启蒙主义的特质和内涵。也就是说,虽然科学、民主、进步观念占很重要的地位,但文明没落与种族退化论也影响深远,个中原由离开西方的世纪末思潮恐怕很难说明问题。
知识源考:“世纪末果汁”在中国
从知识考源的角度来看,西方学术意义上的“世纪末”(原系法语Fin de Siécle)有两种含义:一是指1870年至1900年这段时期西方人对世界前途和文明前景普遍抱有的悲观恐惧心理,即所谓的世界末日之感,二是指19世纪末在法英等国兴起的以波德莱尔、王尔德、比亚兹莱等艺术家为代表的具有近代颓废和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艺思潮。西方“世纪末”思潮是一种特定的历史产物,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自身演化出的一种反动倾向,带有极其强烈的反传统主义和典型的非理性主义色彩,它既是西方现代文明走向危机阶段的产物,又是对这种危机的文明的深刻反思和强烈抗议。这种思潮反映到文学上,是对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反拨,其主要表现在艺术追求上的唯美主义和精神特征上的颓废主义。西方近代心理科学的发展,哲学主体观念的变革,以及宗教精神的异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观念和结构形态,使文学明显地倾向于语言和结构的唯美化,倾向于主题内涵的心理化。这种文学思潮形成于19世纪最后30年,到本世纪初达到高潮。从世纪末思潮在历史上的演变,地域方面的伸展,美学的实质,以及它的种种表现来看,其现实性和独创性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文艺思潮是对19世纪后期西方社会和文化变革进行的一次探索性的认识活动,是欧洲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是沿着启蒙运动和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发展而来,本质上是沉没了一个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化思潮的复兴或变种。西方19世纪后期的中心问题是追求人或自我在社会群体中的价值和地位,是人的第二次解放。但是,由于这是一个新旧历史的交错时期,所以,这次运动表现出某些颓废和忧郁倾向,既有对日渐破碎的传统意识的追念,也有对新时代来临前的迷茫进行痛苦挣扎的成分。它首先是作家内心世界中产生的一种对生活的战栗情绪,一种把衰老文明看透了的懒散感觉。不妨说,这是一次具有“灵魂骤变”意义的整体颓废主义的文化体现。陈独秀说欧洲“世纪末”是“赤裸时代”、“揭开假面时代”,指的就是“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一切破坏”。[(3)]张闻天的观察更细致,他认为欧洲的精神状态“由怀疑而生苦闷,因苦闷而厌世悲观,由机械的命定论而绝望,由绝望而消极愤世。……于是在法兰西发生所谓‘世纪末’,在俄罗斯发生所谓‘世界苦’(Toska)”。张闻天认为“在这种愁云惨雾底中间”,人类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正视丑恶人生,二是逃避丑恶人生。[(4)]这两条路在艺术上的表现即所谓“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二者的矛盾和冲突构成了西方世纪末文艺思潮的主旋律。这种思潮在世纪初的中国得以广泛传播,主要源于和西方社会某种相似的深刻的社会和精神危机。正如鲁迅指出的那样:
那时觉醒起来的知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是分明的看见了周围涯际的黑暗。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纪末”的果汁:王尔德(Oscar Wild)、尼采(Fr.Nietzsche)、波德莱尔(Bauder Laire)、安德莱夫(L.Andrev)们所安排的。“沉自己的船”还要在绝处求生,此外的许多作品,就往往“春非我春”“秋非我秋”,玄发朱颜,低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5)]
可以说“世纪末果汁”所蕴含的个体本位主义和触及人的内在生命力的艺术哲学,为五四作家提供了崭新的视野:象征主义的神秘与幽微、唯美主义的怪僻与耽溺、颓废主义的焦虑与绝望使五四新文学的精神特征呈现出全新的“现代性”色彩。下面我们试以这三种思潮的代表人物为例,看看世纪末思潮在中国的具体反应。
王尔德是作为极具革命性的理论家和富有挑战性的戏剧家而引起五四文坛注意的。作为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乃至整个世纪末思潮的领袖和奠基人,他所鼓吹的“文艺复兴论”激起五四作家的极大热情。王尔德曾对英国的唯美主义运动从两个方面加以定性:第一,他称英国唯美主义文艺运动是“英国的文艺复兴”,理由是“因为它的确是人的精神的一次新生,同15世纪伟大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一样,它渴慕更为美好,更为通情达理的生活方式,追求肉体的美丽,专注于形式,探索新的诗歌主题,新的艺术样式,新的智力和想象的愉悦。”第二,他称唯美主义是“我们的浪漫主义运动”,理由是“因为它是我们对于美的最新表达”,也就是“在气度恢宏,意向清明,静穆优美的希腊精神与异国情调、张扬个性、情感激荡的浪漫精神的联姻中,产生了英国的19世纪艺术”。[(6)]这种本质上是一种反抗与抗议的运动,无疑非常适合五四文学革命者的期待视野,1921年和1922年是王尔德在中国声名显赫的两年,其实反映了中国文坛的某种现实需要。特别是王尔德的剧本《莎乐美》引起中国作家的极大兴趣。王尔德在剧中运用反讽的技法,强化莎乐美身上的“美的邪恶”来反衬世俗社会对“美”的恐惧和扼杀,并从其一贯的对苦难的病态崇拜出发,将莎乐美的命运推至极端,在西方社会掀起轩然大波。然而在中国王尔德却并未被看作是“堕落派”(Decadent),对《莎乐美》的评价,张闻天就不同意外国评论家指出的“色情和肉感的气氛”,而宁愿把它看成是“恋爱悲剧的妙品”,认为此剧是“描写灵肉冲突而结果是肉的悲惨的运命”。五四作家几乎不约而同都抓住了《莎乐美》的这一主题,以至于章士钊和陈独秀在评论苏曼殊的小说《降纱记》时都想到了《莎乐美》。也许正是莎乐美的悲剧命运打动了中国的戏剧家,使得该剧成为中国早期戏剧界第一部从内容到形式产生广泛影响,并有实质性借鉴的戏剧作品。
波德莱尔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白话诗单纯而浅直的浪漫主义境界,赋予现代诗以较大的思想深度,使孤独、焦虑、恶魔般的解剖和本源性的绝望,成为五四作家某一时期着重的人生体验和精神特征。田汉把波德莱尔与一般的浪漫主义者区分开来,把他称为“醴卡耽主义(Decadent)和象征主义先驱”以及“恶魔主义的泰山北斗”。他不仅从波德莱尔身上发现了“人性之真”,而且从《恶之华》怪异、险奇、凄怆的“纯艺术品”中发现了对世纪末社会的现实投入。[(7)]周作人为波德莱尔辩护说:“他的貌似的颓废,实在只是猛烈的求生意志的表现,与东方式的泥醉的消遣的生活,绝不相同,所谓现代人的悲哀,便是这猛烈的求生意志与现在的不如意的生活的挣扎”。[(8)]这说明五四作家最初对波德莱尔的同情与理解,看重的是他对世纪末生活心态的无情剖露,其作品里充斥着透不过气来的窒息感,行动上的无能为力,精神上的孤独与苦闷,无法救药的厌倦,阴森可怖的环像,不得不生活的痛苦,可以说波德莱尔以一种愤世嫉俗而又玩世不恭的态度所表达的这种“世纪末情绪”极大地感染了正在寻求出路的五四文学青年。
插画家奥勃莱·比亚兹莱是英国世纪末颓废派艺术活动的重要代表,19世纪末著名刊物《黄面志》(The yellow book)的美术编辑,今天的文学史家习惯称十九世纪末的英国文坛为“比亚兹莱时代”,指的是以这位短命的画家为中心,以《黄面志》为阵地的那一批画家、诗人和散文家。世纪末的英国是一个充满苦闷和颓废的社会,比亚兹莱就是在这种倾向上反映得最敏锐的一个画家,他的画那种浓郁的装饰趣味的影响并不亚于其它艺术门类。五四新文艺爱好者能够有机会知道这个刊物和比亚兹莱是因为郁达夫发表在《创造周报》(1923)上的一篇介绍文章《The yellow book及其它》,叶灵凤回忆过:“我年轻的时候是爱好过王尔德的作品的,也爱好过英国‘世纪末’那一批作家的作品的。这可说全是受了郁达夫先生的影响,那时大部分的文艺青年都难摆脱这一重罗网”。[(9)]除此之外,田汉、张闻天也较早的介绍过比亚兹莱。唯美诗人邵洵美、性博士张竞生都是比亚兹莱的崇拜者,创造社的小伙计叶灵凤干脆以“中国的比亚兹莱”自称,并刻意模仿其美术风格,引起鲁迅的反感和讥讽,也促使鲁迅开始认真的来介绍比亚兹莱。冯至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境:“五四以后,中国的思想界无时不在起着重要变化,西方文学二、三百年中各种流派顺序产生的成果在短时期内介绍到中国来,都被青年读者作新事物接受。《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后的两三年,人们就读到田汉翻译的王尔德的《莎乐美》,书内附有毕亚兹莱表现世纪末风格的黑白线条的插图。……美国‘现代丛书’收有一册《毕亚兹莱的艺术》,售价低廉,北京上海都能买到。因此这个仅仅活了26年的画家的作品在中国也风行一时”。[(10)]比亚兹来是世纪末愤世嫉俗的代表,是世纪末阴暗心理的部白者,他以无与伦比的胆魄揭露了人类的隐恶和私欲,使得人们在他的艺术中看到了人生可能经过的恶行,这是世纪末那个时代所给予比亚兹莱特有的启示。正如鲁迅说的那样:“90年代就是世人所称的世纪末(Fin De siēcle)。他是这年代底独特的情调底唯一的表现者。90年代底不安的,好考究的,傲慢的情调呼他出来的”。[(11)]比亚兹莱在中国的传播反映了五四作家的一种独特的艺术趣味。
从西方历史来看,世纪末的价值转换在政治上倾向于柔性支配,人性上则要求生命的解放,浪漫主义相当浓厚,思想上则倾向于现代价值的批判。世纪初的中国对世纪末思潮的接受与传播,看重的是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的革命意义。就其精神实质而言,西方世纪末思潮上承19世纪浪漫主义的余绪下,下启20世纪现代主义的序幕,居于审美范式的过渡阶段,也就是说,“世纪末果汁”搀进了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种种复杂因素,而五四新文学对这一“果汁”的摄取,自然也并非是一种孤立地挑逃,而是渗透着对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认识和杂取,这三者之间的某种血缘关系是我们理解“世纪末果汁”在中国发生影响的内在机制至关重要的一点。正如冯至所说:“18世纪的维特热和19世纪的世纪末,相隔120年,性质很不相同,可是毕亚兹莱的画和《少年维特之烦恼》在中国20年代都曾一度流行,好象有一种血缘关系”。[(12)]郑伯奇在谈到创造社作家时,即将象征派、表现派、未来派甚至尼采、伯格森等哲学家看成是一脉相通,而且在思想上与浪漫主义有血缘关系,这个“血缘”就是“尊重主观,否定现实”的精神。创造社的浪漫主义从开始就接触到“世纪末”的种种流派,而统一到创造社作家身上则是“始终富于反抗的精神和破坏的情绪”。[(13)]世纪末文学思潮的东移,是伴随着五四启蒙主义中个性解放,青年觉醒和女性发现运动而进行的。中国封建社会以儒学为主的传统价值体系的崩溃,新旧文化的混沌杂糅,政治环境的空前混乱构成了世纪末思潮东移的外在契机。正如穆木天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否定的,当时在中国是新文化的萌芽期,可是在同时代的欧洲,19世纪的文学已解体,到处漂露着世纪末的悲哀。而从旧的地主贵族的环境转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的诗人,更容易怀有着凭吊的悲哀的”。[(14)]中国知识分子由此产生了深刻的信仰危机和精神危机:盲目的反叛意识,无出路的困顿感和时不我与的绝望感构成了接受世纪末思潮的内在心态;几乎与此同时发生的“五四”革命的落潮则构成了世纪末情绪滋长蔓延的导火线。在这种历史情境下,西方现实主义的悲剧观\消极浪漫主义和世纪末颓废主义思潮,作为三种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文化精神,成了影响中国五四新文学持续不断的整体力量。由于作家个性气质和自身经历的差异以及文学团体的影响,文学取法的倾向性和侧重点也就不同,就五四文学而言,西方世纪末文学思潮的影响在创造社作家身上的表现最为突出,到三、四十年代,则主要对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成熟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文学接受除了直接来自欧洲以外,俄国和日本也是两个重要的周转站。走出国门的中国作家,处于世界广泛联系中的中国文学,面对世界文化思潮的合围,接受影响和争取并轨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所以穆木天才说:“中国的‘五四’运动,发生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末期,是强烈地带着世纪末色彩的”。[(15)]
焦点透视:“世纪病”和“都市病”
尽管西方“世纪末”思潮与五四新文学存在共时性的同构,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与世界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着无法割舍的联系。但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作家对包括世纪末思潮在内的西方文学并非盲目的模仿和简单的照搬,而是有所选择有所创造的。并且仍然未能割舍中国传统的血脉。这里需要探讨的倒是摄取“世纪末果汁”的五四文学在文学品格上发生了哪些独特变化。大致而言,西方世纪末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刻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文化观念上,受世纪末思潮的影响,五四新文学表现出某种非理性主义和反现代化的色彩,使五四启蒙主义思想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矛盾形态。以人本主义为主要性格的启蒙主义文学由于运用了“非理性主义”的态度和方式来进行“理性”启蒙,使五四文学的“人学”建构带上了现代色彩。《狂人日记》所表现的不是西方近代以来的对人的乐观和自信,而是对人的社会本质的否定。也就是说,西方世纪末思潮赋予了五四作家以20世纪的眼光来打量尚未走出中世纪的中国社会,从而产生超前的批判方式与滞后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其次,在主题内涵上,受世纪末思潮的影响,五四新文学表现出反传统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倾向。在中国作家心目中,只要是对现代价值的批判,卢梭与波德莱尔可为同调,哥德与尼采能够统一在一处,种种西方思想资源的合力共同加深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深度,扩宽了其文化蕴含。第三,在精神特征上,五四文学因世纪末果汁的渗透,表现出孤独\忧郁\颓废\绝望的情绪基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悲剧性。这种悲情因素在五四时期主要表现为“身世之悲”,30年代主要表现为“文明之悲”,到40年代则让位于“民族之悲”,并使得某些非理性的情绪体验进入了文学世界。比如鲁迅对尼采思想意气的批判性吸收,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对安德莱夫艺术精神的革命性转化,深刻地铸就了鲁迅高远的艺术境界。第四,在审美风貌上,表现出唯美、内倾、象征、怪异的艺术追求,在语言和文本方面开拓了一种新奇的现代艺术境界。中国文坛对旬征主义的引进和发扬正是基于一种现代美学观念的确立,郭沫若认为:“真正的文艺是极丰富的生活由纯粹的精神作用所升华过的一个象征世界”。[(16)]这说明五四文人不仅仅满足于把文学简单地理解为对现实生活的映射和描绘,而把精神生活和心理过程引进艺术表现领域,他们大胆地从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精神分析方法中寻找灵感。这很在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深切感受到的心理情绪充满着现代人生的幽微苦涩和生命存在的悲剧意味,难以借助一般浪漫主义或写实主义的手法作淋漓尽致的表现,所以才瞩意于世纪末的艺术。而象征主义内部包含一种从浪漫性审美到现代讽刺性审美的转移,它大大改变了诗人的感知状态,这种状态伴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扩展,进而扩大了诗人从精神上拥抱世界的能力和总体感受力,深化了诗人对生活的观察力。所以郑伯奇才说:“象征派诸人的思想,实可以应我们心坎深处的要求”。[(17)]中国诗歌的现代化成就最根本的在于它唤醒了对语言的敏锐感知,语言不再被当作人的自然表露,而是被当作具有自己的法则和有自己特殊生命的物质来对待。中国诗人把情绪和经验的表现放在首位,不仅是一种精神危机的产物,同时也是对语言表现力的有益尝试。
西方世纪末思潮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的焦点最终通过两大文学主题:“世纪病”和“都市病”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在浪漫主义、世纪末和现代主义文学之间有一脉贯穿始终的主题血缘值得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就是“世纪病”主题的产生和发展。“世纪病”(Le Mal Du Siēcle)的概念最初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是对法国大革命后思想界普遍产生的怀疑厌世情绪的总称。这种倾向反映在文学上即催生出俗称消极浪漫主义的一系列作家,先是有“诗坛拿破仑”之称的拜伦崛起于英国,他那热情的呼唤迅即将厌世之声带入欧洲,法国的拉玛丁(Lamartine)、德国的海涅隔海唱合,此前哥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夏多布里昂的《荷耐》(Kene 1802)早已成为一代青年人精神苦闷的写照,此外象塞南库尔(Senan court)、抒情诗人维尼(De Vigny)、意大利的雷奥帕第(Leopadi)以及雷诺(Leanau)等都是风行一世的厌世文学作家。在这个时代,不管是启蒙主义者,还是狂飚突进者,抑或是浪漫主义者,他们的名字大多同叛逆、孤独、抗争、忧郁、狂暴、感伤等情绪特征联系在一起。1836年,26岁的缪塞(Al Fred De Musset)发表了《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对这个悬空时代作了有力的概括:“过去所曾经存在的已不复存在,将来总要到来的尚未到来”。一种无法形容的忧郁情绪,开始在所有青年们的心中作怪。缪塞把这种病症命名为“世纪病”。到19世纪末,这种精神病症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波德莱尔、王尔德、尼采几乎都是这种时代精神的有力表现者。“世纪病”在本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作为一种普遍的时代情绪,“世纪病”成为五四精神写照的一个重要侧面。五四后的大批作品中出现了一系列的“世纪病”患儿:鲁迅的“狂人”和“孤独者”系列、郁达夫的“零余者”系列、郭沫若的“漂泊者”系列、冰心的“超人”系列等,他们几乎都是世界文学“世纪病”患者谱系的分支。世纪病在五四文学中的表现,预示着旧时代向新时代过渡中知识者所付出的精神代价,反映了一代青年的心理现实:他们或是要冲决封建主义的罗网,追求精神和肉体的解放和自由;或是忍受不了个性和社会的矛盾而自惭形秽;或是因心灵的空虚和性格的软弱而消耗了才智,毁灭了爱情;或是要追求一种无名的幸福而在无名的忧郁中呻吟;或是对事业、爱情乃至生命失去希望而傲世独立,走向死亡。他们的思想倾向或是激进的向前的,或是消退的反动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呈复杂胶着状态。但他们有一个一脉相承的精神状态:忧郁、孤独、悲观、颓废、反叛,他们都是顽强的个人主义者,都是“人的觉醒”的新生儿。这种“世纪病”是一种特殊的具有五四时代特色的精神状态,那就是一代青年在“去者已不存在,来者尚未到达”的转折时代所遇到的无可名状的苦恼,甚或是一种源于个人的追求和世界的秩序之间尖锐失谐和痛苦的对立情绪。显然,这种病症带有普遍的世界性和深刻的本体意义,它是人类在面临社会、历史和时代转型期,普遍产生的一种对自我和世界关系的根本处境的焦虑与探求。可以说,在这些五四“世纪病”患者身上既有“少年维特”的性格,又不乏“当代英雄”毕巧林的血脉,而同时充溢着波德莱尔的忧郁和尼采的反叛激情。我们已很难用某一种流派来界定他们了,可以肯定的是,“世纪末果汁”将是不可或缺的一种营养。说他们具有一种世纪末情绪当不为过,正如茅盾小说《追求》中的主人曼青所说:“什么是现在的时代病?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常说的世纪末的苦闷,自然这是中国式的世纪末的苦闷”。也就是那种“幻灭的悲哀,向善的焦灼和颓废的冲动”。
据心理家荣格观察:“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倾向、特有的偏见与心理病症,一个时代就像一个人,它的意识有自己的局限,所以需要补偿性的调整。这种调整由集体无意识来实现。在这种集体无意识中,诗人、先知或领袖接受他那个时代难以表达的愿望的引导,并用自己的言行指出一条人人都在盲目追求和期待的成功之道——无论其结果是好是坏,能治愈一个时代或者毁灭这个时代”。[(18)]像“世纪病”一样,“都市病”也是西方世纪末精神和心理症候的一种。近代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实质上也是城市化的过程,在世纪末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内,城市生活随着工业的膨胀而在人类的生活中取得了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纵横交错的街道和川流不息的人群、汽车,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喧嚷的市场,不计其数的酒吧、舞厅、赌馆、剧院、赛马场,这一切都市生活的新景观都以自己的形象和意义撞进了人们的生活。人们每天随着都市大机器的各个传动装置运转,工作和生活接触的都是规范化、集约化,都是否定个性、否定情感和创作欲的冷水冰冰的机器事实,城市成了一种没有愉悦意境、亲切感和诗意的聚集地,一种烦闷、焦躁、痛苦不安和忧郁甚至绝望的情绪弥漫在都市空间,“这种精神病态的所谓‘都市病’,很明显地表现在世纪末,尤其从事文艺工作的人,这种倾向更加严重”。[(19)]从城市中发现诗意素材标志着现代主义文学的诞生,这一起点是从波德莱尔开始的。他眼中的巴黎,妓院、监狱、疯人院错综林立,可他能从中体会恶之美,寻找那从堕落的黑色深渊中绽放出来的花朵。这预示着一种新的文学观念、新的文学题材及艺术体式将取代古典意境的诗意表现,有人把世纪末文学对“都市之恶”的描绘称作是“诗中的现代性”(modernity in verse)。[(20)]这种对“都市病”的“现代性”表现,也成为30年代中国文学的主要命题之一。波德莱尔、保尔·穆杭和日本的“新感觉派”作家成为施蛰存、戴望舒、刘呐鸥、穆时英等人的师法对象。1926年,刘呐鸥在致戴望舒的信中就意识到: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已经远去,可是我们还能赶上“战栗和肉的沉醉”的现代主义这班车,与世界并驾齐驱。[(21)]而作为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精神和物质得以双重畸形发展的大都市上海,正好给他们提供了充分的想象和灵感,在30年代“都市文学”中,我们所看到的最鲜明的都市形象并不全是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繁华”、“宏伟”或“光彩夺目”,面对一个崭新的都市世界,中国作家们似乎并不为它的五彩缤纷,为它的辉煌所打动,他们所体验的似乎并不是欣喜、陶醉、赞美之类的情感,而是恰恰相反,他们感到的是抑郁、愤怒、失落和不满。他们生活在城市里,他们的作品人物在城市里,但他们却好象并不属于这个城市,他们像一群旁观者,一群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陌生人,对城市的环境进行冷静或冷酷的、讥讽或抨击的描绘和渲染。他们与城市格格不入,这种格格不入并不仅仅产生于一些卢梭式的浪漫主义理想,不仅仅来自于他们朴素的乡土观念。而是来自于他们自身的矛盾,来自于他们的存在与生存环境的不协调,来自于他们无法同这个环境达成一种沟通,一种感觉上和精神上的联系。新感觉派小说正是揭示了这样一种强烈的、破碎的、主观的个人意识,他们通过描述闪现各种印象的环境——都市,来表现人的孤独和忧郁,传达人与城市的抗拒与吸引,宣示一种对都市文明沦落的末日情绪。鲁迅在谈到勃洛克这位“都会诗人”的特色时,特别强调都市文学的观察角度——“幻想的眼”和“朦胧的印象”,[(22)]指的正是都市文学对于“城市经验的浓缩”,既带有“非真实性”,又带有相信不可的城市特征,亦即是“象征与写实”的文学精神。现代都市文学把城市当作一个隐喻,带着与浪漫主义主观性不同的绝望的心灵转向内心的深处,拼凑着文化的零章片断,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秩序和环境,并把城市意象发展为寓言的形式,表现现代人的悲剧性的分裂状态——“都市病”。穆时英提出人被城市“压扁”的命题,张爱玲思考城市人“孤独与苍凉”的心境,施蛰存探讨“失落和离异”的命题,甚至茅盾的《子夜》也表现了城市青年“浮躁与凄惶”的精神状态,应该说这些思考都把都市作家在上海这个特定现代城市的感触提升到反映人类精神困境的哲学高度。与城市小说一样,城市诗人笔下的人海,也在种种具有现代风的意象下得以驳杂呈现。诗人们纷纷效仿波德莱尔,在上海这座浮华之都中寻找“恶之花”,诗人眼里的“舞会:“一丛三七丛,/柏枝间嵌着欲溜的珊瑚的电炬,/五月的通明的榴花呀?/Jazz的音色染透了舞侣,/在那眉眼,鬓发,齿颊,心胸和手足。/是一种愉悦的不协和的鲜明的和弦的熔物”。(前人《夜的舞会》)吴汶的诗《七月的疯狂》,干脆把上海称为充满“接吻市场”的“妖都”,人们疯狂地扭动,仿佛“棺盖开后的尸舞”。城市的色彩、节奏产生了丰富多采的意象,这些“意象”构成了诗人观察城市,感受城市,表现城市的独特语言。虽然30年代的现代诗标榜师法英美意象派,可他们传递的仍然是一种世纪末情绪,正如孙作云所指出的:
现代派诗究竟不是意象派诗,那便是横亘在每一个作家的诗里的是深痛的失望和绝望的悲叹。他们怀疑了传统的意识形态,但新的意识并未建树起来。他们便进而怀疑了人生,否定了自我,而深叹于旧世界及人类之溃灭。这是一个无底的深洞,忧郁地,悲惨地在每一个作家的诗里呈露着。这是现代诗的内容的共同特点。到后来,竟有诗人写肺病,吐血,思想的不健康,心理的病态,竟达到这样的地步。这一种世纪末的悲哀使少年诗人们在法国象征派的诗中找着了同调。[(23)]
世纪末情绪在30年代文学中的蔓延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严酷的政治和文化现实,找不到出路的个人困窘,都是他们沉溺于悲哀与颓废的重要诱因,许多诗人逃向自己的内心深处,以情绪、感觉和意识作为诗的主要表现内容。杜衡说戴望舒热衷于“一个人在梦里泄漏自己的潜意识,在诗里,泄露隐秘的灵魂”,其实,这表现了大都市一代知识分子的时代病,并不能简单的加以排斥和否定。这种深刻的精神危机本身就赋予了中国诗人一种对严峻现实的审视心态,中国现代诗所表现的城市人的苦恼与焦虑情绪显示了作家相当深刻的观察力和领悟力,与世界现代主义诗潮进行了成功的历史汇流,这是应予充分理解的。
意义论析:“现代性”和“新感性”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世纪末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遇合”,这种“精神的遇合”,其意义我认为应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它促进了“五四”新文学“现代性”的生成;二是它构成了“五四”新文学“新感性”革命的重要契机。
在我看来,“现代性”是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颇具生命力的概念,它是一个中西文学乃至文化在现代交汇、冲突的联结点,我对这个概念的选择,倾向于一个价值的取向,亦即认为“现代性”是中国近百年来尚未完成的综合工程,它仍然是本世纪末中国索求的根本目标。所谓“现代性”,在西方自19世纪以来体现为两种潮流:一种是启蒙主义经过工业革命所表现出的政治、经济等层面的“理性化”过程,对科技发展,理性进步的观念继续乐观;一种是由浪漫主义运动以来的美学和艺术领域中的现代性,崇尚人的灵性,和中产阶级的价值系统相抗衡。[(24)]“现代性”在世纪初的中国呈现出与西方历史不尽相同的复杂形态,一方面它与西方启蒙思想的传统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经由知识的重新组合而杂糅诸如理性主义、人本主义和进步观念等等;另一方面,由于西方世纪末的非理性主义和悲观主义思潮的东移,其中不可避免地浸染上反现代、反文明的色彩。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把“民族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分开来看,这两个概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民族现代性”的索求在文学上表现在以“改造国民性”为主题的现实主义文学运动,而“文学现代性”的索求在文学上则表现在以“文明批判”为主题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我之所以把西方“世纪末”文学思潮在中国拿出来单独立项,目的在于对这种“现代性”索求过程进行重新溯源、探讨、思考和解构,通过研究西方前期象征主义、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文艺思潮的起源、特质及其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我发现,所谓的“世纪末”情绪——颓废的、阴冷的、怪诞、绝望的情绪,在中国现代作家眼里,不仅仅是现代美学内涵的先河,而且规定了现代主义文艺运动的基本内容,正如徐志摩所认识的:“从《忏悔录》到法国革命,从法国革命到浪漫运动,从浪漫运动到尼采(与道施滔曳夫斯基),从尼采到哈代——在这170年间我们看到人类冲动性的情感,脱离了理性的挟制,火焰似的迸窜着,在这光焰里激射出种种运动与主义,同时,在灰烬的底里孕育着‘现代意识’,病态的,自剖的,怀疑的,厌倦的,上浮的炽焰愈消沉,底里的死灰愈扩大……”[(25]在实质上,文艺的“现代性”表现,都没有超出“世纪末”文艺思潮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学对“世纪末”文艺思潮的认识和接受,则标志着现代主义艺术精神在中国的最初诞生。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作为一种美学意义上的现代革命,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学主题、新的文学样式和对美最新表达方式的确立。“五四”作家凭借自身的生命体验和对现代生活的真切感悟,凭借西方“世纪末果汁”所触发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态度,努力挖掘现代生活所寓含的现代性本质,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把握住了现代人生的某种内在特征,以鲜活的现代化风采和色调斑斓的艺术品格构成了“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空间。使得中国文学几千年来形成的思维模式、审美框架和叙述体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鲁迅的《野草》那种超拔的艺术形式和卓异的意象选择,李金发、王独清、冯乃超和穆木天那种新异的诗性体验和语言创造,郭沫若、郁达夫、叶灵凤小说中对人物心灵暗角的成功透视,田汉、向培良戏剧中对美与生命的艺术思考,无不得益于对西方世纪末文学的普遍感兴。
“新感性”概念的提出,我主要是想试图解构学术界长期以来形成的“历史政治化”和“历史道德化”思维模式,在中国,西方世纪末思潮一直是被作为消极的颓废主义而大张鞭挞的,评价一种文艺思潮的正负面,必须把现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时代要求、时代精神的一般状况和这种思潮本身的特殊内涵和意义联系起来看。在我看来,五四以来的颓废主义文艺,作为一种反叛的颠覆性的精神自卫,意味着一种新的精神实体和新的感知方式的形成,它从根本上激化了中国传统士人心理的裂变,激化了社会精神基础的震动,从而也激发了艺术创造的审美活力,促使艺术的价值和功能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因此,颓废主义在中国的产生,标志着一种“新感性”革命,是中国文学“现代性”追索的一部分。颓废主义本来是西方一部分作家的一种挑战性的自称,是对世纪末社会危机状态的惶恐不安的感受。本质上是这批作家对人类处境和内心世界的某种哲学表露,带有很强的浪漫反抗色彩。颓废主义东移是与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整个时代的危机相联系的。所谓精神萎顿,心理颓倦,行为悲观,进而追求享乐和刺激,都是人类在追求个性解放,民主自由的过程中的自然现象,用周作人的话说“便是这猛烈的求生意志与现在的不如意的生活的挣扎”。从20年代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气质”和丁玲作品表现的“莎菲女士性格”到30年代李金发、邵洵美、施蛰存、叶灵凤等人作品中折射的西方“颓废主义”文艺思潮,本质上是对道德主义传统的有力反拨,是对废弛社会中自我灵魂的激情透视,本文中关于“世纪病”和“都市病”主题的探讨,事实上就是研究“颓废”在美学和感情系统的现代性方面所展示的城市文化的特征,亦即其某种程度上对抗现代文明的成分。中华文明的衰败与复兴,一直是20世纪中国作家苦心积虑的大命题,对这100年梦想的观察和思考构成了大多数作品的总体出发点和总体基调,20世纪真正的经典文本之一可以说是这种忧思和梦想的象征性文学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未始不是一种带普遍象征意义的民族“寓言”。不同的文本与民族文明的历史经历、政治意识乃至经济状态构成和谐一致的对应关系,文学中所表现的个人奇特复杂的经历和命运,本质上内在地展示出民族的心灵史。
当然,在评价西方世纪末文艺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积极影响的同时,不能忽视其负面影响,比如思想的过分悲观对作家人生选择和民族前途展望的消极影响,艺术创新的矫枉过正而往往流于形式和语言的怪僻偏涩,更有一些作家沉溺于恶俗的艺术趣味不能自拔,甚至走向民族政治和民族文明的对立面。由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的局限性,特别是中国现代作家在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之前,我们不能苛求他们所作出的思想探索和艺术探索,但其中的教训也应该引起当代人的足够重视。事实上,我这里也主要倾向于一种历史判断而非价值判断。“世纪末果汁”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是一种现实的深刻反映,五四作家从尼采的偏激,波德莱尔的忧郁,王尔德的颓废,安德列夫的阴冷中获得了反叛主义的激情,并创造性地运用到反封建的文化启蒙和艺术解放的追求之中,使刚刚摆脱传统羁绊的新文学获得现代性的思想深度,对世纪之交的中国现代价值的转换更是功不可没。随着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文化的发展,许多作家把个体生存与民族复兴结合起来,“世纪末果汁”中那些过分强调自我、主观、唯美的消极因素受到作家的冷淡,代之而起的是对民族文明衰败与复兴这个宏伟主题的观察、体验和思考,这恐怕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了。
从“世纪末”思潮在东西方的传播来看,“世纪末”的确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如前所述,作为资本主义文明处于危机阶段的产物,其本质是一种危机的文化,一种文明没落的恐惧感,一种时不我与的焦虑意识。从19世纪末西方文艺发展的状况来看,世纪末文艺思潮正是西方民族文化反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旧交替阶段文化斗争的产物,同时也是思想变革的反映,它所显示的特有情绪,大多是20世纪文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源头。尤其它所显示的危机意识几乎贯穿了西方20世纪整个哲学和文学思维。恰如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言:这种危机意识是一百多年间渐渐形成的,今天它已经普遍地变成了几乎所有人的意识。“世纪末果汁”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集中在二三十年代和80年代,曾对思想启蒙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化起到过积极的促进作用。无庸讳言,这两个时期的文学界也出现了某些恶俗趣味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近几年来,这种文学上的“颓废情绪”还有蔓延的趋势。伴随20世纪末的来临,中国又面临一个“价值转换”的关键时期,通过探寻上世纪末思想与艺术的源流和特质,以及中国文学摄取“世纪末果汁”所产生的经验和教训,无疑可为这个世纪末提供一面历史之镜,果如此,本文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有人说:世纪末是第二次文艺复兴的开始,但愿这一预言对21世纪的中国并非虚妄。
注释:
(1)季羡林:《东西方文化的转折点》,转引自1995年6月28日《北京日报》。
(2)梁启超:《小说丛话》,《新小说》第7号,1903年。
(3)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载《青年杂志》1卷3期。
(4)张闻天:《王尔德介绍》,《狱中记》,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5)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6)王尔德:《英国的文艺复兴》,译文引自徐京安编《唯美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7)田汉:《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载《少年中国》,第3卷4-5号,1921年11月21日。
(8)周作人:《三个文学家的纪念》,《展报副刊》,1921年11月14日。
(9)叶灵凤:《郁达夫先生的〈黄面志〉和比亚斯莱》,收入《读书随笔》1集第341页,三联书店1988年。
(10)(12)冯至:《外来的养分》,收入《立斜阳集》,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
(11)鲁迅:《〈比亚兹莱画选〉小引》,《集外集·拾遗》。
(13)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
(14)穆木天:《郭沫若的诗歌》。收入《穆木天诗文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15)穆木天:《王独清及其诗歌》。收入《穆木天诗文集》。
(16)郭沫若:《批评与梦》,《创造季刊》第2卷第1期。
(17)郑伯奇:《鲁森堡之一夜·代序》,泰东图书馆1922年5月版。
(18)荣格:《心理学与文学》,三联书店,1988年版。
(19)厨川白村:《西洋近代文艺思潮》,据[台]志文出版社,陈晓南译本。
(20)萧石君编:《世纪末英国新文艺运动》,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34年版。
(21)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
(22)鲁迅:《〈十二个〉后记》,《集外集拾遗》。
(23)孙作云:《论“现代派”诗》,《清华周刊》,1935年5月15日,第43卷第1期。
(24)参见《学人》第8辑,浙江文艺出版社,第523页。
(25)徐志摩:《汤麦士哈代》,《新月》第1卷第1期。
标签:文学论文; 比亚兹莱论文; 王尔德论文; 浪漫主义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少年维特之烦恼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莎乐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