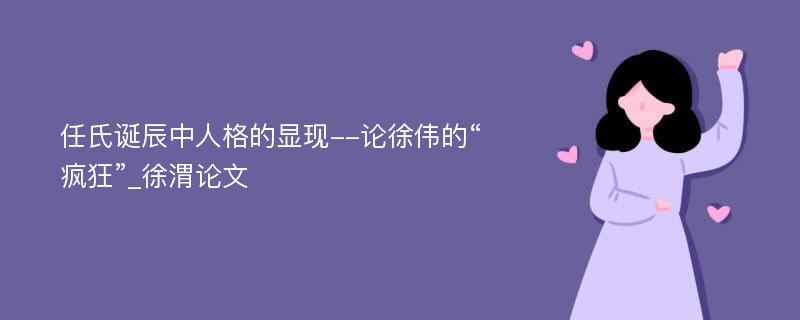
任诞中的人格显现——徐渭“疯狂”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格论文,疯狂论文,任诞中论文,徐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多的戏曲史文献几乎都认为,徐渭(1521~1593)在中年后患了疯狂症(即今人所称“精神病”)。
如果我们对徐渭的生平、品性及人格追求稍作回顾,便不能不怀疑这种说法的可靠性。众所周知,徐渭一生著述颇丰,尤以中年以后为巨。据初步统计,从其四十四岁(1565)直至去世(1593)这28年中,计留下诗文近500篇。为后人所一致称道的那些辉煌篇章,大都出于这一时期。如《自为墓志铭》、《与汤义仍书》、《畸谱》、《张母八十序》、《狂鼓史渔阳三弄》、《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等。此外,他还完成了《周易参同契》、《葬书》及《西厢记》的校注,编撰了《会稽县志》,修改了梅鼎祚的《昆侖奴》杂剧,并作《题〈昆侖奴〉剧后》,还完成了组剧《四声猿》及书稿《徐文长初集》的刊刻出版……。这些,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决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所能实现的。校注典籍、修改他人剧作、刊刻文集尤须有较强的理性能力,至于编撰县志,则更要求清醒、理智。很难想象,一个“精神病”患者能被委以如此重任,很难理解,一个“疯狂”病人能够严格地胜任这一使命。当代医学认为,精神病患者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逻辑的无序和注意的失恒。遍览徐渭中年以后的全部文字,我们还不能发现任何逻辑无秩或混乱的迹象,也见不出任何朝三暮四、喜怒无常的注意失恒或散逸征兆。相反,从他能专心完成大量校注和编撰工作看,他的理性应是完全正常和始终有效的。美国心理学家康克林在他的《变态心理学原理》一书中说,许多天才和伟大是没有疯狂病的。“如果疯狂是天才的一个主要现象,则疯狂医院应当是产生哲学、文学和艺术的策源地了。显然,实际情形并非如此。”①
值得注意的是,举凡认为徐渭中年以后“疯狂”的文字,似大都以他“多次自杀”为立论表征。仿佛“自杀”或“打算自杀”就是“疯狂症”的表现,就是“发了精神病”的证明。这不仅不能令人信服,而且也显示出立论者与徐渭,即常人与“奇人”(磊砢居居士的《〈四声猿〉原跋》起首一句便称“徐山阴,旷代奇人也。”②)价值观念的差异。这已涉及徐渭的人生态度和人格追求,拟于后文详述。
那么,徐渭中年以后(或“四十四岁”)患了精神病又是从何说起呢?我想可能是由徐渭自作的生平年表《畸谱》引出的。在这份“生平年表”中,徐渭先后6次提及自己的病情。其中,涉嫌精神病的有4处,它们是——
四十五岁,病易。丁剚其耳,冬稍瘳。
四十六岁。易复,杀张下狱。隆庆元年丁卯。
五十八岁。春,某者起,孟夏,拟至徽吊幕,至严,崇见,归复病易。
六十一岁。是年为辛巳,予周一甲子矣。诸祟兆复纷,复病易,不谷食。
一般以为,这里的“易”即“癔”或“痬”,系指某种精神病。我不相对“易”的确切含义作更多的考证,我只想说,设若徐渭果真患了精神病,那么,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自述”又何足为信?现代法律都认为,精神病患者的证词不具有法律效益。故此,我以为,若联系他每当病发时的过火行为——刺耳(“丁剚其耳”)、杀妻(“杀张下狱”)、绝食(“不谷食”),以及他对往事始末,甚至年代时间、地点变易的惊人记忆和行文中所体现出的缜密逻辑来看,他这里所说的“易”,实际上指的是情绪的超常激动,是一种短暂的心理变化,而非真正的生理发病。至于“祟见”、“诸祟兆复纷”之类的现象,则很可能是其到了晚年(“五十八岁”后),由于年老体弱、辱病交加、耳目失聪所出现的一种“幻视”。这是一种偶然,实难与精神病相联。
究竟如何解释徐渭中年以后确曾出现的某种反常呢?我以为袁宏道等人的“佯狂说”道出了问题的实质。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说(徐渭)“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③。这里的“佯狂”未必是指“装狂”、“充狂”等有意而为的行为,而是指“一种与真狂(精神病)形似神非的“假狂”,一种包蕴着精神追求的非狂之狂。这是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奇特的狂,一种把人生高度哲学化、艺术化了的浪漫的狂。实质上是一种人格在行为上的无意外化。正象诺曼·梅勒所称,属于“一种哲学上的精神变态者”。④
在接触了有关材料之后,我坚信:对徐渭的“疯狂”作如下的解说是合乎逻辑的。
渲泄:融苦痛于狂放
众所周知,徐渭的一生是坎坷潦倒的一生,中年以后尤不幸。本来,他寄身胡宗宪帐下也是不得已而为。岂料胡宗宪获罪,这个一向痛恨严(嵩)党的人却染有严党之嫌,有口莫辩。可以想见,一个“志不媚世”的人反遭世人的攻讦,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极大的烦恼、懊恨、屈辱。社会的不公,命运的戏弄,中年以后的他,魂灵上,“旧伤痕上新伤痕”,伤痕累累;胸臆间,“冷泪退处热泪生”,泪雨滔滔。而此时,他已御任回乡,满腹的苦痛无从倾诉,强烈的孤独感时时困扰着他。于是,他需要渲泄,需要呐喊,需要摆脱困扰,寻找平衡。面对心灵的极度苦痛,世人不外乎采取两种平息之法。其一是调整或消弥自己,以与现实同化;其二是燃烧或毁灭自己,以向现实宣战。徐渭生性孤傲,宁断不折,显然,他不会选择前者。袁宏道说他:“其胸中又有一段勃然不可磨灭之气”⑤,故他只能选择后者。他要融苦痛于狂放,以一种超常或极端形式来抒发自己。陶望龄在《徐文长传》中这样描述:“渭貌修伟肥白,音朗然如唳鹤;常中夜呼啸,有群鹤应焉”⑥。这里,“有群鹤应焉”,可能有些夸张之嫌,但其所告诉我们的徐渭“常中夜呼啸”这一情状,不是足以使我们感受到徐渭那深深的内心苦痛么?“中夜呼啸”无非是要渲泄那让人窒息的内心苦痛,以使他的灵魂得到暂时的安宁。之所以是“中夜呼啸”,更见出他孤独之深、压抑之重、煎熬之烈。见出他“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⑦。这实际上是一个痛苦灵魂的哀嗥。这种人生意义上的深刻痛苦,决非一切人都能理解的。
在《喜马君世培至》一诗中,徐渭对自己的所谓“狂病”作了生动的描述,其情况似与阮籍十分相似。诗曰:
仲夏天气热,戒装远行游,
访我未及门,遇子桥东头。
时我病始作,狂走无时休,
吾子一见之,握手相绸缪。
却云始作病,未可药饵投,
欲以好言语,令我奇痾瘳。
……⑧
这里,我们看到徐渭的所谓“病”的某些特征。似乎一旦发“病”,便“狂走”不息。这与阮籍“喝醉了酒,驾车奔跑,一直到无路的地方才停下来”殊多相似。由于从表面上看,阮籍是“喝醉了酒”“奔跑”,人们仿佛还不大会认定他是“精神病”患者,而徐渭则是在声称有“病”的时候“狂走”,便很容易招致“精神病”的误读。其实,我们只要注意一下诗中另外提到的“未可药饵投”、“欲以好言语”的情形,便不难理解徐渭真正的“病”到底在哪里了。若有“好言语”,话逢知己,便可使久压于心底的苦痛得以抒发。但是,在一时寻不到知己,得不到慰籍的时候,徐渭也就只能以“狂走”来渲泄内心情感了。于是,痛苦融于狂放,外在的“狂走”包蕴了内心深重久远的苦痛。世人以为他是“狂”,而他自己感到的则是一种释放。
故此,他在给他的朋友郁心斋的信中,便严词驳斥了世人说他因狂而杀妻的“浮言”。信中,尽管他并没有言明到底是因何杀妻,但却十分鲜明地否认了“因狂杀妻”的说法。在我看来,徐渭杀妻的原因固然很多,如某种情绪上的超常激动,某种现实强加给他的极端苦痛,但直接造成其妻身死的,则很可能是一种情急误伤。由于这苦痛的外泄选择了一种非理性的形式,一种狂放的外观,故此,在外人看来,便是所谓“因狂杀妻”了。徐渭四十五岁之后,直到七十三岁去世,也就只杀过继妻张氏一人。并且,他亦十分清醒地懂得“杀人伏法”非“轻犯之科”,纵是“至愚亦知所避”。可见,这杀妻的狂放中,定然包裹着心灵的巨大苦痛。
十分有趣的是,明·詹詹外史评辑的《情·史》中,恰巧对徐渭的“杀妻”有所描述。作为一种笔记小说,这种描写是否有所虚构不得而知,但由于它所记录的是同时代的真人真事,我想主要情节应属可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两层意思。其一是现实给徐渭造成的痛苦。妻子不贞,白日勾奸和尚。而他“欲击之”又不知奸僧去向,这种愤懑自可想见。更让他痛苦的是,这一对奸男淫女根本不把徐渭的尊严放在眼里,几日后,竟又“并枕昼卧于床”,仿佛有意要往徐渭眼里揉砂子。于是,苦痛化为“不胜”的“愤怒”,化为如雷的吼声(“声如吼雷”),呈现了一种超常的狂放形态。其二是他对继妻的误杀。徐渭“取铁灯檠刺之”的目标应为奸僧。只是在情绪过度激动之际,误伤妻子而已。这一点,清·顾公燮的记述可作补证。顾在《销夏闲记》中说,徐渭某次外出回家时,见一僧与妻通奸,怒中执刀杀僧,再看却并无他人,被杀的是自己的妻⑨。由此可见,徐渭的杀妻并非因为患了精神病,而只是盛怒之下的误伤。
在“呼啸”、“狂走”仍不能得到社会对他的理解与同情,仍不能彻底消融他内心的巨大苦痛的情况下,徐渭又采取了另一种极端的渲泄方式,这就是自残和自杀。这也是招致他背负“疯狂”之名的又一因由。
从已有的相关资料中,我们知道,徐渭的自杀大体有如下几种方式:
其一,“刺耳”。骆玉明、贺圣遂的《徐文长评传》说:“……嘉靖四十四年的夏天,徐渭在一次狂病发作中,从壁上拔出一枚三寸长的铁钉塞入耳窍,然后摔倒在地,把铁钉撞没进去”⑩。
其二,“击颅”。袁宏道《徐文长传》说:(徐渭)“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11)
其三,“槌囊”。陶望龄《徐文长传》中说他“又以椎击肾囊碎之,不死”(12)。
其四,“绝食”。张汝霖《刻徐文长佚书序》中说,(徐渭)“归则捷户,不肯见一人,绝粒者十年许,挟一犬与居”(13)。
之所以列举徐渭的这些自杀方式,主要是想说明徐渭的心灵痛苦,由此洞见他的“痛不欲生”的精神实质。徐渭的融苦痛于狂放的渲泄方式,使他的自杀呈现了远比一般“上吊”、“投井”、“吞金”之类更加惨烈、更加酷残、更加悲壮的外观形态。它的实施,需要超常的勇气和超强的耐受,非把整个肉体置之度外而不能!这一种狂放的自杀形式亦需透彻的人生认识和升华了的理性追求为支柱。决不是一时的情感冲动或“发狂”所能做到的。一般说来,因疯狂而杀身,其情懵懂,多属一念之差;而因苦痛欲求死,其心澄明,乃为矢志追求。徐渭的自杀虽历九死而不惧,可见其志之坚,其心之坦,其情之韧,其苦痛之深。
认为徐渭中年以后患精神病者,大多以徐渭的多次自杀为依据。徐渭如此执着地自杀,不是患了“疯狂”症又是什么呢?但这只是停留在对徐渭现象的表层读解上。在我看来,徐渭的自杀与所谓“疯狂”之间的关系不应是“患病导致自杀之举”,而应为“自杀招来患病之议”。个中因果不容颠倒。熟悉徐渭生平的人大都知道,徐渭在决意自杀前曾写过一篇《自为墓志铭》,这其实就是作者面对死亡留下的一份遗书!在这份遗书中,徐渭对自己四十五年的生命历程作了概略的回顾,对自己的自杀原因作了陈述,并且把自己对人生世事的看法和盘托出,甚至后事交待亦细致周详。这份遗书至少让我们见出两点。其一是它的写作本身就雄辩地证明了徐渭的自杀是经过审慎思考的理性行动,而决非“因狂自杀”;其二是文中所呈现的见解、逻辑、记忆及后事安排的高水平,足以说明他此时理智的清醒与精神的健全。
抗争:求自由于任诞
徐渭在把苦痛融于狂放,进行自我渲泄的同时,还不断以一种非常形式与给他造成苦痛的那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进行抗争。他说:“渭无状造化太苛猛相迫”(14),于是,他要与之战斗。现实对徐渭的极端不公正,徐渭当然要以不公正待之。古人说他的作品是“嬉笑怒骂也,歌舞战斗、也(15)”。其实他的整个人生态度何尝不是这样?!他在把求自由于任诞的抗争投诸作品的同时,也付诸人生实践,于是,给他自己的行为染上了更多的“疯狂”色彩。有类于西方的所谓嬉皮。蔡翔同志在《中国嬉皮——中国文学中的“任诞”问题》一文中说:“在一般的意义上,嬉皮是正统文化的不孝之子,他们表现出的正是一种‘孤独的人们对抗孤独的勇气’”。(16)徐渭正是这样一位“正统文化的不孝之子”!
陶望龄在《徐文长传》中曾记述过这样一件事,说徐渭常常“日闭门与狎者数人饮噱,而深恶诸富贵人,自郡守丞以下求与见者,皆不得也。尝有诣者伺便排户半入,渭遽手拒扉,口应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怪恨之”。人常说:“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山林有远亲”。那富贵之人常是人们争相拜谒的对象,那达官郡守则更是凡夫俗子们抢着巴结的“圣贤”。而徐渭却偏偏不予理睬,恶于相见。足见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正统文化的不孝之子”。这里,一方面呈现了他洁身自好、豪荡不羁的品性,一方面又给世人留下了诸多不可理解处,误认为这是一种“疯”、“痴”。更有甚者,有时这些达官贵人已推门“半入”,徐渭竟然还忙把门抵紧,并口称徐渭不在,这实在不能不说是有点“精神病”了。然而,这正是他的一种向任诞讨自由的追求,是他对现实的一种抗争。表现出的乃是“孤独的人们对抗孤独的勇气”。徐渭自己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嗟哉,吾谁与语!众人所忽余独详,众人所旨余独唾。嗟哉,吾谁与语!”(17)寥寥数语,竟两度发出“吾谁与语”的呼号,可见其孤独之深,压抑之重。而“日闭门与狎者数人饮噱”,正是他苦心营造的一个找回自由、找回真性的非礼法的天地。为了这个崇高的追求,他也就不再去理会世人的“怪恨”了。
据考证,徐渭的“天池”一号是中年以后才启用的。他在《天池号篇为赵君赋》诗中说:
予耽庄叟言真诞,子爱江郎石更奇。
讵意取为双别号,遂令人唤两天池。
这里徐渭借用了庄子《逍遥游》中的“南冥者,天池也”的“天池”二字,正显示出他要效大鹏鸟逍遥于天地之间,显示出他对“逍遥”之境的向往。徐渭中年后取号“天池”,也说明了他人生态度的转变。而恰恰是在这中年以后,世人又认为他患了“精神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人格追求在另一种人格框范中产生的歧义与误读。徐渭要用“逍遥”来面对人生,要用任诞来获取自由,从而实现精神的彻底解放。这种“逍遥”当然与封建社会正统文化的“格物致用”、“仕途经济”、“治国齐家平天下”之类行为准则格格不入。于是,这在社会,便认为徐渭疯狂,《中国文学史》就说他“被当时统治阶级看作不可理解的狂人”;(18)而在徐渭,则认为社会是错乱的,颠倒的,需予再颠倒之。
还是在那份遗书(《自为墓志铭》)中,他曾剖白自己“贱而懒且直,故惮贵交似傲,与众处不凂袒裼似玩,人多病之,然傲与玩,亦终两不得其精也。”这里,我们能见出徐渭的某种孤傲实质。首先,他自认为“贱而懒且直”,即感到自己在那个社会中所处的低微、卑贱的地位,政治上,心理上受压迫的情状。“懒”,即他对仕途功名的心灰意懒,不欲入世的心态。“直”则是指他宁断不折、不欲随波逐流的品性。正是由于这样的内外因素,他誓不与权贵相往还,却甘愿敞开胸襟与普通大众同欢乐。这便是一种人生价值的“颠倒”,故“人多病之”,把他作为不正常的疯子。其实,真正“有病”的应是那个社会,以及在那个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封建正统文化。徐渭只不过是以较为激烈,较为极端的方式向这个病态的社会,病态的文化发出抗争与挑战罢了。他的“傲”与“玩”仅仅是这种抗争与挑战的手段。他要以自己的“似”病,去换取社会的健康与正常,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在决意结束自己生命的当口,他承认,“傲与玩”,“终两不得其精也”。在疯狂、病态的社会现实和疯狂、病态的正统文化面前,他的努力,他的追求,他的抗争,反使他自己被看作是“不可理解的狂人”。
自纵:发真性于佯狂
既然现实是颠倒的,人性是扭曲的,那么,要保全真性,不与污淖齐流,便不能不“另有所钟”。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真性是不能直接袒示的。于是,徐渭便以“佯狂”自纵,从而,让真性在“狂”的掩护下,淋漓而出,完成人格的整肃。
还是在《歌代啸》楔子中,他曾作《临江仙》一首,申明了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
谩说矫时励俗,休牵往圣前贤。屈伸何必问青天,未须磨慧剑,且去饮狂泉。世界原称缺陷,人情自古刁钻。探来俗语演新编,凭他颠倒事,直付等闲看。(19)
这里表现了他对社会的由厌恶到失望。自我“屈伸”无需向社会去乞讨,甚至也无须责问“青天”。这本不是命运范畴的事,而是现实过于黑暗所致。故此,在他看来,用不着去孜孜寻求答案,去为一些小的满足而苦争苦求。而要彻底抛开一切幻想,去自纵,去“饮狂泉”,去着手自我解放,以使人生得以潇洒。“凭他颠倒事,直付等闲看”。只有这样,才能最终保全真性。这是何等的超然与洒脱。无怪乎前人说他“先生志不媚世,存吾真而已矣。”(20)一旦他“存吾真”的内心追求与显现出的“饮狂泉”(自纵)相合一,便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精神现象——佯狂。即从人格的向度理解可读出“佯”;从社会的视角去察看便呈示“狂”。这是古中华人格面貌的一种颇耐玩味的现象。
我在前面曾经说过,徐渭中年以后开始使用“天池”一号,其取意正是由庄子《逍遥游》而来。可见他对庄子哲学的兴趣。《庄子》的要旨乃在于个人精神的绝对自由,心性自然。这些都势必对徐渭产生重要影响。《四库总目提要》说他“自知决不见用于时,盖愤激无聊,放言高论,不复问古人法度为何物”。(21)这里,徐渭的“放言高论”、“不复问古人法度为何物”,与庄子的“啸傲纵逸”、“大行不顾细礼”似已显示出某种精神上的同一。
王思任在《徐文长先生佚稿序》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对我们理解徐渭的“佯狂”颇有帮助——(徐渭)“终以对贵人为苦,辄逃去,与不如公荣者饮即快。卒然遭之,科头戟手,鸥眠其几,豕接其金,老贼呼其名氏,饮更大快。一有当意,即衰童遢妓,屠贩田佁,操腥熟一盛,螺蟹一提,敲门乞火,叫拍要挟,征诗得诗,征文得文,征学得字。”(22)这里,徐渭“与不如公荣者饮”的确已“饮”到了“啸傲纵逸”、“不问法度”的境界。与魏晋名士的风采绝不相上下。你看他摇头竖手,乏则伏案作“鸥眠”,兴则就盏而饮似“豕接其盆”。有名不称而以“老贼”相唤,于是酒兴更酣,“饮更大快”。这实在是狂放之极。一股强烈的“啸傲”之气扑面而来。这里没有了“古人礼法”,没有了荣辱尊卑,有的只是真性的畅然流泻,心性的自在“纵逸”。人完全回复其本来面目,这是对异化的有力反拨。只是由于社会的局限,徐渭的这种保全真性还不能以正常的方式求得,必须假道“科头戟手,鸥眠其几,豕接其盆,老贼呼其名氏”的佯狂。这是社会的扭曲,是历史的悲哀。
徐渭为保全真性的佯狂,除了表现在“惮贵交”和与“衰童遢妓”“饮更大快”两个方面外,还表现在他的某种看破红尘、带有嘲世意味的极端行为上。徐渭在“杜门八年”,誓不与“富贵人”相往还的同时,还挑战似地与“衰童遢妓”“屠贩田佁”狂斟豪饮。然而,当如此仍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情欲之时,他便采取了更加激烈极端的方式——“挟一犬马居”。这是对社会的无情嘲弄。这使我们感到,在当时的社会中,人性丧失,真诚殒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险恶。与人相处已远不及与犬相伴。这是何等的辛辣!当然,徐渭作出如此极端的举动,其心中也决不会平静。他曾狂中画雪压梅竹而题云:“云间老桧与天齐,滕六寒威一手提,折竹折梅因底事?不留一叶与山溪!”由此可见,他是抱定了主意,要在自纵中毁灭,以保全真性,决不与污淖同流。这里的“与犬居”,使他摆脱了世事污秽,心灵得以舒展,如同返归自然一般,真性得以回归。这里,他通过“捷户”割断了与社会的联系,又通过“绝粒”切断了与物质的联系,为心灵开拓出了一块不受世俗污染的安宁空间。这是一般人,尤其是受封建正统文化影响过深的人以当时社会的一般价值准则“难以”“谛测”的。
为了追求真性,徐渭还常常作出更加极端的举动来。他的《自为墓志铭》说他“与众处不浼(疑为‘免’——引者)袒褐似玩”。会稽章重说他:“往往卧臭堑中”。(23)把自纵已推向极致,达到了彻底清除我相的境界。衣服可以不穿,一切社会的(遮盖)、物质的(避寒)需要皆可抛开,完全呈现真实的、自然的人本体。以此向那个表面上文质彬彬、道貌岸然,而骨子里却到处写满了“吃人”二字的社会宣战,用一种完全反常的行为,完全非礼的举动来嘲弄、亵渎以致沉重地摇撼那个社会的秩序与道德准则。这里,徐渭丢失的是礼教的枷索,得到的是心性的自由。
元结在《丐论》中说:“乡无君子,则与云山为友;里无君子,则以松柏为友;坐无君子,则以琴酒为友。”(24)鉴于徐渭的精神现象,我们似还可再加上一句,那就是:“心无君子,则自纵为友”。唯其如此,真性才可在佯狂的自纵中重新回照主体人格,矗立在“疯狂”表象背后的是一座辉煌灿烂、弘扬真性的精神丰碑!
入境:忘自我于痴颠
在面对徐渭的所谓“疯狂”的时候,我们还不应忘记他不仅是一个有血性、有骨气的铮铮男儿,而且还是一个造诣颇深、成就巨大、堪称一代大师的艺术家。正如会稽商维濬在《刻徐文长集原本述》中所说:“才思奇爽,一种超轶不羁之致,几空千古。”(25)足见其艺术境界的博大精深。并且,据史家考证,他的艺术成就又恰恰是在“中岁以后”更见纯青。籍此,我甚至以为,所谓的中年以后“患了疯狂症”是否正是对他艺术上入境(一种有如尼采所说的“醉境”)的误读呢?这也许是判定艺术家与常人在人格状态上差异的重要标识。
我们知道,胡宗宪事变后,徐渭落拓回乡是带着一肚子委屈与痛苦的。为了排解这痛苦,他除了我们在前面所说的融苦痛于狂放,不与权贵者交的散诞外,还遣愁思于笔端,发奋写作,把痛苦化解在艺术的创造过程中。于是,我们看到他借“祢衡骂曹”之典渲泄了自己对贪官奸相的愤懑,并特将此剧命名为《狂鼓史》,与他此时的心境殊相吻合。请看祢衡唱的这支“寄生草”:
你狠求贤为自家,让三州直甚么。大缸中去几粒芝麻罢,馋猫哭一会兹悲诈,饥鹰饶半截肝肠挂,凶屠放片刻猪羊假。你如今还要哄谁人?就还魂改不过精油滑。(26)
如果我们能感到此处骂得真叫痛快淋漓的话,那便是徐渭压抑情感的痛快淋漓的渲泻!个中对为官者假慈悲的深刻揭露不正得益于徐渭对封建官场的透彻认识,对险恶人际关系的切身感受吗?出于这种渲泄的需要,这一时期,他笔走龙蛇,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戏剧、书画作品,从而最后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戏剧史、绘画史以及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他在《与肃先生》一文中说:“自前月二十七日以至今,四旬中间,症候不可言说,绝不饮食者十九日,顷方粥食,强起移步,扶杖可至中堂,欲过门而门限也。……他每于清晨精神生复之时,便执笔构赠别诗文。文成于心而书法于手,中止十数,战兢便发。”(27)由此,我们看到,徐渭即便是在饮食不进的大病中也未曾放下手中之笔。写作已成为他中年以后生活的第一需要。徐渭在创作上的“入境”与“忘我”有三个层次,其一是创造过程中的忘我,如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样:“关门累月不梳头”、“经旬不食似蚕眠”。(28)呈现出一种形态的“痴狂”。其二是体现在作品中的忘我,把个人的真情真性、所激所感全都投注于作品,而毫不顾忌社会评价和可能招来的祸患。其三是在创作目的方面的忘我。由于他的创作,是“有动于中”,“于诗文发之”,故此,他所追求的便不是作品所带来的名誉及物质利益,只重过程而不计目的。对呕心沥血完成的作品,“才脱稿辄弃去”,亦是常人难以理解的。然而,他的追求恰恰是“宁使作我,莫可人知,绝不欲有枕中之授,亦不乐有名山之封,故著作随付随佚。”(29)由以上三个层面的忘我,徐渭便在表象形态上构成了一种“痴颠”。在常人得出“疯狂”读解的同时,他已然进入了艺术创造的无我之境。我以为,正是这种看似“痴颠”的入境,为我们推出了一位不朽的艺术大师。
还必须指出的是,徐渭为了这种“入境”,为了构成以“痴颠”为外观的人格状态,从而切断现实的干扰与侵袭,他还取了古代诸多艺术家所常取之法——以酒燃情。使理性得以麻醉,使激情得以催发。从而保证主体始终畅游在自我精神的王国里,造成“杯中索句,酒底成诗”的艺术境界。徐渭之所以如此,无外乎两点动机。一是表现出他对现实的冷漠,追求我行我素,目空一世的人格境界。从而实现“世人皆醉我独醒”或“世人皆醒我独醉”的精神完善。二是构筑浓酽的艺术之境。从杯中引发灵感,汲取力量,点燃激情。以实现蔡邕所说的“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狂”(30)的创造情势,忘自我于痴颠。这不独是特定时空中特定艺术家的人格状态,也是古代中国文学家、艺术家的整体精神现象和整体人格面貌。
遗憾的是,从明至今,人们对这样一种人生境界误解太多,偏见太厚。这也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土壤上较难产生更多的跨民族、跨时代的大师的原因之一。传统评判常把可以纳入法典化的社会程序的个人行为视作“正常”,而把被此一法典化的社会文化所拒斥的个人行为称为“荒诞”、“疯颠”或“不正常”。这不仅无益于艺术和艺术家,也无益于民族个性和民族精神的健康与成熟。
注释:
①转引自吕俊华:《艺术创作与变态心理》,第12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重点为引者所加。
②徐渭:《畸谱》,《徐渭集》第四册,第1329~1330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重点为引者所加。
③袁宏道:《徐文长传》,《徐渭集》第四册,第1342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重点为引者所加。
④诺曼·梅勒:《白种黑人》,转引自《艺术广角》1991年第6期。重点为引者所加。
⑤袁宏道:《徐文长传》,《徐渭集》第四册,第1342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⑥陶望龄:《徐文长传》,《徐渭集》第四册,第1339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重点为引者所加。
⑦袁宏道:《徐文长传》,《徐渭集》第四册,第1342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⑧徐渭:《喜马君世培至》,《徐渭集》第一册,第73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重点为引者所加。
⑨参阅骆玉明、贺圣遂:《徐文长评传》第123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⑩骆玉明、贺圣遂:《徐文长评传》,第12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1)袁宏道:《徐文长传》,《徐渭集》第四册,第1343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12)陶望龄:《徐文长传》,《徐渭集》第四册,第1339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13)张汝霖:《刻徐文长佚书序》,《徐渭集》第四册,第1349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14)徐渭:《与萧先生》,《徐渭集》第四册,第1128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15)钟人杰:《四声猿引》,《徐渭集》第四册,第1356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16)蔡翔:《中国嬉皮——中国文学中的“任诞”问题》《艺术广角》1991年第6期。
(17)《徐文长佚草》卷一,转引自叶长海:《中国戏剧学史稿》,第10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18)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册,第7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
(19)徐渭《歌代啸》,《徐渭集》第四册,第1233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20)章重:《梦遇》,《徐渭集》第四册,第1344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21)转引自骆玉明、贺圣遂:《徐文长评传》,第14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2)王思任:《徐文长先生佚稿序》,《徐渭集》第四册,第1350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23)章重:《梦遇》,《徐渭集》第四册,第1344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24)元结:《丐论》,《全唐文》第382卷。
(25)商维濬:《刻徐文长集原本述》,《徐渭集》第四册,第1347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26)徐渭:《四声猿》,《徐渭集》第四册,第1183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27)徐渭:《与萧先生》,《徐渭集》第四册,第1128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28)徐渭:《画菊二首》,《徐渭集》第二册,第396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29)王思任:《徐文长先生佚稿序》,《徐渭集》第四册,第1350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30)摘引自《艺谭》1984年第1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