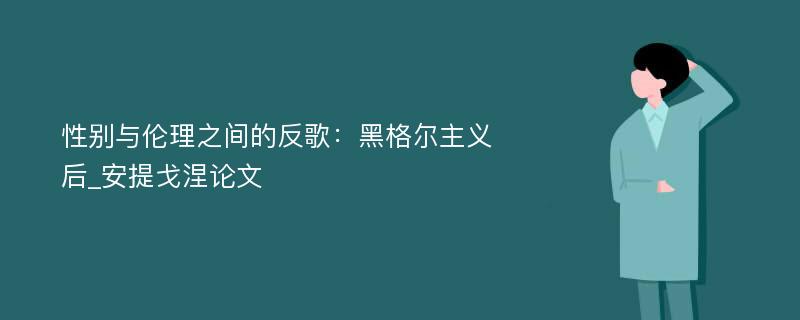
性别与伦理间的安提戈涅:黑格尔之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格尔论文,伦理论文,性别论文,安提戈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是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文化文本之一,而围绕这个文本的阐释则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批评的范围。在其解读史上,黑格尔、克尔凯郭尔、荷尔德林、德里达、拉康、伊利格瑞、朱迪斯·巴特勒等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都留下了他们的阐释轨迹。自1900年弗洛伊德在《释梦》中提出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结”后,《安提戈涅》作为俄狄浦斯研究的潜流却没能浮出地表(Steiner 18)①。但是,20世纪后半叶,《安提戈涅》在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分析学、法学和舞台艺术等领域的意义重构,成为西方重新认识自我、进行深度文化探寻的必经之旅。尤其近些年来,国外有关《安提戈涅》专题研讨会的召开,专刊、专著的发表②,以及大学里有关《安提戈涅》课程的开设,都将安提戈涅研究推向性别、伦理、法学、神学等跨学科批评的前沿。其中最为活跃和最具批判精神的当属性别伦理中的安提戈涅研究。 正如当代美国批判型知识分子朱迪斯·巴特勒在重读《安提戈涅》时指出:“如果将安提戈涅,而不是俄狄浦斯作为精神分析理论的出发点,那会怎样?”(Butler 57)如果说弗洛伊德创建的“俄狄浦斯情结”厘清了一条以“父亲”的名义建构的父权统治秩序的线索,那么,是否也可以认为性别伦理视域中的安提戈涅批评,也是在建构一种“安提戈涅情结”?本文试图围绕安提戈涅的批评史,讨论安提戈涅在性别伦理转向中的典范性和当下意义,藉此回答上述问题。 伦理与政治 黑格尔第一个甄别了安提戈涅的女性性别意蕴,把这个古希腊经典人物引入了性别伦理的批评视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安提戈涅的伦理意识进行了解读。就作为悲剧的《安提戈涅》而言,黑格尔认为冲突的两极是克瑞翁和安提戈涅。底比斯王俄狄浦斯得知自己弑父娶母,罪孽深重,因此去位,客死他乡。他身后留下二子二女。二子为争夺王位,对峙疆场。一子波吕涅克斯攻城,另一子厄特克勒斯守城,结果两人双双战死沙场。克瑞翁,俄狄浦斯王之母/妻的弟弟继位,为惩罚叛徒,警示臣民,下令不得埋葬波吕涅克斯。国王的禁令看似有理有据,但却违背了神律。神要求任何死者的尸体必须得到掩埋和祭祀,未被埋葬者,其灵魂是不洁净的,会得罪冥王哈德斯和诸天神。安提戈涅遵从神律、违反克瑞翁的禁令埋葬了哥哥。为此,克瑞翁依法将安提戈涅关进墓穴,让其慢慢死去。安提戈涅的未婚夫、克瑞翁之子海蒙殉情自杀,其母也为失去儿子而死,致使克瑞翁陷入极度痛苦之中。 在黑格尔看来,克瑞翁代表律法、城邦、公共秩序和政治理念;安提戈涅则代表神律、家庭、私人领域和家庭伦理。安提戈涅违令的实质在于她是遵从神律还是人律。在这个问题上,安提戈涅其实别无选择。索福克勒斯给安提戈涅设置了一个两难境遇,她要么遵从家族的责任埋葬家兄,要么屈从克瑞翁代表的政治律法,二者必选其一。如果违抗城邦的律法埋葬波吕涅克斯,她一定会死;如果她没能尽家族的义务使得家兄暴尸荒野,她一定使家族蒙羞,最终郁郁而终,甚至遭天谴。在黑格尔的法律或政治视域中,这是谁最终拥有话语权的问题。当波吕涅克斯攻打底比斯城的时候,当权者是厄特克勒斯。厄特克勒斯死后,克瑞翁给予他民族英雄的称号,举行了体面的葬礼,克瑞翁也因此继承了王位。而当波吕涅克斯死时,克瑞翁却禁止为他下葬,也因此违背了神律。神律和人律被置于生与死的两极,但在政治秩序中,拥有话语权的始终是人律:“人律,就其普遍的客观存在来说,是共同体(community),就其一般性活动来说,是男性,而就其现实的活动来说,是政府,人律之所以存在、运动和能保存下来,全是由于它本身消除或消融家庭守护神的分解肢解倾向。”(黑格尔34-35) 那么,安提戈涅的“别无选择”是否是自觉的选择?安提戈涅此行为的动机是伦理的还是政治的?为什么总是把政治放在意识一边,把伦理放在无意识一边?黑格尔的回答是,安提戈涅的选择不可能也不会是自觉的;这是由性别差异决定的。她的性别决定了她不具备伦理意识。性别差异是黑格尔认识的出发点:“一种性别给定一种规律,把另一性别给定另一种规律,是自然而不是环境上或抉择上的偶然,或者,两种伦理势力是自己分别在两种性别中择其一获得给定的存在而实现的。”(24)黑格尔在讨论《安提戈涅》之前,视女性是自然、神律的代名词;男性是文化、人律的化身。只有男性才有理性的“判断”和“言说”的能力;一个具有“伦理意识”的个体“知道他自己应该做什么”,并且已经做出了要么领受“神的规律”,要么遵循“人的规律”的决定(24)。而安提戈涅依照亲属关系的伦理原则埋葬了哥哥,她知道这是正确的,却不知道为何正确,甚至不具有行为主体的伦理意识。 伊利格瑞认为,黑格尔的先在的性别差异论决定了女性不能是伦理意识的主体,并将女性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然而,伊利格瑞认为安提戈涅作为家神的代表,正是通过进入公共领域——下葬亡兄——才成为伦理典范的。在她看来,安提戈涅的行为和反抗的意义,在于子宫和洞穴之间的联系:女人的子宫造就了男人,同时也把男人带进冢一样的坟墓。只有通过埋葬哥哥,通过这一卓越的政治行为,安提戈涅才能从女性的角度使家兄获得人性,并成就了自己的人性。也就是说,安提戈涅通过埋葬哥哥的行为,走进公共领域,表明了抵抗的立场,并因此走出了黑格尔建构的以克瑞翁为代表的城邦政治体系。虽然安提戈涅为此付出了死亡的代价,但她用女性身份守护了家族的名誉。正如美国哲学人类学批评家蒂娜·钱特所说:“安提戈涅把自己附属的地位转变为对现状的挑战,作为女性,她以死亡为代价捍卫并承担了家族义务”(Chanter 81)。 但是,安提戈涅既不是妻子也不是母亲。作为妹妹,她不具有通过丈夫和孩子获得“进入家庭义务的当下的普遍性”的可能(Irigaray 117),只能在和哥哥无欲望的关系中得到承认。在这个意义上,伊利格瑞的安提戈涅也没有逃出黑格尔“同一性中的他者”秩序。③伊利格瑞的安提戈涅迷失在十字路口:一面是以女性性征为标志的欲望,另一面是无法实现而又不能窒息的欲望,最终只能以死亡作为失败的无产出形式而结束。 伦理与差异 黑格尔对《安提戈涅》的阐释依赖二元对立的两极:家族血亲和国家政权。一方面,黑格尔的分析否认安提戈涅具有伦理意识——由于安提戈涅是女性,所以她不能获得进入政治领域的纯粹道德主体。另一方面,黑格尔认为,如果以血亲关系和家庭伦理划定和标注政治领地的话,那么,安提戈涅就因为没有承担女性(妻子和母亲)的功能而“从未进入这个领地”(qtd.in Butler 2)。但是,安提戈涅埋葬家兄的行为却表明她认可依血缘而定的伦理秩序,其家庭也因此成了具有伦理意识的共同体。况且,安提戈涅以死捍卫兄长尸首的完整和纯洁,履行了对兄长的伦理义务,也使她由于完全遵循神律而具有了神圣性。安提戈涅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清楚地认识到她自己的行为和克瑞翁的行为分别处于神和人设定的法律的两极。作为“自为存在”的个体,安提戈涅具有明确的死亡意识。当克瑞翁质问她:“你真敢违背法令吗?”安提戈涅回答说:“我敢,因为向我宣布这道法令的不是宙斯,那和下界神祇同住的正义之神也没有为凡人制定这样的法令;我不认为一个凡人下一道命令就能废除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不成文的律条,它的存在不限于今日和昨日,而是永久的,也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450-457行)④ 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社会,神律高于一切。安提戈涅的伦理行为遵从神律,为了家人,为了家族的荣誉,与人律抗争。她的行为虽然受限于家族事件,但“在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中,家庭占有真正重要的地位”。自然家庭的个人事件通过“真实和鲜活的生命”完成了对亲族血缘关系的认可(Chanter 96)。安提戈涅认识到了亲属义务,她把纯粹的家庭个体行为看作唯一能尽手足之情的伦理行为,走出了从家庭到国家,从个体到共同体,从个人到政治的性别分工。她固守个体行为正是由于她对这个行为的伦理性有了直觉认知。安提戈涅说:“做这件事,我根据什么原则这样说呢?丈夫死了,我可以再找一个,孩子丢了,我可以靠别的男人再生一个;但如今,我的父母都已埋葬在地下,再也不能有一个弟弟生出来。我就是根据这个原则向你致敬。”(905-913行) 家兄的无可替代性促使安提戈涅走出家庭,对抗代表国家的克瑞翁。这里,个体即是政治。安提戈涅用这一曲悲壮的女性“挽歌”对抗的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社会的文化传统。在被送进墓穴之前,她感叹说:“没有听过婚歌”,没有“上过新床”,没有享受过“养儿育女的快乐”。而观众从她“向死而在”的果敢的告白中更清楚地看到的是一个向暴政说“不”的政治人物。安提戈涅以死为代价,将属于家庭领域的个体事件转变成了公共事件,用性别来抵抗希腊社会的家庭分工,进而用血缘伦理意识消解了克瑞翁违反神律的政治原罪。 伊利格瑞重读黑格尔的安提戈涅,试图在父权制的象征系统中建构女性逻各斯中心的典范。她把安提戈涅从黑格尔的同一性秩序中剥离出来,演绎成对立的性别差异伦理,试图用母系传统替代父系秩序,致使安提戈涅扮演了这个位移的角色。但是,就这一点而言,伊利格瑞的安提戈涅也具有模糊性和矛盾性。一方面,安提戈涅占据了母系秩序中的位置,但是她对兄长的膜拜导致她把死置于生之上,结束了自己在母系秩序中占有位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她没有延续血脉,放弃了生而选择了与死者同逝。在这个意义上,伊利格瑞的安提戈涅也就没有逃出黑格尔的伦理秩序。 伦理与血亲 就家庭与伦理而言,安提戈涅能否算是普遍意义上理想亲属关系的典范?安提戈涅的死是否说明政治权力取得了对血亲伦理的胜利?美国批判型知识分子朱迪斯·巴特勒对《安提戈涅》的解读极具新意。她围绕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展开——安提戈涅在血缘关系中到底处于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引发了安提戈涅式的亲属关系危机。 巴特勒认为安提戈涅不能代表与国家对立的传统的家庭关系,因为她本身血亲混乱(安提戈涅的父亲也是他的哥哥)。正如安提戈涅自叹道的:“我母亲的婚姻所引起的灾难啊!我那不幸的母亲和她亲生的儿子的结合呀!我的父亲呀!我这不幸的人是什么样的父母所生的呀!我如今被人诅咒,还没有结婚就到他那里居住,哥哥呀,你的婚姻也不幸,你这一死害死了你还活着的妹妹”(858-872行)。巴特勒进而认为,正是由于在这个规范家庭的血脉关系中占据了一个破裂的位置,安提戈涅才能保持与中心对话。“尽管血缘关系复杂,但是她同时游离在规范之外。她的罪行因为她的血缘关系的混乱而变得模糊起来,她的存在是乱伦行为的后果,这个后果使得她的父亲也成了她的哥哥。在语言上,她占据了除母亲之外的每一个位置。但是‘占据’是以打破亲属关系和性别的连续性为代价的。”(Butler 72) 巴特勒提出了安提戈涅血缘关系不清的观点,以此质疑社会规范和文化理解力的合理性。她把安提戈涅看作是对传统家庭政治的挑战,认为亲属关系不仅仅是血缘问题,而且是认可的问题。亲属关系是社会结构中的一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是相对于自然的一个概念,归属于人类学和人种学范畴。在现代社会中,单亲家庭、同性恋家庭和双性恋家庭的重组凸显了亲属关系的不确定性。巴特勒认为是安提戈涅引发了这种亲属关系的危机。 安提戈涅所代表的非常态亲属关系不仅不符合黑格尔的伦理要求,也不符合拉康象征界中的亲属关系规范。对巴特勒来说,拉康划定的象征界是规范的代名词,任何试图越界的事物都将面临真实的或符号性的死亡——如同安提戈涅。安提戈涅因俄狄浦斯带给她的混乱的亲属关系,而不得不服从拉康的象征界的亲属关系规范。在文化的意义上,她实际上已经死去了。安提戈涅自认为她的死是与那些已故亲人的联姻:“坟墓啊,新房啊,那将永久关住我的石窟啊,我就要到那里去找我的亲人。”(896行)事实上,对血缘不清的亲属的爱,在文化上是行不通的,注定要面临死亡,并以此来结束象征界所不容的“偏离”现象。 在巴特勒看来,象征本身只不过是社会习俗的“沉积”。对她来说,语词或能指在空白的空间里建构起真实界,使之充满了规范和表演的力量。但安提戈涅声明要遵循神律,致使语词的超凡力量超越字面意思,指向了文化理解力的危机。安提戈涅拒绝与海蒙结婚生子的结局,而是像拥抱婚姻一样拥抱石窟,拥抱死亡。虽然她没有创建一种新的亲属关系模式,但她表明以功利性的生育为目的的婚姻模式不是建构亲属关系的唯一办法。她呼吁打破文化认同的界线,对规范的短暂“偏离”似乎预示了两性关系的开放。 对于黑格尔之后的安提戈涅,批评界聚焦于她的性别伦理意识。黑格尔暗示介于国家与家庭之间的安提戈涅不具备共同体的伦理意识,因此也没有公民身份。伊利格瑞拆解了黑格尔关于性别差异和伦理选择的定论,证明黑格尔的错误是把安提戈涅仅仅放在兄妹的关系之中。伊利格瑞的安提戈涅是被父权-暴君克瑞翁驱逐出民主进程的一个政治人物。巴特勒则从黑格尔和拉康那里甄别出安提戈涅的血缘不洁和象征界界线不清的盲点,用对文化规范的暂时“偏离”来批判正统规范的局限性和文化理解力的危机。 这些批评所表达的“安提戈涅情结”并不是要把安提戈涅变成像俄狄浦斯那样的文化典范,而是通过安提戈涅表明女性在文化规范外的边界上生存的事实。通过安提戈涅,伊利格瑞、钱特、巴特勒等女性知识分子对伦理规范提出质疑,经过周密的辩证思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在亲属关系的边界上文化理解力的局限性”(Butler 20)。实际上,伊利格瑞、蒂娜·钱特和巴特勒等人解读的并不是安提戈涅,而是她们自己。她们并不是要把安提戈涅树立为现代女性的榜样,而是要通过安提戈涅来承担现代女性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即通过对经典文学人物的解构“介入”当下政治,履行她们视为己任的批判使命。 注释: ①美国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考察1790-1840年间的《安提戈涅》批评史时谈到,在弗洛伊德之前,《安提戈涅》中兄妹间横向的血亲关系一直是批评界争论的焦点;1900年之后,弗洛伊德提出两代人父子间的血缘身份问题,安提戈涅因此被“俄狄浦斯情结”所代替。 ②2006年,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召开“质问安提戈涅”专题研讨会。这次研讨会就安提戈涅在古典艺术史中的姿态、再现、身体、表演、主体性等主题展开了有关安提戈涅的美学争论。2008年6月,Mosaic杂志专刊发表14篇《安提戈涅》最新研究论文,从哲学、性别理论、伦理学、政治学、比较文学、舞台艺术等多学科挖掘安提戈涅研究的生命力。其中朱迪斯·巴特勒的“安提戈涅的诉求:生与死之间的血缘关系”成为新世纪重读《安提戈涅》的一个导入口,生发了三篇有关安提戈涅的性别理论研究论著:其一,安提戈涅批评史研究成果《受难的悲剧:黑格尔、巴特勒与斯泰因(George Stein)论安提戈涅》;其二,比较文学研究成果《满目疮痍的巢穴:〈呼啸山庄〉与〈安提戈涅〉的身份危机》;其三,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成果《波伏瓦与〈安提戈涅〉:女性主义和政治伦理之间的冲突》。 ③朱迪斯·巴特勒认为伊利格瑞没有超越黑格尔的伦理价值批评框架,仍旧将妇女置于边界,在黑格尔的二元对立的伦理矩阵中,依然与男性对峙。 ④本文引用的作品汉译均出自《罗念生全集第二卷:埃斯库罗斯悲剧四种索福克勒斯悲剧四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293-342。以下凡引用出自该著的引文,只随文标注出处行数,不再一一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