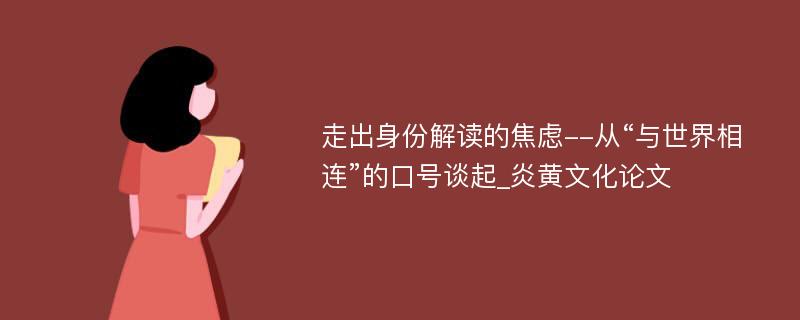
走出身份阐释的焦虑——从“与世界接轨”等口号说开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去论文,焦虑论文,口号论文,身份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铺天盖地的“与世界接轨”和“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等口号,实际上要么反映了当代中国对于西方的盲从,要么反映了部分国人忽略中国传统与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性的断裂。这些相互矛盾的口号,反映了中国文化身份阐释的焦虑。重新构建中国的文化身份,降解中国文化身份阐释的焦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谈到文化身份的建构,我们首先必须厘清以下几个问题:解构西方对于中国文化身份再现中的权力话语,了解其中的权力运作机制是必要的,但我们会不会在解构霸权的时候试图建构一个新的霸权?后殖民批评家们批判西方话语遮蔽东方文化身份表达的论述是否为中国自我文化身份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蓝本?后殖民语境下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自我文化身份?中国文化身份的建构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一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文化身份,是如何被西方建构并赋予其合法性的。西方对于中国形象的再现是在从18世纪初开始大量出现在西方的文学、文化文本中,后来在西方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西方汉学研究。具有戏剧性的是,西方文化文本中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一个由好转坏的过程。18世纪,中国文化的研究,曾经在法国形成一股热潮。法国人对于中国的丝绸、瓷器、园林艺术十分钟爱。在普通法国人甚至在法国宫廷贵族眼中,中国是一个富庶的国度,充满着各类奇珍异宝。同时,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如伏尔泰、蒙田,尤其推崇中国文化中的理性,认为中国是按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制度最严密的国家。然而到了19世纪中期,西方对于中国形象的再现,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中国人被描述成为狡猾、肮脏、不开化的一群软体动物。如英国的小说家笛福通过他小说的主人公罗宾逊的眼睛,这样再现中国:
“他们的建筑与欧洲的宫殿和皇室建筑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他们的城市和我们的城市相比,哪有那样富强,哪有那么鲜艳的服装、富丽的摆设和无穷的多样?他们的港口不过有几只破船和舢板,哪里比得上我们的商船队和我们强大的海军?我们伦敦城里做的生意,比他们整个帝国的贸易还要多,一艘有八十门炮的英国、法国或荷兰的军舰,便能战胜并且可以摧毁中国所有的战船……中国人……只是一群可鄙、下贱而无知的奴仆,屈服于只配统治这样一个民族的政府。”[1](P279)
伏尔泰、蒙田也好,小说家笛福也罢,他们都没有到过中国。他们对于中国的形象的再现,都是主观的臆想。这种建立在主观臆想基础上的再现,实际上是主体欲望的投射:西方特别是18世纪法国称赞中国的理性,目的也在于为法国的启蒙运动张扬理性找到依据;而小说家笛福,也不过在为大英帝国的全球殖民扩张寻找借口。从表面上看,这种东方落后、不开化对应于西方进步、文明的“善恶对立寓言”是一种话语关系,在话语背后,它体现出来的“西方与东方的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一种支配关系,一种不断变化的复杂的霸权关系”。[2](P38)把东方说成一个有别于“我们”(西方)的“他们”,需要“我们”去开化,而“他们”所能理解的方式只有武力和暴政,“他们”和“我们”不一样,是应该被统治的。
随着西方的全球殖民扩张,一门涵盖更大研究领域的东方学建立并发展起来,西方汉学从此被纳入到东方学的研究领域,并成为它的一个分支。所谓的东方学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美国家学术机构中的以教授东方、书写东方或研究东方人为目的的一门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学科。[2](P3)我们可以从东方学对于东方的文化身份的建构中找到我们所需要的理论资源吗?因为西方的学术不是号称建立在以理性、客观、独立、超然的人文主义原则的基础之上吗?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批评家们,为我们揭示了东方学隐藏在中立外衣下的权利运作机制。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福柯的话语理论为基础。德里达解构了传统的真理观,认为物与再现物之间并不相符,真理还是一种叙述,而叙述就意味着权力。福柯更是认为“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指涉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也不会有任何知识”。[3](P26)赛义德据此认为,东方学知识同福柯所考察的知识一样,它也不是对真实东方的客观反映,它也充斥着权力。不仅如此,权力在东方学中的表现比在其他知识领域中的表现更为明显。他说:“权力与知识的并存在近代语言学历史中远没有在东方学中那么突出。”[4](P343)东方学家、传教士、政客、旅行者们自以为他们对东方的研究反映了真实的东方,而实际上他们再现的东方形象充斥着西方的意识形态话语和权力话语,根本反映不了真实的东方,而只能是他们的想象,即东方主义,是对真实东方的歪曲。他说:“关于东方的知识,由于是从权力中产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创造了东方、东方人和东方人的世界。”[2](P40)因而东方主义不是东方的一部分,而是西方的一部分。
那么这种权力产生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有思想家认为正是西方特别是美国清教徒的上帝选民的观念和民族救世的空想使得他们认为,白人种族的优秀性注定了他们拯救世界的使命。正是这种拯救世界的崇高使命感使西方的民族主义将殖民世界变成了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殖民者把自己的民族想象得至高无上,而在疆界之外生活的其他民族,尤其是被殖民者则被想象成低下的、劣等的种族。“(上帝)选民的思想,对遥远过去共同种族记忆和对未来希望的强调,最后是民族救世的乌托邦思想……”。[5](P59)此外,对欧洲的殖民者来说,对于殖民地人民的残酷剥削和镇压使他们面临人格分裂,因为他们在本国所倡导的一直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所谓政治自由、民主、平等。为了赋予殖民暴力合法性,殖民主义者与所谓的东方学知识合谋,发展出一套白人职责的理论,打着知识的幌子,将东方民族建构为没有秩序甚至是不开化的野蛮人,没有能力、缺乏理性来管理好他们自己的国家,因而需要西方人的“帮助”。霍米·巴巴说:“殖民话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在他者化意识建构中‘定向性’(fixity)概念的依赖。定向性作为殖民话语中文化/历史/种族差异的符号,是表征的一种矛盾形态:它既表示混乱无序、堕落和恶性循环,又表示不变的秩序。同样地,作为推论的主要策略,其文化认同方式变成了刻板的模式,……在这种话语中,亚洲的表里不一和非洲的淫荡好像从来都不需要证明。”[6](P66)殖民者将他们扭曲的东方形象刻板化的核心动机是建构知识暴力,并将这种建构知识暴力的企图披上“东方学”这件看似中立的外衣,说白了,也还是为西方的扩张、侵略、殖民寻找学理上的合法性。所以,赛义德说:“东方学是西方用以控制、重构和支配东方的一种方式。”[2](P3)
有的中国学者认为中国没有经过完全殖民化,传统文化保存相对完整因而没有必要对西方保持警惕。他们不顾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大声呐喊与世界(实际上是西方)接轨。更有的人完全认同西方的东方学学者或汉学家们为中国所建构的文化身份,并无原则地去迎合他们对于东方的想象。如一位国内的知名导演,专门臆造一些中国的野趣去博得西方人的掌声,满足他们的意淫癖。西方对中国的“言说”、“书写”及“编造”的这套话语中所呈现的中国,只是他们眼中心中所认为的想象性的中国,而并不是,也绝不可能是真正的中国。想想美国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看看美国的《关于中国的人权报告》,不就是所谓的东方学与权力合谋的很好的例子吗?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7](P693)道出了其中的逻辑:在美国看来,不开化的中国无法管理好自己的事务,需要美国这样“公正”、“理性”的国家帮助中国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汉学话语既是由霸权生产出来的,又不断地生产出霸权,对中国进行渗透、控制和欺压。福柯说殖民话语就是这样一种与殖民统治相互为用的知识。殖民者拥有的权力使他们能够操纵话语,建立自己的文化霸权,而他们拥有的知识又反过来巩固了殖民者的权力,使这种权力进一步合法化。有些人无原则地认同西方的建构,鼓吹全面与西方接轨,不也正好中了西方的预谋吗?而另一部分人高喊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否会在无意间为西方的“中国威胁论”提供口实呢?
但是,我们主张抵制西方的话语霸权,并不是要全面拒绝西方文明,退守到我们的传统中自我陶醉。相反,我们主张以开放而审慎的态度,来学习西方。
二
西方的后殖民批评揭开了西方学术公正、客观的虚伪面纱,让我们能够洞悉西方学术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那么,后殖民理论家的学术活动有助于我们认识一个真正的东方并进而对中国的文化身份建构提供理论资源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真实的中国,当前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文化身份,这个问题我们留到后面去讨论。这里我们想声明一点的是,建构中国的文化身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去解决,发展我们本土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将话语权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让自己的头脑成为别人思想较力的战场。在这方面清华大学罗钢教授和王宁教授已经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并已经引起了西方后殖民批评界的注意。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批评家只能提供我们解构西方文化霸权的策略,却无法给我们提供建构自我身份的借鉴,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我们从后殖民批评家的个人身份来看,这些后殖民批评家都是具有双重身份的人,他们从东方到西方,从西方的边缘步入主流社会,拿着丰厚的薪酬,使用着西方的话语资源,使他们的批评难免不带上西方的权力话语,从而掉人与西方殖民话语同谋的陷阱,如霍来·巴巴和斯皮瓦克在自己的整个学术生涯中,始终受到那些充满精英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和资产阶级学术特权的责任的影响,尤其是受到新马克思主义和欧洲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此外,东方对于这些海外的游子来说,具有相当程度的外在性,民族身份的历史记忆已渐渐远去。因此有不少中国本土的学者认为,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所最关心的,并非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受西方文化遮蔽的问题,而是在进行一种后现代文化性质的文本层面上的重新建构、重新言说,并不强调具体所指,是整个后现代文化社会批判的一部分。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偏颇,忽略了这些后殖民批评家双重文化身份的另一面,但是后殖民批评理论对异域民族,尤其是第三世界的文化,确实具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解释权。同时他们的外在性使其不可能深入到东方国家的问题核心中去。此外他们对于东方文化被西方文化遮蔽的现实的揭露,有可能被西方学术界利用,从而制造新的一个让人怜悯的东方,从而为殖民者“帮助”东方提供新的合法性。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为跨国资本所追求的区域化、分离化,提供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与跨国资本主义的文化想象形成了某种共谋。
其次,这和他们的后殖民批评理论的渊源有很大关系,他们继承了后现代批评家对于传统真理观的批判意识——任何的真理都是一种书写,一种叙述,叙述的后面必然隐藏着权力的玄机。因此赛义德既反对西方人对真实东方的歪曲,同时也反对任何本质主义的客观真理。他指责东方学家歪曲了东方,但也否认自己能正确地认识真实的东方。他说:“我没有兴趣,更没有能力再现真实的东方和伊斯兰究竟是什么样子。”[2](P331)在他看来,一切认识都具有误解的性质。赛义德不相信语言陈述可以穷尽对象的全部外延和内涵——即知与物相符的真理,而只对知与物的关系感兴趣,即描述东方的话语的产生、变化和其背后的权力进行分析。后殖民批评家们所感兴趣的是话语如何遮蔽和扭曲了东方,而不是遮蔽什么。换句话说,后殖民批评传承了后解构主义、解构主义的衣钵,意在疯狂解构,而不着意建构。
最后,他们所依据理论的学院派性质,决定了他们的批评只可能是停留在话语层面而不是为前殖民地话语的建构提供实际甚至是理论上的帮助。从历史上看,后殖民主义批评所依赖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是具有强烈政治逃避主义色彩的学院性的话语。20世纪60年代西方轰轰烈烈的文化与社会革命失败之后,左翼知识分子纷纷回到学院书斋。当年的政治反叛青年,现在成了文化精英。因此,革命和改变社会的实践也就渐渐演变成了一种纯理论的话语活动,但是,这种话语革命是以遮蔽和忘却了政治经济问题为代价的。我们应该知道话语的背后是权力,那权力的背后无疑是经济。马克思很早就关注到商品拜物教和物化,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不公正和不平等的现象。在今天这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商品化的问题,更加突出,资本主义的全球市场化、商品化,已经全面渗透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到人类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当中。按理说,后殖民主义批评对这个问题应该更为敏感。因为当代社会商品化在文化领域里特别严重,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前殖民地国家。但可惜的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对此基本上是回避和保持沉默,把这么严重的问题转换成语言和心理意识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本末倒置。比如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的批判基本上停留在抽象的、纯理论的层面,很少涉及社会实际,对于母国印度今天的文化发展和未来,从不关心,更不用说关怀印度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了。
综合上述理由,我们认为,在中国自我文化身份的建构过程中,我们不可能从这些后殖民批评家的资源库中,找到建设性的理论话语资源,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他/她们的贡献。我们中华民族自我身份的建构,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解码西方资本主义编码在文化和艺术产品中的文化殖民主义的霸权,我想,他/她们理论的意义,便在于此吧。
三
自我文化身份建构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什么是真实的中国?自从中国被迫走进统一世界史的现代性历程之后,当我们询问文化的“真实”,问的是按照自身规律运转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的真实的中国呢,还是进入统一世界史后,被西方他者话语主宰的迷失了传统本真性的混杂体式的自我?这里涉及的基本理论是,文化的自我本质是静态的呢还是动态的。按静态自我立论,传统自我才是本质,才算自我,而进入现代性的自我,是自我的迷失,是受他者控制的自我,是非我。按动态自我立论,传统的自我是自我,进入现代性的自我,是自我的变化,自我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重释不可避免地造成对传统文化真实的遮蔽,因为现代性是在西方传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认为只有接受动态自我理论,中国的未来才有活力。历史上,中国文化一直都是开放变化的,中国的宗教和文化一直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并且,进入统一世界史之后,殖民扩张时期帝国主义文化在殖民地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同时也使殖民地文化在宗主国打上了自己的烙印。长期以来东西方之间的相互交流使两者之间的界线消失了,从而不再有纯粹的东方文化和纯粹的西方文化之分。东方文化已渗透到西方文化之中,西方文化也已渗透到东方文化的血脉里。福柯说:“一切文化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一种文化是独有的和纯粹的,所有文化都是杂交的、异质的、千差万别的和多元的。”[3](P25)主张杂糅理论的霍米·巴巴也论述说“民族文化的‘本土性’既非统一的也非仅与自身相关联,它也没有必要仅仅被视为与其外在或超越相关联的‘他者’”。[8](P4)既然当今这个世界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那么任何纯真的东西都是靠不住的,内在/外在之界限也绝不是泾渭分明的。倒是混融的和多种成分交融一体的东西也许正是新的变体可赖以产生的平台。
我们主张以开放的心态接受杂糅的新的文化身份,并不是提倡像某些人那样拿着奶奶的裹脚布叫嚷着去和世界接轨,也不是提倡像某些导演那样挂几个红灯笼去迎合西方人诱奸中国传统文化的色相。后殖民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意识形态编码在文化产品的糖衣中,但是在意识形态无以依托的器物层面我们可以大胆地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积极提升我们的国力,因为我们知道话语的背后是权力,而权力的背后呢?无疑是经济势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借用西方的先进技术,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综合国力上的差距,这就为平等对话搭好了一个平台,并使最终解构话语权的垄断成为了可能。对于可能蕴涵西方思想意识形态的东西如文化产品,保持一定的警惕,用意识形态的筛子进行过滤,把握话语的主导权;对于已经受到“西方话语暴力”控制或污染的,我们应该进行解码,进行文化反抗。那么,采用什么方式来消解西方话语霸权呢?赛义德认为,争夺话语权的方法很多,比如重写宗主国经典、重新命名山水、拥有文化和自我再现的权力等等。罗钢教授指出杰姆逊的《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以自己在欧美文学典范中形成的趣味来判断第三世界的文本,背后隐蔽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权力话语。这就是对于话语权的争夺。
但是我们许多人对权力存在太大的误解,这主要是不少学者在理解西方解构理论时仍然带着传统的二元对立的认识论,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他们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时又试图建构中国中心论,如盛行一时的“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口号。我们中国要争夺的是平等的说话、对话的权力,而不是话语中的霸权。凤凰卫视首席评论员阮次山先生在中山大学的花旗论坛上说中国应该进行大国民教育,使国民以开放、宽容的心态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去面对全球化的世界,只有这样中国未来的发展才有希望。这一观点我认为是务实且颇有建设性的。
我们在器物层面积极学习西方,在掌握话语主动的情况下引进西方的“体”,同时我们也应该积极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阐释。经过现代化阐释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嫁接,有可能产生既不同于西方,又有自我融入其中的现代化道路。东亚国家儒学的复兴,就是一个例证,根据韦伯的经典论述,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只与清教伦理有关,其它宗教,包括中国的儒道两家,与资本主义精神都是格格不入的。然而儒家文化圈经济崛起的事实却证明了儒家的伦理精神同样可以配合资本主义的成长,它能够有效地减轻资本主义竞争造成的社会功能紊乱,抑制个人欲望的过度膨胀,协调人际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他由此认为,“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显然是缺乏依据的臆测。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崛起就为我们中国的文化身份建构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蓝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