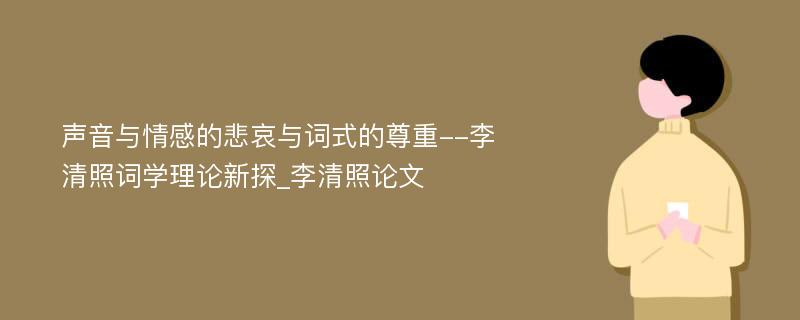
音情之悲与词体之尊——李清照《词论》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清照论文,词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9639(2007)03-0024-07
一、引言:《词论》渊源略辨
李清照《词论》的出现确实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不仅文献出处较为模糊,而且《词论》的名称也是后起的。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和魏庆之《诗人玉屑》在引用这篇文字前,只是冠以“李易安云”或“李易安评”,文字略有出入,后人盖缘其所论而题为《词论》。至于胡仔引用的文献来源,则已难确考。但在李清照时代,出现这样较为系统的论词文字则是毫不足怪的。
论词之风,随词创作的兴盛而兴盛,北宋中期特别是元祐以后,苏轼及其门下弟子都喜欢谈词论词,有的三言两语在口头流传,有的形成书信、题词或序跋等短文,如苏轼有《与鲜于子骏书》,晁补之(1053~1110)有《评本朝乐府》,李之仪(?~1117)有《跋吴思道小词》,黄庭坚有《小山词序》、《跋东坡乐府》,张耒有《东山词序》,陈师道有《书旧词后》。论词之人渐成规模。苏轼多感性言谈之论,而晁补之和李之仪的观点则较为系统。晁补之大体以“摘句品评”为基本模式,通过精选的词句来概括词人的创作风格。如言东坡词“横放杰出”、晏几道词“风调闲雅”、张先词“韵高”等等。这些评价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也几乎成为后来立论的重要基础。李之仪更具全局意识和文体观念,他立足词体、词人和词史,其《跋吴思道小词》,开宗明义,确定了词与其他文体之间的区别,所谓“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这篇跋最为突出的成绩是回顾了歌词从唐人发轫直至北宋中叶的大致发展历史,是最早的词史述略。在阐明词史从唐代的因诗而和声到晚唐的因声以填词演变过程中,以简明而精到的语言,钩勒词史的发展轨迹和其间主流词人的创作特色,如评柳永词“铺叙展衍,备足无余”,评张先“才不足而情有余”,评晏殊、欧阳修、宋祁等人词“风流闲雅,超出意表”,等等,都堪称要言不烦。李之仪追奉《花间》词风,并根据自身的创作体会,揭出“辅之以晏、欧阳、宋,而取舍于张、柳”的作词门径,要求卒章见妙,有“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的艺术神韵。李清照的《词论》从基本观念和写作思路来看,明显继承了李之仪的路径①,但她抽去了李之仪引以为评判标准的《花间集》,专力为词的体性定制,后出转精,分析更为细致,立论更为鲜明,理论内涵也更为突出。
二、词史意识与尊体观念
李清照从“乐府声诗”开端,以音乐性作为词的基本理念,追溯了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李八郎在曲江一曲惊听的故事,既展现了唐代乐曲昌盛的局面,又揭示了宋词繁盛的基石和渊源。由此而下,李清照回顾了唐末五代至北宋中叶以来歌词发展的历史,大致分为高峰—低潮—高峰3个时期,并对其间的一些重要词人如柳永、张先、晏殊、黄庭坚等作了点评。言简意赅,精彩到位。如评柳永有“变旧声作新声”的特长,但“词语尘下”;评张先等人虽“时有妙语”,但“破碎何足成家”,等等。特别是以音乐性为前提,分析了歌词的平仄、声韵、音律等文体性特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重要观念,对诗词体性的差异性和以诗为词的创作风气,从正体的角度提出了批评,所以简单来说,李清照此文是为词的尊体而作,反对当时词界的“破体”之风气。
《词论》展现了鲜明的历史意识。李清照把此前三百余年的词史分为3个突变时期: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和北宋是两个高峰,而介于其间的晚唐是一个低谷,五代虽有上升,但格局过小,未成气候。北宋词的繁盛已得到公认,不暇再论,而对于唐词的看法,则与后人之论颇异其趣。就词体而言,现在学术界的一般看法是词经过初盛唐时期的草作,中唐时期的过渡,至晚唐五代而臻于成熟②,而尤以温、韦、冯和南唐二主为其中翘楚。李清照倒置其序,或有其隐衷。对于北宋的“礼乐文武大备”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词坛盛况,李清照总体是肯定的。但因为有的不协音律,如晏殊、欧阳修、苏轼,如同“句读不萁之诗”;有的虽协音律,但或词语尘下,或结构破碎,在歌词的内容和形式上都存在缺陷,所以在肯定的基础上多予以批评。值得注意的是,李清照对于北宋词的重视,虽仍以音乐为考察重点,但对音乐和歌词的悲哀情感和凄美意识则不再关注,主要是从一般的体制来考察的。文体的丰富复杂及其各自拥有的独特体性,是需要历史来提供展示的舞台的。《词论》篇幅不长,措辞矜严,但其中包含的词史观念,稍加铺展,也宛然是一部近似莱辛论绘画和诗的界线的《拉奥孔》。李清照是有着深厚的历史观念的人,她不仅写过《乌江》、《咏史》、《浯溪中兴颂和张文潜》、《上枢密韩肖胄诗》等以咏史为内容的诗歌,也曾协助丈夫赵明诚编纂过《金石录》,在《金石录后序》中,李清照自云:“丞相在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这种对历史素材的近距离接触和由此衍生出来的对历史的浓厚兴趣,都为李清照历史观念的锻造准备了条件。传世的《哲宗皇帝实录》也可能是包含了李清照的笔墨和眼光的。
李清照梳理词史,从本质上说,并非要做一种文学史层面的学术研究,而是为她提出词需要尊体的观念蓄势。李清照“别是一家”说的提出充分体现了她强烈的尊体观念。之所以到了北宋后期,李清照强调对词体的规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随着词的发展,破体的现象也愈演愈烈。具体表现为:或不讲音律,或措语欠雅,或整体结构不统一。这些现象的产生除了词体的观念不够鲜明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以晏殊、欧阳修和苏轼为代表的词人用“以诗为词”的方式,王安石、曾巩用“以文为诗”的方式,试图来拓宽词的表现领域和表现方式,但其实将词的体制淹没在诗的体制当中了,所以李清照觉得要重提诗与词的体性的区别问题。由之前的李之仪从语言角度提出“长短句自有一种风格”到陈师道《后山诗话》说苏轼“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再到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可以看出,词的传统体制确实已面临着崩溃的危险,李之仪和李清照可以说是对此有所警觉并力主恢复词的本体的理论家。李清照梳理词史,并非做词史本体意义上的考察,而是通过对词史的描述来展示词体的正宗和词体遭致破坏的过程,所以在基本完成对北宋以前词史的描述后,接以“乃知别是一家”,乃由引言而归入正题。综合而言,李清照认为词的体制应该具有5个基本要求:1.情志纯正,力戒轻靡,偏重悲哀。2.语言典雅,反对尘俗,不求“奇”“妙”。3.结构浑成,自成名家,不以片言妙语影响全篇结构的完整。这是针对当时慢词需要铺叙的特点来说的,而当时不少人由于不太谙熟慢词的体制,而以小令作法写慢词,没有形成小令与慢词之间应有的体制差异。4.协音合律,五音、五声、六律、清浊轻重,皆须一一求合,一调押韵应予统一,特别是仄声韵,应押上声,如此细密要求,不惟求便歌,亦惟求可读。词史盛衰,端赖于此。5.合理修辞,此专就歌词而言,以增强词的文学性为目的。李清照认为北宋词非患在不修辞,而患在修辞失度和修辞手段的单一,缺少彼此衬合的均衡之美,从而造成歌词整体艺术风貌的缺憾。以上5点要求,并非并列关系,协音合律是词体基石,其余则是更进一步的要求。李清照关于词的体制的论述,不仅周密全面,而且具有明显的针对性。虽然对词体的变化似乎不能接受,但从南宋词的体制大体遵循李清照的词体要求来看,对宋词的发展,李清照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
李清照《词论》评论的16位词人,完全包括了晁补之在《评本朝乐章》评论的柳永、欧阳修、苏轼、黄庭坚、晏几道、张先、秦观7人,可见当时词学批评的热点所在。李清照以自成名家为目标,所以悬格甚高。她的著述视野既有创作者的理论自审,也有接受者的审美需求,更有研究者的条贯分析,其中更融入了女性的冷静细密和恢复词体本原之尊的使命意识,接续风流,其风可仰。
三、悲音悲情与词的审美内涵
目前关于李清照的研究论文,在对于李清照的词论与创作之间是否一致尚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夏承焘《评李清照的〈词论〉》一文说:“我们读她的《漱玉词》,常会怀疑她的创作并不能实践她自己的文学理论。如她的《凤凰台上忆吹箫》《一剪梅》《醉花阴》《壶中天慢》《永遇乐》诸名篇,并不都是很典重、尚故实、擅长于铺叙的作品。除《声声慢》之外,也不都是很讲究声律。我以为这篇词论如果作于南渡之前,到了南渡那时,由于流离民间,生活激变,使她的创作实践能够突破早年保守的理论,这正是她的作品应该肯定的地方,我们不应该责望她后期的创作和前期的理论必须一致。”夏承焘的这一段议论主要从典重、故实、铺叙、音律等方面揭示出李清照理论与创作之间不一致的地方,有其合理性。但如果对《词论》细加斟酌,我们也完全可以看到其理论与创作的一致性,如对于唐五代词史的论述就已透出其中端倪。《词论》开篇讲了李八郎③ 一曲惊宴的故事,貌似闲笔,实寓深意。其文曰:
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坐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
试推测其论,或对于词之演唱功能有特别强调,但在盛唐声诗的描述上,李清照主要强调其演唱特性和时人对音乐的迷恋,同时也包含对凄美音乐和内容的肯定方面。对于当时歌坛的领军人物曹元谦和念奴,诸进士的反应是“咨嗟称赏”,显然是属于对于歌唱技艺的称赏,而非音乐特性和歌词内容的深层感动。而李八郎转喉发声,一曲歌罢,却是“众皆泣下”。李八郎所歌究竟何曲,已不可确考,但李八郎所歌的悲音和悲情显然是感动诸进士的直接原因。其实这种悲音悲情正是唐代燕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胡夷之乐的主要特色所在。《通典》卷142描述龟兹乐的特征说:“自宣武已后,始爱胡声,泊于迁都,屈茨琵琶,五弦、箜篌、胡直、胡鼓、铜钹、打沙罗、胡舞,铿锵镗镗,洪心骇耳;抚筝新靡绝丽,歌音全似吟哭,听之者无不凄怆。琵琶及当路,琴瑟殆绝音。”洪心骇耳的震撼与“全似吟哭”的歌音,正是胡声的本色所在。李清照对唐代开元、天宝时期音乐的怀恋,正包含了对燕乐本色的崇尚之意。李清照为了突出悲音悲情的特殊魅力,不惜使用曲笔,做了不少的语言铺垫,先写李八郎表兄对李八郎的低调介绍,接着写诸进士的“众皆不顾”、“众皆哂”、“或有怒者”。先写曹元谦、念奴歌唱的高超歌艺④,再写李八郎的悲音动人。一前一后,对应写来,正是曲写其对悲音悲情的特殊共鸣⑤。而批评晚唐,则将立论基点转移到“郑卫之声”方面,是音乐同非其评定词史地位的惟一依据,当包含对音乐的特性本身的区别和歌词的内容变化方面。“郑卫之声”和“流靡之变”的音乐特征恰恰是以言情绮靡为特征的,是典型的用身体写作,与悲音悲情适成反比,内容上的风花雪月和浮泛的相思离别成为主流,所以李清照用“斯文道熄”来表示自己的否定。实际上晚唐五代的词何尝“道熄”呢?但在追欢逐乐的氛围中,悲音悲情之“道”确实是“熄”了⑥,李清照用“斯文道熄”来概括这一段词史,可见其心中强烈的感情意识。李清照列举的《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牌,音乐虽已失传,但就现存的歌词来看,确实偏于轻靡,而且这一时期词人品行的狎邪也异常受人关注,温庭筠和韦庄等就备受时人非议。五代李氏君臣的“尚文雅”和“哀以思”的作风,李清照应该是认同的⑦,而且“亡国之音哀以思”正是宋代及此后对李煜词的一个基本评价,如黄升《花庵词选》对李煜《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评曰:“此词最凄婉,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陈鹄《耆旧续闻》卷3也曾经引苏辙评李煜《临江仙》(樱桃落尽春归去)词云:“凄凉怨慕,真亡国之音也。”所谓“亡国之音”,其实就是指一种悲怆伤感的音乐和歌词特征,《旧唐书·音乐志》记御史大夫杜淹语云:“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也。”而李清照套用“亡国之音”来评论五代之词,在对悲怨音情的强调上,与她对盛唐乐府声诗的强调是一致的。但或许是限于创作规模而未能形成词史高峰。总体来说,李清照对于唐五代词的发展不仅注重音律,而且注重音乐和歌词中悲哀情感的抒发和凄美意识的张扬。在《词论》中被列为“知”词“别是一家”的人当中,晏几道被第一个提及,而且李清照感到不足的仅是他铺叙的手法运用而已,可以说是被否定最轻的一个词人了,追溯其思,当也有对晏几道词悲苦情感的认同在内。晏几道《小山词自序》述及为高平公缀辑成编,“考其篇中所记悲欢离合之事,如幻如电,如昨夜前尘,但能掩卷悟然,感光阴之易迁,叹境缘之无实也”。则晏几道平生的沉沦下僚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词的“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1](P51),当也是被李清照引以为能明了词的悲情体制的重要原因。秦观也被列为少数深明词体特征的词人,李清照揭示其“专主情致”的特色,而所谓情致,即“诣往既深,趋向又远且有姿态的一种感情”[2](P17)。在宋代词论中,以“情致”论词并不鲜见,这种“情致”虽然在理论上可以有悲苦与欢愉的分途,但如晚唐“温、李之徒,率然抒一时情致,流为淫艳猥亵不可闻之语”,亦即李清照《词论》中被称为“郑卫之声”和“流靡之变”的晚唐词坛,其情致的欢愉内涵显然是被否定的。但秦观词的情致属于被肯定的范围⑧,秦观词在当世就以“愁如海”被叹为新奇[3](P315),后世更将秦观与晏几道并称为“真古之伤心人”[4](P)。王国维《人间词话》也说:“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为凄厉矣。”其词的悲苦凄婉基调,乃是得到公认的。李清照明确提出情致而暗中带出词的悲苦内涵,其中包含着以此尊体的目的。而李清照自己的词,也是以悲愁为主导情感的,她的词没有承袭《花间词》的镂玉雕琼、裁花接叶,而是大体承传了南唐特别是李煜词的哀婉低转[5](P160~171),她的“人比黄花瘦”、“载不动、许多愁”、“泪向愁中尽”、“柔肠一寸愁千缕”、“凄凄惨惨戚戚”、“怎一个愁字了得”、“又摧下千行泪”等等,以及充塞在《漱玉词》中“残”的意象的反复展现,无一不传递着她的深深哀愁和寂寞心态。对于她的《金石录后序》,洪迈《容斋四笔》也云:“予读其文而悲之。”吴衡照《莲子居词话》评易安《武陵春》“悲深婉笃”,南宋刘辰翁尝云:“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刘辰翁对易安词的赞赏与《词论》中记载的诸位进士对李八郎的赞赏如出一辙。刘麟生在其《中国文学史》中称赞李清照:“她的长处,在以白话的字句,充分表现其哀怨的情感。”[6](P309)即以“哀怨”作为易安词的情感主流,也可见出李清照理论与创作的一致性。
四、批评理念和批评方式的新变
李清照之前的词学批评大都以摘句的方式来作语言层面的肯定。其著作方式比较涣散,大体是针对具体篇章的个别批评。如潘阆《逍遥词附记》提及其《酒泉子》11首,苏轼《跋黔安居士渔父词》系专就黄庭坚《诉衷情》《浣溪沙》《菩萨蛮》三首题作“渔父”的词而言的,苏轼的《与鲜于子骏书》也是针对自己“作得一阕”之《江城子》立论的。但从晁补之《评本朝乐章》开始,摘句就成为一种主流的词学批评方式,如评柳永,摘其“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之句;评欧阳修,摘其“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之句;评晏几道,摘其“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之句;评秦观,摘其“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之句。相应的批评也主要集中在语言的层面。陈师道《后山诗话》中的词评也大体如此。李之仪的《跋吴思道小词》除了批评柳永“韵终不胜”和张先“才不足而情有余”外,大体是一种正面词史的梳理,否定的色彩并不浓烈。这种或针对具体篇章、或摘句以做语言层面的考量的方式,到了李之仪虽渗透了一层历史的观念,但立足于遣词用语依旧是一个重要的逻辑前提,否定也是立足在肯定的基础上的。而到了李清照的笔下,单纯语言层面的考量不见了,摘句的方式被冷落一旁,正面的立论也被弃之不用,肯定也是建立在否定的基础上的,反面的批评勃然而兴。这种批评方式和批评基点的转变隐含了李清照特殊的思维方式和批评理念的转变。
词在发展过程中,一直以男性词人担当着主角,并最终形成了“男子而作闺音”的创作传统。但性别的差异终究是难以完全克服的,甚至隔膜巨大。既然是作为一种女性化的文体,从学理上来说,当然女性最有发言权。但唐宋词在事实上,只有一种男性的声音在主导着词的发展方向。李清照强烈的女性意识和强烈的尊体观念,决定了她的批评只能是以否定为基本方式,除了盛唐声诗未加指责外,此后从晚唐起,批评的声音便一直是她的主流。有的是整体否定,如晚唐的“郑卫之声”和“流靡之变”,大多数则是个别或组别的批评。个别批评如柳永的“词语尘下”,晏几道“苦无铺叙”,贺铸“苦少典重”,秦观“少故实”,黄庭坚“尚故实而多疵病”,等等,皆是其例;组别批评如张先、宋祁兄弟、沈唐、元绛、晁端礼等六人一组的“破碎何足名家”,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三人一组的“不协音律”,王安石、曾巩二人一组的“不可读”。仅有的一些肯定,也是在简单评说后,迅即转入批评的话题。如评论柳永“协音律”,但话题随即转入对其词语的批评;评论张先等六人“时时有妙语”,随之转入对结构破碎的批评;评论晏殊等三人只是“学际天人”,而无关乎词,接下更直言其“不协音律”;评论王安石等二人“文章似西汉”,也无关与词,但对其词的“不可读”则直言其非;对于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虽肯定其能明辨词的体制⑨,但又在修辞等多方面存在不足。这种批评的模式充分体现了李清照补偏纠弊的写作初衷,盖矫枉容或过正,所以李清照不论其是否为朝中大臣、词坛名家或父执长辈,一律出语犀利,不留情面,其胆识固足称雄,而其力挽颓势、重整词体的使命意识尤足令人尊敬。
在《词论》中,李清照明确表达对“奇语”、“妙语”和“尘下之语”的否定,她认为抽掉全文的这种摘句批评不足以论定词人,如江南李氏君臣的“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等句的“奇语”,张先等人的“时时有妙语”,都不足成为称赏的理由,至于柳永的“词语尘下”自然更在否定之列。词语尘俗和词语虽佳但有句无篇,都不符合李清照的审美要求,所以在《词论》中,李清照不取传统文学批评“摘句”的批评模式,而注重在清理词史的过程中来论定词人。其从全篇、全人和词史角度对词人的评论,自然要更具理论的涵盖力。
饶有意味的是,李清照力反摘句的批评方式,但后人对李清照的批评无论是肯定和否定,往往仍是采用摘句的方式。此与易安初衷,想来是悖反的。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60有云:“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小词云:‘昨夜雨疏风骤……应是绿肥红瘦。’此语甚奇。又《九日》词云:‘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此语亦妇人所难到也。”张端义《贵耳集》亦云:“易安居士李氏……南渡以来,常怀京洛旧事,晚年赋元宵《永遇乐》词云:‘落日镕金,暮云合璧’,已自工致。至于‘染柳烟轻,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气象更好。后叠云:‘于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皆以寻常语度入音律。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调则难。且秋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此乃公孙大娘舞剑手。本朝非无能词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叠字者,用《文选》诸赋格。后叠又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又使叠字,俱无斧凿痕。更有一奇字云:‘守定窗儿,独自怎生得黑’,‘黑’字不许第二人押。妇人中有此文笔,殆间气也。”罗大经《鹤林玉露》也评论起头连叠七字,堪称“创意出奇”。黄升《花庵词选》评易安《念奴娇》“宠柳娇花”之语为“甚奇俊”,等等。易安传播众口的正是这些高度凝练而意象鲜明的词语。而批评易安的人也往往从词语一端切入,如许昂霄《词综偶评》:“李清照《壶中天慢》词,造语固为奇俊,然未免有句无章。”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称易安“铸语则多生造”,并批评张端义和黄升对《声声慢》中叠字和“宠柳娇花”的欣赏是见识浅陋,堪称魔障,并由此而认为“宋人论词,且多左道”,造语纵或奇俊,而无关于词境之深浅。其立足全篇词境的批评理念⑩ 或许与李清照心有戚戚。
五、余论:女性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困境
中庸的言论,能赢得一片唯唯诺诺,但其实空虚;率真的批评易导致诸多反对,但厥功可期。正因为李清照的女性身份和批评锋芒,也招致了后来无端的指责。正如沈曾植《菌阁琐谈》所云:“才锋太露,被谤殆亦因此。”南宋胡仔在引录了李清照《词论》后以“苕溪渔隐”的名义加了一段“案语”,并带着讽刺的语调说:“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之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发也。”“未公”处到底在哪?未见一字分析,倒是充斥在字里行间的诋毁漫骂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扭曲的批评心态。无独有偶,清人裴畅也说:“易安自恃其才,藐视一切,语本不足存。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7](P1872)女性在文学和文学批评圈中的艰难,真是可观可感,然而备受非议的李清照其价值也就更为突出了。
回顾整个宋代对李清照的接受过程,北宋时期,仅三两种文献涉及李清照或以“赵明诚妻”或以“李格非女”相称,而其语言所及,往往是一二诗句。赵明诚作金石序跋多种,也从未论及李清照之诗词成就。南宋的批评也是肯定与否定间出,肯定多在其诗或个别词作、词句。王灼似乎肯定李清照的“诗名”,推许为本朝妇人“文采第一”,但又在人品上对李清照做了更大程度的否定,所谓“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则其视界所及,仍在否定方面。朱彧应该说是最早对李清照进行全面肯定的人了,他既认为李清照的“诗之典赡,无愧于古之作者”,又认为其“词尤婉丽,往往出人意表,近未见其比”,但这一段评论在明抄本和影抄本《萍洲可谈》中均无记载,则其所论之影响,也当相当有限。其余如胡仔、朱弁、洪迈、晁公武、朱熹、张端义等,或以为其人“无检操”,或评其四六文、诗歌等,唯独吝于评词。可见宋人对于女性词人接受之艰难[8](P1~25)。从熟视无睹到王顾左右,从专论其诗到旁及其词,李清照的词和词论一直隐退在主流文学和文学批评之外,反而与文学无关的再婚等事,为宋人笔记津津乐道,资以为口实之快。胆识兼具、文采焕发的李清照恐怕真的要浩叹“音实难知,知实难逢”了。然而在口实与是非中锤炼出来的李清照,其文学的光彩和文学批评的光彩,也就更让人肃然起敬了。
注释:
①陈祖美认为可能受晁补之的影响也许更为直接。李清照在屏居青州期间,晁补之当时也在今山东境内的缗城守母丧,有可能李清照曾向晁补之请益,或睹其《评本朝乐章》,并踵此而作《词论》。此为猜测之词,略备参考。参见《李清照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也在“李清照”条目下说:“(李清照)善属文,于诗尤工。晁无咎多对士大夫称之。如‘诗情如夜鹊,三绕未能安’,‘少陵也自可怜人,更待来年试春草’之句,颇脍炙人口。”,但此是针对李清照的诗歌来说的,并未及词。
②如陆游《跋后山居士长短句》云:“唐末诗益卑而乐府词高古工妙,庶几汉魏。”参见施蛰存《词籍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页。
③此故事并非小说家言,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云:“李衮善歌,初于江外,而名动京师。崔昭入朝,密载而至,乃邀宾客,请第一部乐,及京邑之名倡,以为盛会,绐言表弟,请登末坐,令衮弊衣以出,合坐嗤笑。顷命酒,昭曰:‘欲请表弟歌。’坐中又笑。及啭喉一发,乐人皆大惊曰:‘此必李八郎也。’遂罗拜阶下。”宋李昉《太平广记》卷第240“乐二”中,也有类似记载,与李清照文中所述略异。
④按,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和宋李昉《太平广记》卷第240“乐二”记载李八郎演唱,并无先有曹元谦和念奴歌唱一事,李清照或另有所闻,或故意为之。
⑤蒋哲伦、傅蓉蓉认为:《词论》开篇所述故事,为很多人忽略,或只是认为强调词的音乐背景。他们认为李清照并列曹元谦、念奴和李八郎歌唱之事,“似在为词澄清以女声演唱和声情柔靡为本色的流行观念”。然这种观点与《词论》接着来论述晚唐五代的词“郑卫之声日炽,流糜之变日烦”的批评态度似存在矛盾。蒋、傅所论,参见其所著《中国诗学史·词学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70~71页。
⑥陆游评论《花间集》云:“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
⑦顾易生《关于李清照〈词论〉的几点思考》亦云:“李清照对南唐二主及冯延巳词的评价极高……至谓之‘亡国之音哀以思’,其辞若有所憾,其实则深许之。”参见《顾易生文史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1页。
⑧陈祖美《评李清照〈词论〉对秦观词的批评》一文根据丁丙《善本书室藏书记》卷四十所云“(秦观词)多出一时之兴,不自甚惜,故散落者多。其风怀绮丽者,流播人口,独见传录,盖亦泰山毫芒耳”,而认为“秦现有好多词李清照没能读到”,这一判断下得略嫌草率。而陈祖美更由此认为李清照评论秦观词“专主情致”是批评秦观“专写男欢女爱、恋妓宿娼”,则两重前提皆缺乏必然性,立论更值得怀疑。依笔者管见,李清照总体上是肯定秦观的“专主情致”的,此从李清照评论秦观这一语段的逻辑性可以得出。如果秦观词的“情致”真的与风怀、风情相近,则与晚唐词的“郑卫之声”“流靡之变”就很类似了,如此李清照绝无肯定秦观“情致”的可能了。陈文载《词学》第15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6页。
⑨魏庆之《诗人玉屑》卷21云:“《苕溪渔隐》曰:‘无己称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耳,唐诸人不逮也。’无咎称鲁直词,不是当家语,自是着腔子唱好诗。二公在当时品题不同如此,自今视之,鲁直词亦有佳者,第无多耳。少游词虽婉美,然格力失之弱,二公之言,殊过誉也。’”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也云:“黄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家语,自是着腔子唱好诗。”可见对于黄庭坚是否尊体,在当时还有不同的意见,李清照与陈师道的观点较为接近。
⑩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2批评宋代陈造以“不经人道语”评竹屋、梅溪词云:“作词只论是非,何论人道与不道?若不观全体,不究本原,徒取一二聪明新巧语,遂叹为少游、美成所不能及,是亦妄人也已矣。”
标签:李清照论文; 宋朝论文; 词论论文; 读书论文; 宋代历史人物论文; 浣溪沙论文; 声声慢论文; 菩萨蛮论文; 苏轼论文; 永遇乐论文; 李之仪论文;
